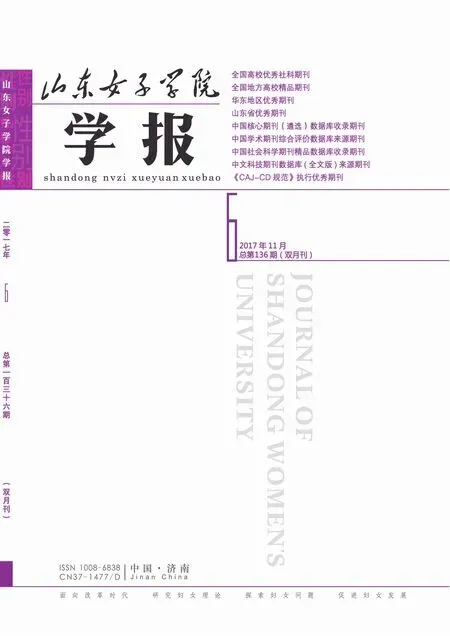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的男權文化闡釋
——兼及對女權主義的啟示
施文斐
(陜西師范大學,陜西 西安 710000)
·性別平等理論研究·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的男權文化闡釋
——兼及對女權主義的啟示
施文斐
(陜西師范大學,陜西 西安 710000)
從意識形態(陽具崇拜)到思維邏輯(從生殖力的父性歸屬推導出性別權力的男性歸屬),再到男權制的兩大保障機制(“亂倫禁忌”與“族外通婚”),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可以說內置了一整套完整的男權文化系統。男權立場的預設使得古老的男權文化在生理解剖學—臨床心理學的科學外衣下獲得了現代意義上的復活,同時又由其必然導致的反女權主義傾向不可避免地使得弗洛伊德學說成為女權運動第二次浪潮的矛頭所指。但論證思路的錯誤并不能詆毀科學研究本身的認識價值,弗洛伊德的許多富于創建性、革命性的臨床發現對于女權主義自身的理論反思乃至于今后的理論發展走向同樣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辯證的科學態度將有助于對弗洛伊德學說的重新審視與重新發現。
陽具妒羨說;性別權力;閹割情結;亂倫禁忌;社會性別;男權制社會;社會建構
20世紀六七十年代女權運動的第二波浪潮對探討婦女從屬地位的制度性根源——“男權制”表現出了極大的理論熱情。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奧秘》(1963)、凱特·米利特的《性的政治》(1970)、蓋爾·魯賓的《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經濟學”初探》(1975)等皆為這一時期重要的理論成果。在這些女權主義的代表性著作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質疑與批判,其中,又尤以凱特·米利特的批駁最為系統、抨擊最為猛烈、措詞最為嚴厲。米利特認為弗洛伊德“作為個人,他無疑是最強大的反動分子”[1](P272),他的精神分析學說是“毫不含糊的主觀和臆斷”[1](P279)的“科學黑話”[1](P312),充斥著大量的“男性偏見”[1](P279)和“厭女情緒的推斷”[1](P279),“他有關婦女的說法中也不時夾雜有對女權主義觀點的刺耳的言詞”[1](P288),“反女權主義的本性”“千真萬確地體現在弗洛伊德本人的著作中”[1](P272)。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是否真的如女權主義者批判的那樣具有反女權主義傾向?他的理論闡釋究竟內含了怎樣的性別立場?其學說是否根本反動而對女權主義運動全無一點借鑒與啟示?將弗洛伊德學說置放于男權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重新審視,將有助于我們探究到其中一些重要觀點形成的原始根源與古老邏輯,明確其學說在整個男權文化中扮演的角色與發揮的作用。同時也有助于我們在將男權意識的解讀與真正的科學論斷加以充分剝離的基礎上,辯證地看待弗洛伊德學說中一些富有創建性、革命性的真知灼見,從而為女權主義自身的理論反思乃至今后的理論發展走向提供一些重要的參考。
一、關于“陽具妒羨說”:“勢”與菲勒斯中心主義
“陽具妒羨說”是弗洛伊德女性人格心理學的理論基礎,弗洛伊德對“陽具妒羨說”在解讀女性人格心理發展時發揮的作用極為自信,“如果你們將我關于缺少陰莖的事實在女性人格的形成中發揮了作用的信仰視為成見的話,我自然無話可說了”[1](P275)。的確,在弗洛伊德版的女性人格心理學中,被動的女性屬性、異性戀的性取向、對生育母職的體認等皆可從“陽具妒羨說”中尋找到原初的心理動機,這一心理動機的產生又無疑根源于“陽具缺失”這一生物學“事實”。盡管弗洛伊德有時也會提及社會因素的影響,但終究還是認為,“在心理研究的領域內,生物的因素確確實實是根本”[1](P289),他的女性心理分析也因此倒向了生物決定論,而且還是菲勒斯(陽具)中心主義的生物決定論,這就決定了他的女性人格心理學必然是否定論調的:由于陽具的缺失,堅信自己遭到了閹割的小女孩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性別自卑,喪失了曾經的“雄心”而轉向被動與自虐;同樣還是由于陽具的缺失,深感性別低劣的她終其一生都無法放棄對陽具的熱切追求,無論結婚生子,還是成就事業,其一切行為都根源于“陽具渴望”這一深層心理動機。尤其對于那些女權主義者而言,她們未能適時地將對陽具的渴望轉化為對生育與男人的渴望,拒絕接受自己的社會性別身份而妄想像男人那樣在事業上有所作為,在弗洛伊德看來,這種“將一項耗費智力的職業堅持下去的毅力”不過是“獲得男性屬性的企圖在無意識中持續下去”,是渴望獲得陽具“這一被壓抑的希望的變體”[1](P301)。這些因成長受挫而未能進入預定軌道的女性顯然需要作為神經疾病患者接受治療,治療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讓她們認清現實、接受定位,從企圖變成男人的病態幻想中回歸到為社會性別規范所認可的母職與妻性上。顯然,弗洛伊德的女性人格心理學里隱含著對女權主義者的強烈否定,依據這一學說,女權主義者無異于患上了陽具妒羨癥的精神疾病患者,都是一些需要接受精神治療的“男性變態”[1](P285)。可想而知,這一不亞于人身攻擊的“科學”論斷會在女權主義者當中激起怎樣的軒然大波。米利特即認為:“在性的反動時期,在削弱和摧毀女權主義起義的企圖中,除了挖苦和愚弄,還沒有一種武器比弗洛伊德的陰莖妒嫉說更具威力。”[1](P291)
但這一令女權主義者憤恨不已的“陽具妒羨說”其實也不完全是弗洛伊德的閉門獨造,而是清晰地刻印著陽具崇拜意識的原始痕跡。據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中提供的材料可知,原始人普遍認為女性外生殖器的“現狀”是由于遭遇了鳥或蛇的襲擊而導致的外傷所致。由于遭到了這一形同閹割的損傷,所以她們的“傷口”處經常流血不止,而流血,亦即月經則被視為上天對女人的懲罰,至今在英文俚語中,月經還被稱為“the curse”(天罰),來月經被稱為“to have the curse”(遭到了天罰)。原始信仰中以男性器官為標準反觀女性,將女性月經以及導致月經的所謂“被閹割”視為懲罰之類的觀念在弗洛伊德的“陽具妒羨說”中均有印證。弗洛伊德關于兩性器官優劣對比的許多表述,如“男孩遠為優越的裝備”“遠為優越的對應物”“她低劣的陰蒂”“生殖器的缺陷”“固有的性低劣”[1](P275)等也同樣是通過貶損女性器官以凸顯陽具優越的陽具崇拜意識的體現。弗洛伊德的“陽具妒羨說”使得陽具崇拜這一古老的意識形態在臨床心理學的科學外衣下得到了現代意義上的復活。
作為一種古老的意識形態,潛藏在弗洛伊德學說中的陽具崇拜意識決定了并不能對其學說中大量出現的“陽具”字眼僅作字面上的理解。法國精神分析學派的代表人物拉康指出,弗洛伊德的學說是“有關信息而不是有關器官的理論”[2](P50),所謂“陽具缺失”的生物學事實顯然并不是什么“事實”,“因為那事實(女人的性器官)是完整的,并不‘缺乏’任何東西”,那種所謂的“被閹割感”“從來不是真實的而是象征的”[2](P53),“弗洛伊德決不是想談論有關生理構造方面的問題,弗洛伊德理論實際上是關于強加在生理結構上的語言和文化意義。”[1](P50)為了更好地突出陽具的象征意義,拉康用“勢” “陽具”對男性生殖器官的象征性與物質性作了區分。女權主義者魯賓接受了拉康的觀點,并從“勢”的象征意義出發對結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描述的親屬關系結構作了重新解讀,指出女人之所以不能成為婚姻契約的簽約方,而只能作為“禮物”被動地在兩群男人之間流通,其原因就在于生理性別上的女性并不具備也不可能具備陽具所象征的天然性別權力(“勢”)。在由婚姻契約結成的男人社會關系網絡中,永遠都是“女人朝一個方向走,‘勢’朝另一個方向”,“‘勢’和女人永遠不在同一處出現”[1](P54)。
將一性之于另一性的性別權力賦予只為男性所獨有的器官,事實上也就等于認可了男性對性別權力的獨占與壟斷。據《圣經·舊約·創世紀》(17:9—17:14)記載,耶和華在與亞伯拉罕立約時需要一個特殊的男性符號作為立約的證據,這一男性符號被最終選定為“受割禮”。耶和華表示:“你們都要受割禮,這是我與你們立約的證據。”(《圣經·舊約·創世紀》17:11)[3](P28)“我的約就立在你們肉體上,作永遠的約。”(《圣經·舊約·創世紀》17:13)[3](P28)作為立約的標記,割禮象征著“已成為立約群體一員的標志”,是對“選民意識”的一種“提醒”[1](P28)。格爾達·勒納對此提出了質疑,認為如果必須要用身體上的標記把上帝的選民區分開來的話,那么,為什么就非要用這種標記呢?然而,也恰恰就是這一“標記”才能“確保”女人無法參與立約,從而保障了簽約的權力以及由契約生成的各項權益只能為男人所獨享。從這一意義而言,“勢”是“男人權力的符號性再現”[4](P140),是“傳播男性統治的一種表述”[1](P54),男性統治正是建立在“勢”的隱喻意味上的“陽具統治”。從這一層面來看,弗洛伊德學說中的反女權主義傾向也只不過是問題的表面,因為菲勒斯中心主義所秉持的二元對立思維必然會導致一性對另一性的壓制,男性的性別優勢唯有在對女性性別的貶損中才能獲得體現,對女性器官的貶低、厭女情緒、反女權色彩不過是其中的應有之義。
二、關于“力比多”:生殖力與性別權力的歸屬問題
男權立場的預設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弗洛伊德的臨床分析。盡管由臨床觀察與實驗獲得的原始材料無疑具有相當的科學價值,但先入為主的男權立場卻阻礙了這些數據獲得真正意義上的科學解讀。譬如“力比多”的屬性問題。盡管弗洛伊德承認力比多為兩性所共有,但還是堅持認為力比多是男性屬性的。無論它體現在男人身上還是女人身上,也無論它指向男人還是女人,力比多都只是“一種有規律的、合法的男性屬性”[1](P295),“在男性和女性身上的表現形式都是一樣的,都是男性的。”[5](P94)為什么一定要將這種生存必備能力,或者說“物種能力”“生活力量”看作是“男子氣”[4](P126)的呢?這一令人困惑的論斷只能從男權立場上才能獲得合理的解釋。簡而言之,力比多之所以必須被賦予男性屬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保障生殖力能為男人所絕對壟斷,這一點對于男權乃至男權制的確立與維護都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依據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論,豐沛的力比多使得男性擁有更為強大的性能量、性能力,他們更關心子嗣的繁衍,對生育活動也負有更大的責任,而力比多微弱的女性則只是充當被動的“容器”,“生物目標的實現,完全被交付給了男性的主動精神,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與女性的合作毫無關系”[1](P296)。對男性生殖力的推崇與對女性生殖力的剝奪是同時發生的,男性在生育過程中的絕對主導地位由此得到了確認。將“力比多”的男性屬性問題與“陽具妒羨說”體現的陽具崇拜意識置放于男權文化背景下加以綜合考察就會發現,對生殖器官的推崇(或貶損)與對生殖力的推崇(或貶損)實為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其共同指向的正是性別權力的歸屬問題。性別權力天然根源于生殖力,這是一個極其古老的性別政治命題。生殖器官是生殖力的物質體現,對生殖器官的褒貶實為對生殖力的褒貶;生殖力又是性別權力的天然來源,生殖力的歸屬直接關系著性別權力的歸屬,圍繞著生殖力的歸屬問題所引爆的正是父權與母權之間的權力爭奪。
始于19世紀60年代的關于男權制的第二次論爭即以原始社會中究竟行使的是父權還是母權為論爭的焦點。母親的生殖力是毋庸置疑的事實,“母親既是一個自然的事實,又是一個社會的事實”[6](P35),嬰兒從母體中直接出來的生育事實無可辯駁地證明了母親的生殖力,并進而宣示了母親對嬰兒的天然控制權。但男人則不同,“一定的時間差距把性交行為與生孩子的行為隔離開來”[6](P35),除非能得到“母親的證詞”[1](P46)的支持,否則父親的身份將無法獲得確認。因此,古典社會契約理論家霍布斯堅信,母權是“在自然狀態下”唯一存在的“政治權力形式”[1](P46)。具有女權主義色彩的精神分析學者克倫·霍尼據此認為,相較于所謂的“陽具妒羨說”,更具初始性的恐怕應該是“子宮妒羨說”才對,并認為男人在公共領域中的一切事功追求都根源于“對女人在私人領域的權力的嫉妒:生育和哺育人類生命的能力,以及對不懂事的孩子行使無限權力的能力”[4](P136)。可以想見,一旦有關父親生殖力的相關知識被發現后,長久以來積郁著的子宮妒羨心理必將引發一場奪權大戰:對生殖力的爭奪,對父親身份的確認,進而對男性權力(父權、夫權)的申明與宣示。因此說,相較于母權的“自然事實”,父權“僅僅只是一個社會事實,一項人類的發明”[6](P34),為父權,以及包括父權在內的男性權力提供制度性保障的男權制,則是“男人克服父親身份的不確定性需要的一種結果”[6](P34),體現了由于“男人在人類再生產方式中被異化”而渴望“超越這種異化的欲望”[7]。
以生殖力的父性歸屬為父權確認的關鍵,這一極為古老的父權(制)邏輯思維廣泛地體現在父權文化系統的神話與宗教之中。古希臘悲劇家埃斯庫羅斯的悲劇三部曲《奧瑞斯特斯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報仇神》的第四場所展現的就是母權之于父權的最后一次悲劇性反擊。圍繞著俄瑞斯忒斯的弒母罪名是否成立的問題,一場論辯在復仇女神與新興的男神阿波羅之間展開。俄瑞斯忒斯的質疑,“我與我這個母親是同一血緣?”[8](P488)令復仇女神極為震怒,“腰帶里怎么生出了你這個殺人犯?竟然詛咒最親近的母系血緣?”[8](P488)男神阿波羅的父性生殖力理論成功地扭轉了局面,“并不是被稱為母親的人生兒女,她只不過是撫育新播下的種子,是授胎者生育,母親如主人與賓客,保護幼芽,若神明不傷害他們,……父親沒有母親也能生育。”[8](P491)阿波羅舉出的“證人”,那位以成人狀態從父親宙斯的腦袋里直接蹦出來的雅典娜更是提供了關鍵性的“證詞”,表示“她并非在母胎的黑暗里孕育”[8](P491)。至此,母權因生殖力的被剝奪而宣告了徹底的失敗。
這場圍繞著生殖力的歸屬問題展開的性別權力大戰也同樣在《圣經·舊約·創世紀》中關于夏娃誕生的故事中殘留下了模糊的印記。米利特認為,夏娃身上“一定存有退化了的,以往被推翻的生育女神的痕跡”[1](P79-P80),因為夏娃被認為是“眾生之母”[3](P12),亦即“萬種生物的母親”[1](P80)。然而,這樣一位曾經的原始母神卻在男權系統的解讀下變成了亞當身體的一部分。神賦予亞當以身體(地上的塵土)并賜名,亞當再賦予夏娃以身體(身上的肋骨)并賜名,亞當因此成為了夏娃的“直接”造物主。從這一意義而言,亞當是夏娃的丈夫,更是夏娃的父親,原始母神的生殖力為男性所剝奪并占有。《圣經》的這段故事曲折地反映了母權被父權戰勝的“前夜”(Eve),而“巧合”的是,“Eve”正是夏娃——這位曾經的生育女神的名字。
生殖力的父性屬性也同樣體現在17世紀的古典父權主義論調中。“單生觀是古典男權主義的核心”[6](P36),父親的生殖力從來都被認為是自在圓滿的,其本身就是將女性力量與男性力量融匯合一的完美整體。女人在生育活動中則完全是無關緊要的存在,“女人不過是男人實踐其性與生殖權力的空洞的管道”,而男人才是“更高貴的主要動因”[6](P93)。這一父權主義論調與上文論及的弗洛伊德的觀點,即力比多微弱的女性只是充當被動的“容器”,“生物目標的實現,完全被交付給了男性的主動精神,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與女性的合作毫無關系”[1](P296)可謂如出一轍。更為重要的是,對父親生殖力的確認并不僅僅關系到父權,更直接關系到父權制的合法性,因為父權往往被認為與君權(政治權力)同源一體。17世紀英國父權制憲政理論的代表人物菲爾默·羅伯特爵士即認為,政治權力(君權)來源于父權,父權則來源于父親的生殖力,亦即父親因生育子女而對子女天然享有的權力。顯然,如果母親的生殖力得到了認可,那么不僅是父權,建立于父權之上的君權的合法性都將遭到質疑,父權制憲政體制的理論基石將隨之崩潰。因此,生育力只能為父親所獨有。至此,關于生殖力的歸屬,已經不僅止于性別權力的爭奪,而實實在在地演變成了政治問題。
由上述分析可知,通過生殖力的父性歸屬以確認男性的性別權力一直以來就是典型的父權(制)邏輯思維。弗洛伊德堅持認定“力比多”具有男性屬性,無疑為生殖力的父性歸屬提供了生理解剖學上的“科學”支持。盡管激烈的社會變革往往會引發上層建筑不得不作出相應的調整,但“男權制”——這一造就了兩性間統治與隸屬關系的社會化機制卻被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一旦它獲得了新的維護,一旦它被新的勢力認可,一旦有人為它提供了意識形態方面的新的依據,它就會再一次被調動起來”[1](P270),而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論正是以一副“對社會進行控制和操縱的最有用、最權威的”[1](P271)“科學”面目成功地擔負起了這一重任。
三、關于“閹割情結”與“亂倫禁忌”:社會性別的建構與男權制社會的再生產
前俄狄浦斯階段的“多態性異常”是弗洛伊德兒童性心理學中一個極具價值的觀點。弗洛伊德認為,身處這一階段的兒童基本上處于一種無意識狀態,他的性感區可以面向廣泛的性對象無差別地開放,這其中就包括他的父母血親。“兒童可以出現多重性變態,可以被引入各種各樣的性反常現象”,他們“先天就存在著這些傾向”[9]。無論是男孩還是女孩,“多態性異常”首先體現為將原欲對象指向自己母親的亂倫情結,且這一亂倫情結對女孩而言更多了一層同性戀意味,因此,弗洛伊德認為,相較于始終保持著異性戀取向的男孩,“女孩向正常婦女的發展”要更為“艱難而復雜”[5](P121)。幼童如何克服本能的多態性異常而建構起符合社會性別規范的性別身份?尤其對于女孩來說,她“是如何從對母親的依戀轉向對父親的依戀的?”又是“怎樣命中注定地從男性階段轉向女性階段的?”[5](P123)弗洛伊德的“閹割情結說”對上述問題作出了解釋。
弗洛伊德認為,男女兩性都有閹割情結,只是內容不同。對于女孩而言,閹割情結更多地體現為“陽具妒羨”心理。由于發現自己“缺失”陽具,原本敢于將母親視為原欲對象的“小男人”喪失了曾經的“雄心”,而不得不以一種被動的姿態將自己的欲望所指轉向父親,并進而由被動轉為自虐,從最初自認為遭到了閹割的沮喪轉變為“我想要被我的父親閹割”[2](P59)。曾經的“小男人”于是逐漸培養出了被動的、自虐的女性屬性,并適時地學會了將“那種不完全適合女性的占有陰莖的欲望,正常地轉變成了對嬰兒的欲望,繼而又轉變成對作為陰莖持有者和嬰兒給予者——男人的欲望”[5](P103-P104),最終成功地轉變為熱衷于母職與妻性的“成熟的女人”。對于男孩而言,閹割情結則更多地體現為“閹割恐懼”心理,尤其是在看到了眼前就有一個“被閹割者”的活生生的例子后,更加劇了小男孩對父親發出的閹割威脅的恐慌,促使他最終斬斷了指向母親的亂倫情愫,為日后于血緣親屬之外尋找性對象,建立起非血緣的社會關系網絡作好心理準備。同時作為對兒子的“獎勵”,父親撤銷了閹割威脅,并認可了兒子具有“勢”所象征著的性別權力,其日后要求獲得一個女人以維護自身性權力的主動性因此得到了保障。由此可見,弗洛伊德的“閹割情結說”主要闡明的是男女幼童必將克服多態性異常以建立起社會性別身份的一整套心理機制,且由于這一整套心理機制建立在“陽具的有無”這一先天生理差異上,也就決定了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之間的必然性關聯,即小男孩必將發展為具有男性氣質的男人,而小女孩則必將發展為具有女性氣質的女人。否則,“任何偏離固有規范的情形,都可被視為某種程度的病態。”[1](P294)“閹割情結說”的運用是弗洛伊德的社會性別理論得以構建成功的關鍵所在。
這一菲勒斯中心主義的生物決定論論調自誕生之日起就毫無懸念地成為女權主義者的矛頭所指,所謂的“閹割情結”乍看一下也確實頗有些匪夷所思的荒誕色彩。不過如果將其置放于整個男權文化的大背景下就會發現,這一理論的提出絕非一時的心血來潮,更非故意地標新立異,而是從人格心理學的角度切實發揮了維護男權制社會的現實作用。首先,由“閹割情結”促成的男女兩性的人格心理發展趨向非常符合男權制社會的空間運作需求。正如上文分析所示,“閹割情結”作為心理機制雖有助于男女幼童克服多態性異常以實現性別的社會化,但其于男女幼童的側重點還是有所不同。就男童而言,閹割情結主要表現為閹割恐懼心理,其作用是使男孩摒棄亂倫傾向以確保其日后能與非血緣的女性建立起婚姻關系,并借此建立和拓展非血緣的社會關系網絡,其所指向的是社會公共領域;而對于女童來說,閹割情結則更多地表現為陽具妒羨心理,其作用除了斬斷指向母親的亂倫幻想外,更集中體現在迫使女孩形成被動的、自虐的女性屬性,以及將母職與妻性作為自身價值體現的性別身份體認,其所指向的是家內私人空間。由“閹割情結”促成的兩性人格發展的不同趨向為男權制社會公、私領域的區分與維系提供了必要的心理基礎。
此外,尚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多態性異常發展的多種可能性在“閹割情結”的干預下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壓制,但唯有“非亂倫的異性戀”獲得了認可并得以發展。這一社會性別規范的制定究竟所據為何?結合弗洛伊德的“閹割情結說”將會發現,除了人格心理學方面的內容外,該理論事實上還論及了男權制社會再生產的兩大保障機制,即“亂倫禁忌”,以及由亂倫禁忌必然導致的于血親之外尋找性對象的“族外通婚”,“非亂倫的異性戀”這一性取向上的規制顯然與這兩大機制極為合拍,其共同確保的正是男權制社會再生產的順利進行。因此,對“閹割情結說”的闡釋并不能僅僅停留在社會性別,或人格心理的建構本身,其所關涉的更是男權制社會的保障機制問題。
弗洛伊德在《圖騰與禁忌》一書中對“亂倫禁忌”與“族外通婚”在男權制社會的建立與維護中發揮的體制性保障作用進行了論述。弗洛伊德認為男權制社會是在原始父親實施的絕對父權統治被眾兒子們推翻后才建立起來的。弗洛伊德借助精神分析法對眾兒子們對父親既敬又畏、既愛又恨的復雜心理,亦即父親情結的矛盾情感進行了精彩的剖析。依據弗洛伊德的解釋,殘暴的原始父親所代表的絕對父權統治之所以被眾兒子們聯合推翻,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占有欲異常旺盛的父親霸占了氏族內的所有女人,對于兒子們來說,“父親是他們在權力欲和性欲上的巨大障礙”[10](P137)。因此,當絕對父權統治被推翻后,兄弟們便達成契約以反對權力獨裁,確保權力共享。弗洛伊德認為在兄弟們簽署的這份原始契約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禁止亂倫”。由于信奉著同一圖騰的氏族成員“相信自己有著同一血緣,是同一祖先的后裔”[10](P101),這一條約的規定迫使兄弟們不得不到氏族外去尋找女人,將血親排除在性對象之外的“族外通婚”由此得到了確立。族外通婚的實施不僅確保了剛剛建立起來的兄弟同盟不會因對族內女人的混亂爭搶而分崩離析,同時亦確保了每個兄弟都能通過有序的族外通婚獲得一個女人的性權力。男性權力得到了保障,兄弟同盟得以存續下去,權力壟斷的絕對父權統治終于為權力共享的男權制社會所取代。
弗洛伊德的關于通過“亂倫禁忌”與“族外通婚”的保障機制以確保男人性權力的觀點,在結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的親屬關系結構研究中得到了回應,列維更進而將婚姻契約的締結描述為以女人這一“最珍貴的禮物”[2](P36)為媒介而在兩群男人之間結成非血緣的社會關系網絡。女權主義者蓋爾·魯賓接受了列維的觀點,并認為列維描述的親屬關系結構深刻地揭示了“女人在其中對自身缺乏完整權利的一種制度”[2](P40),洞悉了男權制這一女人受壓迫的從屬地位形成的制度性根源。然而,列維以及接受了列維理論的魯賓尚僅僅停留在“亂倫禁忌”與“族外通婚”這一男權制社會得以形成的結構機制上,而未能有效地解釋在婚姻契約中體現出的性別的穩定性,即男人永遠都是簽約者、賜禮者、流通過程的組織者,而女人卻永遠只能充作被動流通的“禮物”。性別穩定性的存在表明了男女兩性在這一過程中被賦予的角色絕不可能僅僅是社會建構的結果,而必然有著更為恒定、穩固的生物學基礎,“必須著眼于生物性或解剖學意義上的差異,否則從邏輯上它就無法解釋性別穩定性”[4](P155),弗洛伊德的社會性別理論即提供了一種解釋的可能。在通過婚姻契約結成的親屬關系中,男人作為簽約者的主動性,女人作為“禮物”的被動性,男人借助姻親紐帶以向社會公共領域拓展的向外趨向,女人作為被交換回來的“禮物”而不得不固守于家內私人空間的向內趨向,都可以從弗洛伊德的社會性別理論中尋找到人格心理層面的解釋,且正如上文分析所示,男女兩性不同的人格心理又恰恰建立在“陽具的有無”這一先天存在、不可更改的生物學差異性上。從這一意義而言,作為社會性別形成的重要心理機制——“閹割情結”雖飽受女權主義者的質疑,但畢竟還是在客觀上為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婦女從屬地位形成的心理學根源提供了理論上的可能性,這相較于女權主義者僅僅停留于體制結構層面上的探討顯然是一個巨大的理論進步。
四、關于“社會建構”與“無意識”:弗洛伊德思想對女權主義的啟示
從意識形態到思維邏輯,再到制度化保障機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可以說內置了一整套完整的男權文化系統,并在借助人格心理學與社會性別理論為男權制建構的合法性提供心理依據的同時,亦使得古老的男權文化在生理解剖學—臨床心理學的科學外衣下得到了新的維護。女權主義者米利特認為,在解釋女性的性別自卑時,弗洛伊德并沒有將“男權制的社會環境以及女性在這一社會的低下地位”這些社會性因素考慮進來,而完全將“基于解剖學上的差異這一生物學的事實的孩童體驗當成了解說一切的原因”[1](P276)。然而結合上文論述將會發現,這種看似純粹的科學面孔不過是一個假象,男權文化的價值觀早已深深地滲透進了弗洛伊德的整個理論構想中,并使其針對臨床觀察資料所作的分析常常在男權立場的預設下陷入循環論證的怪圈。這就要求我們在考察弗洛伊德學說時必須要采取一種辯證的科學態度,將那些真正具有科學價值的臨床發現與為男權意識所左右的傾向性解讀充分地剝離開來。論證思路的錯誤并不能詆毀作為論證對象的原始資料本身的認識價值,在剔除了男權立場的干擾后,我們將會發現,弗洛伊德的許多富于創建性的臨床發現對于女權主義而言同樣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
多態性異常的發現表明了性別本身是一個社會化過程,主動性的男性氣質、被動性的女性氣質、“非亂倫的異性戀”取向,乃至于生育母職的所謂女人“天性”都只是后天建構的結果。更具革命意義的是,多態性異常的存在還極具顛覆性地暗示了在原始(“自然”)的混亂狀態與后天(“社會”)的理性建構之間存在著某種天然聯系,閃耀著人類理性之光的秩序與規范恰恰植根于原始狀態的混沌與無序中,究竟何者為正常的、規范的,何者又為反常的、病態的,都只不過是一種選擇的結果,性別的社會建構本身其實是非常不穩定的。人類自認為純粹的理性判斷往往都有著混沌不清的原始基礎,追溯得越久遠,就越會發現我們所認定的現代性,往往都有著古老的心理根基;我們所標榜的社會建構,往往都有著植根于人類潛意識中的深層動因,并非完全是清醒的、理性的選擇。正如“禁忌”與“欲望”的永恒較量所顯示的那樣,“禁忌的強度及其強迫特性完全要歸因于潛意識對抗,歸因于那種隱蔽了的、絲毫未衰的欲望”[10](P34),理性未必是唯一真實的原因,未必有理由阻止我們向心靈的更深處去探求那些隱匿在無意識中的真正動因,純然理性的社會建構不過是一個一廂情愿的幻覺。弗洛伊德學說的“無意識”理論揭示了多態性異常的絕對自由本性,對社會建構論構成了嚴重的威脅,這是女權主義者所無法接受的。
女權主義者對弗洛伊德學說的猛烈抨擊幾乎全部集中到了具有鮮明男權立場的“陽具妒羨說”“閹割情結”等理論上,此類明顯根源于菲勒斯中心主義的學說也確實有問題。但論證邏輯上的錯誤并不意味著觀點本身的全盤錯誤,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之間畢竟還是有一定關聯的,社會性別的生物學基礎終究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已有研究表明,月經、懷胎、分娩、生育等生物學事實確實極大地限制了女性的活動空間,在節育、避孕技術都十分匱乏的時代,她們成年之后的絕大部分時間都消耗在此類活動中,這就決定了女性不可避免地成為“合乎邏輯的壁爐守衛者、家庭事務的承擔者,同時也是(通常與其他女性合作)緩慢成熟的蹣跚學步者合乎邏輯的監護人和教育者”[4](P61)。生育、家居、撫育幼兒等獨特的生命體驗會使女性更加關注肉體的、物質的、現實的內容,更易為生命個體之間的情感性、關聯性所牽絆。而很少被束縛在此類事務中的男性則獲得了更大的性別自由,具備了更有可能向社會公共領域拓展自我的性別優勢。“自我基本的女性意識表現為與世界的聯系”,“女性氣質是本質上的生命關注(與生命相關連)”,而“自我基本的男性意識則是分離”,“男性氣質是本質上的疏離(與死亡相關連)”[4](P137,139)。“存在于生育和分娩的生物性事實及其文化含義之間”[4](P155)有一種直接的聯系,自然的生理差異決定了兩性建構自我的不同方式,進而又導致了兩性諸方面的差異,社會性別正是在與生理性別的比照中得到確立的,而這一點正是弗洛伊德學說的應有之義。
由上述分析可知,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之間的關系雖不像弗洛伊德主張的那么絕對關聯,可也不像女權主義者所希望的那么毫無關聯。任何標榜著純然理性的社會建構都有著無法否認的自然基礎,真正的“主我”恰恰存在于無法為社會建構所限制的自然與無意識中,并在與社會建構而成的“受我”的分離中保持了相對的自由。否則的話,個體的整個生命歷程都將被動地全部淪為“對白板的社會化印刻”[4](P187),在自認為掙脫了自然束縛的幻影中,又在劫難逃地成為“過度社會化”[8](P183)的犧牲品。
生理性別差異是男權制得以建立的“自然基礎”。女權主義者急于借社會建構論以否定生物學差異、否定人的自然限制,一些激進的女權主義者甚至直接否認了生理性別本身,認為完全沒有區分生理性別、社會性別的必要,二者都是社會建構的結果。給人的感覺似乎是一旦承認了生理性別差異,就等于承認了男權制的存在合理性一樣。而且,女權主義者的許多無異于自我貶低的言論,如對“生育的身體”的厭惡,對哺乳、育兒等生物性母職的痛恨、對“體外懷孕”等“生物技術革命”的熱望,將女性的社會性別角色貶低為“過著一種不事思考的經驗性生活”的“心滿意足的母牛”等[11],以及與之相對的一些“正面”言論,如強調女性氣質的優越性,對所謂“母權制”社會的熱烈暢想等,盡管乍看之下頗有些革命色彩,但終歸還是在社會性別的二元對立中陷入了男權話語的邏輯圈套。
“婦女解放運動的真正力量并不在于申明她們的性的特殊性,以及要求與此相關的權利,而在于從性的機器內部運作的話語中分離出來。”[12](P95)過多地糾纏于性別的社會建構對于女權主義的理論出路而言并無多少好處,或許真正的啟示還是來自于“無意識”理論所暗示的那個“雙性同體”的性別自由時期。“雙性的心靈”[13](P156)是“自己的性別特征和異性的生理特征的混合體,是主動和被動的統一體”[14](P129),它并不會“特別地或孤立地考慮到性別”[13](P156),而是很自然地將兩性氣質的優勢集于一身并為我所用,同時又能借助性別氣質中的異性因素實現與異性的良好溝通。誰也無法否認在遭到社會性別規范的強行制約前,內含了“雙重性別氣質”[5](P120)的幼童(尤其是女童)是多么地虎虎有生氣,無所謂“主我”與“受我”,甚至也無所謂“自我”與“他者”,神采飛揚地擁抱整個世界。跳出男權制的話語邏輯與思維模式,在尊重性別差異的同時超越性別差異,在勇于自我認同的同時容納多種認同可能,并在此基礎上,真正“喚醒”曾一度擁有的理想人格。“黃金時代”的模糊記憶將有可能為女性解放的道路指出明晰的未來,“婦女運動中最具創造力和活力的因素”[12](P196)或許正在于此。
[1] [美]凱特·米利特.性的政治[M].鐘良明,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2] [美]蓋爾·魯賓.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經濟學”初探[A].王政,杜芳琴.社會性別研究選譯[C].北京:北京三聯書店,1998.
[3] 圣經(精讀本)[M].香港:牧聲出版有限公司,2012.
[4] [英]約翰·麥克因斯.男性的終結[M].黃菡,周麗華,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
[5] [奧]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導論講演新篇[M].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0.
[6] [美]卡羅爾·帕特曼.性契約[M].李朝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4.
[7] [美]瓊·W·斯科特.社會性別:一個有用的歷史分析范疇[A].王政,張穎.男性研究[C].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2.9.
[8] [古希臘]埃斯庫羅斯.古希臘悲劇喜劇全集:埃斯庫羅斯悲劇[M].王煥生,譯.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譯林出版社,2007.
[9] [奧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性學三論[M].趙蕾,宋景堂,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0.53
[10] [奧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圖騰與禁忌[M].邵迎生,譯.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11] [澳大利亞]薇兒·普魯姆德.女性主義與對自然的主宰[M].馬天杰,李麗麗,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3.
[12] [法]米歇爾·福柯.性史[M].張廷琛,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9.
[13] [英]弗吉尼亞·伍爾夫.一間自己的房間[A] .論小說與小說家[C].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
[14] [美]約瑟芬·多諾萬.女性主義的知識分子傳統[M].趙育春,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ThePhallocentricInterpretationofFreud’sPsychoanalysis——andRevelationtoFeminism
SHI Wenfei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00,China)
From ideology (phallus worship) to logical thinking (father of fecundity,belonging to patriarchy) two security mechanism (“incest” taboo and “marriage within family” taboo),Freud’s psychoanalytic theory can be said with a complete set of patriarchal culture system.The ancient patriarchal culture is resurrected in the coat of modern Anatomy-Clinical Psychology,and its anti-feminist tendency inevitably makes Freud’s theory the target of the second wave of feminist movement.But the error in reasoning cannot slander the value of scientific research.Freud created many rich clinical and revolutionary theories significant for feminist reference and future development.Dialectical attitude will be helpful to re-examine and rediscover Freud’s theory.
penis envy theory;gender power;castration complex;incest taboo;social gender;male dominated society;social construction
2017-08-20
陜西師范大學優秀博士論文資助項目“性別書寫與近世白話小說”(項目編號:2014YB11)
施文斐(1978—),女,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礦業大學銀川學院中文系講師,主要從事近世小說與性別研究。
C913.68
A
1008-6838(2017)06-0006-09
(責任編輯 魯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