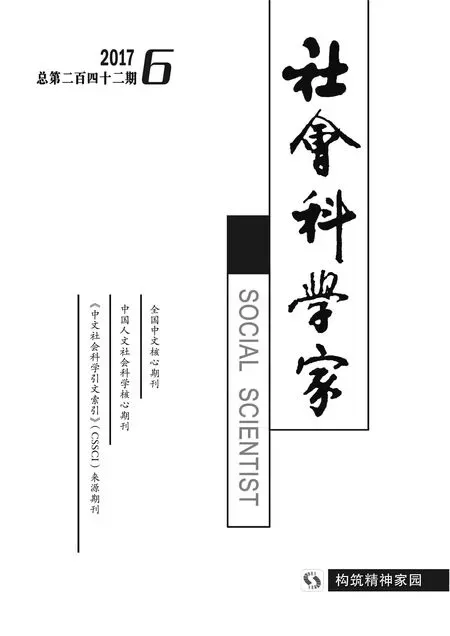云南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特征及其價值
——基于綠色發展理念
龍麗波,吳若飛
(1.陜西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陜西 西安 710119;2.云南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云南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特征及其價值
——基于綠色發展理念
龍麗波1,吳若飛2
(1.陜西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陜西 西安 710119;2.云南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民族生態文化是少數民族生態智慧的結晶,是少數民族生存方式的原真反映。綠色發展蘊含著與民族生態文化相同的價值訴求,民族生態文化需要綠色發展的育養和支撐,綠色發展離不開對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特征和價值的解讀與挖掘。在民族生態文化多元性基礎上,云南少數民族生態文化具有習俗性、珍貴性、地域性、動態性等特征。民族生態文化具有巨大的開發利用價值,具有經濟價值、社會價值、生態價值。因此,以民族生態文化為切入點推進少數民族地區的綠色發展,成為少數民族地區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現實選擇和歷史必然。
綠色發展;民族生態文化;特征;價值
云南少數民族生態文化是族群生存方式的原真性反映,而綠色發展作為一種可持續發展形態,體現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社會發展模式的創新,民族生態文化與綠色發展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民族生態文化需要綠色發展的支撐,綠色發展離不開對民族生態文化資源價值和特征的深度挖掘,綠色發展已經成為實現“云南夢”、“中國夢”的歷史使命。當前,民族地區社會發展在深化改革的背景下面臨諸多掣肘,生態環境遭到破壞,資源短缺制約趨緊,各類環境問題呈現高發態勢,生態危機成為制約少數民族地區綠色發展的短板,民族生態文化無疑給我們思考如何實現綠色發展提供了突破口和思路,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統一。民族生態文化是民族地區綠色發展可資利用的寶貴資源,在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的時代背景下,認真把握、解讀云南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特征及其資源價值,成為一個重要的實踐與理論問題。
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與綠色發展理念相契合
云南是一個多民族的省份,各少數民族在彩云之南共同創造并且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民族生態文化。深化改革背景下民族生態文化只有融入到綠色發展的全過程,才能在新時期迸發出時代價值,使民族生態文化充滿生機和活力。少數民族生態文化不是孤立發展的,更不是單線演變的結果,而是和社會經濟發展相互作用形成的,融合綠色發展優勢更有助于推動民族地區的先進文化建設。
(一)觀念生態文化契合
觀念生態文化作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往往以宗教信仰、民族諺語、民族歌謠、民族服飾等形式表現出來。具有多民族特色的不同文化在社會歷史進程中不斷交流與融合,在生產、生活實踐過程中形成了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觀念,并逐漸形成了樸素的民族生態文化,少數民族生態文化與綠色發展在社會發展中是內在統一的關系。
少數民族的生態文化是在生產生活實踐中逐漸積累形成的,以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民族諺語、民族歌謠、民族服飾等方式體現出來,突出了既保護民族地區的生態環境,又使生產、生活處于良性發展之中,使生物多樣性與社會經濟發展平衡發展。首先,傳統宗教信仰。少數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這些宗教教義滲透在少數民族的生活方式之中,不同程度地影響了少數民族群眾的倫理道德和傳統生態文化,使其形成自覺意識。如彝族信奉的佛教,每逢初一十五,要點燈、吃素和“不殺生”,敬畏生命不能對自然索取太多,否則將觸怒神明導致災禍降臨。少數民族對動物和自然界的崇拜,是人們在生產、生活中依賴自然界的直接表現,一切生產、生活方式按照自然界的發展規律才能安泰民富。其次,民族諺語。少數民族諺語中也蘊含著綠色發展理念,這種習俗積淀在諺語中,如“樹大不可砍,砍樹如砍人,村里有大樹,村里老人才長壽”。哈尼族在長期生活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生態習俗,在蓋房子之前要在房子周圍先植樹,哈尼族民居周圍都是茂密的樹林,說明哈尼族植樹的環保行為,也體現了他們綠色發展的生活觀念。再次,民族歌謠。在云南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有這樣一首彝族歌謠,“酒要少少的喝,多少粒苞谷釀出一滴酒;煙也要少少的抽,防止森林火災,愛護身體保護環境。煙酒少少的才能讓阿媽阿爸高興,阿媽阿爸才能長壽,”少數民族歌謠透露出綠色可持續發展理念。最后,民族服飾。各個少數民族的服飾多以鮮艷的花草和形態各異的鳥獸、生產生活圖景相配,體現了生態文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得益彰,反映出了少數民族服飾文化中的生態環保意識和綠色發展理念的有機結合。上述少數民族環保觀念反映了民族生態文化是在少數民族社會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積累起來的,說明各族人民群眾的宗教信仰、民族諺語、民族歌謠、民族服飾中不僅蘊含著保護生態的思想,也有綠色發展的傳統。
(二)制度生態文化契合
制度生態文化是一種強制性的文化規范,“鄉規民約”是民族地區最常見也是最核心的制度生態文化。納西族的《東巴經》甚至規定了明確的禁條:“禁止在河里洗屎布;禁止向河里扔廢物或倒垃圾,禁止向河里吐口水,禁止堵塞水源;不得在水源地殺牲宰畜,不得在水源旁大小便,不得毀林開荒,立夏過后實行‘封山’,禁止砍樹和打獵等等”[1]。哈尼族有自己一套森嚴的森林保護規定,對薪柴和建房用材嚴格區分,對于建房用材必須事先得到審批。傣族、景頗族則是將某些山林圈起來作為本民族的寨神林或者勐神林,神林之內的一切東西都不允許碰觸,哪怕是掉落的樹葉、熟落的果子都不準碰,不準人們隨意進出神林,不然將觸怒寨神、勐神致災禍降臨,也將受到以族長執行的族規的嚴厲懲罰。難能可貴的是少數民族生活方式中滲透著節制的生態觀念,“糧谷豐,勿墾荒”,“非獵戶,勿捕虎;非射手,勿擒禽;非樵者,勿伐木”是居住在麗江一帶納西族的傳統生態觀念,體現了納西族人保護生態環境,不隨意開荒、狩獵、砍伐的行為規范。
從以上的闡述分析得出,少數民族生態文化與綠色發展具有深度結合的思想基礎,可謂是不謀而合。在少數民族生態文化觀念的影響之下,“仁慈好生的倫理情懷”、“萬物有靈的大地倫理觀”、“忌貪婪、少索取”等生態環保思想滲透在少數民族的各個方面,成為了一種保護自然生態和民族居住環境的“內源調節器”,是綠色發展重要的生態文化資源。雖然民族地區的生態文化與經濟的關系并非亦步亦趨,但是生態文化不可能隨著生產方式的變革而完全消逝,而是會以某種形式將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一部分生態文化保留下來,并在新時期發揮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作用。
二、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特征
少數民族的生態文化在不同的生態環境中,隨著環境的變化和資源狀況的改變而改變,每個民族生態文化都蘊含著現實生活形態,在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使生產方式、生活方式逐漸生態化,使少數民族地區得以永續發展。民族生態文化是與時俱進的動態系統,各個民族生態元素之間相互交織、相互融合使民族生態文化具有多樣性。在多樣性的基礎上,民族生態文化具有習俗性、珍貴性、地域性、動態性等特征,這些特征成為民族凝聚力的動力源泉。
其一,習俗性。云貴高原的山脈、氣候以及物產等獨特的特征形成了云南少數民族獨有的狩獵生存方式和經營模式,少數民族的生活習俗、思維方式以及宗教信仰等的形成受到自然資源和地理環境的深刻影響。一般而言,少數民族和外界的聯系相對較少,民族群眾勤勞樸實,認為花、草、樹、木、山、石等都有神保佑,神法力無邊、無所不能,是自然界的主宰。神與自然界是統一的,人們應該膜拜,尊重自然和敬畏神明,不然將會降臨災禍。禁止在水源地洗浴,禁止濫殺野生動物,尤其不能殺害具有靈性的動物,比如老虎、豹子等,保持封山育林的環保習俗,禁止在繁殖期捕獵,這些是少數民族地區動植物正常生長的重要習俗。在飲食習俗之中也透著生態性,吃食尤其講究食物的原味性,注重食物的天然綠色,注意包裝對環境的污染,比如景頗族的手抓飯就非常環保,食物用清洗過的蕉葉包裹,美味的食物透著蕉葉的清香,既美觀美味又健康環保。通過極具生態性的習俗透露出云南少數民族的生態文化觀:在自然崇拜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愛護生態環境、保護動植物的生態文化思想。目前,在云南少數民族地區仍然保留著狩獵的生活方式,在狩獵的過程中人們認識到人與動植物之間和諧共生的互動關系。狩獵也有嚴格的限制,不過多索取自然,形成了保護動植物的習俗。少數民族科學合理的利用自然資源,尊重自然遵守自然規律,在生產生活中處處透露出綠色發展的理念。
其二,珍貴性。少數民族的文化自信來自對本民族文化特質的充分肯定,是民族自我意識中最活躍的元素之一。少數民族的生態文化在以科技為首的現代文明進程中受到了極大的負面影響,民族地區的自然生態文化的原真性受到破壞,甚至有些就此滅絕。這不僅僅是云南少數民族面臨的困境,也是大多數民族地區面臨的問題。從民族地區的社會環境方面來分析,在全球化和現代化浪潮的沖擊下,大大削弱了少數民族對自身文化的自信程度,錯誤地以為民族文化就是愚昧、落后的象征,對西方文化和現代文化趨之若鶩,造成對民族生態文化的冷漠化。加之現代都市生活方式的影響,“自然生態”被現代化逐漸消解,民族生態文化的根基不再堅不可摧,這種自卑思想使民族生態文化減少多樣性,使得民族生態文化彌足珍貴。從民族地區的自然環境方面來看,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縮小了生態文化的生存空間,生態文化多樣性逐漸減少。如“從森林覆蓋率來說在1950年代中期,基諾山地區的森林覆蓋率在60%以上,而到了1990年代中期則下降了40%。”[2]在云南的少數民族地區,不僅僅是基諾族中出現此類生態問題,其他民族亦如此。自然生態系統遭到嚴重破壞,自然資源減少的同時,生態文化資源也在減少,現代經濟發展和民族生態文化之間的矛盾使民族生態文化被割裂。因此,民族生態文化的稀缺性喚起了人們必須重視其資源價值,使其在綠色發展中發揮意義和價值。
其三,地域性。自然地理環境承載著民族生態文化的產生和發展,不同的地域形成了差別迥異的文化。在氣候適宜的云南,多種民族世代居住在這里,各個民族具有獨特的風俗習慣,不同的地域有著各自特色濃郁的生態文化。在民族地區開展綠色發展,必須正確認識不同地域之內的生態環境特征及其發展規律,因為民族生態文化也屬于地域性資源中的一種。民族生態文化的特征通過地域性、民族性顯示出來,同時把民族生態文化把地域性和民族性有機統一起來。任何一個生態文化都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間,地域性是民族生態文化得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元素。生態文化在一定空間中生存,在地域空間中進行文化交流和實踐,進而獲得文化認同。例如“云南省祿勸彝族自治縣幾乎每一個自然村都有他們視為本村保護神的“神樹”,神樹大多是上百年歷史的老樹,或在村落的高處,或在村中的要道處。他們認為神樹能夠給村子帶來平安、吉祥和豐收。”[3]彝族人民勤勞樸實形成了多元化的生態文化,不同地域風格略有不同。例如居住在紅河石屏的彝族支系花腰彝的女子舞龍,向全國乃至全世界展現了花腰女子舞龍的獨特魅力,以地域性、藝術性、互動性、觀賞性為一體,突破性的向世界展現彝族花腰女子的舞龍技藝和豐富的民族生態文化。同屬一個地區的彝族支系阿細族和撒尼族,因生活的自然環境不同,地理地貌的差異而出現顯著的文化特征。因此,不同民族或是同一民族在不同地域中,民俗行為具有明顯的差異,這著重反映了根植于環境的生態文化的地域性特征。云南各個少數民族繼承了本民族獨特的文化脈絡,因而民族生態文化具有顯著的差異性,相連的地域環境使各自的生態文化在交往過程中體現了深刻的融合性。此外,云南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地域性具有明顯的邊緣性,各個少數民族地處偏遠地區,遠離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民風淳樸自然生態環境良好,人與自然和諧共處。云南民族生態文化的地域性還有差異性,與主流現代文化相比較具有顯著的差異,正是這一差異性使民族生態文化具有無窮的吸引力,使其擁有不可替代的地域性價值。
其四,動態性。任何一個民族生態文化的發展變化,不僅受到民族自身的文化發展規律以及文化連續性的深刻影響,而且也深受到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影響,體現為動態發展的過程。動態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民族生態文化內部各要素的產生、發展、變化的動態性。“民族生態文化在整個動態性的過程中,其內部各要素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交織,共同發揮功效維護民族生態文化的穩定發展。”[4]二是民族生態文化與自然環境、社會環境之間是一種動態的制衡關系。民族生態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以自然環境為前提條件,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文化生成環境的影響,在不斷調試和淘汰過程中形成和發展。民族生態文化伴隨實踐的變化而不斷發展變化,生態文化得以生存和發展的承載基礎——村寨文化,現如今受到嚴重破壞。在邊遠山區,由于人口的不斷增多,使原本平衡的生態系統失去平衡,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不再適應自然環境,與環境產生了矛盾。少數民族原有的一些生產方式,在人口稀少、土地廣大的情況下,對自然生態系統的影響不大,自然生態系統可以自行修復保持生態平衡。但是如今人口劇增,人口聚居超出了生態環境承載能力范圍,人均土地面積不足,在利益驅動下砍伐森林日漸增多,森林覆蓋率逐年下降,生態惡化不斷加劇,使其賴以生存的空間不斷縮小。不僅民族生態文化載體的自然環境發生了變化,社會環境也有動態發展的趨勢。位于滇中高原和滇西橫斷山脈的麗江,麗江古鎮聞名遐邇、文化燦爛,現如今交通發達,游客爆滿,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深度融合,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然而淳樸的民風和古鎮文化受到了強烈的沖擊。古鎮、古村落是民族生態文化生存和發展的重要空間,古鎮、古村落的變化直接影響民族生態文化的生存和發展。民族生態文化的生成和發展,總是與所處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歷史環境聯系在一起,在這一動態發展中互動交流與融合,以動態的形式進行創新和發展,少數民族群眾廣泛地參與生態環境保護活動,是民族生態文化在特定時空下的最為活躍的主體。民族生態文化在一定意義上促進了少數民族的發展,任何民族生態文化在各自的自然環境中發揮積極功效,都必須與其他民族進行互動交流,使各種生態文化進行融合具有多元性。因此,在挖掘民族生態文化的進程中,必須正確認識到民族生態文化的動態性,注意分析民族生態文化自身發展邏輯,結合各個少數民族自身發展的歷史進程、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等,深度挖掘民族生態文化資源,使其發揮最大價值。
民族生態文化是少數民族生產方式的重要體現,是少數民族生態倫理智慧的集體結晶,是綠色發展的重要資源。對云南少數民族生態文化進行認真解讀和深度挖掘,對民族生態文化的特征進行深入分析,驅動民族生態文化實現價值轉化,進而尋找民族生態文化與綠色發展的轉化機制。因此,以民族生態文化為靈魂的綠色發展,是新時期云南民族地區跨越式發展的必然選擇!
三、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資源價值
少數民族生態文化是少數民族成員的精神支柱,也是少數民族生存態度的真實寫照,體現了少數民族在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中的生存方式和發展方式,更是自身區別于其他民族的象征。然而相對落后的生產、生活方式和脆弱的自然生態環境,是制約云南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掣肘,但恰恰就是這些封閉、落后和脆弱的因素,迫使人們在長期的實踐中逐漸形成了民族生態智慧以及具有無窮資源價值的民族生態文化。綠色發展與民族生態文化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民族生態文化蘊含著可供開發和利用的巨大潛能,具有經濟價值、社會價值、生態價值,這些價值將在綠色發展中煥發出新的活力。
其一,經濟價值。少數民族生態文化在經濟發展語境中,以商品的形態作為消費品帶來價值,對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起到促進作用。首先,民族生態文化是云南文化產業發展最核心的動力。在當今經濟發展的語境下,伴隨著人們觀念的更新,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人們的生活質量得到提高從而在精神生活方面有了質的飛躍,注重生態化的消費。生態性的文化產品成為消費增長點,促進了對民族生態文化的開發力度,民族生態文化正在逐漸成為文化產業飛速發展的不竭動力。如楊麗萍在她的文化作品《云南印象》中融入了云南民族生態文化,向全世界展示了云南民族文化的生態性,成功占領了文化資本市場。云南文化產業的發展需要開發和利用民族生態文化,大力促進文化企業搶占市場份額,不僅實現經濟效益,而且還能不斷的提升文化品位,為民族文化產業的發展壯大注入生機。另外,民族地區的生態旅游需要民族生態文化作為支撐。民族生態文化是一種地域象征,人文景觀獨具民族特色,自然景觀迤邐秀美,符合都市居民心之向往的心靈回歸,是人們感受原生態、親近自然的理想之選,成為吸引游客的寶貴資源。以生態文化和自然為基礎的生態旅游,極具環境教育作用,在促進民族地區旅游創收的同時,還能保護生態文化和維護生態平衡。因此,生態旅游與民族生態文化在本質上存在一致性,民族生態文化成為云南旅游業不斷發展的不竭動力。云南省打造的“麗江-大理-香格里拉旅游圈”已經是著名的旅游景點,充分發揮了民族生態文化的資源優勢,激活了少數民族地區的旅游產業的可持續發展,破解了一直以來制約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的交通、體制等瓶頸,推進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綠色經濟發展。
其二,社會價值。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促進社會發展進步的同時,在機械科學技術觀、急功近利傾向的影響下,人與自然走向了對立面,出現了“生態異化”現象。民族生態文化的原真性,使人與自然的良好互動關系得以存續,這將豐富綠色發展的途徑,并推進云南民族地區實現跨越式發展。民族生態文化喚起了人們對生態觀念的認同,民族生態文化的社會價值有以下幾方面:首先,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建設美麗云南。少數民族在長期與自然的相處中逐漸形成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民族生態文化,形成了一個全面的生態系統,維護著民族地區自然生態系統的平衡。而云南的綠色發展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實現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良性互動,并形成互惠共存、共榮共生的統一體,需要各個少數民族的共同參與和努力。其次,促進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有利于民族地區的社會穩定。民族生態文化滲透在少數民族的歷史發展中,是少數民族獨特精神特質的重要體現,是民族識別、民族認同以及身份認同的依據,是少數民族能夠不斷發展的關鍵性因素。民族生態文化貫穿在日常生產、生活之中,是推動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尤其是推動文化產業發展的核心動力。例如麗江、大理、香格里拉、普者黑等國內外知名的景點都在民族地區,這些景點之所以成為云南旅游的名片,成為人們出游的首選之地,與當地保留完好的民族生態文化息息相關。如果沒有生態文化思想熏陶的少數民族世代保護自然生態環境,在生產、生活實踐過程中遵循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發展規律,今天就不會有極具生態化的迤邐美景供人們欣賞。最后,推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各個少數民族在長久的發展實踐中積淀和傳承形成的民族生態文化,是少數民族的精神符號和靈魂,是維護民族團結、社會穩定、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的文化基礎。
其三,生態價值。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民族生態文化的主要內容,這種思想在人類發展的歷史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在當今的社會生活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文化仍然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各少數民族生存發展的物質基礎是自然生態環境,生態環境制約和影響了少數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的選擇。從一定意義上看,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生產方式、消費方式、集體人格和精神價值的重要體現。生態文化是一種力求實現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形態,致力于實現人與自然的共榮共生。民族生態文化是我國乃至全世界生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種蘊含民族精神價值、民族特色、生產生活方式的生態共同體。少數民族在民族生態文化的長期指引下,形成了具有各自民族特色的集體人格,這種集體人格具有濃厚的生態意識,使人們更愿意親近自然和保護自然,并且崇尚有節制的生活,禁止過多的向自然索取。民族生態文化倡導身體和心靈、人與自然、世俗生存和精神信仰之間的和諧,建立在這種和諧理念上的民族生態文化充分彰顯了少數民族的生態智慧,表達了少數民族和自然萬物之間最親密的關系,體現了人與自然之間最自然的本真狀態。少數民族生態觀認為人與自然界的萬物生靈是聯系在一起的,與所有的一切渾然相通不可分割,人是自然界的組成部分,人類的生存、發展必須依賴自然界,人與自然是有機統一的整體,人類尊重和善待自然,才能與之和諧共存共生。民族生態文化為現代人所向往的休憩之地和心靈回歸的訴求提供了精神指引,使民族地區得以保留著原生態的民族本真文化和環境。
綜上所述,在現代化、全球化浪潮沖擊之下,云南少數民族的生態文化及其資源價值適合以綠色發展模式實現民族地區的跨越式發展。與此同時,云南少數民族地區自然地理環境脆弱,這樣的自然環境決定了必須以生態文化為資源動力走綠色發展道路,從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社會發展共贏的角度考量發展模式。
四、結束語
云南是我國少數民族最多的省份,不管是從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利益考慮,還是從維護民族團結、實現共同繁榮出發,深度解讀和挖掘少數民族生態特征及其資源價值是民族地區實現綠色發展的重要內容。民族地區的綠色發展之動力,得益于民族生態文化所提供的穩固定力,民族生態文化獨特的精神特質邏輯自洽于民族地區社會的發展規律。民族生態文化需要綠色發展的育養與支撐,綠色發展同樣離不開對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特征和資源價值的挖掘,驅動民族生態文化價值轉化并服務于綠色發展,使民族生態文化內斂于綠色發展中,實現民族地區的可持續發展。
[1]李本書.善待自然:少數民族倫理的生態意蘊[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4.
[2]袁國友.中國少族民族生態文化的創新、轉換與發展[J].云南社會科學,2001.1.
[3]王永莉.試論西南民族地區的生態文化與生態環境保護[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6.2.
[4]鄧先瑞.長江流域民族文化生態及其主要特征[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6(11).
[責任編校:陽玉平]
F323.22;G812.4
A
1002-3240(2017)06-0152-05
2016-12-30
本人主持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少數民族地區民族生態文化與綠色發展互動關系研究,項目號[2016TS002],階段性成果;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五大理念”的制度實踐與美好生活的價值邏輯”項目編號(15ZDC004),階段性成果
龍麗波(1986-),女,彝族,云南紅河人,陜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15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吳若飛(1964-),云南人,副教授,云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黨委書記,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