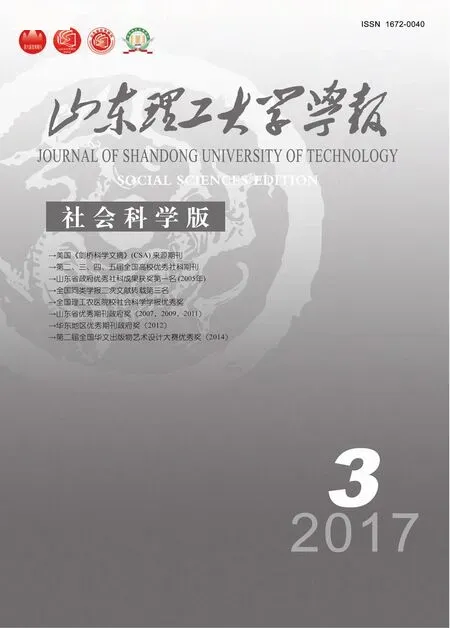魯迅與莫言文學創作思想比較研究
楊 超 高 (暨南大學文學院,廣東廣州510632)
魯迅與莫言文學創作思想比較研究
楊 超 高
(暨南大學文學院,廣東廣州510632)
魯迅與莫言分別揭示了國民的兩種“病癥”:國民劣根性與“種”的退化。魯迅以啟蒙的方法救治愚弱的國民,莫言卻是以野性精神來強化生命,有意味的是,他們表現出兩種相反的路徑:啟蒙意味著向“前”走出愚昧,而野性精神是向“后”借鑒原始生命力。無論如何,啟蒙與野性精神都是極有意義的療救之法,但也有必然的限度。
魯迅;莫言;國民劣根性;“種”的退化;啟蒙;野性精神
一、魯迅與莫言:影響與影響的焦慮
中國的現代小說成熟于魯迅,并達到了后人難以逾越的高度,魯迅開創的文學主題與資源也成為后人難以繞過的寫作傳統。莫言是當代最優秀、最富于個性的作家之一,尤其是獲諾貝爾文學獎后,更確認了他在中國當代文學中的獨特地位。魯迅與莫言是中國新文學上兩座高峰。莫言在多次講演與訪談中直言不諱地承認他的寫作受到了魯迅的影響,可以說,莫言很大程度上繼承了魯迅傳統,并有一定的創新;然而,在另一層面上,莫言又表現出迥異的姿態。
自20世紀80年代,劉再復就注意到魯迅與莫言的聯系。迄今30年,已經有更多的學者撰文研究莫言對魯迅的借鑒。如孫郁《莫言:與魯迅相逢的歌者》,《莫言孫郁對話錄》;吳義勤等《“吃人”敘事的歷史變形記——從〈狂人日記〉到〈酒國〉》;彭秀坤《魯迅〈故鄉〉與莫言〈白狗秋千架〉的互文性》;欒建梅《從“啟蒙”到“作為老百姓寫作”——莫言對魯迅文學傳統的繼承與創新》;張立群等《論莫言對魯迅傳統的繼承與創新》*孫郁:《莫言:與魯迅相逢的歌者》,當代作家評論,2006年第6期;《莫言孫郁對話錄》魯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10期;吳義勤等:《“吃人”敘事的歷史變形——從〈狂人日記〉》到〈酒國〉》,文藝研究,2014年第4期;彭秀坤:《魯迅〈故鄉〉與莫言〈白狗秋干架〉的互文性》,魯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10期;欒建梅:《從“啟蒙”到“作為老百姓寫作”——莫言對魯迅文學傳統的繼承與創新》,南京社會科學,2015年第1期;張立群等:《論莫言對魯迅傳統的繼承與創新》,河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等。二者的相通之處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吃人”文化與批判意識。魯迅在《狂人日記》中,揭示了數千年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藥》也寫到吃人血饅頭,這既是一種現象,更帶有深刻的文化寓意。莫言承續了這一主題,他的《酒國》也寫到“吃嬰孩”的現象,所揭露的是“人性中的丑惡和社會的殘酷”,《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等著也具有濃重的批判意識。莫言坦承“《藥》與《狂人日記》對《酒國》有影響”,“作品中對肉孩和嬰兒筵席的描寫是繼承了先賢魯迅先生的批判精神,繼承的好還是壞那是另外的事情,但主觀上是在沿著魯迅開辟的道路前進”[1]7。
其二,殺人主題:“看”與“被看”。《阿Q正傳》與《示眾》都涉及了殺人主題“看”與“被看”的二元對立結構,魯迅著重寫的還是看客:他們并非個人,而是群類;他們既是“看”者,也是“被看”者。莫言寫殺人,當數《檀香刑》。在一次談話中,莫言說到“《檀香刑》在構思過程中受到了魯迅先生的啟發。魯迅對看客心理的剖析,是一個偉大發現,揭示了人類共同的本性”[1]7-8。《檀香刑》殺人殘忍,又生出高超技藝與暴力美學。與魯迅不同的是,莫言雖也寫看客,但更著力寫劊子手(魯迅也寫劊子手,如《藥》中“滿臉橫肉”的“康大叔”,雖很傳神,卻不是小說著重刻畫的人物),將其作為第一主人公來寫,揭示劊子手的獨特心理。
其三,“離去—歸來”的敘述模式。魯迅的《祝福》《故鄉》都呈現出“離去—歸來(再離去)”的敘述模式,莫言的《白狗秋千架》(以下簡稱《白狗》)《大風》等篇,也有類似的運用。這種敘述模式,既有“外來者”(或“歸鄉者”)的外部視角,保持一定的觀照與敘述距離,又能夠“入乎其內”,利于敘說故事與表達深切感受。與此同時,在歸鄉者的身份設定上,他們也表現出相同的姿態與面貌:《祝福》中的“我”是知識分子,《故鄉》中的“我”被稱為“少爺”,《白狗》《大風》都是城市歸來的知識者。他們都以現代視野來看傳統鄉村,又以“離去—歸來”模式講述故事。
魯迅對莫言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甚至莫言也多次坦承他的寫作從魯迅身上汲取資源。只是這種影響并不是單方面的學習與借鑒,而是一種較為復雜的形態。必須注意到,莫言在某些方面走到了與魯迅相反的方向。這或許就是布魯姆所謂的“影響的焦慮”,前代先賢對后來者將產生一種具有焦慮感的影響。“取前人之所有為己用會引起受人恩惠而產生的負債之焦慮”[2]3,魯迅因自身的巨大貢獻、偉大意義與后人的造就(如毛澤東的夸贊與文學史的書寫),一度成為一個“神話”,莫言當然感受到魯迅對于自己的巨大壓力。他確實有著向魯迅學習,但絕不愿做魯迅的“亦步亦趨”者。其實,莫言的寫作對魯迅傳統也有有意的規避,他恣謔狂歡的語言風格與魯迅的冷峻凝練實不相同;同時,他在很大程度上將魯迅傳統予以“修正”,他將魯迅所不及的、未充分展開的細節進行放大,開拓成自己的寫作資源,如《檀香刑》中對劊子手心理的充分揭示。莫言曾說道:“我想,再寫看客,寫罪犯,魯迅先生在前邊佇立著。那我就想,魯迅先生作品中,似乎沒有特別多的描寫劊子手。《藥》里有一個劊子手康大叔,給華家送來人血饅頭那個,那么牛氣,活靈活現,但似乎沒有把這個人物充分展開。我想,如果在一部小說里,把劊子手當作第一主人公來寫,會非常有意義。通過魯迅作品我們可以知道看客的心理,也可以知道罪犯的心理,但是我們不知道劊子手到底是什么心理。而劊子手在一場殺人大戲里,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啊,是鐵三角的一個角啊。”(見《莫言孫郁對話錄》),如“作為老百姓寫作”命題的提出(區別于魯迅“為老百姓寫作”的“啟蒙”立場),如對于文體的特別追求,都具有創新意義,從而實現自我特色。莫言不能夠成為第二個魯迅,恐怕他也無意如此,正如孫郁所言,莫言與魯迅是“相逢的歌者”,他在魯迅傳統上,又生發出自己的特色出來,甚至在某些方面表現出迥異的姿態:他們的寫作立場與敘述風格都有極大的反差。
二、兩種“病癥”:國民劣根性與“種”的退化
魯迅對于國民的清醒與冷察無疑是深刻的,愛之深責之切,甚至“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3]291。在鼓吹“勞工神圣”與“新青年”的狂熱時代,魯迅卻執拗于挖掘與剖析國民的劣根性,意在改造國民的精神,“棄醫從文”就是一個極好的明證。當魯迅在日本仙臺學醫時,從“幻燈片事件”中目睹了國人在同胞被殺頭時圍觀看熱鬧的行為以及他們所表現出的麻木神情,深受刺痛,于是生發出“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4]439的悲感。因之,他的小說“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5]526。這就是對于國民劣根性的深挖與深思。
愚昧與麻木是國民劣根性的典型癥狀,這又具體表現為國民積習甚深的奴性與無聊的看客行為。在《故鄉》《祝福》等篇中,閏土與祥林嫂都深刻地表現出國民的奴性來,“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甚至“想做奴隸而不得”或只是“暫時坐穩了奴隸”[4]224-225。閏土的一聲“老爺”,深藏著巨大的冷漠與隔閡,它也顯示出一種不可喚醒的麻木,他的靈魂已死;祥林嫂“抗婚”與“捐門檻”,都可看作是她對禮教與神權的畏懼與遵從,她的奮力掙扎,竟也只是想坐穩了奴隸。《示眾》《祝福》《藥》也揭示出一種無聊又可悲可嘆的看客心理,他們是一群無名的“庸眾”,所看者,或是“庸眾”中的一員,或是“獨異個人”。“看”的姿態,也就昭示了他們的自私與冷漠、麻木與愚昧。《示眾》中的看客“怕失了位置”,里里外外圍了三四層;《祝福》中的男人女人甚至小孩也圍看著祥林嫂的悲苦,終于也露出幾分冷嘲熱諷。
瞞與騙也是國民劣根性的又一表現。“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4]254。魯迅曾苦索“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6]226,在他看來,我們民族最缺乏的便是誠與愛。《阿Q正傳》是魯迅對國民劣根性思考與批判用力最深的一篇,阿Q這一形象,表現出農民的愚昧與看客的無聊,他對于革命的理解也暴露出他的狹隘與自私;當然,阿Q的深刻更在于他自欺式的“精神勝利法”,諸如“我先前比你闊多了”之類的論調,其實是一種夸耀式的解脫與廉價的自我安慰。“愛”的缺乏表現為冷漠,諸多人物(如單四嫂、祥林嫂)的悲劇命運,也不能排除缺少他人必要的、愛的原因。
整體而言,魯迅筆下的人物是沉郁委瑣晦澀暗淡的,缺少希望與生命的光亮,“底層人物是悲苦無助的,他們往往沉默寡言,悄悄地陷入死亡的圈套;知識分子是迷茫的,軟弱的;權勢者是專橫和冷漠的”[7]5,在他們身上,魯迅認為都帶有劣根性。與之相比,莫言的文學世界卻是另一番喧鬧景象:他們同樣是身處邊緣、底層的小人物,他們敢愛敢恨,有勇有謀,從不妄自菲薄也決不可低估;他們始終奮力掙扎、頑強生存,奏響了一曲曲可歌可泣、動人心魄的生命樂章!如果說魯迅對于他的“國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莫言則是用一支濃墨重彩的筆,塑造出他的理想人性。然而,從另一意義上說,莫言對于“英雄”群像的極力塑造,隱含的恰恰是他對于當下“種”的退化的關注與思索。
莫言筆下的人物,大多帶有強烈的原始性,也寓意著一種蓬勃有力的生命意識,紅高粱家族的英雄好漢們是如此,敢作敢為的司馬庫是如此,上官家族的母親與女兒們是如此,施刑臺上毫無懼色的“犯人”是如此,甚至輪回于生死間的驢牛豬狗也是如此。典型如《紅高粱家族》,“我爺爺”“我奶奶”甚至“我父親”一輩,他們個個都是英雄好漢,個個都譜寫了生命壯歌。余占鰲的一生,就充滿了許多壯舉:捏小腳、殺劫盜土匪、帶領隊伍伏擊日本人,尤其是在高粱地里的野合,更洋溢著他強烈的生命欲望與濃郁的野性氣息!可是,正是在先人強大的生命力面前,莫言越發察覺到當下的“病癥”,誠如他的慨嘆:他們殺人越貨,精忠報國,他們演出過一幕幕英勇悲壯的舞劇,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相形見絀,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地感到種的退化[8]4。
誠然,《紅高粱家族》以一種間接方式,在突顯祖輩旺盛生命力與壯烈的生命歷程中,反襯出子孫后代的精神孱弱。而《食草家族》則直接地表現了“食草家族”的生命萎縮與衰退。《豐乳肥臀》中上官魯氏不惜四處借種而得的唯一兒子,卻是一個懦弱無為、患有戀乳癥的“雜種”,他身上缺失著上官家族女性以及司馬庫等類的剛毅性格。《生死疲勞》西門鬧六道輪回先后化為“西門驢”“西門牛”“豬十六”“狗小四”“猴”“世紀嬰兒”,從動物到人,從倔強生命到病態嬰兒,是一個生命弱化的歷程,這也正昭示了“種”的命題。
“種”的退化是莫言小說的一個重要命題,既指向現實問題,又表達出特定的歷史觀念。莫言著重從時間(歷史,如“我爺爺”“我奶奶”)與空間(地域,如高密東北鄉)概念的轉換,從正面的揭示與反面的襯托,來找尋富于強力的生命之“種”。“我有時忽發奇想,以為人種的退化與越來越豐富、舒適的生活條件有關。但追求富裕、舒適的生活條件是人類奮斗的目標又是必然要達到的目標,這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個令人膽戰心驚的深刻矛盾。人類正在用自身的努力,消除著人類的某些優良的素質”[8]137。這其中,既有他的深刻困惑,更包含了巨大的憂患意識。
魯迅與莫言年齡相差73歲,“國民劣根性”與“種”的退化這兩個命題,也是基于不同時代、不同社會語境的不同認識:“國民劣根性”是一種有著漫長歷史,漸漸形成而又積習太深的人的惰性與陰暗面;“種”的退化是一種在現代文明進程中被“閹割”的生命狀態。魯迅對“國民劣根性”的剖析與莫言對“種”的退化憂患,其指向也有幾分相似,魯迅多注意國民精神與性格,莫言更關注生命層面。總括而言,他們所揭示的都關乎人性,是針對于精神與肉體的病態或殘缺。這二者都是特定時代(或者也是普遍時代)國人不可忽視的“病癥”。
三、兩副“藥方”:啟蒙與野性精神
魯迅是以啟蒙的方法來救治愚弱的國民。何謂啟蒙?簡言之,啟蒙(Enlighten)是使人擺脫愚昧和迷信。它的詞根是“light”,也即燭照與光亮之意。魯迅是一個真正的啟蒙主義者,他也從來沒有放棄過這種啟蒙立場,在其后期雖知啟蒙的艱難,卻仍抱著不愿破滅的希望,沒有從根本上否認啟蒙的意義。誠如魯迅所說:“幸而誰也不敢十分決定說:國民性是決不會改變的。在這‘不可知’中,雖可有破例——即其情形為從來所未有——的滅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復生的希望。”[3]18當然,也有研究者認為魯迅“始終把自己當作邊緣人,自我流放在社會底層,不找導師,也不當導師”[1]12,我以為這一觀點可以商榷。魯迅是啟蒙者,代表著一種精英文化,他所指向的對象才(主要)是社會底層;同時,魯迅也一直意識到自己是時代的先驅者,他在“鐵屋子”的譬喻中,以“現在你大嚷起來”標示了自己的先覺者與先驅者的身份。
在《〈吶喊〉自序》《我怎樣做起小說來》中,魯迅也談到小說創作的緣由,他認為“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4]439“說到為什么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可見,魯迅將小說作為啟蒙與改造國民性的工具,因之,“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為‘閑書’,而且將‘為藝術而藝術’看做不過是‘消閑’的新式別號”,“我也并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里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5]525-526正因為此,他的小說有強烈的批判意識:一指向社會,尤其是封建社會中不合理的現象與落后的傳統;二指向國民的精神,即對國民性的批判。通過小說,魯迅旨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狂人日記》揭示“吃人”傳統,《阿Q正傳》《祝福》《故鄉》《藥》等篇,也書寫了形形色色卻又本質相同的病態國民。魯迅以他的深刻察覺與清醒文筆,寫出阿Q的落后、不覺悟、自私、冷酷、虛偽、怯弱、自輕自賤與自欺自慰等弱點;揭示出祥林嫂悲劇命運的外部緣由與自身原因;表現出華老栓、閏土的冷漠與愚昧,他們安于天命,安身為奴。
魯迅在對國民弱點的批判中實現他的啟蒙思想,但批判只是啟蒙的一個方面,他也曾提出“立人”的理念:“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4]58“立人”是魯迅對于“新人”(不同于有劣根性的國民)的一種設想,它在于“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而所立之人,是注重個性與精神,帶有“摩羅”“超人”氣質的人,這正是《吶喊》《彷徨》里面眾多人物所不具備的素質。相對而言,魯迅“破”有余而“立”不足,他花費更多精力在于挖掘、剖析國民性劣根,對于“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的問題缺乏有力回答。
有意味的是,對“種”的強化,莫言所走的路與魯迅恰恰相反。莫言通過野性精神的呼喚,來鍛造生命的強度與硬度。野性是一種未經馴順、蓬勃野蠻的狀態,具有很強的原始傾向。它表現在對尚武精神、狂躁暴力的推崇,對旺盛生育力的贊美,對倔強生命力帶來的震顫的癡迷,或許正是這無端殺戮(如余占鰲)、“動物式”的生命繁衍(如上官魯氏)與在蠻荒之境與生命極限中奮力掙扎、搏斗(如孫丙),才更能顯現亢奮的血性精神與頑強的生命意志。“種”與性欲有著本質的聯系,因為生命本身的欲求也與生命力緊密相連。在莫言筆下,那些強勁有力的人“種”,那些蓬勃野性的生命,總暗含著不可抑制也無須抑制的性愛行為。余占鰲如此,司馬庫亦是如此,甚至那些女性也因不羈的性愛而為自身抹上一筆重彩。另外,莫言也從未經馴化的動物(驢、牛、豬、狗、蛙等類)身上汲取野性精神,它們的熱烈沸騰喧囂狂野,無疑都成為反觀人類的鏡子,它們以壯烈的生命演繹來啟示人類怎么才是優秀的“種”,怎樣才算是強力的生命。
莫言回答了這個問題。濃密而挺拔,如同焰火又似鮮血的“紅高粱”就是一種強勁、純正的“種”,它也是“我們”家族(民族)精神的象征:“一方面它是人與自然契合冥化的象征;另一方面,它也象征著偉大的民族血脈、靈魂和精神。”[9]146莫言說,“我痛恨雜種高粱”,二奶奶墳頭“秸矮、莖粗、葉子密集、通體沾滿白色粉霜、穗子像狗尾巴一樣長”的雜種高粱正喻示著“種”的退化,而紅高粱才真正象征著強盛的力與旺盛的“種”。因此,整個家族亡靈,對“我”發出了追找純種紅高粱與原始生命力的啟示:在白馬山之陽,墨水河之陰,還有一株純種的紅高粱,你要不惜一切找到它。你高舉著它去闖蕩你的荊棘叢生、虎狼橫行的世界,它是你的護身符,也是我們家族的光榮的圖騰和我們高密東北鄉的傳統精神的象征[8]351。
在相似的“病癥”下,魯迅與莫言所給的兩副“藥方”竟然如此不同,他們走向了兩個相反的方向。魯迅意欲用啟蒙之光來醫治麻木、愚昧的國民,啟蒙在于從黯淡走向光明,走向“自由”“平等”“民主”“科學”,魯迅的“藥方”是引入現代的概念、方法,引導國民“向前走”,走出封建愚昧淹人甚深的泥潭。而莫言卻表現出明顯的“向后走”的傾向,他從先祖與動物身上借鑒有益的精神資源,為實現生命的強化而不惜回到人的原始階段,強調一種桀驁不馴、放蕩不羈與自由自在的野性生命形態。甚至他發現文明進化與“種”的退化的悖論,他走的是與現代文明相反的一條救贖之路。與此同時,魯迅尊崇理性、啟蒙、現代等觀念,其核心也是理性,有理性方能驅除封建與愚昧,才能使國民成為合理又健全的人。莫言所引用的“藥方”卻是非理性的,野性精神其實也意味著無端無理無拘無束甚至無法無天,似乎只有打破理性束縛,生命才可無所顧忌地張揚與怒放。
四、啟蒙的限度與對野性精神的思考
啟蒙是有意義的,但卻也有限度。康德對于啟蒙的理解應該是可以借鑒的,他認為啟蒙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10]22,這就表明了啟蒙不能只靠他人言說,而須自救。魯迅也反對所謂的“導師”,認為他們“圓穩而已,自己卻誤以為識路。假如真識路,自己就早進向他的目標,何至于還在做導師”[3]58。“聽將令”也好,抱著一絲一縷的“毀壞這鐵屋子的希望”也好,無論如何,魯迅還是走在啟蒙的狹路上,這或許是他的使命,多少有一點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意味,因此,他也飽嘗寂寞、悲哀、失望乃至絕望,魯迅自己也曾感嘆道:難道所謂國民性者,真是這樣地難于改變的么?[3]18這恐怕是一個悲涼的事實,從現實的角度上說,他們(包括魯迅)的啟蒙并沒有取得相應的效果,更甚至他們“希望以現代性精神改變鄉村,啟蒙農民,但是,從歷史上看,作家們沒有改變鄉村,倒是作家自身精神受到了改變”[11]194。
其實,魯迅對于國民性批判的啟蒙路徑不乏懷疑和反思,他的小說本身也詮釋了啟蒙的限度。其中的知識分子——“我”(《故鄉》《祝福》)、魏連殳、呂緯甫——無一不是以失敗告終,“我”與閏土之間存在一堵厚墻,“我”也不能回答祥林嫂“人死后有沒有靈魂”的問題,魏連殳與呂緯甫也都失了昔日的顏色:他們與群眾之間有著不可化解的隔閡,更無力拯救,甚至他們在冷漠與隔膜中碰撞而敗下陣來,再沒有啟蒙的勇氣,成為徹徹底底的邊緣人。《藥》更有啟示意義,它所反映的是“獨異個人”與“庸眾”的關系,揭示啟蒙者的悲劇,更揭示被啟蒙者的悲劇。對于靈魂徹底死去的愚昧者而言,即便是犧牲生命的啟蒙也毫無意義。革命者夏瑜肉體被殺,人血被吃,他從群眾那換取的竟是“瘋了”的罵名,這是何等的悲哀。誠如宋劍華所言:死者的“無辜”與生者的“無知”,是無“藥”可救的“國民性”痼疾[12]103。
頗有意味的是,莫言在《作為老百姓寫作》一文中也表達出他對啟蒙立場的否定。“對那種自認為比別人高人一等,自己把自己當救世主,自認為比老百姓高明,自認為肩負著拯救下層人民重擔的作家,我很反感。”[1]12當然,莫言并沒有具體指向魯迅,而且也只是對當今語境下而言,但在一定意義這也是上對啟蒙的一種反思。不僅如此,莫言所引入的野性精神也同樣需要作深入思考。
野性精神正如其名,“野”就意味著形態復雜,其內容難以收束,倘若不加分辨地引用,恐怕也會造成相應的問題。莫言對人的動物本能、生命原欲的書寫幾近癲狂,最典型的是性愛,他也旨在以性愛來表現生命力。但是,性愛(甚至暴力)只是生命的本能,而非生命本體,也絕不是生命的意義所在。莫言在糾偏中走到了“種”的退化的另一極端:生殖崇拜與性愛崇拜。他的筆下有諸多生殖器描寫,甚至也常有割生殖器的書寫——這恰恰是對生殖的敬畏與贊頌:要毀滅一個人,便要將他最偉大的東西毀滅。他也樂于寫狂野的性愛,在融于天地的野地里(高粱地、黃麻地、棉花垛)交合,將人的野性發揮到了極致。同時,野性精神意味著不受束縛、自由自在,它是在“規范”與“秩序”之外,是有破壞傾向的強力,對于野性精神的過分強調,必然造成倫理的混亂,因為倫理本身就是去“野”就“正”,現代文明也意味著對野性的剝離與壓制。暴力(如《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等)與亂倫(如《豐乳肥臀》《生死疲勞》《蛙》)及與過多的丑(如《紅蝗》《紅高粱家族》)的展示,都是莫言小說的顯在問題,更甚至,莫言還有意擱置價值評判,多少造成了價值失范的遺憾。過度的暴力、殺戮與嗜血,即便成就了血淋淋的英雄好漢,卻也有無數生命如同草芥成了冤魂;無序的性愛,熱烈而迷醉,雖然在毫無遮掩、毫無禁忌中釋放灼熱的生命激情;同時也在原欲之火中燒毀了所有的文明。當然,我們也可以說,他的獨特成就與現在缺陷都源于此。
其實,啟蒙與野性精神都是一種極有意義的療救之法,二者在社會的進變與人的衍進中,起到了很大作用,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啟蒙是有限度的,對于野性精神也需要有清醒的認識,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才能更好地借鑒魯迅與莫言所走的路,繼續思索“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這一命題。
[1]姜異新.莫言孫郁對話錄[J].魯迅研究月刊,2012,(10).
[2]哈羅德·布魯姆.影響的焦慮[M].徐文博,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
[3]魯迅.魯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4]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5]魯迅.魯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6]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魯迅研究月刊》選編.魯迅回憶錄:上[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7]馬海良.從魯迅的“立人”到莫言的“活人”[J].中國作家,2013,(4).
[8]莫言.紅高粱家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9]楊揚.莫言研究資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10]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
[11]賀仲明.一種文學與一個階層——中國新文學與農民關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2]宋劍華.啟蒙無效論與魯迅《藥》的文本釋義[J].天津社會科學,2008,(5).
(責任編輯 魯守博)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u Xun’s and Mo Yan’s Creative Ideology
Yang Chaogao
(Collegeofliberalarts,JinanUniversity,GuangZhou510632,China)
Lu Xun and Mo Yan exposed two kinds of “disease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ty: the national weakness and the degradation of ethnic group. Lu Xun treated the national stupidity with enlightenment, however, Mo Yan is to make the life robust with wild spirit. It is meaningful that they have exhibit two opposite paths: enlightenment means going forward and out of ignorance, while the wild spirit means moving backward to attain the primal vitality. Anyway, both enlightenment and the wild spirit are extremely meaningful methods of treatment, however they also have a certain limit.
Lu Xun; Mo Yan; national weakness; degradation of ethnic group; enlightenment; wild spirit
2016-12-03
楊超高,男,江西撫州人,暨南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I210.96
A
1672-0040(2017)03-006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