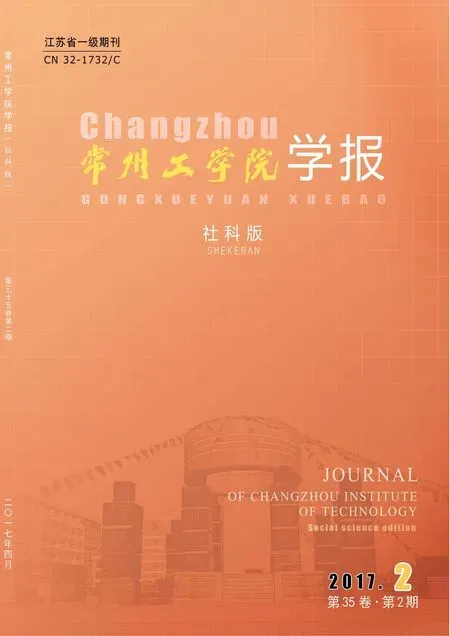從成語視角看張愛玲《傾城之戀》的敘事設置
錢亞玲,陸克寒
(常州工學院教育與人文學院,江蘇常州213022)
從成語視角看張愛玲《傾城之戀》的敘事設置
錢亞玲,陸克寒
(常州工學院教育與人文學院,江蘇常州213022)
文章從漢語成語“傾城傾國”的語源和語用角度,結合文本的細讀,探析張愛玲小說《傾城之戀》的敘事設置。張愛玲通過演繹一個現代“傾城”的“傳奇”,表達了她對諸多歷史“傾城傾國”事件的質疑,對古老的“紅顏禍水”思維定勢的顛覆,也正是通過這一藝術化的解構過程,張愛玲表達了她的現代女性觀。
成語;傾城傾國;敘事設置
談到語言在社會生活與文化傳承中的作用,現代小說名家張愛玲曾有過文學性的表述:“中國人向來喜歡引經據典。美麗的、精辟的斷句,兩千年前的老笑話,混在日常談吐里自由使用著。這些看不見的纖維,織成了我們活生生的過去。傳統的本身增強了力量,因為它不停地被引用到新的人,新的事物與局面上。”①她特別提及成語與現代中國人的親密關系:“但凡有一句適當的成語可用,中國人是不肯直接地說話的。而仔細想起來,幾乎每一種可能的情形都有一句合適的成語來相配。”②“我國近年來流傳的雋語,百分之九十就是成語的巧妙的運用。”③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以小說創作見長的張愛玲顯然也是運用現代語言的大師,對漢語的拿捏純熟,老到。不難發現,在張愛玲諸多現代“傳奇”敘事中,作為漢語語匯精華的成語被頻繁地運用,俯拾即是而又精彩紛呈,鮮活又恰到好處。
作為文化的載體,成語素有中華文化“活化石”之稱,生動形象地折射了民族文化和社會歷史。在運用民族語言從事小說創作時,得力于深厚的中國古典文學積淀、西方文化的吸納滋養和東西方文化背景的對照,張愛玲對漢語語言尤其是成語的理解、引用和演繹,也鮮明地折射出張氏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意識,發表于1943年9月的中篇小說《傾城之戀》堪稱其中的經典實例。這個文本較之張愛玲其他小說,至少有三點非同尋常。第一,它是張愛玲的成名作,但當時受到著名翻譯家兼文藝批評家傅雷先生較為嚴苛的批評。第二,張愛玲幾近同時(亦即1944年)又將它改編為四幕八場話劇,并于上海新光大戲院上演,映現了張氏本人對這部小說的厚愛。第三,故事以大團圓的喜劇形式收場,這在以“蒼涼”為底色的張氏小說敘事中實不多見。不過在我們看來,這篇小說還有一處意外,在于結尾: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誰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跟著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
傳奇里的傾國傾城的人大抵如此。
不知張愛玲是擔心讀者疏漏,還是低估了讀者的理解力,作了一番本該略去的絮叨,多少有損文本的余韻。我們認為,正是作者的“畫蛇添足”,導致這個結尾未被充分地釋讀,成了“顯在”的“盲區”,通過這些貌似“多余的話”,張愛玲分明在強調自創的“傾城”與歷史上“傾城傾國”史實的關聯與對照。回歸文本可以發現,張愛玲意欲通過演繹一個現代“傾城”的“傳奇”,表達她對歷史上“傾城傾國”事件的質疑,對古老的“紅顏禍水”思維定勢的顛覆,也正是通過這一藝術化的解構過程,張愛玲表達了她的現代女性觀。
一、成語“傾城傾國”語源與釋義
《傾城之戀》篇名出自成語“傾城傾國”。《詩經·大雅·瞻卬》:“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意謂有才的男子可稱霸王,有才的女子使國覆亡,婦人有才便如梟如鴟,花言巧語善于說謊。禍亂不是天降,而是出自婦人一方,也不是他人的教誨,只因貼近女子紅妝。整首詩歌諷刺周幽王寵幸褒姒,荒政滅國,這是“傾城”一語的最早出處。
漢代班固《漢書·孝武李夫人傳》記載,李夫人的哥哥李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因為愛悅佳人之深而使得城與國傾覆,后人自此便用“傾城傾國”一詞形容女子容貌的絕美。又據班固記載,漢武帝聽罷李延年之語感嘆:“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公主告訴他,李延年的妹妹正是這樣的一個絕代佳人,于是,“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這位受寵的美人便是后來被尊為孝武皇后的李夫人。
漢代袁康所作《越絕書·外傳計倪》亦云:“禍晉之驪姬、亡周之褒姒,盡妖妍于圖畫,極兇悖于人理。傾城傾國,思昭示于后王,麗質冶容,宜求監于前史。”古人顯然極其重視歷史教訓的歸結,最后達成共識:泱泱邦國的傾覆,多與女子尤其是妖妍的女子相關,她們貌美,但通常心狠手毒,不恪守人倫,故面對絕色的女子,無論君臣都要以史為鑒,免蹈歷史的覆轍。然而,歷史偏偏總以相似的面目輪回,繼驪姬、褒姒之后,有西施之于吳王夫差,貂蟬之于董卓,楊玉環之于唐玄宗李隆基……,男人們斷送了江山偉業,古人進一步歸納,得出更為明確的論斷:紅顏乃禍水也。檢視中國的社會歷史不難發現,從驪姬到楊貴妃,這些絕美的女子,幾近個個身敗名裂,背上了恥辱的罵名。
從“傾城傾國”的語源以及后人使用的情形,我們至少可以發現以下三點。第一,中國人不論男女,自古便對女子的外在美有著感同身受的體認。第二,在古人的理念中,何種女子謂之美?首先要經得住視覺的檢驗,要有閉花羞月、沉魚落雁之貌,然而僅外在好看還不夠,假如內里有才華有技能,譬如能歌善舞,精通音律,或能說會道,才是風華絕代。第三,絕美的女子多巧言令色,每每使帝王耽溺其間,輕則腎虛體虧無力朝政,重則亂政而誤國,最終導致國家覆滅。由于女子美貌潛伏著危險,具有殺傷力,出于恐懼心理和警戒的意圖,古人便用“傾城傾國”指代女人的絕色,直陳其造成的嚴重后果。
今人看來,古人貌似合乎邏輯的推斷,其實是經不起論證的,他們借以推斷的事例僅為歷史長河中的個別和偶然,美顏與政權大廈的顛覆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更何況在一個女性歷來被“消聲”的男權專制社群。將家國的傾覆毀滅歸于“紅顏”之罪,不僅有失公正,一定程度上折射了社會中心地帶男人擔當意識的缺席和主體意識的萎縮。
二、白流蘇:寡婦再嫁
張愛玲《傾城之戀》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同步行進,城邦與家國正處于傾覆之中,20世紀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的中國,從北到南由東向西,一路淪陷,愛情的故事便發生在這個惶惶的動蕩背景下。動蕩慌張的亂世背景的設置,初步顯露了張愛玲意欲背離傳統“傾國傾城”故事模式。
故事中的女主角白流蘇亦非風華絕代,從傳統世俗的角度看,白流蘇不過是個寡婦,張愛玲要講述一個寡婦再嫁的故事。小說伊始的“報喪”情節,顯示了女主人公生存現狀的不容樂觀——“離婚”而后“返家”,她的家是一個跟不上時代彌溢著腐味暮氣的舊式家庭。毋庸置疑,在男權中心的家長制家庭,“失婚”對女子又意味著事實上的“失家”。白流蘇離婚的主因是丈夫“當初有許多對不起”她的地方,“兩個姨奶奶”的存在,讓白流蘇守著“活寡”。現在,前夫死了,本應和她無關,但是,兄嫂所堅守的“天理人情,三綱五常,可是改不了的”,一致認為流蘇“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離異后的流蘇成了真寡婦。俗世的經驗表明,一個待字閨中相貌平常的女子要嫁人幾乎沒有難度,一個漂亮寡婦再嫁也沒有太多困難,是寡婦又長相一般且生于亂世想要再嫁,難度就非同小可。小說標題給了讀者無比美好的閱讀期待和跨越時空的藝術想象,而事件的核心人物的身份卻如此平凡、低微,乃至“另類”。張愛玲顯然有備而來,鉚足勁要講述一個現代版的“傾城傾國”傳奇。
“離婚”,折斷了白流蘇通往未來人生的理想翅膀,而現實又不予她立足之地,浮在半空的流蘇“覺得自己就是對聯上的一個字,虛飄飄的,不落實地”。然而,白流蘇的“心虛”,不僅緣于現實中無定位,生活上缺乏物質長久的支撐,更在于“離婚”女子的心理禁忌。小說借四奶奶之口,傳達了現世社會對失婚女子和寡婦們的成見:“她一嫁到了婆家,丈夫就變成了敗家子。回到娘家來,眼見得娘家就要敗光了——天生的掃帚星!”“離婚”成了“不吉不祥”“不潔”的代碼,白流蘇聽后“氣得渾身亂顫”,表明在心理上她難以逾越這一傳統的惡俗陋見。離婚,寡婦,不復年輕,“又沒念過兩句書”,白流蘇的人生將從這里重新開啟,張愛玲的故事打這兒開場,這場傾城的戀愛該何去何從?小說一開始,觀者就得屏氣凝神,張愛玲不愧是講故事的高手。談到寫小說,張愛玲曾直陳:“是個故事,就得有點戲劇性。戲劇就是沖突,就是磨難,就是麻煩。”④距離歷史上“傾城傾國”的標桿越遙遠,預示即將到來的磨難越深重,白流蘇得付出超乎常人的努力,一路披荊斬棘方能殺出一條生路。
事件的進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白流蘇最后收獲了婚姻,成了華僑商人范柳原名正言順的妻子。頑固的遺老遺少與現代洋派,半老的寡婦和年輕的商人,熟悉的故土與陌生的香港,這些參差的對照,著實迷離了人們的眼睛。然而在小說中,事件的進展又如此地合情合理。梳理白流蘇經歷的各種磨難,她的圓滿歸結于作家張愛玲設置的兩個關鍵點:其一,和范柳原初識時的共舞,其二,香港周旋之際心智的發揮。這兩個關節點的設置,既折射出張愛玲對歷史上諸多“傾城傾國”故事某些質素的揚棄,又傳達出作家主體的現代女性意識。
范白之戀發于白流蘇陪妹妹與范柳原相親,為了敷衍面子,白流蘇和范柳原跳了幾次舞而為范柳原所注目,妹妹的親事由是告吹,被眾人目為敗柳殘花的白流蘇進入公眾視野,在此,技藝打敗了年齡,外形屈服于質里,這與歷史上的傾城絕色形成了某種遙遠的回應。驪姬、褒姒、西施、李夫人、趙飛燕、楊玉環,無不能歌善舞,乃至身懷絕技。以現代眼光觀之,這些絕色的美女,原來都有一技之長,而不只是瓷質“花瓶”。面容姣好的女子天下有的是,為何獨獨她們成了帝王將相身旁的寵兒?古人崇尚母儀天下,顯然強調的還是舉止的風范。如是看來,單憑“紅顏”便定為“花瓶”“禍水”,未免武斷,實在是委屈了歷代的美女子,也低估了歷代帝王的治國用人之道。歷史證明,女子欲立足社會,尤其欲立足于男權中心社會,核心要素是內里,靠才藝。歷史的發展同時證明,女性的才能于人類物種的繁衍和社會文明的演進意義非凡。故張愛玲于20世紀40年代毫無掩飾地說:“女人取悅于人的方法有許多種,單單看中她的身體的人,失去許多可珍貴的生活情趣。”⑤與其說這是女性的自白自賞,毋寧說是張愛玲對男權中心社會的揶揄和警醒。
即便如此,“女人無才便是德”的女性觀代代相承,女性的才能,自古被歷史歪曲,擱置,蔑視。白流蘇僅因能舞,搶了妹妹的風頭,攪黃了一場媒妁之約,在兄嫂看來便是“失德”。事實上,白流蘇的舞技顯然還不足以贏得范柳原的傾心,對于一個留過洋的新派人物,見識過的“舞女”實在太多,譬如,小說中的配角——印度女人薩黑荑妮便是一個舞林高手。白流蘇征服范柳原的殺手锏是智慧,女性的智慧——在社會邊緣和屈辱生活中累積的生存經驗、人生見識和觀世心態。女性的智慧向來被男權中心社群所無視,即便沐浴著現代科學文明之光,女性的智慧在現代社會仍遭低視,傅雷批評《傾城之戀》的缺陷在于“兩個主角的缺陷”,認為他們都是“渾身小智小慧的人”,尤其是白流蘇,“‘沒念過兩句書’而居然夠得上和柳原針鋒相對,未免是個大漏洞”⑥。傅雷顯然疏漏了一個常識,人類的智識包括書本知識最終源自生活經驗和人生的歷練,白流蘇固然不是腹有詩書的女子,但離婚、返回母家、遭兄嫂攆趕等各種人生逆難,于白流蘇等無數傳統中國女性都是磨礪,更是心智的沉積,只是在一個歧視女性歷史悠久的社會,女性的智慧連同女性的身體,被無情地遮蔽,更被殘忍地剝離。
換言之,在巨大的生存危機面前,徐娘半老的白流蘇比待字閨中的妹妹們更沉穩、老到,也更有膽識與勇氣。張愛玲為白流蘇設置的赴港之旅,較為逼真地呈示了一個被逼到生存絕境的女子雙手辟開生死路的決絕與勇猛,在所謂“玩世不恭的享樂主義者的精神游戲”⑦中,張愛玲透過細膩的人物心理活動,呈現了傳統中國女性在歷史積壓之下練就的生存智慧,它們無疑是“近乎病態的社會的產物”⑧,自然免不了有些扭曲與畸形。
三、范柳原:浪子回歸
原本,一個女子的容顏和國家的傾覆,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情,用“傾城傾國”的狼藉和危重來贊譽一個女子的美色,實在有些荒唐,但古人又云“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兩者發生關聯和纏繞,一是借助女子的巧言,二是靠男人的傾聽和吸納,說者和聽者都不可或缺。縱覽中國社會歷史,從驪姬、褒姒,到趙飛燕、楊玉環,個個擅長在帝王耳旁“吹枕邊風”,從商紂到唐李隆基,個個又都是“聽話”的君王,于是悲劇便發生了。中國古人用“傾城傾國”的廢墟之象,警示后人紅顏所招致的駭人圖景,流露出強烈的譴責之意,看似驚嘆女性的絕美,暗含對女性的諷刺和對女性形象的歪曲。作為一國之君的帝王,才是掌握歷史走向的核心質素,而將國家政體的傾覆和毀滅歸咎于女子,實質上抹煞了無能的覆國之帝本該承擔的歷史罪責,反映了中國傳統社會絕對的男權中心地位及其對女性的凌辱與歧視。無數的史實證明,女性在長期的歷史積壓中,不僅塑造了自身,強健了心智,還憑借生命的本體特質和才智影響,改造乃至凈化了男人及其世界,成為拯救父權社會的無形之力。歷史上固然存在家國社稷因“紅顏”而傾覆之諸多偶然,但又存在凡夫俗子因“紅顏”而建功立業之現象。“浪子”在“紅顏”的影響下脫胎換骨,皈依人生之途,是張愛玲諸多篇什演繹的又一主題,《傾城之戀》中范柳原這一人物形象,正體現了作家張愛玲這一現代女性意識。
在張愛玲文壇知己蘇青看來,范柳原只是“一個華僑的少爺,嫖賭吃喝樣樣都來……”⑨,蘇青的評價有失全面,吃喝嫖賭、玩世不恭只是其表象,確切地說,范柳原本質上是一個自暴自棄的浪子。范柳原沒有歸宿,但與白流蘇的“失婚”導致“失家”不同,他的心結與隱痛是“無家”和“無國”所致的無根浮游狀態。首先,他是個“無家”的“棄兒”。范柳原是父親與一位華僑交際花的庶出,依照中國人傳統,他仍是范氏家庭的一分子,在法律上仍有繼承權,但由于族人的報復思想與敵視的態度,范柳原自小在英國長大,及至而立之年,依然得不到族人的認同,所以,范柳原喪失了作為男性所擁有的對于“家”的絕對占有權。其次,范柳原又是一個“無國”者。在中國人視界中,范柳原寄居英倫多年,是位地地道道的“洋派”人物,“不能算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其生活習慣、行為舉止、思維方式都很難被中國舊式家庭所認同,而另一方面,無法更改的外形氣質、性格嗜好,又使范柳原難以被外族所接納。如同無根的浮萍,范柳原四處流浪,“無家”“無國”的雙重失落,顯然給予他很深的內心創傷,放浪形骸的生活便是發泄情感的一種表征,當然,土生土長的中國婦人白流蘇根本無從體認他“家國認同”的焦灼和思想意識的危機。在小說設置的多個范白兩人對話場景中,范柳原文雅而高深的言語在白流蘇聽來莫名其妙,與其說這樣的情境彰顯了白流蘇“骨子里的貧血”,毋寧說這是張愛玲為其男性主角精心設置的獨語舞臺,藉此展覽一個漂泊浪子內心的迷茫、困惑與期盼。
家國認同的缺失,既造就了范柳原“浪子”的身份,又使他與人交往時難有誠意和責任意識。與白流蘇交往之初,范柳原潛意識中,便欲將白流蘇變成他眾多情人中的一分子,那么,是什么促使范柳原由最初狎玩到后來莊重心理的逆轉?吸引范柳原的是白流蘇“那一低頭的溫柔”,白流蘇這個充滿個性特質的小動作,暗合了他想象的中國女性獨有的風韻與魅力,換言之,范柳原眼中的白流蘇是“一個真正的中國女人”,她點燃了范柳原家國認同的欲望之火,強化了其民族認同感,范柳原要借助這個真正中國女人實現自己的中國人身份認同。
白流蘇并不是圖畫上妖妍的畫像,亦非美麗的幻影,她是實在而平凡的。前文已述及,白流蘇離過婚,守著寡,被目為枯枝敗柳與不祥的災星,比照異國搖曳生姿、性感年輕的薩黑荑妮,也沒有驚艷的外表,但中國女人白流蘇有的是本分和內斂,優雅和謹慎,她恪守著傳統的忠貞,執著于安穩的家庭生活理想。她外在柔弱而內心隱忍、堅毅,充滿智慧。她又很勇敢和無畏,為了婚姻和家庭可以孤注一擲甚至生死不顧……白流蘇身上呈現的中國傳統女性的特質給變動不居、內心孤傲的范柳原未曾有過的踏實、溫暖與親切,使他對人倫關系和現實生活有了新的體認。正是白流蘇,使飄浮的范柳原回歸自己的家園,也是白流蘇,使范柳原回歸了平凡而健康的日常生活,開啟了未來人生的行程。
故事圓滿收場,但“流蘇并不覺得她在歷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點”,這是傳統女性普遍存在的自視盲點,這無疑也是女性經年被遮蔽置于邊緣、被“妖魔”化的歷史之必然。然而,張愛玲是清醒的,她用文字還原出日常的真實和女性存在的真實:有多少白流蘇似的女子將范柳原樣的男人從晝夜顛倒的無序帶進有序的日常,把放浪形骸的男人從自我放逐中拯救出來。什么比拯救一個男人的靈魂更有意義?又有什么比促使一個男人向上向善地生活更有價值?拯救,無疑是女神之舉,不能無視女性的拯救之力和存在之美。慶幸的是,古今中外的不少文學經典,都曾觀照女性的拯救之行,張愛玲當屬其一。檢視張愛玲筆下的女性世界,只有強壯、安靜、踏實、充滿母性的地母才是最美女神,因為是她拯救了大地,象征了重生和希望。
四、結語
與其說是香港的淪陷成全了白流蘇,不如說是白流蘇向死而生的決絕、勇猛和智慧感動了港城,以自身的陷落銘記一場跨越時空的戀情,紀念一位平凡女性的神奇與一個浪子的回歸。張愛玲在《傾城之戀》中運用特定的人物、情節設置等敘事手段,對傳統世俗的“紅顏禍水”女性觀進行了一次合情合理的顛覆,藝術地揭示歷史上“傾城傾國”乃“紅顏”之過的荒謬不實,很顯然,張愛玲最想表達的還是:女性的價值和美取決于女性的才智,有才智的女性不僅能解放自己,還能拯救這個世界中墮落的男人和男人的世界。
注釋:
①②③張愛玲:《洋人看京戲及其他》,《張愛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22頁,第22頁,第22頁。
④張愛玲:《論寫作》,《張愛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83頁。
⑤張愛玲:《談女人》,《張愛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72頁。
⑥⑦⑧傅雷:《論張愛玲的小說》,《張愛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413頁,第411頁,第411頁。
⑨蘇青:《讀〈傾城之戀〉》,《私語張愛玲》,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年,第264頁。
責任編輯:趙 青
10.3969/j.issn.1673-0887.2017.002.014
2016-09-11
錢亞玲(1968— ),女,副教授。
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2015SJD516)
H136.31;I206.6
A
1673-0887(2017)02-005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