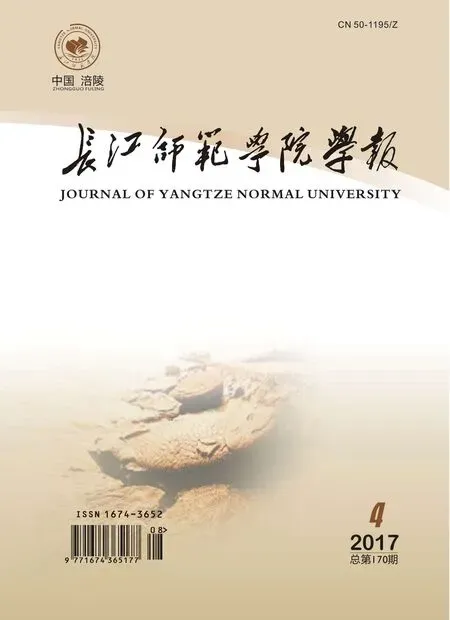中世紀基督教哲學“上帝存在”證明行為探析
李銀兵,羅金吉
(貴州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貴陽 580001)
□哲學研究
中世紀基督教哲學“上帝存在”證明行為探析
李銀兵,羅金吉
(貴州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貴陽 580001)
上帝作為西方文化中一個最具形而上性的概念,其對整個西方歷史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世紀基督教哲學家們試圖通過理性方式去證明上帝的存在,力圖把信仰中的上帝和知識體系中的上帝有機結合起來。殊不知,這種證明行為不但沒有證明上帝的存在,反而證偽了上帝的存在,最終結局則是導致了上帝在西方近代社會的消逝。中世紀對“上帝存在”的證明行為是偶然的,但其背后推動的理性發展則是必然的。
中世紀;“上帝存在”;基督教哲學;證明行為
愛迪生說過:“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的、充滿萬有的、至高至尊的上帝的存在。”[1]5-6的確,人需要一個形而上的關懷,需要愛、光明、溫暖、希望等力量。基于此,本文在簡單描述西方中世紀不同時期對上帝的論說基礎上,著重去探討中世紀3個證明行為出現對于社會所帶來的影響,進而對中世紀上帝證明行為進行一定評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中世紀基督教哲學家“上帝存在”證明行為
康德說:“我們所有的知識都開始于感性,然后進入到知性,最后以理性告終。沒有比理性更高的東西了。”[2]25西方文化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上,通過理性,西方人展現出了熱愛知識、崇尚知識的熱情。而這種熱情也表現在他們關于人離不開上帝和上帝存在的證明行為上。從遠古時代的《荷馬史詩》,到希羅多德的《歷史》,再到《圣經》中,我們都看到了上帝的影子。雖然近代這個最世俗的社會中出現了諸如尼采“上帝死了”的呼聲,但人類在面對日益增多的困境,特別是當今社會的諸多精神饑荒的時候,上帝好像又回到了人們的目光中,并得到了廣泛的議論。總的來說,人與上帝的關系是剪不斷、理還亂,而這種關系貫穿了整個西方歷史的始終。同時,人又是一個功利性的存在,既然離不開上帝,就想辦法去證明上帝的存在,以此來蔭蔽自身的不足。具體而言,在西方中世紀歷史中,對于上帝的證明主要是通過3個視角入手來進行的,即用知識的角度去包圍它,從知識的層面去證明上帝的存在,這就是奧古斯丁關于“上帝存在”的知識論證明;從先天的角度去說明上帝的存在,即安塞爾莫的本體論證明;從后天的角度去證明“上帝存在”,即是托馬斯·阿奎那的“上帝存在”證明。
(一)奧古斯丁關于“上帝存在”的知識論證明
奧里略·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354-430年)生于羅馬帝國北非努米底亞省的塔架斯特鎮,是教父思想的集大成者。奧古斯丁從知識論的角度出發,認為人類知識的確實可靠性是顯而易見、無可置疑的事實。他采用柏拉圖思想,分析了理性與真理的關系問題來說明真理高于理性,從而得出他的結論:“如果真理既不低于、也不等于我們的心靈,它必然比心靈更高級、更優越。”通過對人類知識確定性的來源的研究,他得出上帝是真理自身和人類真理來源這一結論。在人類知識等級之上,存在著一個處于最高級地位的真理,它賦予人類理性以確定的規則,使人的心靈認識真理。這一最高的、外在于人類知識的真理就是上帝。
(二)安塞爾莫關于“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明
坎特伯雷的安塞爾莫(Anselm of Canterbury,1033-1109年)生于意大利北部奧斯塔的一個貴族家庭。年輕時棄學而成修道院的一名世俗學生,被稱為“經院哲學之父”。安塞爾莫試圖告訴人們,“上帝存在”不僅是一個信仰問題,而且可以通過邏輯推理來加以證明,這個證明被叫做“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明”。安塞爾莫推論可以表達為:大前提——上帝是最完美的東西;小前提——最完美的東西必然包括存在;結論——上帝存在。當時就有一個叫高尼羅的舉例反駁說:傳說中有一個海島叫做迷失島,據說它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島。如果它是一個最完美的島,那么它就應該包括一切好的屬性,當然也應該包括存在,所以迷失島是存在的。但是迷失島明明是一個子虛烏有的傳說,在現實世界中并不存在,由此可見這個論證的荒謬性。因此,從邏輯上看,似乎這個推論沒有問題,可在康德看來則是有問題的。康德提出兩點批判:第一,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在它的本質(概念)中必然地包含著存在,存在是不可能單純地從一個概念中分析出來的,它只能通過經驗才能確定;第二,存在并不是事物的一種屬性,而只是表示事物的一種狀態,它并不會影響到該事物的完美性。康德還通過舉例來說,我的頭腦中的100塊錢與口袋里的100塊錢都是100塊錢,但是這兩個100塊是不一樣的,一個是概念中的100塊錢,另一個是實實在在地可以影響我的經濟狀況的100塊錢。我不能僅僅根據頭腦中的100塊錢,就推論出口袋里也有100塊錢。我的口袋里是否真有100塊錢,只能通過驗證,即用眼通過經驗感受去確定,要想僅憑邏輯推理從一個概念——哪怕是上帝的概念——中推論出來,那只能是癡心妄想!康德的批判是如此之深刻[3]108-185。安塞爾莫實際上是用一個信仰(上帝是最完美的東西)推出另一個本來屬于信仰的命題(上帝存在)。經過兩個世紀之后,經院哲學大師托馬斯·阿奎那指出了安塞爾莫證明的缺陷,他說安塞爾莫的本體論證明充其量只能使已經信仰上帝的人更加堅定他的信仰,而不能使沒有信仰的人產生信仰,因為他的前提還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礎上。
(三)托馬斯·阿奎那關于“上帝存在”的后天證明
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年)生于意大利的洛卡塞卡堡,是中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托馬斯·阿奎那從另外一個角度出發提出了關于上帝存在的證明。與安塞爾莫從上帝的概念推出“上帝存在”的先驗方法不同,他試圖從經驗的角度來證明上帝的存在,這就是著名的“托馬斯五路證明”。看起來他的證明要比安塞爾莫論的證明更有說服力,但是實際上也是存在著局限性,因為他的證明仍然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這五路證明包括5個證明,大部分在邏輯上都具有一種同構性。第一個證明是推動——受動序列的論證,得出這個“第一推動者”就是上帝。第二個是因果序列論證,得出“第一因”就是上帝。第三是偶然和必然序列的論證,一定會有一個“絕對必然的存在”,它是一切必然存在物的最后根據。這個“絕對必然的存在”就是上帝。第四個是完美性序列的論證,在這個序列中總會有一個頭,那就是“最完美的東西”,那些不完美的東西都趨向它,而這個“最完美的東西”就是上帝。這4個推理具有相同的邏輯結構,它們都是由前向后地不斷溯尋,推出一個最后的東西。這4個論證叫做“宇宙論證明”,它們都是從經驗事物出發,最后推出上帝的存在。第五個證明叫做“目的性證明”,托馬斯指出,人們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目的的,所以根據世界本身的合目的性或和諧有序性,我們就可以推論出一個至高無上的目的賦予者,他就是上帝。
總之,這3種關于上帝存在證明行為體現出了以下特點。托馬斯的這五路證明,從經驗世界出發,至少在出發點上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在他的推理中,同樣也存在一個前提,那就是信仰。托馬斯的證明,也是存在一個共同的大前提,大數學家羅素概括為“沒有首項的數列是不可能的”。羅素對此進行了相應的論述:世界到底有沒有開端呢?有沒有所謂的第一項?這完全是一個信念或信仰的問題[3]185。康德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一書中很好地解釋認為,關于世界有沒有首項的問題,這不是科學所能解決的,因為它超出了經驗的范圍,而科學只能運用于經驗世界。對于中世紀經院哲學家來說,信仰必須是第一位的,所有的論證都必須在以不威脅、不影響和不動搖信仰的權威為前提下進行的,否則是不被允許的。但是在他們運用理性來為信仰進行論證時同時,也無意識地開啟了一個“所羅門魔瓶”,放出了一個日后對基督教信仰構成巨大威脅的東西,那就是理性。毫無疑問,“一旦我們試圖對上帝加以界定,那么,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只有‘虛無’”[4]752-753。梯利也認為,永恒不變的真理世界的源泉是上帝。如果沒有上帝這一絕對的主宰,真理世界存在同樣是不可想象的[5]163。明知道會產生如此的結果,西方宗教哲學家們為什么要執意去證明上帝的存在?這就涉及證明行為背后的相關緣由。
二、中世紀“上帝存在”證明行為出現的原因
(一)政治原因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中世紀生產力水平低下,經濟發展困難,人民生活水平十分低下。中世紀的歐洲社會局勢動蕩不安,統治者為了維護其封建統治、加強對民眾的控制,迫切需要一個能對民眾實行強有力控制的機構和思想的出現。因此,證明了“上帝存在”,信徒就會更加堅信上帝,君權神授的思想就會被民眾所接受,統治者就能達到維護其統治地位的目的。中世紀政治是為宗教服務的,宗教也是為維護封建統治而服務的。當時的歐洲社會正處在封建社會時期,王室和封建主掌握著世俗的一切權利,地主階級占有大量的土地和財富。早在羅馬時期的《羅馬法》就規定土地可以私有,有錢人大量購進土地,農民則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歐洲封建時期的經濟是以農場和莊園經濟為主,農民失去土地就去租賃大地主土地,慢慢地就成了農場、農莊和大地主們的附庸。在中世紀,依附農民有義務為領主服徭役、繳納賦稅。根據相關記載,農民在管理好自己的土地的同時,還要額外管理領主的一部分葡萄園。除了定期的徭役之外還要去服不定期的兵役,許多農民通常要服兵役1~6次/年。這樣,統治者一方面壓迫民眾,一方面需要通過上帝的存在來論證君權神授的思想,使民眾心甘情愿地接受他們的統治不反抗而甘為人奴。同時,廣大人民深受封建地主階級的剝削,生活苦不堪言,各種權利得不到相應的保護,作為人的尊嚴更是得不到保證,遭受著各種壓迫和迫害。在當時的情況下,絕大多數民眾都屬于被壓迫的階級,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受盡人間之苦,他們心理上也需要尋求慰籍。不僅需要生活狀況得到改善,還需要一個能拯救他們的上帝,使他們在精神上得到解脫。總之,證明上帝存在是為政治服務的,是政治統治的需要。
(二)社會原因
中世紀的歐洲戰爭頻繁,新興的國王不斷地征戰擴充領土。中世紀歐洲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勞動生活是雞鳴而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同時中世紀歐洲長期的干旱導致氣候的惡化,如果夏季太干旱,莊稼就會枯萎;如果太潮濕,就會糜爛;有時還要遭受野獸和蝗蟲的威脅,蝗蟲能在很短的時間里橫掃整個田地。不論地區大小,當地每一次的歉收都會導致饑荒發生,而饑荒又會抬高物價,民不聊生。編年體、年代記都較為詳細地紀錄了中世紀時期廣泛存在的降雨、霜凍、自然災害和干旱的情況。饑荒所造成的后果是瘟疫和疾病,很多史料證明,營養不良引起的疾病、瘟疫都是饑荒導致的惡果。由于中世紀醫療技術十分落后,一些持續性的危險時刻威脅著人們健康、乃至生命。像麻風病、傷寒、天花、霍亂在地中海地區流行的瘧疾,如果誰得了像諸如這些可以致人死亡的疾病,在中世紀他們就被稱為“著了魔的人”。另外,沒有遭受饑荒和疾病之苦的人,也可能會是戰爭、械斗和搶劫的受害者。疾病和戰爭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中世紀人均壽命很低,大概只有25~32歲[6]8。由于中世紀的人們飽受戰爭、自然災害、疾病之苦,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在身體上和心靈上受到了極大的傷害,再加上社會如此的冷酷無情,唯有自救,于是在心中不斷地創造出一個充滿愛、光明、溫暖、希望的上帝,來拯救深處苦難之中的萬民,為他們尋找到一個心靈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因此,證明上帝存在的行為在中世紀有廣泛地群眾基礎,成為了中世紀神學家們迫不及待地要去解決的棘手事情。
(三)思想原因
當你在武力征服別人的時候,同時也在被被征服的文化所征服。馬羅帝國在武力征服希臘后,卻被希臘的文化所征服,因此羅馬帝國在文化上繼承了希臘時期的傳統和衣缽。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關提出了“神”的概念,“神”實際上是形而上學的最高原則和首要原因的代名詞,它的出現是為了解釋可感的物理實體的合理性而做出的理論設定,亞里士多德在物理領域之外設立一個超自然的神圣領域,為形而上學與各種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神學的同盟開辟了道路。當然,盡管羅馬文化與希臘文化有著一脈相承的沿襲關系,但是在這兩種文化之間卻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希臘人對羅馬人的自然態度,是一種夾雜著恐懼的鄙視;希臘人認為自己更文明,但是政治上卻較為軟弱。如果羅馬人在政治上有著更大的成功,這只說明了政治是一樁不光彩的行業。”[7]348戰爭的發展,特別是在羅馬帝國時期的對外征服中,東方關于神的思想不斷地傳入西方,加上古希臘多神教的宗教神學思想,它們一起為中世紀上帝存在論證明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支撐。整個中世紀的思想是極其匱乏的,人們可以接觸到的思想基本都是關于基督教信仰的。在中世紀,一切的哲學都是為宗教服務的,哲學淪為神學的婢女。因此,思想上的傳統和貧乏直接為中世紀上帝存在論證明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四)宗教哲學家們的主體性發展
人的發展歸根到底是人的思維的進步、主體意識的不斷提高。古希臘哲學從神話傳說中產生之后,則集中對宇宙本源的探討。我們一般稱之為自然哲學的米利都學派、愛利都學派和原子論的哲學家們很重視對自然科學的研究。從認為世界的本源是“水”“氣”“火”“變與不變”“一”“多”到“思維”與“存在”概念的提出,各個學派提出自己的觀點,并對其論證或與其他的學派展開論戰,這一些行為都在有意與無意之間推動了自然哲學的發展,促進了哲學家思維方式的不斷進步,這為哲學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從公元5世紀開始,希臘哲學的研究方向由自然界轉向人。如:智者代表普羅泰戈拉提出了著名的哲學命題“人是萬物是的尺度”;蘇格拉底是第一個把哲學從天上拉回人間的人,“認識你自己”是他的名言;柏拉圖的“理念論”客觀唯心主義的發展;亞里士多德關于感官與理念兩個世界的提出及其哲學體系的發展;希臘化時期的伊壁鳩魯主義與斯多亞學派的不斷發展。隨著哲學的不斷發展,宗教哲學家們的主體性意識也得到了不斷提高,他們在思想上就更需要和更有能力去追求形而上的思考。
三、“上帝存在”證明行為反思
(一)證明行為用理性去反信仰
我們可以把安塞爾莫的本體論證明和托馬斯·阿奎那后天證明放到中世紀基督教文化的大背景中去看這些證明所具有的意義。總的來說,這些證明都表現出一種注重理性的傾向,這成為了近代理性主義的重要來源。事實上,當經院哲學家開始用理性來證明基督教教義信仰時,他們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把信仰架空了。從基督教的發展過程來看,單純的信仰到邏輯的論證是第一步轉變,邏輯論證到感性直觀則是第二步轉變[8]2018。這就是說,我們試圖通過感性直觀的方式來追問基督教教義的細節時,那么一切荒謬的結論就會應運而生,最終結果將是導致基督教神學大廈土崩瓦解。但不可否認,用感性直觀的方式理解教義,開啟了一個經驗的方向。因此,我們可以這么說,從狂熱的信仰到理性的理解,再到感性的直觀,這個過程的發展是不利于基督教神學,但是它卻有利于近代科學和哲學的生長。這一切都在對“上帝存在”證明后得到了印證。
基督教哲學家用理性來論證神學教義的做法導致了一種惡果,即是宗教在信仰中建立起來的神秘性和神圣性受到了巨大的挑戰。經院哲學家們運用理性來論證基督教教義原本是為了加強對基督教的信仰,沒想到帶來的結果卻是隨著理性的運用,信仰受到削弱。雖然在中世紀,這種影響并沒有真正顯示出來,但到了近代,理性精神開始逐漸壯大,并反客為主地成為了人們的認識目的,進而對基督教信仰進行猛烈的、無情的批判。以信仰為前提是中世紀基督教哲學的一個基本特點,神學家們認為只有在信仰的前提下才能進行所謂的理性證明,這種證明的結果一定是要與信仰相符合的。的確,阿奎那很有分寸,他知道哪些教義可以證明,哪些是不可以證明的。他認為“上帝存在”是可以證明的,而“三位一體”就是不可以被證明的,這只能完全地信仰它。因此,與經院哲學相比,教父哲學是進步的,因為它不再完全排斥理性的信仰主義或神秘主義,而且想通過理性來論證信仰。總之,基督教哲學家們對“上帝存在論”的證明實際上推動了西方的理性思維的發展,為之后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及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學的發展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二)證明行為形式強于邏輯
中世紀3位神學家對上帝存在證明的思路和方法,從形式上來講都是沒有問題的,通過形式邏輯的分析,證明確實得到了上帝存在這個結果。奧古斯丁第一次對“上帝存在”進行了系統的邏輯論證。安塞爾莫的本體論證明可以表達為一個形式的推理公式:大前提——上帝是最完美的東西;小前提——最完美的東西必然包括存在(否則它就不是最完美的東西);結果——上帝存在。這個推理從邏輯形式上看是完美的。托馬斯·阿奎那的后天證明,即五路證明也在邏輯形式上是相當強的,他從不同的事實角度出發,經過推理論證,得出上帝存在的結論。總之,從奧古斯丁的知識論證明到安塞爾莫的本體論證明,再到托馬斯·阿奎那的后天證明,從邏輯形式上看,其形式邏輯性越來越強,更加嚴謹。從知識角度看,證明方式越來越細化和明晰化,層次上更加深入,確實體現出了人類的邏輯思維和知識水平在不斷上升。同時,這些證明對于中世紀的唯名論和實在論者來說,則是令人信服的。當然,我們現在知道這僅僅是形式上的邏輯分析,而要從邏輯實質去看,則是另外一番情形。
(三)證明行為的結果是證偽
中世紀的基督教哲學家通過對“上帝存在”的證明,維護了基督教中最核心的概念和范疇——上帝。11世紀以后,在整個歐洲,羅馬天主教會已經高高凌駕于整個世俗社會之上,它不僅成為歐洲最大的莊園主,還通過教俗之爭一步步得到至高無上的權利,成了歐洲最大權利的控制者。當然,我們從證明中可以看出,西方人是充滿理性和崇尚知識的,而且從當時的社會來看,證明也符合時代需求,因而證明很有必要。但西方世界中的上帝是唯一的,是全知、全能、全善的無所不能的統一,因此,它才成了民眾信仰的對象。但一旦人類用有限的知性去認識無限的上帝的時候,就把上帝變成了我們知識體系的一部分。以有限的思維去認識無限的事物的結果,則是把無限的事物變成了有限。上帝一旦都是有限的事物,上帝就和我們一樣,其帶給我們的形而上關懷將隨之消逝。因此,我們才會看到尼采說“上帝死了,是我們把上帝殺死了[9]108。從這個意義上去看,中世紀對上帝的證明恰恰是證偽了上帝。
(四)證明行為表征了現實和理想間的矛盾
基督教早期是窮人的精神撫慰所,是人們靈魂的歸宿地。唯靈主義和超越精神的宗教品質使得基督教教義成了人們靈魂得救的福音。隨著中世紀戰爭的頻繁發生,人口大量的流動帶來的傳染病、饑荒等慢慢開始籠罩整個西歐。在這樣的情形下,民眾需要一種形而上的關懷,需要一個有愛、有希望、有溫暖的世界,而無所不能的上帝就能使這一切達到。但基督教在成為正統宗教后,在物欲橫流的世俗社會的沖擊之下,其變得不再圣潔,而與世俗社會融為一體。因此,西方社會后來的發展史告訴我們,中世紀對上帝存在論的證明行為打破了信仰和知識的界限,把現實和理想混在了一起,進而開啟了人類社會理想和現實的矛盾濫觴。上帝是無限的,它歸之為人們的理想范疇,因而不需要去證明,何況我們有限的思維也證明不了。世俗生活是有限的,它需要我們去認識和澄清,這是我們人類的分內之事。
總之,人很自信,認為自己的能力能夠證明一切,其實這只是人類自我陶醉而已。接下來發生的事,足以讓中世紀的神學家無地自容。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17世紀人類心靈經受了來自于自然科學界的3次巨大震撼,即天文學上日心說的提出、生物學上達爾文生物進化的提出、科學心理學的發展。經過這三大思想變革,曾經被證明存在的上帝被趕走了。證明上帝,其實是證偽了上帝。隨著近代笛卡爾的一聲“我思故我在”,跪了幾個世紀的基督徒被喚醒了,從而開始了又一場轟轟烈烈的“理性革命”。中世紀對“上帝存在論”的證明,是偶然的但其背后推動的理性發展則是必然的。我們相信,正是在人類理性的指引下,人類社會將變得更加和諧、更加美好!
[1]拉皮羅夫·斯科勃洛.愛迪生傳[M].南致善,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5-6.
[2]康德.純粹理性批判[M].鄧曉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5.
[3]趙林.基督教與西方文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108-185.
[4]劉小楓.二十世紀西方宗教哲學文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752-753.
[5]弗蘭克·梯利.西方哲學史[M].葛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163.
[6]漢斯·維爾納·格茨.歐洲中世紀生活[M].王亞平,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2:8.
[7]羅素.西方哲學史(上卷)[M].何兆武,李約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348.
[8]趙林.西方哲學史講演錄[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208.
[9]尼采.快樂的科學[M].黃明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108.
[責任編輯:慶 來]
B13
A
1674-3652(2017)04-0109-05
2017-02-10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創新視域下西部少數民族傳統節日的社會功能研究”(14BSH057)。
李銀兵,男,四川資中人。博士,教授。主要從事文化哲學、民族學、歷史人類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