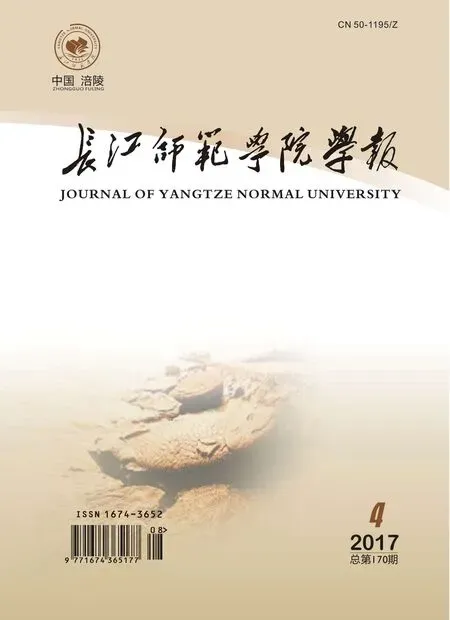作為思想與哲學行動的小說
——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記憶的美學追求
張羽華
(長江師范學院 文學院,重慶 408100)
□文學研究
作為思想與哲學行動的小說
——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記憶的美學追求
張羽華
(長江師范學院 文學院,重慶 408100)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學記憶書寫,體現了作家獨特的美學追求。從思想和哲學角度切入,更能夠體察作家對歷史的整體認識和價值判斷。作家以深切的現實生活體驗和豐富的歷史想象去追尋中國民族文化心理、人的生存方式以及精神世界,從而使得小說獲得了實質性的藝術突破與創新。但是過分夸大作家的思想意識和劇烈思辨,或者悖逆歷史的主體認知,也會導致小說的抽象化、平面化,進而喪失藝術的表現力和感染力。
90年代小說;文學記憶;思想深度;美學追求
哲學、思想歷史意識的批評標準,不是文藝批評的唯一準則,但它卻是傳遞作家思想和價值判斷的有效途徑,是幫助提升文藝作品藝術表達力的催化劑。一部經典的文藝作品必然折射出作家深厚的思想內涵和對人生本質無窮的追問與探討。“真正的思想性是引領讀者一同思索、一同探究、一同警醒、一同‘思想’,而不是告知某種‘思想成果’‘思想答案’。從這個意義上說,小說中的‘思想’從來就不是藝術的添加劑或附屬物,它在一部小說中之所以是必要的,本質上正是因為它本就是藝術的一個必不可缺的因素,一個有機的成分。或者說,思想其實也正是藝術化的,它就是藝術本身。”[1]同樣,一個成功的作家,必須在歷史的流動過程中具備敏銳的思想穿透力和深厚的哲學基礎。因此,作家在具體創作過程中應以個體的生命體驗燭照人生,思考歷史,讓作品能夠反映歷史與現實生活中的本質,從而加深小說的藝術表現力。文學是形象的,同時也是理性的。形象在于日常生活的自在呈現,理性在于對人生本質的回顧與展望,對人的本質的探索與人類生存的無限探幽。然而,令人遺憾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作家對文學記憶的書寫過分注重形象的塑造,而忽視了文學理性的思考。淺層次的、快餐式的藝術形象的塑造難以真正引領我們體悟到在歷史化進程中人類存在的本質和終極思考。于是面對泡沫化、時尚化、快餐式的小說創作,我們不得不多了一份擔憂。作為思想與哲學行動的小說,我們的作家應該如何去敘事,如何去思考和探索社會與人類本質存在,這是當前作家最基本的美學追求。
一、如何體現小說的歷史思想深度
懷特認為任何文本或人造之物都可能閃現出思想世界,甚至可能閃現出影響這種感情的世界以及當地產生這種世界的現實環境。那么對于文學來說,一部思想內涵豐富的小說,同樣能夠影響到它的讀者以及讀者周邊的人。作家的思想就是作品的靈魂。其靈魂不是直接地裸露出來,而是通過作品中的“形象代理人”體現出來。“藝術和思想的杰作是人類創造力的永恒紀念,因為永恒不易的模式超乎表象流變之外,而惟有這些杰作體現人類對此永恒模式的洞識。”[2]但是,綜觀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大多數小說,所蘊含的思想和哲理是很膚淺的,難以反映人生存在的本質特征。
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記憶的歷史敘述,存在一個致命的問題:小說自身歷史內涵的空洞和思想貧乏的敘事,難以給人一種藝術的美感和靈魂的啟迪。一部文學著作,如果缺少了作家歷史思想的滲透,小說的藝術質量是會大打折扣。“文學作品滲透出思想,就像肝臟制造膽汁一樣:這就像是一種體液分泌,液體的滲透、流淌和發揮。”[3]西班牙著名歷史學家喬斯·卡洛斯·貝爾梅霍·巴雷拉在論述創造歷史和講述歷史這個相互對立的主題時,首先提出了一個問題:“在歷史文本中是誰在述說?歷史文本中的敘述是針對誰而發的?敘述者是以何種身份來講述歷史的?敘述者所訴說的是什么?”[4]去弄清誰創造歷史和講述歷史不是我們的本意,也不是論述所關注的重心所在。在這里,我們所好奇之處,就是借助喬斯·卡洛斯·貝爾梅霍·巴雷拉看問題的視角來閱讀小說也能說明同樣一個問題。這些都涉及到作家對歷史的掌握問題以及對歷史認識的立場問題。歷史的本質并不是人的思想活動的產物,它是人在具體社會實踐中不斷發展的產物,所以,作家要進行深度思考人類歷史的本質,才能夠真正提升小說藝術表達的思想深度。
對歷史的審視與體察,是一個作家的責任,也是傳達作家思想的有效傳播媒介。國外經典作家諸如巴爾扎克、大仲馬、雨果、赫爾岑、列夫·托爾斯泰、帕斯捷爾納克、納博科夫、布羅茨基、卡巴科夫、索爾仁尼琴等作家對歐洲本民族歷史的記錄和刻寫,始終閃耀著燦爛的藝術思想光輝。首先在于這些作家本身就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他們對歷史、現實社會和生命都有著深刻的認識和豐富的體察。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有著自己的信仰,耐得住寂寞,不為名利牽引,能夠沉下心來對歷史作出本質的思考,并在生活體驗中不斷豐富自己,錘煉自己,逐漸達到一種高深的思想境界。他們的小說閃耀出恒久的藝術魅力,不僅僅體現在它們的“審美性”,更重要的是這蘊含著作家第一次由它發現、彰顯、表露的“思想”。
聯系到中國當代作家的文學記憶與想象,其小說透視出來的歷史思想是膚淺的。即使像莫言這樣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也難以與西方名家的思想境界相比。評獎者看中的是他擅長搬運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藝術寫作手法,與中國高密東北鄉的民間文化的對接與熔鑄,能夠給讀者一種新的認識和思考。莫言作品有一定的思想力度,相對于西方一些經典作家的作品而言,還有一定的審美差距。他的小說獲得的榮譽之所以能夠達到他本人理想的維度,除了偶然的運氣和評審者的投其所好之外,當然也與莫言潛在的藝術素質有關。不過,即使像莫言這樣的作家產出相對有深度的作品還是不多的。比如蘇童、葉兆言、賈平凹、余華、張煒、嚴歌苓、尤鳳偉、畢飛宇等作家的很大一部分作品,算得上是有思想深度的。這些作家對歷史的把握度和穿透力比較強,具備獨立的自省意識,能夠擺脫各種在精神和物質上帶來的雙重束縛,擁有獨立的藝術思維空間。他們在書寫歷史的過程中,自覺地凸顯一種歷史意識,能夠較好地把歷史與現實,歷史與生命,歷史與苦難巧妙地熔鑄在一起,達到一定的思想深度和美學厚度。蘇童說:“我最大的敘述目標,就是用我的方式來表達‘那個時代’的人的故事和處境。”[5]這里“我的方式”當然主要指作者的思想流露和對“那個時代”的認知方式。
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多數作家都試圖以文學敘事的方式進入歷史的記憶,闡釋歷史和重建歷史,再現歷史中的人與事,探索人性的生命追問,凝析出明亮的歷史結晶。這幾乎是每一個作家的夢想。蘇童的寫作思維和寫作路徑是離不開歷史書寫的。當然,蘇童的寫作也不容我們質疑。理由在于,他從一開始就把主要的筆力放在他理想的香椿樹街和楓楊樹鄉村的故事和環境的構建上。無論是寫《1934年的逃亡》《紅粉》《城北地帶》《米》《碧奴》,還是前幾年出版的最能體現蘇童超越性的史詩性長篇小說《河岸》,蘇童都能準確地把握歷史,穿透歷史的云霧,扒開表面的面紗,認真揣摩所建構歷史中的人與事,并賦予深厚的思想。他建立了具有地理坐標意義上的香椿樹街和楓楊樹故鄉,通過想象生活或歷史的方法重新展示出新的美學元素,情不自禁地講述對真實的——也就是歷史的——藝術中的歷史真實所激發他的令人陶醉的人與事。蘇童在處理河岸邊的故事,格外用力。他在處理歷史與社會經驗,真實與虛構方面非常注重文學本身具有的藝術性的因素而絕不投降功利性的世俗化的敘述意圖。
蘇童在《河岸》里面寫出了人物的生命和氣息。河與岸成為人物與社會、生活、理想、現實關系的某種坐標。少年庫東亮在河與岸之間焦慮的生存,被時代譽為“空屁”,這本身體現出豐富的時代意義。庫東亮的思想和追求,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了蘇童自我的理想又在某些方面獲得突破。正如蘇童在訪談中所言:“我覺得這部小說存在著對我寫作的很多挑戰。最有挑戰意味的在于,在我的作品當中,尤其是長篇小說,這還是第一次非常直接地面對一個時代。時代或者說時間、年代這樣的概念,在我以前很多小說中基本上是把它虛化的,有時候甚至變成一個背景,就像一個人在上面活動的舞臺布景一樣。但是我對那個時代本身幾乎不做詳細的刻畫,或者說是避過,不是抱以正眼面對、擁抱的姿態。但是在這部小說當中,完全不同。”[6]
作品的思想既是個人的洞見,又是對歷史、社會心理、事物本質的有力揭示與高度概括。綜觀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大多數文革小說的書寫,無論是以少兒視角敘述還是以成人視角書寫成人的生活世界的小說,真正具有思想穿透力的小說并不多。大多數小說都是以親歷者的身份書寫對現實生活的體驗,并沒有自覺的文體意識。比如雪屏的長篇小說《大串聯》雖然在敘事模式上獲得了一定突破,卻在藝術思想上挖掘不夠,這或許與作者本身的思想蘊藏并不豐富有關。小說圍繞兩條故事情節來鋪展,即敘述少兒時代大串聯的生活感想和對社會的初步認識,又以成人對40多年前“文革”記憶的回顧。作家不僅在記憶上去探索從前的真實故事,而且以中老年的身份重走大串聯的路線引起的切身感受為線索。兩條線索將過去與現在交叉進行,用已過去的經歷和現在的社會經驗來審視歷史,固然體現出作家的主體意識。問題是,作家在敘述過程中,由于語言的蒼白與思想的膚淺,小說本應呈現的美學蘊含被遮蔽。同樣,靳元亮《我和我的知青哥兒們》、陳肖人《我這把生銹的大刀》、楊爭光《從兩個蛋開始》、高建群《大平原》、韓東的《扎根》《絕地三尺》《田園》、沈喬生《狗在1966年咬誰》、王璞《畢業合影》、張執浩的《安亦靜的夢魘史》、胡廷楣《生逢1966》、馬原《牛鬼蛇神》、曹文軒《紅瓦》、沈善增《正常人》、陶少鴻《少年故鄉》、東西《后悔錄》、木凸《慢慢呻吟》等大批小說,從某種程度上說,都缺乏一種自省的思想厚度和審美的力度。
尤其是一些棲居在偏僻地區的作家,在進行歷史記憶的書寫時,都顯得沒有底氣,思想淺薄、平淡。比如一些作家在敘述故事情節時,還是把主要的階級對立作為作者敘述的價值批判立場,認為地主就是剝削者和壓迫者,而忽略了對他們白手起家、披星戴月勞作過程的精神發掘。實質上,就是地主也還幫扶了一些人,讓無立錐之居的貧困勞動者有了生存的保障。另外,一些作家從根本上也忽略了農民的一些劣根性,農民對財產過多擁有者的仇恨,較大因素來自于農民心態的不平衡。一旦他們找到了立足的理由,就把無理的矛頭指向較多財富的擁有者,以此依靠政治運動來獲得自我生存的資本。一些作家在書寫宏大歷史的政治運動時,在跨越歷史闡釋中,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土改的話題,沒有去尋找出其中的意義,患了嚴重的思想“貧困癥”。
同樣,對于“反右”寫作而言,除了尤鳳偉的《中國:1957》(長篇)、《一九五七年的愛情》(短篇)以及王安憶《叔叔的故事》、楊顯惠《夾邊溝記事》引起學術界關注以外,其他諸如石英《透視靈魂的世界》、方方《烏泥湖年譜》、胡君強《不成樣子》、張賢亮《習慣死亡》、池莉的中篇《滴血晚霞》、石杰《狗魚》、李倫新《非常愛情》、智量《饑餓的山村》、白石和馮一平的《從囚徒到省委書記》等,盡管在敘事視角、對情節故事的營構上有所突破,但是在敘述層面上仍然缺乏思想認識和哲理判斷的深度。
以智量的長篇小說《饑餓的山村》為例。在李家溝處于極度饑餓狀態時,王良既不能以他的身份拯救瀕臨餓死的村民,也不能在領導面前拯救自己。王良的人生理想就是為了盡快脫掉右派的帽子,回家團聚,但是在強大的政治勢力和惡劣的自然環境面前,他都以失敗告終。作家塑造王良最根本的缺陷在于現代生命自由的缺乏和生命理想主義眼光的短視。這種精神世界的坍塌必然限制了作家創作視野和思想。
從小說的個案分析來看,作家在看待歷史問題上還是淺層次的。如果僅是為了呈現歷史原貌,那不如去翻閱歷史教科書,或許從中感受到的歷史更加真實可信。但是,文學必定是一門審美藝術。雖說陳忠實的《白鹿原》被讀者普遍認為是一部“民族的秘史”,但“缺乏一種真正的思想透視的眼光,也缺乏一種生命的自由的精神想象力,僅有淋漓的生命元氣而無自由的思想力量,要想表現中國歷史文化及其生命理想自然就不可避免內在的思想局限”[7]。
二、如何體現小說的哲學意味
徳裔美國歷史學家格奧爾格·G·伊格爾斯認為:“每種歷史敘述中都有歷史哲學的暗示。”同樣,在小說的歷史敘述中也應該有哲學的暗示,否則,小說的藝術表達就沒有穿透生命的本質。小說的歷史敘述,不是純粹的歷史書寫,也不是高深的哲理高談闊論,而是在離析作家的思想、哲學、歷史、社會知識過程中生發出具有修辭藝術的帶有審美愉悅的文學作品。
小說創作不僅是要表述作家所認識的世界,而且要賦予這個世界以豐富的哲理內涵。文學的歷史哲學意義不是顯在地呈現在小說里面,而應是通過作家文學藝術演繹的天賦和豐贍的思想內涵潛在地隱含在小說之中,由高明的讀者去捕捉和咀嚼。克羅齊說歷史哲學意味著對歷史的思考,同樣,文學的歷史思考,也離不開哲學的自覺參與。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小說的歷史記憶,就是以作家現在的眼光和理性的思維去感受和評判這段歷史中的人與事。作家創作的意義在于,盡最大限度地在他的小說世界中呈現想象的歷史人物圖像,以記憶的形式還原到歷史的現場,跨越時間和空間界限,透過表面的現象,通過隱喻類似的修辭方式來作出小說的暗示。然而,通讀大多數有關歷史記憶的小說,我們會發現無論是小說的情節構造、語言表述,還是人物的設置和作家理想化的人物出場,幾乎都是平面化的,缺乏深刻的哲理內涵,沒有反映出人生存的本質。目前大多數讀者對當代文學普遍失望的原因也就在于此。當前作家只有通過自身的敘述優勢,結合歷史與現實生活體驗,去發掘別人難以企及的富有詩意的內在生活,去捕捉被歷史迷霧遮蔽了的真實人性,在自我的審美理想中作出藝術開拓,才是擺脫凡庸思想束縛的有效出路。
“認識(判斷)一個事實等于思考它的存在,因此思考它的產生和在各種條件下的發展,反過來各種條件也在變化和發展,因為其存在不在別處,就在其生命的進程與發展中:人們徒勞地試圖在這種生命之外思考其存在,由于在無能努力的失望之后,就連事實本身的影子都未留下。我們越是深入把握其本性,就越能感覺到在其歷史中同它一起運動。”[8]缺乏歷史性的內在認識和思考,不顧各種條件的變化和發展,機械地看待歷史和事物表象,否認歷史固有的而不是外在的性質,都是缺乏哲學依據的。過去與現在,理應存在著一個真正的事實判斷,這才是探索作家在創傷記憶中的寫作的最基本的依據和標準。當然,任何個人看待歷史的結果,又與自身的價值立場和人生觀念存在很大的干系。但總體來說,20世紀90年代以來作家在看待歷史問題上,忽視了哲理意蘊的有意追思和探索,造成了小說藝術深度的缺乏和詩意的存在。
任何一種小說的歷史敘述都應有歷史哲學的暗示或隱喻,這是優秀的小說必備的基本條件之一。然而,對于小說中歷史哲學的暗示,不在于通過作家赤裸裸地指定出來,而是應當通過作品中的歷史場域,主要人物的塑造,時間和空間的把握,語言的巧妙表達等隱蔽性地暗示出來。當然,還可以直接通過作家的哲理語言直接表述出來,讓讀者從小說的故事、情節、人物等環節中去捕捉,去咀嚼話語中的本質含義,才能受到心靈的震撼和人生的啟迪,并豐富人的生活意義。西方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阿爾都塞的弟子皮埃爾·馬舍雷在論述《贊文學哲學》這一論題時,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哲學會回到一種理論深思的結果,透過寫作的諸多手法,將這些寫作手法納入一種事先設計好的‘知識’空間中,即完全確定好目標的空間。”“貫穿所有文學文本的問題性思想就像一個歷史時期的哲學意識:這個時代對自己的反思,正是文學所要說出的問題。”文學的哲學意識,只有通過暗示或者隱喻的形式表露出來,才能增加文學藝術的審美內涵。
小說應該充滿歷史性暗示和體現出隱喻性的意義。蘇童的長篇小說《河岸》是一部具有哲理意義的小說。這部小說的核心是圍繞庫文軒的身份問題展開,在敘述者的講述中,“一切都與我父親有關”,由于庫文軒是烈士鄧少香的兒子,在一切講究階級成分的年代,庫文軒在榮譽和社會地位上無疑都有先天的優勢。但是當他在權力面前風光一陣后,一個神秘的“烈士遺孤鑒定小組”忽然降臨,庫文軒以冒充烈士兒子的罪名被剝奪了權力,遭受批斗,并放逐到向陽船隊生活。蘇童在借敘述者少兒“我”即庫東亮講述父親的悲劇命運時,沒有放棄對其他歷史人物的描繪。庫東亮遭受父親嚴厲的懲戒,在日常生活中見證了人世間的冷暖,體悟到了隱藏在歷史、意義、價值的虛妄與現實生活的要義。庫東亮與七癩子姐姐爭奪面包,僅僅是為了填肚子,“吃”隱含著人活著的意義。一切“吃”都與人的出身有關。七癩子姐姐理直氣壯地從庫東亮手中奪去面包,首先就在于她在階級成分上優先于庫東亮。具有“河匪”“反革命”“走資派”“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身份的庫東亮理應是被搶的對象,同時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庫東亮在階級社會生活流中,沒有任何優越感,屈辱、孤獨和苦痛幾乎成為他生活的全部。“空屁”的綽號不僅是來自普通人的調侃和戲謔,更來自于世俗生活和革命意識對他的捉弄和排擠。蘇童在對歷史記憶的建構中,把兩種日常生活展露出來。油坊鎮與向陽船隊由于“河”的人為阻隔,體現出兩種不同人的精神世界。油坊橋鎮上的人們,過著優越的生活,而向陽船隊上的人們,盡管遭受到身份的歧視和放逐,但他們仍然有滋有味地生活,特別是一個來歷不明的慧仙到了向陽船隊后,船上的人們爭相撫養她。這體現了弱勢群體應對強勢力量的生存智慧和生存哲學。
蘇童的敘述力量在于不斷地超越自己,突破已有的歷史敘事常規。在《河岸》的歷史布局中,他注重人物獨特個性的挖掘和塑造,把宏大的歷史化解到日常世俗的生活中,既體現人的普遍性,又抓住了作為個體的人的生活的獨特性。《河岸》的結尾完全可以隱沒父親庫文軒的出場,但是敘述者又始終在追逐父親的腳步聲中尋找父親的最后歸屬之地。“河”的隱喻在于庫文軒游離到了不能正常生活的彼岸。這是他命運突變的轉折之地,同時又是他命運的最終歸屬之地。小說的歷史哲學暗示:庫文軒在兒子庫東亮的幫助下,偷偷從岸上把鄧少香烈士的石碑推到向陽船隊屬于父親的那艘船上,是“我”的善意幫助,加速父親命運的悲慘結局。“我父親生命的最后一刻和紀念碑捆在一起,成為一個巨人,我拉不住他,一個巨人投奔河流,我拉不住他。”[9]敘述者讓庫文軒和石碑捆綁在一起,在靈魂中見證了鄧少香烈士的孤兒的確鑿性。庫文軒的這種暴烈的命運結局是作家不愿看到的,也是讀者難以預料的。鄧少香烈士的石碑成為了一個時代的象征,歷史的見證,這在小說的開頭就暗示了孤兒庫文軒悲慘的人生命運和結局。
從這幾部長篇小說可以看出,無論是作家對歷史的思想把握,還是付諸歷史給予哲理的思考,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藝術性的展示。嚴歌苓《第九個寡婦》中的王葡萄可以說是書寫新中國歷史中塑造的最成功的女性形象之一。王葡萄的命運轉折受制于政治運動。本貧苦農民出生的王葡萄本來可以擺脫土改運動帶來的苦難命運,可是嚴歌苓卻違背了常理,在強大的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勢力面前,作家把王葡萄塑造得非常成功。王葡萄以童養媳的身份掩護、孝敬公爹幾十年,真正體現了作家豪邁的藝術勇氣和哲學智慧。同樣,在莫言《生死疲勞》中,對藍臉的塑造也具有典型性。藍臉敢于在政治運動風潮浪涌中按照自己的意志搏擊前進,沒有向任何一次政治運動低頭,這充分體現了作家的哲學思考和對人物形象的理想把握。李西閩《好女》塑造了鄉村女人——一個被地主家族遺棄的女兒李大腳傳奇的一生。
文學不僅需要作家的個人生活體驗,更需要作家在人生體驗和時代的搏擊中凝聚出來的哲學智慧和思想光芒。“文學回顧和復活歷史,不是出于好古之心,更不是逃避現實,而恰恰是出于強烈的現代意識。”[10]敘述歷史,不是對歷史史料的考證,而是通過歷史的甬道,展現人的現代意識和價值取向。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作家在小說的敘述過程中,刻意地把觀念的東西強加進去,大發議論,必然造成小說形象與理性的剝離。因此,作家在小說的敘述中,那種哲理思想的熔鑄,是自在自然的,不是強硬地灌注進去。馮積岐《沉默的年代》雖然揭示了特定年代主人公周雨言生活中的愛情故事和苦難生存境遇中的心理現實,同時對一些女性形象的塑造也有所成功,但是歸結到本質上,拙劣的故事情節把戲、情節漏洞、敘述設計以及政治和道德價值的讓位妨礙了作家強烈的現代意識的散發。一切強有力的文學作品都具有豐富的哲理內涵,散發出人性的光輝。在小說中,作家反復寫了饑餓,把身體的饑餓與肉體的饑餓含混起來,但沒有真正寫出饑餓的本質所在。潘婧《抒情年代》以過多的抒情取代了故事本身,抽象的哲理言說,卻沖淡了故事本身的現代意義。王安憶《啟蒙時代》在人人需要啟蒙的時代,唯獨需要啟蒙的是南昌。頗有意味的是,王安憶把南昌設置在一場場思想言說的場景中,頻繁出現的“談話”“演說”“大辯論”等措辭,這些具有修辭性意義的詞匯對于南昌來說,確實具有啟蒙性質,卻沖淡了小說藝術的形象性。
三、附帶的闡釋與必要的結論
在納博科夫看來,一部文學作品成功的關鍵,嚴格說在于作者的敘述結構和敘述風格,與思想關系不大。而在米蘭·昆德拉看來,小說主要是表達作者生命的主題,小說的智慧不是在于哲理性的智慧,也不是它的思想,而在于他對生命本真的追思。文學作品中折射出來的思想是記憶、觀察、思考,西格麗德·努涅斯對此似乎也有所探究。“一直以來不那么容易判斷的就是一部文學作品的價值在多大程度上有賴于——或應該有賴于——其思想的重要性,作者處理它們又有多大成功。”[11]對此,她深表猶豫。但她似乎又從蘇珊·桑塔格的行文論述中找到了答案——她(蘇珊·桑塔格)不愿意、也無法放棄思想。無論作家們為自己的創作怎么辯護,事實是在他們的創作中,都滲透著作家深刻的思想和深厚的哲理。
作家首先要具有自己世界觀的哲學意識,要對歷史提出個人性的看法和見解,要表達出作家一種最根本的精神追求和價值立場。范穩《水乳大地》里面呈現出一種全新的宗教思想和對宗教文化的闡釋。雖然我們對范穩是否是一個宗教偏執狂不得而知。在小說的敘述中,宗教是大地的水乳,精神生活是人的存在價值。西藏與云南邊界的多民族,就是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下依靠精神的力量生存下去的。任何政治的力量在濃厚的宗教文化面前,都顯得力不從心,軟弱無力。另外,宗教文化的滲入,擴大了文本的敘述空間和敘述容量,同時也穿透著現代人的精神力度。
“哲學或者說思想意識的內容,在恰當的語境里似乎可以提高作品的藝術價值,因為它進一步證實了幾種重要的藝術價值,即作品的復雜性和連貫性。一種思想認識的見解可以增加藝術家理解認識的深度和范圍。”[12]作家筆下的人物和場景不僅代表了文藝作品本身的思想,而且也體現了作家自身的思想。作家在從事文藝創作時,往往會從自己獨特的哲學和思想歷史的立場出發敘述文學。20世紀90年代以來作家對政治運動的歷史記憶,在思想上有所突破,但其局限性也是明顯的。盡管蘇童《河岸》、嚴歌苓《第九個寡婦》、劉慶邦《遍地月光》、賈平凹《古爐》、尤鳳偉《中國:1957》、李西閩《好女》、莫言《生死疲勞》等幾部小說都有著較為復雜的思想內涵,典型的人物塑造,深厚的文化品格,這對每年出版幾千部長篇小說來說,卻難以代表文學創作的整體水平。小說創作不是把作家的哲學思想和歷史知識生硬地強揉進去,而是在于通過文學表達作家最為根本的人生態度和價值追求。但是很遺憾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作家缺乏80年代初期作家的那種自省意識和探索精神,他們的價值價值理念難以在文藝作品中得到有力的滲透和展露,未能對自身的文學世界給予足夠的理性觀照,任憑個人的興趣剪接歷史,夸張地虛構歷史,無病呻吟地對歷史發泄,這勢必會影響作家對文學藝術發掘與提升。作家對新中國歷史記憶的文學敘述,仍需作出艱苦的努力和大膽的探索。
[1]吳義勤.中國新時期文學的文化反思[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173.
[2]以賽亞·柏林.俄國思想家[M].彭淮棟,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169.
[3]皮埃爾·馬舍雷.文學在思考什么?[M].張璐,張新木,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298-303.
[4]喬斯·卡洛斯·貝爾梅霍·巴雷拉.創造歷史與講述歷史[M]//陳啟能,倪為國.書寫歷史(第一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45-51.
[5]蘇童.追憶那一段殘酷青春[N].鄭州日報(數字報).2009-04-17(08).
[6]梁海.尋找“河”與“岸”的靈魂——蘇童訪談錄[J].作家,2010(3):50-55.
[7]李詠吟.公民生命自由教育的沉淪[J].當代作家評論,2004(1):66-74.
[8]貝內德托·克羅齊.作為思想和行動的歷史[M].田時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125.
[9]蘇童.河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287.
[10]曹文軒.中國八十年代文學現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328.
[11]西格麗德·努涅斯.文學與思想[N].姚望,譯.光明日報,2013-06-28(15).
[12]勒內·韋勒克,奧斯汀·沃倫.文學理論[M].彭淮棟,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138.
[責任編輯:志 洪]
I206.7
A
1674-3652(2017)04-0090-06
2017-06-12
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族群互動與烏江流域鄉村戲劇研究”(16YJAZH077);長江師范學院高層次人才引進科研啟動項目“當代西南地區多民族文學生態研究”(2013KYQD04)。
張羽華,男(土家族),重慶酉陽人。博士后,副教授。主要從事地域文化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