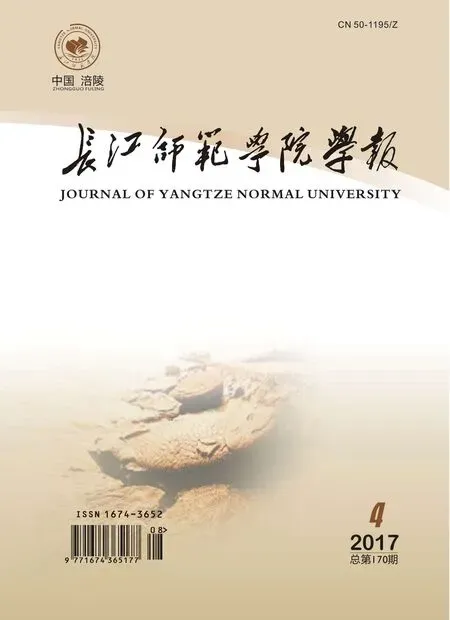六朝小農逃避賦役行為析論
郭 超
(廣西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1)
六朝小農逃避賦役行為析論
郭 超
(廣西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1)
六朝時期租調繁重,各類雜調、徭役層出不窮。小農欲改善家庭經(jīng)濟狀況,最有效的行為莫過于不納或少納賦稅。其時不乏各類竊改籍注者,他們謊報年齡、疾病等狀況;尋蔭大戶,入僧道戶;混入仕流,詐買軍勛、爵位;著錄官、私學生。這些逃稅避役行為雖然可以減少賦役方面的支出,但納賄或資買方式畢竟有二次行賄或大族役使的代價,且加劇了下層小農生活的貧困化。
六朝;小農;逃避賦役;依附;行賄
中古時期,朝廷正賦或輕,而各種橫調、雜稅、徭役多繁于正賦,小農①本文“小農”指以耕、織為主要生計,生活在鄉(xiāng)村社會中的以自耕農為主體的著籍民戶。賦役負擔實在不輕。正如王家范所揭示的那樣:“產(chǎn)量長一寸,賦稅量增一分,緊追不放,大體多占總產(chǎn)量的30%~50%上下。”[1]168但小農并非愚弱不堪,坐守困局,他們在政府課役、官吏盤剝以及天災人禍時,也有比較豐富的應對經(jīng)驗。就六朝時期小農而言,在通常情況下會選擇耕織結合,兼以園圃、采集、漁獵等補充生計。大多數(shù)小農還會將剩余農副產(chǎn)品及簡單手工業(yè)成品、半成品拿到市場出售,以及從事傭工、向富豪權貴借貸等度過危機。此外,小農為了規(guī)避或減少課役負擔,也有許多行為,這里僅就六朝時期小農逃避賦役行為略作分析。
一、竊改籍注
“古之有天下者,必有賦稅之用。”[2]1379控制編戶,編纂內容詳細的各類籍簿,依律征收賦稅是朝廷財政收入最重要的來源之一。從長沙走馬樓吳簡看,孫吳治下各類籍簿編纂已經(jīng)相當完善。自東晉始,紙取代簡牘成為官方文書書寫普遍采用的材料。小農著黃籍,黃籍登記家庭成員名字、地位、性別、年齡、健康狀況等。所有著籍項目都與小農是否承擔賦役以及是否享受政府優(yōu)撫政策密切相關。
漢代成丁年齡區(qū)間為15~56年,7歲以下以及60歲以上無課役。孫吳大致繼承了漢代的成丁標準。從走馬樓吳簡上看,吳國成丁的年齡仍為15歲,稱為大男、大女,15歲以下者稱小男、小女。老的年齡據(jù)簡牘所見最低為61歲,如“老男胡公年六十一踵兩足”(壹·5162),老男陳州年六十一(壹·5312),或許老的年齡界限為61歲。兩晉時期正丁的年齡區(qū)間擴大,為16~60歲,老的年齡推遲到66歲,半丁區(qū)間分為13~15歲、61~65歲。與之前相比,正丁的年齡段雖未增加,但老的要求提高到66歲;南朝大致延后,將正丁的年齡后延至18歲,“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3]674,征收體系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由之前“計貲定課”,按戶等征稅,逐步轉為按丁計征的丁中制度,調的標準也有所提高。
成丁年齡以及不課老人年齡規(guī)定事關小農切身利益,為了規(guī)避或減少賦役負擔,小農大多希望將成丁的時間推遲,免老的年齡提前。據(jù)尹灣漢簡,“西漢后期東海郡80歲以上老人有33871人,90歲以上者有11670人,分別占總人口比例2.42%、0.83%,這種比率甚至高于上世紀(筆者注:20世紀)90年代的高雄。”[4]557嘉禾年間,臨湘縣內有確切年齡記載的2499人,其中61歲以上的有271人,占比高達10.84%;臨湘縣殘疾人口約占樣本人口的9.68%,且男女比例為4∶1②相關統(tǒng)計可參見侯旭東《走馬樓吳簡初探》,文津出版社,2004年,第123-140頁。。臨湘縣老年人口過多,已經(jīng)達到人口老齡化的標準,其中不乏為了獲得免役特權而改齡者。在殘疾人口中男性比例很高,所患疾病多為“刑”“腹心”“雀”“踵”“盲”,雖可解釋為戰(zhàn)爭負傷或真實患病,但如此高的比例使我們不得不懷疑其中有假冒病殘以避征役者。
齊高帝時,竟陵王蕭子良上疏痛陳時弊,提到:“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應充猥役,必由窮困。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5]696百姓通過自殘來避徭役已經(jīng)成為一種無奈的選擇。在更多情況下,小農會選擇相對和緩的方式,如沈勃自恃吳興土豪,“輒聽募將,委役還私,托注病叛,遂有數(shù)百”[6]1687。沈勃通過招募部曲的方式,假以雜役,偽注病叛,成功使數(shù)百編戶脫離了朝廷控制。虞完之論道:“自頃氓俗巧偽,為日已久,至乃竊注爵位,盜易年月,增損三狀,貿襲萬端。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托死叛,停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疾。編戶齊家,少不如此。”[5]608百姓逃稅避役各有其法,大多是在籍注項目上做文章,主要有改齡(盜易歲月)、注疾(身強而稱六疾)、注爵(竊注爵)、注絕(戶存而文書已絕)以及托言死叛、偽言隸役等,從“編戶齊家,少不如此”可以看出當時社會避役的普遍化。南朝后期,來自北方的軍事壓力增大,南朝中央政府控制力僅局限于長江中下游部分地區(qū),這時各種征調課役的重壓也集中到這些地區(qū)的百姓,尤以揚州為劇。史載:
東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詐病,遣外醫(yī)巫,在所檢占諸屬名,并取病身。凡屬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假,并是役蔭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積年,皆攝充將役。又追責病者租布,隨其年歲多少。銜命之人,皆給貨賂,隨意縱舍。又橫調征求,皆出百姓。[7]156
從這段記載看,詐病避役由來已久,政府并非不知,只是安平之際,貨賂公行,不便揭露。一旦軍國所需,征調急迫,往年因行賄而避役者不得不在追還租布與繼續(xù)賄賂官吏中作出艱難的選擇。在此過程中,唯一沒有遭受利益損失的只有各級官吏。他們里通上下,緩則納輕賄,急則納重賄。最終沒有納重賄的小農不得不追償稅調,承擔新的橫調。在一輪“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余稅,且增為千”[5]692的過程中飽受煎熬。對于他們而言,改齡、注疾等并不能真正改善家庭經(jīng)濟狀況。
二、入仕流與買軍勛
六朝時期門戶觀念甚熾,對于小農而言,權門士族高不可攀,而士族內部分又為不同等級,舊門、次門雖勢不顯,但依然享有免役特權。朝廷歷來明士庶之別,在黃籍上甚至登記門第等級。有不少發(fā)跡之士人、將軍便出身于“三五門”“次門”“舊門”,如劉宋武念“本三五門”[6]2112。所謂“三五門”源自三五取丁制,來自民戶,后入役門,社會地位低下。宗越“本南陽次門”,趙倫之條次氏族,已淪入役門之列,后因軍功,得復列士族。小農當中資產(chǎn)豐厚者也可以改注籍狀,“詐入仕流,昔為人役,今反役人”[5]60。劉宋吳興太守王僧虔就因“聽民何系先等一百十家為舊門”[5]592以及私“度民與弟子”而遭免官。他之所以這么做顯然是收到了不少的好處。唐寓之起義攻占富陽時,“三吳卻籍者奔之,眾至三萬”[7]1928,。這里所說的卻籍者,即有不少昔日賄賂官吏詐注仕流近遭朝廷檢戶而去士籍的人。民間士庶之分在一定程度上演變?yōu)橘Y產(chǎn)厚薄之爭,出現(xiàn)“凡有貲者,多是士人復除。其極貧者,悉皆露戶役民”[5]808的社會狀況。上流社會“士庶之際,實屬天隔”,對于基層社會而言,士庶之別,蓋由貲定。凡貲厚者,歷盡巧偽,所謂“吏貪其賂,民肆其奸。”由于貪瀆之風盛行,原本嚴格的士庶界限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了,正如梁武帝時沈約上書提到的那樣:“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7]1462當然對于乏資露戶而言,這種賄賂成本過高,是他們難以承受的,而冒入行伍,竊得功勛或許更易為之。
將領與部曲之間之所以能夠形成較強的人身依附關系,除領主控制部曲生活的命脈——土地外,還與將領樂施小惠、濫注軍勛有關。蘇峻之亂平定后,“庾亮就溫嶠求勛簿,而嶠不與,以為陶侃所上,多非實錄”[5]609。可見逢戰(zhàn)之后,勛簿所上,多非其實。宋明帝泰始元年,益州刺史蕭惠開不遵朝廷法度,明帝遣其弟惠基宣旨慰勞。之后引起氐民不安,益州土人引“氐賊圍州城”。蕭惠基曉諭利害,幾乎兵不血刃就平定了益州之亂。還朝后,“惠基西使千余部曲并欲論功,惠基毀除勛簿,競無所用”[5]810。在沒有經(jīng)歷大的戰(zhàn)爭的情況下就有“千余部曲論功”,可以想見,在規(guī)模較大的平亂戰(zhàn)爭后,爭功者當不啻萬人,勛籍所載,可謂濫矣。宋大明年間后,“緣寇難頻起,軍蔭易多,民庶從利”[5]608,通過濫注軍勛而免役更加普遍。蕭齊時,朝廷籍簿不實十分嚴重,虞完之曾上書道:“自孝建已來,入勛者眾,其中操干戈衛(wèi)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勛簿所領而詐注辭籍,浮游世要,非官長所拘錄,復為不少。”[5]609濫注軍勛者多非前線將士,“天下合役之身,已據(jù)其大半”,這些人正是通過詐買軍勛而免役。
蕭齊初年,民間“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競行奸貨,落除卑注,更書新籍,通官榮爵,隨意高下。以新?lián)Q故,不過用一萬許錢。昨日卑微,今日仕伍”[8]59-60。“一萬許錢”于富人不過九牛一毛,但對于小農來說仍是一筆較大的數(shù)額。以當時物價而言,略相當于百斛之米,非尋常人家所能承受①蕭齊時“米當口錢,優(yōu)評斛一百”,既是優(yōu)評,當屬優(yōu)質米的高于市價的估價,可見常評米價尚不及百錢。拙文《東晉小農家庭經(jīng)濟狀況分析——以經(jīng)濟支出為中心》(《蘇州教育學院學報》,2016年5期)曾以80畝墾田數(shù)額估算支出、收入,認為年結余米23斛左右,這只是一種較為理想的狀態(tài)。東晉南朝雖然畝產(chǎn)達到2.5斛(米),但小農家庭墾田因大族侵奪、戰(zhàn)亂、災異等原因往往不過50畝,小農家庭年口糧約為百斛(米),若將稅調等支出考慮入內,則很難有較多的剩余產(chǎn)品。。時人亦深知其弊,鐘嶸曾上書梁武帝,奏稱:“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勛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臣愚謂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僥競。”[9]694梁武帝雖以為然并“敕付尚書行之”,但不見有顯著效果。騎都尉、散騎侍郎等職向來“二品士流”充當,庶民揮金而得,不難想見,二職以下買授必定亦濫。
總之,有資者有逃避賦役的訴求,而各級貪婪官吏有著錄籍簿、征收賦役的職能,二者一旦結合,便出現(xiàn)了不少通過買軍勛而混入仕流者。南朝后期,國家編戶不滿百萬,正常賦稅本就不能足納,這種行徑使本已陷入危機的財政狀況雪上加霜。未買軍勛、入仕流者在“雜役減闕”后承擔了更多的正調以及雜調、雜役,加劇了下層小農生活的貧困化。
三、尋蔭大戶與入僧道戶
六朝時期,士族地位上升,他們不僅左右朝政,控制地方,而且大肆“封略山湖”,孫吳時期已是“僮仆成軍,閉門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10]。其言雖不免夸張,但形象地反映出世家大族在經(jīng)濟生活中的強勢。王公貴人在法禁寬弛下莫不挾藏戶口以為附庸,小農依附大族,充當?shù)杩汀⒁率晨汀⒏诫`等也成為一種有效的逃稅避役行為。以“蔭客”為例,依制是“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衣食客三人……九品佃客五戶,衣食客一人”[3]674。實際情況是權貴依勢多逾此制。史載吳時會稽焦征羌“人客放縱”[11]1236。東晉時期,京口“刁氏素殷富,奴客縱橫,固吝山澤,為京口之蠹”[12]1846。大族蔭客放縱成為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重要因素之一。蕭齊時,“諸郡役人,多依人士為附隸,謂之屬名”[7]156。所謂役人即是須服役之吏民,多依士人無疑是為了取得附隸身份而免除徭役。他們雖能免朝廷之役但卻仍免不了為大族提供各類役使,“有奴客者,類多使役,東西分散,住家者少”[6]1319。由于被指派從事各種雜役,蔭客們已經(jīng)失去完整的家庭生活,可以說是附隸大族的代價。還有一類所謂“門生義故”,他們多非真正意義上的授業(yè)門生,而是大族依附人口中的一種,可以資賄買。劉宋顏竣“多假資禮,解為門生”[6]1966。又如徐湛之“門生千余人,皆三吳富人之子”[6]1844。一旦成為門生,便可不納課役,甚至可以得門主薦舉,獲得一官半職。但說到底,門主與門生之間只是利用與被利用的關系,門生雖然部分脫離了朝廷的控制,得以“優(yōu)復蠲免”,但仍不免于為門主從事農作、雜役等。謝靈運“義故門生數(shù)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7]540。門生還要忍受各種索納,沈勃“周旋門生,競受財貨,少者至萬,多者千金”[6]1687。從索賄金額上看,非富室不堪承受,通過納資禮等賄賂手段成為門生并得以維持的只是極少部分的富裕小農。
六朝統(tǒng)治者對佛教多加扶持,不僅施以數(shù)以億計的錢財,而且設僧正管理天下僧眾。一時之間,“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7]1720。在世家大族中也有大量信徒,例如王坦之“舍園為寺”[13]482;張孝秀“有田數(shù)十頃,部曲數(shù)百人”,敬慕三寶,“率以力田,盡供山眾”[9]752。世風浸染,小農多有事佛者。對于普通民眾而言,信奉佛教不僅是一種精神生活的安慰,更有現(xiàn)實的經(jīng)濟利益。僧道戶不著民籍,不納賦稅,“寸絹不輸官庫,升米不進公倉”[14]3455,他們甚至“家停大小之調”。小農入僧道戶或將自己的土地寄名寺產(chǎn)以避賦稅,這種風氣在南朝尤甚。“民間生不長發(fā),便謂為道人,填街溢巷,是處皆然。”[5]609百姓剃度為僧或假名出家,“所在郡縣,不可勝言。又有白徒尼則皆畜養(yǎng)女,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7]1721-1722。上層僧尼大多資產(chǎn)豐沃,富比封君,乃有一僧資財數(shù)百萬者。朝廷甚至將富裕僧尼與富有之家并稱,宋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南侵,形勢嚴峻,宋文帝詔:“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有之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并四分借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8]250可見寺產(chǎn)之豐厚。
對于小農而言,寄名僧籍或者托為寺產(chǎn)并非萬事大吉,只是剝削方式由政府課役轉為寺僧役使。劉宋時釋法顯3歲便度為沙彌,“嘗與同學數(shù)十人,于田中刈稻”[13]87。僧眾尚且如此,細民為生計所迫,受寺門奴役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東晉海陵人董幼,“年十八,謂母曰:‘幼病困,不可卒愈,徒累二兄,終不得活。欲依道門灑掃,以度一世。’”[15]784除此之外,僧尼不守寺界,肆意侵占原屬國有的山林、水澤,對民產(chǎn)也不放過。梁武帝就曾下詔:“公私傳、屯、邸、冶,爰至僧尼,當其地界,止應依限守視;乃至廣加封固,越界分斷水陸采捕及以樵蘇,遂致細民措手無所。”[9]86他們還欺騙信眾,“交納帛布,賣天堂五福之虛……豫征收贖,免地獄云(六)極之謬殃”[14]3769。
寺院依附者眾多,儼然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桓玄在與僚屬討論沙汰僧眾時談到都下“避役鐘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廟,乃至一縣數(shù)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積不羈之眾”[14]2141。不羈之眾,多為貧民,由于衣食無著,這些依附寺院者甚至“謀反”。比較大的如宋孝武帝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羌人高阇謀反”[6]2386,皇帝因之震怒,下詔:“精加沙汰,后有違犯,嚴加誅坐。”民間非戒行精苦者,強令還俗。梁時北兗州“沙門僧強自稱為帝,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9]463,一時聲勢頗大。寺產(chǎn)豐厚一度成為統(tǒng)治階層覬覦的對象,“武帝軍東下,用度不足,偉取襄陽寺銅佛,毀以為錢”[7]1291。依附大戶的小農,“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帥妻孥,為之服役”[8]13,不僅從事農業(yè)生產(chǎn)活動,還要為富人提供各種雜役,這實際上不亞于朝廷各類勞役。他們的人身自由受到較為嚴格的限制,“左右驅馳,動止所須,出門甚寡”[6]1319。他們并沒有獨立的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小農非形勢逼迫,一般不會選擇依附大戶,奴事富人。
四、著錄官、私學生
以資納賄成為大族門生或者買軍勛、入仕流畢竟需要較高的成本,且有二次行賄或被著籍官吏糾正的風險,通過入官、私學而免役相對來說其成本較低且屬合法。此時六朝教育也呈現(xiàn)多樣化趨勢,“官學與私學并存,是六朝教育的基本格局。”[16]無論著籍官學生還是私學生本人都享有免役權。在走馬樓吳簡中有私學簡數(shù)百枚,私學別立籍簿,“從目前掌握的資料,孫吳時期的私學除了繳納限米之外,未有繳納其他賦役的記錄,也沒有服徭役的跡象。”[17]215虞翻遠徙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shù)百人”[11]1321,當有不少“因連避役”者。同時期的蜀人李寬“能祝水,治病頗愈”,至吳后,“避役之吏民,依寬為弟子者恒近千人”[18];東晉時庾亮在武昌開設學館,明言“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為生”[6]364,從中可以窺見入學免役成為當時之通例,故需禁止。這些官員、名士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號召力也與小農“避役”訴求的強烈有關。東晉孝武帝時,國子祭酒殷茂進言:“自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yè)避役,就存者無幾;或假托親疾,真?zhèn)坞y知。”[6]364由于生源“混雜蘭艾”,平民子弟多為避役,故一旦著錄為學生,目的達成,便不篤志向學。
南朝中央官學生享有免役、供食宿以及物質賞賜等權利,其生源通常有士族身份限制。名士隱居教授,對學生沒有出身限制,其數(shù)目少則數(shù)十百人,多則數(shù)千人。例如沈驎士“講經(jīng)教授,從學者數(shù)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5]943。賀玚“于鄉(xiāng)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yè)者三千余人”[7]1509。徐孝克,“每日二時講,旦講佛經(jīng),晚講禮、傳,道俗受業(yè)者數(shù)百人”[18]337。之所以形成如此宏大的授學場面,一方面與為師者學藝精湛、師德高尚有關。另一方面也是徭役繁重、細民以避役為目的而著錄為學生的結果。
五、結語
通過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小農逃稅避役主要是:編戶民改籍注與改變隸屬脫離編戶。買軍勛、官爵,入仕流實施的成本較高,“一萬許錢”并非普通小農家庭所能承受。改籍注在政府括戶和檢籍下有被糾正或二次行賄的風險,著錄官、私學生只能本人免役,作用有限。尋蔭大戶與入僧道戶只是剝削對象由政府轉為大族、寺觀,仍須忍受各種役使。六朝尤其是南朝富裕小農通過行賄或資買不納或少納賦稅十分普遍,陳時山陰“縣民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奸,全丁大戶,類多隱沒”[18]460。在這種情況下,中下層小農不得不承受朝廷編戶損失后稅調增加的負擔。
參考文獻:
[1]王家范.中國歷史通論(增訂本)[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2.
[2]鄭樵.通志二十略(下)[M].王樹民,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5.
[3]魏征,等.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4]邢義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與社會[M].北京:中華書局,2011.
[5]蕭子顯.南齊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2.
[6]沈約.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7]李延壽.南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5.
[8]杜佑.通典[M].王文錦,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8.
[9]姚思廉.梁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10]楊明照.抱樸子外篇校箋[M].北京:中華書局,1991.
[11]陳壽.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1959.
[12]房玄齡.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13]釋慧皎.高僧傳[M].湯用彤,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
[14]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M].北京:中華書局,1958.
[15]張房慕.云笈七簽[M]//道藏(第22冊)[M].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16]張承宗.六朝教育格局多樣化[J].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1):5-10.
[17]于振波.長沙走門樓初探[M].[中國臺灣]臺北:文津出版社,2004.
[18]王明.抱樸子內篇校釋(增訂本)[M].北京:中華書局,1986.
[19]姚思廉.陳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2.
[責任編輯:丹 涪]
K235
A
1674-3652(2017)04-0077-05
2017-01-11
郭超,男,河南信陽人。主要從事魏晉南北朝經(jīng)濟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