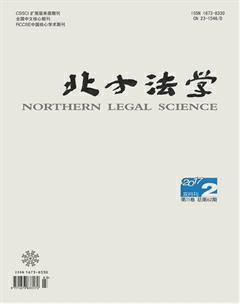1952年司法改革運動與法學界的反思
趙曉耕+段瑞群
摘 要:1952年至1953年的司法改革運動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司法改革,其理念與制度產物仍影響著現今司法體制的建構。司法改革運動的一條隱形動因是破解“案多人少”,重塑審判工作模式,為新中國司法制度提供“人民屬性”的法理詮釋,并嘗試建設“政治維度”、“人民維度”和“法律維度”和諧共生的新型司法制度。1957年整風期間,法學界對司法改革運動進行了反思與批判,但囿于意識形態干擾,最終釀成“反擊右傾擴大化”,導致“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突出,司法制度全面傾斜“政治維度”,進而演變成為新中國法制建設的災難。
關鍵詞:司法改革運動 舊司法人員 人民司法
中圖分類號:DF0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330(2017)02-0149-12
1949年,勝利來臨,中國共產黨控制區突然大擴展,使黨深感進行全國統治所需要的人員和技能不足。①一方面中國共產黨自身極度缺乏專業司法人員,另一方面為了更好地團結大量國民政府留下的司法工作人員,服務于政權建設,采取了“包下來”和“量才使用”的政策。②但是,“國家本質變了,法律也變了”,所以“舊的司法工作人員”必須經過改造。1952年元旦,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舉行的團拜會上號召全國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員一致行動,大張旗鼓、雷厲風行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斗爭。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下達限期發動“三反”運動的指示。③隨后,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指導中央政法各機關聯合組織四個觀察組,于1952年5月中旬前往華東、中南、東北、西北及華北山西、平原等地,視察各地人民法院的情況。
視察的結果令新中國的領導們頗感失望,認為法院存在嚴重的“組織不純和思想不純”問題,無法通過“三反”運動徹底解決,有必要發動一場“轟轟烈烈”的司法改革運動,徹底改造人民法院。于是,經中共中央批準,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從1952年6月到1953年2月在全國司法系統發起了一場大規模的司法改革運動。1952年8月13日,政務院審議通過司法部《關于徹底改造和整頓各級人民法院的報告》,8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必須徹底改革司法工作》的社論,要求組織開展司法改革運動,以“徹底改造和整頓各級人民司法機關”。參見《必須徹底改革司法工作》,載《人民日報》1952年8月17日第1版。相比其他地方,北京市司法改革運動進行得要快一些,總體上在1952年11月中旬基本結束。北京市司法改革經驗經中央向全國推廣,產生了很強的示范效應。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北京歷史》(第二卷),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87頁。筆者主要以北京市司法改革運動,特別是舊司法人員的清理改造為視角,試圖為學界展示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司法改革”的歷程,并嘗試剖析發動司法改革運動的深層次動因。
一、北京市司法改革運動概述
1948年2月6日,中共北平市委8名干部正式接管北平地方法院及其檢察處、河北高等法院及其檢察處,最高院民刑分庭及檢察署、看守所及第一、第二模范監獄等9個單位。對于舊司法人員的定性與分類,主要參考中共地下黨掌握的資料,并且作出了擬試用、受短訓、送學校、資遣回籍、另行安置等處置。《北平市法院接收工作初步總結》(1949年4月8日),載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48.12—1949)》,中國檔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367—368頁。或許是因為和平解放的緣故,北京地區的舊司法人員并不是完全“包下來”,而是采取了以舊司法人員的職級作為“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具體而言,對舊司法人員的甄別處置主要區分為三種情形:一是推事、檢察官以上的高級職員(職級屬于國民政府縣級以上)以及法警、看守、執達員等履行國家暴力職權的人員,被停止職務和收繳武器,聽候處理;二是下級職員,主要是文書人員、技術人員等組織集中學習教育,如果不愿意參加學習教育,亦可聲明退出;三是年老體弱并且缺乏工作能力的,可以資遣回家轉業。除此之外,凡是在舊法院中工作的地下革命工作人員不能按舊司法人員處理;過去參加革命斗爭的民主人士,只是具備舊觀點、舊作風的,應該作為思想問題處理,不能作為舊人員看待;學過舊法律而沒有做過舊司法工作的青年,不與舊司法人員同等看待。張友漁:《在司法改革報告會上的講話(1952年9月6日)》,參見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2)》,中國檔案出版社2002年版,第477—478頁。據此,北京市人民法院對原北京地區舊法院385名人員分別做了處理。其中,試用人員(即書記官以下)137人,占全部舊司法人員的35%。北京市司法機關的接管工作成為全國參照標準,例如蘭州解放后,甘肅省舊司法機關接管的主要依據就是中共中央《關于平津司法機關之建議》和《關于接管國民黨司法機關的補充建議》。參見甘肅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甘肅省審判志編纂委員會編纂:《甘肅省志(第七卷)·審判志》,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126頁。
1952年6月,北京市司法改革委員會正式成立,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張友漁擔任主任,時任北京市法院院長王斐然、市公安局副局長馮基平、北京市法院副院長賀生高三人為副主任,公安局、檢察院、監察委員會、市總工會、市農會、市婦聯、市青年團各推一個負責人為委員。委員會下設司法改革辦公室,負責搜集整理材料、組織學習、發動群眾、檢查工作、宣傳報道等具體工作。前引⑤,第85—86頁。根據工作方案,北京市司法改革運動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由市人民法院召開市、區人民法院干部會,報告并闡明司法改革的意義,號召全體干部對主要干部的舊法觀點進行檢查、揭發,并搜集、提供有關舊法觀點的實際材料。1952年8月23日,北京市人民法院召開全市法院干部會,院庭領導進行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北京市司法改革運動正式開始。8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進行司法改革工作應注意的幾個問題的指示》,提出司法改革運動從清算舊法觀點為切入口,但手段必須是“組織辦法”。至此,中共中央明確此次司法改革運動的重點是“組織整頓”,實際上就是重在清理舊司法人員,提升司法機關“純凈度”。第一階段發現法院的主要問題是:市人民法院的領導在使用舊司法人員方面,存在不經過改造就使用或邊使用、邊改造的問題;另外,使用老干部也是以有無舊法基礎作為重用的標準,還要學習舊司法人員的“業務”、“技術”,致使舊司法觀點和作風蔓延。具體表現為:缺乏群眾觀點和對人民負責的精神。例如,因受虐待請求離婚的“離婚到民庭,刑庭不管”;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輕信口供、假證據、表面情節或憑主觀臆斷處理案件;工作作風嚴重脫離群眾,單靠坐堂問審。《中共北京市委關于司法改革第一階段進行情況和初步總結向中央、華北局的報告(1952年10月8日)》,載前引⑦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書,第531—533頁。
第二階段,由司法改革委員會召開市、區人民法院干部及公安局、檢察署等有關部門參加的干部會,號召所有司法干部檢查、檢討,并動員市民對法院工作提出批評。1952年9月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及市司法改革委員會,召開了市、區人民法院、全體工作人員、公安局偵訊工作人員、檢察署、監委會有關干部,及市府所屬各單位科長以上干部大會。張友漁在大會上作了報告,認為北京市人民法院依然存在較為嚴重和普遍的“組織不純”和“思想不純”問題,主要是舊司法人員比重高達52%,存在重用舊司法人員的現象。此外,少數人員貪贓枉法,對反革命分子重罪輕判,甚至舊司法人員中的反革命分子未被清除。參見《北京市司法改革工作全面展開》,載《人民日報》1952年9月13日第1版。在這次大會上,北京市人民法院院長王斐然、民庭庭長李葆真作了檢討報告。為促使司法改革運動深入開展,司法改革運動進入發動群眾揭露舊司法人員違法亂紀階段。9月10日,北京市司法改革委員會發布《關于開展司法改革運動的公告》,號召全市人民揭發一切訴訟上的不合理現象。這個階段發現的主要的舊司法觀點是強調“契約精神”、“先公后私”、“同情資本家”、“為封建殘余勢力辯護”、“無法可司”、“官無悔判”等。參見《中共北京市委關于司法改革運動第二階段總結向中央、華北局的報告(1952年11月22日)》,載前引⑦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書,第632—634頁。
第三階段,是總結與建設階段,對具體人、具體事,分別處理;批判舊制度、舊方法,建立新制度;清理舊司法人員,補充干部。10月中旬以后,北京市司法改革委員會根據運動中發現的問題,開始甄別舊司法人員,調整機構和補充干部。因為“三反”運動中已經清理大批舊的司法人員,在“三反”運動中,北京市人民法院清洗了40名(另有執行員等16人未計入)有貪污和其他違法行為的分子,其中,大部分為留用或新吸收的舊司法人員。參見《北京市人民政府關于政法工作的報告(1952年8月11日)》,載前引⑦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書,第354頁。這次司法改革運動確定清洗8人,另有5人被調離審判工作崗位。經過整頓,北京全市法院中還有在舊法院參加過審判工作,仍被留在審判部門工作的11人,占全部審判人員的5%。為了徹底解決“組織不純”的問題,北京市人民法院分別從轉業軍人、市政府行政干部學校學員以及其他就業人員中調用了78名干部,這些人員黨員29人、團員25人,即黨團員比例約69%。《中共北京市委關于司法改革運動第三階段工作總結向中央、華北局的報告(1953年1月27日)》,載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3),中國檔案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9頁。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3年1月27日北京市委上報中央、華北局關于司法改革運動第三階段工作的總結中提及,從司法改革運動開始到1952年10月20日,市司法改革委員會共收到來信537件,其中,對案件處理本身不滿的48%,對處理案件遲緩不滿的29%,反映法院干部作風不好的9%,懷疑法院干部貪贓枉法的1.6%,建設性意見4%,其他意見8.4%,并且得出結論:“這些來信中正確的占60%,說明我們法院的確存在不少缺點”。前引B15,第37—38頁。可是,根據相關學者查證,此前市人民法院認為,這537件來信中“正確的占26%, 不正確的占74%”,后來因為迫于壓力和政治需要而調整為“正確的占60%”。參見《市府關于堅決糾正統計、報告中的粗枝大葉作風的通報》,北京市檔案館 002- 005- 00017;《北京市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運動中群眾來信情況的檢查報告》, 北京市檔案館 002- 005- 00017。轉引自董節英:《1952 年北京市的司法改革運動》,載《北京黨史》2007年第2期,第23—24頁。1952年11月1日,《人民日報》在報道各地司法改革運動中,點名表揚北京市是“認真開展司法改革運動的地區”,并指出其具備的三個特點,即領導高度重視、思想改造與組織整頓相結合以及法院內部檢查和發動外部群眾揭發檢舉相結合。參見《全國司法改革運動逐步深入華東區 大部省市法院已進入建設階段》,載《人民日報》1952年11月1日第1版。
二、清理舊司法人員與“案多人少”矛盾
1952年8月13日,司法部部長史良向政務院政務會作了題為《關于徹底改造和整頓各級人民法院的報告》。在報告中,史良分析了全國各級法院舊司法人員的狀況以及問題:一是舊司法人員比例過高。截至1952年8月,舊司法人員平均占全部法院干部的22%,并且不少大、中城市及省級以上法院,舊司法人員比例更高,甚至少數地區法院工作人員絕大多數都是舊司法人員;二是舊司法人員掌握審判權;三是舊司法人員的改造教育,僅有一部分人員有進步,多數人不僅進步很少,甚至還是反動的,情況是“極為復雜與嚴重的”。史良:《關于徹底改造和整頓各級人民法院的報告》,載《人民日報》1952年8月23日第1版。具體闡述如下。
第一,“共產黨法院,國民黨掌握”。新中國成立初期,絕大多數法院是在軍事勝利迅速發展形勢下,派少數干部接管了原來的舊法院而建立起來的。這一點在國民黨長期掌握控制權或軍閥割據的地區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在武漢、廣東、江西、廣西等各級法院的舊司法人員中,反動黨、團、特務分子就高達64%。其中,太原市人民法院舊司法人員中的反動黨、團、特務分子占舊司法人員比例高達83%。前引B19。再例如,浙江省、福建省、蘇南區、上海市法院的1259個舊司法人員中,反動黨團、特務骨干分子等占66.1%,其中,有偽省院委員、偽特刑庭庭長和“戡亂條例”起草人,偽軍統特務訓練班指導員和偽中統特務行動支隊長等。魏文伯:《從司法改革問題談起》,載《法學》1958年第1期,第2頁。由此可見,“在司法改革以前,我們全國各地的不少人民法院,確如當時群眾所指責的,是‘共產黨法院、國民黨掌握”。陶希晉:《論司法改革》,載《法學研究》1957年第5期,第13頁。這對于主張徹底廢除舊法制和舊法統,徹底清算舊法思想,并努力建立革命法制的新執政者而言,絕對無法忍受。
第二,充任資產階級“爪牙”。資產階級對新中國司法機關的進攻方式是“打入”和“拉出”,但特點卻是和舊的反動統治階級的爪牙(部分未經改造的舊法官、舊律師等)互相勾結,為非作惡。具體而言,一是賣放案犯;二是盜竊和出賣審判情報;三是有罪判無罪,重罪輕判,盜竊國家財產;四是恐嚇欺騙,敲詐勒索;五是利用調解的機會,索取賄賂;六是利用職權,偷蓋印章,營私舞弊;七是和行賄當事人互相勾結,編排供詞,甚至偽造證據,借以顛倒是非,為行賄人安排有利于“勝訴”的條件,從中貪贓受賄;八是侵吞、盜賣沒收的贓物,克扣囚糧,貪污監所生產款。雖然該文章總結出八條部分舊司法人員的罪惡行徑,但實質上僅涉及四個司法腐敗個案(即哈爾濱市人民法院審判員關東平、廣州市人民法院學習審判員李自強、最高人民法院民庭書記員史靖侯、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人員顧裕尚),且其中五條罪狀均是其中二人所為(最高人民法院民庭書記員史靖侯、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人員顧裕尚)。參見李堅:《貪污分子在人民司法機關中的罪惡活動》,載《人民日報》1952年3月16日第3版。據上海、南京、杭州三個市法院和蘇南全區統計,在法院系統的貪污分子中59.52%是舊司法人員,而在全體舊司法人員中有50.09%有貪污行為。前引B19。例如,北京市人民法院看守所戒護員沈鴻德、郝銳新原系舊的司法機關工作人員,不改舊習,因為收受犯人家屬賄賂、私自為犯人傳遞信件與物品、嫖妓等行為被判刑。《肅清舊法院傳統惡習 沈鴻德等貪污腐化被判徒刑》,載《人民日報》1950年1月18日第4版。再例如,福建省人民法院舊人員很多,大部分貪污成習,他們在外面有專門的“經紀人”包攬訴訟,在法院內有兩個貪污“辦公室”,專門研究敲詐、勒索、分贓的辦法,并根據行賄的多少,來決定官司的勝負。李劍飛:《資產階級向人民司法機關的猖狂進攻》,載《人民日報》1952年3月20日第3版。
第三,舊法思想和舊司法作風。留用人員和混入的舊司法人員中壞分子的貪贓枉法和違法亂紀現象突出,集中表現為是“四幫五不”。“四幫”,即幫助反革命危害人民,幫助地主壓迫農民,幫助不法資本家壓迫工人,幫助違法分子開脫罪責。“五不”,即不理:強調不合司法程序,不受理人民群眾的控告;不傳:雖然理了,但又拖延很久,不發傳票;不問:當事人傳來了又拖延不問;不判:問了以后也好久不判;不行:判后又不執行。參見《堅決克服部分司法機關中的嚴重不純現象 全國將展開司法改革運動》,載《人民日報》1952年8月17日第1版;曾鏡冰:《福建省的司法改革工作》,載《人民日報》1952年9月2日第3版。此外,在審判反革命案件時“毫無人民立場,敵我不分”。具體表現在:一是舊司法人員堅持“法律不溯既往”的所謂舊法觀點,導致一些罪惡深重背負血債的反革命分子,重罪輕判,甚至無罪釋放。二是堅持所謂的“法無明文規定者不罰”以及以“預備犯”、“未遂犯”等為理由,從輕懲處蓄謀組織暴亂或潛伏待機破壞的反革命分子。三是以所謂“非本庭管轄”、“須另案起訴”等舊“司法程序”和“管轄制度”為托詞,放任反革命分子逃脫法律制裁。參見周增華:《舊法觀點是怎樣包庇了反革命罪犯的 必須徹底改革司法工作》,載《人民日報》1952年8月31日第3版。再例如,不聯系群眾,問案不調查研究,不實事求是,坐守衙門,孤立辦案;玩弄反動的司法八股,判決書艱澀冗長,堆砌舊法術語,滿紙陳詞濫調、空話連篇,使人看了不懂。參見前引B21。
第四,毒害法院其他干部。1951年5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批判司法機關的一些干部被反動法學理論“俘虜”,推崇所謂的“六法全書”,參見《進一步鞏固與發展人民民主專政》,載《人民日報》1951年5月29日第1版。甚至一些法院的負責人和老干部不僅階級立場模糊、舊法觀點濃厚,把舊法人員當成“專家”,還號召青年干部向他們學習,甚至讓反革命分子作鎮壓反革命工作的總結,讓有三個老婆的舊司法人員主持宣傳婚姻法等等。參見前引B19。
司法改革運動結束后,全國2063個法院共清除了壞分子和不適宜作為人民司法工作者5557人,占原有干部的24.71%。在這批人員中,大部分是舊司法人員,另有小部分是蛻化變節的新老干部和成分不純混入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與此同時,各級法院又補充了6505名干部。周繼湖:《駁斥資產階級右派對司法改革運動的誣蔑》,載《中南政法學院學報》1957年第2期,第36頁。根據1953年司法部統計,全國還有舊司法人員2369人留在司法機關,其中有1142人做審判工作。此外還有調訓的500人,受訓后一般又回去繼續工作。前引B21,第3頁。1953年4月11日至4月25日第二屆全國司法會議召開。董必武在大會上發言時,認為當前司法工作存在最嚴重的問題,一是錯捕錯押、刑訊逼供和錯判錯殺;二是案件大量積壓,并且認為這是由于缺少辦案水平和經驗的革命知識分子和軍人的審判人員,以“簡單、粗暴、魯莽的辦法辦案的結果”。參見《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280頁。
通常認為,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展司法改革運動,大范圍清理和改造舊司法人員是“鞏固人民政權、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維護革命秩序的要求”,參見陳光中、曾新華:《建國初期司法改革運動述評》,載《法學家》2009年第6期,第1頁。或者“是以反對舊法觀點和改造整個司法機關為內容的運動……在司法和其他法律工作方面進行的一次群眾性的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前引B22,第12頁。這些評述固然沒有實質性問題,但是卻沒有從“技術層面”,即司法審判工作需求角度進行解釋。筆者認為,司法改革運動深層次的原因是傳統的司法審判模式無法破解“案多人少”的現實矛盾,“技術派”的“坐堂問審”無法為新生政權的司法機關供給“政治屬性”和“人民屬性”。也就是說,司法改革運動,特別是清理改造舊司法人員的過程就是“人民司法”轉變為“人民的司法”的過程,趙曉耕、沈瑋瑋:《人民如何司法:董必武人民司法觀在新中國初期的實踐》,載《甘肅社會科學》2012年第2期,第91頁。進而實現“人民政權”的合法性詮釋。
新中國人民法院成立以來,案多人少的矛盾始終如影相伴。例如,截至1950年5月4日,北京市法院除反革命案件之外,尚有積案3508件。其中,羈押待判的犯人1156名,當時北京共有戶口44萬,平均125戶即有一未了案件(每案牽涉的人數平均4~5人)。案件的嚴重積壓,導致群眾頗有怨言,甚至有人說“解放后,諸事都有改革,就是法院積壓案件還和國民黨差不多”。彭真:《關于清理積案問題(1950年5月24日)》,載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0)》,中國檔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頁。嚴峻的案件積壓和百姓評價,對新生政權的領導者造成巨大壓力,對政權的“合法性”和“人民性”直接造成威脅。案件積壓產生的原因,除司法人員不夠、法院經驗不足之外,主要還是舊案件審理方式的“坐堂問審、提筆下判”和司法程序的“文牘主義”,無法滿足新中國成立初期案件的急劇增長的客觀要求。除了北京,各地法院也普遍存在積案多而干部太少的問題,特別是市縣一級基層組織更為嚴重。例如,1950年6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沈鈞儒在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作的法院工作報告中就以上海市、天津市、唐山市為例,認為就當前法院的收案、結案和干部比例來說,實現收結平衡“難以做到”。例如,上海1950年2月底有積案10962件,經過2個月的突擊清理,到4月底積案尚有6733件;天津和唐山就其收案、結案和干部比例來說,天津必須每月每人平均辦案80余件,唐山每月每人辦案50件,才能收結平衡,但這是難以做到的。參見沈鈞儒:《人民法院工作報告(1950年6月17日在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的報告)》,載《人民日報》1950年6月21日第1版。
為了改變“案多人少”矛盾,1950年5月中旬,北京市抽調247名干部到法院協助突擊清理積案,到6月22日,共清理4328件案件,主要工作方法就是審判組分駐各區就審,采用簡易判決書,案卷單替代繁雜的判決書和調解書。聶榮臻:《關于執行1950年度工作計劃的報告(1950年8月8日)》,載前引B39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書,第305—306頁。但是,臨時抽調其他機關干部,“幫助”法院清理積案只能是杯水車薪,無法徹底扭轉案件的快速增長與審判效率之間的矛盾。1951年,北京市人民法院、區法院和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收初審案件34728件,比1950年增加43%。其中,刑事案件增加14.7%,民事案件增加59%,結案31987件,未結5189件。北京市認為,司法工作的主要不足與缺點就是“留用的舊司法人員很多,舊司法制度的殘余影響很大,官僚主義和文牘主義也很嚴重”。《北京市人民政府關于政法工作的報告(1952年8月11日)》,載前引⑦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書,第363—354頁。從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來講,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司法改革運動,清理舊司法人員,清算舊司法作風便成為當時執政者的最佳選擇。
三、法院新干部選任與審判模式重塑
1953年1月底,全國大部分地區司法改革運動的組織整頓與思想改造階段已經基本結束。《全國大部地區司法改革工作已收實效 少數地區有“夾生”現象還須進行補課》,載《人民日報》1953年1月28日第3版。大批舊司法人員被清理之后,案多人少的矛盾進一步加劇,補充法院干部成為現實且緊迫的任務。8月31日,司法部在《關于執行第二屆全國司法會議決議的指示》中指出,“目前各級人民法院缺額甚大,骨干甚弱,而積案又多,應盡速停止司法領導骨干的外調”,要求以省、市為單位通盤籌劃,在1954年6月以前分批、分期按應增加的數目補齊。選拔各級法院干部的標準是“德才能夠勝任”,重點是“政治純潔,并有一定工作經驗與文化程度,經過短期訓練即可稱職的干部”。《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關于執行第二屆全國司法會議決議的指示(1953年8月31日)》,載《人民日報》1953年9月10日第1版。從上述指示來看,“德”與“才”的標準與其他黨政機關領導干部選任標準并沒有本質的區別,司法審判的專業屬性并未得到突出與強調。從各地的實踐來看,新法院干部的選任標準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政治標準:立場堅定。各級法院補充的領導干部和審判業務骨干,主要來源于其他單位和系統中“立場堅定、觀點正確和熟悉政策的老干部”,以及現有司法干部中經過實踐證明立場堅定、工作努力的積極分子。前引B19。以北京市為例。新中國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法院院長、副院長、審判員由市人民政府任免,但須經過中央和華北局批準。區法院院長由市人民政府任免,其他人員由區人民政府任免,但須經市人民法院同意。1953年,根據中央人民政府任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暫行條例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暫行組織大綱,北京市人民政府明確規定:市人民法院院長、副院長的任命須經市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報請政務院任免或由政務院直接任免。根據1954年9月頒布的《人民法院組織法》規定,法院院長與其他審判人員只要具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年滿23歲,且沒有被剝奪政治權利即可擔任。即無論是法院院長還是副院長、庭長、副庭長、審判員及其他工作人員的任用,無須進行法律專業知識考試,學歷和專業也僅僅是參考條件。經過1952年司法改革運動之后,任命審判人員的政治審查十分嚴格。凡是家庭及本人政治條件不符合要求者,一般均不予任命,甚至社會關系復雜者也要受到影響,致使當時北京法院的工作人員有相當數量的初中或小學文化程度者。
二是階級標準:工農青婦。司法改革運動結束后,全國各級司法機關調進了6500多名干部和工人、農民、青年、婦女中的積極分子進入法院工作。《全國各地司法改革運動收到良好的效果 司法工作人員開始樹立了人民司法觀點和作風》,載《人民日報》1953年5月16日第3版。之所以如此,首先是這些新審判員具有鮮明、堅定的維護工人階級利益的立場;其次,他們具有執行群眾路線,“善于不辭辛苦地赴現場調查案情,細致分析事實,依據案件性質,作出嚴正的判決”。例如,1957年8月,新華社記者對上海市15個基層人民法院中70個工人、店員出身的審判員的辦案情況進行了調查。為了說明“工農法官”案件辦理質量,記者選取了1957年1月到7月,這些審判員審結的7000多件刑事和民事案,其中一審判決或者調解處理正確,以及因當事人無充分理由被駁回上訴而維持原判的案件,共占案件總數的96%以上;由于當事人上訴,上級法院發現判決欠妥而進行重審和改判的案件,不到4%。在這7000多件審結案中,沒有一件是完全冤枉和完全判錯的。魯影:《誰說工農審判員不懂法律?》,載《人民日報》1957年8月22日第4版。
三是業務標準:又紅又專。所謂“紅”,就是共產主義的思想和政治;所謂“專”就是專門的業務和技術。司法工作者不紅就不可能專(不是紅色專家,就只能是白色的“專家”,或者灰色的“專家”),而不專也就不會運用法律來貫徹政策方針,實現政治目的,并且在政治、思想上容易上別人的當,甚至被敵人繳械。據1956年底統計,全國司法干部中,有60%是1949年解放后參加工作的,既缺乏革命斗爭經驗,也缺乏生產知識和勞動鍛煉,一般地說,很少做到“又紅又專”。韓幽桐:《司法工作者需要又紅又專》,載《人民日報》1958年4月10日第7版。相比較其他地區,北京地區審判人員文化水平和專業素養還是較高的。到1957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共有審判員、助理審判員46人,有大專學校畢業及在政法院校學習過的31人。賀戰軍:《嚴斥右派分子向人民司法工作進攻的幾個謬論》,載《法學研究》1957年第5期,第40頁。
四是作風標準:群眾路線。司法改革后,各地人民法院普遍采用了調查研究、聯系群眾的審判方法,組織巡回法庭,實行“帶卷下鄉、就地審判”,“下鄉收案、及時審判”,改變了過去單純“坐堂問案”的舊作風。例如,山東省大多數縣級人民法院院長在司法改革后先后帶領干部下鄉,和群眾一起調查案情,向群眾講解政策,就地審判,及時解決了不少懸案。陜西省人民法院在司法改革后曾組織工作組到長安、武功等10個縣(市)進行巡回審判,在一個月內處理了130多件復雜的案件。天津市人民法院普遍采用了集體調解與公開審判相結合,全面調查與就地審訊相結合的辦法,45天就清理了4760件積案和540件長期積壓的復雜案件。新參加審判工作的浙江省嵊縣人民法院女勞動模范黃苗琴,以高度積極性克服了自己文化程度低和業務不熟悉的困難,依靠群眾,采取調解的辦法辦案,她領導的巡回審判小組在7天內就處理了48宗案件。前引B47。1952年底,即北京市司法改革運動末期,中共北京市委曾經對新并入京西礦區人民法院的原宛平縣人民法院存在嚴重的特權思想和違法亂紀的現象進行整頓。該法院除了存在隨便拘押當事人、打罵群眾、與女犯通奸、甚至包庇罪犯等問題之外,還養著一條惡狗,時常咬破群眾衣服,有一次竟然把一個來告狀的婦女的腿咬破兩個洞。群眾中盛傳:“法院有狗,不敢進去”,影響極壞。《中共北京市委關于司法改革運動工作總結向中央、華北局的報告(1953年4月6日)》,載前引B15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書,第110頁。根據當時的認識,法院有無“惡狗”或許不是關鍵,關鍵是工作作風脫離群眾。
五是模范標準:人民司法。例如,“模范司法工作者”張輝系云南省楚雄專區姚安縣人民法院副院長,他在法院建立了問事代書處,替人民群眾解答法律問題和免費代寫訴狀;處理案件時,深入到群眾中去進行調查研究,從不草率從事,主觀臆斷。參見云南省司法改革委員會辦公室:《依靠群眾辦案的模范司法工作者張輝》,載《人民日報》1953年2月4日第3版。“優秀的人民司法工作者”呂志杰系陜西省洋縣人民法庭審判員,他創造了“游行審判”模式。惡霸邵世杰對自己的罪行認小不認大,人民法庭便采用了“游行審判”方式。具體而言,就是審判員押解著邵世杰到各個村莊游行,凡是遇到群眾圍觀并控訴其罪行的,便當面質問并收集罪證,就地查清其罪行。“最后邵犯終于在確鑿的人證物證面前承認了自己的罪惡”。參見薛述明:《優秀的人民司法工作者呂志杰》,載《人民日報》1952年9月20日第3版。“模范司法工作者”王文軒系河南省開封縣人民法院院長,創造了“群眾大會審判”模式。在審訊反革命分子孫書堂時,該犯曾矢口否認自己的罪行。王文軒便帶案下鄉,在群眾大會上宣布了政策,講明處理案件的經過,結果人證物證都從群眾中找到了。王文軒和四個干部依靠群眾在15天內,處理案件164起。陳一超:《模范司法工作者王文軒》,載《人民日報》1952年12月18日第3版。
有學者認為,新中國的成立并不是革命的終結,因其后還發生了一系列大規模的革命性變革。“革命”與“政權更迭”的區別在于,“政權更迭”僅僅是從一個國家機器向另一個國家機器過渡,而革命還包含了大規模的社會結構變遷。黃宗智:《實踐與理論:中國社會、經濟與法律的歷史與現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36—137頁。具體到司法領域,1952年開始的司法改革運動不僅清理和改造了舊司法人員,司法審判工作模式與機構設置也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以北京地區法院的機構設置為例,1949年北京市人民法院建立初期,市人民法院下設審判委員會辦公室、秘書處(室)和看守所等三個二級部門,審判委員會下設民事組(11個法庭)、刑事組(10個法庭)、調查組、代書組、問事處和執行組(包括贓物庫、檢驗室、執行排“偽法院的法警執達員貪污敲詐,人民法院成立后,除對四個作風老實的準予試用以外,一律遣散,代替他們的是從老解放區調來一批榮軍同志和一部分工人,加以編組訓練,組成的執行排。正如一般革命干部一樣,這些執行員們不但廉潔自守,每遇當事人按照舊習慣請他們坐車、吸煙、吃飯、給他們送禮的時候,他們還都作了人民政府政策的很好的宣傳員。”參見《北京市的司法工作》,載《人民日報》1949年10月21日第4版。),秘書處(室)下設文書科、總務科、干部科。此時北京市人民法院的機構設置與1951年9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暫行組織條例》第23條和第15條基本保持了一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暫行組織條例》第23條規定:“省級人民法院設院長一人,得設副院長一人或二人;設刑事、民事審判庭,庭設庭長一人,得設副庭長一人或二人;設審判員若干人。院長(副院長)得兼庭長。省級人民法院得設審判委員會,其組織和職務準用第十五條關于縣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的規定”;第25條規定:“省級人民法院設秘書處長或主任秘書一人,下設各科,科設科長一人、科員、辦事員若干人,掌理人事、宣傳教育、文書、庶務、會計、統計、檔案等事務;并承辦全區域的司法行政事宜;設書記員若干人(得設主任書記員),掌理記錄及其他有關事務;并設問事代書室。省級人民法院設法警若干人,并視需要設翻譯員、法醫、檢驗員。”
1953年2月4日,華北局在《中共北京市委關于司法改革運動第三階段工作總結向中央、華北局的報告》上批示,“茲將《北京市人民政府黨組關于司法改革運動第三階段的總結報告》轉發給你們參考。其中關于組織機構方面的措施(即第(一)條)可試行。”《中共北京市委關于司法改革運動第三階段工作總結向中央、華北局的報告》(1953年1月27日),載前引B15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書,第36頁。具體而言,1953年司法改革運動之后,北京市人民法院下設刑庭、民庭、人民接待室、辦公室、司法行政處等五個二級部門,刑庭下設執行組(贓證物庫)、檢驗室、審判組,民庭下設勞資組、公證組、審判組,人民接待室下設來訪組、來信組、案件處理組,辦公室下設拍賣組、總務科、文書科,司法行政處下設司法建設科、宣教科、人事科、秘書室。參見北京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北京志·政法卷·審判志》,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40—41頁。1949年北京市人民法院的機構設置基本上堅持了司法行政管理與司法審判工作的分離,體現了一定程度的司法專業化。與此相反的是,經過司法改革運動之后,專業的司法審判力量被削弱,人民接待(涉法涉訴信訪)得以制度化建設。在全國范圍內,人民接待室、集體調解、集體審判、基層調解委員會、當事人座談會、巡回審判、就地審判等體現“人民觀點”和“人民路線”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全面鋪開。例如,司法改革后,南京建立了一支1300多人的調解委員隊伍,在3992件結案中,經調解解決的就有3020件,占結案總數75.6%。前引B47。此外,截至1957年,全國選出人民陪審員24.6萬人,遼寧、浙江、安徽、福建等省各級人民法院,已經有80%到90%的案件,依法實行了人民陪審員制度。《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全體司法干部團結在黨的周圍徹底打垮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史良的發言》,載《人民日報》1957年7月13日第3版。
四、1957年整風運動中法學界對司法改革運動的批判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以“開門”的形式,既在黨內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也歡迎黨外人士參加,對黨和政府及黨員、干部中的缺點錯誤予以批評。當時一些法學家,特別是“舊法學家”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政法工作,尤其是1952年司法改革運動提出了很多比較中肯、甚至尖銳的批評以及改進意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羅隆基、黃紹竑、譚惕吾、王造時、楊兆龍、楊玉清等人。前引B62。他們對司法改革運動的意見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法律界的黨與非黨。一些“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認為,司法改革運動是“宗派斗爭”,“制造了黨與非黨之間的矛盾”,認為“司法改革運動今天作結論還早”、“是否合乎馬列主義還值得懷疑”、“現在法律界不是爭鳴而是哀鳴”。前引B33,第34、39頁;前引B22,第14頁。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原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楊兆龍在《文匯報》發表的題為《法律界黨與非黨之間》,批判司法改革運動把大量非黨的工作人員清理出審判隊伍。楊兆龍:《法律界的黨與非黨之間》,載《文匯報》1957年5月8日第2版。1957年5月,時任上海法學會副會長羅家衡在上海市政協會議上說:“司法部門采取限制、利用和改造的方法來對待黨外知識分子,這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羅家衡污蔑肅反政策》,載《人民日報》1957年8月6日第7版。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顧問、民盟北京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昱恒說,最高人民法院在執行干部政策上有宗派主義。幾年來,非黨干部得到了提高和改造,可是到目前,沒有一個非黨干部做審判員和助理審判員。參見《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中有哪些缺點 高院整風領導小組邀請院內民主人士座談》,載《人民日報》1957年5月21日第2版。時任北京政法學院院長、中國政治法律學會副會長錢端升認為:“由于過去強調法律的階級性斗爭性強,對于政法干部特別注重政治條件,這當然是對的,但也往往因此而把參加黨團與否,作為衡量一個人政治上是否進步的界限。這樣一條線,容易使政法部門的人變成清一色。”參見葉邁:《為黨群關系創造新經驗 北京政法學院院長錢端升先生談整風》,載《人民日報》1957年5月16日第7版;《妄圖幫助羅隆基成立反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政黨 錢端升是政法學界的右派陰謀家》,載《人民日報》1957年7月20日第7版。
二是法津的科學性和專門性。在整風運動中,時任上海法學會副會長的王造時和理事楊兆龍強調不能忽視“法津的科學性和專門性”,要突出法律的技術性和專門性。何濟翔:《著名法學家楊兆龍》,載《百年潮》2000年第11期,第46—48頁。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顧問、民盟最高人民法院區分部委員俞鐘駱認為,經過司法改革運動之后,有些人對審判是專門業務、法律是專門科學這一點是弄不清的,好像有了馬列主義就可以代表一切,能掌握政策就不需要一切。由于否定了舊法律的一切,就全國來說,對舊法律的知識分子一腳踢開。前引B67。“右派分子不僅要反動的舊法復辟,而且要舊司法人員復位。為此,他們不僅攻擊我們的法制,同時也攻擊我們的司法干部,說現在的司法干部是不能勝任的,因為不懂法律,分不清犯罪和不犯罪的界限,文化低,寫不出一個像樣的判決等等。”韓幽桐:《粉碎法學界右派分子的復辟企圖》,載《人民日報》1957年9月16日第7版。時任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法院審判員、民盟盟員嚴文雄認為“普陀區法院錯判案件有70%”、“刑庭錯判案件比民庭多”,是由于刑庭審判員大都是黨員,并認為刑庭審判員“政治上不負責,大老爺筆一揮,別人家破人亡”。《陰謀篡奪普陀區人民法院領導權嚴文雄妄想對勞動人民專政 他承認自己是民盟司法界右派的“開路先鋒”》,載《人民日報》1957年9月12日第2版。
三是“一棍子打死”。多數所謂的“右派分子”并不是反對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而是對于以是否學過舊法學和是否從事過舊司法工作作為劃定“舊司法人員”,進而清理出法院的做法表示不解,認為不應該“一棍子打死”。例如,時任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長樓邦彥說:“過去對政法界舊知識分子是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辦法。過去我們遭到了兩個方面的徹底否定,一是政法界知識分子全部歷史被否定,二是政法界的全部科學知識被否定。”《打垮右派分子對人民法制的進攻 首都政法界駁倒樓邦彥》,載《人民日報》1957年9月14日第2版。有人提出1952年到1953年期間的司法改革運動讓多數舊司法人員改行轉業是浪費人才。舊司法人員在專業知識和素養方面超越現在司法干部,這些人員都是經過建國后的嚴格政治審查,政治立場應該沒有嚴重缺陷,完全可以被改造成為有用的司法工作者。參見前引B65。還有人為舊司法人員被一律清洗感到惋惜,認為舊司法人員所謂存在舊法觀念,但是壞分子畢竟是個別和少數現象,打擊面過大,挫傷了舊司法人員的積極性。此外,“那些老干部做審判員,法律和文化水平低,判決、總結還要書記員寫”。倪征燠在《淡泊從容蒞海牙》一書中憶及1957年的“鳴放”說:“1957年春,中國共產黨開始整風運動,邀請黨外人士對黨提意見,機關團體都不例外。有些整風會上,群眾提了不少意見。中國政治法律學會于1957年的五、六月間,也舉行了幾次這樣的座談會。在6月17日的座談會上,我也發了一次言。當時政法界不少人有這樣的看法:對法制不夠重視,執法者無法可依,不能挖掘舊法人員潛力,人事調配不盡得當等等,我也大體上同意這種看法。”參見倪征燠:《淡泊從容蒞海牙》,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197頁。
四是法和法律的歷史繼承性。1957年初,上海、北京等地的不少學者撰文研討“法和法學在歷史發展中的繼承性問題”,一些政法院系也就此問題舉辦了研討會。學者們重點對新舊法和法學之間有無繼承性、法和法學的繼承性與階級性的關系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認識。楊兆龍發表了題為《法的階級性和繼承性》的文章,從歷史上新舊法律的繼承和發展的角度分析,新的法律并不能完全拋棄舊的或先產生的法律而存在,總要吸收和借鑒舊法或者受到舊法的啟發而完善,“至于那些輔佐性或從屬性的法律規范,其牽涉面很廣,并且絕大部分是過去長期經驗智慧積累的結果”。楊兆龍:《法律的階級性和繼承性》,載《華東政法學院學報》1956年第3期,第26—34頁。張晉藩先生也就法律的階級性和繼承性發表文章,認為堅持法律的階級性不能否認或者排斥法的繼承性,二者之間并不是完全對立關系。張晉藩:《關于法的階級性和繼承性的意見》,載《政法研究》1957年第3期。
五是無法治即無民主。王造時明確提出“無法治即無民主”的觀點,認為社會主義法治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構成部分,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指導原則。1957年5月,王造時在上海市政協一屆四次會議上作了書面發言,認為要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必須健全法制,并且由法定的機關具體執行。馮英子:《1957年的王造時——建國以來法學界重大事件研究(十)》,載《法學》1998年第3期,第2頁。1957年5月9日,楊兆龍在《新聞日報》發表文章,呼吁盡快制定頒布一系列重要法典。有學者介紹該文章的原標題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立法問題》,發表時編者將其改為副標題,而另加正標題為《我國重要法典為何遲遲還不頒布?》。參見前引B69,第47—48頁。隨后,王造時在《新聞日報》召開的座談會上指出,雖然新中國已經成立八年,但是“還有不少的人治主義的封建殘余”。傅季重:《駁右派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法律觀點》,載《學術月刊》1957年第9期,第19頁。1957年6月,在上海民盟主持的座談會上,楊兆龍再次呼吁實行民主和法治,“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不是空談,應當有一套辦法;沒有一套行政訴訟制度,是無法制止官僚主義的;現在的人事工作只講歷史和階級出身,是不好的……”穆廣仁:《楊兆龍的功與“罪”》,載《炎黃春秋》2015年第1期,第73頁。在復旦大學座談會上,他再次批判了解放以來歷次群眾性的社會改革運動,特別是司法改革運動和肅反運動,認為要檢查“歷次運動的合法性,特別是肅反運動”,并且強調要“建立民主法制秩序”。前引B80。否則,“無論是在刑事或民事方面都難免使壞人感到無所顧忌,使好人感到缺乏保障”。葉孝信:《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的批判——從老根上清算右派分子關于民主、自由、法制等的謊言》,載《法學》1958年第4期,第36頁,
六是司法獨立和審判獨立。整風期間主張司法獨立和審判獨立的主要是政法界的“右派分子”。例如,浙江省司法廳廳長、民盟浙江省委主任委員姜震中,福建省司法廳廳長、民盟中央委員兼福建省委副主任委員何公敢,四川省司法廳副廳長、民盟四川省委委員張雪巖,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長樓邦彥以及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庭長、民盟機關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何濟翔,安徽省司法廳副廳長、黨組書記陳仁剛,山西省司法廳審判機關管理處副處長丁仰軒,甘肅省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刑庭庭長李煜,安徽省律師協會籌委會秘書長吳桐,昆明市法律顧問處律師、九三學社成員張慎,烏魯木齊市法律顧問處見習律師楊騰高等。《全國司法界反右派斗爭初獲勝利 右派妄圖奪取人民民主專政武器的陰謀破產》,載《人民日報》1957年9月20日第2版。其中,有代表性的“右派言論”有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審判員賈潛說的“服從法律,就等于服從了黨的領導”。若泉、何方:《不許篡改人民法院的性質——駁賈潛等人“審判獨立”“有利于被告”等謬論》,載《人民日報》1957年12月24日第7版。吉林省通化專區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員林天程認為黨委領導司法工作對審判員是“最大的限制”。參見《企圖使人民法院反對人民 審判員林天程高唱“獨立審判”》,載《人民日報》1957年9月16日第2版。福建省司法廳長何公敢、省高級人民法院助理審判員林登文、吳大新和福建省、廈門市、南平市等人民檢察院的工作人員任敦卿、任家德、姚煥興等人,認為“黨委不懂法律、不能領導政法工作”。參見《福建各地政法部門揭露一批右派分子》,載《人民日報 》1957年9月23日第3版。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么?》的社論指出,少數右派分子想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最廣大的人民是絕不許可的。同日,毛澤東起草《中共中央關于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標志著反右派斗爭正式開始。參見前引③,第450—451頁。自此,整風期間法學界對于新中國司法工作,特別是司法改革運動提出的許多箴言,被定性為“惡毒地制造各種顛倒黑白的荒謬言論,就是要使反動的舊法律和舊司法制度復辟、舊司法人員重新‘上臺 ,抓‘刀把子”。前引B33,第34、39頁;前引B22,第14頁。寬松的“百家爭鳴”與嚴謹的“學術討論”,瞬間成為“敵我矛盾”,成為“生死斗爭”,導致錯失對1952年司法改革運動的反思與糾偏時機,甚至“這樣批右傾的結果是越批越‘左,越‘左越批,成了惡性循環”。張慜:《試論1952年司法改革運動》,載《法律適用》2004年第8期,第57頁。司法改革運動后重構的審判機關在“人民維度”上的“狂奔”,最終導致其與“政治維度”發生激烈沖突。1971年,北京市檢法軍管會在《認真搞好民事審判工作斗、批、改》中提出:“大叛徒劉少奇、彭真一伙鼓吹‘一切按法辦事,法院受理民事案件采取了‘有訴必究、‘民訴官斷,把本來屬于基層單位通過思想政治工作可以解決的大量人民內部糾紛也立案受理,甚至‘貓偷吃香腸、‘雞啄窗戶紙、‘狗咬兔子所引起的爭吵,也要由法院判個‘誰是誰非。1962年,全市受理案件24188件,其中民事案件18386件,占全部案件74%。各區縣法院除一兩個人辦刑事外,其余90%以上的審判人員投入民事也忙個不可開交。人民法院幾乎變成了‘民事調解處、‘離婚登記所,大大削弱了人民法院的無產階級專政職能。”參見《北京法官(院史展專刊)》(內部刊物)2015年第10、11期,第19頁。歷史總是如此荒誕,1952年司法改革運動本意是破解“案多人少”的矛盾,反而最終成為“案多人少”的“元兇”,于是“文革”期間司法審判工作要堅持的原則是破“辦案第一”,立“政治掛帥”;破“以法制人”,立“毛澤東思想教育群眾”,司法改革成果亦被隱匿在“十年動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