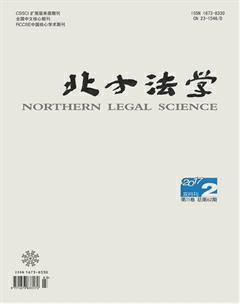聚眾哄搶財物與聚眾“打砸搶”的刑法教義學
摘 要:聚眾哄搶財物行為通常成立聚眾哄搶罪;哄搶使用中廠房的物資設備的,是聚眾哄搶罪與破壞生產經營罪的想象競合犯,以聚眾哄搶罪定罪處罰;聚眾是與哄搶并列的行為或者是哄搶行為的方式或狀態,說明了聚眾哄搶罪的必要共同犯罪特征;成立聚眾哄搶罪未必要有首要分子組織、策劃或糾集;聚眾哄搶罪的對象是他人占有的動產或者不動產中可以分離的部分;哄搶的本質是公然搶奪或盜竊;不符合聚眾哄搶罪的哄搶財物行為可認定為搶奪罪或盜竊罪;聚眾哄搶罪與搶奪罪、盜竊罪的共犯有差異;哄搶人采取對人暴力或脅迫等方式,壓制被害人反抗而哄搶財物的成立搶劫罪,聚眾哄搶罪可以成立事后搶劫;聚眾“打砸搶”是聚眾實施某些尋釁滋事行為的特別規定;“致人傷殘、死亡”應限制解釋為聚眾“打砸”人所致;“毀壞或者搶走公私財物”是搶劫罪的法律擬制,首要分子以外的人成立尋釁滋事罪(或與敲詐勒索罪、聚眾哄搶罪、故意毀壞財物罪等的想象競合犯)。
關鍵詞:聚眾哄搶 事后搶劫 聚眾“打砸搶” 尋釁滋事
中圖分類號:DF6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330(2017)02-0086-12
聚眾哄搶財物案件容易引起人們關注,具有較大社會影響。見諸報道的哄搶案件如,哄搶散落錢鈔,哄搶翻車貨物,哄搶林木瓜果,哄搶廠礦、工地或運輸中的物資設備,災后哄搶財物等。哄搶行為聚眾實施,具有公然性、突發性和隨機性等特征,多偶發于事故、災害之際,或者肇始于勞資糾紛等。時間、地域沒有限制。與財物的所有人、保管人或運輸人是否在場沒有關系。哄搶人持“法不責眾”、“是撿不是搶”等錯誤觀念,趁他人對財物不能有效管控之機,“挾眾揩油”,搶了財物各自歸屬。哄搶的財物涉及各類生產、生活資料。哄搶案件事后追查嫌疑人和挽回財產的難度較大。因此,哄搶財物是侵犯公私財產權益、擾亂社會秩序的危害行為,對社會公德也具有很大的破壞力和腐蝕性。嚴重的哄搶財物行為成立犯罪,應該追究刑事責任。然而,由于哄搶財物行為具有多樣性,刑法上有關財產罪(第263、264、267、268、269、276條)與相關法條(第289、293條)的規定錯綜復雜,長期以來,哄搶財物行為的犯罪認定與處理沒有受到刑法學界的足夠重視。筆者認為,有必要對哄搶財物的行為事實加以歸納,揭示哄搶行為的本質,體系地解釋聚眾“打砸搶”的刑法規定,從而對聚眾哄搶財物和聚眾“打砸搶”行為作出合理的認定和處理。
一、聚眾哄搶罪的構成特征與刑罰
為了防治通常的聚眾哄搶財物行為,我國刑法于第268條規定了聚眾哄搶罪,即“聚眾哄搶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對首要分子和積極參加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聚眾哄搶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聚眾哄搶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行為。目前,刑法理論和實務界對本罪的本質和構成要件研究得還不夠細致。
(一)聚眾哄搶的行為本質
聚眾哄搶罪屬于財產罪中的取得罪,與毀棄罪和拒不履行債務罪相異;在取得罪中,聚眾哄搶罪又屬于違背被害人意志的奪取罪,從而與交付罪相異。根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財產罪大致可分為取得罪與毀棄罪。其中,取得罪根據行為方式又可以分為違反被害人意志的奪取罪(如搶劫罪、盜竊罪和搶奪罪等),與基于被害人瑕疵意思的交付罪(如詐騙罪、敲詐勒索罪)。但是,奪取罪中又有多種行為類型,聚眾哄搶罪的具體行為本質是什么,與盜竊、搶奪或搶劫行為是何關系,學界尚無定論。
較有影響力的觀點是,聚眾哄搶罪“本質上屬于聚眾搶奪犯罪”,曲新久:《刑法學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71頁。其行為方式是“公然奪取”。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508頁;趙秉志、李希慧主編:《刑法各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44頁;黎宏:《刑法學各論》,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08頁。有的表述為“公然搶奪”。“所謂‘哄搶,是指蜂擁而上,搶奪占有。‘哄是表現形式,‘搶是本質特征”。謝望原、赫興旺主編:《刑法分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81頁。該觀點在早期司法解釋中即有體現,比如《鐵路法》(1990年9月7日頒布,現已廢止)第64條規定:“聚眾哄搶鐵路運輸物資的,對首要分子和骨干分子依照刑法第151條或者第152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最高人民法院《〈中華人民共和國鐵路法〉中刑事罰則若干問題的解釋》(1993年10月11日頒布,現已廢止)第4條作如下解釋:“聚眾哄搶鐵路運輸物資的,對首要分子和骨干分子應當以搶奪罪,依照刑法第151條或者第152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一般應從重處罰。”值得關注的是,有學者提出不同見解,認為聚眾哄搶罪是“多人實施的使被害人難以阻止的公然盜竊”。張明楷:《刑法學》(下),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000頁。也有學者兼收并蓄,提出了“公然奪取或竊取”的觀點。參見阮齊林:《刑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535頁。
筆者認為,把握聚眾哄搶的行為本質,要點在于認清生活中該行為的實際樣態,以明確聚眾哄搶的內涵,并且要厘清搶奪與盜竊的內涵和關系。首先,搶奪與盜竊的內涵和關系,是近年刑法學界爭論較大的課題。搶奪是“乘人不備,公然奪取”,盜竊是“秘密竊取”,這樣的傳統觀念已然松動。事實上,搶奪也可以乘人有備,盜竊也可以公開進行。參見阮齊林:《論盜竊與搶奪界分的實益、傾向和標準》,載《當代法學》2013年第1期,第79頁。“從‘秘密與公開角度區分盜竊與搶奪的觀點與做法存在諸多缺陷;盜竊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違反被害人的意志,采取平和的手段,將他人占有的財物轉移為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的行為;盜竊行為既可以具有秘密性,也可以具有公開性;以對物暴力的方式強奪他人緊密占有的財物,具有致人傷亡可能性的行為,才構成搶奪罪;盜竊與搶奪的區別在于:對象是否屬于他人緊密占有的財物,行為是否構成對物暴力”。張明楷:《盜竊與搶奪的界限》,載《法學家》2006年第2期,第119頁。就搶奪罪和盜竊罪這兩個對他人財物的奪取罪而言,只要排除了搶奪罪,就都可以認定為盜竊罪。搶奪的本質特征是行為具有致人身傷害的可能性,對此判斷的條件有兩個,即手段是采取對物暴力(非平和)的方式,對象是針對被害人緊密占有的財物。所謂對物暴力,就是對物施加強制力、迅速瞬間性的奪取。被害人對財物的緊密占有,最典型的例子比如,提在手上、背在肩上、裝在口袋等財物與人身緊密聯結在一起。不限于此,被害人在當場、財物的不遠處,也可規范地評價為緊密占有財物。
生活中聚眾哄搶財物的實際樣態顯示,有些是被害人在場,可以及時(盡管無法有效)管控的情況下實施的,比如,貨車傾翻或者錢包散落以后,人們哄搶散落一地的貨物、水果、錢鈔等財物。參見趙志鋒:《甘肅榆中哄搶橘子處理34人》,載《法制日報》2014年1月13日第5版。也有些是在被害人不在場,完全無法管控的情況下實施的,比如,進入房間、辦公樓、廠房或農場等,哄搶生活、辦公用品、物資設備或農林水產品等財物。其中,有的使用非暴力的平和手段(門窗庭院未鎖、物品容易拿取搬運等),有的使用對物暴力的手段(砸門撬鎖、硬砍強拆等)。那種認為哄搶是不用暴力而奪取財物的觀點,參見曲新久主編:《刑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55頁。顯然是有失偏頗的。綜上,根據案發時間、被害人是否在場以及能否及時管控等情況的不同,聚眾哄搶行為有的可能符合搶奪,也有的可能符合盜竊。因此,聚眾哄搶行為的本質不能一概斷定為“公然搶奪(或奪取)”或“公然盜竊”的單純一種,將其歸納為“公然搶奪或盜竊”更加合理。也就是說,有的聚眾哄搶財物情形的行為本質是“公然搶奪”,有的聚眾哄搶財物情形的行為本質是“公然盜竊”。舉例來說,白天乘他人錢鈔或車載水果散落在地而哄搶的,本質上屬于公然搶奪;夜間乘廠房無人而哄搶物資設備的,本質上屬于公然盜竊。
(二)聚眾哄搶罪的構成要件
聚眾哄搶罪的行為本質,涉及的是對聚眾哄搶,特別是“哄搶”的理解。然而,對于“眾”、“聚眾”的含義、“聚眾”與“哄搶”的關系、對象財物的范圍等,學界還存在著不同理解。作為成立條件的數額和情節,也有必要予以明確。下文對這些問題逐一探討。
1.“聚眾”與哄搶人。首先,“眾”指三人及以上,這是聚眾哄搶罪的外在特征之一。極個別觀點認為,哄搶人“至少應當在五人以上,再少不能稱之為聚眾”。李忠誠:《哄搶罪》,載《中國刑事法雜志》1998年第2期,第33頁。該觀點不符合刑法學對“眾”的通常理解,況且做此人數限定也缺乏依據。聚眾哄搶的特點是,哄搶人依靠人多勢眾取得財物,參與哄搶的人處于隨時可能增加或者減少的狀態。因此,與其在“眾”的基礎上再劃定人數限制,作機械的算術判斷,不如劃定最起碼的人數要求即三人,然后根據案情中哄搶人是否隨機、延散,靈活地進行事實判斷。其次,聚眾與哄搶的關系。“聚眾”是與“哄搶”并列的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亦或不是客觀行為,僅為“哄搶”行為的方式或狀態?學界存在不同認識。聚眾哄搶罪處罰的行為主體是首要分子和積極參加者。根據《刑法》第97條的規定,“首要分子,是指在犯罪集團或者聚眾犯罪中起組織、策劃、指揮作用的犯罪分子。”聚眾哄搶罪屬于一般共同犯罪中的聚眾型犯罪。于是,比較流行的一種觀點是,該罪的首要分子就是在聚眾哄搶財物的犯罪中起組織、策劃、指揮作用的犯罪分子;積極參加者是指在哄搶財物中起主要作用,帶頭哄搶,哄搶財物較多或者具有其他嚴重情節的人。亦即,“聚眾”是組織、策劃、糾集眾人的行為。有學者認為,聚眾哄搶罪中“必然存在著明顯的首要分子”,王英松:《論聚眾哄搶罪》,載《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00年第11期,第32頁。“沒有首要分子就沒有聚眾哄搶行為”。吳秀云、王義樹:《聚眾哄搶罪的多視角分析》,載《江西公安專科學校學報》2007年第3期,第28頁。與此觀點不同的是,有學者認為,聚眾哄搶是一種行為方式,并不要求存在所謂“聚眾”與“哄搶”兩個行為。所以,沒有首要分子時,也不妨礙本罪的成立。例如,被害人駕駛的卡車側翻后,周圍的眾人自發哄搶財物的,即便沒有首要分子,也應對積極參加者追究刑事責任。參見前引⑤。
筆者認為,沒有首要分子組織、策劃或糾集,因偶然事故而造成被害人對財物占有松弛,眾人哄搶財物的情形,現實生活中確實是存在的,對此完全有必要、也可以根據聚眾哄搶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此類案件中即使沒有首要分子,對于可以評價為積極參加者的行為人,追究其刑事責任,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當然,如果有首要分子進行組織、策劃或糾集,然后實施哄搶財物行為的,則首要分子和積極參加者都應被追究刑事責任。因此,聚眾哄搶罪的“哄搶”可作兩種理解,代表了本罪的兩種行為類型:一是與哄搶行為并列的聚眾行為,即首要分子組織、策劃、糾集眾人,然后眾人哄搶財物;二是描述哄搶行為的方式或狀態,即眾人自發地聚集起來哄搶財物,此時的“聚眾”是“眾人聚集在一起”的意思。哄搶行為符合上述行為類型之一的,即可成立本罪,只是實際上被追究刑事責任的行為人的范圍不同而已。但是,不能認為“聚眾”只是與“哄搶”并列的行為,這種縮小本罪構成要件的解釋論,會導致缺少該行為的第二種類型不成立犯罪,不符合社會現實,致使本罪的刑法規范不能有效地預防和懲治哄搶犯罪,不利于對被哄搶財物法益的保護。
總之,有首要分子“聚眾”然后哄搶財物的當然成立本罪,但不一定非要有首要分子的組織、策劃或糾集,眾人聚集到一起哄搶財物即可符合本罪。換言之,“聚眾”說明的是聚眾哄搶罪的必要共同犯罪的特征,既可以是“聚眾”行為,也可只表示“哄搶”行為的方式或狀態。
需要說明的是,刑法規定聚眾哄搶罪的處罰對象限于首要分子和積極參加者。于是,極個別觀點認為,本罪是特殊主體。參見郭自力主編:《中國刑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05頁。這是對犯罪主體的身份概念的誤解。刑法上的身份是指行為主體在社會關系上的特殊地位或者狀態。它必須是在主體開始實施犯罪行為時就已經具有的特殊資格,比如男女性別、國家工作人員等;在實施犯罪后才形成的特殊地位不屬于身份,比如首要分子和積極參加者等。因此,本罪是一般主體實施的犯罪。
2.財物范圍。聚眾哄搶罪的行為對象是他人占有的財物,既可是公共財物,也可是私人財物;既可是生產資料,也可是生活資料;既可是室內、廠房等封閉場所內的財物,也可是馬路、田野等開放場所的財物;動產屬于本罪的對象。這些均是學界共識。但是,不動產能否成為本罪的對象,存在爭議。傳統觀點認為,聚眾哄搶罪的“犯罪對象是動產,主要是處于運輸、保管和儲存過程中的公私財物”。參見前引B15。該觀點顯得保守和滯后,已被立法、司法人員的認識以及司法實踐所突破。立法部門有代表認為,“哄搶財物,意味著財物發生轉移,從所有者、保管者的控制之下,轉移到哄搶者的手中,而不動產一般是不能用上述方法轉移的,但是不能排除發生以貪利動機侵犯不動產的可能性,諸如哄搶果林。由于我國刑法未明確規定哄搶只限于動產,因此,對于哄搶不動產的,也可以本罪定罪”。劉家琛主編:《新刑法條文釋義》(下),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4頁。最高人民檢察院有工作人員認為,本罪對象“主要是動產和可以分割拆卸的不動產”。前引B11。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聚眾哄搶林木數額較大(5立方米以上)的行為,以聚眾哄搶罪定罪處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森林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0〕36號,2000年11月22日頒布,2000年12月11日施行)第14條。該解釋肯定了不動產可成為本罪對象的觀點。司法實踐中也存在哄搶不動產的聚眾哄搶罪判例,案情如下:周某所在的江蘇省沭陽縣沂河鄉瓦房村部分集體土地被趙某等人承包,周某等人對該土地租金的繳納、使用等問題存在疑問和不滿。2004年9月18日,周某伙同魏某、趙某、鄭某(均已判刑)等人為索回上述土地,經預謀后聚集本村部分村民,采用哄搶的手段,將趙某等人在承包田內種植的大蔥、山芋、蘿卜等農作物搶走。經鑒定,被搶農作物共計價值147萬余元。沭陽縣法院經審理認為,周某伙同他人聚眾哄搶他人財物,數額巨大,且系積極參加者,其行為構成聚眾哄搶罪。參見李金寶:《聚眾哄搶農作物 行為不端觸刑律》,載《檢察日報》2011年10月30日第2版。
顯然,探討財產罪對象的動產與不動產時,刑法不存在有別于民法的特殊概念。在民法上,“所謂不動產,指依自然性質或者法律規定不可移動的物,包括土地及其定著物。……所謂定著物,指固定且附著于土地之物”。梁慧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頁。比如建筑物、養魚塘、林木瓜果等。同時,林木瓜果一旦被砍伐、挖掘或采摘后,就成為了動產。傳統觀點將聚眾哄搶罪的對象限定于動產,有可能是出于對一部分針對動產的聚眾哄搶案件的事實歸納,但這種歸納顯然是不全面的,因為針對不動產的哄搶案件是確實存在的;也可能是以哄搶前后的對象均為不動產為設定條件的,但這樣的設定不符合理論邏輯,因為哄搶以后成為了動產,并不能否認對象在被哄搶之前是不動產這一性質。限定于動產的觀點也缺乏刑法規范上的依據,會導致對哄搶行為規制不充分,對法益保護不完善。因此,學界越來越傾向于認為,聚眾哄搶罪的對象“只限于動產以及不動產中可以拆分的部分”。周光權:《刑法各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16頁;劉艷紅主編:《刑法學》(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99頁;劉憲權主編:《刑法學》(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43頁。張明楷教授曾經認為本罪對象只能是動產,參見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44頁。但在最新版教科書中刪除了該觀點。前引⑤,第999—1000頁。
不動產可以成為聚眾哄搶罪的對象,但顯然不可能是所有的不動產,其范圍受到限制,也就是不動產上可以分離的部分。聚眾哄搶罪是財產罪,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目的。在大陸法系刑法理論和司法實務中,日本通說認為,不法取得意思(即非法占有目的)包括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但對其內容存在緩和化理解的傾向。利用意思是指遵從財物可能具有的用途進行利用、處分的意思,不限于遵從財物的經濟用途、本來用途,而是包括了所有的享受由財物所產生的某種效用的意思。德國通說認為,非法占有目的包括排除占有(消極要素)和建立占有(積極要素),前者是指意圖獲取財物本身或其經濟價值,而持續性地排斥或破壞他人對財物的支配關系,后者是指意圖使自己或第三者具有類似所有人的地位,而將所取得之財物作為自己或者第三者所有之財產。參見張開駿:《盜竊物品以勒索錢款的犯罪認定與處罰——從剖析非法占有目的入手》,載《政治與法律》2015年第3期,第45—46頁。在民法上,土地及附著其上的林木瓜果是不動產。林木完全可以被挖掘或砍伐然后移動,被挖掘而用于自己或出賣給他人移栽時絲毫不損其價值,即使哄搶人不是將其作為林木種植,而是在砍伐后用作建筑木材,甚至當作柴禾燒火的,也符合刑法上非法占有目的意思。由此可見,作為不動產的林木可以在非法占有目的支配下成為聚眾哄搶罪的對象。但是,土地與此不同,它不可移動,土地負有地契或承包合同,所有權、使用權屬的轉移需要登記,由此決定土地不可能通過聚眾哄搶的方式取得。現實生活中圈占土地并耕種的行為不過是一時享用土地的使用權,而不可能真正取得土地,因此不成立聚眾哄搶罪。例如:張某等9名被告人都是甘肅省張掖市甘州區大滿鎮馬均村農民。2011年3月,被告人以甘州區水務局農場的土地在1970年代系馬均村所有為由,經相互聯系,召開會議,策劃搶種甘州區水務局農場土地。被告人組織、指揮馬均村村民將農場的土夯圍墻推倒5處,長度達15625米。農場的260畝土地被耱耙,其中1124畝土地被耕種。甘州區法院認為,被告人無視國法,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組織村民逾百人公然哄搶他人合法土地,在共同犯罪中起了組織、策劃、指揮的骨干帶頭作用。在聚眾哄搶過程中,參與人員多,同時將農場的土夯圍墻推倒,48株新疆楊、金絲柳、國槐因焚燒玉米桔桿、雜草時被焚燒,毀損物品價值729550元,在社會上造成了惡劣影響,屬情節嚴重。9名被告人的行為均已觸犯刑律,構成聚眾哄搶罪。《甘肅省張掖市甘州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1)甘刑初字第181號。
筆者認為,在上述案例中,將張某等9名被告人的行為認定為聚眾哄搶罪是不妥當的。聚眾哄搶財物行為并非只能被評價為聚眾哄搶罪,當哄搶對象具有特殊性質時,存在其他評價的可能性。比如,聚眾哄搶使用中的廠房里的物資設備的,也可以評價為第276條破壞生產經營罪。該罪是指由于泄憤報復或者其他個人目的,毀壞機器設備、殘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壞生產經營的行為。根據同類解釋規則,“其他方法”應是與毀壞機器設備、殘害耕畜相類似的毀壞財物的方法。大陸法系刑法理論在解釋“毀壞”時,日本出現了“物理毀損說”向“效用侵害說”的變遷,參見[日]西田典之:《刑法各論》,弘文堂2012年版,第280—281頁。德國出現了“實體破壞說”向“功能妨礙說”的變遷。參見林東茂:《刑法綜覽》,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73頁。根據效用侵害說或功能妨礙說的通說,凡是有害財物的效用或功能的行為,都屬于“毀壞”。不僅包括財物的物理毀損(比如將物資設備完全砸爛),還包括被害人對財物占有的喪失(比如將物資設備扔進河里)。這是立足于法益保護的刑法目的,而對構成要件行為進行的實質性解釋或評價。基于此,聚眾哄搶生產經營用的物資設備,對被害人而言就是毀壞了該物資設備,該行為破壞了他人的生產經營活動,因而可以被評價為破壞生產經營罪。在前述甘肅省張掖市甘州區聚眾哄搶土地案中,張某等9人搶占農場土地并耱耙、耕種,必然毀壞農場土地上原有的種植物,還推倒了農場土夯圍墻,燒毀了價值七千余元的新疆楊、金絲柳、國槐等財物,破壞了農場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可依破壞生產經營罪定罪,結合共犯理論合理劃定處罰范圍。由此,聚眾哄搶使用中的廠房里的物資設備的行為,成立聚眾哄搶罪與破壞生產經營罪的想象競合犯。取得罪與毀棄罪能夠成立想象競合犯,這符合刑法法理。比如,盜鋸景區內的銅制雕塑一部分的行為,就成立盜竊罪與故意毀壞財物罪的想象競合犯。由于破壞生產經營罪的刑罰輕于聚眾哄搶罪,根據想象競合犯的從一重處罰原則,聚眾哄搶使用中的廠房里的物資設備的行為,最終以聚眾哄搶罪處罰。當然,如果不是哄搶廠房里使用中的生產設施而只是產品的,或者工廠停產之后工人或周圍居民不顧看守阻攔,強行將值錢的物資設備拆卸回家的,則不符合破壞生產經營罪的犯罪構成,只能以聚眾哄搶罪定罪處罰。
3.哄搶故意。聚眾哄搶罪的故意內容是,明知與其他人聚眾在一起哄搶財物會發生被害人的財物被侵害的結果,而希望或者放任該結果的發生。具體來說,行為人認識到自己和其他人在共同哄搶財物,且有相互借勢以使被害人不能有效管控,進而取得財物的意思。有學者認為,聚眾哄搶“通常是因為某偶然事件所致,因此,其與數人事先通謀主動尋找機會搶奪作案的情形不同”。前引③黎宏書。該觀點指出了聚眾哄搶特征的“通常性”一面,但不能概括全部現象。比如,前述江蘇省沐陽縣周某哄搶農作物案是有預謀的。盡管通常的聚眾哄搶行為(比如貨車傾翻或者錢包翻袋后,人們哄搶散落的貨物、錢鈔),哄搶人出于偶然事件而當場臨時加入哄搶,在此之前不可能有通謀。但是,共同犯罪的主觀方面不要求嚴格的通謀,只要有意思聯絡即可。當行為人聚集到現場,加入到哄搶行為中,該行為本身便是默示的意思聯絡。況且,現實生活中的聚眾哄搶案件,不排除因為存在矛盾糾紛,周圍民眾基于通謀而有組織地哄搶,或者基于單純的謀利動機,而無故地通謀聚眾哄搶特定的財物。比如,兩個村莊對林地歸屬有爭議,一方怕吃虧而聚眾哄搶林木;工廠倒閉后長期無人管理,眾人聚集前往廠房洗掠物資設備等。在這些情形中,哄搶人可以有所準備(攜帶儲物工具、使用運輸工具等),按照約定的時間行動,哄搶結束人就一哄而散。因此,聚眾哄搶罪既可以是在沒有事先謀劃的情況下,也可以是有預謀地聚集,從而公然獲取公私財物。參見胡云騰主編:《刑法條文案例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91頁。
4.數額與情節。根據刑法規定,哄搶財物“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才追究聚眾哄搶罪的刑事責任。本罪的“情節”,可以從哄搶人數、對象、次數和后果等方面把握。目前,最高司法機關沒有關于本罪的定罪量刑標準的司法解釋,上海市司法系統出臺了地方規范性意見,對數額和情節作了規定:聚眾哄搶數額在4000元以上的,屬于“數額較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其他嚴重情節”:(1)組織30人以上參與哄搶的;(2)哄搶一般軍用物資的;(3)哄搶一般文物的;(4)哄搶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醫療等款物的;(5)哄搶急需的生產資料的;(6)哄搶三次以上的。聚眾哄搶數額在4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其他特別嚴重情節”:(1)組織150人以上參與哄搶的;(2)哄搶重要軍用物資的;(3)哄搶珍貴文物的;(4)哄搶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醫療等款物,造成嚴重后果的;(5)哄搶急需的生產資料,嚴重影響生產,或者導致公司、企業停業、停產的;(6)導致被害人精神失常、自殺的。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檢察院、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司法局《關于本市辦理部分刑事犯罪案件標準的意見》(滬檢發[2008]143號,2008年6月24日發布,2008年10月1日施行)第31條。該規范性文件的規定具有參考價值。
(三)聚眾哄搶罪的刑罰
從刑法體系的位置來看,聚眾哄搶罪被規定在搶劫罪、盜竊罪和搶奪罪之后。由“聚眾哄搶”的立法表述可見,它屬于取得型財產罪中的奪取罪一類。從法定刑來看,聚眾哄搶罪輕于盜竊罪和搶奪罪,表現在:其一,聚眾哄搶罪只有兩檔法定刑,法定刑最高是“十年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而盜竊罪和搶奪罪都有三檔法定刑,且最高檔法定刑是“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其二,雖然聚眾哄搶罪的第二檔(最高檔)法定刑與盜竊罪和搶奪罪的第二檔(中檔)法定刑相同,且它們的第一檔法定刑的主刑也相同,但是在情節的刑法規定上,聚眾哄搶罪的入罪條件更加嚴格,聚眾哄搶罪有“嚴重情節的”處基本法定刑,有“特別嚴重情節的”處第二檔法定刑;而對于盜竊罪和搶奪罪來說,有“嚴重情節的”就可處與聚眾哄搶罪法定刑相同的第二檔法定刑,有“特別嚴重情節的”則可處第三檔法定刑。
從客觀違法性上看,聚眾哄搶罪不低甚至高于搶奪罪、盜竊罪。有學者在提及聚眾哄搶罪侵犯的客體時指出,“本罪的犯罪客體是復雜客體,即公私財物所有權和社會的正常管理秩序”。前引③高銘暄、馬克昌主編書。然而,聚眾哄搶罪的法定刑卻低于搶奪罪、盜竊罪,其原因在于有責性和預防必要性的差異。人有占便宜的私心,也存在“法不責眾”的僥幸心理,因此聚眾哄搶罪的有責性低于盜竊罪和搶奪罪;從發案率來看,聚眾哄搶罪明顯低于后兩種財產罪,其預防必要性也相對小一點。聚眾哄搶罪只處罰首要分子和積極參加者,也是出于刑事政策的考慮,符合我國刑法對聚眾型犯罪的一般處罰原則。如果不考慮刑事政策的因素,單從財產罪體系的科學性來看,聚眾哄搶罪似無獨立設置的必要。綜觀外國關于財產罪的刑事立法,罪名不多,卻對量刑情節規定得很詳細。根據財產罪的行為本質,刑法設立簡約而具有周全性的罪名,并致力于量刑情節的明確化,會更加科學、嚴謹,契合罪刑法定原則,有利于司法。
二、聚眾哄搶罪與其他財產罪的關系
(一)與搶奪、盜竊的關系
刑法學界提出了大量的聚眾哄搶罪與搶奪罪“主要或關鍵區別”的論斷。比如,有人認為“兩者的主要區別在于是否聚眾實施”。前引B11,第34頁。毫無疑問,不聚眾則不足以成立聚眾哄搶罪,在不聚眾搶奪財物的情況下,該觀點提供了界分標準。但是搶奪罪也可以共同實施,那么在聚眾哄搶罪與共同搶奪兩者之間又該如何區分,論者沒有給出答案。也有人認為“二者區分的關鍵在于……聚眾哄搶既可以當著被害人的面實施,也可以在被害人不在場的情況下實施哄搶;而共同搶奪必須當著被害人或其他人的面實施,或者采取可以使被害人立即發覺的方法實施搶奪”。王作富主編:《刑法分則實務研究》(中),中國方正出版社2013年版,第985頁。有的聚眾哄搶情形符合盜竊罪,而不符合搶奪罪,該觀點提供了符合盜竊情形的聚眾哄搶行為與搶奪的界分標準。問題是,如果聚眾哄搶是當著被害人或其他人的面實施,或者說是在被害人能夠立即發覺的情況下實施的,又該如何界定犯罪,該觀點也給不出答案。以上列舉的兩種觀點,正是目前我國刑法學界熱衷提出顯而易見的界分標準,卻忽視競合情形下犯罪認定的表征之一。以上偏頗論斷的根本原因在于,沒有認清聚眾哄搶罪的行為本質,于是無法全面地認定哄搶財物罪。
如前文所述,聚眾哄搶財物的行為本質是“公然搶奪或盜竊”,對于應該承擔刑事責任的單個哄搶人而言,其行為可能完全符合搶奪罪或盜竊罪(假如符合了搶奪罪或盜竊罪的入罪標準)。但是需要注意,該哄搶人畢竟不是搶奪罪或盜竊罪的主體,而是在聚眾哄搶罪的罪責名義下承擔刑事責任,因為,聚眾哄搶罪是與搶奪罪、盜竊罪不同的獨立罪名。實際上這些罪的入罪量刑標準也存在差異。當哄搶財物行為不符合聚眾哄搶罪的構成要件時,可以搶奪罪或盜竊罪定罪處罰(如果達到了入罪標準)。比如,哄搶人在三人以下時,不符合“聚眾”要件,不成立聚眾哄搶罪,可認定為搶奪罪或盜竊罪。再如,聚眾哄搶財物不符合聚眾哄搶罪的“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要件時,也可認定為搶奪罪或盜竊罪。那么,在搶奪或盜竊的人數達到三人以上,而且符合了各罪的成立條件的,該如何區分聚眾哄搶罪與搶奪罪、盜竊罪(共犯)呢?這確實是司法中的難點。
仔細考察,聚眾哄搶罪與搶奪罪、盜竊罪共犯存在如下的差異:其一,作為侵犯財產的獲利性犯罪,在主觀的利益考量上,聚眾哄搶罪是哄搶財物各自歸屬,即單純“為了自己”。搶奪罪、盜竊罪的共犯在犯罪實施之際是“利益共同體”,即“為了我們”,至于得逞后分贓多少是另外一回事。其二,聚眾哄搶罪的人員構成具有多眾性、延散性,處于隨時可能增加或減少的不確定狀態。搶奪罪、盜竊罪的共犯人盡管也可以是多數,但某次犯罪的參與人數是固定的,參與人是確定的。其三,聚眾哄搶罪的行為方式屬于“各自為政”、“獨立作戰”,盡管客觀上也會相互借勢以使被害人首尾不能兼顧,但不過是外在環境上乘機借勢而已。搶奪罪、盜竊罪的共犯在客觀上處于協力關系,可以有所分工,彼此相互配合、促進。其四,在犯罪行為結局上,聚眾哄搶罪是一哄而散、化整為零。搶奪罪、盜竊罪的共犯則會在現場相互掩護、配合撤離,事后還有分贓或者下次共同犯罪等活動。由上可見,對于現實生活中的聚眾哄搶財物行為,完全可以通過主、客觀特征,區分出聚眾哄搶罪與搶奪罪、盜竊罪共犯。不能因為聚眾哄搶的本質是“公然搶奪或盜竊”,就混淆了犯罪認定,否則就會造成刑罰不公。因為,聚眾哄搶罪的法定刑輕于搶奪罪、盜竊罪,且只處罰首要分子和積極參加者。對于多人實施的搶奪罪、盜竊罪的共同犯罪,不能因為人數較多,就錯誤認定為聚眾哄搶罪,這會使有的行為人逃避刑罰,也會在整體上造成量刑畸輕;反過來,將原本符合聚眾哄搶罪的情形,錯誤地認定為搶奪罪、盜竊罪的共同犯罪,也會擴大犯罪打擊面、加重刑罰。
(二)與搶劫(含事后搶劫)的關系
如果哄搶人在聚眾哄搶過程中,采取了對人施加暴力或脅迫等方式,壓制了被害人反抗的,就超出了聚眾哄搶罪和搶奪罪、盜竊罪的構成要件范圍,而符合了《刑法》第263條搶劫罪的犯罪構成,無疑應認定為搶劫罪。
值得探討的問題是:被害人阻止哄搶或者抓捕哄搶人,哄搶人為了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對哄搶人如何處理?毫無疑問的是,如果哄搶財物正在進行中,哄搶人遭到被害人及時阻止或抓捕,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屬于犯意轉化,應直接適用《刑法》第263條認定為搶劫罪。這種情況存在司法判決的實例,案情如下:2004年4月9日,山西萬榮縣一輛大貨車翻車,車上的果脯等貨物引起當地村民哄搶。司機為制止哄搶,將農藥灑在貨物上。但村民陳升平仍幫助他人從車廂底下掏果脯,進行哄搶,并毆打司機等人。哄搶共造成被害人經濟損失11萬余元。法院判決陳升平犯搶劫罪。參見肖和勇等:《漳州國道貨車側翻遭瘋搶 大叔嘲笑記者不搶是傻子》,資料來源于東南網:http://zzfjsencom/2014-04/18/content_13911584_allhtm,最后訪問時間:2015年9月10日。如果是在哄搶財物行為完成后的現場以及被抓捕的過程中,哄搶人對被害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該如何處理,便與對《刑法》第269條事后搶劫的理解有關。
事后搶劫的前提行為是否限于《刑法》第264條盜竊罪、第266條詐騙罪和第267條搶奪罪,學界基本存在如下幾種觀點:一是僅限于這三個法條的三個普通罪名;參見劉明祥:《財產罪比較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頁;鄭澤善:《轉化型搶劫罪新探》,載《當代法學》2013年第2期,第36頁。二是限于這三個法條的三個罪名,但能評價為侵犯財產的特殊盜竊、詐騙和搶奪行為,例如符合盜伐林木罪的盜伐林木行為,也完全符合第264條盜竊罪的犯罪構成,可以評價為盜竊罪,因而可以成立事后搶劫;參見張明楷:《事后搶劫罪的成立條件》,載《法學家》2013年第5期,第116—120頁。三是不限于這三個法條的三個普通罪名,還包括具有財產罪性質的盜伐林木罪等特殊的盜竊、詐騙、搶奪罪名。參見劉艷紅:《轉化型搶劫罪前提條件范圍的實質解釋》,載趙秉志主編:《刑法論叢》(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07頁。相比之下,觀點二的表面結論與觀點一相同,但實際的認定范圍更大,接近于觀點三。根據觀點一,聚眾哄搶財物的行為人肯定不成立事后搶劫,觀點二、三的舉例中都沒有提到聚眾哄搶罪,只能推測觀點三對此認可的可能性稍大。
對于聚眾哄搶罪能否成立事后搶劫的問題,有學者明確表示反對,理由是“適用《刑法》第269條(轉化搶劫)的前提是在盜竊、搶奪、詐騙犯罪過程中,不能當然認為包含聚眾哄搶行為。”同時認為,“如果聚眾哄搶者實施暴力哄搶財物的,考慮到這是因偶然事件觸發的群體性失范行為,一般也不宜按照搶劫罪處罰。”前引⑥,第535頁。在筆者看來,該觀點得出“第269條前提不能當然包含聚眾哄搶行為”時,并沒有認真地解釋法條,是以結論代替了論證,缺乏依據;在哄搶財物的過程中對被害人施加暴力,直接適用第263條搶劫罪,已是刑法學界的共識。論者認為聚眾哄搶是“因偶然事件觸發的”群體性行為,并不符合現實生活中聚眾哄搶財物行為的全貌。也有學者認識到司法實踐中,聚眾哄搶罪存在盜竊、詐騙、搶奪罪轉化為搶劫罪的相同情況,但認為這是第269條的立法漏洞,應該補充規定聚眾哄搶罪。參見前引B13,第30頁。該觀點采取了立法論上提倡、解釋論上否定的立場。有學者認為,聚眾哄搶行為可以轉化為搶劫罪,具體理由是:為了預防聚眾哄搶行為,減少被害人損失,可考慮對第269條擴大解釋。該條規定的盜竊、詐騙、搶奪罪應理解為犯罪行為,而非僅指盜竊、詐騙、搶奪罪罪名。參見李淼:《聚眾哄搶,情形不同定罪不同》,載《檢察日報》2013年1月25日第3版。
筆者傾向于實質解釋論,主張聚眾哄搶財物的犯罪行為可以成立第269條事后搶劫。理由是:其一,如前所述,聚眾哄搶行為本質是“公然搶奪或盜竊”,成立聚眾哄搶罪的聚眾哄搶行為,其實也符合搶奪罪或盜竊罪,只不過是眾人同時、公然地實施。相比于普通搶奪罪或盜竊罪,聚眾哄搶罪限定了行為方式,增加了一些附隨情狀而已。其二,前述《〈中華人民共和國鐵路法〉中刑事罰則若干問題的解釋》第4條曾規定:“犯罪分子如果在哄搶鐵路運輸物資過程中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或者為窩藏贓物、抗拒逮捕、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應當以搶劫罪論處,從重處罰。”這是聚眾哄搶財物行為可以成立事后搶劫的一個明確的法規范例證。盡管該司法解釋已經失效,但本條解釋規定仍具有合理性。其三,解釋論上肯定聚眾哄搶犯罪行為可以成立第269條事后搶劫,有利于實現罪刑均衡。否則只能成立法定刑輕于搶奪罪、盜竊罪的聚眾哄搶罪,明顯罪刑失衡,不利于懲罰和預防此罪行。總之,只要聚眾哄搶財物行為具有獲得數額較大財物的危險性,不論既遂與否以及實際取得財物數額大小,可以適用第269條認定為事后搶劫。
三、聚眾“打砸搶”的體系解釋
與聚眾哄搶財物行為緊密相關的是《刑法》第289條聚眾“打砸搶”。該條的內容是:“聚眾‘打砸搶,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條、第232條的規定定罪處罰。毀壞或者搶走公私財物的,除判令退賠外,對首要分子,依照本法第263條的規定定罪處罰。”也就是說,聚眾“打砸搶”,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前段);毀壞或者搶走公私財物的,對首要分子依照搶劫罪定罪處罰(后段)。
“打砸搶”不是一個嚴謹的刑法規范術語,現實生活中既有針對人身的“打砸”行為,比如用拳頭打人、用石頭砸人,也有針對財物的“打砸搶”行為,比如用皮鞭打寵物牲畜、用石頭棍棒砸門窗店鋪、搶財物,因此“打砸搶”并非單一地侵犯人身權利或財產權益,而是可能侵犯其一或者同時侵犯兩者。現行刑法將其規定在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一章的擾亂公共秩序罪一節是合理的,突出了它擾亂公共秩序的性質。第289條的內容基本沿襲了1979年《刑法》第137條,舊刑法將其規定于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一章,顯然看重它對人身權利的侵犯。
第289條規定的行為以相關的人身犯罪、財產犯罪定罪處罰,在刑法體系上卻被規定在刑法分則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的擾亂公共秩序罪一節,加之該條不是對獨立罪名的規定,因此一直以來被刑法學界所忽視。筆者的基本觀點是,第289條聚眾“打砸搶”是聚眾實施某些尋釁滋事行為的特別規定,其中“毀壞或者搶走公私財物”是搶劫罪的法律擬制。考慮聚眾“打砸搶”的立法沿革及其在現行刑法中的體系位置,結合刑罰正當性等因素,該條應作如下理解與適用:
其一,第289條聚眾“打砸搶”的規定,處在擾亂公共秩序罪一節的聚眾擾亂社會秩序和特定場所秩序、聚眾沖擊國家機關、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等犯罪行為之前,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尤其是從“打砸搶”的行為來看,與第293條尋釁滋事罪的某些罪狀接近。具體來說,“打砸”人符合該條第1款第1項“隨意毆打他人”;“打砸”財物符合第3項“任意損毀”公私財物;“搶”財物符合第3項“強拿硬要”、“任意占用”公私財物。尋釁滋事罪也可以聚眾實施,該罪第2款就是“糾集他人”尋釁滋事有關情形的加重犯。因此,第289條聚眾“打砸搶”可以看成是對第293條尋釁滋事罪的特別規定。
其二,根據司法解釋,尋釁滋事罪“隨意毆打他人”的“情節惡劣”,在人身傷害程度上頂多是“輕傷”(致1人以上輕傷或者2人以上輕微傷),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尋釁滋事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3〕18號,2013年7月15日頒布、2013年7月22日施行)第2條。而聚眾尋釁滋事的法定刑最高為10年有期徒刑。第289條前段規定對聚眾“打砸搶”限制為“致人傷殘、死亡”,此時以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就可以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詳言之,僅造成輕傷程度的尋釁滋事罪的最高刑是10年有期徒刑,一旦致人傷殘、死亡,就按照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這樣就使得刑罰銜接起來。由此可見,前段對人身犯罪的特別規定是有道理的。反過來則可認為,如果實施聚眾“打砸”人的單純侵犯人身行為,且沒有“致人傷殘、死亡”的,完全可以尋釁滋事罪認定處理。有學者認為,“隨意毆打他人致人輕傷的行為,既符合故意傷害罪的犯罪構成,也符合尋釁滋事罪的犯罪構成。對此,按想象競合犯從一重罪處罰即可”。同樣的思路,尋釁滋事罪第1款第2、3、4項行為,也符合尋釁滋事罪與過失致人重傷罪、過失致人死亡罪、非法拘禁罪、侮辱罪、敲詐勒索罪、搶劫罪、聚眾哄搶罪、故意毀壞財物罪、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交通秩序罪的想象競合犯,均應從一重罪處罰。參見前引⑤,第1069—1070頁。
其三,第289條后段以搶劫罪定罪處罰的規定是法律擬制。因為搶劫罪屬于取得型財產罪,主觀上要求非法占有目的,而毀壞意思異于非法占有目的,固而,“毀壞……公私財物”原本不符合搶劫罪的主觀要件,但是本條將聚眾“打砸搶”過程中“毀壞……公私財物”以搶劫罪定罪處罰,就明顯屬于法律擬制。再說,聚眾“打砸搶”只處罰首要分子,但搶劫罪沒有理由只處罰首要分子。將“毀壞”財物擬制為搶劫罪的實質理由在于:一方面,不管是基于利用意思的非法占有目的,還是基于毀壞意思,其實質都是侵犯了他人對財物的利用可能性,在這點上,“毀壞”或“搶走”公私財物具有共通性(這是所有財產罪可罰性的共同基礎);另一方面,聚眾“打砸搶”行為人的主觀方面可能具有毀壞或搶占的故意,客觀上存在既毀壞了部分財物又搶占了部分財物的復雜情形,加之聚眾犯罪過程中人員眾多,司法實踐中不容易區分,法律擬制便于司法操作。從第289條的刑法體系位置來看,它理應是對法條排序其后的擾亂公共秩序罪特別是尋釁滋事罪的某些行為的法律擬制。換句話說,是將尋釁滋事罪的某些侵犯財產行為法律擬制為搶劫罪。
其四,由于第289條后段是搶劫罪的法律擬制,因此對后段法條應作如下理解:首先,法律擬制的實質理由在于法益侵害相同或相似,搶劫罪是同時侵犯財產權益和人身權利的犯罪,因此聚眾“打砸搶”過程中,既要求實施了“打砸搶”財物的行為(即“毀壞或者搶走公私財物”),也要求實施了“打砸”人(對人暴力)或者通過“打砸搶”財物進而形成對人脅迫的行為。其次,正如同事后搶劫的成立不需要手段行為在先、目的行為在后,對于搶劫罪法律擬制的聚眾“打砸搶”來說,“打砸”人或財物的手段行為,也不要求是在“打砸搶”財物目的支配下實施,而可以是在“打砸搶”財物的過程中伴隨發生,或者是在“打砸搶”財物之后才發生。最后,法律擬制的規則之一是要按照法條本身的表述進行解釋,也即為了成立擬制的搶劫罪,“打砸搶”可能是手段行為完全抑制被害人反抗,但最后僅是“毀壞……公私財物”,而不必非要取得財物。反之,如果“打砸”人或財物的手段行為與“打砸搶”財物的目的行為完全符合普通搶劫罪的構成要件,就應直接適用第263條定罪量刑,而且處罰對象不限于首要分子,而不能適用第289條的擬制規定。
其五,搶劫罪法律擬制的效果是,嚴懲聚眾實施某些尋釁滋事行為的首要分子。聚眾尋釁滋事的客觀違法性大于個人尋釁滋事,如前所述聚眾“打砸搶”是聚眾實施某些尋釁滋事行為的特別規定,而搶劫罪也重于尋釁滋事罪(搶劫罪最高可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因此,將聚眾“打砸搶”中的“毀壞或者搶走公私財物”的行為擬制為搶劫罪,并處罰首要分子,效果便是嚴懲聚眾實施某些尋釁滋事行為的首要分子。言外之意,對首要分子以外的人僅需要按照正常情況進行刑罰處罰即可,通常來說就是尋釁滋事罪(或與敲詐勒索罪、聚眾哄搶罪、故意毀壞財物罪等的想象競合犯)。不能認為以搶劫罪定罪處罰的首要分子以外的人就不成立犯罪、不需要被刑罰處罰了,那樣會造成處罰漏洞。這從聚眾“打砸搶”財物與聚眾哄搶罪的比較中可以更加明了:聚眾哄搶罪的本質是“公然搶奪或盜竊”,客觀違法性當然輕于聚眾“打砸搶”財物,既然聚眾哄搶罪規定了處罰首要分子和積極參加者,那么聚眾“打砸搶”財物中應受刑罰處罰的當然不應限于首要分子。至少對于積極參加者,如果能夠通過合理解釋符合其他犯罪構成要件,就理應追究其刑事責任。
其六,協調第289條前段和后段進行理解。前段“致人傷殘、死亡”應作限制解釋,即聚眾“打砸”人的單純侵犯人身行為所致,不能伴隨“打砸搶”財物的行為。否則,要么成立擬制的搶劫罪,適用第268條后段,要么符合普通的搶劫罪,直接以第263條定罪處罰,而不再以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但是,有學者卻認為,聚眾“打砸搶”的“打”就是對被害人進行人身傷害,如果造成了輕傷、重傷或者死亡的,以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砸”就是故意毀壞公私財物,“搶”只能是搶劫財物,聚眾“打砸搶”行為定搶劫罪時,客觀危害行為是毀壞或搶走公私財物的行為;在聚眾“打砸搶”過程中,打人又砸搶財物的,成立故意傷害罪和搶劫罪,予以數罪并罰。參見金澤剛、張正新:《搶劫罪詳論》,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年版,第511—512頁。該觀點完全將第289條的前、后段割裂開來理解,實際上也完全忽視了該條與其他財產罪、擾亂公共秩序罪的聯系。法律擬制的實質理由是法益侵害的相同或近似,既然論者承認后段的搶劫罪是法律擬制,而搶劫罪是侵犯人身和財產的犯罪,那么,就不能認為“打砸搶”財物與人身侵犯無關。協調地理解前后段,就不能得出聚眾“打砸搶”中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與搶劫罪并罰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