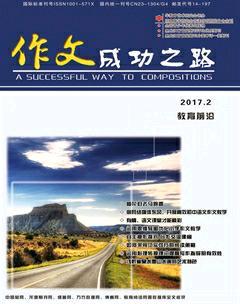病中隨想
2017-03-26 11:26:11周一婷
作文成功之路·教育前言
2017年2期
周一婷
圣誕節前后,病毒性流感跌撞著迅速蔓延。班里此起彼伏的咳嗽聲像是打了結解不開的耳機線。我把咳得疼痛的胸口拍得咚咚響。體溫計里的水銀柱無聲得上升又下降,上升又下降,循環往復。旁桌、后桌、斜前桌,都請假回家了。
中午回到宿舍,脫掉外套蜷縮在角落里。舍友趿著拖鞋的“啪嗒”聲,塑料袋嘁嚓的刺耳響聲,頭部傳來的灼熱溫度和時有的昏厥痛感,以及咳嗽帶來的顫抖——忽然間有莫名的想家的感覺。
給媽媽撥通了電話,接通后我扯著燒啞的的嗓子喚了一聲,忽然眼淚控制不住地涌了出來。“怎么了怎么了?生病了嗎?”透著焦急,和濃重的鼻音。我一頓,“嗯……有點燒……”本想向媽媽撒嬌,讓她接我回家,開口卻成了這樣。早上時體溫已經飆到了三十八度半,上午的歷史課總感覺地面在晃。“回來打針吧?”“不用了吧……下午的課不想落下。”我嘟起嘴,蒙在被里,嗚囔著擠出幾個字。聽到媽媽有些粗重的呼吸聲,我實在不想讓她再來學校。也許此時,她和我一樣蒙在被里吧。
今年圣誕節沒有下雪。在學校里住校,也不知道鬧市區的冬夜又會是怎樣的燈紅酒綠。想起去年圣誕,和死黨瑩逛遍了市區各大飾品店,購置著圣誕禮物。一路上或呢喃細語輕聲訴說兩個人間的秘密,或敞開笑聲細碎了一地小幸福。似乎回憶起來的事物永遠是美好的,要問我,兩人間有沒有吵過架鬧過別扭?想想,說,是真的不記得。那時候的我們初三,老師天天給我們算著日子。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小雪花·初中高分作文(2021年4期)2021-08-27 09:21:34
火花(2020年9期)2020-09-21 02:25:16
大灰狼(2019年11期)2019-12-17 08:01:18
小雪花·初中高分作文(2018年4期)2018-12-12 10:32:28
絲路藝術(2018年8期)2018-09-27 09:24:40
Coco薇(2017年10期)2017-10-12 19:26:55
時代青年·視點(2016年11期)2017-01-14 19:34:24
Coco薇(2016年8期)2016-10-09 16:46:39
小雪花·初中高分作文(2016年2期)2016-05-30 16:36:19
小學生·新讀寫(2016年5期)2016-05-14 13:4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