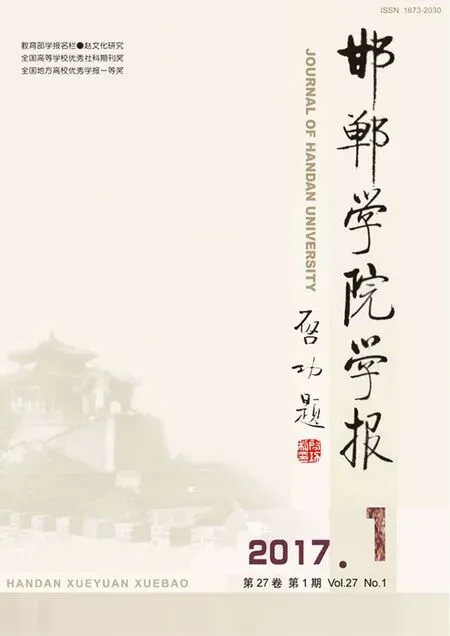趙都邯鄲故城考古新發現與探索
喬登云
?
趙都邯鄲故城考古新發現與探索
喬登云
(邯鄲市文物保護研究所,河北邯鄲056002)
根據趙都邯鄲故城眾多新的考古發現,重點對戰國兩漢時期趙都大北城與大漢城、趙王城南防御系統及趙都城郊祭祀遺跡作了重新審視或全新探索。初步認為趙都大北城與大漢城的城垣及城區范圍可能并不完全重合,趙王城南壕溝除屬防御體系外,也不排兼具引水或排水功能;而城郊多處較特殊的以填埋灰綠土和銅箭頭等兵器為特征的坑穴遺跡,則很可能屬于與軍旅或戰事祭祀活動相關的“祃祭”遺存。
戰漢時期;趙國都城;邯鄲故城;新發現
邯鄲是戰國時期趙國的國都,也是兩漢時期趙郡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并保留下了眾多的文化古跡和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此前,筆者曾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邯鄲古城的主要考古發現進行過梳理,并以《趙都邯鄲故城考古發現與研究》及《試論邯鄲古城的歷史變遷》為題,闡述了自己對所發現考古材料的基本觀點和初步認識①。近年來,隨著城市建設規模的擴大及考古工作的廣泛開展,又有不少新的考古發現及材料面世,既向過去某些傳統認識提出了挑戰,也為趙都邯鄲故城考古及歷史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課題。故本文擬主要對近年來部分新的考古資料予以必要敘述,并就某些相關問題予以初步分析和探討。以期拋磚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趙都大北城與大漢城問題
眾所周知,戰國時期趙都邯鄲故城由相對獨立的王城和居民城兩部分組成。王城即宮城,俗稱為趙王城;居民城,也有的稱為廓城,今按相對位置則多稱為“大北城”。至于兩漢時期的趙都邯鄲,一般認為是以戰國時期趙都之居民城也即“大北城”為基礎,經維修利用而形成。而且,筆者還曾提出在西漢吳楚七國之亂后,因趙都邯鄲城曾遭到嚴重破壞,又興建了范圍較小的新城,且以“大漢城”和“小漢城”為名以示區別,并認為大、小兩漢城最初很可能同時使用,直到東漢以后大漢城才逐步被小漢城取代而廢棄②。那么,戰國時期的“大北城”與兩漢時期的“大漢城”究竟是如何演變的,或者說兩者的具體范圍是否完全重合,是否存在變化呢?按照以往的觀點,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或者至少截止目前尚無人提及其間有何大的變化。
究其原因,除了文獻資料匱乏或失載等因素外,與考古資料較少或有限也不無關系。因此,有必要將近年來部分新的考古發現及所獲資料予以簡要梳理并敘述如下。
自2009年5月開始,為配合邯鄲市區舊城改造,市文物保護研究所分階段對大北城南垣進行了詳細勘探調查,進一步確定了地下城垣的確切位置和范圍,并發現了新的東南城角。其中5~6月間,除對今中華大街以東地下墻址作了探查,并在距中華大街250米處的賀莊村中部發現一條寬10余米與南垣相接并轉向北去的地下城墻,也即過去所稱的東南城角外,還發現南垣在此并未中斷,而是呈丁字形繼續向東延伸。9月,對中華大街以西至107國道(邯磁公路)間的五倉區所涉城垣作了探查,在渚河路中心線以南,西端相距約360米、東端相距約210米處東西一線,均發現有保存狀況不一的大北城南垣地下墻址。10月,對賀莊村以東至維多利亞港灣(原市啤酒廠)段進行了勘探,次年3月,又對該段東端進行了復查和定位,發現大北城南垣由原賀莊城角繼續向東延伸約400米,于今渚河路中心線南側120米、光明大街以西75米處原邯鄲啤酒廠院內北轉,過渚河路北去。地下城墻寬約25~30米左右,距現地表深8~9米,殘高約1米。墻體為花土,內含陶器碎片、磚塊、紅燒土粒等,由人工夯筑而成,夯跡明顯。從新發現墻體來看,東延部分與南垣連為一體,北轉部分恰與今曙光街方向原發現的“大北城”東垣處于南北同一條線上,且墻體規模大體相同。并由此判定,“原啤酒廠院內才是‘大北城’真正的東南城角,而南垣的長度也應由原3090米修正為近3500米”,城址面積也由原來的約1380多萬平方米修正為約1390萬平方米。①
2011年12月至2012年1月間,在對陵西大街與水廠路東北角的上都名苑深約5米的建筑基礎實施勘探時,于地槽北壁發現了橫貫東西的城墻基址及墓葬等遺跡,槽內城墻長約342米,頂部距現地表約2.2米,殘存最大高度為4.3米。經解剖發現:西段墻體坐落在細黃淤土及其下的灰褐土上,皆為不含文化遺物的自然堆積;斷面呈梯形,上寬6米、下寬7米、殘高1.2米;墻土呈灰褐色,內含部分料姜石和細黃土,偶見陶片或獸骨,夯打堅實,夯窩密集,夯層清晰,層厚6~18厘米;夯土墻南北兩側基部有墊筑的護坡或塌落形成的坡狀堆積。東段墻體分內、外兩重,北側即內側墻體縱剖面呈梯形,現可見殘高1.8米,上寬6.5米,基底寬7.1米,層厚6~16厘米,墻土及堆積情況與西段類似,應屬同一墻體;南側即外側墻體疊壓在內側墻體護坡之上,經探查槽內東西長約90米,南北寬約30米,本次未能解剖至南邊,現殘存高度1.8米,經探查寬約30米,墻土呈黑褐或深灰褐色,質堅,夯層清晰,層厚5~16厘米,內含燒土塊、草木灰,并夾雜有較多的碎瓦片或陶片等,其修筑年代或時間要晚于北側墻體,夯筑質量也略遜于北側墻體。此外,在西段城墻外側還發現一組南北向排水管道,方向約3°,計3道,呈品字形上下排列,分別由圓筒形陶管套接而成,北高南低,高差約0.3米,殘存長度11.4米,單節陶管一端略粗,直徑約0.3米,長0.42米,兩端接頭處飾橫向瓦棱紋,管身飾縱向繩紋,管道內填滿淤土或淤沙,顯然屬于排水設施。因其北端距城墻基部寬約24米已被施工破壞,與城墻間交接關系已不得而知,但從斷面看似疊壓在城墻塌落土層之上,鋪設年代應與城墻同時或略晚。另在夯土墻上或緊靠城墻內側發現東漢墓葬5座、唐墓2座。②
2012年3月間,在對渚河路與滏河大街交叉口東北角的新東方購物廣場已開挖的基槽實施勘探時,于地槽東部發現一道南北向夯土墻遺跡,并對殘存夯土墻南、北兩端作了解剖斷面,采集了部分陶片標本,還在地槽內夯土墻中上部偏東處清理宋代殘墓一座。北側墻體基底寬約20米,距地表深約10~10.4米,分內外三重,似分階段或經補筑形成,現頂面距地表約8米,殘高約1~2米,夯層一般厚5~15厘米,少數厚30厘米。主墻體位于最外側(東側),底寬約14米,頂寬約8.4米,殘存厚度1.5米,為紅褐與黃褐色混合土,夯層下部較薄,上部較厚,夯窩清晰,內含少量陶片;中部墻體打破或疊壓在外側墻體之上,基地寬約6米,殘存厚度0.8米,為黑色土,夯層明顯,夯窩清晰,夯打堅實,其內基本不含文化遺物;內側墻體向下開挖有基槽,打破并斜倚在中部墻體之上,底寬4.5米,厚存1米,為黃褐色土,夯層清晰,夯打不甚堅實,內含少量陶片和瓦片。南側斷面為地槽南壁,上部已噴漿加固,槽內暴露部分基底寬約13米,底面距現地表約11米,夯層厚5~15厘米,以5~10厘米居多,內含少量陶豆、瓦片等遺物。墻體分三次夯筑,但先后次序及土質土色與北側不同。西側墻體最早,底寬約4.5米,為黑褐色土,中部黑色土墻體打破西側墻體,東側黃褐土墻體又打破中部墻體,夯筑以中部墻體最為堅實。根據夯層中出土的陶片、瓦片等,初步判定夯筑墻體的年代為戰漢時期。此外,為了搞清本墻體的走向及范圍,2015年5~6月間又進行了追蹤勘探,發現墻體由此向南跨越渚河路延伸至邯鄲大學西側的寶恒汽車配件維修城內,因該處地面硬化而未能勘探,其南亦無墻址發現,似已中斷,現查明部分南北長約350余米;由此向西橫跨滏河大街也勘探發現一條東西向地下墻體,現已追溯至滏陽河羅成頭閘附近,其顯然屬于由寶恒汽配城轉角向西的連續墻體,查明部分東西長約670余米,故本墻體應屬與過去所發現墻體關系尚不明確的一段新的城墻基址。
2012年4月,在配合渚河路以南、浴新大街以西、邯磁公路以東、水廠路以北城區改造時,于趙都新城三號(S3)地塊15號住宅樓基槽東南部,發現并解剖發掘了一段東西向城墻基址。據觀察分析,該城墻應與其東側上都名苑所發現夯土墻為同一道墻體。從城墻橫斷面來看,暴露部分底部總寬約27米,殘高4.7~5.1米,墻體由主體墻和內、外五重經夯筑的附加墻(有的或為護坡)組成。其中主墻體及內側附加墻或護坡,基本以地勢較高的生土底經修整并鋪墊一層厚0.1~0.25米的紅土為基礎,南北寬12.45米;外側數重附加墻體及護坡則多直接疊壓在戰漢文化層之上。主體墻及內外附加墻體,不僅夯層厚度及土質土色不同,主體墻夯層厚僅4~14厘米,附加墻夯層則厚薄不等,薄者10厘米左右,厚者40~60厘米,甚至厚達1米以上;而且包含物品種及多寡不一,主體墻僅見部分紅土塊和料姜等,內外第一或第二重附加墻包含物也很少,外側第三重附加墻夯層中則夾雜有少量繩紋灰陶片、瓦片、空心磚塊等。尤其主體墻上半部局部疊壓在外側第一道附加墻下半部之上,外側第一、二附加墻之間和內側附加墻北側底部,還分別疊壓有一條口寬1.4~1.8米、底寬0.8~0.9米、深0.9~1.1米斷面呈斗形且與城墻平行的溝槽,外側附加墻上半部也發現一條口寬4.25米、深3.7米,與城墻平行且打破第二、三重附加墻的漏斗形壕溝;外側墻體下溝槽經夯打填實,內側墻體下溝槽填以較疏松的黃褐土,外側壕溝底部則填有鵝卵石、繩紋灰陶片、瓦片等。本段城墻與過去探明的由龐村轉角沿渚河路以南向東延伸的“大北城”南垣處在同一條線上,且走向、寬度基本一致,說明該墻體即大北城南垣之一段,但復雜的多重墻體和交錯的疊壓層次,以及寬窄不一的溝槽、壕溝和不同的包含物等,又說明本墻體曾經多次拓寬、加固或補修,其中的溝槽或壕溝還很可能與不同階段墻體的排水系統或防御設施有關。
根據上述新的考古發現,至少可以說明下幾點:一是近年考古勘探或發掘所發現的墻體主要集中在戰國大北城或兩漢“大漢城”南垣一線,從而證明今邯鄲城區之下確實還保存有較為完整或斷續相連的戰漢時期大城南垣基址。二是所發現的南垣墻址并不是東西一條直線,而是彎彎曲曲、左右擺動和充滿變化,但總體上均位于今渚河路以南200~360米范圍之內,這很可能與當時的自然地勢和地貌環境有關。三是所發現墻體多數并列數重,且夯土層次結構、厚度密度、土質土色、疊壓關系和包含物等也存在明顯變化,這除了在修筑過程中采取錯列疊筑工序及夯筑先后次序或人工作業等原因形成的差別外,最主要的應屬后期拓寬、加固或補修等原因所致,說明城垣年代跨度較大,延續使用時間較長。四是南城垣由賀莊又向東延長了約400米,并在維多利亞港灣即原市啤酒廠內又發現了新的城角,說明原大北城或大漢城至少出現過今賀莊和啤酒廠兩個東南城角,城區范圍也有所變化。五是在原大北城東側又發現了新的城墻及城角基址,其雖然與大北城或大漢城尚不連接,但從位置上卻與前者的南垣處在同一直線上,說明期間很可能也存在著某種聯系。
既然如此,可以說又向我們提出了以下幾個問題:一是大北城或大漢城究竟有幾個東南城角,其說明了什么或意義何在?二是大北城或大漢城本身是否存在過變化,其城區范圍究竟有多大?三是大漢城與大北城是否完全重合,兩者間是否存在過變化?對此,可以說目前我們確實還難于做出圓滿的解答。原因是所發現城址多為地表勘探所獲,即使進行過發掘解剖,發掘面積也非常有限,只能作為局部現象或個例,更主要的是戰漢兩類遺存因經過當時及其后長期的翻擾,致使兩種遺物相互混雜而難于準確區分,從而為墻址年代的判定造成了困難。即使如此,筆者仍然認為無論大北城與大漢城本身或兩者之間還是應當存在有變化的。從兩者本身而言,每處或歷次墻體發掘都可發現,墻體多有加固、拓寬或補筑現象,當然也不排除因國力盛衰、人口變化、墻體本身或環境因素等重筑墻體,以及拓寬或縮小城區使用面積的可能。如兩漢時期即存在過大漢城與小漢城的區別和變化,那么在戰國至西漢前期長達200多年的都城歷史中,大北城或大漢城東南城角由今賀莊村向市啤酒廠或相反方向位移,城區面積也在1380~1390多萬平方米之間轉換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新發現的邯鄲大學西側的城角,也不排除屬于大北城或大漢城又一東南城角的可能,如此則城區范圍會更大。從戰漢兩座大城而言,鑒于現有資料尤其是城垣確切年代尚難準確判定,我們還不敢妄下結論,但既然同朝同代或同一時期的城垣及城區范圍都可多次發生變化,那么我們自然相信經改朝換代兩個時期的城址絕不可能毫無變化,有可能的只是時間早晚或何時變化,以及我們尚未識別而已。
二、趙王城南的防御系統問題
趙王城是戰國時期趙國的宮城,有著較為完備的排水及防御系統,根據以往的考古發現,筆者曾提出“趙王城外圍當普遍有護城壕存在”,并認為借以“提高城墻的相對高度”和“加大攻城的難度”應是其最主要的功能。對此,不僅得到了新的考古資料的證實,而且又取得了新的收獲,進一步加深了我們對趙國宮城“趙王城”防御系統的了解。
其中,2005年省文物研究所對趙王城西小城南垣外側進行發掘解剖,再次證實了城壕的確實存在。“西城南垣外側的城壕,北距城垣基約 17米至19米。斷面大致呈倒梯形,口部 寬10米,底寬2.4米,深3.8米。”①既與1997年5月市文物研究所在配合邯鋼化肥廠住宅樓建設時,于西小城西城垣中心線以西24米處發現的寬約7~8米、深約5米的西城壕相似,也使2001年在西小城南墻外勘探發現的護城壕遺址得到了明確證實。②
2007年,為了配合南水北調工程建設,省文物研究所在鄭崗村西勘探發掘時,于趙王城南垣以南約1000米處,發 現了人工開挖的東西向的外圍壕溝系統。壕溝與趙王城南垣基本平行,依形制結構,大體可分為東西兩部分。其中“西段部分主要為三條平行壕溝,長1100余米,間距10米,均開掘在生土層中,被戰國晚期文化層疊壓。橫斷面呈倒梯形,北壕溝(G1)口部寬4~4.6米,底部寬0.4~0.7米,深2.25~2.6米;中間壕溝(G2)口部寬4.3~4.9米,底部寬0.55~0.6米,深2~2.6米;南側壕溝(G3)口部寬3~3.8米,底部寬0.6米,深2.5~2.6米。溝內填土分多層,多呈垂弧狀堆積。包含物有戰國時期的灰陶罐、 盆、豆及板瓦、筒瓦殘片等。根據地層及出土遺物分析,壕溝的年代在戰國晚期到末期,其中北面兩條壕溝的年代相近,最南面第三條溝的年代較之略晚。”東段部分主要發現于鄭家崗村東,已經探明長約1200米,為東西向單條壕溝,口部寬約10米,深約3米,東端情況尚未探明。③發掘者認為,“根據目前的考古勘察資料判斷,趙王城南郊的這條外圍壕溝,向西連接渚河,向東的情況尚不清楚,推測應與東面不遠處的滏陽河相連。如此人工開挖的壕溝與天然河道有機聯系起來,構成了趙王城東、南、西面近郊的壕溝防御體系,并且它們與城垣外側附近的城壕一起,共同構成了趙王城規模宏大而完整的壕溝防御系統。”④
2013年9~11月間,市文物研究所在對位于趙王城南側、機場路西側的華北鋼鐵物流園區實施文物勘探時,也對所探明的數條壕溝作了局部解剖發掘。其中3條壕溝(G1~G3)年代相對較晚,約在漢代乃至唐宋以后,均疊壓或打破其下的壕溝(G4),且范圍尚不明確,不排除某些或屬于其下所疊壓壕溝不同堆積層次的可能;另2條壕溝年代相對較早,形制結構及范圍也相對較明確。后兩條壕溝中一條(G4)恰位于園區南圍墻之下,呈東西向,北距趙王城南垣約1000米,現已探明園區內東西長560米,向西可延伸至鄭家崗村東,向東過機場路業已中斷或已遭破壞,未見明顯蹤跡,東西全長約1100米。為搞清壕溝的結構及年代,在園區內東段和中段開挖探溝4條,對壕溝作了縱向解剖發掘,但因受征地范圍等條件限制,多數只清理了壕溝的北半部即園區圍墻內部分。從發掘情況看,壕溝開口于漢代層下,打破戰國地層,有的并被晚期地層或擾溝破壞。橫斷面呈敞口鍋底形,坑壁上半部坡度較緩,下半部相對較陡,底部較平緩;口部多未清至南邊,以底部中線測算,口寬約8~9米,底部寬1.5~2米左右,殘深1.2~2.55米。坑內堆積均包括黃褐色粘土、紅色膠粘土和黑褐色粘土3層,內含細沙粒、料姜石、草木灰、紅燒土粒和碎陶片等,溝底局部有較純凈的料姜石層;其中上層堆積為平底,內出3枚五銖錢幣,年代為西漢中期,中、下層為弧形堆積,據所出陶片初步判定屬戰國至西漢早期階段。另一條壕溝(G5)位于園區東部原“高級渠”以東,呈西北東南走向,方向33°,探明部分長243米,園區外西北方向未予追蹤勘探,東南方向已伸入園區東南角圍墻之外,似與前述壕溝(G4)存在銜接或疊壓、打破關系。經解剖發掘獲知,壕溝疊壓在宋代層下,直接開鑿在含料姜石的黃色生土層內;橫斷面呈斗形,斜壁平底,口寬3~3.5米,底寬0.5~1.2米,深1.5~2米。溝內填土為一次性堆積,均為黑褐色粘土,含有細沙粒、料姜石、紅燒土粒、灰屑及陶片等,溝底局部有較純凈的料姜石層。根據出土的泥質灰陶罐、盆、碗等殘片,初步判斷為戰國時期堆積,甚或早至戰國中前期。
從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趙王城南垣外從西到東確實存有數條大型壕溝,盡管目前尚未完全搞清其關系,但大體上可劃分為兩組:一組位于趙王城南垣外約1000米處,為東西走向,全長約2600~2700米,其中西段由南北并列的3條平行壕溝組成,長約1100米,間距10米,口部寬3~4.6米,深2~2.6米;東段僅見1條壕溝,2007年省文物研究所探明長度約1200米,2013年市文物研究所探明長度約1100米,機場路及以東或許已遭施工破壞,但兩者實為同一壕溝當毫無疑問,解剖地段口部寬約8~9米,殘深1.2~2.55米;中間長約400米疊壓在鄭崗村之下,其銜接關系或如何由3條壕溝匯為1條壕溝,目前尚難于判定;據溝內堆積及包含物,壕溝的年代雖然判定為戰國晚期至西漢初期,但其開鑿年代至少應在戰國晚期。另一條壕溝大體上位于趙王城西小城10號門闕以東,為西北東南走向,現僅在機場路以西的華北鋼鐵物流園區內發現一段,長約243米,口部寬約3~3.5米,約深1.5~2米,兩端尚未追蹤探查,其來龍去脈及總長度不詳;據溝內堆積判定,壕溝的年代約當戰國時期,而實際開鑿年代應更早,或可至戰國中前期。
關于兩條壕溝的用途或性質,段宏振先生即對前述東西向壕溝提出過應屬趙王城外圍“防御系統”的看法,并認為該壕溝“向西連接港(渚)河”,向東可能“應與東面不遠處的滏陽河相連”,使“人工開挖的壕溝與天然河道有機聯系起來,構成了趙王城東、南、西面近郊的壕溝防御體系。”但也有的發掘者認為兩條壕溝應均屬“由西向東引水”之灌渠。筆者雖未參加過兩條壕溝的實際發掘,尤其對溝內的堆積及溝底情況并不十分了解,但通過對發掘材料及壕溝所處位置與環境等因素分析,認為前述兩條壕溝不僅所處位置、走向和規模不同,而且開鑿年代也可能存在著差別,所以對于其用途或性質并不能一概而論。
對于前者即東西向壕溝,筆者基本上贊同屬于城市“防御”系統的認識,但也不排其兼具引水或排水功能的可能。首先,從地理環境來看,趙王城大體上位于太行山余脈堵山西南部丘陵的邊緣,屬傾斜平原地帶,雖然微觀上城區較四周地勢相對較高,但宏觀上西部為低山丘陵區,且溝壑縱橫,相對易守難攻;東部地勢較低洼,且多有積水,也有利于防守;南北兩側地勢較平緩,但北側古有牛首水(即今渚河、沁河)之險相阻隔,而唯南側無險可依,無障可據,因此,于趙王城外圍尤其南側人工構筑防御工事既是地理環境所迫,也是當時戰爭環境及軍事防御所必需。其次,從壕溝形式、規模及所處位置來看,不僅東西與趙王城南垣平行,長度達2600米以上,基本上可將南垣一線屏敝或阻隔,而且,從距離上于趙王城南垣外約1000米處構筑防御工事,也正好可起到增強多重防御能力、有效阻擊外敵進攻和提高王城安全保障的作用。至于壕溝與周圍自然河流的關系,自然不能不提到由趙王城北小城穿城而過的渚河。據新修《邯鄲縣志》稱:“舊志載:渚河上游有二源,皆出于堵山。一是自縣西南25公里處東北流稱藺家河,二是自縣西南30公里處東北流稱閻家河,二河合流而東流稱渚河。渚河往東又分為南北兩支,南支經本縣的羊井、大隱豹、小隱豹向東北,流至邯鄲市的西大屯村;北支自賈溝、經喬溝、藺家河、中莊、霍北、酒務樓等村,然后到西大屯村與南支匯合”。①似乎是說渚河上源二流匯合后向東又分為南北兩支,并于趙王城北的西大屯村再次匯流,這實際上是借以命名的閻家河村因早已湮沒而為人淡忘所致。筆者認為舊志所謂“藺家河”和“閻家河”均因該河流經其地而命名,且兩河很可能就是新志所稱的“南北兩支”,所謂北支即原稱的藺家河,而南支即原稱的閻家河,其匯流處或許就在今西大屯村附近,由此向東始稱為渚河。從現存河道來看,因受自然地勢限制,趙王城以西渚河上游其實至今并無太大變化,而且筆者懷疑戰國時期渚河很可能由趙王城之北折而向南,并由大北城南垣外繼而東流,現渚河由西大屯向東南穿趙王城北小城而過,或許是趙王城廢棄后因某種需要逐漸導流所致,如清光緒年間渚河由今渚河路一線向東由羅城頭閘北側入滏陽河,上世紀50年代渚河北支由酒務樓向東南改道、60年代再由西大屯向南改道,繞過邯鄲市,經南十里鋪南至張莊橋村南入滏陽河就是最直接的證明。換言之,筆者認為最初的渚河及其上源很可能并未穿越趙王城,而是由城北東流,并由趙王城與大北城之間折而向南,再由大北城南垣外或附近東流而過。之所以如此推測,不僅因為河流穿城而過必然會給城垣的封閉帶來較大的構筑難度,而且敞開的河流通道也必然會為軍事防御及洪澇治理埋下巨大的安全隱患。相反,如渚河由城外繞行,不僅可以使趙王城之西、北及東北角,以及大北城之南及西南角構成一道天然屏障,而且,也為城市用水及排水提供了較為便利的條件。或許這也正是趙王城與大北城選址及兩城曲折的城垣和現存布局形式的原因所在。如此則壕溝西端與相距僅數百米的大隱豹村旁的渚河南支,也即渚河南源閻家河相接,東端或由趙王城東城外折而向北并再次與渚河下流交匯,從而即可形成趙王城外圍一條更大范圍的環壕或護城河防御系統。當然,上述認識僅是筆者目前的一種推測,尚有待將來新的考古發現予以證實或否定。此外,東段壕溝底部局部發現有較純凈的料姜石,且下層堆積為黑褐色粘土,似乎與溝內曾經過水流沖刷及泥沙沉淀等有關,或許這就是某些發掘者認為壕溝屬于“由西向東引水”之灌渠的依據,也是筆者認為并不排除其兼具引水或排水功能之可能的原因之一。
對于后者西北東南向壕溝,因目前尚缺乏具有說服力的證據,自然還很難對其做出較為合理的判斷,但根據現有資料及某些跡象分析,筆者認為最大的可能應屬因某種特殊需要而構筑的臨時性排水系統。因為從壕溝所處位置來看,大體上位于趙王城東、西小城南垣中部之南,兩端雖未追蹤勘探,但其向西北恰與趙王城西小城5號門闕位于同一直線上,兩者間距僅約840米,向北與南垣直線距離更近,且壕溝寬僅3~3.5米,深1.5~2米,顯然并不能為趙王城的軍事防御提供防護作用或安全保障,反而還會為軍事進攻并逼近城垣提供掩護或通道,從而對趙王宮城的防御構成較大的威脅。相反,推測其屬于臨時性排水系統,一是基于壕溝西北端恰與西小城5號門闕相對,或許兩者并非偶然巧合,而是存在某種必然的聯系及相互連接之可能。二是從地勢上西小城所處位置最高,5號門闕處海拔高度在90米以上,而壕溝東南端高僅80米左右,高差達10余米,具有向東南排水的自然條件。三是壕溝規模特別是寬度及深度有限,且溝內為一次性堆積,似為臨時性設施,延用時間較短;溝底局部還有較純凈的料姜石層,似為流水沖刷所形成,或許這也是某些發掘者將其判定為“由西向東引水”之灌渠溝的依據。四是壕溝的開鑿年代應較早,發掘者判定為戰國早中期,或許在趙王城建城初期,當時可能因城區的排水系統尚不太完善,鑒于某種特殊需要,特別是將趙王城龍臺以南的暴雨洪水由5號門闕排出,并通過開挖的臨時性壕溝,將城區內外的積水排泄至東南部較低洼區域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當然,這同樣需要將來新的考古資料予以驗證和確定。
三、趙都城郊的祭祀遺跡問題
近年來,在邯鄲城區西北部即趙都西北城郊附近還發現一種較為特殊的遺跡。該遺跡現象不僅在趙都邯鄲周圍此前的考古遺存中從未發現,而且在國內其他同時期遺存中也非常少見,因此有必要對所獲材料予以簡單梳理和介紹,并對其用途及性質予以初步分析和探索。
2009年11~12月間,市文物研究所在建設大街以西、八一路以南的綠樹林楓住宅小區實施文物勘探發掘時,發現并清理了兩組坑穴遺跡。第1組坑穴發現于小區中部地下車庫的西段,地表向下深約1.5米已被建筑施工清除,坑穴上部也已遭破壞,共計6座,編號H1~H6。從整體布局來看,大體分東西兩列、南北三排,排列整齊,間距約1米,方向較一致,均呈西南-東北向,約在30~40°之間。坑穴平面多呈長方形,口大底小,有的坑底不平整或呈坡狀;現存坑口長在1.05~1.71米、寬在0.32~0.63米、底部長在0.6~1.66米、寬在0.2~0.44米之間,殘存深度多1米左右,少數深達2~2.3米,若上部未經破壞,口部及深度還應略大,實際深度均應在2~3米及以上。坑內填土多分灰綠土和褐色土兩層,但疊壓次序或上或下,層次或厚或薄,不盡一致;灰綠土多為較疏松的粉末狀,分綠、黃、灰白等多種顏色,含土成分較小,質量較輕,似腐爛的有機物形成,其內多有碎骨和文化遺物發現;褐色土多為混合土,既含有灰綠土,又含有少量木炭、燒土顆粒或碎塊,且含土成分較大,質地較密,而文化遺物發現相對較少。遺物包括銅箭頭、鐵箭鋌、鐵釘和銅錢等,另有部分陶片、石塊和獸骨等。其中以箭頭和箭鋌所見數量最多,如H1內共發現帶鐵鋌銅箭頭68枚,除11枚散置于上部外,另57枚集中出土于現坑口下深0.3~0.45米處,基本為平置,箭頭朝南,鐵鋌居北,為一次棄置或埋藏;H5在距現坑口深1.65米處東北角的灰綠土中出土一捆鐵箭鋌,但卻無一箭頭發現;在H6中也發現少量鐵鋌殘段及鋌長18厘米的三棱形銅箭頭1枚。另以動物碎骨發現較普遍,在H1~H5等坑穴內均有出土,如H2、H4各出2塊,H5共出5段;而陶片和石塊則多為零星發現,僅少量殘片器形可辨,顯然屬填土時無意中擾入;銅錢僅見半枚,圓廓方穿,似為“半兩”,可能也非有意埋藏,但卻說明坑穴的年代應不早于西漢前期。第2組坑穴位于小區東北部13號樓基槽內西段,與第1組呈西南向遙望,相距約118米,坑穴發現于深2米的基槽表面,上部已遭施工破壞,共7座,編號為H7~H13。從整體布局來看,大體可分為南北兩部分、東西三列,3座居北,呈南北向左(西)2右1排列;4座居南,其中3座亦呈左2右1南北向排列,且左列與北右列相對應,唯1座橫排于兩列之左側;相鄰坑穴間距約1米左右,最大間距約3米,僅1座為東西向,余均為南北向,且5座為35°,僅1座為32°。坑穴平面亦呈長方形,多數四壁較直且規整,有的底部不平;現口長1.5~2米、寬0.45~0.85米、殘深0.30~1.50米不等,另加上部破壞部分,實際深度也應在2~3米左右。填土較雜,除灰黑土、黑花土和黃花土外,下部也常見較松軟的綠色或灰白色腐殖土,內含陶片、箭頭、鐵釘、獸骨及石塊、燒土塊和木炭等顆粒。因坑穴上部至少1.5米已被清理破壞,殘存部分多不足1米,故所見遺物相對較少,但在H11下部灰綠土中仍出土銅箭頭5枚,在H12內也發現銅箭頭22枚及少量鐵箭鋌、鐵刀殘段,而銅箭頭半數尖部殘缺;在H7、H10和H12中還分別發現有獸骨,另在H9內底部發現1件殘為兩半的陶鼎,似為殘破后置入。據出土遺物分析,坑穴年代為戰國時期。
2011年6月,在對今百花大街以西、叢臺西路(原嶺南路)北側的邯鄲市社會福利院實施考古勘探發掘時,發現并清理一組坑穴遺跡。坑穴位于綜合樓西部偏北側東西寬8米、南北長9.5米的范圍內,均開口于深約0.5米的表土層下,多直接打入生土,且多數被西漢中前期墓葬打破,計10座,編號K1~K10。從整體布局來看,大體上由西南向東北依1、2、3、4座為次分作4排,略呈等腰三角或扇面形分布排列,排間距0.5~1.3米;各坑穴均呈西南-東北向,且依所居位置北端向外傾斜,南端向內聚合,方向約在25~45°之間,坑間距約1.2~1.5米。坑口平面呈長方形,多口大底小;口長1.3~1.85米、寬0.64~1.1米,底長1.3~1.7米、寬0.6~0.9米,深1.8~3米不等。填土有的分兩層,上層為夾雜白色顆粒的黃色土,土質較硬,下層均為較松軟的含腐殖物成分的灰綠色粉末土。其中7座坑穴內出土有銅箭頭、鐵箭鋌等遺物。如K2在距坑口深約2.1米處發現鐵質箭鋌和木桿朽痕,在深2.6米時發現銅箭頭67枚,在近底部也發現有鐵質箭鋌和木桿痕,另有少量銅箭鋌、銅質兵器及鐵臿1件;K8在深0.7米處偏北側發現箭鋌一堆,在深0.75米處偏南側也發現有箭鋌一堆;K3內出有大量朽爛的鐵質箭鋌,K1填土中有散亂的箭頭和箭鋌,K5、K10等坑穴中也均有零星銅箭頭發現;其他自然遺物可能相對較少或未予記錄,已不得而知。據開口層位、打破關系及出土遺物判定,坑穴的年代應屬戰國時期。
2013年3~4月間,在對今聯紡路南側、鐵西大街西側的錦玉中學建筑工地實施考古勘探發掘時,發現并清理一組坑穴遺跡。坑穴發現于距地表深1.6米的擾土層下,上部已被破壞,個別被西漢早期墓打破,共12座,編號K1~K12。整體布局可分為幾部分,K1~K4在最南側,呈西南東北向直線分布,坑間距0.8~1米;K5~K10居中,略呈側“丁”字形排列,坑間距0.8~2.7米,與南排間距6米;K11、K12居東北兩側,與中部坑穴間距約5~7.5米;坑穴方向分三類,包括南北向3座,東西向3座,西南東北向6座。坑口平面多呈長方形,立面為梯形,口大底小,四壁或兩長壁均存在向內擠壓現象;現口長1.16~1.9米、寬0.46~0.8米,底部長0.88~1.76米、寬0.25~0.8米,殘深0.7~2.2米不等,若上部未經破壞,口部應稍大,實際深度應在2~3.5米左右。坑內填土上部多為花土、下部多為紅粘土及由腐殖物形成的灰綠土等,后者一般分布范圍不均、厚薄不一,多見于坑壁四周,或僅見于底部或底部一端,厚約0.2~0.3米,中部則漸少漸薄,而多為紅粘土;包含物有箭頭、箭鋌及殘碎陶片、瓦片、獸骨等,并以箭頭、箭鋌和獸骨所見數量較多。其中11座坑穴內發現有銅箭頭、鐵箭鋌等,一般1~3枚(枝),K7內箭頭則多達15枚,K2坑底西南側還出土銅矛頭1個。此外,K3、K11填土內還見有個別銅帶鉤、鐵臿等。另在K1、K5、K6、K11等坑穴內還發現有豬骨和雞骨等遺骸。據地層關系及出土遺物判定,坑穴年代為戰國時期。
從上述三個地點4組坑穴遺跡,可以看出以下特點:一是上述坑穴遺跡主要發現于地勢較高的邯鄲城區西北部,也即原趙都大北城或大漢城西北部城郊附近的崗坡地帶,與城垣直線距離僅500~1000米左右,如綠樹林楓小區所見兩組坑穴距建設大街“王郎城”段分別約680~700米,距插箭嶺城垣段約1100米,而福利院和錦玉中學所見兩組坑穴距鐵西大街插箭嶺段城垣均不足500米。二是坑穴多成組出現,少者每組6~7座,多者每組10~12座,以西南東北向或南北向為主,有的甚至很少差別,似經事先規劃及同時開挖而成,且成排或成列分布,具有一定的布局形式,坑或排間距約1米左右,最大不超過3米。三是坑穴多呈長方形,一般口大底小,底部狹窄不平;除個別坑穴較大或較深外,一般坑口長在1~2米、寬在0.5~1米左右,深約2~3米不等。四是坑內堆積層次及土質土色雖不盡統一,但卻普遍發現有似腐殖物形成的質地疏松的灰綠色粉末土堆積,并成為區別與其他遺跡的顯著標志和基本特征。五是填土中除含有多寡不一經擾入的陶片、瓦片或石塊等雜物外,遺物以銅箭頭、鐵箭鋌、帶桿或帶鋌箭鏃及銅矛頭等兵器最常見,且數量最多,表現也最突出;而且動物骨骼遺骸也是部分坑穴較常見的實物遺存之一,其他遺物則相對發現較少。
關于上述坑穴及其用途或性質,因筆者的學識水平及所掌握資料有限,目前尚未查閱到同類遺存發現情況的報道,對其用途或性質更是一無所知;但根據上述坑穴所呈現出的種種特點,筆者懷疑其很可能與某種軍旅或戰事祭祀活動有關,或者說應屬某種與軍旅或戰事相關的祭祀遺跡。
首先,從坑穴的形制結構及布局來看,均為長方形,且成排成列分布,方向基本一至,甚至很少差別,顯然是經過事先規劃專門開挖出來的。那么其是否為灰坑或窖穴等生活遺跡呢?所謂灰坑和窖穴,前者考古上是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用來傾倒垃圾的坑穴,并非專門挖制,一般為廢棄坑穴利用所形成,且多發現于村落或生活區內;后者與現代意義上的窖穴相同,是指為儲藏某種物品而專門開挖的坑穴,上述坑穴雖然為專門挖制,但窖穴一般無需苛求統一的方向和布局,也不會為儲藏些許箭頭等而特意挖制,顯然上述坑穴不屬于此類遺跡。那么其是否為墓葬或陪葬坑呢?如單從形制上來看,似乎與戰漢時期的墓葬非常相似,且周圍常有不同時期的墓葬發現,但與常規墓葬所不同的是上述坑穴多數規模較小,下部較窄及底部不平,明顯不便于人體埋葬,更主要的是所有坑穴內均不具有棺木葬具及人骨遺骸等墓葬的必備條件。可能有人還會考慮到虛冢,即為某此因戰爭或其他特殊原因客死在外的人建立的衣冠冢等,雖然坑穴內常有箭頭等兵器發現,但在邯鄲周圍乃至國內所發現的成千上萬座戰漢時期墓葬中尚未見有關同類現象的報道,而即使確需建立虛冢,也不可能僅僅集中發現于邯鄲西北城郊區區幾個地點;何況在以往所見戰漢墓葬中以兵器隨葬的中小型墓葬并不多見,即使為死者建立虛冢,也不可能僅以數件兵器予以隨葬而不見生活用具等。作為墓葬的陪葬坑,雖然戰漢時期大型王侯墓常有車馬坑或其他陪葬坑發現,但僅存幾枚或數十枚箭頭的陪葬坑卻很少,而中小型墓葬不僅沒有設置陪葬坑的可能,而且在已發現墓葬中也未曾發現過有關先例,更何況有的坑穴周圍并無可陪墓葬之發現,即使有墓葬發現,也多有打破關系,因所處年代不同而與坑穴并不相干。
其次,從坑穴內的堆積和包含物來看,填土內均發現有灰綠土堆積,除含有木炭顆粒、燒土塊、碎陶片、瓦片和石塊等雜物外,還常見豬骨、雞骨等動物骨骼遺骸;出土遺物則以箭頭、箭鋌或銅矛頭等兵器為主,而生活類器物很少。所謂灰綠土,雖未經科學化驗,還不敢確定其究竟屬于什么成分,但其屬于植物等有機物腐爛而形成則毫無疑問。因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遺址中,即發現有成百上千座含有此類灰綠土的坑穴,經相關部門檢測確定其內含有粟和黍的成分,上述坑穴顯然與之相似,所見灰綠土也很可能屬于谷類食物腐爛后所形成,而坑穴內所發現的豬骨、雞骨等動物遺骸也屬于肉類食物,如此眾多的植物和動物食品集中發現于同一區域成組的坑穴內,如非專門用于儲藏供人們食用,其指向自然只能是祭祀的供物或犧牲。因為,古人認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所以,祭祀先祖或神靈是當時最重要的活動之一,而谷物或動物則是供先祖或神靈享用的最主要食品,古代所謂“葛伯仇餉”故事及商周以來所流行的殺牲血祭就是最好的說明。此外,出土遺物中以箭頭等為主,則說明上述祭祀活動很可能與軍旅或征伐戰事有關。
再次,從坑穴分布范圍及所處位置來看,主要發現于邯鄲城區西北部地勢較高的雞毛山周圍,也即趙都邯鄲西北部城郊附近的崗坡地帶,尤其與插箭嶺城垣段相距較近,僅500~1000米左右。眾所周知,邯鄲城區的自然地勢為西高東低,今京廣鐵路沿線以西海拔高度在65米以上,西北部的雞毛山丘陵地帶則可達70~90多米,城區東部的高度卻只有60米左右;而且,戰漢時期東部城區的地勢更低,據考古發現證實至少較現地表低8~10米,因此,城區西北部插箭嶺一帶實屬趙都軍事進攻和防御的戰略要地,也是傳說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改革的練兵場所。所謂插箭嶺是一座長數百米、最寬處達140米、殘高約8米的土丘,經考古工作者證實其實際上是戰國時期大北城西北部城垣的一部分。據清代《邯鄲縣志》載:“插箭嶺,在靈山南,彎環高數丈,多卵石,夏日雨后耕牧時,常獲金鏃(即銅鏃),赤質青斑,非近今物,嶺得名于此。”而且,2002年為配合嶺南路污水管線埋設,曾對插箭嶺南側地下墻址進行過發掘,除發現夯土墻體或壕溝外,還出土鐵鋌銅箭頭上千枚,說明這里可能確實舉行過練兵活動或發生過激烈的戰事,按照古代對“祀與戎”的重視程度及傳統習慣,在插箭嶺以西城郊附近約500~1000米的范圍內,舉行與軍旅或戰事有關的祭祀活動是毫不奇怪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最后,關于坑穴的祭祀屬性或對象問題,目前尚缺乏較確鑿的證據,但筆者推測很可能屬于祃祭遺跡。所謂“祃祭”,有關學者曾進行過專題研究,現摘引如下:“《禮記·王制》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祃于所征之地。’鄭玄注云:‘祃,師祭也,為兵禱,其禮亦亡。’孔穎達疏認為,祃祭是指到了作戰地點以后,祭‘造軍法者’即黃帝或蚩尤,以壯軍威。《春秋公羊傳·莊公八年》云:‘甲午,祠兵。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何言乎祠兵?’何休注:‘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徐彥疏:‘何氏之意,以為祠兵有二義也:一則祠其兵器,二則殺牲享士卒,故曰祠兵矣。’郝懿行《爾雅義疏》曰:‘按《公羊傳·莊公八年》:出曰祠兵,何休注:將出兵必祠于近郊,是祠兵即祃祭,古禮猶未亡也。’”并總結說“先秦時期,祃祭的內容比較寬泛,大致與軍事活動有關,分三種情況:一是四時田獵時立表而祭,也就是田獵中的獻獲之禮;二是在軍隊出征之前,祭祀兵器和初造兵器之人,造兵器之人被稱為‘戰神’或‘軍神’,一般認為是蚩尤和黃帝;三是到了征戰之地舉行的祭祀活動,主要是為了嚴軍法、壯軍威,祭祀的對象是戰神黃帝與蚩尤。祃祭的方式有:殺牲,以牲血涂軍旗和戰鼓等。”①據此可以看出,根據上述坑穴所處位置、年代及所呈現出的特征,無論屬于祃祭中的何種情況都是有可能的。因插箭嶺一帶曾傳為趙武靈王的練兵場所,當然也包括田獵活動,不時舉行獻獲之祃祭自然是順理成章的。同時,插箭嶺一帶也應是戰國時期趙國的軍事基地,軍隊出師前于近郊祠兵或祃祭,祀其兵器及兵器的創始者,并殺牲犒勞士卒,不僅既有文獻可征與史實可據,又是兵禮祀法和激勵將士之必需,而且與上述坑穴以動植物等食物及兵器為顯著特征完全一致。而作為到達征戰之地舉行祭祀活動,雖與趙都近郊發現的坑穴遺跡似乎不符,但也并非毫無可能。如前所述,綠樹林楓第1組坑穴的年代約當西漢前期,而且因受各種條件限制,上述坑穴材料實際均未系統整理,所以各組坑穴的年代尚未完全確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下限當不晚于西漢早期或前期。據文獻記載,公元前154年趙王劉遂曾參與吳楚“七國之亂”,與酈寄等平叛漢軍對峙邯鄲達七月之久,后遭到漢軍引水灌城攻擊,以至城破而自殺②。酈寄等平叛漢軍所引之水自然為城西地勢較高的沁河等,其軍隊駐扎之地自然也應在城西一帶,而插箭嶺附近眾多箭鏃的發現當不排除屬于兩軍對壘激戰時所遺留的可能,當然也不排除酈寄等平叛漢軍到達征戰之地后舉行祃祭,并殺牲釁旗鼓、以壯軍威的可能。如果上述推斷不誤或可以成立的話,那么邯鄲城郊附近的祭祀遺跡則很可能是先秦時期祃祭遺存的首次發現,其重要意義及學術價值是不言而喻的。
四、結語
綜上所述,是目前趙都邯鄲故城考古所取得的最新成果,也是筆者對某些相關問題所獲得的最新認識。盡管某些材料或證據還很不充分,我們的看法也很不成熟,還有待新的考古資料予以證實或修正,但起碼為今后趙都邯鄲故城考古工作提出了亟待解決的問題或任務,也為邯鄲歷史和考古研究提出了新的課題,若能籍此而引起考古及歷史研究工作者對上述問題的重視,并促進相關問題的及早解決,便達到了拙文撰寫的初衷和目的。
(責任編輯:蘇紅霞 校對:李俊丹)
①喬登云、樂慶森:《趙都邯鄲故城考古發現與研究》,《先秦兩漢趙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2003年。喬登云:《試論邯鄲古城的歷史變遷》,《邯鄲學院學報》2010年2期。
②同上注。
①喬登云、王永軍:《趙邯鄲故城大北城東南城角考古新發現》,《邯鄲文物簡訊》(內部資料)2009年第84期。
②本文凡考古勘探發掘資料未注明出處者,均援引自邯鄲市文物保護研究所內部檔案資料。
①段宏振等:《邯鄲趙王城遺址勘察和發掘取得新成果》,《中國文物報》2008年10月22日第二版。
②同注1a。
③段宏振:《趙都邯鄲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
④同注5。
①邯鄲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邯鄲縣志》,中國人事出版社,1993年。
①艾紅玲:《古代祃祭流變考》,《社會科學論壇》2009(6),第95頁。
②《水經注》卷十。
K231
A
1673-2030(2017)01-0022-09
2016-08-15
喬登云(1956—),男,河北武安人,原邯鄲市文物保護研究所所長、研究員,邯鄲學院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