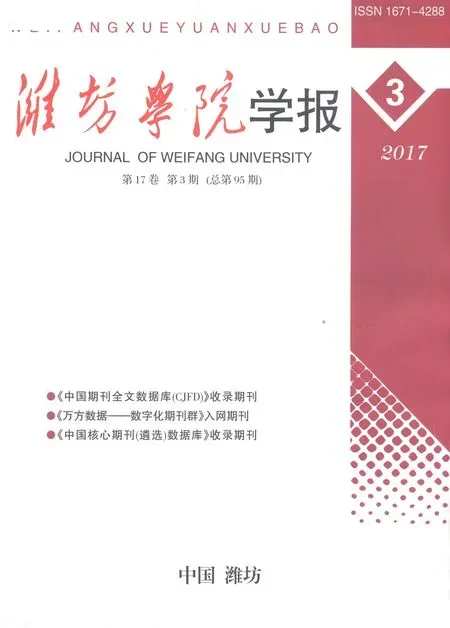論貪污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
臺培森
(濰坊市高新區檢察院,山東 濰坊 261061)
論貪污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
臺培森
(濰坊市高新區檢察院,山東 濰坊 261061)
非法占有目的是貪污罪必備之主觀要素,貪污罪是斷絕的結果犯,非法占有目的是責任要素,不是主觀的超過要素。貪污罪中非法占有目的核心就是永久性的、以所有人身份的占有。無非法占有目的的對向行為不是貪污罪的共犯。貪污罪的行為對象不能等同于非法占有目的的對象,挪用公款以外的其他公共財物造成財物價值轉移、損失較大的,依然可以構成貪污罪。
貪污罪;非法占有目的;據為己有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刑法修正案(九)》的頒布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貪賄解釋》)的實施,我國刑法對貪污罪的入罪數額、方式以及刑罰種類都進行了明確規定,這為司法人員辦理貪污案件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據。但《貪賄解釋》對貪污罪的主觀目的問題依然語焉不詳,這給司法人員懲辦貪污案件帶來了很多困惑和分歧。其中廣受關注和爭議的有,如何理解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的貪污行為,它是否必須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非法占有目的是責任要素還是主觀的超過要素?非法占有目的指向的是財物本身還是財物的價值?公款既然是貨幣,適用“占有既所有”的基本原則,“是否侵犯所有權”怎么可能成為區分貪污公款與挪用公款的標準?挪用公款以外的其他公共財物的行為如何定性?非法占有目的的主體可否包括第三人?所有這些問題都直接影響著貪污罪的認定。對此,司法實踐和學界鮮有人研究,據此,本文試就貪污罪主觀目的的地位、內容等問題略陳管見,以期求教于同仁。
二、非法占有目的是貪污罪必備之主觀要素
我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對貪污罪的規定中沒有明確規定主觀目的要素,這與現行刑法中的絕大多數取得型財產犯相似。但我國曾在其他侵財犯罪中明確規定非法占有目的,如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明確規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雖然該解釋已經被2013年兩高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所取代,但其體現的立法精神卻得到了廣泛認可。目前我國實務界和學界通說對取得型財產犯的定義已經達成一致,即“理論上的通說一直認為,應該以非法占有目的。”[1]問題是,雖涉及財產權,但貪污罪終究在現行刑法中被定性為職務犯罪,作為職務犯罪的貪污罪是否必須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呢?對此,學界一直有人否定侵奪犯的認定需要考慮非法占有目的,認為“刑法并未明文規定非法占有意思的必要,從有利于維護財產秩序的實質出發,可以認為無須將非法占有意思作為主觀要件要素。”[2]為嚴格遵循罪行法定原則,應該否定非法占有目的存在的必要性。筆者認為這種機械的刑法解釋論是不足取的。刑法的解釋、適用必須以體系解釋為方法,以合理性為標準。刑法本身是一個由刑法分則和刑法總則組成的整體,罪刑法定的“法”絕不僅僅是刑法分則,它指的是整個刑法體系。刑法總則具有統攝整個刑法典的作用,它的條文往往具有高度的概況性和指導性,其規定對所有刑法分則和單行刑法都具有指導、制約作用。因此,刑法分則的“犯罪構成雖然具有法定刑,但這絕不意味著任何構成要件要素都必須有刑法的明文規定。”[3]如果認為刑法分則關于貪污罪的規定沒有“非法占有目的”字樣,就斷定其不是構成要件要素,那故意呢?難道可以因為分則沒有規定貪污罪的主觀罪過為故意就認為過失也可以構成貪污罪?這顯然是荒謬的。因此,司法者對刑法分則和單行刑法的每個條文的理解都必須結合刑法總則,而刑法總則的解釋、適用又必須受憲法和社會基本倫理規范的制約。
具體到貪污罪法條的解釋問題上,我們必須結合刑法總則第十四條、第十六條以及分則第三百八十二條的規定來解釋。首先,從犯罪故意的角度來看,刑法第十四條中關于“明知……的結果”、“并且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規定決定了犯罪主觀罪過方面的內容包括故意的“知”與“欲”,犯罪的主觀方面不僅具有認定罪與非罪的功能,更具有區分此罪與彼罪的功能。僅從客觀危害結果而言,我們是無法把貪污罪與挪用公款等非占有型罪名區分開來的,因為巨額的挪用公款行為造成不能歸還的,往往比貪污造成更大的公款損失。但即便是從主觀方面而言,僅僅反映行為人對客觀對象本身“知”和“欲”的一般故意也很難區分二者。比如,在不能歸還的挪用公款罪中,行為人在挪用之前已經對其行為對象有著明確認識,也可能明確認識到了不能歸還的風險,但是他鋌而走險的挪用行為卻不能認為是貪污。換言之,剔除目的之后,無論從認識因素還是從意志因素,區分二者都是困難的。拋開主觀目的要素,一個轉移公共財物占有的客觀行為既可能是貪污行為,也可能是挪用、毀壞甚至暫時性的藏匿等行為。
其次,結合刑法總則第十六條的規定來看,“不是出于故意或過失”不是犯罪,這就是說,認定犯罪必須堅持主客觀相統一原則,行為本身就是主客觀的結合體。我們在理解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中的“侵吞、竊取、騙取”等手段時,必須正確把握背后支配該行為的主觀故意及其要素,“侵吞、竊取、騙取”等行為都是故意支配下實施的客觀構成要件,但“非法占有目的”又是界定這些客觀構成要件不可缺少的主觀要素,因為在缺少目的要素的情況下,這類行為根本就無法得到正確描述,因為“吞”、“取”這些詞本身就包含了“占有”的意思。可見,即使從分則的角度,非法占有目的屬于那種通過對客觀部分要素的描述、結合總則規定就可以明確的要素,根本不需要在分則中明確規定。結合刑法總則確定分則中行為的主觀要素的內容,這本來就是刑法解釋、適用的一項基本原則。
三、貪污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是責任要素而非主觀的超過要素
既然貪污罪的主觀要素中必須包含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那么貪污罪就是目的犯。在貪污罪中,非法占有目的與客觀貪污行為是什么關系?非法占有目的與貪污故意又是什么關系?在犯罪構成中處于什么地位?它是故意的內容,還是獨立于故意之外的主觀要素?這不僅是一個知識論意義上的學術探討,更是一個直接涉及非法占有目的認定的重要問題。因為占有目的,作為一種存在于行為人內心的主觀要素,不可能脫離客觀行為而獨立存在。目的不同于客觀行為,它既缺乏有體性也無法被直接感知。但從存在論角度,目的一定是一種客觀實在,且必須也只能通過一定的行為得以客觀現實化。因此,客觀行為是包括目的在內的所有主要要素的征表,特定主觀目的一定有特定的客觀行為與之對應。但是,在刑法中,我們不可能關注行為人的所有細節,通常而言,只有犯罪構成要件規定的行為內容才是我們需要認真研究、重點認定的要素。如此而言,非法占有目的,是否像貪污的故意一樣,僅以構成要件意義上的客觀貪污行為為征表足以?換句話說,在貪污罪的構成要件之外,是否還需要其他客觀行為來支撐該“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
對非法占有目的的體系地位而言,我國刑法學界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非法占有目的本來可以為故意所包含。”,[4]故而是一種責任要素;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它不是故意的內容,不是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而是故意之外的主觀要素。”,[5]繼而認為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種獨立于故意之外的主觀的超過要素,這是現在學界的通說。筆者認為兩者的觀點都過于絕對化,限于篇幅不做展開,但就貪污罪而言,更贊同前者的觀點,非法占有目的本身是故意的內容,是責任要素而非主觀的超過要素。
1.貪污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結構決定了它可以為故意所包含
從目的犯中目的的實現與行為關系的角度,目的可以分為兩種,一種目的是只要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被實行完畢可以達到;另外一種目的則不然,它不僅要求行為人實施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之后還需借助其他行為才能完成。“德國刑法理論稱前者為斷絕的結果犯,后者為短縮的二行為犯。”[6]我國刑法學者將前者稱為故意之內的目的,將后者稱為故意之外的目的。筆者認為,貪污罪斷絕的結果犯,其目的是故意之內的目的。因為在貪污罪中,轉移公共財物,破壞占有、建立所有的結果本身就是行為人的目的,行為人利用職務之便,侵吞、竊取、騙取等非法占有行為中本身就已經包含了“非法占有”的目的,只要行為人在貪污的故意支配之下完成了上述行為,非法占有的目的自然實現,不需要在此之外實施其他行為。這與短縮的二行為犯有明顯的區別,短縮的二行為犯主觀目的的實現不僅依靠構成要件的行為,更需要構成要件之外的其他行為才能實現。比如,在偽造公司印章罪中,單純以仿造為故意實施的偽造行為不一定構成偽造印章罪,因為行為既可能是出于試驗機器的目的、也可能是出于娛樂或學習等其他目的,只要被刻出的印章不以使用為目的就不可能具有實質的法益侵害性。行為人在偽造的故意的偽造行為之后還必須借助使用行為(構成要件之外的行為)才能實現其目的,而且這種使用目的是需要以前一些行為的結果(印章)為對象,后面的使用行為就超出了構成要件的范圍,這種使用的目的就超出了故意的內容。但貪污罪中,根本不存在如此復雜的行為結構,行為人占有目的的實現也不需要依靠第二個行為,公共財物本身即是故意的對象也是非法占有行為的對象,它不存專以特定目的為指向后續性行為,一個貪污行為就能足夠完成包括非法占有目的在內的全部故意內容,按照大陸法系關于目的犯的認定和分類,貪污罪是目的犯,但屬于斷絕的結果犯,貪污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就是故意的意志因素的一部分。
2.貪污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不是主觀的超過要素
所謂的主觀超過要素是指“在某些犯罪中,主觀要素僅存在于行為人的內心即可,不要求與之相對應的客觀事實。”[7]就短縮的二行為犯而言,主觀目的與構成要件意義的客觀行為之間不存在對應關系,如要實現這一目的,行為人必須借助其他行為,這個“目的”就成了超過客觀行為的目的,而該“目的”所指向的行為當然也就成了構成要件的故意之外的行為,如偽造印章罪中的使用目的和行為。但并非所有的目的都是主觀的超過要素,特別是對斷絕的結果犯而言,因為斷絕的結果犯中包括目的在內的主觀要素都會在構成要件范圍的客觀要素得以對應,根本不存在所謂“超過”一說。就拿貪污罪來看,貪污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就包含在貪污的故意之內,它與貪污罪構成要件的客觀行為是具有對應關系的,因而,它是典型的斷絕的結果犯,貪污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是可以在貪污罪的構成要件行為中得以體現的。那種不加區分的把所有目的都歸入主觀的超過要素的主張,實際上沒有搞清楚兩種目的犯的結構上的區別。因此,貪污罪中的目的只是責任要素,“只有短縮的二行為犯中的目的才是名副其實的主觀超過要素。”[8]在認定貪污罪的過程中,我們一方面不僅要注意一般犯罪故意的證明,更要通過客觀行為確定行為人主觀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另一方面,非法占有目的就體現在“侵吞、竊取、騙取”等貪污公共財物的構成要件行為之中,不必以構成要件之外的行為來證明非法占有目的。
四、貪污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內容
在確定了非法占有目的在犯罪論體系中的地位之后,貪污罪中明確非法占有目的的內涵又成為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對此,我國理論和實務界都提出了諸多觀點,但究其闡釋的內容,“不外系對下列要素的取舍:物之本體、物之價值、排斥所有、獲得所有。”[9]筆者認為貪污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本質就是據為己有,其內部是一種“排除占有——建立所有”的基本結構。
(一)非法占有目的的實質是據為己有
關于財產犯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學界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強調排除意思的權利人意思說,即“以將財物非法轉為自己或者第三者不法所有為目的。”[10]另外一種則是強調所有意思的利用處分意思說,認為“非法占有目的是按照財物本來的用法利用的意思。”[11]筆者認為,排除意思和所有意思是非法占有目的不可分割的兩個面,他們共同組成了非法占有目的,它的實質是據為己有。具體而言,貪污罪中的據為己有包括“永久占有”和“以所有人身份占有”兩層含義。
首先,排除意思是非法占有目的的第一層內容,它的主要機能是將對財產的暫時使用和永久所有區分開來。具體而言,貪污罪中的排除占有是一種永久性占有,是否改變所有權不是貪污罪與挪用公款罪的本質區別,拒不歸還意圖,永久排除其他主體對公共財物的所有權,才是二者的本質區別。傳統的刑法觀念都認為貪污罪與挪用公款罪的本質區別是前者是侵犯了公款的所有權,而后者僅僅侵犯了公款的使用權。但事實并非如此,如果是特定物品,這一理論尚可成立,但就一般等價物(如公款)而言,該理論就難以成立。因為從物權法角度而言,作為貨幣的公款本身就是流通工具,適用民法“占有即所有”的基本原理。這在法學界已經是一個共識、毋庸置疑,“這是由貨幣注重流通的特性、貨幣由國家保障其價值以及方便交易三個方面決定的。”[12]因此,作為貨幣形式存在的公款,占有人就是所有人,不可能出現占有和所有分離的情況。也就是說,無論所有人內心如何,只要他將公款轉移為自己占有,就事實上擁有了該筆資金的所有權,不管是用于消費還是物理持有。那么,如何區分貪污公款和挪用公款罪呢?從排除意思的角度,永久占有是最好的界定標準。因為針對公款的貪污行為是從實質上永久剝奪了國家對公共財物的占有和所有,它不但從物權的角度非法改變了公款的占有和所有,而且其拒不歸還的意思還將國家享有的債權一同消滅,這就是試圖永久性剝奪了國家的財產權。①這里的財產權是包括物權和債權的,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刑法嚴格區分財物和財產性利益,債權是不能被占有的,與之不同,我國刑法對此不加區分,侵財性犯罪的對象既包括物也包括債權。僅從所有權角度是不可能區分貪污行為與挪用行為的,貪污行為的實質對象已經由物權中的所有權擴展到了債權,債權只存在實現問題,不存在占有問題,因為刑法中占有的對象只能是物,債權是不能用占有來說明的。所以,貪污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最核心的內容是拒不歸還的永久占有,拒不歸還的意思才是貪污罪與挪用公款罪的本質區別。
其次,以所有人身份占有是非法占有目的的第二層內容,它的“主要機能是將不值得科處刑罰的盜用、騙用行為排除在犯罪之外。”[13]貪污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必須是據為己有,通說認為財產犯中的非法占有對象包括第三人,如認為非法占有目的是“以將財物非法轉為自己或者第三者不法所有為目的。”,[14]但這種認識是否合理并適用于貪污罪呢?筆者對此持否定態度。現通過一案例說明:
嫌疑人肖某系某市農業委員會技術指導站副站長,負責指導全面工作;嫌疑人陸某系水產養殖戶。2009年至2012年期間,陸某利用該市對高效漁業、循環養殖工程等項目進行財政補貼的優惠政策,編造材料、虛報項目向肖某處申報。肖某為追求所謂“政績”,在明知陸某申報的項目存在問題,可能是虛假的情況下,仍向驗收組人員指示驗收通過,陸某以此騙取農業專項補貼資金共計120萬元。
在該案例中,筆者認為肖某構成玩忽職守罪,而非貪污罪。第一,從構成要件該當性和違法性的角度來看,該行為缺乏貪污罪的客觀行為結果,肖某的行為的確造成了國家財產的重大損失,但他既沒有從該行為獲得財產收益,也沒有利用職務之便非法占有任何公共財物,其行為對象也是唯一收益即所謂“政績”,這根本不符合貪污罪的前提條件;第二,從責任方面看,肖某主觀上不具備貪污罪的主觀故意,他既不存在非法占有這120萬元補貼資金的目的,也沒有貪污的故意,其主觀目的就是追求所謂政績,以此換取自己升遷的資本。雖然他已經發現存在問題,但他對公共財物采取的是漠不關心,聽之任之的態度、這是典型的玩忽職守罪的故意內容,與貪污占有這筆錢的故意有著本質的區別;第三,從犯罪行為形態上看,肖某為了升遷的目的,陸某為了詐騙國家補貼資金的目的,二者既沒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也沒有共同的貪污行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從行為方向上看,一個是詐騙行為的實施者,一個是被詐騙的對象,二者行為具有對向性,沒有共同的利益,沒有共同的犯罪行為,故也不可能成立共同犯罪。因此,肖某應定玩忽職守罪,而陸某則應以詐騙罪定罪處罰。
這個案例進一步說明,貪污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必須是據為己有,這也與貪污行為本身的性質有關,因為國家工作人員在利用職務之便控制公共財物之前,就已經基于其公職取得了對財物“主管、管理、經手”職權,而“主管、管理、經手”本身就是一定程度的“職權占有”,這種職權的背后都涉及“公”、“他”、“己”的處理問題,行為人即使排除國家的“公”的占有之外,“他”和“己”的占有仍是可能利益對立或無關的關系,這與傳統的非“公”即“私”的觀念是完全不同的。當然,這里也必須明確如下三點:其一,據為己有中的“己”必須做廣義的理解,不能狹義的理解為行為人一人所有,這里只是一個行為方向上的概念。根據我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三款的規定,“與前兩款所列人員勾結,伙同貪污的,以共犯論處。”這意味著,貪污罪的共同犯罪人也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出于共同利益而產生了對公共財物共同的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在貪污罪的共犯中,利益共同體的形成決定了任何一個人取得公共財物的占有都可以被視為“據為己有”;其二,必須對共同行為進行對向性分析,區分對向行為和共犯行為。前者而言,各個行為人直接的行為方向相對,所代表的利益具有對向性,這和刑法中的對向犯是一個道理。如上面案例中的肖某和陸某的行為就是一種對向行為,二者在行為對象和利益上都具有對向的特點,不能認定為貪污罪共犯;其三,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規定貪污罪中的“非法占有”應該與第二百七十一條規定的職務侵占罪中的“據為己有”做統一性理解。從法律淵源上看,貪污罪與職務侵占罪都源自我國舊刑法對貪污罪及其補充規定的演化,它們最初都是為了規制職務侵財犯罪而設的規定,除主體和對象的區別外,二者并沒有本質區別,“這里的職務侵占罪,實際就是公司、企業工作人員貪污罪。”這里的財產權是包括物權和債權的,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刑法嚴格區分財物和財產性利益,債權是不能被占有的,與之不同,我國刑法對此不加區分,侵財性犯罪的對象既包括物也包括債權。[15]因此,出于體系解釋的考慮,貪污罪中的非法占有也必須包括據為己有。
(二)非法占有目的指向的對象是物之價值
貪污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行為對象是什么?占有意圖是取得物之本體還是物之價值,或者兼而有之?對此,筆者認為,應該將行為對象與目的對象區分開來。在貪污罪中,本體是公共財物存在的基本載體,是行為的對象,也是判斷占有和所有權轉移的客觀對象,國家工作人員的貪污行為指向的對象只能是物之本體。但目的則不同,目的所指向的對象往往是財物本身的使用、消費價值。從貪污罪的客觀要素來看,公共財物的性質決定了行為的性質,物之本體的性質決定了貪污罪侵犯的法益不是普通的財產權,而是職務廉潔性,所以,貪污罪的客觀行為對象是公共財物。而非法占有目的則不然,行為人實施貪污行為絕不僅僅是為了得到公共財物載體本身,而是為了獲得財物本身所具有的財產性消費價值。這種財產性消費價值又包含兩層含義:第一,這種價值不限于經濟利益,比如國家博物館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侵吞館內珍藏的名字畫,他既可能是為了出售獲得經濟收益,也可能是為了自己欣賞,亦或是為了僅僅滿足自己收藏的欲望,無論哪種都屬貪污罪的目的所指;第二,這種價值指向的是財產本身的“消費價值”,而不是其帶來的“孳息”。比如,在挪用公款罪的情形下,行為人也對公款進行了使用,但是這種使用的目的是為了獲取利息、利潤等“額外收益”,獲取的對象是公款之外的“孳息”而非公款本身,雖然這種“孳息”不一定是財產性利益,甚至不一定是利益,但對公款而言,它卻是被借用的工具,而非消費品,挪用中“用”的目的不在于消耗公款本身。因此,貪污罪的行為對象是公共財物本體,非法占有的目的指向的是公共財物的價值。
這又延伸出一個問題:行為人以獲取物之價值的目的挪用公共財物,導致財物價值大幅貶值的行為如何界定。筆者認為,應該從刑法實質解釋的角度認定為貪污罪,通過如下案例予以說明:
嫌疑人齊某是某國有A公司的總經理,另外他還與其家人經營著B公司,為節省成本,齊某利用職務之便將A公司新購買的設備挪至B公司使用達6年之久,在設備即將報廢前1年,齊某將該設備運回公司,經鑒定,該設備價值200萬元,設計使用壽命為7年,齊某的行為導致A公司因此損失180余萬元。
在該案例中,齊某對設備本身并沒有以所有權人為處分的意思,他的主觀目的屬典型的假公濟私,就是拿公家的設備裝備自己的公司,拿公家出資購買的設備賺自己的錢。該行為造成了嚴重的危害結果,但根據傳統觀點,其定罪卻是個問題。因為:一方面,就齊某的主觀方面而言,行為人實施的是挪用公物的行為,對設備本身不具有非法據為己有的目的,因而,若從物之本體的角度,這種改變占有的行為與挪用行為更為符合;另一方面,就客觀方面而言,行為人挪用的是公物而非公款,而我國刑法并未規定挪用公物罪,根據罪刑法定原則,顯然無法以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
難道齊某無罪?筆者認為齊某構成貪污罪。首先,從實質上理解貪污罪,齊某的行為具備構成要件該當性和違法性。對構成貪污罪的對象之物應做實質理解,物之價值是其本質,物之本體只是載體。齊某利用職務之便轉移財物行為的對象是國有公司的設備,這決定了其行為公權力性,其轉移設備占有的行為注定會侵犯國家財產權和職務的廉潔性。但占有設備的行為并不是其行為的終點,其產生的孳息也不是其目的指向的對象,其目的指向的對象是設備的消費價值,行為人通過使用該設備節省自己的成本,榨取設備的財產價值直至其接近報廢才是行為的結束點。此時,行為的性質已經發生了改變,因為齊某的使用行為導致歸還的設備已接近報廢,與原設備相差甚大,這已經超越了“借雞生蛋”的挪用范疇,行為人移走的是價值200萬的新設備,使用達6年之久,歸還的卻是一部價值不足20萬、接近報廢的舊設備,這種公私之間的“得”與“失”已經呈現出明顯的貪污罪的客觀危害結果。因此,無論從實質上還是從形式上,這種手段都屬于我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規定的與“侵吞”、“竊取”、“騙取”相當的“其他手段”,這種行為本身已經構成針對設備本身消費價值的侵犯,具備貪污罪的構成要件該當性。同時,在沒有違法阻卻事由的前提下,當然應予以違法性評價。
其次,齊某的主觀罪過內容是貪污故意而非挪用的故意。齊某通過其轉移占有的行為所要達到的絕不僅僅是臨時使用的目的,從物之價值的角度,齊某行為的主觀目的是獲得該設備的財產消費價值而非設備本身,其行為就是一種排除占有——建立所有的非法占有模式,其達到的目的效果就是將該公共財物的消費價值據為己有。就是要將公物的使用價值消費殆盡,而非僅僅占有它借用帶來的“孳息”,換言之,這種主觀故意的內容包括了對該設備的消費價值的占有和對使用孳息的占有,它以二者的轉移為最終意志要素的內容,這完全符合非法占有目的的基本特征,對此,作為國有公司負責人,齊某有著明確的認知,他主觀上就是為了對公共財物的消費價值的“侵吞”。因此,其罪過形式應認定為貪污的故意,應該以貪污罪定罪處罰。
當然,這種定性不能絕對化,應對非法占有目的指向的對象本身的價值和損耗的價值做綜合比較。
五、結語
非法占有目的是貪污罪中最具爭議的要件,它不僅是罪與非罪的決定因素,還具有區分此罪與彼罪的重要機能。從法律適用的角度,我們要堅持體系的、合理的解釋方法確定非法占有目的在貪污罪和整個犯罪論體系中的地位,以法的實質精神合理確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內容。從目的犯的角度,貪污罪行為是貪污主觀要件的客觀化,貪污罪是斷絕的結果犯,非法占有目的是貪污故意的內容,貪污罪的客觀要件就是非法占有目的唯一的征表。從非法占有目的的結構上看,貪污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包含“排除意思”和“獲取意思”兩個方面,其核心就是“永久占有”和“以所有人身份占有”兩層含義。應該區分貪污的行為對象和非法占有目的的對象,前者是物之本體,后者是物本身的價值。當然,貪污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涉及問題眾多,由于篇幅和能力所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僅希望以此文能引發大家的思考和關注。
[1]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下編[M].北京:中國法制史出版社,1999:889.
[2][日]木村龜二.刑法學詞典[M].顧肖榮,譯.上海:上海翻譯出版社,1991:684.
[3][13]張明楷.論財產罪的非法占有目的[J].法商研究,2005,(5):71,76.
[4]鄧宇瓊.非法占有目的:犯罪成立體系的比較[J].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2008,(9):60.
[5]張明楷.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160-161.
[6]張明楷.論短縮的二行為犯[J].中國法學,2004,(3).
[7]張明楷.詐騙罪與金融詐騙罪研究[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310.
[8]尹曉靜.財產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之否定——“侵害占有、建立占有”客觀分析之提倡[J].政治與法律,2011,(11).
[9]張小虎.論盜竊罪的非法占有目的要素[J].法學雜志,2014,(12).
[10][14]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506.
[11]劉明祥.刑法中的非法占有目的[J].法學研究,2000,(2).
[12]鄭玉波.民法:物權:修訂 17 版[M].北京:三民書局,2011:540-541.
[15]陳興良.刑法疏議[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7:444.
D924.3
A
1671-4288(2017)03-0051-06
2017-03-11
臺培森(1983-),男,山東諸城人,濰坊市高新區檢察院檢察官,山東大學法學院刑法學博士研究生。
王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