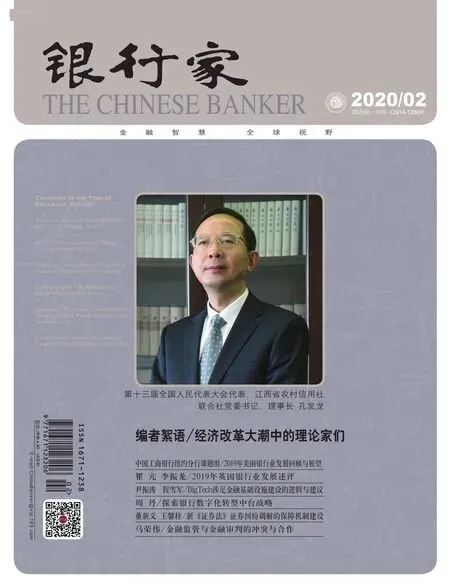中國真的可以藏匯于民嗎?
謝亞軒



編者按:中國居民部門逐步增加持有對外資產已是大勢所趨,不論從理論模型推算還是國際經驗看,藏匯于民所引致的國際資本外流規模都相當可觀。中國能夠在穩匯率、保外儲及藏匯于民這個三難迷局中找到一條中間道路嗎?突破口又將在哪里呢?讓我們拭目以待。
2016年12月31日,外匯局發布《國家外匯管理局有關負責人就改進個人外匯信息申報管理有關問題答記者問》。表面上看,該文主要針對的是個人結售匯特別是購匯的問題,就像有人調侃說是針對“大媽買外匯”。但其背后,更深層次的是如何看待近年來居民部門不斷增加持有對外資產,國際資本持續外流(Capital Outflow)的問題。中國居民部門的對外資產是不是足夠多?居民部門會以怎樣的速度增加持有對外資產?中國的國際資本外流是不是一定要以人民幣匯率的大幅貶值和外匯儲備的顯著消耗為前提?如果不是,該如何既穩匯率,守儲備又能逐步滿足居民部門對外資產配置的需求呢?
居民部門增加對外投資是大勢所趨。在統計上,個人購匯目前計入結售匯經常項目的服務貿易項下,2015年下半年該項目月均逆差規模231億美元,較之2015上半年匯改前月均180億美元的規模增大28%;2016年前11個月月均逆差249億美元,較之匯改前的規模增大31%。該項目逆差規模在匯改后顯著擴大的事實已不能簡單用出境游人數和開支增加等基本面因素來解釋,一部分個人購匯后長期存入外匯賬戶或到境外購買儲蓄型的壽險(而非消費性的比如一些重疾險),這本質上屬于資本和金融賬戶交易,是居民部門增加對外投資,增持對外資產的典型交易類別。而且,中國居民部門對外投資這個大趨勢似乎才剛剛開始。
需要說明的一點是,這里的“居民”是個國際收支概念,對應于“非居民”,包括所有經濟利益在中國的個人和企業,而不是僅僅指個人或者家庭部門。
為何說中國居民部門增加對外投資是大勢所趨呢?一言以蔽之,中國居民部門的對外資產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啦。截至2015年年末,中國私人部門持有的對外資產與GDP的比為25.9%,較之G20國家平均的124.7%低99個百分點,僅僅相當于G20國家20世紀80年代初,即35年前的水平。即使考慮國際儲備資產,中國私人和官方的對外資產總額與GDP之比為57.2%,也僅相當于G20國家20年前,即1996年的水平。鑒于中國仍可能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保持經常項目順差,這就意味著中國作為一個整體仍將不斷增加持有對外資產。2014年之前,對外資產主要由中央銀行以外匯儲備的方式持有,其優點是安全性和流動性高,缺點是收益率低。從目前的趨勢看,對外投資將轉由個人和企業等私人部門完成,其投資的安全性和流動性可能會下降,但收益率可能上升,比如曹德旺先生在美國的投資。
理論估算的中國年均新增國際資本輸出規模將高達6000億~22100億美元。不少研究機構非常重視對于中國私人部門對外投資大趨勢的研究,目前看有兩種比較典型的估算方法。一種方法更多參考其他經濟體的國際經驗來進行估算。比如,加拿大央行2016年10月的一篇工作論文假定,中國的整體對外投資將在20年后追上G20國家2015年的水平,即與GDP之比為125%左右。也就是說,假定每年對外投資規模平均分布,考慮GDP的增速,簡單據此推算,到2020年,中國當年新增對外投資規模就將達到6300億美元。
另外一種方法,分別估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證券投資以及其他投資的規模。比如,當時就職于香港金融管理局的何東先生在2012年完成的《資本賬戶開放對跨境資本雙向流動的影響》工作論文中認為,考慮中國資本項目開放程度、股票市值與GDP之比、M2與GDP之比、外貿與GDP之比、儲蓄率、人均GDP、世界GDP和中美股票投資回報率等一系列變量,到2020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資產存量將達51490億美元,較2015年增加38010億美元,這期間平均每年對外直接投資7602億美元;到2020年中國的對外證券投資資產存量將達54740億美元,較2015年增加42010億美元,年均對外證券投資8402億美元。
何東先生的模型未估算資本和金融項目另外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他投資”變動情況。作者給出的原因是其他投資以銀行存貸款等為主,受短期周期性因素影響大,波動性非常強,無法用上文提及的長期宏觀變量來估算。
中國對外其他投資的簡單估算:微笑曲線分布。筆者無意在此開展關于中國對外“其他投資”決定的學術研究,但希望用一個簡單的描述統計方法來推測未來5年中國對外其他投資的變化。我們觀察到“貨幣和存款”這個部分在整個其他投資資產中的占比穩定在30%左右,而且與“貿易信貸”等其他幾個組成部分之間的相關度非常高。因此,考慮用估算“貨幣和存款”的方法來倒推中國未來的對外其他投資資產。
估算“貨幣和存款”的方法來自一個指標:國內企業和個人外匯存款占本外幣存款總額的比重,它描述的是經濟主體在銀行存款這類資產上的幣種選擇。從圖2可見,2002年至2011年中,由于存在人民幣升值預期和國內外利差等因素,經濟主體在存款資產上優選人民幣資產,外匯存款的比重從最高點的6.8%下降到最低點的2.0%。此后,隨人民幣匯率等因素逐步發生變化,該比重逐步回升至目前的3.1%左右。觀察圖2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推論:一是,外匯存款和本幣存款存在多種共性,比如安全性高,收益率低,與實際經濟交易聯系密切等,因此兩者之間有很強的關聯關系。二是,從時間維度看,由于存在交易需求以及幣值的不確定性,外匯存款與人民幣存款之間會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比重,不會出現劇烈波動。比如,2005~2007年間,就算是存在人民幣升值預期和正利差,經濟主體并不是快速把外匯存款全部兌換為人民幣存款。三是,國內經濟主體的存款資產本外幣幣種選擇并非一成不變,可能受到國內外利差、全球金融市場風險狀況和人民幣匯率預期等因素影響,而在中長期持續保持一個趨勢,比如目前看是一個穩步回升的趨勢。
以上三點決定我們可以利用推算人民幣存款的增速來推測外匯存款增速,或者說經濟主體對外匯存款資產的需求。
假定中國未來的外匯存款在本外幣存款總額中的占比將呈一個穩步上升的趨勢,其分布呈圖2所示的“微笑曲線”走勢。如果人民幣存款按照年均8%的速度增長,則到2020年,中國家庭和企業部門的外匯存款年增量將達到4348億美元,年度對外其他投資資產的增量達9716億美元,對外其他投資資產的存量規模將達到44691億美元(見表1)。
2015年末,我國對外其他投資資產存量規模為14185億美元,5年增加30506億美元,年均增加6100億美元,增速也相當可觀。
如果再加上何東先生估算的年均7602億美元的對外直接投資,8402億美元的對外證券投資,則未來5年中國年均對外投資規模將高達22100億美元。
這個規模相當驚人,一方面,按照這個對外證券投資的速度,中國可以一年半買下澳洲股票市場,四到五年買下整個香港或英國股票市場(當然,這樣的表述只是為了形象化,并不規范,比如證券投資中大部分是對外債券投資等等)。另外一方面,與未來5年中國的年均對外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合計近22100億美元的遠景相比,2015年中國實際對外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的規模僅3886億美元的現實顯得過于“骨感”。
造成中國對外投資現實值與理論估算之間存在巨大反差的三個主要原因:一是,投資的本土偏好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對外投資的積極性。實證和理論均表明,各國居民持有海外資產體現出了不同程度的本土偏好。本土偏好最早由弗朗斯和柏特巴(1991)提出,是指各國股市的海外投資者比例一直很低、投資者更傾向于投資在本土而非海外市場的現象。即使是近年來的金融全球化進程也并沒有很好的推動投資者金融資產的跨國分散化。例如,2007年,美國投資者持有的權益資產中美國資產占比80%以上。造成本土偏好的原因可能有三個:第一個,對沖風險動機(實際匯率風險、收入風險);第二個,交易成本(交易費用、稅收、法律上的國別差異等);第三,信息摩擦和行為上的偏好。各個國家普遍存在的投資本土偏好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中國有QDII、滬港通和深港通等制度安排,但對外證券投資的比重仍然處于低位。
二是,中國對外投資產生的市場“沖擊成本”阻礙投資規模擴張速度。沖擊成本是指在套利交易中需要迅速而且大規模地買進或者賣出證券,未能按照預定價位成交,從而多支付的成本。比如,最近數年,在國際市場上打算標售資產的銀行家都非常希望來自中國的投資者出現,因為他們可能會幫助推高價格。收購價格“水漲船高”還只是問題的一方面,更大的問題來自包括美國、歐元區和澳洲等多個國家對中國投資所采取的高度警惕的態度。比如最新的德國拒絕中資對其芯片制造商愛思強(Aixtron)收購案,又如澳洲希望通過加強對外資的審核以阻止中國國家電網和中國南方電網控股收購澳大利亞最大配電企業Ausgrid等等案例。
三是,中國資本項目可兌換路徑安排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對外證券投資和衍生品投資。中國的決策層一直認為國際證券投資和衍生品投資的波動性大、風險高,因此對于金融市場的“引進來”和“走出去”開放都持比較保守的態度,放在資本項目可兌換隊列的末尾。因此,對比中國和G20國家的對外資產結構可以看到明顯的差異,截至2015年年末,G20國家對外證券投資資產與GDP的比平均達41.4%,是占比最高的對外資產類別,而中國僅為2.4%;G20國家對外衍生品投資資產與GDP的比平均達20.3%,而中國僅為0.03%。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國際儲備資產與GDP的比為31.3%,較之G20平均的18.6%高12.7個百分點。中國國際儲備與GDP的比高于G20的平均水平,而私人部門對外資產的比例低于G20平均水平。這給我們一個不同的角度看待國際儲備的多少和充足率的問題。其實,儲備的充足與否與匯率制度有密切的關系,如果未來人民幣匯率的浮動程度逐步提升,對儲備規模的要求和外匯市場干預的必要程度都將下降。從國際比較看,中國整體的對外資產究竟是更多由國際儲備的方式持有,還是由私人部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外證券投資等方式持有各有利弊。但從外匯市場建設和匯率的市場化和清潔浮動的角度看,似乎私人部門持有更多對外資產的重要性更高。有鑒于此,保匯率還是保儲備這個本來就似是而非的問題的答案應該是不言自明的吧。
可以預見的是,隨著中國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的不斷推進,未來中國對外投資和對外資產的規模將逐步向理論估算規模靠攏,盡管這個進程所需要的時間還相當長。但是,一個問題接踵而至,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年均僅2500億 ~3500億美元,如此大規模的國際資本外流,人民幣匯率將何去何從?
答案在于兩個方面,一方面,需要進一步開放中國的金融市場,通過國際資本流入(Capital Inflow)來平衡國際資本流出;另外一方面要進一步提高人民幣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程度。
對外資產需要對外負債來平衡,資本流出需要資本流入來平衡。同樣觀察G20國家,截至2015年年末,其平均對外負債與GDP的比為143.4%,對外資產與GDP的比為124.7%,對外凈負債與GDP的比為18.7%,其高對外資產存量由高對外負債存量為基礎;中國對外負債與GDP的比為42.5%,對外資產與GDP的比為57.2%,對外凈資產與GDP的比為14.7%。據此,就不難理解為何中國的高層最近一再強調要“積極”利用外資。
通過開放金融市場,吸引國際資本流入以實現國際收支平衡也是中國在2016年全面開放債券市場的政策初衷。根據筆者的研究,參考國際債券市場開放的經驗,估計未來5年境外商業機構有望帶來約4200億美元,年均840億美元的債券國際資本流入。
筆者重點參考2000年代以來,亞洲新興經濟體債券市場國際資本流動三輪周期波動中,債券市場國際資本流動與GDP平均比值的波動情況進行估算。如果假定2016年開始新一輪資本流入周期,國際資本流入6年,流出2年,則未來的5年間中國債券市場將吸引4000億~4400億美元的國際資本流入。2016年9月末,境外投資者在我國債券市場中的占比僅為1.3%,在國債市場中占比也僅為3.7%,遠低于新興經濟體債券市場中外國機構平均10%的占比和國債市場中平均20%的外國機構占比。即使考慮未來的國際資本流入,到2020年,境外機構在中國債券市場中的占比仍不到4%,在國債市場中的占比可能仍不到8%,這個估算規模并不激進,且與6000億~22100億美元的理論估算年均資本外流值相比有如杯水車薪。
有鑒于此,進一步提升人民幣利率和匯率的彈性和市場化程度,充分發揮價格的調節作用顯得尤為迫切。國際貨幣基金在最新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中認為,過去數年新興經濟體的經驗表明,有彈性的匯率的確能夠一定程度上減少國際資本外流的沖擊。展望未來,中國居民部門增加對外投資當然應該“量入為出”,但是這個“量”并非通過事先計劃來確定,而更應該遵從靈活的利率和匯率的指揮棒的指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