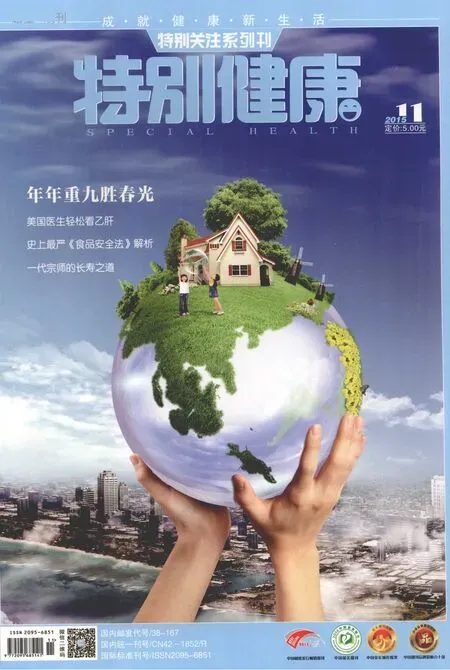圍在一起也不是一家人
◎王露露

在中國,我們習慣了被圍墻包圍。可是在歐美國家,不只普通住宅區是開放的,就連富豪別墅也常常是開放式,不設置任何圍墻。他們的心為何如此之大?
西鄰是個白眼狼
且說有一天,一位好友來我家玩。第二天,我西邊的鄰居敲門找我,讓我朋友賠他的車。他說,我朋友昨天停車沒小心,刮蹭了他的汽車。我答應他,當天下午我就到朋友那兒去問個究竟。若確有此事,我了解那位好友,他一定會辦理賠償手續的。無論如何,我明天早上十點都會帶他去鄰居家洽談此事。
下午,我風風火火地趕到好友那兒,劈頭蓋臉道:“你為啥刮蹭了別人的車卻不言語一聲?搞得我像你的犯罪同伙似的!”他撓了半天腦袋,才嘟囔道,他昨天在我家門口停車時,確實有點不順利,但他真的不知道刮蹭到別人的車了。
當天晚上,我正要洗洗睡呢,兩位警察來了。原來我那位高鄰當天下午竟然帶著證人到警察局報案去了。警察問我,我那好友是否答應賠償損失?我呆了,立馬帶著兩位警察到鄰居家當面對質。我說:“出爾反爾呀,咱們不是說好了,明天早上十點來你家洽談賠償之事嗎?”他躲到警察后邊一聲不吭。
警察走后,我躺在床上睡意全無。我發誓,從今以后,再也不每天下午幫那個鄰居遛他的大黑狗了!在荷蘭,遛一小時的狗五到八歐元,我饒上兔耳朵、羊下水等等給那大黑狗買的零食,免費給鄰居遛了五年的狗,換來了一只披著西裝的白眼狼。
第二天,我帶著好友去白眼狼家填寫賠償表,再次問他:“你干嗎派警察來,狐假虎威地坑我?”他說,他擔心我賴賬。我驚訝道:“咱們是鄰居啊!中國有兩句俗語,遠親不如近鄰,兔子不吃窩邊草,我再想賴賬,也不會拿你開涮呀!”
鄰居的沉默如同無聲的警鐘,把我給敲醒了。是了,鄰居沒錯,是我不識時務。我在荷蘭這么多年,咋還沒看清楚形勢?
東鄰只吃不幫忙
又一天,天剛蒙蒙亮,我的一位荷蘭讀者就帶著她的吉娃娃不請自來了。她非要進屋和我小敘一番不可。她只是讀過我的小說,我們素不相識,所以我沒答應她的要求。這位姑奶奶便和她的狗在我家門口大喊大叫和狂吠亂撲。
我慌了神,跑到東邊的鄰居家求救。鄰居說:“找我干嗎?打112,讓警察來管,這是他們的職責。”我頓時透心涼。這家鄰居沒少得我的好處,只要我包餃子、烙餡餅,回國帶北京稻香村的點心來,都屁顛屁顛地跑去送給他們嘗鮮。
我心里正涼著呢,那位讀者惱羞成怒,開始踹我的門了。我六神無主,只好真的打了112。警察來后,先是檢查那位讀者的身份證,然后與警察總署通電話。總署調出她的檔案查看之后再通知警察,沒發現她有犯罪記錄。于是警察勸她帶著吉娃娃到附近海邊去散散心、消消氣。讀者罵罵咧咧地走后,警察遞給我一張傳單,我定睛一看,傳單上的號碼是受害者咨詢熱線。俺啥時成受害者了?咨哪門子的詢呀?
自工業化起,從農村涌入城市的歐洲貧民,在陌生的環境里舉目無親、孤立無援。按理說,他們應該窮幫窮、親幫親吧,就像過去進城謀生的中國農民那樣。但是不然,正如荷蘭俗語所說:“你管你,我管我,上帝管大家。”在荷蘭等歐洲國家,人與人的正常交流,人幫人,甚至人坑人的行為,早已隨著個人主義的精致化和人際關系的法律化,而淡出歷史舞臺了。鄰居只是一個地理位置概念,沒有任何感情或道德倫理色彩。在我西邊那位鄰居的眼里,我跟路人甲路人乙沒啥區別,都有坑他、拐他、騙他的動機和潛力;至于我東邊那位,我有事希望他幫忙,門兒都沒有。
沒有圍墻有心墻
我的另一家鄰居,本來好好的,可突然女的出軌,男的借酒澆愁,他們的兩個孩子放羊沒人管。女兒今天把頭發染成天藍色,明天往鼻孔里穿個銀環;兒子今天學抽煙,明天踏著滑板車橫沖直撞。我看著心急如焚。其實我很想和他們談談,試圖幫他們一把,但前面那些經歷讓我不敢多管閑事。
后來聽說他們雇傭了“勸架專業戶”——婚姻咨詢調解公司,來盤活他們僵硬的夫妻關系。我覺得蹊蹺,便問一位荷蘭朋友:據說那男的父母大人健在,還有六個兄弟姐妹,女的爹娘就住在附近,為什么不請雙方的家人來調停?荷蘭朋友反問道,他們夫妻倆的事情,跟雙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有半毛錢關系嗎?
感謝這位荷蘭朋友,他無意中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我從祖國帶來的對感激之情的定義需要修改了。我給東邊鄰居送中國餃子和餡餅,給西邊鄰居遛大黑狗,那是我一廂情愿,誰也沒逼著我去做,這跟鄰居在關鍵時刻幫不幫我、坑不坑我,是兩碼事。這里的人很有原則性,一碼是一碼,兩件事不能混為一談。
這些事讓我更清楚地看到荷蘭等許多歐洲國家鄰里關系的異化。法律雖然能保護居民的安全,但如果讓它完全代替鄰居與鄰居、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溝通,就不靠譜了。
在荷蘭等許多歐洲國家,人與人之間有著一道厚厚的“心理圍墻”。“他人即地獄”的思維,鄰里關系的過度法律化,以及人與人關系的異化,導致街區內的居民各自為政,互不干涉,互不幫助。一旦有事,甚至連相互使壞,都常讓第三方——警察等公檢法部門來出面。美國前總統小布什曾呼吁國民“多對話少訴訟”,其原因用腳后跟都能想出來,不是嗎?
歐洲居民小區為何不建圍墻?大家不抱團,缺乏集體認同感,小區四周建圍墻圍誰去呀?當擺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