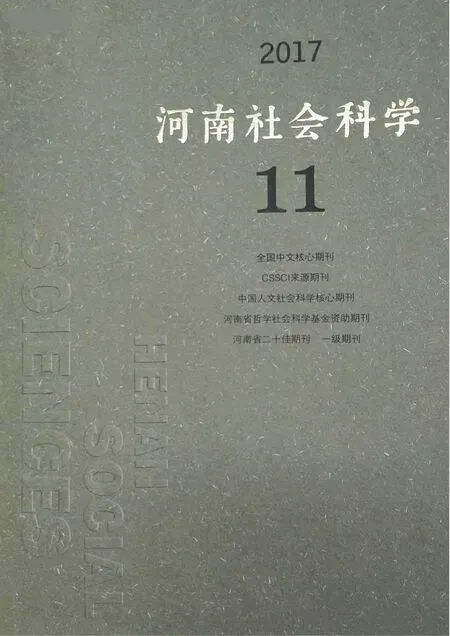社群社會視角下的在線基層治理研究
閔學勤,李少茜
(南京大學 社會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3)
社群社會視角下的在線基層治理研究
閔學勤1,李少茜2
(南京大學 社會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3)
移動互聯時代基層治理受到多方主體的共同推動,正在呈現電子化、在線化趨勢,并有重塑社群社會的傾向。南京市棲霞區的“掌上社區”實踐探索,通過政民共在一個移動社群,并時時互動和積極回應,將政府、市場及社會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在線基層治理架構。同時“掌上社區”所建構的移動社群社會,也為加強社區的參與度和凝聚力提供了強有力的平臺支撐。
在線基層治理;社群社會;移動社群社會
移動互聯技術與人類歷史上前幾次重大技術革命一樣,正在逐漸通過對經濟領域的滲透向社會、文化等領域蔓延,區別在于這次席卷全球的移動互聯技術創新幾乎同步撬動了各領域,并形成了許多混合跨界新概念,例如“社群”。新興社群經濟、網絡社群營銷和虛擬社群互動等糅合了商業、文化及社會理念,將每個移動終端的個體聯結起來,并正在建構包含利益取向并略帶理想色彩的社群社會,而這樣的移動互聯社群社會也正在悄然影響著基層治理。
近年基層幾乎都在摸索如何從管理走向治理,而移動互聯時代的來臨將這一過程進行了壓縮、精煉和再造,來不及過多思索,習慣了自上而下行政思維的基層直接開始了在線基層治理之旅,網絡社群社會的自主創建在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37次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12月,手機網民規模已達6.95億,其中八成在使用微信群、QQ群等移動互聯平臺,這為前所未有的規模化社群互動鋪設了綠色通道。這一自主多點聯結的網絡社群看似可以跨越時空,如果沒有一定的運營資本和情緣關系,多半仍屬陌生社會。而基層社會裹挾了地緣性特征,一旦與移動互聯結合相比其他社群多了一層黏性,也就是說只要基層政府愿意借助移動互聯平臺,即可與民眾相對便利地實現在線傾聽、溝通和協商,并建立常態化的互動關系。從社群社會的視角,這樣的在線政民互動關系是否能確保有效性和可持續性、是否能真正實現在線基層治理非常值得研究。
一、移動互聯網下的社群社會
就一般意義而言,社群指的是由個人組成的社會群體,在這個群體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相當親密,具有一定的凝聚力,而且還存在著某種道德上的義務[1]。社群一直都被學界賦予理想主義色彩,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認為在社群中“人們愿意相互幫助并且接受其他人的指導”,他將社群區分為血緣社群(Communityby Blood)、地域社群(Community of Place)以及精神社群(Community of Spirit)[2]用以對應親屬關系、鄰居關系和友誼或同志關系。英國政治哲學家米勒視野中的理想社群更富情懷,共有七大特征:(1)社群是這樣一種社會團體,在其中每個人都把整個團體的起源和自尊等同于自己的起源和自尊,在社群中我們把自己看作一個更大的有機體的內在組成部分;(2)在社群中我們對其他人的感情就是團結、友愛和親近;(3)團結友愛成為社群全體成員的共識;(4)社群團結的制度體現就是按需分配利益的公共所有制;(5)社群不僅在物質利益分配方面是平等的,而且在社會地位和權力的分配方面也是平等的;(6)在社群內,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將是統一的,人們相互之間沒有特殊的關系;(7)社群存在于社會的各個層次,小到家庭、鄰里,大到社會、國家,它們都是成員的團結合作精神和互助友愛的精神聯結起來的[3]。社群之所以被美化和理想化,既源自個體的社會生活需要,也與個體均渴望在團體中獲得尊重、友善和認同相關,以至于到20世紀80年代,在反對個體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背景下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開始興起,并在哲學、政治學和社會學諸多領域頗成聲勢,影響廣泛[4]。社群主義講求團體優先、公共的善和利益優先,而這些都不是生來就有的,需在社會中養成。當然極端社群主義有時也會依附于社會政治化[5],成為專制的合法邏輯而變得與社群社會建構的初衷相背離。
進入互聯網時代,平地而起的跨時空網絡社群曾一度被冠以虛擬社區或虛擬社群,用以區分于現實的在地性社區,并表達網絡社群的模糊邊界、互動關系的不確定性以及其本質上的弱連帶性。但是,當移動互聯時代來臨時,網絡社群內的互動侵占了個體大部分碎片時間,并直接影響到個體的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它的所謂虛擬性正在被便捷性、高效率及某種意義上的黏合度和依附性所替代。相比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時期的社群,移動互聯網下的社群社會已偏離理想主義軌道,正朝著現實主義的方向演化。
(一)從互相需要到互動共在
人們之所以選擇親疏遠近的社群生活,從本質上看還是互相需要,并因此而成為社會人,但在傳統社會,哪怕是工業社會,這一過程漫長且選擇機會非常有限。而移動互聯社會中是否需要進入陌生社會、是否需要與他者互動幾乎每時每刻都可以選擇,各種免費在線社交平臺確保了每個入口的低門檻和開放性,事實上一旦選擇進入某一網絡社群,與看不見的認識或不認識的他者就已經處于互動共在的狀態。曾有學者質疑這樣的線上互動大量擠占了有效時間,不過也有研究表明被互聯網替代的活動和面對面的互動相比,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例如看電視、打電話、睡覺等。相反,互聯網用戶比其他人表現出了一種更為積極的生活方式,并且和他們的朋友產生更多人際互動,而且使大規模的社區成員群體的溝通變得容易,原先沒有直接聯系的社區成員可以直接接觸[6]。由在線互動而共在的社群與傳統社群相比也有一定程度的階層消融作用,不同階層的群體因某一特定的社會屬性而結群,并在同一個平臺發聲,它對社會的扁平化和再建構有積極的意義。
(二)從團體優先到社群認同
團體優先是社群主義面向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揭竿而起的理由,但團體優先的前提是有足夠的情感基礎或社群認同。網絡社群以松散性著稱,理論上它無法與親緣關系、友緣關系或地緣關系比情感基礎,不過它的自由進出原則決定了它的維系法則必須基于認同,即便是沉默、潛水,只要不選擇退出就有存在的合理性。傳統的社群認同來自權威、規則及利益,網絡社群其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幫助[7],但這樣的外部性并非源源不斷,而且一般而言人們在網絡社群里會謹慎談論共同目標、任務和事業[8],在此情境下網絡社群的認同變得稀缺,認同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也受到挑戰,這也是在網絡社群中圍觀者數量遠超發聲者的原因之一。不過社群走到網絡時代,維系它的基本認同已不再苛刻,它允許多元認同、接受認同的短暫移轉或異化,因為網絡社群對團體的依附正在向個體傾斜。
(三)從個體歸依到自我建構
傳統社群講究個體歸依甚至忠誠,確保社群共同目標的達成,自我的安放和建構成為次選。互聯網社群以各種名目搭建,以各種主題內容來維系運營,且大部分與經濟利益無關,每一個進入者都須遵從內心,在其中的表達也都更富自我的需求,并在“我不是一個人”的空間里互相觀察、效仿、學習,目的是找到歸屬感和認同感。歸屬感依賴社群整體的文化建構,而認同感不僅源于社群里與他者的互動,更與自我在社群中的建構和被認同有關,因此網絡社群更有讓每個個體發現自我、釋放自我、修復自我和創造自我的效用。“所以也有學者認為網絡社群最根本的結構性影響在于它是一個個以個體為中心的社會網絡的集合,每一個個體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來構建自己的社會網絡。而傳統虛擬社區是無中心的,或者只是以少數意見領袖為中心的。”[9]
(四)從理念統一到目標多元
滕尼斯和米勒筆下的社群經常被另一名詞所代替,即共同體。共同體既是物質利益的共享,也是理念的統一和精神的歸依,但是如何實現它,路徑并不明確。網絡社群相對去政治化、去血緣性,它完全因各個自由主體的偏好而起,它并不追求遠大的目標,個體都因不同的目標走到一起,當然這樣的穩定性、持久性就會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因此相比傳統社群的一些天然稟賦和較統一的文化目標,網絡社群的長期互動關系需要系統運營。
二、移動社群社會對在線基層治理的滲透
移動社群社會將建構及維系成本頗高的傳統社群社會電子化、即時化和去時空化,不僅節約了個體及社會的整體耗能,而且因其攜帶著與生俱來的互動共在、自我建構和多元認同等互聯網基因,它對基層社會治理滲透的速度也超乎了想象。以往線下基層治理中最棘手的居民弱參與問題,與網絡空間中的公眾積極參與形成鮮明對照,當基層通過自己的行政末梢——社區——開始有計劃、有準備地吸納轄區內居民參與到微信、QQ等移動互聯平臺中來,“互聯網+”基層治理或曰在線基層治理模式開始被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和民眾嘗試接納時,移動社群社會也被一并帶到了基層治理中。
在線基層治理作為新興治理模式,是移動互聯網、公眾需求和基層政府創新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相比以PC機為終端的互聯網,以手機多功能應用平臺為切入口的移動互聯網率先顛覆了人們的消費模式、支付模式和社交模式,而這些日常剛需行為的在線移轉也開始規模化地刺激到公眾的社區生活、社會生活:既然在線可以與商家溝通并最終形成交易,那么能否在線與物業、社區委交流改善小區環境、治安和停車等問題?以往工作日時間上班族無法參與社區活動,如果與社區共在一個移動互聯社群,是否能在線參加社區活動、在線參與社區協商呢?社群與經濟嫁接所形成的社群經濟正成為新經濟的一種形態,那么在線社群社會、移動社群社會為什么不能在身邊興起?這些需求和追問既是倒逼基層政府,也成為基層政府治理創新的原動力,更何況來自頂層設計中的信息政府、電子政府和智慧政府等理念一直在不斷下沉實踐中。例如上海市黃浦區打浦街道推出以智能手機為載體,建立街道事務處理中心、周圍商圈、社區內居民三方互動信息交流平臺的“IN標簽”[10];成都等地借助微信、微博等微平臺開展的基層“微治理”[11];杭州市上城區在社區建設中構建“二化四網六平臺”[12];深圳市羅湖區創建移動“家園網”[13]等。它們都試圖打造線上各基層組織聚合的社群,回應公眾對基層治理的在線需求,并打通電子政務的最后一公里。相比之下,作為民政部第三批社會治理創新實驗區的南京市棲霞區,正在探索實踐的“掌上社區”在線治理模式,從一開始便植入移動互聯基因,圍繞從線下陌生社會走向線上熟人社會的目標,經過近一年的運行,移動社群下的在線治理正初顯成果。
地處南京城郊接合部的棲霞區,坐擁“六朝勝跡”棲霞山和人文薈萃的仙林大學城,下轄390.52平方公里,其九個街道119個社區幾乎包含商品房小區、單位小區、經濟適用房小區、保障房小區、小產權房小區和村改居小區等各種類型,常住人口中也融入了原住民、新移民和大量流動人口。不過與其他城區不一樣的是,由于各類小區情況復雜,棲霞區政府一直以“物業托底”,即對無物業或物業較差的小區輸出物業管理作為一項基本施政方針,使得被視為基層政府末梢的社區委一直保持過半以上的聲望[14],因此一旦社區吹響在線建群的集結號,響應者、追隨者來自各個階層,并很快形成在線治理的初期場景。
(一)從地緣在線社群到社區在線治理
同樣是微信建群,社區因有地緣優勢,入群的居民會自然有在地感、親近感,加之每天聊的都是身邊事、社區事,所以棲霞以社區居委會為群主,以微信群為平臺搭建的“掌上社區”從2016年年底剛興起便獲得諸多響應,截至2017年5月,像馬群街道的“芝嘉花園掌上社區”“美麗寧康掌上社區”、西崗街道“晶都家園”“仙林湖片區掌上通”、八卦洲街道的“八卦花園社區居民交流群”“東江村交流群”等近500人群每天的有效活躍信息數均超過300條,從物業維修、社區治安、社區環境、養老到停車問題、寵物問題和違建問題等。只要涉及社區民生,就會有無數跟帖和響應,以往社區需要走訪才能了解的民情民愿、需要座談才能協商的問題、需要多次通知才能傳達的信息在線幾乎都可覆蓋。社區從擔心共在一個群可能會有各種不良信息或不當言論,到最先棲霞26個試點“掌上社區”的三個月良性試運行后,全區119個社區全部跟進就近搭建了基于地緣的“掌上社區”,開啟居民、社區、物業、駐區單位和社區組織共在的在線治理之旅。
(二)移動社群正改變社區弱參與
社區弱參與一直是困擾基層治理的關鍵問題之一,其中社區中青年群體沒有時間、沒有興趣參與是主要原因。與此相反的是棲霞“掌上社區”最先吸引的恰恰是熟練使用智能手機的中青年群體,他們無意中發現可以掃二維碼進社區群,便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加入,進群后發現都是不曾謀面的街坊鄰居,每天聊的都是那些自己原本有意關心卻無時間過問的社區公共事務,一下子他們的“社會人”身份就被激發:“小區樓道里堆滿了雜物,不知物業或社區能否來清理下”“小區安裝電梯的政策文件可否在群中再發布一下?我們單元有幾戶常年沒人,是否需要我們共擔他們的費用”“有領導在嗎?我們小區的停車位劃分能否參照一下隔壁小區”“還有社區漫談會一說,為什么沒有早點通知我們”“我今天在小區門口菜場買五花肉,靠拐角的那個攤主居然一轉身換了一堆下腳料給我,你們千萬別再去他攤位上買肉啊”……無論是工作日還是休息日,類似這樣的社區關心、網上參與幾乎隨時都在,作為群主的社區工作人員也沒有想到“掌上社區”創建的移動社群就像打開的閘門,居民們在工作場所或家中任意點擊表達即可加入社區大家庭,以往線下被社區老年積極分子包裹的場景,在“掌上社區”中正被越來越多的中青年群體取代,而這一群體對社區的理解和視角更容易擊中社區問題的要害:“老實說以往社區哪里亂哪里不干凈,我們社區工作人員可以睜一眼閉一眼,現在居民在群里一張圖,幾個字,再@一下你,不得不回應。”從弱參與到廣泛參與,“掌上社區”對社區委的挑戰也正從根本上改變基層治理的固有結構。
(三)社區的快速有效回應激發社群認同
在線下基層治理中,大多數情形下社區只能服務到弱勢群體,社區當然需要積極回應他們的訴求,但他們并不要求“速回”“秒回”,而線上不同,“掌上社區”里每天等待回復的訴求不下十條,有時更多,如果社區漠視或慢回就可能引發不滿,畢竟塔西陀陷阱一旦形成,短時間內就很難消解。“咱們群里是不是有律師呀,有些事情想咨詢”“好幾個律師,你到群成員里搜”“你是律師嗎?”“我不是,我是群主,我幫你搜一下,稍等,群里就有四位”“收到,謝謝!”類似這樣的快速有效回應在棲霞“掌上社區”的前十大優質運營群里幾乎每天都會出現多次,隨著時間和事件的累積,社群認同進而對社區的認同即會自然孕育。其實居民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掌上社區”,最起初的想法都是“哇,這里有這么多我們小區的人啊”,慢慢才發現群主是社區工作者,不是物業工作人員也不是業主,無論以往線下對社區如何認知,線上仍是新的生態圈,所有的認同還需重新建構,而積極有效地快速回應群中大小事件,幾乎是獲得初級社群認同的敲門磚。“領導,這輛貨車占據小區停車位好幾天了,能不能管管”“我們社區規模大,能不能搞個相親聯誼活動”“小區前面的公交線路還是多少年前的老線路,城市變化這么大,能不能和公交公司談談重新設計下線路啊”。每天這樣的訴求瑣碎平凡,單靠社區一方回應,如果沒有形成多方聯動,社區也會不堪重負。
(四)良性的社群互動培育社區共治
傳統的社群關系由于團體優先、目標統一,社群中的個體很容易被淹沒。“掌上社區”中即便有群規,一般個體只要好好說話,發言幾乎不會受限,那么一旦信息呈現,群中的互動全憑群內日常養成的氛圍:“我們小區打籃球去哪里?百水芊城派出所嗎?”“還可以去中山學院,我每周都去。派出所那個球場人太多”;“咱們這誰家出租房子啊?精裝修的那種,干干凈凈的”“是的,我這里有房子出租”;“我剛才出門有事,一開門一只狗對著我亂跳狂叫,嚇死我了。養了小狗在門口,既影響環境,也打擾別人休息,門口衛生很不干凈”。五分鐘過后,有群內居民回復,“三種辦法:(1)上門友好協商,此為上策;(2)找物業,讓物業清理公共空間的衛生。此為中策;(3)實為無奈之舉:打110要求警察按照犬類管理規定進行處理”。事主回復“感謝您的好點子,我現在已經把事情告訴業主了,請他協調解決,這房子是一幫女孩子租的,謝謝您”。就運行大半年的“掌上社區”而言,群中這樣的互動非常常見,沉浸其中的居民可能沒有意識到實際上他們已經在參與社區共治,而社區若能發現或有意識地培養那些積極良性互動的居民成為社區精英,社區既可借力亦可獲得更多社區資本,為制度層面的社區共治奠定基礎。
三、在線基層治理重塑社群社會
如果說基層治理的創新有相當多來源于頂層設計或上級政府的行政需求的話,那么基層治理的在線化趨勢更多發端于自下而上的涌動,這里的“下”包括百姓對基層政府的電子化、在線化需求,也包括基層政府本身接地氣。移動互聯網時代與百姓溝通繞不開免費的社交平臺,為了提升治理效度和到達率,他們自主需要建構電子社群、移動社群來應對基層社會的發展,并由此形成的各類創新實踐逐漸影響到他們的上線政府。
像南京棲霞區這一“掌上社區”在線基層治理形式,看似基層政府與百姓可以每天“不見面”互動,互相增進了解,互相磨合成長,其實本質上是一個基于地緣、鄰緣的移動社群社會的萌發,并且是對傳統意義上的時間成本、情感成本及行動成本頗高的社群社會的重塑。首先,這里的“重塑”涵蓋對社群社會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的重新定義,從線下關系相對固著、理念相對統一和團體相對忠誠的傳統社群社會到線上互動扁平頻繁、認同多元豐富和隨時切換更迭的移動社群社會,這一跨越更貼近人性之日常,由此更易激活社會中的每一分子。其次,這一“重塑”裹挾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共在一個場域,他們每天為社區日常對話,喜百姓之喜,憂百姓之憂,即便有爭吵、有懷疑,也不乏群里的冷嘲熱諷,不過到哪里能找到三者無時無刻的社群共在?假以時日,若各自學會了有序、寬容地互相面對,那么所謂“大政府”向“強政府”轉型、“小社會”向“強社會”過渡也未嘗不可期待;再者,“重塑”的社群社會若能被悉心維護,它對后單位下每個個體的在地心靈歸屬,對社區多年期盼的強參與和凝聚力都是極大的平臺支撐,更何況在線社群可以通往線下,并與線下融合形成立體的社群社會,為各個階層、各年齡群體都營建一個充滿能動性和關懷度的新興場域。
當然,無論是在線基層治理也行,還是移動社群社會建構也好,都還只是剛剛勃興,所有的參與者都還未完全準備好,也沒有通達平順的路徑可循,各社會主體在其中的角色扮演也都邊界模糊、切換頻繁,但是由技術變遷引發的社會變遷清晰可見,社會生活、特別是社區生活的在線移轉與基層政府的治理創新一起正在建構一個不可估量、極具想象的社群。
[1]Robert Nisbet,The Social Philosophers:Communityand Conflict in Western Thought[M].New York:ThomasY.Crowell Company,1973,1.
[2]Ferdinand T?nnies,Community and Civil Society[M],edited by Jose Harris,translated by Jose Harris and MargaretHolli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26—27.
[3]俞可平.社群主義[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78-80.
[4]成伯清.社會建設的情感維度:從社群主義的觀點看[J].南京社會科學,2011,(1):70—76.
[5]Sandermann,P.The Transnational Social Politicization of Communitarianism in Germany.[J].Transnational Social Review.2014,4(1):73—88.
[6]Barry Wellman.Computer Networks as Social Networks.[J].Science,2001,293(5537):2031—2034.
[7]張文宏.網絡社群的組織特征及其社會影響[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1,(4):68—73.
[8]Pape,B.,Reinecke,L.,Rohde,M.,Strauss,M.E-Community-Building in WiInf-Central.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ssociation of Computing Machinery acm,8-12 Jan.,2003,Florida,USA.
[9]彭蘭.從社區到社會網絡:一種互聯網研究視野與方法的拓展[J].國際新界,2009,(5):87—92.
[10]朱琳,劉曉靜.基于移動互聯網的智慧社區服務公眾采納實證研究:以打浦橋街道“IN標簽”為例[J].電子政務,2014,(8):27—37.
[11]郭祎.成都基層微治理的探索及完善建議[J].中國國情國力,2016,(12):33—35.
[12]汪錦軍.城市“智慧治理”:信息技術、政府職能與社會治理的整合機制——以杭州市上城區的城市治理創新為例[J].觀察與思考,2014,(7):50—54.
[13]張志安,范華,劉瑩.新媒體的社區融合和公民參與式治理:以深圳市羅湖社區家園網為例[J].社會治理,2015,(3):111—119.
[14]閔學勤,賀海蓉.掌上社區:在線社會治理的可能及其可為[J].江蘇社會科學,2017,(3):16—22.
Online Grassroots Governance:A Perspective of Communitarian Society
Min Xueqin,Li Shaoqian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jointly propelled by various subjects in the era of mobile Internet,is gradually being electronized and realized online,which tends to reshape the communitarian society.Mobile Community explored by Qixia District of Nanjing has formed a new framework for online grassroots governance.It integrates government,market,and society through their constant interaction and active responses in the mobile communitarian wherethe governmentand the peoplecoexisttogether.Besides,thismobile communitarian established by the mobile community has provided a powerful platform for strong degree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cohesion.
Online Grassroots Governance;Communitarian Society;Mobile Communitarian Society
C91
A
1007-905X(2017)11-0114-05
2017-06-16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7BSH035);南京大學文科雙重項目(010914902122)
1.閔學勤,女,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主要從事城市社會學、公共社會學研究;2.李少茜,女,南京大學社會學院,主要從事城市社會學研究。
編輯 張志強 張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