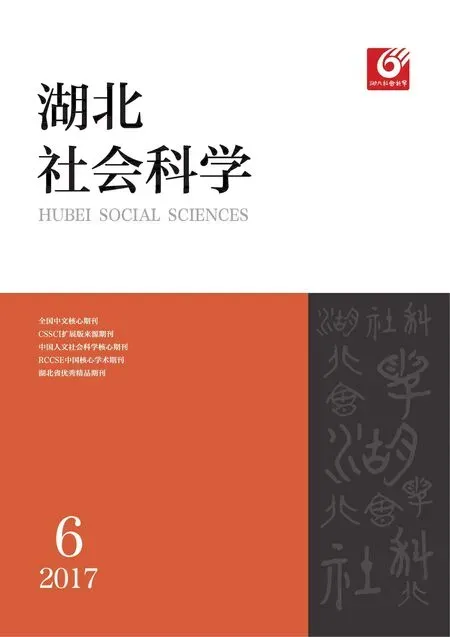是的,歷史就是被制度決定的
——答孫、樊二位先生的商榷
韓東屏
(華中科技大學(xué) 哲學(xué)系,湖北 武漢 430074)
·人文視野·歷史·文化
是的,歷史就是被制度決定的
——答孫、樊二位先生的商榷
韓東屏
(華中科技大學(xué) 哲學(xué)系,湖北 武漢 430074)
《歷史是被什么決定的》一文提出歷史決定論之后,很快引來一些文章的質(zhì)疑。其中的質(zhì)疑焦點(diǎn),主要集中在方法論、制度化社會(huì)賞罰與人們活動(dòng)的關(guān)系、制度與生產(chǎn)力的關(guān)系和制度的來源這四個(gè)方面。盡管這些批判性的質(zhì)疑都有自己的理據(jù),但經(jīng)逐一分析后,還都不能對(duì)我的這套觀點(diǎn)形成有效威脅。不僅如此,它們還等于又從反面幫我證明了:歷史就是被制度決定的。
制度;歷史;制度決定論;制度化社會(huì)賞罰;生產(chǎn)力;制度安排者
我的文章《歷史是被什么決定的》,由于提出了一套不同的新歷史觀,在上海的《社會(huì)科學(xué)報(bào)》公開發(fā)表后,①參見韓東屏:《歷史是被什么決定的》,《社會(huì)科學(xué)報(bào)》2017年2月23日。很快引來了一些質(zhì)疑文章。它們分別是孫力先生的《歷史是被制度決定的嗎》②參見孫力:《歷史是被制度決定的嗎》,《社會(huì)科學(xué)報(bào)》2017年3月9日。《唯物史觀真的終結(jié)了真理》③參見孫力:《唯物史觀真的終結(jié)了真理?》,《社會(huì)科學(xué)報(bào)》2017年4月30日。和樊衛(wèi)國先生的《歷史的走向由“合力”來決定》。④參見樊衛(wèi)國:《歷史的走向由“合力”來決定》,《社會(huì)科學(xué)報(bào)》2017年3月23日。
能有這樣的結(jié)果,是我期待并歡迎的。一來一套新理論是否真有道理,不能自以為是,還應(yīng)接受學(xué)界同仁的批判性審視;二來正如學(xué)界老話所言:理是越辯越明。因此,我要為之感謝孫、樊二位先生。
然而,若從這三篇文章立論的理路、理據(jù)來說,還不能對(duì)我的這套觀點(diǎn)形成有效威脅。其中道理,分四個(gè)論題來說。
一、方法論的問題
孫先生對(duì)我的文章的質(zhì)疑和批判,首先是方法論方面的。但實(shí)際上,正是他自己的思維方法存在問題。
我的這套理論可謂“制度決定歷史”的制度決定論,它本來就不是運(yùn)用通常理解的唯物史觀的原理和方法得出的,而是以馬克思的“歷史不過是有著自己目的的人們的活動(dòng)而已”這一正確且得到學(xué)界公認(rèn)的觀點(diǎn)為大前提,再通過論證兩個(gè)事實(shí),即“人是懷賞畏罰的理性自利人”和“制度具有最強(qiáng)的社會(huì)賞罰功能”,然后將這二者結(jié)合起來思考推論出的。在這種情況下,孫先生仍然用這是“把制度說成是‘社會(huì)的決定因素’、‘決定歷史的走向’,不是唯物史觀”之類的話語來進(jìn)行責(zé)難,就沒有什么意義了,甚或只有消極意義。因?yàn)樗蛘咭馕秾?duì)社會(huì)歷史問題的研究和論述,只能用過往理解的唯物史觀的理論和方法;或者意味凡是過往用唯物史觀已有結(jié)論的問題都不容再加討論;或者意味只要是后發(fā)理論,均不如在先的理論。
孫先生對(duì)我人性觀的質(zhì)疑也有方法不當(dāng)?shù)膯栴},他避而不談我關(guān)于“人是懷賞畏罰的理性自利人”的人性判斷是否符合事實(shí),只是單純指責(zé)它屬于抽象的人性論,“不是科學(xué)的歷史觀”。“因?yàn)槿诵圆皇瞧桨谉o故產(chǎn)生的,社會(huì)存在決定社會(huì)意識(shí)。唯物史觀的深刻之處就在于它揭示了人性背后的社會(huì)存在。”
在我國學(xué)術(shù)界,一直以來有一個(gè)不好的傾向,就是所有概括一般情況的普遍性命題,都可以被輕易通過扣上“抽象”的罪名而絞殺。不錯(cuò),具體的人是生活在具體的社會(huì)之中,可這就會(huì)使他們沒有一般的人性或共同的人性嗎?而我關(guān)于“人是懷賞畏罰的理性自利人”的人性判斷,又會(huì)在不同的社會(huì)及社會(huì)存在中發(fā)生任何實(shí)質(zhì)性變化嗎?想必沒有任何一個(gè)人能找到任何一個(gè)這樣的反例。
唯物辯證法的一個(gè)基本觀點(diǎn),就是“具體”和“一般”相互依存,“特殊”和“普遍”相互依存,可怎么到了人性這里就不管用了?何況,當(dāng)馬克思說“人的類特性,恰恰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dòng)”[1](p96)、“人的本質(zhì)并不是單個(gè)人的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xiàn)實(shí)性上,它是一切社會(huì)關(guān)系的總和”[2](p56)時(shí),難道說的不是人人皆有的一般人性嗎?其實(shí),它們也是馬克思通過抽象而來,只不過是通過理論抽象,而不是通過歸納抽象即簡單的經(jīng)驗(yàn)總結(jié)而已。而我的文章既然是論述整個(gè)人類歷史的一般情況,而不是某個(gè)歷史階段的具體情況,又怎么不能用理論抽象的方法和人人皆有的一般人性說事?至于人們共有的這種懷賞畏罰的自利性,會(huì)在某個(gè)特定社會(huì)歷史時(shí)期又有哪些特殊的表現(xiàn),則已不是談?wù)摎v史一般情況所必須討論的問題。
二、制度化社會(huì)賞罰與人們活動(dòng)的關(guān)系問題
樊先生質(zhì)疑我關(guān)于制度化社會(huì)賞罰通過決定人們的活動(dòng)也就決定歷史的觀點(diǎn),認(rèn)為我“放大了制度的賞罰功能,并做了簡單的推導(dǎo)”,還為之提供了若干理據(jù)。
樊先生之所以會(huì)做出這樣的論斷也難免,因?yàn)槲疫@篇文章其實(shí)只是一個(gè)用于報(bào)紙推介學(xué)術(shù)研究動(dòng)態(tài)的縮略版,原文題為《制度決定歷史》,有一萬五千多字。①參見韓東屏:《制度決定歷史》,《南國學(xué)刊》2016年第1期,人大報(bào)刊復(fù)印資料《哲學(xué)原理》2016年第5期全文轉(zhuǎn)載。如果他看了我的原文,知道了我說的制度化社會(huì)賞罰機(jī)制,既包括表現(xiàn)為顯性賞罰的法律性賞罰和行政性賞罰,也包括表現(xiàn)為隱性賞罰的體制性賞罰,知道了制度化社會(huì)賞罰即便是失靈無效的,也照樣對(duì)人們的活動(dòng)具有塑導(dǎo)作用,只不過是異類的塑導(dǎo)作用,他也許就不會(huì)再把“賞罰機(jī)制主要是處罰機(jī)制”、“制度的賞罰主要針對(duì)極端事件、個(gè)別事情”、“賞罰機(jī)制難以規(guī)制人們的基本社會(huì)活動(dòng)”、“一個(gè)制度能否真正地得以貫徹執(zhí)行,主要在于……是否合理有效”這些說辭,還當(dāng)作其立論的理據(jù)了。
而其他那些或許仍會(huì)被他繼續(xù)堅(jiān)持的批判理據(jù)也難生實(shí)效。
一是說“制度的賞罰均有相當(dāng)?shù)膱?zhí)行成本,其執(zhí)行的力度和廣度與執(zhí)行者的能力、財(cái)力相關(guān)……其功能和績效不可無限放大。”這個(gè)說法本身有一定道理。但問題是,人類歷史上,有沒有沒有制度的社會(huì)?而人類社會(huì)中,有沒有一個(gè)社會(huì)曾對(duì)人的某一類實(shí)踐活動(dòng),即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政治活動(dòng)、文化活動(dòng)和民生活動(dòng)中的某一種活動(dòng),沒有任何制度的規(guī)定?回答自然都是否定的。既然如此,我的制度決定歷史的走勢走向,也就是制度決定人們活動(dòng)的方式方向的觀點(diǎn),就不會(huì)受社會(huì)制度成本高低的影響。換言之,一個(gè)社會(huì)的制度的成本不論是高還是低,全都能無一例外地決定歷史的走勢走向。
二是說“如果一個(gè)制度影響人的正常的生存、生活,那么這個(gè)制度即使有再強(qiáng)的賞罰功能,也不能規(guī)制和阻止人的生存活動(dòng)。”首先,這句話中的“規(guī)制”一詞就用錯(cuò)了。有史以來,人們的生存生活有過沒有被制度所規(guī)制的時(shí)候嗎?顯然是沒有的。當(dāng)然,說“不能阻止”還可以,但歷史上有誰制定過阻止人們生存生活的制度呢?顯然也是沒有的。退一步講,如果真有,也就是“苛政猛于虎”之類,可它豈不仍是制度?如上所說,這樣的制度同樣對(duì)人們的活動(dòng)有塑導(dǎo)作用,這就是:或是逼民逃離,或是逼民造反。
三是說“制度不能覆蓋人的所有活動(dòng)”。這話有一定道理,但“法無禁止即可為”,因而人們的自由活動(dòng)權(quán)利及其范圍其實(shí)也是由制度規(guī)定的。這就表明,人們的活動(dòng)又沒有制度所覆蓋不到的。加之人們自由活動(dòng)的領(lǐng)域,通常也會(huì)有廣義利益分配制度即體制性社會(huì)賞罰機(jī)制的“游戲規(guī)則”在其中實(shí)行隱性賞罰,如市場經(jīng)濟(jì)就獎(jiǎng)勵(lì)競爭不獎(jiǎng)勵(lì)保守、房地產(chǎn)財(cái)政就鼓勵(lì)炒房不鼓勵(lì)實(shí)業(yè)。是故,人們在這里的活動(dòng)還是會(huì)被制度塑導(dǎo)。
四是說制度不是人們活動(dòng)的唯一約束條件,與利益、理念或價(jià)值觀念這兩種約束條件相比,并不是更具有決定性。然而,制度在本質(zhì)上豈不就是一種關(guān)乎權(quán)利與義務(wù)的利益分配規(guī)則?而制度的賞罰,豈不就是對(duì)各種利益的給予與剝奪?至于理念或價(jià)值觀念,由于基本上沒有任何事關(guān)利益的賞罰功能,所以即便本身是有某種導(dǎo)向功能,也完全不可與掌握了多種賞罰之物的制度導(dǎo)向相匹敵。例如,盡管我國前此實(shí)施多年的計(jì)劃生育國策與人們的傳統(tǒng)價(jià)值觀念存在嚴(yán)重沖突,可在賞罰兩手并用的舉措之下,還不是起到了大幅降低出生人口的效果?
五是說“歷史的走向是合力作用的結(jié)果,而合力取決于總體力量的對(duì)比,而非人數(shù)的多寡。”但合力究竟是指什么,樊先生沒有明確說。如果是指恩格斯提出的由無數(shù)個(gè)人活動(dòng)構(gòu)成的合力,那它怎么會(huì)不取決于“人數(shù)的多寡”?如果是指樊先生認(rèn)定的制度、利益、理念或價(jià)值觀念,那上面已有分析,制度本身就是利益分配,其力量遠(yuǎn)勝理念或價(jià)值觀念萬倍。何況,一種或一套制度一旦實(shí)施開始起作用,遲早也會(huì)成為人們不得不接受的理念或價(jià)值觀念,如“計(jì)劃生育好”的觀念就是如此。
于是可知,對(duì)人們的活動(dòng)即歷史起決定作用的還是制度。
饒有趣味的是,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甚至樊先生自己有時(shí)也在不自覺地為之提供證明。其文在與孫先生商榷生產(chǎn)力的最終作用的那個(gè)部分,用西方工業(yè)革命和新型市場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的形成說事,盡管先說這是經(jīng)濟(jì)、政治、科技等“各項(xiàng)因素綜合的結(jié)果”。可在最后時(shí)刻,他還是自己也承認(rèn)了“這里制度更具決定性”。
三、制度與生產(chǎn)力的關(guān)系問題
孫先生側(cè)重反對(duì)我的“制度決定歷史”的立論,基本理由是“制度受制于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界限”。所以,他在反駁我的人類歷史“只能是人為選擇史的過程,即制度安排者選擇制定什么樣的制度,大眾就選擇按這種制度的導(dǎo)向行動(dòng)的過程”的觀點(diǎn)時(shí)說:“任何人的制度設(shè)計(jì)都不可能是隨心所欲的,商鞅變法能夠設(shè)計(jì)出現(xiàn)代民主制度、政黨制度、市場交易制度嗎?在制度設(shè)計(jì)背后起決定作用的是其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水平。”而在批評(píng)我的“制度具有最強(qiáng)的社會(huì)賞罰功能”的觀點(diǎn)時(shí),他又是避而不談它是否符合事實(shí),卻文不對(duì)題的再次強(qiáng)調(diào)生產(chǎn)力對(duì)制度的決定作用,認(rèn)為“不能夠把制度的設(shè)計(jì)看成是主觀的產(chǎn)物,它背后具有不可忽略的客觀必然性。”并對(duì)這種客觀必然性進(jìn)行了自問自答的解釋:“為什么不同的歷史時(shí)代會(huì)有根本不同的制度安排,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制度特色呢?實(shí)際上,制度設(shè)計(jì)和制度安排并不是決定人類社會(huì)的上帝之手,它會(huì)受到更加重要因素的制約,即與生產(chǎn)力發(fā)展水平相適應(yīng)的物質(zhì)資料生產(chǎn)方式的制約。”
我認(rèn)為,孫先生關(guān)于“制度設(shè)計(jì)不能隨心所欲”的說法顯然太過輕率。試問:希特勒的種族滅絕政策和朱元璋的荒唐反腐詔諭之類的制度安排,難道不是“隨心所欲”的嗎?因而他在此處準(zhǔn)確的表述應(yīng)該是“制度設(shè)計(jì)不可隨心所欲”。既然只是“不可”,其中豈不就有可供選擇的空間?至于商鞅設(shè)計(jì)不出現(xiàn)代民主制度之類制度的詰問,也根本證明不了任何問題。難道它意味商鞅當(dāng)初再?zèng)]有任何別的制度選項(xiàng),而只能“必然”地去設(shè)計(jì)耕戰(zhàn)制之類的法家制度嗎?實(shí)際上,為何當(dāng)時(shí)其他國家都沒用法家制度,唯獨(dú)秦國用了?這個(gè)事實(shí)恰恰證明的是人在制度安排上是具有選擇性和創(chuàng)造性的。正因如此,不僅孫先生提到的具有不同的生產(chǎn)力發(fā)展水平的不同的時(shí)代、不同的民族,會(huì)有不同的制度安排,而且,即便是具有同樣生產(chǎn)力發(fā)展水平的同一個(gè)時(shí)代的同一個(gè)民族,也同樣可以有不同的制度安排。
這就從事實(shí)層面說明,制度不可能是來自于孫先生所說的“生產(chǎn)力及其發(fā)展水平”。這個(gè)結(jié)論,也可以從理論上得到說明。這就是,由于物質(zhì)生產(chǎn)力在本質(zhì)上不過就是人通過勞動(dòng)作用于外在物而取得所欲之物的活動(dòng)能力,所以這種活動(dòng)能力,不管是作為既有的力量還是潛在的力量,都既不能直接生產(chǎn)出任何制度來,也不能告訴或“要求”人們要設(shè)計(jì)什么樣的制度。能向人提要求的,從來都只能是人自己,而不是其他,也不是什么人的任何活動(dòng)能力。況且,如果是人的某種活動(dòng)能力在給人提要求,那這跟人的主觀選擇又有多大區(qū)別?又哪里會(huì)有孫先生反復(fù)申明的“客觀必然性”?孫先生把我國清末的共和制取代帝王專制和當(dāng)代的農(nóng)村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制的改革,都說成是適應(yīng)生產(chǎn)力要求的必然結(jié)果。但實(shí)際上,前者分明是人們有了“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的民主意識(shí)之后的要求,后者分明是人們開始把“富裕”看得比“平等”更重要之后的要求。正因制度安排及改制只是適應(yīng)人的要求,所以其中并無必然性,所以也自然能夠被人自己推翻,猶如袁世凱在共和之后的帝制復(fù)辟。
退一步講,即便承認(rèn)生產(chǎn)力作為前人留下的既得力量,客觀上會(huì)對(duì)當(dāng)代人的制度安排形成孫先生所說的某種“界限”,它也起不了必然的作用或決定性的作用。任何制度安排都需要一定的前提或基礎(chǔ)這不假,但這并不意味制度安排者在安排制度時(shí)就不能選擇或創(chuàng)造。而創(chuàng)造作為人的“無中生有”的能力,也與客觀必然性無關(guān),它只能是人的擁有想象力的大腦思維的結(jié)果。否認(rèn)這些,一味強(qiáng)調(diào)“客觀必然性”,不僅等于在否認(rèn)人是歷史的主體和創(chuàng)造者,而且會(huì)意味一切制度安排者,不管其制定的是好的制度,還是壞的制度,都完全不必為之負(fù)責(zé)。因此,即便是生產(chǎn)力對(duì)制度的設(shè)計(jì)制定確實(shí)有一個(gè)客觀界限,在此界限之內(nèi),也仍然是會(huì)有很多甚至近乎無限之多的不同制度安排選項(xiàng),這又怎么會(huì)存在只能如此的所謂“客觀必然性”呢?
孫先生為了否定制度選擇的主觀性,在自己文中不得不用“制度選擇”的說法時(shí),都忘不了要加上這種選擇是出于某種必然性的附加說明。但如果選擇是必然的,那還能叫選擇嗎?孫先生為了強(qiáng)化其論點(diǎn),還特地引述了馬克思“人們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的歷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的話。可此話恰恰證明的是相反的意思,即歷史是被人們創(chuàng)造的而不是必然的,只是這種創(chuàng)造性,在任何時(shí)候都不是無限的而已。
其實(shí),不僅歷史是被制度決定的,就連被孫先生認(rèn)定為能決定制度的生產(chǎn)力,同樣也是被制度決定的。馬克思曾說,生產(chǎn)中生產(chǎn)者要與生產(chǎn)資料結(jié)合,同時(shí)生產(chǎn)者與生產(chǎn)者也要相互結(jié)合,否則就形成不了活的生產(chǎn)力。而我的另一篇最新研究成果即《制度決定生產(chǎn)力》證明,①參見韓東屏:《制度決定生產(chǎn)力》,《南國學(xué)術(shù)》2017年第1期。能讓這兩種結(jié)合得以實(shí)現(xiàn)并形成某種固定的生產(chǎn)方式的,正是生產(chǎn)制度。并且,能決定生產(chǎn)力發(fā)展?fàn)顩r的,同樣也是生產(chǎn)制度。
四、制度來源的問題
我想,我的制度決定歷史的觀點(diǎn)之所以不容易被孫先、樊二位乃至其他很多人接受,一個(gè)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們認(rèn)為制度不是終極性的東西,制度也會(huì)有決定者,即便它不是孫先生強(qiáng)調(diào)的生產(chǎn)力,也會(huì)有其他。樊先生就認(rèn)為在制度的背后“還有另一些深刻的東西”,“至少還有人的行為方式、思維方式和文化傳統(tǒng)等因素。”但是,所謂“行為方式”,只能是制度型塑的結(jié)果而不可能是制度形成的原因,而“思維方式和文化傳統(tǒng)”,也不是制度的決定因素,見下便知。
的確,制度不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制度作為來自組織的正式規(guī)則,只能是被組織中的制度安排者制定出來的。
問題是,制度安排者在制定制度時(shí),難道不需要有所根據(jù)嗎?
需要。其中首要的根據(jù)就是制度意圖,即通過制度要實(shí)現(xiàn)什么目的的想法。任何具體制度都會(huì)有自己的特定目的,如民主制度的目的就是實(shí)現(xiàn)人民當(dāng)家做主,皇權(quán)制度的目的就是實(shí)現(xiàn)皇帝的統(tǒng)治;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的首要追求是平等,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的首要追求是效率。因此,所有制度的制定都要服務(wù)于某種制度意圖。在制度意圖明確之后,還需要根據(jù)已有的制度理論來設(shè)計(jì)或選擇具有可行性的最有利于實(shí)現(xiàn)制度意圖的制度形式。由于制度意圖和制度理論都屬于制度意識(shí)或制度思想,所以制度安排者制定的制度,就是來自于制度安排者的制度思想。這種制度思想有的是繼承前人的,有的是來自當(dāng)代他人的創(chuàng)造,有的則就是出自自己的創(chuàng)造,有的是以上這些因素混合而成。盡管歷史中,制度安排者沿襲前人制度的情況居多,但歷史上最初的制度一定是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因它再?zèng)]有任何前例可援;還有歷史中替代舊制度的新制度也一定是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否則無新可言。而人類歷史也正是因此之故才得以誕生并能不斷地有所進(jìn)化的,人類也正是在這個(gè)意義上,才能創(chuàng)造歷史并成為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西方經(jīng)濟(jì)學(xué)包括新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之所以在制度的起源和演變(變遷)的問題上總是糾纏不清,除了錯(cuò)將正式規(guī)則與非正式規(guī)則混為一談,都說成是制度之外,另一個(gè)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都忽略掉了一個(gè)最基本的事實(shí):制度從來都是由制度安排者制定和改變的。①參見韓東屏:《制度安排者決定制度演變》,《天津社會(huì)科學(xué)》2015年第6期。
因此,出于自由意志的制度思想就是制度的來源,從而也是社會(huì)歷史中的每一個(gè)因果鏈條的開端或終極原因。
那這里為何不直接將歷史的終極決定因素歸結(jié)為制度思想?這是因?yàn)椋绻覀兂姓J(rèn)馬克思關(guān)于歷史就是人們的活動(dòng)的命題,那么,能決定人們活動(dòng)的方式方向的,就是制度安排者制定的社會(huì)制度,而不是制度安排者所擁有的制度思想。更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任何一個(gè)人的制度思想或任何一種制度理論都能成為社會(huì)制度!至于樊先生提到的“思維方式和文化傳統(tǒng)”,盡管也可與制度安排者的制度思想拉上一定的關(guān)系,卻不僅距人們的活動(dòng)即歷史更遠(yuǎn),而且它們也絕對(duì)不能決定每個(gè)受到其影響的制度安排者,都必然會(huì)設(shè)計(jì)安排出同樣的制度。
至此,我對(duì)孫、樊二位先生之質(zhì)疑的回答是:是的,歷史就是被制度決定的。確切說,是被制度安排者決定的。因此,歷史絕不是自然史的過程,而是人為史的過程。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責(zé)任編輯 唐 偉
K01
A
1003-8477(2017)06-0111-05
韓東屏(1955—),男,華中科技大學(xué)哲學(xué)系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研究費(fèi)項(xiàng)目“歷史規(guī)律研究”(2017);國家教育部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一般項(xiàng)目“制度在社會(huì)歷史中的地位與作用”(14YJA7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