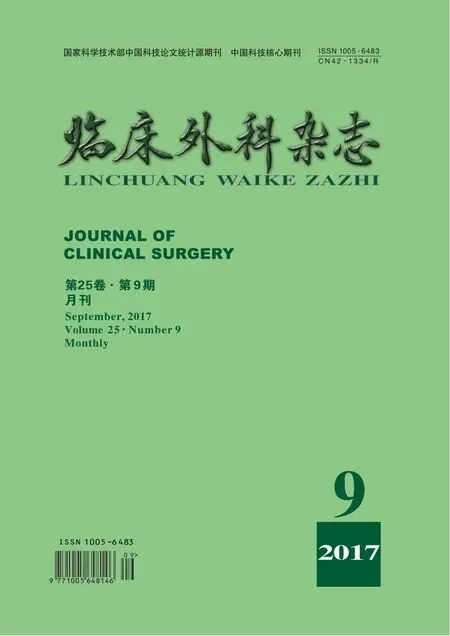復雜顱底手術中的團隊協作和多方式聯合
姜曙 周培志 尹森林
·專家筆談·
復雜顱底手術中的團隊協作和多方式聯合
姜曙 周培志 尹森林
顱底; 手術; 多學科
顱底區域的組織結構解剖毗鄰關系復雜,同時又具備重要的功能,因此,顱底外科一直以來都是神經外科最具挑戰性的亞專業方向之一。近年來神經外科、耳鼻咽喉科、眼科等學科在各自的領域逐步探索和推進。隨著手術入路和手術器械的改進,各學科手術可達區域逐步擴大、重合,尤其是在顱底區域,在實踐中面臨新的挑戰。以下將從多個角度探討團隊合作在顱底外科中的意義。
一、顱底解剖的復雜性需要多學科團隊合作
顱底有面向腦組織的顱內面以及面向鼻腔、鼻旁竇、眶、咽部、顳下窩、翼腭窩、咽旁間隙和巖下間隙的顱外面,顱內面和顱外面有許多血管及神經通過的管、孔、裂[1],顱底為腦顱和面顱交界,位置深在且結構復雜。以經鼻蝶顱底外科手術為例,神經外科醫生在成長過程中對開顱顱底外科熟悉的同時也積累了大量經鼻蝶鞍區手術的經驗,隨著近年來神經內鏡的發展,可視及可操作范圍不斷擴展至前顱底、中顱底及側顱底、斜坡等區域。由于神經外科醫生成長過程中缺少對鼻腔及頜面部解剖的培訓,在經鼻腔/上頜竇等結構建立手術通道時就容易誤傷本該保留的結構或操作中因解剖不熟悉而“畏手畏腳”;另一方面,耳鼻咽喉科、眼科等醫生由于不熟悉神經系統解剖及術中并發癥的處理而導致手術范圍局限于硬膜或顱底骨之外。因此,涉及顱底的各學科人員需要在臨床工作中相互學習并進行相應的解剖訓練,從而取長補短,提高對局部解剖毗鄰關系的認識,能夠更好地提高手術質量并開展新的手術入路。有條件的醫療中心應組織多學科聯合成立解剖實驗室,用于醫生培訓和手術入路開展前的摸索和嘗試,并在此基礎上聯合舉辦學習班,以促進顱底外科人才培養,提高手術的安全性。
二、顱底外科手術療效改善及術后快速康復迫切需要多學科的參與
顱底外科在神經外科最具挑戰性,其手術難度高、風險大、并發癥多、療效相對較差。隨著顯微內鏡解剖的深入和先進醫療設備的應用,一些曾被認為是手術禁區或者認為手術弊大于利的區域不斷被神經外科醫生征服。為了進一步提高手術療效,外科醫生開始更加注重術中神經血管的保護和有效的顱底重建。手術入路選擇中盡量減少對神經血管的干擾是近年來一個重要的新理念,即現已為人熟知的無牽拉和不干擾原則,其關鍵在于充分利用顱底或者完全顱底入路。因此,加強與耳鼻咽喉科、眼科和頜面外科的合作就顯得至關重要,尤其是在神經內鏡方面。十余年前,神經內鏡操作范圍的擴大使得一部分顱底手術已經完全實現了“顱外操作”,但顱底的顱外面入路也帶來了新的挑戰,其難點在于顱底修復的困難及腦脊液漏、顱內感染等并發癥的高風險。通過與耳鼻咽喉科醫生的合作,帶蒂鼻黏膜瓣技術的應用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這一問題。該技術在神經外科和耳鼻咽喉科醫生的合作推動下得以發展、推廣,并不斷優化[2]。有效的顱底重建,以及更少的血管神經干擾,無疑將顯著降低手術并發癥風險,并促進病人的快速康復。除與其他外科醫生合作以外,內分泌科等內科醫生的參與也將進一步改善垂體功能障礙及病人術后生存質量,促進病人術后快速康復。另外,腫瘤放療科醫生的參與也有助于提供規范的后續治療,尤其是對于治療術后腫瘤殘留的病人。顱底疾病的診療過程較為復雜、繁瑣,切實需要相關學科的密切合作[3]。
三、圍繞顱底外科疾病的各學科醫生合作模式
由于顱底疾病病人起病癥狀不一,首診科室各異,各相關科室均可能在診療中擔當關鍵角色。此外,諸多顱內外溝通性病變的病人往往需要輾轉多個科室分次手術。隨著醫患對手術療效要求日益提高,各科醫生分期手術的缺點也逐漸暴露。如術后解剖結構的變化及粘連會增加二期手術的全切難度,二期手術醫生不了解首次手術的具體術中情況,難以保證完美的治療效果。近年來醫療模式不斷變化,外科系統從以解剖部位劃分學科界限的傳統模式,過渡到目前以病人和疾病為中心診療模式,許多顱底交界部位的病變迫切需要以團隊合作的形式來進行診治,如此才能充分發揮不同學科醫生各自對局部解剖、疾病認識、手術操作、并發癥管理等的信息優勢,使病人在診療過程每一環節中都能得到最佳的治療,同時有利于病人遠期療效的提高。
團隊合作的形式主要有三種模式,即多學科團隊合作、學科間團隊合作以及跨學科團隊合作[4]。多學科模式即在臨床診療過程中,各相關學科的不同專家以聯合討論、資源共享并在診療過程中實現本學科各自的治療目標,該模式在復雜疾病病人和存在合并癥/并發癥的病人診療過程中較為常用;學科間團隊合作即不同學科的團隊共同制定診療目標及方案,在診療過程中共同遵守并實現診療目標,該模式已普遍應用于多種神經外科疾病的診療,例如國內諸多大型醫院的垂體瘤中心;跨學科團隊合作跨越了學科的界限,即在診療和手術過程中,全程共同參與,例如美國諸多顱底外科中心模式,神經內鏡手術病人可能由神經外科首診并收治,而由神經外科醫生和耳鼻喉科鼻內鏡醫生嫻熟且默契地共同完成手術,兩者在手術過程中分工明確,相輔相成,作為團隊共同研究、改良手術入路,就像同一個醫療組。就國內的實際診療運行而言,三種模式通常并存,尤以前兩種最為多見。
在顱底外科臨床實踐中,最常涉及的科室包括神經外科、耳鼻咽喉科、口腔頜面外科、整形外科、放射影像科、神經電生理科、內分泌科、病理科等。典型的疾病包括垂體腺瘤、脊索瘤、顱咽管瘤、顱底腦膜瘤、聽神經瘤、鼻咽癌等。最常合作的術式為神經內鏡顱底手術。因卓越的神經內鏡手術聞名于世的美國匹茲堡顱底外科中心,有著相對固定的神經外科-鼻內鏡外科醫生團隊。耳鼻喉科鼻內鏡醫生負責建立經鼻腔手術通道,之后掌控內鏡提供視野和輔助;神經外科醫生負責磨除顱底骨質及切除腫瘤,病變切除后兩者共同完成顱底重建,鼻腔修復則繼續由耳鼻喉科鼻內鏡醫生完成[3,5-6]。這樣兩位醫生分別負責最熟悉的手術部分,將手術的每一個環節都能做到最好。經過長期的磨合,兩人四手操作形成動態操作視野,手術范圍更為開闊,對術中危險情況的處理也更得心應手。在匹茲堡顱底外科中心,這種團隊合作貫穿在解剖實驗室培訓、臨床診療、學術交流以及新手術入路的研究與開展之中。由于國內歷史原因,多數單位仍是神經外科醫生/耳鼻咽喉科醫生以顱面解剖標志為界分別診療的模式,有的單位還存在神經外科醫生和耳鼻咽喉科醫生各自開展經鼻蝶垂體腺瘤手術的情況,這種模式不利于學科發展和診療效果的提高,同時也更容易引發醫療糾紛。因此,由熟練掌握本學科入路且了解相關學科入路的多學科醫生組成手術團隊,能夠從多個角度、多種手術入路中選擇最適合的入路,有助于提高手術效果,改善病人預后。
四、放射影像及導航技術是團隊合作診療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
目前,神經影像的價值已不僅局限于為臨床提供客觀診斷依據,而是貫穿在顱底疾病的整個診療過程之中[7]。建立多學科合作模式的框架后,放射影像科醫生與外科醫生之間更容易建立相對固定的聯系,明確各自工作責任。為了實現更為精準的手術入路和更好的手術療效,跨學科手術團隊需要在手術前制定詳細的手術計劃,因此需要精確的術前影像學資料,有時還需要增加特殊序列掃描及重建(如DSI顱神經顯像)以顯示細微結構,結合病人癥狀,明確病變部位與顱神經、血管的關系[8]。手術過程中,精確的導航系統可縮短手術時間,確保手術過程中位置的準確性,這在解剖標志被病變破壞的情況下尤為重要。因此,術前放射影像科醫生所提供影像學資料的精細程度和術中導航的精確程度在精準神經外科手術中扮演著重要角色[9-10]。
五、神經電生理及大動脈監測在顱底外科中的價值日益顯現
神經電生理監測正是在近年來顱底外科手術療效要求不斷提高的背景下萌芽并迅速發展的,廣泛應用于聽神經瘤等后顱底、腦干手術。隨著多學科合作及大型醫院顱底外科手術的廣泛開展,神經電生理監測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能夠極大降低神經功能廢損風險。目前,神經電生理監測已被寫入顱底手術指南推薦,其重要性可見一斑[11-12]。術中神經電生理監測要求電生理監測醫生主動關注手術進度,同時需要麻醉醫生協作配合。另外,在顱底病變侵入海綿竇、顱內外溝通性病變包繞推擠顱內大動脈的情況中,術中血管的多普勒探測對于盡可能安全地全切腫瘤也非常重要[13-14]。術中神經電生理監測和動脈多普勒監測均需要多學科團隊協作,共同確保病人術中安全,降低術后并發癥風險。
六、顱底疾病病人的診療過程中需要內科醫生、康復科醫生的加入
在復雜顱底疾病中,除因病變本身對神經功能、內分泌功能的影響外,還包括手術可能帶來的損傷。這需要內科醫生術前介入診療,并輔助術后隨訪,及時發現并處理內科問題;而對于部分顱神經受損病人,術后有賴康復科醫生進行多方面的功能康復訓練,改善生存質量;對于需要放化療的腫瘤病人[15],在術后重建過程中也需要外科醫生、腫瘤科醫生、放療科醫生共同協作,加強對重要結構周圍的重建和血供支持,以減少放射治療并發癥。外科醫生與腫瘤科醫生應密切溝通,結合手術情況共同優化銜接過程和放化療計劃,改善療效和病人生活質量[15-18],從而克服傳統會診模式無相對固定人員、效率低下的弊病。
七、顱底外科的發展面臨更多的挑戰
為了完成高質量的顱底外科手術,必須重視前述內容。然而,要實現高效的團隊合作和多學科診治,在我們國情下尚面臨以下問題。
1.國內各級醫院水平及多學科合作能力差別較大。盡管有些醫院開展了顱底手術,但以活檢、減瘤等為主,尤其針對良性腫瘤,如因能力所限未能實現首次全切,一旦腫瘤復發,將對周圍結構形成嚴重的粘連,增加二次手術風險和失敗率。因此,在分級診療制度日益強化的時代背景下,有必要建立符合國情的顱底手術準入制度和規范,對于有意愿開展顱底手術的基層醫療機構,由高水平醫療機構負責加強理念和技術方面的培訓并給予資質認證,使外科醫生明確如何在條件允許情況下保護重要神經血管,提高遠期療效。
2.重視顯微解剖及內鏡解剖培訓。美國等發達國家非常重視外科醫生的解剖培訓,經過對正常神經、血管、顱骨的解剖培訓,能夠增強外科醫生對重要結構的保護意識和三維立體定位認知,為臨床手術奠定較為扎實的基礎。
3.醫院管理模式的支持在促進多學科合作中亦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醫院的績效管理,在越來越廣泛多學科合作尤其是多科聯合手術時的分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促進或者阻礙多學科合作。因此,醫院管理層應當與時俱進,改革創新配套的分配制度,充分調動相關科室的積極性。
4.在技術方面,盡管血管吻合技術已比較成熟,但在復雜顱底手術中的應用,尤其借助大血管吻合技術提高切除程度尚需探索。復雜顱底病變手術后骨性重建及頸內動脈周圍組織重建亦非常重要,而在骨性重建中對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成果的利用也有待加強,需要進一步的基礎應用研究和轉化研究。
5.更多學科的加入。隨著手術及診療效果要求的提高,未來仍會出現新的手術入路,尤其是經鼻腔、開顱以及頜面部切口的入路將更多地應用于復雜顱底病變和顱內外溝通性病變。如何更好地進行頜面部重建,有賴于頜面外科和整形外科醫生的參與[19],這方面的合作交流仍有待加強。
[1] Albert L,Rhoton.The anterior and middle cranial base[J].Neurosurgery,2002,51(1):271-302.
[2] Hadad G,Bassagasteguy L,Carrau RL,et al.A novel reconstructive technique after endoscopic expanded endonasalapproaches:vascular pedicle nasoseptal flap[J].Laryngoscope,2006,116(10):1882-1886.
[3] Snyderman CH,Wang EW,Fernandez-Miranda JC,et al.The making of a skull base team and the value of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in the management of sinonasal and ventral skull base malignancies[J].Otolaryngol Clin North Am,2017,50(2):457-465.
[4] Young CA.Building a care and research team[J].J Neurol Sci,1998,160(1):137-140.
[5] Gardner PA,Kassam AB,Thomas A,et al.Endoscopic endonasal resection of anterior cranial base menigiomas[J].Neurosurgery,2008,63(1),36-52.
[6] Zwagerman NT,Zenonos G,Lieber S,et al.Endoscopic transnasal skull base surgery:pushing the boundaries[J].2016,130(2),319-330.
[7] Stenin I,Hansen S,Nau-Hermes M,et al.Minimally invasive,multi-port approach to the lateral skull base:a first in vitro evaluation[J].Int J Comput Assist Radiol Surg,2017,12(5):889-895.
[8] Yoshino M,Abhinav K,Yeh FC,et al.Visualization of cranial nerves using high-definition fiber tractography[J].Neurosurgery,2016,79(1):146-165.
[9] Matsushima K,Komune N,Matsuo S,et al.Microsurgical and endoscopic anatomy for intradural temporal bone drilling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electromagnetic navigation system:various extensions of the retrosigmoid approach[J].World Neurosurg,2017,103:620-630.
[10] Toki Saito,Naoyuki Shono,Seiji Nomura,et al.Usefulness of high-resolution 3D multifusion medical imaging for preoperative planning in patients with posterior fossa hemangioblastoma:technical note[J].J Neurosurg,2017,127(1):139-147.
[11] Elangovan C,Singh SP,Gardner P,et al.Intraoperativeneurophysiological monitoring during endoscopic endonasal surgeryforpediatric skull base tumors[J].J Neurosurg Pediatr,2016,17(2):147-155.
[12] 中國顱底外科多學科協作組.聽神經瘤多學科協作診療中國專家共識[J].中華醫學雜志,2016,96(9):676-680.
[13] Sima Julián JA,Sanrománlvarez P,et al.Endo ICG videoangiography:localizing the carotid artery in skull-base endonasal approaches[J].Acta Neurochir(Wien),2016,158(7):1351-1353.
[14] Dusick JR,Esposito F,Malkasian D,et al.Avoidance of carotid artery injuries in transsphenoidal surgery with the Dopplerprobe and micro-hook blades[J].Neurosurgery,2007,60(2):322-328; discussion 328-329.
[15] Kim YH,Jeon C,Se YB,et al.Clinical outcomes of an endoscopic transclival and transpetrosal approach for primary skull base malignancies involving the clivus[J].J Neurosurg,2017,172(2):1-9.
[16] Stacchiotti S,Gronchi A,Fossati P,et al.Best practic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local-regional recurrent chordoma:a position paper by the Chordoma Global Consensus Group[J].Ann Oncol,2017,28(6):1230-1242.
[17] Kauppila JH,Xie S,Johar A,et al.Meta-analysis of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after minimally invasive versus open oesophagectomy for oesophageal cancer[J].Br J Surg,2017,104(9):1131-1140.
[18] Homer JJ,Lesser T,Moffat D,et al.Management of lateral skull base cancer:United Kingdom National Multidisciplinary Guidelines[J].J Laryngol Otol,2016,130(S2):119-124.
[19] Cherubino M,Turri-Zanoni M,Battaglia P,et al.Chimeric anterolateral thigh free flap for reconstruction of complex cranio-orbito-facial defects after skull base cancers resection[J].J Craniomaxillofac Surg,2017,45(1):87-92.
2017-08-10)
(本文編輯:楊澤平)
10.3969/j.issn.1005-6483.2017.09.004
四川省科技廳科技支撐計劃資助項目(2015SZ0120)
610041 成都,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神經外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