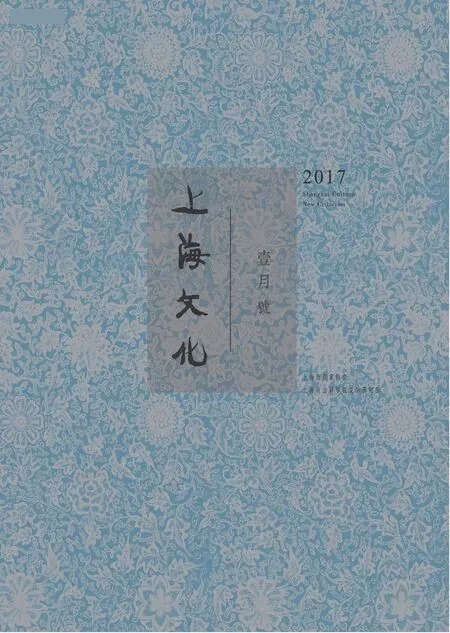一種失落的寫作和閱讀方法①
梅爾澤 萬 昊 譯
一種失落的寫作和閱讀方法
梅爾澤 萬 昊 譯
顯白的和隱微的,形容詞性, (哲學史類):第一個詞的意思是“外在的、表面的”,第二個詞的意思是“內在的、里面的”。古代哲人們有兩種學說,一種是外用的、公開的,或者說是顯白的;另一種則是內傳的、秘密的,或者說是隱微的。
——狄德羅的《百科全書》
……所有哲人都十分樂意接受了這兩種學說之間的區分,并憑借這種方式信奉與其公開教誨相反的秘密觀點。
——盧 梭
我們現代人信仰進步(progress)。但即便是我們也必須承認,時光的流逝不僅帶來智識進步,也導致智力衰退;不僅帶來知識上的發現,也導致思想上的僵化、拒斥和遺忘。而前者自然而然吸引人們的注意,令人印象深刻,而后者則受到忽略。各種發現、探索無人不知,而忘卻、遺漏則隱沒無形。
已經有不計其數的書籍贊頌人類發現了許多重要現象。我則要考察人們對某個現象的遺忘。
一
1811年10月20日,歌德寫信給一位朋友,談到他親眼所見人們正在遺忘某些東西:
在上世紀后半葉,人們不再區分顯白與隱微。我一直認為這是一種惡行,甚至是一場愈發蔓延的災難。
歌德在此宣稱,西方社會的智性生活正在逐漸經歷一次陌生而不幸的轉變。人們以緩慢的集體失憶的方式,悄然忘卻某種眾所周知的現象——哲學式的隱微寫作。這是指一些人因為害怕迫害,或出于其他原因,以種種符合傳統的虔敬文字作為掩護,根本上卻在“字里行間” (between the lines)交流各自的異端思想。
歌德的警告雖不受重視,卻被證明是富有先見之明。他在哲學層面上所指出的這種遺忘現象將在下一個百年中持續蔓延和惡化。其實,隱微寫作在18世紀上半葉仍十分出名,可以公開討論,并幾乎得以普遍踐行(就像自古以來那樣),前文狄德羅和盧梭的引言也表明了這一點。在下文中,我們將為這兩種論述找出百倍的類似說法。這種廣為接受的現象在19世紀的進程中逐漸遭到遺忘了,而20世紀則干脆宣稱其為一個神話。
對隱微寫作的重新發現主要由施特勞斯(Leo Strauss)完成。他是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哲學家,從上世紀30年代末開始就這一主題發表著作。正如科耶夫(AlexandreKojeve)對這一成就的感謝詞所說:
施特勞斯使我們想起自19世紀以來就被輕易遺忘的觀點,即人們不應該僅僅從字面上理解早期時代偉大作家們所寫的一切文字,也不應相信他們在著述中會暢所欲言。
我并不想恢復隱微地寫作,卻試圖復興隱微地閱讀——一項至關重要卻丟失已久的哲學素養
然而,施特勞斯恢復隱微主義的努力基本上被置之不理。
我是對往事的一次追憶和挽回。它試圖更清晰地展示、記錄,尤其是扭轉(如果可能的話)這一不同尋常的遺忘行為。我旨在恢復人們對隱微書寫的總體認可:19世紀以前的西方主要哲學作家曾普遍踐行隱微寫作;而隱微地寫作出于多種原因。在此,我的目的不是激發人們熱愛隱微主義(我本人并非它的愛好者),也不是鼓勵人們從事隱微寫作(我也并不這么做),只是幫助人們認識、領會并接受隱微主義在歷史上的真實存在以及它確實對西方兩千多年智性生活中的全部行為有著巨大影響。我并不想恢復隱微地寫作,卻試圖復興隱微地閱讀——一項至關重要卻丟失已久的哲學素養。
我也不是要探明一脈相承的思想家中每個人(或任何一個人)個別、具體的隱微教誨——我這部綜述性的著作做不到;要完成這項工作,我們得一絲不茍地一次只討論一名哲人。所以,我不是要寫《古往今來的隱微奧秘大揭露!》,只不過是要說《隱微寫作已被忘卻,讓我們重新認識它》。這種研究對當下來說已經夠用。
至此,我還沒有出示能證明這項古怪實踐真實存在的大量證據,讀者當然會對我的價值持保留意見。不過,我們至少應該明白我論題的重要性。以下是其重要性的具體體現。
如果哲人們隱微地寫作,而我們并不隱微地閱讀他們,則我們必然會誤解他們。我們會系統性地自絕于他們思想中最不正統、最富原創和最自由的部分
如果我們能證實,過往的大多數哲人習慣在習俗的(conventional)觀點表面下隱藏自己最重要的想法,那么我們最好能認識這一點。如果哲人們隱微地寫作,而我們并不隱微地閱讀他們,則我們必然會誤解他們。我們會系統性地自絕于他們思想中最不正統、最富原創和最自由的部分。
這危害已然不小,卻還沒完。我們不但會誤解每一個思想家,而且隨著這類錯誤的積累,也將誤解以下事項:思想家之間的關聯、思想如何隨著時間發展和西方知識史的整體進程與意義。這些誤解對現代哲學特別具有破壞性,因為現代哲學或明或暗地依賴于某種“歷史理論”,依賴于對哲學思想發展的各階段及軌跡的解釋。
事實上,還有進一步更為關鍵的危害。如果出于各種原因,我們誤解了早期的哲人,并因此誤解了哲學思想的歷史,我們難道不怕自己最后將會誤解人類理性的品性嗎,尤其是人類理性是如何與它所在的政治和文化環境互動?因為,我們主要是通過觀察人類理性做過什么,透過它的歷史、它的失敗及成就的具體記錄,來知曉理性的運作方式及其能力范圍。系統性地曲解理性的歷史造成的重大危害是我們會誤解理性本身。
具體來說,正是對上述危害的恐懼,使施特勞斯全神貫注地研究隱微主義的課題。在此我將闡述他復雜論證中的一個部分。施特勞斯認為,對隱微寫作的無知使我們誤讀哲學史,而這種誤讀并非隨機發生。在解讀所有思想家時,我們除了對個別思想家犯下各種個別的解讀錯誤,還不斷重復著一個普遍錯誤,即我們誤以為哲人表面的、顯白的(exoteric)教誨是他真正的教誨。再者,不論思想家表面上的教誨有多么不同,它們卻有一點共通的本質:它們由思想家精心設計,用來營造虛假的表面以迎合彼時最強有力的思想教條,公開質疑那些教條過于危險。
因此,既有的閱讀習慣——用非隱微的方式閱讀隱微的作者——對學術研究的影響清晰可見,后果可想而知。它導致不斷再現的系統性錯覺:放眼望去,我們看到的是令人沮喪的景象——在不同時代中,當時占支配地位的觀念壓抑著人的心靈。看來,即便是我們人類最著名的天才,比如亞里士多德們和莎士比亞們,他們的非凡天賦和艱辛努力,最后也總以確認其特殊的“洞穴”神話而告終。就這一反復出現的經驗現象,人們容易低估其深刻影響。它形塑了我們時代至關重要卻隱而未現的知識背景,誘發了現代晚期或后現代對理性的偏見:理性應被徹底批判和打倒(disempowerment)。在隱微主義遭到遺忘的時代,每個人看似都知道人類的心靈并不自由,而是完全由語境、文化和社會決定。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所有的真理最終都是局部的、偶然的、一時的;而我們最高的智慧,只會是改良過的鄉鎮民族中心主義(hometown ethnocentrism)。
相比之下,抱著對隱微主義的意識,我們會察覺到哲學對各種思想教條的迎合,是某種普遍的假象,背后隱藏著各種謬誤和蓄意犯錯——現在看來,這是一種反諷而機智的抵抗。 在這道防御墻背后,一個大膽而秉持異見的秘密地下組織在蓬勃發展,一個使心靈無所拘束的非法地下酒吧正生意興隆,它們都受到這道墻的庇護和支持。我們本應為之慶幸,卻不知何故不愿相信它。然而,正如一句古老的埃塞俄比亞諺語所說:“當主子出巡時,聰明的農民深深鞠躬,暗暗放屁。”每一個被統治階級,各自都有進行沉默抵抗的手段,哲人們也一樣。當缺乏強力時,欺詐和守密就是自由的主要代理人。如果現代的學者們多像狡猾的農民那樣思考,他們會更愿意接受這一本質真理:即世界上真實存在的自由,總是多于他們基于事物表面上的服從所認識的自由。因此,人類理性的真實歷史必然是一部秘史:一旦我們目擊到哲學式的守密行動,那我們就不再會認為,人類的理性能力缺乏獨立性并受文化制約。
總之,對隱微主義的無知,阻礙我們看見那隱蔽的自由世界,使我們無法認識自己——無法認識到人類的心靈具有驚人的力量和獨立性,對時間和空間有意想不到的抗拒能力。
最后說一點。如果我們能證明哲學式隱微主義的傳統是一個事實,就會馬上揭示第二個關鍵事實,即我們長期無視并抗拒第一個事實。我們將不得不搞明白:我們究竟是如何錯過如此重大且(以往)眾所周知的東西呢?換言之,隱微主義的利害問題,也是攸關我們自身利害的重要問題:現代世界觀(worldview)有哪些特殊的缺陷或偏見,以致使我們變得不能看到如此重大的事實?
就現象而言,發現某些現象引人注目,而遺忘某些現象將意義深遠。憑借這些發現,我們探索并歌頌自身的洞察力,而透過某些遺忘,我們察覺到自身的盲目性。只有碰見我們所不理解的事實,我們才能看到自身知覺的局限性,并由此開始逐漸地超越自身局限性。
然而,不論上文說得多么引人入勝,很多人依舊會拒斥這一被長期遺忘的傳統,即西方哲人們曾隱微地寫作。他們認為這種說法是異想天開,它與其說是被遺忘的真理,不如說是象牙塔里的都市傳說(urban legend),其始作俑者大概是沉迷于中世紀觀念或塔木德式(Talmudic)思維的學者,他們過度渴求通往秘密智慧的特權。
就這一議題,正反兩方爭執激烈。但在所有這些爭論中,有三點內容可以大致得到確認:第一,如果關于隱微主義的理論是正確的,那這可不得了;第二,我們當代人發自內心地愿意相信它是假的;第三,因此,我們迫切需要對隱微主義進行一次嶄新而更加周詳的研究。
再者,這種研究看來也正逢其時。在過去幾十年中,各種解釋學理論爆炸性地增長。無論在什么地方,人們都對文本解讀的諸多話題——如修辭性、受眾、讀者反應、游戲性以及其他新的或被長期遺忘的話題——有高度的自覺。
啟蒙運動以來我們對寫作、閱讀和出版活動在性質上的所有設定——這些設定都事關思想與生活的整體關系——已遭到徹底地批判。長久以來不可撼動的諸種范式正分崩離析,使當今的學者可以不受限制地就隱微主義的問題展開新穎而富有原創性的研究。
二
據說,公元前6世紀的哲人,斯基泰人(the Scythian) 阿那卡爾西司(Anacharsis)睡覺時用左手捂著自己的私處,右手捂著嘴巴,以此暗示人應該管好這兩樣東西,而守口如瓶比守身如玉更重要。
——亞歷山大的克雷芒, 《雜說》
被遺忘的領域,就像未除草的花園,變得有些荒蕪。因此,首先有必要試著更精準地表述我為之辯護的論題。我們將區分“哲學式隱微主義”與大量圍繞在其周圍的相關現象,接著會清楚地分辨“哲學式隱微主義”的內部類型或變種。
實際上,隱微主義的實踐,貫穿于西方主流的哲學、文學和神學傳統
按照一般的用法,esoteric一詞常常能與recondite或abstruse同義替換,僅僅表示某種知識(比如量子力學),因其聚焦的問題有其內在的困難、深刻或專業性,超越了大多數人的理解能力。但就更嚴格的詞義來說,esoteric表示某物,因被隱藏或被保密,顯得難以理解。 esoteric一詞的古希臘詞源是esoterikos,意指內在的(inner)或內部的(internal)。隱微寫作的作者,或隱微寫作,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他們努力通過一些間接或秘密的交流模式,向一組特定人員傳遞某些真理(“隱微的”教誨);第二,與此同時,他們努力向大多數人保留或隱瞞上述真理或教誨;第三,常見但并非絕對的特征是,考慮到大多數人,他們努力散布某些虛假教誨(“顯白的”教誨)以代替被隱藏的真正教誨。
基于上述對esoteric一詞的理解,我們可以看到,從古至今有多種[思想]運動突出地強調了西方長期存在著某種“隱微”傳統。其中最突出是各式各樣的神秘主義:如神智論(Theosophy)、諾斯替主義或靈知主義(Gnosticism)、赫爾墨斯秘學(Hermeticism)、薔薇十字團(Rosicrucianism)、喀巴拉(Kabbalah)、新柏拉圖主義(Neoplatonism)和新畢達哥拉斯主義等。所有這些思想運動用各自方式表達了如下看法:存在某種單一的、秘密的“隱秘知識”體系,它具有神秘或超自然的性質,并將各時代的隱秘思想家連結起來組成兄弟會(brotherhood)。
當施特勞斯在上世紀30年代晚期開始討論隱微主義時,他敏銳地意識到,人們對隱微主義這種現象唯一的完整記憶或鮮活意識,存在于上述的神秘主義傳統。他寫道, “目前,隱微主義這一現象被放在‘神秘主義’的標題下加以討論”。即使施特勞斯和其他人已努力改變這種狀況,上述判斷放在今日仍大體正確。如果人們在互聯網上搜索“隱微主義”,或在國會圖書館的目錄中搜索帶有“隱微主義”標題的書目,絕大多數的搜索結果會指向神智論。
但是,神秘主義版本的隱微主義僅僅是更廣泛現象中的一小部分。實際上,隱微主義的實踐,貫穿于西方主流的哲學、文學和神學傳統。可以說,施特勞斯重新發現的是這種廣泛存在的隱微主義。
更廣泛地說,隱微主義并不意味著(神秘主義反之)存在某種單一的“隱微的哲學”,連結起所有純種隱微主義者(esotericists)。在此,“隱微的”并非意旨某種特定的秘密或超自然的知識體系,僅指向某種秘密的交流模式——不是指某些具體的想法,而是部分揭示又部分隱瞞某人想法(不論其內容)的這一做法。隱微主義不是一種哲學學說(doctrine),而是一種修辭方式,一門寫作藝術(雖說筆者下文將論證,人們認為有必要采用如此修辭方式的原因正是來源于更廣泛的、哲學的觀念)。
更廣泛地說,奉行隱微寫作的作者,其各自之間的差別,自然比神秘主義傳統中的作者之間的差別來得多:前者固然都使用某種秘密的溝通藝術,但各自的動機和目的不同,使用的隱微技巧和策略也不同。
進一步說,就我們感興趣的哲學式隱微主義來說,其各種子類之間,存在重要差異。這些差異的首要來源是剛剛提到的更廣泛的、哲學的觀點。哲學式隱微主義,不是神秘主義的現象,也不僅是文學或修辭現象,更不只是應對某些具體實際問題(比如迫害)時的手段。在其多種不同的形式中,哲學式隱微主義產生于某個根本性的、由來已久的哲學難題——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尤其是哲學理性主義與政治共同體的關系問題,或者說沉思生活與實踐生活的關系問題。這兩種生活方式在根本意義上是和諧的,還是敵對的?啟蒙運動實質上贊成前者,主流的古典思想擁護后者。顯然,對這一哲學問題的態度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思想家對寫作行動的立場,更確切地說,將決定思想家公開傳播其哲學思想的真實目的及他為此所選擇的修辭方法。
具體來說,啟蒙時期以來的大多數思想家寫作時大多抱有如下信念,即哲學如果能被恰當地傳播,就能照自己的樣子改造實踐領域:哲學能夠使政治世界與理性融洽和諧。基于這樣的動機和認定,他們往往出于兩個理由使用某種形式的隱微主義(其隱藏性或掩飾性相對寬松):一是作為宣傳的修辭方式,幫助推進雄心勃勃的政治和宗教變革計劃;而這類革命性計劃難免(雖說只是暫時地)給思想家招惹迫害,于是思想家也使用隱微主義作為免遭迫害的防御手段,這是第二個理由。
相反,古典及中世紀的思想家往往踐行更隱蔽,更徹底的隱微主義,也即最完整意義的隱微主義。他們這么做,不是期望哲學理性主義能啟蒙和改革政治世界,相反的,是出于某種恐懼——理性主義如果得到公開傳播,將顛覆政治世界必不可少的各種神話和傳統,不可避免地損害政治世界。同樣地,他們也害怕政治世界遭到破壞后所必然引發的迫害。與啟蒙思想家不同,他們出版哲學書籍的用意,并非主要是為了某些政治方案,而是為了某些教育目的。這些教育目的反過來讓他們踐行隱微主義有進一步的、教學方法的理由:使文本呈現為各種暗示和謎語,而不是答案,這種做法在文體上最近似蘇格拉底式教學法——它迫使讀者思考,自己去發現答案。
就此,我們可以區分哲學式隱微主義的四種主要類型。用更具分析性的話來說,一個哲學作家有意隱瞞自己真正的意圖,要么是為了避免某些邪惡,要么是為了獲取某些好處。需要避免的邪惡本質上有兩種:要么是政治社會對作者的傷害(迫害),要么是作者對政治社會的危害(“危險的真理”),或兩者兼而有之。為避免這兩種危險而使用的隱微主義,我分別稱為自衛式隱微主義和保護式隱微主義。
但是,想避免寫作帶來的危險,當然存在更簡單的方式:不寫作。所以,盡管有相當大的危險,哲人們決定出版書籍,還為了某些好處。好處主要有兩種:或是為了社會上普遍的政治(文化、智識、宗教)改革,或是為了極少數天才的哲學教育,或兩者兼而有之。而這些積極正面的目標各自要求某種巧妙的修辭學——或是宣傳式,或是教育式——我分別稱之為政治式隱微主義和教學法式隱微主義。
哲學式隱微主義產生于某個根本性的、由來已久的哲學難題——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尤其是哲學理性主義與政治共同體的關系問題,或者說沉思生活與實踐生活的關系問題
因此,思想家實踐隱微主義,各自的動機不同,其基本形式也不同。舉例來說,一個哲人可以什么都不寫,只局限于口傳教誨,在公開場合說一套,私下傳授另一套——畢達哥拉斯被認為是這么做的典型。哲人也可以僅通過口傳教誨傳播自己的真實想法,但同時寫書闡述對公眾有益的、顯白的學說。他也可以針對不同的受眾,創作兩類不同的作品:一類隱微,另一類顯白——但考慮到書籍流通方便,隱微的作品也不敢完全公開。或者,他的作品可能包含多個層次,其表面是顯白的教誨,“字里行間”則通過暗示和影射間接地傳播隱微的學說。
接下來,我們將主要關注這種多層次寫作(multilevel writing),這似乎是隱微主義最普遍的形式,但是記住其他所有可能形式也很重要。
同時,隱微主義的實踐在程度上差別很大。在某些情況下,顯白的學說僅僅是隱微教導的普及或凈化過(sanitized)的版本。而在其他場合下,情況可能完全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同理,一部分隱微的作者會對真理予以部分保留或隱藏,但不會說與真理相違背的東西。他們不會說出“全部真相”,但他們“除真相以外什么都不說”。換句話說,他們只呈現隱微的一面,省去顯白的一面。另一部分作者,既隱藏真相,又展示謬誤或“高貴的謊言”,仿佛它們是真的一樣。
盡管諸種隱微主義的具體內容、動機、形式和程度各有不同,存在著某種隱微主義這一事實卻具有驚人的連續性。事實上,今天所有學者都愿承認,他們發現任何時代總有一兩個哲人多多少少在踐行隱微寫作。我們將看到,幾乎不可能否認這種現象,因為在哲學傳統中如此廣泛地存在著隱微寫作的證據,以致學者幾乎在任何地方最后都能發掘出能證實這一實踐存在的細碎證據。然而,面對這些發現,典型的回應是宣稱,雖然隱微主義真實存在,但這種少見、古怪和不尋常的做法只出現在某些偶發的、異常的情況中。這樣,我們常常在確認隱微主義存在的那一刻就放棄了對它的繼續追問。這是我們拒斥這一真實現象的最常見方式。
重復一遍,曾經廣為人知,如今卻被遺忘的現象或觀念是:在歷史的大部分時間中,哲學式隱微主義并不是稀奇的例外(exception),而是慣例(rule)。隱微主義是哲學生活近乎恒定的伴奏,它像影子一樣跟隨著哲學生活。再者,正因為隱微主義并非源自某些偶發的、異常的情況,而是在某種程度上源自哲學自身與實踐世界的關系中所固有和不變的性質,源自“理論與實踐”的難題,所以,隱微主義具有相應的普遍性。
問題是:隱微寫作是奇特的神話,還是被莫名遺忘的真理?
三
向大多數學者令人信服地證明哲學式隱微主義的存在,是一項艱巨的任務,這至少有兩個原因。其一,作為一種秘密行為,隱微主義就其本性顯然抗拒公開而明確的揭露。有關它的大多數證據,其清晰性可能遠非完美,因此要求研究者具備高度敏感、良好判斷和同情心。其二,對如今大多數人來說,隱微主義作為秘密行為,同時也是某種異類、有欺騙性和精英主義的行為,喚起的是正好與上述必要情操相反的感情。因此,為隱微主義召開它所特別需要的公正而具有善意的聽證會(hearing)在當下十分困難。
考慮到上述的諸多困難,特別是證據的不確定性,我們顯然必須謹慎地面對隱微主義這一議題,每次只討論一名哲人。這樣我們可以盡可能細致地篩選證據,并把這些證據置于歷史語境中,在二手文獻的幫助下評估它們。這項工作已持續了一段時間,進展緩慢,但成果扎實。
這種“每次只討論一名哲人”的學術進路,雖說必要,難免也有缺點。它需要得到與之截然相反進路的引導和補充,即在其完整的理論和歷史范圍內,展示隱微主義的整體現象。這就是我的用力所在。因為,如果只在某個特定哲人的語境中審查與之相關的[隱微主義]證據,不論審查多么仔細,證據往往還是會顯得十分模糊。但是,當我們把其他思想家那兒類似的證據與之相聯系,這些證據便能呈現出新的內容。在個別作品的層面,我們會看不到宏觀層面上的諸種樣式。
進一步說,透過這種提綱挈領的視角,我們可以看到隱微主義的實踐如何隨著時間而變化,同時也會看到其中不變的和本質的東西,看到它潛在的基礎和統一性。最后,重要的是認識到,一個人對隱微主義問題的判斷,根本上并非不需要他物進行支撐(freestanding)。與判斷力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是更宏觀的世界觀,是對哲學真理和政治生活的本質及兩者間互動方式的深刻認定。因此,令人信服地論述隱微主義,最終需要一種能處理(address)這些深刻認定的宏觀哲學敘事。這要求一次庫恩式(Kuhnian)的范式轉移。
所以,為了更全面地認識隱微主義,我主要采納三種形式的證據或論證。第一,在實證層面,我將提交明確的“證人證詞(testimonial evidence)”:不同的歷史時代中,哲人們對自己或他人作品中使用隱微書寫的公開指證,這類指證數以百計。這類大量的實證證據,是余下論證的基礎。
第二,在哲學層面,我嘗試解釋上述的驚人指證:是什么原因導致不同時空中的眾多哲人,都從事了這項古怪的行動?我將仔細探究,那些激發了諸種哲學式隱微主義的永恒哲學課題,即思想與生活、哲學與社會、理論與行動之間的根本性緊張和矛盾。
但在第三個層面的分析中,我們有必要感謝最初提及的歷史事實:隱微主義已被我們遺忘。這一引人注目的事件為本節初始的提議提供了有力證據:在某種意義上,現代的世界觀對隱微主義抱有強烈厭惡,而這并不容易被前兩個層面中的事實和解釋所消除。由此,有必要把目光轉向我們自己,轉向被稱為“自我認識的層面”,并試著識別、處理和克服抵抗隱微主義的文化根源。
畢竟,事情有其光明的一面。一個曾真切失落的大陸在我們時代被重新發現。盡管困難重重,一片嶄新的、尚待開發的領域突然展現在我們這個令人膩煩(jaded)、沒有新鮮感(seen-it-all)的后現代世界面前,有志之士將在這個幾乎未被涉足的研究領域中做出許多開創性工作。我們需要重新討論一些重大議題,如哲學真理與政治生活的關系、出版哲學著作的用意、觀念在歷史中的作用、哲學教育的真正性質、現代“進步-哲學”被遺忘的前提條件(premise)和其他許多重要問題。西方哲學思想的整個歷程,并非我們長久以來所理解的那樣稀松平常和大局已定。在尋常的外表下,它勇于冒險,重視原創,生機勃勃。
“聽著,隔壁有一個絕然美好的宇宙;一起上路吧。”
——卡明斯(E. E. Cummings)
? 本文譯自梅爾澤(Arthur M. Melzer)Philosophy Between the Lines:the lost History of Esoteric Writing,是該書前言。梅爾澤系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政治科學系教授,及“科學、理性與現代民主研討會”的主辦者與負責人之一。除本書外還著有《人類的自然美德》等十數部專著。
? 歌德給帕森(Franz Passow)的信, 1811年10月20日,見《歌德的書信和寄給歌德的書信》(GoethesBriefe und Briefe an Goethe, ed. Karl Robert Mandelkow, Translated by Werner J. Dannhauser, Munich: Beck, 1988),卷3頁168。
? 科耶夫,“朱利安皇帝與他的寫作技藝”(“The Emperor Julian and His Art of Writing”),見《古代與現代:為紀念施特勞斯而作的論政治哲學之傳統文集》 (Ancients and Moderns: Essays on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Honor of Leo Strauss, ed. Joseph Cropsey, trans. James H. Nichols J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4),頁95。
? [譯注]作者用“亞里士多德們”指代“哲人們”,用“莎士比亞們”指代“詩人們”。
? [譯注]“非法地下酒吧” (speak-easy)誕生于美國禁酒令時期(1920-1933),其時販賣酒水屬于非法,但仍能通過這樣的地下酒吧或地下組織買到酒。 speak-easy的名稱得自于前去買酒的人需要輕聲說服看門人讓他們進去,而看門人的責任則是過濾看起來像是禁酒探員的人。
? 持守著“秘密” (secrecy)的個體自由這個概念常常給我們帶來有悖常理的第一印象,因為對此我們更容易聯想到的是“公開” (openness)和“透明”(transparency)。由政府所操持的守密是一種對自由的威脅,這點誠然屬實。而當我們思索個體行動時,難道我們不會更加珍視“隱私權”——亦即“守密權”嗎?如果我們是全然透明的,如果別人可以輕易地閱讀我們的信件、進入我們的電子郵箱,并竊聽我們的電話,我們便會感到我們的自由瀕臨險境。總而言之,個體自由與某些能夠在政府與公眾面前隱藏自己的能力是不可分割的。
? 見斯科特(James C. Scott), 《統治與抵抗的技藝:隱秘的書寫》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此書的題記和主題便是前述的埃塞俄比亞諺語。這部卓絕而振奮人心的著作研究了被統治群體用以悄然維護他們自身獨立性的無數方式,無可回避地指向(作者對此了然于胸,卻又有些許不安)施特勞斯式的論點,即哲學式隱微主義。本書的注釋中提到:“寫就了西方政治哲學的政治環境,只為思想的透明留有極少的余地”。
? 對此觀點,有個強有力的例證來自于一個意想不到的角度,可見于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這位出色的文學評論家關于莎士比亞的最新著作。幾乎無人否認,格林布拉特對于某位作者遭受著來自于其所身處時代的各種束縛的見識不遜于任何人。就像他在著作首頁中所強調的,莎士比亞“終其一生作為臣子受君主約束,他所處的社會等級森嚴,政治呈現于言談和出版中”。然而,格林布拉特以其書名《莎士比亞的自由》 (Shakespeare’s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巧妙地論證道,在閱讀時若能鑒別其中的反諷以及農民式的狡猾,那么就能看見在莎士比亞筆下其自身便是“人類自由的化身”。作為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t School)的開山鼻祖,這部著作卓絕地廓示并頌揚了莎士比亞超脫于時代的非凡自由。
? [譯注]神智論來自古希臘語“神(theo)”和“智慧(sophy)”兩個詞,通常指探索人與宇宙或神關系的神秘哲學思想,其三個目標是形成一個超越于種族、宗教和社會階級的普遍的人類兄弟情誼;研究傳統宗教、哲學和科學;探索自然法則以開發潛藏在人類中的神秘的精神力量。





也許部分地考慮到這種情況,施特勞斯實際上更偏愛談論“顯白主義 (exotericism)”而不是“隱微主義”。對施特勞斯來說,如果一本書既包含一套外在的、“顯白的”教誨,同時隱藏在其之下有一套秘密的、“隱微的”教誨,那它就是一本“顯白的書”。而一本“隱微的書”則用相對公開(但不是完全公開)的方式呈現秘密教誨。參見施特勞斯,《迫害與寫作藝術》,前揭,頁111和頁111的注釋45,以及氏著, 《什么是政治哲學?》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Glencoe,IL: Free Press, 1959),頁273。施特勞斯的用法讓人稍有困惑,所以筆者在此遵循更常見的用法,即如果一本書同時擁有表面和隱藏的教誨,那它就是一部“隱微的”的作品。
另一個要提及的術語問題是:當表達“隱微的”和“顯白的”時,不存在本質的或通用的術語。在不同的場合下, “隱微寫作”有許多不同的表達方式,包括寓意文學(Aesopian literature)、深奧寫作(acroatic or acroamatic writings)、雙重學說(double doctrine)、兩重學說(twofold doctrine)、兩重哲學(twofold philosophy)、善意的欺騙(pious frauds)、高貴的謊言(noble lies)、治療性謊言(medicinal lies)、真相的節約(economy of truth)、秘傳教規(disciplinaarcani, discipline of the secret)、謎一般的寫作(enigmatical writing)、自衛式嘲弄(defensive raillery),等等。

但是,正如我一直強調的,讀者不能忘記還存在其他形式的隱微主義。而且,這些形式不僅彼此不同,其隱微程度也各有深淺。舉例來說,啟蒙時期的政治式隱微主義相較于古典的隱微主義,可以說其隱微程度不夠徹底:前者的隱蔽性較低,更多是權宜之計或作為過渡,且動機狹隘;而后者有較高的隱蔽性,與哲學之間存在更恒久或更本質的聯系,其用途更廣泛,同時結合了自衛式、保護式和教學方法式隱微主義的動機。因此,雖然筆者對“隱微主義”的界定相當寬泛,但依舊認為古典的隱微主義才是最完整意義上的隱微主義。



編輯/黃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