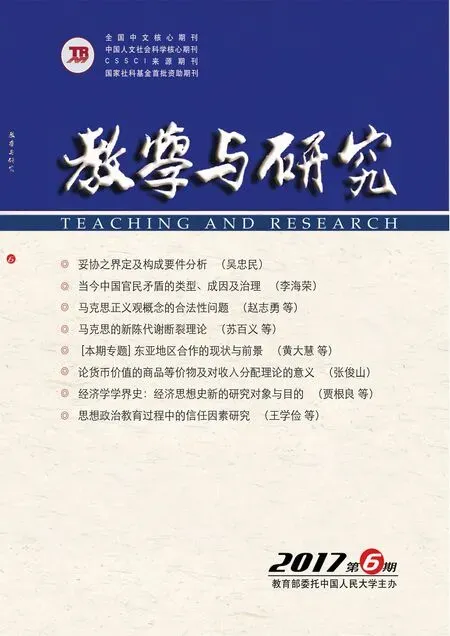勞動與工作,可以是“政治的”嗎?
——阿倫特《人的境況》批判解讀
文 兵
?
勞動與工作,可以是“政治的”嗎?
——阿倫特《人的境況》批判解讀
文 兵
勞動;政治;工作;阿倫特
阿倫特對勞動、生產與(政治)行動在概念上進行了嚴格區分,認為勞動只表明了人類與動物的共同之處,因而與政治自由無關;而生產過程是離不開“目的—手段”范疇,也必然與政治自由的特性相抵牾的。她對馬克思提出了相應的批評。從根本上來說,阿倫特概念分析是反歷史的,她要求回到古代希臘的原初政治經驗中去,即在政治中排除勞動與生產。這不僅與古代希臘的真實歷史相違,而且其理論自身亦有不少謬誤。
阿倫特在1958出版的《人的條件》一書,認為人類的“積極活動”包括了勞動、生產和行動,它們一起構成了人類生活的條件。她對這三個概念進行了著名的區分。她認為,勞動是與人體的生物過程相應的活動,提供的只是生存所需的消費物品;工作則是與人的非自然性相應的活動,提供的則是“人造”的事物世界;行動是直接在人與人之間進行的活動,創建了人們政治生活的公共空間。阿倫特認為,在古代希臘,只有行動,即政治生活,才被視為人之為人的特性。不僅如此,勞動、工作都是不能納入政治之中的。但是,現代的思想顛倒了全部的傳統,顛倒了積極生活之中的各種活動的等級。阿倫特認為,古代希臘的原初政治經驗才是政治概念的本真意義,而現實的一切都是遠離它而去的。阿倫特長于概念的分析,她在概念上對勞動、工作與行動進行了嚴格的區分,對于思維的嚴謹來說是必需,但概念的嚴格區分絕不是現實的絕對對立。但可惜的是,雖然她提出了極有意義的問題和極有啟發的思想,但用概念去剪裁現實、用概念的關系去取代歷史的邏輯,必然使理論難以令人信服。阿倫特的政治哲學最近二三十年來在西方又重新引起了人們的關注,而《人的境況》是其最為哲學、最為系統的一部著作,值得我們對其進行必要的考察。
一、勞動與政治
阿倫特在談到馬克思的勞動理論時,曾有這樣的判斷,認為馬克思對于勞動充滿著“頌揚和誤解”,而他的頌揚基于他的誤解,即“根本沒有看到人類生活的最根本的現實”。[1](P113)這個最根本的現實,在她看來,就是政治行動所特有的“自由”。她進而斷言:馬克思“對自由或正義并沒有興趣”。[1](P12)應該說,馬克思對于勞動(也包括阿倫特所區分的“工作”)確實充滿著“頌揚”。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把勞動規定為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并提高到人的本質這一高度。雖然馬克思其后放棄了費爾巴哈式的人本主義的表述,但一直是把現實的生產勞動視為社會生活的根本內容和人之為人的本質屬性。馬克思恩格斯說得很清楚:“一當人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人本身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2](P22-23)阿倫特也很清楚地表達了這樣的看法:馬克思是在勞動中看到基本的人性,而這就使他與傳統區別開來,因為“傳統總是排斥勞動,認為勞動和完整而自由的人類存在互不相容”。[1](P112)因此,阿倫特聲稱,將人界定為勞動動物(animal laborans),馬克思是第一人。我們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當馬克思提及“勞動動物”的時候,并不是在肯定的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而恰恰是在否定的意義上,也就是在勞動異化的意義上來使用這個概念的。我們可以看到,這正是他在批評國民經濟學時所說:“國民經濟學把工人只當做勞動的動物,當做僅僅有最必要的肉體需要的牲畜。”[3](P125)阿倫特則認為,在古代希臘人看來,勞動并不是人的特性,“人與所有其他類型的動物生命共有的東西,都不被看成是屬于人的”。[2](P62)“勞動”與“動物”是可以直接劃上等號的。阿倫特雖然說這是“古代希臘”的觀點,但確實也是她所維護的。但這樣一來,從邏輯上來看,阿倫特就有些混亂了:勞動既然不被看成是屬于人的,何以列入到人的“積極生活”的三種形式之中呢?
阿倫特把勞動與行動對立起來,把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嚴格劃分開來,宣稱:“在希臘政治意識的根底處,我們發現這兩種生活的區分得到了無與倫比的清晰闡述。所有只服務于謀生或維持生命過程的活動,都不被允許進入政治領域。”[2](P22-23)阿倫特的“政治”概念與我們的理解不同,她是在古代希臘所理解的“政治”概念上加以使用的。她認為,在古代希臘,“政治”與“城邦”具有相同的意義,指的就是城邦的公共生活。但是,不論她如何理解,這種對立在事實上并非古代希臘的政治經驗。普魯塔克對于梭倫有這樣的記載:“他看到本國土地只能維持耕種者的生存,不能維持大量沒有生業的閑人,因此,他把一切行業都看得很高貴,要元老會議檢查每一個人的謀生之道,懲罰沒有行業的人。”[4](P190)從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古代希臘的實際的政治經驗中,生計、謀生、勞動就是政治的問題。在一百年后的雅典由盛轉衰的關頭,在面對伯羅奔尼撒人的入侵時,伯里克利就是這樣來動員他的人民:“一個人在私人生活中,無論怎樣富裕,如果他的國家被破壞了的話,也一定會牽入普遍的毀滅中;但是只要國家本身安全的話,個人有更多的機會從私人的不幸中恢復過來。”[5](P145)在伯里克利這里,保護國家的安全,是人們利益所在,城邦政治關乎著人們的生計、謀生和勞動。阿倫特對伯里克利演說的實質卻是這樣的闡發:“在伯里克利的表述中十分清楚的是……行動和言辭的最內在意義與成敗無關,與最終結局無關,也不受效果好壞的影響。”[2](P161)按她的說法,伯里克利訴諸“偉大”就可以把雅典民眾煽動起來。可以說,這樣的說法,完全是反直覺的。在古代希臘,勞動并不是被完全交付給奴隸。按照艾倫·伍德的研究:“歷史學家通常都贊成大多數雅典公民為生計而勞動的觀點”。[6](P185)雖然希臘城邦完全符合“奴隸社會”的特點,但自由勞動者仍然是雅典民主的支柱。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第七卷第四章中,就曾探討過以農民或以牧民為城邦主體的各類“平民政體”。如果人數遠遠超過奴隸的為了生計的自由勞動者,在他們的政治討論之中根本不涉及利益,不涉及生計、謀生和勞動,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我們為了分析的方便,可以將出于生計的勞動與出于政治的行動進行概念上的區分,但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在現實中將兩者截然分開,把兩者當成“截然有別、獨立存在”的實體。阿倫特只是承認了勞動是政治的前提,但就是不承認勞動也是政治的議題。阿倫特就是要反對政治的功能化,也就是反對政治為經濟服務。因此,她就反對“政治經濟學”這樣的提法,認為它就是一個矛盾的術語,因為,任何“經濟的”事情,即與個人生命和種族繁衍有關的一切,都是非政治的。
二、政治與經濟
政治是否可以與經濟脫離開來?經濟領域中的剝削、貧困、分配不公等,是不是一個政治的問題?艾倫·伍德有一個批評:把政治與經濟脫離開來,正是資本主義的發明,而這一發明也是使“政治”更好地為“經濟”服務。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社會經濟的不平等是由政治所造成的,生產者遭受著“超”經濟力量的剝削。而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者遭受著獨立于其政治地位之外的“純”經濟力量的強制,這就造成人們這樣的一個印象: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中,人們在社會經濟上的也就是實質上的不平等可以與在政治上的也就是在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共存,似乎經濟與政治可以脫離開來。在艾倫·伍德看來,這種脫離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任何經濟關系都是受法律保護的。經濟與政治的這種脫離,實際上是更加無視了生產與分配領域的剝削與壓迫。“資本主義制度中經濟和政治的分離,更確切地說,是政治功能本身的分化,將分化出來的功能分別分配到私人的經濟領域和國家的公共領域。這種分配將直接與榨取和占有剩余勞動相聯系的政治功能,與那些更具普遍性和公共性目的的政治功能分離開來。經濟的分離實際上是政治領域內部的分化,這種概括從某些方面來說更適于解釋西方發展的獨特過程和資本主義的特性。”[2](P31)法國著名經濟學家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認為“經濟科學”這樣的表述體現了極度的傲慢,因為這樣的表述暗示了它比其他社會科學更高的科學地位。他更喜歡“政治經濟學”這樣的表述,因為這樣的表述“傳遞了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唯一區別:其政治、規范和道德目的。”[7](P592)他宣稱,政治經濟學從一開始,就是在研究一國的經濟和社會組織中國家的理想作用,要解決的是何種公共政策和制度可以引領我們更加接近理想的社會。
阿倫特認為,如果經濟與政治兩者的界限模糊了,會導致嚴重的后果,那就是政治組織會依照家庭形象建立起來,如此一來,必然使可以自由行動和言說的政治空間喪失。古代的“一人統治”的君主制(one-man ,monarchical rule),正是按家庭的方式組織起來的,其表現形式正是只有一人觀點、一人利益的專制主義和絕對主義。這種“一人統治”君主制后來又轉化為“無人統治”的官僚制,但這種官僚制可以說是“最殘酷最專制的形式之一”。[2](P26)因為這種制度期待它的成員遵從某一行為,并用過程規則來“規范”它的成員,進而消除各種自發的行為和出眾的成就。阿倫特對于勞動的輕視,根本地還在于勞動建立在人的同一性之上,抹煞了人的差異性。在她看來,正是在勞動中,生物節奏與集體勞動的統一,達到了這樣的程度:“每個人都感到他不再是一個人,而是跟所有其他人相連的一份子。”[2](P167)這也就是消除了人的復數性,而復數性正是政治的特性,因為政治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而更為重要的是,政治中的人,是一個獨特差異中的人,是在言說與行動中確證自己的。阿倫特的這個比附有些簡單了。在一些簡單的謀生勞動中,也是存在著分工上的差異。而在復雜的政治行動中,也應該存在著協同上的一致,這也就是阿倫特所說,政治行動中必須有人們聚集在一起“協同行動”(act in concert)。如果沒有這種“一致”,任何政治的目標都是達不成的。
阿倫特貶低勞動,還因為在她看來,勞動受生命必然性的支配,因而具有奴性,而行動則是具有偶然性的,因而就是自由的。她認為,政治行動總是具有不可預期性,具有開端啟新的作用。這里的問題是,政治領域是不是就不存在必然性?我們知道,長期以來,婦女就是被排除在政治之外,至少她們沒有與男性同等的政治權利。只有到了資本主義時代,婦女的政治解放才成為可能。“因為資本正在努力地把人們吸引到勞動市場,并把他們簡化為從所有特殊身份中抽象出來的可相互交換的勞動單位。”[6](P263)政治領域的必然性,其實就是政治領域的被制約性。馬克思講得很清楚:“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3](P699)這種“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正是人們政治行動中的必然。
三、工作與政治
阿倫特認為工作與勞動的區分很重要,但更重要的則是工作與行動的區分。她反對以工作來取代行動。因為,工作的制作過程完全是由手段與目的的范疇來決定的。目的不僅證明手段的合法性,目的還創造和組織手段。對于技藝工匠(homo faber)來說,目的證明了對自然施加暴力以獲得材料的正當性。阿倫特的推論是,如果以制作來解釋行動的政治規劃或思考,必然要把暴力置于核心位置。在現代的觀念之中,暴力本身受到了頌揚。在她看來,除美國革命之外的所有現代的革命,都是充滿著對于為新政治體奠基的熱情,也充滿著對于暴力之作為“制作”它的手段的頌揚。阿倫特對于暴力的使用及其結果,是極為警惕的。她對權力(power)與暴力(violence)等進行了區分,認為權力是公共領域得以存在的東西,因為“權力是從一塊行動的人們中間發出的力量,他們一分開散開,權力就消失了。”[2](P157)阿倫特對于“權力”的闡釋與傳統政治哲學很不相同。這個權力,在她那里,其實就是人們在言說與行動中展現出來的力量,是由人們“協同行動”所產生的力量。阿倫特接著指出,暴力很容易摧毀權力,但并不能代替權力。唯一可以取代權力的就是強力(force)。強力是一個人可以單獨用它反對他的同胞的,是可以由一個人或少數人通過暴力加以壟斷的力量。而一旦強力與暴力結盟,那就是出現“專制政體”。暴力雖然與革命有關,但是,暴力之被頌揚,則完全有可能導致極權政體,這正如她在后來的《論革命》中說的:“在暴力絕對統治之處……不僅法律……而且一切事物、一切人,都一定要陷入沉默。”[8](P8)她之所以對美國革命有較高評價,是因為在她看來,在美國的立國者眼中,“新政治體乃是為人民而設計”,而這個“人民”是復數的。因此,在美國的立國者那里,他們充分尊重不同意見之間的交流,沒有效仿法國革命者樂此不疲的對“公意”的追求,因而也就避免了法國那樣的“恐怖統治”。在她看來,讓語言交流沉默,讓復數的人消失,從根本上來說,是“制作”本身的特性。制作,就是個人“從頭到尾是他行為的主人”,“以制作代替行動的嘗試,體現在所有反‘民主制’的論證中,這些論證無論多么鏗鏘有力和首尾一貫,都會轉化成一種拒斥政治之本性的論證”。[2](P172)
“制作”,其實也就是“創造”,故而,阿倫特不同意馬克思關于歷史是由人們自己創造的觀點,因這種“制作”是以目的—手段的范疇進行思考的,除了導致現代以來的對于暴力的頌揚之外,還會衍生一種烏托邦的政治體制,因為這種烏托邦正是“一個由精通了人類事務技藝的某個人依照模型而造的”。[2](P177)這種烏托邦的構想,雖然鮮有成功,但卻構成了一種政治思想的傳統。我們在這里要探討的一個問題是:“目的-手段”范疇是否根本不可能存在于政治思考之中。
如果“創造”歷史的“人民”是一個現實的具體的主體,有著特殊的人格,有著自己的頭腦,有著清醒的目的,就像一個現實的具體的工匠一樣,那就真如“上帝”一般了。如果是這樣,阿倫特把“人們創造歷史”說成就如“上帝創造自然”一樣,這種比附就完全是可接受的。但是,這樣的“人民”事實上是找不到的,是不可想象的。就“人民”之中的每一份子來說,他在參與歷史活動過程中沒有自己的意識和目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人們在歷史活動中不追求自己的目的,言語表達就成了純粹的自說自話,而政治行動就成了純粹的布朗運動。事實上,“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3](P295)而且,在歷史過程之中,目的從來不是結果,人們像工匠一樣“制作”出預期的歷史結果,從不是馬克思所堅持的。正如恩格斯所批評的那樣,歷史活動中的許多個人的意志相互之間的沖突,“最后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9](P605)在這一點上,阿倫特也肯定政治行動一旦開始,這個過程的結果就是無法預料的。但是,這并不能否定每一個體或某些集團在政治行動中都有著自己的明確的目的。
按阿倫特的說法,在政治領域中,言說與行動僅是為彰顯行動者“獨一無二、與眾不同的身份。”[2](P142)而馬克思的基本錯誤就是忽視了這一點。按她的說法,如果不是彰顯行動者的這個“who”而只是他的“what”,即不是彰顯他的人格而只是他與其他人共有的屬性,行動就失去了它的獨特性質而變成了諸種成就之一,也就是變成了達到一個目的的手段,正如制作成為生產一個對象的手段一樣。她也肯定,在言語與行為中,人們必定會關涉到他們活動于其間的事物世界(阿倫特對勞動與工作的區分,最重要的一點是,勞動的產品直接進入了消費,沒有持久性,因而是“無世界性”,而工作的產品具有持久性,因而構成了一個“事物世界”),而正是從這個世界之中產生出人們特定的客觀的實際利益,但言語與行為仍然不失其揭示行為人的能力。我們要追問的是,言行與利益之間是一個什么關系?在她那里,兩者并沒有必然聯系,因為她反對政治的功能化。這樣一來,政治就完全漂浮在空氣之中了。
阿倫特反對政治功能化的這些思想,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又被人們所重視。很多論者認為,她的理論術語恰當地描述和解釋了自1989年“天鵝絨革命”以來的歷史事件和政治現象,即人們似乎只是“為了政治自由而戰”。[10](P106)這種說法,不僅是有些行動者所聲稱的,而且也是有些觀察者所描述的。但事實果真如此?所有的這些所謂的“革命”,皆是要實現明確的政治主張,要達成明確的政治目標,也就是要獲得所謂公民權利。哈維爾在領導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之前,就在其1977年作為政治鼓動即所謂“七七憲章”中,明確地宣示他們的“憲章”就是為了促進“公民作為自由人生活和工作的可能性的實現”。這里不僅有明確的政治目標,而且把“生活”與“工作”也上升到了政治的層面。
阿倫特非常看重政治行動所具有的開端啟新的能力,認為這個行動過程一旦開始就帶有不可預測、不可逆轉的復雜后果,因而是人們所不能主宰和把控的。這樣一來,政治行動中的人,似乎有一種存在的荒謬:既是自由(freedom)的但不是自主(sovereignty)的。她認為,這種荒謬,只是因為傳統思想將自由與自主相等同。阿倫特聲稱,在行動能力本身中就包含著某種潛能,可以讓它幸免于非自主的無能:對于不可逆性來說,則是給予寬恕的能力,它可以讓我們擺脫我們無法補救的后果,可以中止無休止的相互傷害行為;對于不可預見性來說,則是信守承諾,以契約和協定為中介把人們約束在一起,進而形成一個共同同意的目標。阿倫特關于寬恕與承諾這部分論述應該是最有價值的。就寬恕來說,雖然具有宗教的背景,但將它直接轉到政治領域,則是她的重大貢獻。她的學生楊-布魯爾聲稱:“自從1958年《人的條件》問世以來,阿倫特對于寬恕的思考直接或間接地產生了重大影響。”[2](P78)楊-布魯爾甚至認為,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成立就是她的思想影響的結果。就承諾來說,阿倫特則認為,它是人建設世界的能力,而美國人在革命行動中發現了正是“通過一項承諾,即憲法來確保自由的可能性。”[2](P88)她認為這是美國政治中的“最偉大的發明”。阿倫特認為,寬恕與承諾“就像是嵌入行動和言說能力的控制裝置一樣,開啟了全新的、無盡的進程。”[2](P191)更為重要的是,由嵌入了寬恕與承諾的行動和言說能力,賦予了人類事務以信心與希望,但是,“信心與希望這兩個作為人存在的根本特征,卻被古希臘人完全忽視了”。[2](P192)如果寬恕與承諾只是由政治行動開端啟新出來的“偉大發明”,給人以信心與希望,我們又何必一定要回到古代希臘的原初的政治經驗中去呢?
[1] 漢娜·鄂蘭.政治的承諾[M].臺北:左岸文化,2010.
[2] 阿倫特.人的境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M].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
[5]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M].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
[6] 艾倫·伍德.民主反對資本主義[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
[7] 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8] 阿倫特.論革命[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
[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 霍爾等.阿倫特手冊[Z].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責任編輯 孔 偉]
Can Labor and Work Be “Political”? ——A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TheHumanConditionby Arendt
Wen B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2249)
Labour; politics; work; Arendt
Arendt made a strict distinction between labour, production and political action. She believes that labor only shows the common ground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animals, and therefor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political freedom. The production process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means of purpose and consequently conflic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freedom. She made a corresponding criticism of Marx. Fundamentally, Arendt’s conceptual analysis is anti-historical. She required to return to the original political experience of ancient Greece, namely, to exclude labor and production in politics. This is not only on the contrary to the real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 but also has many fallacies in the theory itself.
文兵,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北京102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