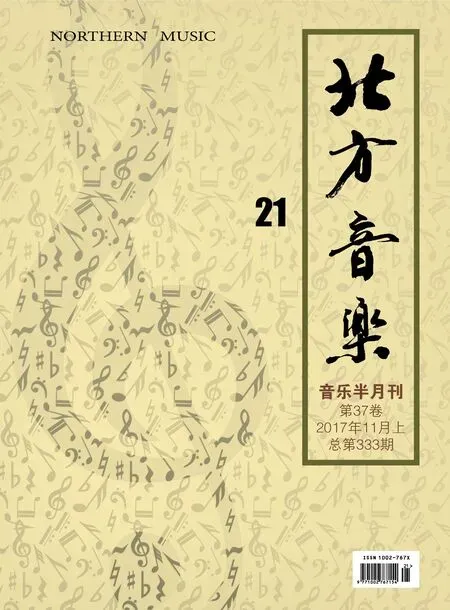樂以耀德,禮以節樂
——論春秋時期音樂美學思想對“禮樂”思想的影響
王達薇
(中國藝術研究院,北京 100029)
周王室東遷洛邑之后,王室衰微,諸侯稱雄,由此開始了近550年的分裂時期(公元前770年—前221年),史稱春秋戰國時期。其中春秋于戰國又以孔子卒年(前476年)左右劃分。孔子作為先秦偉大的思想家,從思想上明顯繼承了前人的觀念。因此,學者們在討論春秋時期音樂美學思想時,將其范疇定位于孔子其思想形成之前至王室東遷之后,即公元前8至6世紀,以此別于之后的百家爭鳴時期,體現出前者對于后者產生的借鑒意義。
上古時期,“和”是音樂美學思想的重要概念。先民們在生產活動中,追求心理活動與實踐活動上的和諧與平衡。“正是人在創造活動中獲得的心理上的諧和、平衡,使得人產生了對‘和’的美感追求”①。這是以人的歷史實踐活動方面來講的,也是探討此時音樂美學思想范疇的基石。及至春秋之時,音樂美學思想在諸多精英知識份子(宮廷諸官)的群智(即宮廷諸官的審美觀)中得以發展,綜合完善了先前的種種思想,形成了一套音樂美學思想體系。
禮樂思想伴隨著禮樂制度的形成而產生,源于上古祭儀及維系宗法之中,其要旨在于配合禮樂制度的實施,以教化臣民甚至君王,達至緩和階級矛盾和維護國家統治秩序的根本目的。這一時期禮樂思想上承上古三代之遺緒,且宮廷諸官又是主要實施者和繼承者,必然受到當時音樂美學思想的影響。
筆者認為,在這影響方面,最基本的是對禮樂思想特征及禮樂思想踐行方面的影響。對禮樂思想特征的影響又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對禮樂思想核心的影響;其二是對“禮”與“樂”關系的影響。
一、春秋時期音樂美學思想對禮樂思想特征的影響
禮樂思想特征集中體現于禮樂思想的兩個組成部分,即“禮”與“樂”二者相互配合以表征出禮樂思想的特性。因此,文章先以禮樂思想核心以及“禮”、“樂”間的關系來闡釋文題。
(一)對禮樂思想核心的影響——“樂以耀德”
何謂“禮樂思想的核心”?在《春秋》、《左傳》等古籍著作中記載春秋時期音樂活動、祭祀活動中,常將“德”、“禮”并提②。可見這一時期禮樂思想的核心是“德”與“禮”。
當時宮廷官員史伯、晏嬰的音樂審美觀認為在“德”的影響下,“和”是音樂的內在屬性,并提出“心平德和”的著名論斷。“夫和實生物,同則不斷”③這是史伯的著名論斷,他認為“和”是促進事務發展的內在動力。因此,他又緊接著談到“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這里講明了“和”的構成原則,即不同事物需經過各式各樣的組合搭配(所謂“以他平他”),繼而可以促進事物的發展(即“故能豐長而物歸之”)。所以,對于音樂,他認為“和六律以聰耳”,音樂內容形式上的美(按:音樂內容形式是指:一、音樂中樂音的組合,如節奏、旋律、調性、速度、強弱;二、音樂的創作背景、表現情感等)必須是以“和”為要旨的。
春秋齊相晏嬰發展了史伯的音樂審美觀,其云“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④他從構成音樂的具體要素論及,認為音樂諸多要素需要保持“和”的狀態,即“相成”、“相濟。”“……(接前)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暇’。”緊接著這里引出“心平德和”的論斷。
由此可見,從史伯、晏嬰的音樂審美觀出發能體現出“德”在音樂美學思想的重要地位。和諧統一的音樂使人達到“心平德和”的目的,“心平德和”自然也就與禮樂思想要旨相符了。與此同時,周王室里圍繞“景王造鐘”⑤而引發的爭論也體現了當時的音樂美學思想。主要是體現在單穆公與伶州鳩的音樂審美觀。從他們對周景王造鐘一事的勸辭中,可見其發展了“心平德和”的觀點,認為好的音樂不僅使人感到“心平德和”,還能夠讓人深深為“德”所教化。“于是乎道之中德,詠之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⑥正是說明了“德”的力量,它能使“神”安寧,使人民大眾服從統治。
對于“德”的闡述比較深刻莫過于季札與郤缺。他們明確說明了“德”是“和”的范疇中重要內容。季札音樂美學思想記錄在他出使魯國時“觀周樂”的儀式中。在此儀式中,他觀看這些表演樂舞后評論時,先前的節目皆以“美哉”作為嘆詞,如“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⑦唯獨到了最后一個節目(按:也可能是紀傳作者為了文學上層層遞進的脈絡而故意寫于最后)“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不載也,雖甚盛,其蔑以加于此矣。”以“德至矣哉”作為嘆詞、以天地用來比襯,亦能說明此樂舞的“德”的思想之廣遠,故他緊接著又說“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能請已!”
郤缺音樂美學思想體現于他與趙宣子的對話中。他說“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而后他闡釋了“九歌”的內容:“六府、三事謂之九歌。”而在“三事”中最重要的、首要的事是“正德”,所謂“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所以他認為“正德”是事物發展所應該追尋的方向。故此,“若吾之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⑧。
在此基礎上,師曠及子產明確言及“德”在禮樂思想的地位及“禮”在禮樂思想中的作用。師曠說:“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也,以耀德于廣遠也。風徳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⑨從他的言論可以看出“德”是禮樂思想重要特征,即“樂以耀德”。這是他基于民本思想,來追尋音樂的本性,即為“德和”。通過音樂美育,使人民群眾的思想境界得以提升,行為素質得到教養,同樣,也促統治者免于聲色犬馬的不良習氣,進而使社會風氣為之一振,以至于“遠服而邇不遷”的目的。
同樣子產曾言:“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趙衰也曾言到“……說禮樂而敦詩書。詩者,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禮之本也。”⑩這里亦能看出要求在音樂中體現出“禮”的約束性及“德”的內涵。
綜上所述,春秋時期音樂美學思想在“和”的范疇下顯現兩個重要概念,即為“德“、“禮”。與禮樂思想要旨相符相合,因此,可概括為“樂以耀德”。禮樂思想充分借鑒了這兩個重要概念,從而成為以后歷代政權在政治(宣傳口徑)上不斷追求完善的基礎之一。
(二)對“禮”與“樂”關系的影響——“禮以節樂”
“和”作為春秋時期音樂美學思想范疇,從具體細化講,是指一個“范圍”抑或是“規律”。規律與范圍表征出對事物的約束性。
師曠與子產曾明確談到了“禮”與“樂”間的關系。師曠言“修禮以節之”,認為樂教美育是優化社會風氣的重要方式,“禮”是節制人們精神活動的方式,音樂作為人類精神活動也必須受制于“禮”。子產言“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他認為禮制是天經地義的事,也是很自然的事。每個人必須以“禮”作為準則。基于民本思想,他們認為音樂是能影響到社會風化和國家安全的,俗樂(按:即所謂“鄭音”、“新聲”)會對其產生的負面影響,必須得到抑制,因此,為了避免國家上至統治者下至黎民百姓耽于聲色而不顧國家安危,故而提出“樂”必須受制于“禮”的觀點,筆者概括為“禮以節樂”。
此時,社會上流行陰陽五行的思潮,認為事物的最基本的元素是“五行”。音樂上,這種思潮認為音樂有“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等內容。史伯言“和六律以聰耳”認為符合“六律”的音樂能“聰耳”。晏子曾說“……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也認為協和的音樂是由這些內相成相濟而形成的。季札從“德”的角度談到“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同樣認為“五聲”、“八風”要“和”、要“平”,有“節”、有“度”才能達到“盛德”的境界。醫和在問晉平公疾病中也曾談到音樂有節的問題。針對晉平公喜聲色之娛的特點,他說“天有大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他以“六氣”、“五味”、“五色”、“五聲”等具有陰陽五行思想來解釋晉平公病根所在,即“淫生六疾”,晉侯喜新聲,“繁乎淫聲、慆湮心耳”不是“五聲”范圍內,勢必對身體不利。子大叔與趙簡子關于禮的問答中也體現了這一思想。“生其六氣,因為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他認為“五味”、“五色”、“五聲”皆“生用”于六氣五行,如果超逾了這一范圍,則會“民失其性”威脅國家統治和安全。
由此看出,春秋時期音樂美學思想要求音樂必須有“節”、“度”才能被認作“和平之音”,“盛德”的音樂。音樂不可以逾出“和”的限制,這樣的話可以政通人和,百姓不知其性,心平德和安居樂業。“禮”自從古來就是實行教化約束的方式,并在具體實行上與音樂相配合。這時的音樂家與思想家出于鞏固統治秩序、關系百姓蒼生存亡的角度,要求音樂本身也要受到禮的制約,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音樂的美,即“德和”,更有利于保障音樂的教化作用。因此可謂之“禮以節樂”。
綜上所述,春秋時期音樂美學思想對禮樂思想特征的影響,體現在對禮樂思想核心的影響和對“禮”與“樂”間關系的影響兩方面。受此影響,禮樂思想的核心有了“德”與“禮”的重要概念,構成了禮樂思想特征的基礎。在此基礎上,思想家與音樂家更是闡釋了何為美的音樂。美的音樂是受制于“禮”的,音樂與禮制約配合,凸現了音樂的教化功用,也為后世提供了借鑒的范本。
二、春秋時期音樂美學思想對禮樂思想踐行的影響
當時音樂美學思想多體現與宮廷諸官與統治者間的對話當中,大多談及政治道德與倫理觀念。禮樂思想的宗旨即是配合禮樂制的實施以維護國家穩定,緩和階級矛盾,鞏固等級制度。所以,音樂美學思想對禮樂思想的踐行的影響是無處不在的。
從史伯、晏嬰,到師曠、子產,到季札、郤缺,到醫和、子大叔,再到單穆公、伶州鳩,從他們的音樂美學思想可以看到這樣一個模式:音和——心和——人和——政和?。先由音樂談起,再談到具體個人的內心反應,最后引申到政治道德和倫理觀念的層面上來。
以單穆公與伶州鳩在反對景王作鐘一事的勸辭先來看。他們先從聽覺感官(樂理、音質等)的和諧談及,論述了無射鐘受其本身限制必會對“心”和“人”產生不利影響?。接下來,他們又擔心到國家國力和社會風氣會因此產生不良影響——“無益于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那么,究竟什么是美的音樂呢?所謂“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未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因此,美好的音樂必須是和諧的,即為“音和”;這會對人的心智乃至身體產生強烈的感化、調教的作用,即為“心和”;使人與人和諧相處、上下級(臣民與君王、屬下與主人、晚輩與長輩等等)和諧融洽,即為“人和”。在此基礎上,單穆公曾說“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伶州鳩言“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于教而離民怨神,非臣所聞也。”?認為國家命運和天下蒼生是政治道德所承載的內容,從此出發,通過“音和”、“心和”、“人和”而一步步追求著“政和”的理想。
季札在欣賞《韶箾》后,發出“德至矣哉”、“不請他樂”的感慨,可以看出他對遠古舜帝的治國思想高度贊揚和推崇,進一步體現了季札“德”的政治觀。
師曠與晉平公的對話亦體現了他的政治觀。他曾說“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認為“德”而“節”是讓“遠”、“邇”(按:“邇”即“近”)服于統治的前提。
子大叔“為禮以奉之”的審美觀也說明當時政治道德與倫理觀念恐陷入“淫則昏亂,民失其性”的境地,而針對性的提出“為禮以奉之”,簡明了當地表明了音樂審美觀對禮樂思想踐行的影響。
春秋時期音樂美學思想對禮樂思想踐行方面的影響,體現于對時下政治道德和社會倫常的影響。無論統治者還是臣民,樹立正確的、高尚的政治道德觀念和社會倫常觀念,是禮樂思想之所追求。故此,受當時音樂上的美學思想影響,宮廷之中的有識之士紛紛要求音樂發揮其教化作用,與禮制相互配合,為國家穩定繁榮、社會安定發展、人民安居樂業而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這也是禮樂思想踐行的要旨。
如上所述,春秋時期音樂美學思想對禮樂思想的影響,體現于兩方面,一是對禮樂思想特征的影響,可概括為“樂以耀德、禮以節樂”;二是對禮樂思想踐行的影響。在此之上,禮樂思想形成了以“德”、“禮”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在此體系中,音樂與禮制為此組成要素,相互配合,更好地發揮出禮樂制度的功用。因此,禮樂思想在踐行中亦受音樂美學思想的影響。可見,這一時期的音樂美學思想對禮樂思想的影響,產生了深遠影響。
三、對禮樂思想影響中表征出的意義
春秋時期音樂美學思想對禮樂思想影響,其意義可從兩個層面展開討論,一是承上,二是啟下。
西周周公旦“制禮作樂”,從此禮樂思想也正式誕生,但此時受社會各因素影響制約,其思想內涵尚待完善。至于春秋時期,奴隸制開始衰落,音樂上的美學思想也開始被當時知識分子所關注和探討,由此產生了“和”的音樂美學思想。受其影響,禮樂思想在繼承的基礎上又豐富了其思想內涵,即繼承而發展,也就是“承上”的意義。
及至春秋末期的孔子,將禮樂思想、禮樂制度推崇到了極致。究其本源,他的禮樂思想亦是在繼承前人(尤其是春秋時期宮廷諸官)禮樂思想之內涵的基礎上、以及春秋末期“禮崩樂壞”的現實,而發展和完善并且自創學派躬親踐行的。這就表征出“啟下”的意義。春秋時期的禮樂思想是中國禮樂思想首次充實和豐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后世禮樂思想以及禮樂制度的完善和踐行。從此角度看,這一時期的音樂美學思想對禮樂思想的影響可謂深遠。
注釋:
①修海林.中國古代音樂美學[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97.
②吳毓清.禮樂思想的早期形態——從《左傳》、《國語》看春秋時期音樂美學思想[J].音樂藝術,1983(3):11—12.
③本文所引史料凡是來自修海林編著《中國古代音樂史料集》(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9年第1版)的,均做出注釋,并簡稱“《史料集》”.此史料為《國語·鄭語》,載《史料集》第39頁.
④摘自《左傳·昭公二十年》,載于《史料集》第32至33頁.
⑤“景王造鐘”——史載,公元前522年,周王朝的國君周景王想造一套名叫“無射”的大型編鐘,因此向單穆公、伶州鳩征求意見,他二人一是擔心到國家國力和社會風氣會因此產生不良影響,二是認為無射編鐘之中的“大林”鐘音域過低,極不和諧,容易對人的心智、身體產生不利影響.而周景王不納諫,依然命人造好了這套鐘,結果他在兩年后便去世了,后來史官對些事所做之結論是:這套鐘果然不和諧.
⑥摘自《國語·周語下》,載于《史料集》第37頁.
⑦摘自《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于《史料集》第32頁.
⑧摘自《左傳·文公七年》,載于《史料集》第29頁.
⑨摘自《國語·晉語八年》,載于《史料集》第39頁.
⑩摘自《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載于《史料集》第33頁.
?摘自《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于《史料集》第32頁.
?摘自《左傳·昭公元年》,載于《史料集》第32頁.
?修海林.中國古代音樂美學[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141.
?修海林先生認為,“‘大林’音域過低,撞擊后聲波中各種泛音使人聽之不和諧。”參見修海林《中國古代音樂美學》,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140頁.
?摘自《國語·周語下》,載于《史料集》第36至37頁.
?摘自《國語·周語下》,載于《史料集》第36至37頁.
?摘自《國語·周語下》,載于《史料集》第36至37頁.
[1]蔣孔陽.先秦音樂美學思想論稿[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2]蔡仲德.中國音樂美學史論[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8.
[3]大可.論先秦禮樂的發展變遷及其思想作用[J].黃鐘,1994(04):36-39.
[4]胡健.論先秦音樂美學思想的爭論與融合[J].音樂探索,1997(04):3-8.
[5]夏滟洲.先秦音樂審美范疇“和”之認識與推衍——兼及對先秦音樂思想史研究的思考[J].交響,2005(03):22-26.
[6]修海林.中國古代音樂史料集[M].西安: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9.
[7]曹玲玉,張碧霞.先秦音樂思想的倫理審視[J].樂府新聲,2009(02): 55-57.
[8]楊輝.先秦禮教與樂教之關系及地位變遷考[J].保定學院學報,2009(05):65-68.
[9]聶濤.季札與先秦禮樂思想[J].文化研究,2009(12):242-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