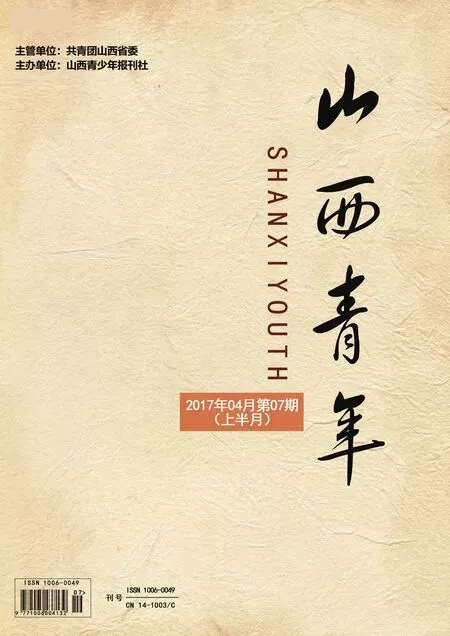阿Q形象的典型意蘊與視角結構特點
楊 航
黑龍江外國語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0
?
阿Q形象的典型意蘊與視角結構特點
楊 航*
黑龍江外國語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0
魯迅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魯迅創造了獨特的對向視角使典型人物獲得了新的意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使魯迅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據了時代的制高點。
民族性;阿Q;對向視角
五四以來,小說正是因為與現代民族國家建設聯系在了一起,才逐步確立了以“典型論”為主導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也正是在民族國家訴求中,底層才獲得了一種道義上的力量。然而魯迅塑造的阿Q形象不僅如此,魯迅又昭示或暗合了后來的現代主義文學的文學機制,對“世界”及“民族想象共同體”所謂“國人”的普遍質疑,使他放棄了傳統現實主義文學中固有的批判的正當性,使阿Q形象在塑造中形成一種喜劇或者反諷的效果。
阿Q作為一個“個體”生存在社會上,幾乎面臨一切生活的困境,連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不斷加強的中國,我們可統稱為“底層”。個人乃至社會的每一次的變革都好似痛苦的掙扎,但又總是陷入絕望的輪回當中。而當時的中國人經常使用“精神勝利法”安慰自己。使自己屈服于現實,進而成為現實的奴隸。國民的麻木與冷淡成為阻礙中國進步的最大精神障礙。魯迅正視這一問題,對其進行猛烈的批判,在這一點上,魯迅和許多五四知識分子并無不同,所謂啟蒙民智是也,然而魯迅的意義顯然不止于此,魯迅顯然不是站在超越的位置上去俯視蕓蕓眾生,正如阿Q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喜劇人物。
阿Q是一個社會底層“三無”人員,即“無名”“無姓”“無籍”。阿Q無論是與趙太爺、假洋鬼子,或是和自己同為底層的王胡、小D的沖突中,無一例外的充當著失敗者的角色。甚至是在賭博中贏錢后,仍會被暴打。但是,他卻對自己的失敗和奴隸地位采取了令人咋舌的辯護態度即“精神勝利法”。例如,在阿Q贏錢被暴打搶錢后,回到土谷祠的他,竟然“用力的在自己的臉上打了兩巴掌,仿佛是自己打了別個一般”。通過這樣的方式去滿足自己的“自尊心”讓自己心平氣和、天下太平。
阿Q自始至終都不承認自己的地位低下和被欺辱、被奴隸的事實。相反,他始終沉浸于自我臆想的思維中。“精神勝利法”實則是魯迅對民族的自我批判。然而對“國民性批判”的理解則不能僅僅停留于書面解釋以及文本內容傳遞給讀者的直觀感受,對于阿Q的閱讀必須擺脫“形式的閱讀”,《阿Q正傳》創立了獨有的一套藝術體系,從文本的語言結構、語言產生的社會背景、表意本體論等多方面因素進行深入的研究。只有這樣,讀者方能超越普通閱讀的直觀性,從而進入一種癥候閱讀,進入到開放性的逐步突破而非逐步還原的文本研究中。
與19世紀盛行的批判現實主義不同,阿Q的形象,不同于以往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阿Q是中國傳統文化價值想象崩塌的環境下誕生的。某種程度上來說:“阿Q就是中國”。而“精神勝利法”歸根到底是語言問題,把比自己強大的對手稱為“兒子”,被打后又稱自己為“老子”。“精神勝利法”雖說在心理學上無足輕重,但從另一個側面也能反映出當時中國人麻木避世的心理。從共性方面看,阿Q的“精神勝利法”集中地反映了舊中國整個國民的劣根性,這種劣根性是長期的封建文化中消極因素的沉淀與鴉片戰爭以后出現的失敗主義相結合的產物。
阿Q的革命,實則是“落后階級”革命的思想。阿Q向往革命,渴望改變艱難處境的強烈愿望,也是具有廣泛的代表性的,可以說是生活在黑暗的舊中國的廣大貧苦農民的共同心聲,然而顯然,這里又包含某種“剩余”,因為資本的邏輯早已滲入,只是在意識層面尚未自覺。從個性方面看,阿Q的心理活動又總是與他的社會地位、生活環境、思維方式有機地聯系在一起的。喜歡自夸也許是舊中國國民的共同弱點,但自夸的內容卻是各不相同的。地主、資本家以錢財傲視他人,官僚們以權勢地位傲視他人,知識界也可以知識傲視他人,然而所有這一切與阿Q無緣,他一無所有,也一無所知,就只好拿“先前”來傲視他人。
阿Q的革命態度也充分體現出前現代的狹隘性和歷史循環論的特征。在阿Q的思想中,革命目的不是進步而是為了報復和索取,對未莊欺負他的人的態度是一概殺掉;而在對錢財的態度上是大把拿盡,無盡的索取。“元寶、洋錢、洋紗衫,秀才娘子的一張寧式床先搬到土谷祠……讓小D去搬,搬的不快打嘴巴。”這充分體現出阿Q的報復心態。這是一種落后的革命觀。阿Q的革命,既表明了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不徹底性,也顯示出農民作為革命主體的重要性與局限性,這些方面的錯綜復雜被小說結構表征得淋漓盡致。
當阿Q被正法后,圍觀的人群卻并不滿足,竟然認為阿Q沒有唱一句戲文,“槍斃沒有殺頭好看,他們白跟了一路。”人們非但沒有惋惜一個人就這樣不明不白的被處決,反而是將生命作為玩笑去打趣。用拉康的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來看,人們的冷漠與麻木恰恰提供了一個“他者”的視角,他者是主體無意識的場所和主體無意識構成本身,圍觀者恰恰為主體提供了一個透明化的對向視角,而這種對向視角在現代主義文學中是通過第二人稱敘事達到這一功能的,而魯迅則是通過第三人稱他者象征達成了這一敘事功能。阿Q“大團圓”的結局,既是他個別主體的悲劇,也是辛亥革命革命主體的悲劇。
《阿Q正傳》在形式上類似章回體小說,但在表達方式上又接近西班牙流浪漢小說的樣式。《阿Q正傳》既不同于社戲般的江南水鄉,而是將讀者帶入了“法庭式”的環境。每一位讀者都是“審判者”、“旁觀者”對阿Q的行為作出自我審判。《阿Q正傳》通篇看似是故事情節的簡單羅列,讀者似乎早已預知了故事情節的發展。阿Q的喜劇性在于他缺少獨立思考和自我反思,得過且過。但在作者的行文過程中,喜劇性逐漸退去外衣,悲劇性的本質暴露無遺,令讀者無心嘲笑,引人深思。閱讀《阿Q正傳》并不能將阿Q作為簡單的人物進行分析。魯迅通過阿Q這個符號,再現了“中國”在那個黑暗年代的癱瘓。文本中的隱含線索是阿Q為了努力證明自我存在的價值,為自己正名的想法時刻貫穿于阿Q之中。阿Q的屈辱性格和形象使某種難以閱讀的變為了一種具有既視感的典型形象,魯迅正是希望通過這個形象達到介入現實的目的,使得阿Q這個形象具有了深廣的社會意義。
楊航(1996-),黑龍江哈爾濱人,黑龍江外國語學院中文系,本科生。
I
A
1006-0049-(2017)07-028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