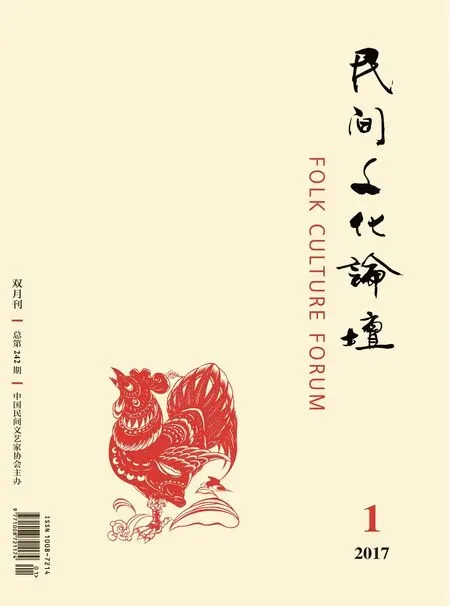試論活形態神話的傳承
李子賢 李 蓮
試論活形態神話的傳承
李子賢 李 蓮
神話傳承研究的重心,主要是探討活形態神話及口頭神話的傳承。除了探討傳承人、傳承場之外,更要關注神話傳承的深層動因及機制,即價值取向、信仰體系、祭儀系統、文化心理結構等文化要素的參與狀態;關注族群成員參與神話傳承的程度,即人們對神話的依賴感及需求度。此外,還要探討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神話傳承狀態及其構成因素的差異性。
神話傳承;活形態神話;傳承狀態及機制;傳承場域;傳承主體
神話的傳承是一個值得討論卻在神話學界少有討論的論題,是一個已有學者進行過探討卻探討得還不夠深入的論題。對于少數民族神話的研究而言,這更是一個繞不開的論題。
美國學者戴維?利明(David Leeming)與埃德溫?貝爾德(Edwin Belda)在其合著的《神話學》中,專列了一章《神話的創造者》,涉及了活形態神話的傳承。該書寫道:“神話往往產生于這些巫師降神時唱的歌曲”。又云:“巫師一絲不茍地用行動把他的神話經驗在生活中表現出來,因此說巫師的儀式歌曲是神話故事的根據,這說法是完全有道理的。對美洲印第安人來說,巫師的確是活著的神話人物”。“古代詩人是人神之間的媒介……荷馬和赫西俄德認為,古希臘人在力求揭示神和英雄的神秘交往,而且正是荷馬和赫西俄德能突破人類生存的界限,用語言把‘道’說出來”。①[美]戴維?利明、埃德溫?貝爾德:《神話學》,李培茱、何其敏、金澤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4—142頁。其實,上述引文中提到的巫師,不僅是神話的創造者,而且更多的是神話的傳承人。當從巫師中分裂出了更高層級的祭司之后,祭司更是掌握和傳承神話的核心人物。至于引文中提及的古代詩人如荷馬、赫西俄德,他們不僅參與了神話的創造,也是神話重要的傳承人。引文中所謂的“道”,就是神話思想與神話思維這一神話創造的母胎。該章的論述不乏獨到之處,卻沒有說清楚神話是在何種具有某種規定性的文化語境中被創造出來。當然,該章主要討論的是神話的創造者,沒有過多提及神話的傳承,是可以理解的。孟慧英教授在《活態神話——中國少數民族神話研究》一書中涉及了少數民族神話的傳承。例如將少數民族神話講述的儀式場合分為四類:祭天祭祖儀式、喪葬儀式、結婚儀式及其他儀式。②孟慧英:《活態神話——中國少數民族神話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59—179頁。楊利慧教授在《神話與神話學》一書中也列了專節探討了神話講述的場合和神話的講述者,提出了一些頗有創意的見解。③楊利慧:《神話與神話學》,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64—179頁。上述兩位學者的相關論述,都為進一步探討少數民族神話的傳承提供了某種啟示。
神話的傳承大致有以下幾種方式:
第一,存活于特定的社會民俗生活之中,作為一種“活體”,在特定的文化生態系統這一“母體”中存活下去的活形態神話。一般而言,活形態神話的傳承必須與民間信仰的存續、祭儀系統的存續以及作為群體的整個社會成員對神話功能的需求度的存續等要素相連屬。活形態神話傳承的載體,是某種特定的民俗生活環境中的族群成員及與活形態神話相連屬的祭儀系統,并有特定的傳承場。離開了上述載體,活形態神話的傳承將失去根基。
第二,口頭傳承的神話。通過存乎于心,口耳相授,經老一輩人的講述,將神話一代又一代地傳承下去。從某種意義上說,口頭傳承的神話也具有活形態神話的某些特征。不過,它已經只是一種“講一講”的故事,不一定與原始信仰和民間信仰、宗教祭儀以及特定的吟誦場域等相連屬。應該指出的是,它仍然是一種集體記憶,神話傳承的主體仍然是該族群的全體成員,只不過它已經是由個體講述、相關受眾在悉心接受而已。這種口頭傳承的方式與作為典型的活形態神話傳承的方式有一個明顯的區別:活形態神話的傳承雖然是由個體吟誦或講述,但是,此時參與其中的所有成員早已將神話的敘事內容諳熟于心,已在與吟誦者發生某種互動,早已進入了神話敘事內容所規定的情境之中。吟誦者也許只開了一個頭,或只吟誦其中的某一個片段,但在所有的參與者中,對整個神話敘事內容所述的一切已了然于心,而不是要等講述者講完或吟誦完神話的敘事內容之后,才明白該神話講的是什么。我們曾經提到過所謂的“潛隱神話”,這僅僅是對非我族族人之外的人而言,才被視為“潛隱”的。因為對本族群的族人而言,在某個象征符號背后隱藏著的神話敘事內容,大家都十分清楚。口頭傳承的載體是存乎于心,口耳相授。離開了上述條件,口頭神話的存續就難以維系。
第三,以文字記錄下來作為書面文本形式傳承的神話,其傳承的載體就是書面文本。例如在我國的《山海經》《楚辭》等文獻中,就有許多被記錄下來并傳承至今的神話。此種傳承方式只是到了文字產生以后才出現的,而在文字產生以前,只可能有上述兩種傳承方式。因此,書面傳承的方式是相對晚近才出現的。雖然用文字記錄的書面文本神話也有許多重大研究課題,例如赫西俄德的《神譜》是如何寫定的,《神譜》究竟是記錄當時傳承的神話呢,還是赫西俄德的創造?日本的“記紀神話”在被記錄下來之時,日本神話的具體存在形態是什么的等,都是些值得研究的論題。不過,當它一旦被用文字寫定之后,就少有發生變異了,而且只要它不是孤本而被丟失,就一直會以書面文本的形式傳承下來。這樣,我們就可以說,研究神話的傳承,主要是研究活形態神話是如何傳承的。
當我們進入研究活形態神話是如何傳承下來這一論題的時候,還必須就神話的發展歷程分階段進行梳理。概括起來,活形態神話的傳承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原始氏族社會時期。現在我們已經不可能回到原始氏族社會去觀察活形態神話是如何傳承的,但通過考古學、原始社會史、原始文化史以及相關資料,是可以窺視或推測出在原始氏族社會時期神話的傳承狀況的,這是一條途徑。還有一條較為便捷并且可以直接觀察、研究的途徑,便是從“我們當代的原始民族”那里去加以考察。這里有必要加以說明的是,“我們當代的原始民族”并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階段上典型的原始氏族社會,但它畢竟是保留原始氏族社會基本特征較多的觀察、研究對象。
在云南,直到20世紀50年代以前尚處于原始氏族社會解體期的少數民族,有長期生活在貢山縣獨龍江河谷的獨龍族,有長期生活在怒江大峽谷的怒族,有長期生活在西盟縣阿佤山中心區的部分佤族。上述幾個地區的少數民族是我們直接觀察、研究原始氏族社會解體期的神話傳承之理想考察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獨龍江河谷的獨龍族。本書中已有專節對獨龍族神話的概貌及特色作了綜合的介紹和論述,這里就不贅言。討述獨龍族神話的傳承,首先要弄清20世紀60年代以前獨龍族社會的整個人文環境及相關民俗。直至20世紀80年代以前,在整個獨龍族社會中仍彌漫著原始信仰的氛圍,巫師還在不斷地產生,以巫師為中心的祭儀仍在傳承①參閱蔡家麒:《獨龍族社會歷史綜合考察報告》,云南省民族研究所,1983年編印,第75頁。。筆者于1963年9月到12月在獨龍江河谷進行田野調查時的強烈感受是,構成對人類最大威脅的是各種自然力、自然災害的化身——“布藍”,它被視為一種對人類極為兇惡的鬼,似乎人們認識了多少種事物就有多少“布藍”(鬼)。例如石崖鬼、山鬼、水鬼、肚子疼鬼、頭疼鬼、牙疼鬼、腳疼鬼等等。據說“布藍”看得見人,人卻看不見“布藍”。對付“布藍”的辦法只有一種,即請巫師將其驅逐之,殺滅之。然而“布藍”卻是趕不盡、殺不絕的,因此人們總是小心翼翼地提防著“布藍”。反映在神話中便是有許許多多人與鬼(“布藍”)作斗爭的神話廣泛流傳。在獨龍族的觀念中,還未出現神的概念,但是某些居于天界或山上且能庇佑人間的鬼具有神的性質。人們對此種類型的鬼懷有虔誠之心、敬仰之意,總是通過某種儀式祈求保佑。其中最典型的祭儀就是每年一度的“卡雀哇”(祭天儀式,又視為年節)。據筆者的調查,類似獨龍族的“布藍”在佤族中也有傳承,佤族將其稱為“內”,也是看不見摸不著,據說有些是獨腳的,對人類危害極大。此外,在日本沖繩諸島的民間信仰中,也有類似于“布藍”這樣的鬼或精靈存在。
獨龍族信仰的神主要有:天上的鬼和南木(人神之間的信使),以及司風調雨順的山鬼、司狩獵的獵鬼等。在獨龍族的巫這一系統中,祭司階層處于初始的產生階段,在筆者的印象中祭司只是一些能與具有神的性質的鬼打交道的巫師開始具備了祭司的性質,但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稱謂。一般來說,他們能夠從事與神交往、溝通的儀式,諳熟本氏族、本民族的神話,而一般的巫師則只與“布藍”打交道,或為人治病,或為人驅鬼,對于與神界相關的祭祀雖然已有所了解,卻不專于此道。在獨龍族的宗教祭儀中,大型活動極少,除了剽牛祭天儀式,即“卡雀哇”之外,似乎就沒有大型的儀式,而不像四川大涼山地區的彝族以及云南麗江地區的納西族,至少有十多種大型的祭祀活動。張橋貴先生在其《獨龍族文化史》中,除“卡雀哇”之外,將獨龍族的宗教習俗及相關祭儀概括為以下八類:辟邪祟、禁忌、釋夢、喪葬、神判、占卜、嬰兒取名儀式、保命儀式②張橋貴:《獨龍族文化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79—91頁。。以上,便是獨龍族神話賴以傳承的文化語境。這是一個神話在不斷產生及傳承的時代,是一個人們對神話的需求度很高的時代,也是一個神話的功能開始彰顯的時代。獨龍族神話的傳承,有的是在氏族內部展開,如氏族起源神話;有的則是在包括氏族、家族在內的整個民族中傳承的神話,如人類起源、天地分裂以及洪水型兄妹婚神話等。由此可見,神話傳承的主體是該族群的全體成員。綜合考察獨龍族神話傳承的狀況,大致有以下幾個鮮明的特點:
第一,人們對神話的態度具有處于原始氏族社會時期的鮮明特色,神話確乎是一種“神圣的歷史”,是人人皆知且必備的知識體系,是人人都必須明白的各種事物(自然及社會現象)由來的權威性解釋,在人們的心目中擁有絕對的話語權。諸如,人們篤信克木克當山曾經是連接天與地的天梯,是天地分裂的地方;人們篤信卡俄卡普神山是洪水時兩兄妹的避難之所,兩兄妹生下的九對兄妹是從這里分手,成了散居于各地的各個民族。由此也可以看出,神話是深藏于人們的心中,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地了解或掌握一些神話,神話確乎是一種集體記憶。
第二,在獨龍族的民俗生活中,與祭儀相關的神話并非獨龍族神話的全部。比較突出的有天地分裂神話與“卡雀哇”由來神話,祭儀與神話二者互相支持,融為一體。此外,關于祭祀“幾布藍”(崖鬼)與“幾布藍”神話相聯系,獵神祭儀與獵神神話相聯系,以及對卡俄卡普神山的祭儀與卡俄卡普神山創造萬物及洪水型兄妹婚神話相聯系。一些與祭儀沒有明顯關聯的神話,如人類起源神話、人與鬼(“布藍”)斗爭的神話,還有一些否定性的文化起源神話,如獨龍族為什么沒有藥、獨龍族為什么沒有文字等,都與祭儀沒有明顯的關聯,但與某些生活理念、生活習俗相關。筆者1963年在孟頂村拜訪了一位百歲老人孟斗,他對筆者講述了許多獨龍族的神話,其中當講到獨龍族的人類起源神話時,鄭重地對筆者說:“我們和傈僳族不一樣,傈僳人是從葫蘆里出來的,我們獨龍長(音zháng,即‘人’)是天神嘎美嘎莎用石巖上搓出來的泥巴捏成的。”每年,人們在刀耕火種的山地里收獲糧食時,總是要將地里的一小塊糧食留下,不收割,用以敬獻天神。原因是:天神的女兒與地上的一個男子結婚后,天神給了他們谷種帶回人間,人間才會種莊稼。
第三,獨龍族神話傳承的一個重要方式,是家族或氏族長老大多會在一些重要活動時在火塘邊講述相關的神話。據筆者1963年的考察,獨龍族神話的傳承人、講述者并不只局限于主持宗教祭儀的巫師,大凡上了年紀、在家族或氏族中享有威望的老者,都知曉神話。一些民間藝人如歌手、故事家,都掌握相當數量的神話。不過也有一些不成文法的禁忌,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人們都不會輕易講述神話。即便是當地有名的女性歌手,雖然她也諳熟本民族的神話,卻不參與神話的講述。筆者當年曾在丙當村拜訪了一位著名的女歌手丙當妮。村民都說她知曉獨龍族神話。筆者在旁敲側擊中也深知她諳熟獨龍族神話,可是當筆者懇請她講述神話時,她總是笑笑,一言不發。當父權制取代了母系制之后,具有某種神圣性、話語權的神話之講述,已成了男性的一項專利。
第二階段:進入文明社會之后的歷史階段。在云南及周邊地區,直至20世紀50年代以前,尚有一些長期停滯在文明社會初期階段上的少數民族,如大、小涼山的彝族,西盟的佤族,怒江大峽谷的傈僳族,以及景頗族、基諾族、哈尼族等。在上述民族中,祭儀系統日臻完善,許多大型祭儀已發展起來。驅鬼與侍神兩個領域的分工日漸明顯,于是原來的巫師系統便逐步分裂為地位越來越高,專門侍神、敬神,專門主持各種求神、娛神儀式的祭司;原來巫師中的一部分仍然從事驅邪送鬼的各種具有巫術性質的活動,與祭司相比,地位相對低下。在納西族中就有了祭司東巴、巫師桑尼;在大、小涼山等地的彝族中就有了祭司畢摩或貝瑪,有了巫師蘇尼;在西盟佤族中就有了祭司巴猜(又稱魔巴),以及巫師巴斯保。大自然的沉重壓迫,階層的分化與對立,社會生活的日趨復雜化與多樣化,使得人們不僅需要一種心靈的慰藉,而且還強烈地期待能在心理上和現實生活中建構一個“安全屏障”和保障體系,因此,人們對祭司、巫師的依賴感、需求度日趨強烈。其中,祭司不僅被視為與神溝通的媒介,是傳遞神意的信使,而且在很多情況下,他們甚至被視為具有半人半神的現世神。20世紀90年代,筆者在元江縣大羊街鄉拜訪一位在當地頗有名氣的哈尼族大莫批(祭司),當談及莫批在哈尼族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時,他說:“如果沒有莫批,哈尼族不會過日子了,娃娃生了長不大,老人過世了送不走。”莫批在哈尼族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可見一斑。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民族中,歷史上曾經出現過政祭合一的情況,即地位最高的祭司也是最高的行政長官,諸如部落酋長等,在唐代前后彝族中出現的大鬼主就是典型的例子。之后,政祭分離,但是祭司在民間仍然擁有崇高的地位。直到近代,在哈尼族中仍然將頭人、祭司與工匠視為地位最崇高的三種“能人”。祭司地位的上升,體現在宗教民俗里面,不僅表現在只有祭司才能主持重大的宗教祭儀,成了唯一能與神對話溝通的人,而且也成了該民族神話傳承的主導性人物。其原因之一,就是他在主持各種祭儀中都要分別吟誦各種類別的長篇祭辭,而這些祭辭則大多與各種神話內容交織、融合在一起。這就要求祭司必須諳熟本民族的神話。不過,此種文化現象的出現,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神話傳承的主體依然是該族群的全體成員這種格局。這是因為,人們不僅對神話的需求度仍然較高,在人們的文化心理結構中仍然留有神話的重要位置,而且每個人從小到老在各種祭儀中一遍又一遍地聆聽祭司們的對相關神話的吟誦,已逐步將本民族的神話納入自己的心靈之中而被儲存下來。
在這個歷史階段上,神話的傳承出現了幾個重要的特征。
第一,神話傳承的場域已出現了較為嚴格的規定性,即只能在某個特定的場域吟唱神話而不能在其他場合隨意吟唱神話;只能在某個特定的場域吟唱什么神話而不能吟唱什么神話。例如喪葬儀式與婚嫁儀式都分別吟誦不同的神話內容,這在大、小涼山彝區就形成了“白勒俄”與“黑勒俄”之分。楚雄彝族也有類似的現象,因此才有各種各樣的《梅葛》出現。
第二,一定的祭儀都以特定的神話內容為注腳、為依據,這樣,某種特定的祭儀與某種特定的神話內容互為表里,融為一體,這就有利于某些類別的神話傳承。例如,歷史上納西族的祭天儀式,幾乎就是創世紀神話的重演。歷史上佤族的從拉木鼓儀式到祭木鼓換人頭儀式,不僅與“司崗里”神話相聯系,而且也是“司崗里”敘事內容的重演。每當我們想到神話講述的時候,大多只想到祭司一字不漏地把整個神話內容吟誦出來,即把神話的敘述文本全部講述出來。這當然是神話傳承的主要方式。然而許多研究者往往忽略了另外一種不容忽視的神話傳承方式,即在某種重大祭儀中,人們已在無聲無息地演繹著某種特定神話的敘事內容,對于非我族群的旁觀者而言,則全然不知其所展現出來的神話敘事內容是什么,必定要通過一定的田野調查才能了解其中的奧秘;而對于主持和參與儀式的當事人而言,則一切已了然于心,個個心知肚明。這也是潛隱神話的一種表現形態。
第三,傳承人多元化。這個歷史階段也當屬于“神話時代”的延續期。神話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它的強大功能,人們仍然將神話視為必備的知識體系,仍然將神話視為神圣事物的由來及歷史,因此,神話傳承人的多元化就是必然的了。除了祭司以外,巫師也了解一定的神話,在驅邪送鬼等巫術活動中,也離不開某種神力的支持,也同某些神話息息相關。因此,巫師也是神話的傳承人之一。一些家族長老、頭人也大多諳熟本民族的神話。每個家庭中的長者也能夠多少講述一些神話。很多民間藝人如故事家、歌手等也或多或少地了解和掌握該民族的一些神話,這是他們成為民間藝人的必備條件之一。
第四,神話傳承載體的多樣化。神話的濫觴,神話功能發揮到了極致,象征符號的拓展與豐富,神話依然深入人心并占據了心靈世界中的重要位置,就使得神話傳承的載體豐富多樣起來。不僅有外顯的各種文化符號,也有許多潛隱的文化符號隨之出現。例如,某座山、山洞、某塊祭石、某種動植物如鷹如虎如魚如蛙如葫蘆如樹等,都成了某種神話的象征符號。魚成了哈尼族的創世神;鷹成了彝族英雄神“支格阿魯”的化身;青蛙成了壯族民間信仰中雷神的信使;虎成了楚雄地區彝族某一支系神話中萬物始創的本源;葫蘆成了各民族神話中母體的象征。
第五,創世史詩的出現強化了神話的傳承。雖然尚處于原始氏族階段上的獨龍族已經產生了創世史詩,但筆者認為,創世史詩的產生和形成大多是屬于這一歷史階段。創世史詩的出現不僅是從氏族神話、部落神話向民族神話過渡的重要標志,不僅是將各自獨立、相對分散的各種類別的神話加以系統化之后而形成了體系神話之重要的一步,而且進一步強化了該民族神話在民間的傳承。
第三階段:傳統農業社會階段上的神話。傳統農業社會指的是直到現當代仍較相對完整地保留著傳統文化的廣大農村。這種傳統農業社會在云南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90年代。與上一個階段相比,神話的傳承又有了新的變化。神話傳承的主體已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知曉本民族神話的人在逐步減少,除了年長者之外,在許多青年人中已逐步失去了對神話的需求度和依賴感。這樣一來,神話的傳承就逐步轉移到了祭司、民間藝人和某些家族長老的身上。在傳統農業社會中,一些重要的民間信仰仍在存續,例如天神崇拜、祖先崇拜、山神崇拜、農業神崇拜、村寨守護神崇拜等。因此,與上述民間信仰相連屬的宗教祭儀仍在存續,從而在許多民族中,祭司仍然沒有“下崗”。許多與祭儀相關聯的神話依然在祭儀中重演,例如納西族的祭天,彝族、哈尼族的喪葬儀式等,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90年代。至于廣泛傳承于哈尼族、彝族等許多民族中的祭竜儀式,即祭祀村寨守護神則一直延續至今。一般而言,竜神都有相關的神跡在民間傳承。一些口承的神話依然有人知曉,還在民間傳承,但講述的頻率已大不如前。在這一階段上,神話的傳承出現了新的特點。
第一,與神話相關聯的祭儀逐步減少,神話的傳承場開始萎縮。例如在西盟的佤族中,自20世紀50年代革除了獵頭習俗之后,《司崗里》及相關的講述獵頭功能的神話便逐漸失卻了傳承的重要載體——拉木鼓儀式和祭木鼓儀式;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些神話逐漸退出了人們的集體記憶,除了祭司、民間藝人、家族長老等少數人員之外,能系統講述神話的人便越來越少了。在滄源地區,由于獵頭習俗革除的時間較西盟早,以致在十多年前就已無人能吟誦《司崗里》;知曉本民族神話的人也越來越少。
第二,這就導致了神話賴以存活的文化生態系統開始發生緩慢的變化。仍以佤族為例,由于與獵頭祭祀相關聯的祭儀逐步消失,連接文化生態系統諸要素的鏈條出現了斷裂,講述獵頭非凡功能的神話也就逐步失傳。同樣,由于拉木鼓儀式、人頭血祭的消失,系統吟誦《司崗里》的傳承場已日漸萎縮,最終導致了與《司崗里》傳承息息相關的文化生態鏈之斷裂。
第三,這又必然導致一個結果:某些神話的功能正在日漸消退乃至喪失。一旦人們對神話的需求度減弱,即神話功能在社會生活中逐步消退,那就離某些神話的失傳為時不遠了。
第四,如前所述,在這個階段上,神話傳承的主體已不再完全是該民族、該地區、該村落的全體成員,那么,能夠了解、掌握本民族神話的人,就只有祭司、民間藝人和家族長老等少數文化精英了。需要指出的是,在傳統農業社會這個階段上,在很多民族中有些支系、有些地區、有些村落,祭司早已不復存在。例如《梅葛》的故鄉大姚縣馬游村,祭司早已消失;在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石屏、開遠、蒙自等地居住在壩區的彝族,大約在20世紀60、70年代前就已沒有了祭司。當然,這并非是神話的絕唱階段,只是與上一階段相比較,神話的傳承出現了新的趨勢與特點:該民族的一些主要的神話,特別是以創世神話、洪水神話為主軸組織起來的創世史詩,仍得以存續;許多與民俗生活中的祭典、婚喪嫁娶相關聯的神話也還在存續。
那么,當下云南少數民族活形態神話還在傳承嗎?其傳承的狀態又有什么新的變化和特點呢?由于云南少數民族乃至某一民族的不同支系社會歷史發展的多樣性及差異性,其聚居地自然環境的多樣性,就使得有些民族或有些民族的支系直到當下仍然維系著自己獨特的民間信仰,維系著與民間信仰相關的某些宗教祭儀與民俗,仍然存續著與民間信仰、宗教民俗相關聯的活形態神話。例如,大理白族聚居區的一些本主神話,寧蒗縣永寧鄉瀘沽湖畔摩梭人的干木女神神話,紅河州哈尼族與昂瑪突祭儀相關聯的神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紅河州開遠市彝族支系仆拉人中仍在存續的竜神神話、洪水型兄妹婚神話及洪水型天婚神話等。這里我們擬以仆拉人的活形態神話為例,對其傳承現狀及傳承特點進行討論。關于祭竜及其神話。在開遠仆拉人中,都普遍傳承著祭竜儀式。除了每年定期舉行的集體祭祀之外,還有以家庭為單位的不定期的對竜神的祭祀。前者是祈求竜神即村寨守護神保佑村寨平安、六畜興旺、風調雨順、糧食豐收,后者則是求子求福,或者當家庭遇到某種災禍時祈求竜神的保佑,化險為夷,轉危為安。人們認為,竜神都具有特殊的神力,能夠斬妖除魔,驅邪禳災,而且都有相關神話敘述其神跡。直到當下,在碑格鄉的仆拉人中,“祭龍習俗仍保留其原生形態,主要特征有三:一是龍樹為村寨守護神的象征;二是祭龍多為群體性之祭儀;三是皆有一則解釋祭龍由來的神話。其母題是:當時,村寨附近出現了一個惡魔,給人們帶來災禍。后來,有一個神制服了惡魔,為民除害,被尊為(非漢族之龍)神,并為其舉行祭祀”①李蓮、曹定安、李子賢:《開遠市彝族傳統文化及其現代適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9頁。。關于洪水神話與相關民俗事象。筆者在2008—2010年間對開遠市仆拉人的田野調查中了解到,大凡有婚喪嫁娶等儀式都會由貝瑪(祭司)吟誦洪水型天婚神話或洪水型兄妹婚神話。值得關注的是,洪水神話還與當下的某些民俗事象互為補充,融為一體。例如,在一則洪水神話中講到:“幾天后洪水退下,兩兄妹藏身的木桶落在了溶洞旁邊。兩兄妹出來后看到木桶被兩棵樹擋著才沒有掉進溶洞。其中一棵叫‘撒瑪石’樹,一棵叫‘師石’樹。由于這兩棵樹救了兄妹倆的命,被稱為是能夠給人帶來吉祥幸福的兩棵樹。后來,仆拉人祭龍的‘龍門’就必須用這兩棵樹搭建,祭龍的龍樹也要從這兩棵樹中選出”。人們仍將洪水后剩下的兩兄妹視為始祖,因此,在“架吉村祭龍開始時,貝瑪所念咒語的頭句必須是:‘男神與男祖,女神與女祖……’”。另外,洪水神話還與 “祖宗木刻”所用的樹木聯系在一起。在宗舍村仆拉人的洪水神話中講到:洪水后兩兄妹是落在了多依果樹上,才未被逐漸退去的洪水卷入溶洞中。后來人們就視多依果樹為一種圣樹,將其用來制作象征祖先的木刻,即祖靈牌,供奉于家中。②參閱李蓮、馮熙:《開遠彝族地區洪水神話與傳承》,見李子賢、李存貴主編:《形態?語境?視野——兄妹婚神話與信仰民俗暨云南省開遠市彝族人祖廟考察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56、357頁。
在當下的文化語境中探討神話的傳承,是一個極具魅力的論題。一般而言,在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神話的傳承場和載體都已經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雖然神話在短期內不會消失,然而它的社會文化功能的發揮已受到了諸多因素的制約。但就開遠彝族地區而言,還保留著有利于神話繼續傳承的民俗環境,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其一,村民中的大多數仍然是彝族神話傳承的主體。其二,仍存續著各種祭儀、節慶等較完備的傳承載體。其三,在開遠彝族的許多村寨中,仍或多或少地保留著傳統文化的傳承場和積淀場。其四,在一些山區村落中,貝瑪(祭司)的存在,是各種祭儀、節慶維系和傳承并發揮其社會文化功能的關鍵因素,也是包括神話在內的彝族傳統文化得以繼續傳承的必備條件之一。其五,筆者在田野調查中發現,在當下特定的文化語境中,參與對包括神話在內的彝族傳統文化之保護、傳承與弘揚的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即在當地工作的一些本民族的中、小學教師以及文化干部③參閱李蓮、馮熙:《開遠彝族地區洪水神話與傳承》,見李子賢、李存貴主編《形態?語境?視野——兄妹婚神話與信仰民俗暨云南省開遠市彝族人祖廟考察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54—355頁。。由此可見,傳統的力量是巨大的。只要民間信仰還在存續,人們對神話還有著某種程度的依存感和需求度,活形態神話的余波就會依然在蕩漾。
神話的存活必須依附于特定的文化生態系統。活形態神話的傳承也必須依存于特定的文化語境。與活形態神話傳承相適應的文化生態系統有哪些構成要素呢?第一,某些原始信仰、民間信仰仍在存續,某些崇拜形式如天神崇拜、祖先崇拜、山神崇拜、守護神崇拜等,仍然是人們宗教、民俗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二,人們對神話的依賴感、需求度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人們的精神生活之中。神話的功能仍然在不同程度地得以發揮,以滿足人們的某種心理需求。講述事物神圣起源的種種神話依然是人們民俗生活中的必備的知識系統之構成要素和權威性解釋。對于許多生活習俗、宗教祭儀,只能這樣而不能那樣是由某種神話來規定的。第三,由于神話與某些原始信仰、民間信仰相連屬,有的神話便具有了某種神圣性及話語權,這樣,神話的吟誦場合就必須是某種特定的場域。例如節日慶典、宗教祭儀或婚喪儀式。雖然有些神話的講述或吟誦并沒有嚴格的場域規定性,但也有講述的嚴肅性、嚴謹性特征。第四,由于以上要素的參與,神話的吟誦者、講述人就擁有了某種特別的身份。也許該族群、該社區、該村落的全體成員都知曉某些神話,但只有祭司、民間藝人和德高望重的長老才能充當神話講述、吟誦的角色。第五,在人們的文化心理結構中,或多或少都留有神話之存在空間。換言之,人們對神話有著一種尊重、敬仰,乃至篤信的態度。正是以上要素之整合,構成了神話賴以存活、賴以世代相傳的文化生態系統。
如果說活形態神話的傳承離不開特定的文化生態系統,那么,為什么千百年來在云南的少數民族中,活形態神話賴以傳承的文化生態系統又一直得以延續下來呢?據筆者初步歸納,主要有以下幾項緣由:
一是在云南大多數少數民族中,其原生性的文化一直得以傳承下來,大多沒有被外來的異質文化所覆蓋①在云南的少數民族中,只有傣族在傳入了南傳上座部佛教之后發生了重大的文化轉型,許多原生性的文化被南傳上座部佛教的相關民俗所取代。不過也有許多傣族的原生性文化保留了下來。例如與稻作祭儀相關的某些文化習俗仍有傳承。傣族周邊的部分佤族、布朗族和德昂族也轉而信仰南傳上座部佛教,不過,他們的很多原生性文化依然有所存續。。19世紀末20世紀初,基督教開始傳入傈僳族、怒族、獨龍族、拉祜族、佤族等民族地區,但遠沒有達到將其原生性文化覆蓋的程度。在云南的很多少數民族中仍然存續著許多非常古老的原始信仰,如萬物有靈、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動植物崇拜等。
二是云南各少數民族在歷時久遠的與其他民族周邊地區的文化交流和互動中,已逐步形成了一種文化自我保護機制,即在與異質文化的交流和互動中大多能做到豐富自我,提升自我,而又不丟失自我。其中最為典型的是白族、納西族,至遲在唐代就產生了與我國中原地區漢儒文化的交流和互動,他們都能夠在吸收漢儒文化的基礎上形成新的文化特質,卻又依然鮮明地保持著本民族文化的個性和特征。即便是傣族,至遲在明代中葉以后就已開始了佛教化的進程,但是我們卻看到了以下兩個鮮明的特點:其一,南傳上座部佛教的傣族化。其二,某些屬于傣族原生性文化的原始信仰與相關民俗依然被保存至今。谷神信仰及谷神奶奶的神話,勐神、寨神信仰及相關神話等的存續就是一些典型的事例。
三是在云南一些少數民族中,該民族自身的傳統因素對其歷史進程的影響極大,其歷史主要是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獨立發展。這就使得某些民族的文化形態及構成要素極為古老。怒江大峽谷的傈僳族、怒族,滇南地區的佤族、拉祜族、基諾族等就屬于此種類型。其中以佤族最具代表性。直到20世紀50年代,在佤族的社會民俗生活中,仍存續著一千多年前就已經產生的古老民俗。有學者指出, “獠即濮”,再將《魏書》中的相關論述梳理出古代濮人之以下民俗事象:“無姓名,男女稱呼按出生的時間先后次序排名;房屋為‘干欄式’建筑;族群首領推舉產生,稱其為‘王’,‘王’者有二鼓,牛角一對;紡織‘蘭干細布’(桐樺布);祭鬼神;獵頭習俗”①段世琳:《佤族歷史文化探秘》,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5頁。。我們由此看到,以上古代濮人的諸種民俗事象,直至20世紀50年代初仍在西盟等縣的佤族中存續。
四是特殊的“文化—地理單元”也為云南少數民族原生性文化的傳承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載體。在云南歷史地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少數民族分布格局,這樣就逐步形成了許多既相對獨立又自成體系,宛如星羅棋布的“文化—地理單元”。以西盟佤族自治縣為例,這里雖然是佤族的主要聚居區之一,但還居住著少量的傣族、拉祜族。在現今西盟縣城所在地的附近,有一個叫勐梭的傣族寨子,雖然只居住著近百戶的傣族,周邊幾乎都是佤族(距離最近的佤族寨子只有幾公里),而距離孟連縣傣族聚居區卻有數十里之遙,猶如浮懸在佤族文化海洋之上的一座文化孤島。然而至今依然完整、鮮活地保持著自己的傳統文化。又如在擁有上百年工業化歷史的開遠市,雖然這里自明代以后由于漢人大量移入,漢儒文化極為發達。一百年前通車的滇越鐵路早已為開遠傳入了西方文化,導入了工業文明。然而在離開遠市區僅80公里的碑格彝族鄉,時至今日還較完整系統地存續著彝族支系仆拉人的傳統文化。讓人驚訝的是,碑格鄉村村有貝瑪,而且新的貝瑪還在不斷地涌現。作為祭司,貝瑪經常被人請去主持各種祭儀,他們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仍然比較崇高,受人尊敬,許多古老而具有仆拉人特色的神話還在民間傳承。在離開遠市區僅20公里的彝族老勒村,雖然周邊都是漢族村寨,卻一直存續著具有彝族鮮明特色的“人祖廟”,仍傳承著與“人祖廟”相對應且具有當地彝族特色的洪水型兄妹婚神話②參閱李蓮、曹定安、李子賢:《開遠市彝族傳統文化及其現代適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類似勐梭傣寨、碑格彝族鄉、老勒彝族村這樣的文化孤島,在云南比比皆是。她們憑藉著這種特殊的“文化—地理單元”,在頑強地維系著自己的文化傳統,保持著自己鮮明的民族特色,讓本民族的文化既連接著古老的歷史,精準地定位著自己的民族屬性,卻又與周邊地區其他民族的文化保持著某種程度的相互接納與交融。這樣就使得許多分散居住的少數民族村落成為了一塊塊神奇、迷人的文化綠州。
[責任編輯:丁紅美]
I207.7
A
1008-7214(2017)01-0055-09
李子賢,云南大學教授;李蓮,普洱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