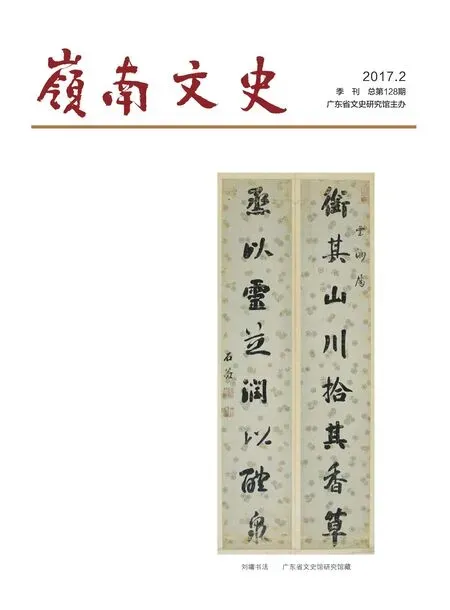平南尚氏父子關系考辨
彭崇超
史海鉤沉
平南尚氏父子關系考辨
彭崇超
一
明朝滅亡之后,滿洲貴族率領八旗鐵騎浩蕩入關,開啟了重新統一中國的進程。在整個統一戰爭中,南部中國一直是反清復明勢力的活躍舞臺,清廷基于自身力量的不足,繼承發展了自皇太極以后團結漢官的政策,決定在南部邊疆實行藩鎮體制,利用前明投降的漢人獨立軍團,穩固滿洲貴族在南中國的統治。吳三桂、尚可喜、耿繼茂相繼被清廷派鎮到云貴、廣東、福建,形成所謂的三藩。三藩設立的初衷本是幫助滿洲貴族加速統一與穩固地方秩序,但隨著明清戰事的結束,藩王在地方上的權勢不斷膨脹,嚴重破壞國家財政的正常運轉,威脅著清廷的統治。康熙親政之后,“以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蔓,馴致不測”,[1]決心撤藩。康熙十二年(1673),由平南王尚可喜的歸老遼東之請引發的“三藩并撤”,激化了藩鎮勢力與清朝中央的矛盾,最終爆發了持續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亂”。
平定三藩維護了清朝國家的統一與穩固,加強了君主專制體制,意義重大。在“三藩之亂”中,平南藩鎮與其他兩藩有著明顯的不同,尚可喜對清朝忠貞不二,在吳耿叛亂發生之后,積極參與平叛,努力替朝廷嚴守南疆。其子尚之信則經歷了從“順逆”到“反正”到最終被賜死的曲折命運。尚之信在“三藩之亂”中的表現與地位一直是研究者們爭論的焦點。一部分學者認為,尚之信為人自私殘暴,在吳三桂的威逼利誘之下,利令智昏,背叛清廷而“順逆”,在沒有得到實際好處的情形下,選擇“反正”,但歸順清廷后,仍然心懷兩端,不聽朝廷調遣,最終以“不忠不孝”之名被康熙賜死,[2]死有余辜;另一部分學者認為,尚之信性格的確有缺陷,但仍頗有才干,盡管因為王位繼承問題對清廷有怨氣,但“順逆”吳三桂是在廣東戰事極為不利、基于維護尚家在粵利益的考慮下,作出的無奈之舉。對清廷,尚氏實無反心,在情勢好轉之后,即刻歸順清廷。至于對尚之信在反正之后,仍懷兩端、不聽調令的指責,經學者考證,實在有失公允。總體看,在參與平叛的過程中,尚之信及其領導下的平南藩軍實在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最終被殺則是康熙故意制造的冤案,目的是實現徹底的削藩。[3]筆者同意后一種觀點。然而,盡管對于尚藩的研究已經十分成熟,但有關尚可喜與尚之信父子間的關系,仍有繼續探討的空間與必要。厘清尚氏父子矛盾關系的發生與演變,對于更好的厘清“三藩之亂”中的相關問題,會有幫助。
二
在清代的一些官私文獻中,涉及到尚之信的描述,都極力渲染其“酗酒嗜殺”的個性特征及與父親尚可喜的矛盾,[4]給人一種尚之信是殺人魔王,忤逆不孝,最終被康熙賜死是罪有應得的印象。但一些研究已經顯示,康熙為了維護強化君主專制體制,對三藩的態度就是堅決撤藩,為達此目的甚至不惜對藩王進行肉體消滅。[5]尚之信是官方欽定的“三逆”之一,有關他的記載,也基本是“后三藩時代”的產物,像《平定三逆方略》這樣的官書自不必說,就是那些非官方的文人筆記亦不免有確保“政治正確”、有意無意歪曲夸張的嫌疑。其實,尚之信其人并非一無是處,雖然尚可喜“起于營伍,無學術”,[6]“自以馬上得功名,始終不延師教其子”,[7]使得自幼缺少管教的尚之信,缺乏基本的文化教養,有公子哥兒任性胡為的作風,但同時必須承認,尚之信“有才略口辯”,[8]亦是“天資高邁,饒遠略,愛人禮士,夙著賢聲”[9]的人,具有“臨陣遇危,瞋目一呼,千人俱廢”[10]的非凡武力,他“酗酒嗜殺”的殘暴行為其實是有針對性和深層原因的。
(一)關于尚之信酗酒
據《尚氏宗譜》載:“尚之信,字德符,號白巖,生于明崇禎九年(1636),即清崇德元年,生而神勇,嗜酒不拘細行”。[11]尚家家譜中對尚之信嗜酒的毛病,并不諱言。之信曾兩次入侍北京,第一次是順治十一年至康熙二年(1654-1663),第二次是康熙七年至十年(1668-1671)。[12]初次進京時才十九歲,酗酒的惡習應是第一次入侍京城時養成的,但筆者并不同意某位同儕的看法,其認為在北京作人質的尚之信,酗酒的習慣源于“對環境長期不滿,壓抑的心情難以以正當途徑釋放,從而選擇的一種發泄手段。借酒精來麻醉自我,忘卻自己所處的不利環境、發泄自己朝不保夕的惶恐心情,久而久之或養成酗酒習慣” 。[13]清初漢人藩王遣子進京,具有解朝廷之疑,拉近與滿洲貴族統治者關系的考慮,確有“質子”之意,但清朝統治者為了利用漢人藩王為其效命嚴疆,對在京的藩王子弟更多的是優待寵愛,著意籠絡。[14]作為平南王世子的尚之信就深得順治帝器重。史載:“出入必從,時稱為唵答”,[15]“以藝能才辯當上意,賜號俺達公,甚愛之”,[16]之信憑借其過人的才能成為三藩子弟中唯一獲得公爵的人。如此看來,藩王子弟在京的生存環境應該是錦衣玉食,極為優渥的,并不會產生什么“壓抑的心情”,以致“借酒精來麻醉自我”。恰恰相反,養成酗酒習慣的真正原因,更可能是在京期間,基于清廷提供的寵渥環境,在與滿洲貴族、王公大臣宴飲觥籌之間養成的,不宜過分解讀。
(二)關于尚之信酒后嗜殺
康熙二年(1663),俺達公尚之信回到闊別九年的廣州,但五年之后的康熙七年,尚可喜第二次將其遣送入京,直到康熙十年才奏請還鎮。之所以有第二次遣子入京之舉,是尚可喜面對尚之信“酗酒嗜殺”惡行的消極應對。回穗之后的尚之信,將酗酒的惡習進一步發揮,竟然達到了醉酒后肆意殺人的地步。
(之信)然酗酒好殺,每醉后嘗手刃人或縛而射之,以為戲,比死乃已,王屢誡之不悛。[17]
俺達公之信,酗酒嗜殺,壺樽、杯斝與弓刀矛戟之屬,隨其所至,必兼攜以行。坐則輒飲,飲醉則必殺人。深宮靜室,無以解酲,即引佩刀刺其侍者,雖寵仆艷姬,瘢痏滿體。[18]
俺達公之信,酗酒暴逆。王之宮監,適有事于公所,偶值其醉,忽指監曰:“汝腹何大也,此中必有奇寶,我欲開視之。”以匕首刺監腹,應刃而斃。王之堂官王化者,年已六十余,盛夏苦暑,袒而立于庭,之信憎其年老,笑謂化曰:“汝須眉太白,我當黑之。”遂縛化曝烈日中,自巳至酉,百計求免,始得脫。王大忿恚,呼之信杖之三十,而專恣益甚。[19]
以上羅列的是一些經常被學者引用,以顯示尚之信“酗酒嗜殺”的史料,基本可以反映俺達公在康熙二年到康熙七年在家期間的反常表現。尚之信酒醉之后就以殺人為樂,所殺之人甚至包括了王之宮監、王之堂官,尚可喜屢勸之而不能制。不難看出,尚之信的種種反常施暴行為,似乎是在對其父親發泄不滿,是父子之間關系緊張不睦的體現,其個中原因絕非用任性胡為的公子哥兒做派就能完全解釋。
平南王尚可喜早年頗具才干,“性明達,曉暢軍事,每上下文移及一切章奏,令左右誦之輒能解其大略,有所處置,得當者當十六七”,[20]然“自以馬上得功名,始終不延師教其子”。[21]“暮年驕恣”,[22]對子女缺乏管教,“多內嬖,有子三十余人,自相仇黨”,[23]寵溺異常,“諸子女頗多,不能不一一為之計,每一女子嫁,非萬金不可,一男子授室,則數萬金”。[24]可喜為人“無定力,游豫多忍”。[25]作為一家之主,不能調解盡在目前的蕭墻之禍,反而聽信藩下小人之言,壟斷粵省各項利源,大為民害,助長了尚家子弟的不正之風。在尚可喜重用的藩下人之中,首推謀士金光。關于金光其人,有如下史料可供參考:
金光字公絢,浙江義烏人,知書,有權略。尚可喜從遼陽入關,得光甚喜,置之幕下,凡有計議,必咨于光而后行。……光因乘間言:“俺達公剛而多虐,勇而寡仁,若以嗣位,必不利于社稷,請廢而立次子固山。”王深然其說,因循猶豫,終未即行。[26]
金光寓舍,在省垣古藥洲北,與平邸相隔一垣,前鴻臚寺卿金光寓舍也。藩府有便門,與光舍可通往來。……光浙江義烏縣學生,為平藩掌書記,多智術,通世變,左足微蹶,藩府呼為“跛金”。尚王頗倚任之。[27]
金光者,故浙人,饒智略,通文義,凡所謀為,能曲得老王心,王愛之甚,與結婚姻,之信故未獲王印時,有所求于光,光輒不應。[28]
金光是尚可喜最為倚重的心腹家人,寓所在王府隔壁,以便門相通,尚王對其信任有加,甚至達到了“凡有計議,必咨于光而后行”的地步,金光儼然通過影響尚可喜把持了平南藩府的實權。康熙二年(1663),作為平南王世子的尚之信回到廣州,一定未曾想到父親竟然會對金光這一跛腳的家下人比對自己這個長子更要信任,未來的平南王竟然對平南藩鎮的事務缺少應有的話語權,有事還需求助金光,而光卻不給他面子,多年缺少相處與溝通的父親對他也并不理解支持。[29]這種情形無疑會使尚大公子惱羞成怒,為了排解心中郁悶的心情,“借酒消愁”成了缺乏人文教養的武人尚之信的必然選擇,前文材料中所展現的尚之信醉酒之后殘暴殺害其父屬下的行徑,似乎在此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釋。有人認為,尚之信“酗酒嗜殺”的殘暴行為,是尚氏父子之間針對藩府權力爭奪的表現。[30]這種解釋固然合理。但筆者以為情況絕非如此簡單,尚之信久在京城,與父親之間缺少溝通,難免有陌生隔膜之感,父子關系相對疏離脆弱。身為長子的尚之信渴望得到父親的認同與信任,只是因為身為武人。自幼缺乏文化教養,找不到一種合適的時機與方式,與父親達成諒解。而尚可喜性格又“無定力,游豫多忍”,容易被人擺布。金光恰恰利用了尚氏父子之間這種脆弱疏離的關系,從中挑撥離間,排擠詆毀尚之信,甚至慫恿老王以尚之孝取俺達而代之,以維護自身在藩府之中的實權地位,只是因為尚可喜“以(之信)嫡長故,又愛其才,終不忍有他意”[31]而未遂。金光應是致使尚之信“嗜殺”成性、尚氏父子關系緊張不睦的“罪魁禍首”。
三
(一)父子關系的持續緊張
尚可喜在康熙七年(1668)再一次遣尚之信入京,以此緩解父子間的矛盾,但后又恐其觸冒法網,遂又于康熙十年,以自己年老為名,奏請之信還鎮,佐理尚藩軍政。回粵代理平南藩鎮軍政的尚之信,行為較前更為乖張不法,父子矛盾徹底公開化。史載尚之信“既掌兵柄,即營別宅,擅威福,可喜不得出一令”。[32]“暴橫日甚,招納奸宄,布為爪牙,罔利恣行,官民怨讟……常于其父前持刃相擬,所為益不法”。[33]“益驕怙,笞其前母舅及姑丈不恤,凡老王用事人,舊有不快者,小則鞭,大則殺,王無如之何,而其尤不能相曰金光……既得志,必欲殺之為快,而老王加意持之,光亦時時有所饋,冀緩死”。[34]可見,尚之信對以金光為首的老王舊人成見極深,恨之入骨。另外,尚之信對自己的兄弟們也極度刻薄,同母弟尚之孝,因金光慫恿過老王以之孝取代之信的世子地位,故兄弟之間漸生嫌隙。[35]七弟駙馬尚之隆,尚之信似乎對之亦有不滿。至于其他諸弟,史載:“老王諸男子未長成者,每宴集,之信嘗指而問侍人,此輩何為者,或以阿哥對,則怒曰:‘雜種耳,何阿哥為’,若是者,老王皆聞之,諸左右及諸姬人,日夜泣王前”。[36]看來,尚家內部父子兄弟之間的矛盾,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關于尚之信二次回粵掌握平藩軍權后的表現,可作兩方面的解釋:一方面,老王尚可喜針對自康熙二年以后產生的與長子之間的矛盾,沒有采取積極正面的處理策略,而是消極的支走尚之信,再次將其遣送進京,以此回避矛盾,這勢必會增加尚之信的不滿,加深父子間的隔膜,還鎮掌權后的尚之信也就自然而然的會將這種不滿,發泄到老王舊人的身上;另一方面,尚之信與父親之間的緊張關系,源于父子之間長期分隔兩地,缺乏溝通交流所致,加之金光輩從中作梗,使得問題復雜化,作為世子且頗具能力的尚之信,渴望得到父親的認可與器重,對于眾多弟弟的刻薄與厭惡,其實是尚之信面對父親忽視自己重用外人的報復。
尚家內部的矛盾使得“游豫多忍”的尚可喜焦頭爛額,同時,金光出于避免被尚之信殺害的考慮,向老王獻策:“謂朝廷方嫌尾大,計莫若率諸少子及左右親信歸耕遼東,避俺達去,朝廷必大喜,則君臣父子之好可兩全無禍,王以為然,具疏上,廷議果喜”。[37]尚可喜的歸老遼東之請,卻成為“三藩之亂”的導火索。
(二)父子關系的極化與最終和解
吳三桂起兵之后,康熙命令平藩照舊鎮守廣東,替朝廷平叛。尚可喜趁機上奏朝廷,以次子尚之孝襲封,朝廷批準:“詔授之孝平南大將軍,而之信以討寇將軍協剿”。[38]尚之信在瞬間失去了軍權及平南王的繼承權,職位亦屈居其弟尚之孝之下,表面上他“反循循不出一語,若不知有其事者”,[39]但實則不可能不對父弟乃至清廷心生怨恨,只是迫于形勢,無可奈何而已。而尚之孝則通過廣東巡撫劉秉權上疏朝廷,辭襲王爵,朝廷給出了“今當諸逆鴟張,大兵進剿之時,平南王尚可喜,籌畫周詳,精神強健,應令尚可喜,照舊管事。俟事平,令尚之孝承襲”的指示。[40]之孝此舉一方面是為避免過分開罪于尚之信,同時也是基于自身條件做出的務實決定,尚之孝遠不具備其兄的軍事才能,“之信雖酷虐而不吝于財,有當意者賞,嘗浮于所事,諸藩下月餉經老王扣克,分隸諸少子者,之信獲印時,盡為清出,給諸窮丁,以是諸窮丁及藩下世職多心屬之信,而之孝者,儒雅安詳,樂與諸文人游,然性鄙甚,其貪吝過于老王,藩下諸將士弗善也”。[41]尚之信較尚之孝更能得到平南藩軍的擁護。
在吳三桂起兵后的三年左右時間里,尚氏父子有效的牽制了叛軍的北上發展,在極端困難的形勢下,堅守廣東,使吳與耿鄭叛軍不能連成一片。在此期間,被貶后“循循不出一語”的尚之信,以大局為重,盡力配合著尚可喜對平叛作出的軍事部署,這使得個性本就“游豫多忍”,對子女向來舐犢情深的尚可喜,對長子的印象漸有改觀,甚至以尚之信援助江西之役上疏朝廷為其請功。[42]
在苦苦支撐三年,且得不到清軍有力支持下,廣東戰勢急轉直下。先是鄭經派劉國軒進兵潮州,大敗尚之孝,迫使尚之孝退守惠州,吳三桂又派遣馬雄自廣西進入廣東,高州總兵祖澤清叛應,總督金光祖退守肇慶,一時間廣東東西交訌,“省會一區,亡在目前,人情洶洶,巨無固志”,[43]為了保命,總督金光祖,藩屬總兵孫楷宗,水師副將趙天元、謝厥扶相繼“順逆”。[44]而此時的尚可喜身體狀況已經迅速惡化,無力統籌全局。在這種形勢下,被“罷黜”又深得平南藩軍擁護的尚之信出于維護尚氏家族的利益,以及奪回失去的權力,最終做出了投降吳三桂的選擇。
十五年春,可喜病益劇,之信代治事。三桂招可喜籓下水師副將趙天元、總兵孫楷宗相繼叛,之信遂降三桂,遣兵守可喜籓府,戒毋白事,殺光以徇。罷之孝兵,使侍可喜,可喜以憂憤卒。[45]
鄭錦下東莞,馬雄入南海,趙天元、謝厥扶俱以舟師迎降。之信計無所出,乃殺光以辭于敵,謂向之抗衡上國,久持弗下者,皆此人之為也,偽遂納款偽周。[46]
時賊將分掠諸郡,皆降。公爺尚之信逼伊父平南王反,全省俱屬周矣。[47]
在尚之信被“罷黜”、尚可喜重新掌權的康熙十三年至十五年初,“王之舊人金光者,益居中用事,招引江浙間輕俊無賴,若黃掌絲輩,布列前后,把持無間,即一言一動非金黃輩不行,自督撫若司道侯其門,求一面不可得,緣是賄賂公行,雖一巡一捕咸計,缺人賄否,即無由補,而東局大壞”。[48]以投降吳三桂偽周為契機,尚之信在平南王府中發動了政變,清除了老王身邊的舊人,殺掉恨之入骨的金光以降周。已病重的尚可喜仍對清廷忠貞不二,不同意兒子的“順逆”行為,但不能制。史載:“可喜聞變涕泣,悔不早從金光言”,[49]“憤甚,自縊,左右解之,蘇,遂不起,十月,卒”。[50]父子之間的矛盾關系再次激化,達到極點。
尚之信的投吳完全是權宜之計,是維護尚氏家族在粵利益的無奈選擇,盡管尚之信因王位繼承問題對清廷難免有埋怨,但絕不會達到想要背叛的地步。[51]據《尚氏宗譜》載:
公念三朝重恩,五代榮寵,值此攻守維艱,救援莫待,以死報國,分所宜然,但死則廣省盡失,南方一帶皆為賊有,其勢愈熾,若乘風破浪,長驅四進,何以御之,況粵地千有余里,將來恢復非數萬之眾,數年之久不克,奏功是死,非報國適足,遺病于國也,吾心可對天日,安適虛名為哉!丙辰春,遂身攝王事,以丸疏入告,陽為順逆,實保地方,大兵一到,即便歸正,潛引將軍舒書率滿洲官兵入京,一無所損。馬雄疑公,立營三水肇慶,以窺公意。吳三桂屢咨公出兵,公于此時陽沉于酒,以安賊志,好為撫慰,內接軍心,逆以公為酒困,不足慮,故至八月,甫以稍緩,公即密差崇陽鍾、侯朔、張永祥、羅思哈等疊次請兵歸正。十月,王薨,公又遣使復奏,丁巳五月,大兵至界,公即率全省軍民迎歸,上嘉公忠誠,遂冊公襲平南親王。[52]
《尚氏宗譜》中的這段記述,是尚之隆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編修家譜時所載,很多人認為家譜中所載有“為親者諱”的嫌疑,不足為據。但筆者以為,這段記載盡管不免有溢美之意,但所傳達的尚之信對清廷絕無二心,暫時順逆只是為了替朝廷保護地方的信息,應是實情。清文字獄異常嚴苛,如非實情的話,尚之隆怎敢在康熙皇帝仍然健在的情況下,“為親者諱”呢?又,康熙十九年,在以“不忠不孝”的罪名殺掉尚之信之后,玄燁特行密諭在廣東善后的宜昌阿等:“尚之信雖經犯法,伊等妻子不可令卑賤小人凌辱,應查明嚴禁,遣人護送來京”。[53]“壬午年,康熙四十一年,上廉知公貞誠,特旨賜公妻子歸宗完聚,仍賜田房奴仆,服役養贍,公有未婚女五人,皆特恩擇配”。[54]這些行為不難看出,精明如康熙者,對尚之信及尚家在“三藩之亂”期間的立場與態度,是心中有數的。
尚之信被迫投降之后,“陽為順逆,實保地方……陽沉于酒,以安賊志,好為撫慰,內接軍心,逆以公為酒困,不足慮,故至八月,甫以稍緩,公即密差崇陽鍾、侯朔、張永祥、羅思哈等疊次請兵歸正”。可以推測,最晚到康熙十五年(1676)八月尚之信遣人請兵反正之時,尚氏父子已達成和解,畢竟家人父子,在金光等人已死,國與家已到存亡危急的關鍵時刻,尚可喜最終理解了尚之信的“順逆”行為,父子之間多年的誤會隔膜也冰釋解除。這年九月,尚氏父子接待了傅弘烈。據后來傅弘烈上給康熙的《陳合謀滅賊情形疏》中言:
于康熙十五年八月自梧州起身,九月初七日抵三水縣,親同安達公臣尚之信商酌,此時平南老王病重尚存,安達公引臣見,平南老王呼臣坐床上,牽臣手曰:我脾氣已壞,不能生矣,清朝恩深難報,兵變至此光景,爾與我大兒子同心協力,殺卻馬雄,取了肇慶,以通廣東廣西咽喉,然后披剃,將兩粵復還朝廷,我死亦瞑目,感激汝矣。囑畢付臣綢緞杯壺多種為記,臣痛哭而出。安達公與臣決謀合兵進取肇慶,擒斬馬雄,剃頭上疏,然后平定惠潮。[55]
尚可喜死于康熙十五年十月,可見在去世之前,老王終歸完全諒解了自己的兒子,將恢復兩廣的重任寄托在大兒子身上。可喜“遺命以本朝冠服殮”。[56]至清朝“大軍入粵時,啟可喜棺,冠服皆尊國制”。[57]看來,尚之信的確遵循了父親的遺命,這一方面表明尚之信與父親相同,認同清朝政權,對滿清忠心不二,另一方面也進一步證實了父子關系的最終和解。
注釋:
[1]《清圣祖仁皇帝實錄》卷九十九·康熙二十年十二月癸巳條
[2]薛瑞錄:《尚之信叛清投吳確鑿無疑——與李治亭同志商榷》、《關于尚之信叛清的幾個問題》、《三藩亂首尚之信傳》,載《清史文苑》,沈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12年;劉鳳云:《清代三藩研究》,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年。
[3]吳伯婭:《傅弘烈與尚之信——兼論康熙的平藩策略》,《清史論叢》,1993年號;李治亭:《〈尚氏宗譜〉與尚可喜研究》、《〈尚氏宗譜〉與三藩史實考辨》,載《微言集:明清史考辨》,沈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12年;滕紹箴:《三藩史略》(上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趙梓淞:《三藩之亂中尚之信立場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北京:中央民族大學,2009年。
[4]如官修《平定三逆方略》、魏源《圣武記》、王鉞《水西紀略》、鈕琇《觚剩》、顧公燮《丹午筆記》、樊封《南海百詠續編》等,均有雷同記載。
[5]吳伯婭:《關于康熙平定三藩的幾個問題》,《清史論叢》,1992年號;姚念慈:《康熙盛世與帝王心術——評“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第28—70頁。
[6](清)王鉞:《水西紀略》,載《世德堂文集》,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康熙40年刻本。
[7](清)佚名著《吳耿尚孔四王全傳》,《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六輯),臺灣大通書局印行,第23頁。
[8](清)王鉞:《水西紀略》
[9](清)釋今釋編《平南王元功垂范》卷下,清乾隆三十年刻本,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68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第225頁。
[10][11](民國)尚其憲:《尚氏宗譜》卷二·大房,民國29年(1940)修,國圖;遼寧海城縣檔案館。
[12](清)釋今釋編《平南王元功垂范》,第196頁、273頁、314頁、318頁。
[13]趙梓淞:《三藩之亂中尚之信立場研究》
[14]滕紹箴:《三藩史略》(下卷),第861—868頁;劉小萌:《清皇室與三藩“額駙”》,《滿族研究》2002年第3期。
[15](清)釋今釋編《平南王元功垂范》卷下,第225頁。
[16][17][20][24][28][31][34][36][37][39][41][48](清)王鉞:《水西紀略》。
[18](清)鈕琇《觚剩》卷八,《粵觚下·俺達縱暴》,載《筆記小說大觀》第17冊,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57頁。
[19](清)鈕琇《觚剩》卷八,《粵觚下·跛金》,第58頁。
[21](清)佚名著《吳耿尚孔四王全傳》,第23頁。
[22](清)王沄:《漫游雜記》卷三《粵游》,載《筆記小說大觀》第17冊,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11頁。
[23](清)王沄:《漫游雜記》卷三《粵游》,第17頁。
[25](清)樊封:《南海百詠續編》,影印本,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第109頁。
[26](清)鈕琇《觚剩》卷八,《粵觚下·跛金》,第58頁。
[27]樊封:《南海百詠續編》,載黃佛頤著,仇江、鄭力民、遲以武點注:《廣州城坊志》,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8頁。
[29]據王鉞《水西紀略》載:“每有事言之王,王不應,輒呶呶出不遜言,王怒甚”。
[30]趙梓淞:《三藩之亂中尚之信立場研究》。
[32](清)魏源《圣武記》卷二·藩鎮·康熙勘定三藩記(下)。
[33](清)勒德洪等:《平定三逆方略》卷一,第4頁。
[35]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卷五·尚之孝傳,第307頁。
[38](清)魏源《圣武記》卷二,藩鎮·康熙勘定三藩記(下)。
[40]《清圣祖仁皇帝實錄》卷四十八·康熙十三年(1674)六月戊辰條。
[42]楊益茂:《尚之信案辨析》,中華文史網,《清史參考》,2016年第3期。
[43][52][54](民國)尚其憲:《尚氏宗譜》卷二·大房。
[44][57](清)魏源:《圣武記》卷二,藩鎮·康熙勘定三藩記(下)。
[45]趙爾巽主編:《清史稿》卷四百七十四·列傳二百六十一·尚之信傳。
[46](清)鈕琇:《觚剩》卷八,《粵觚下·跛金》,第58頁。
[47](清)陳舜系撰:《亂離見聞錄》卷下,載李龍潛等點校:《明清廣東稀見筆記七種》,第43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
[49](清)佚名著:《吳耿尚孔四王全傳》,第24頁。
[50]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卷七十八,《尚可喜傳》,第6442頁。
[51]滕紹箴:《三藩史略》(下卷),第1116—1122頁。
[53]《清圣祖仁皇帝實錄》卷九十一·康熙十九年(1680)八月丙戌條。
[55](清)傅弘烈撰:《傅忠毅公全集》卷一,《陳合謀滅賊情形疏》,載清代詩文集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匯編》八二,第651—653頁,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56](清)佚名著《吳耿尚孔四王全傳》,第24頁。
(作者是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