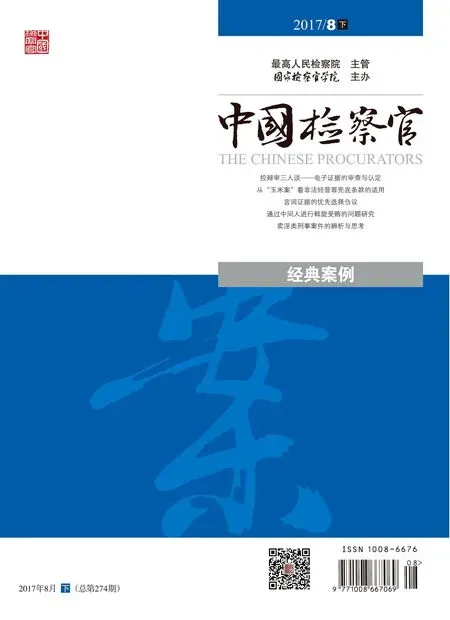試析聚眾斗毆罪的犯罪主體
文◎王明江
試析聚眾斗毆罪的犯罪主體
文◎王明江*
聚眾斗毆犯罪的客體是公共秩序和人身權利雙重客體,其犯罪構成應包含“聚眾”、“斗毆”兩個要件,但在司法實踐中,往往對“聚眾”要件的適用產生分歧。本文通過司法實踐中的真實案例,站在該罪客體的角度,重新定位認識犯罪主體在確定行為性質方面的意義,以期運用刑法理論,為統一司法適用有所裨益。
聚眾斗毆 犯罪主體 尋釁滋事 不足三人一方
[基本案情]2016年8月,甲因與其前女友秦某的感情糾紛,與秦某的現任丈夫A在電話中發生激烈爭吵,并在電話中相互威脅要弄死對方。之后,甲購買了一把折疊刀,并帶著秦某,邀約了乙一起前去找A解決問題,在等待A到來過程中,乙受甲的要求去買了一根金屬軟水管;之后,A邀約了B、C、D等共10人徒手前往約定的地點找到了甲、乙及秦某。雙方見面后,甲先是與A爭吵,B見狀后,動手毆打了甲背后一拳,A一方人員遂對甲圍毆,乙持水管毆打A一方人員,F、G等人遂與乙互毆。此時,甲被圍毆后遂拿出先前準備的折疊刀,亂捅圍毆的人員,將C捅傷并追趕C,D、E等人見狀上前欲控制持刀捅人的甲,甲反身將D捅傷,之后甲被A、D、E等人控制。經鑒定,C、D損傷程度屬重傷。[1]
一、爭議焦點及分歧意見
本案中,甲因感情糾紛邀約了乙前往與A解決問題,A得知甲意圖后遂邀約了B、C、D等人趕至現場,后雙方言語不和遂發生斗毆。因A一方聚集人數已達三人,且均參與打架斗毆,對A一方所有人員定性為聚眾斗毆是沒有爭議的;但甲、乙一方僅二人,他們參與打架斗毆的行為是否符合聚眾斗毆犯罪構成要件,存在著如下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甲、乙二人聚集人數不足三人,不符合聚眾斗毆罪之“聚眾”要件,不應成立聚眾斗毆罪,但甲、乙二人基于發泄情緒、逞強耍橫的動機,無故毆打他人,其行為構成尋釁滋事罪的共同犯罪,甲因實行過限,單獨認定為故意傷害罪。
第二種意見在承認第一種意見不構成聚眾斗毆罪的前提下,認為甲、乙二人相約毆打他人,致人重傷,應成立故意傷害罪的共同犯罪,但乙在共同犯罪中起輔助作用,可認定為從犯。
第三種意見認為:甲、乙一方雖不足三人,但明確與對方相約斗毆,雙方中一方已達三人的情況下,應對整體人數進行評價,故甲、乙二人仍應成立聚眾斗毆罪的共同犯罪。
上述三種意見的爭議焦點在于對聚眾斗毆罪之犯罪主體的理解,筆者贊同第一種意見,第二種意見在定性方面缺乏對犯罪主觀方面的考量,本文不另作討論,第三種意見對犯罪主體認識不清,有違罪責自負的原則。
二、刑法理論一般分析
按照我國刑法傳統的四要件理論,犯罪構成包含犯罪主體、客體、主觀方面和客觀方面,根據此理論推導,對案件的分析與運用大陸法系之“三階層”刑法理論得出的結論,一般是具有一致性的。本文作者擬以傳統四要件理論為基礎,借鑒“三階層”在入罪、出罪方面的邏輯性,站在犯罪客體的角度,重新認識犯罪主體的意義,以期解決對“聚眾”犯罪的法律適用爭議問題。
(一)一般犯罪主體認定的意義
法律關系的主體“人”分為自然人和法人,刑事法律關系領域,犯罪主體的規定是自然人和單位,這里的單位一般可理解為法人,單位犯罪由分則明文規定,本文不作討論,以下討論的犯罪主體均指自然人。定義犯罪主體的意義在于確定刑事責任的承擔者,即對造成法益侵害的行為人科以何種罪行并以此承擔相應責任。在一般情況下,對于大部分非必要共同犯罪而言,犯罪主體一般等同于單個行為人自身,此時定罪中的犯罪主體與量刑中的行為人具有一致性,確定行為人最終承擔之責時,進一步考量其責任能力、量刑情節等因素即可。但在諸如聚眾犯罪情形下,筆者認為有必要對犯罪主體在定罪與確定罪責方面加以區分,以期更好地貫徹對單個行為人適用法律罪責刑相一致的原則。
(二)聚眾犯罪主體的認定意義
聚眾犯罪首先是一種必要的特殊共同犯罪,認識一般必要共同犯罪主體的“共同性”,對厘清認定“聚眾”共同犯罪主體之標準具有重要的意義。
1.共同犯罪中“共同性”的一般理解。刑法條文規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這種共同性主要體現在不同行為人基于共同的故意,針對同一法益實施了共同的侵害行為。
2.“共同性”中的“一致性”是區分行為人之責的標準。根據上述共同犯罪的基礎理論,對于一般犯罪而言,基本能夠解決司法實踐中復雜的情形,但對于聚眾型犯罪而言,比如本文討論的“聚眾斗毆罪”,機械運用上述理論則會出現如前所述中關于甲、乙定罪量刑的分歧意見。按照唯物辯證法的觀點,矛盾既是統一的,又是對立的。筆者認為,對共同犯罪中“共同性”內涵的理解,也是存在兩方面的,即意思、行為的“一致性”和“非一致性”。“一致性”體現為意思上的鼓勵支持,行為上的協作配合,“非一致性”體現為意思上的對抗,行為上的獨立和沖突。一般而言,行為人之間存在“一致性”是成立同種性質的犯罪前提,而“非一致性”則往往會導致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結果。如,甲販賣毒品給乙(少量毒品用于吸食),甲的意思和行為體現為“賣”,乙的意思和行為體現為 “買”,從交易習慣角度來看,“買賣”這兩個單獨的行為是具有承繼、配合一致性,但法律何以認為“買毒品”不能一并作為販賣毒品的共同犯罪處理,究其原因即是站在刑法所保護法益之毒品管理角度來看,“買賣”是獨立的兩個行為,不具有共同犯罪的一致性,因而也就不能作為同性質的共同犯罪處理。由此可見,對一致性與非一致性的理解,應站在具體法益的角度考量,站位不同,意思和行為之間的共同性可能既體現出一致性,又體現出非一致性。而這種一致性,對于我們確定行為人行為性質是具有標準意義的。
3.聚眾斗毆罪中“一致性”的體現。根據上述理論分析,首先,我們考量聚眾斗毆罪所保護的法益。雖然聚眾斗毆犯罪規定于刑法分則第六章第一節擾亂公共秩序罪,所保護的法益主要是公共秩序,但從其條文表述上來看,該罪仍然保護公民個人的人身權法益,即公共秩序和人身權益。其次,站在兩種法益角度單獨考量。從法益之公民人身權益的角度來看,斗毆雙方行為人的“一致性”體現在單方各行為人內部的協作配合;從法益之公共秩序的角度來看,斗毆雙方行為人的“一致性”又體現在通過雙方各自互相傷害的行為共同破壞公共秩序。最后,我們可以看出,聚眾斗毆罪不論是站在何種法益的角度觀察,其立足點均為具有對立利益訴求的“一方”或“雙方”,而非一般犯罪以單個人為出發點,即評價該罪犯罪主體時不再是以單個的行為人,而應當是行為人的一個集合為出發點,換言之是臨時結成的團伙或基于某種目的糾集的集團,均要求三人以上,才能被認定為該罪的行為主體,也即在確定行為人行為性質之時,應當將這一個“多人集合”確定為行為主體,以此有利于打擊行為人出于私仇、爭霸或者其他不正當目的而成伙結幫地毆斗,公然藐視法紀和社會公德,破壞公共秩序。
4.聚眾斗毆犯罪主體認定辨析。通說認為,“聚眾”之“眾”指三人以上,這在理論和司法實踐中得以認可,但對聚眾的理解則存在難以統一的分歧,即本文討論的未聚集到三人一方的行為人是否承擔聚眾斗毆罪之責。筆者認為,這個問題的焦點就在于如何認定該罪的主體,主體確定之后,承擔罪責就有了依據。
(1)“聚眾”應當理解為單方所為之行為,即該單方完成“聚眾”行為后,所聚集人數這個集合認定為符合聚眾斗毆罪之主體要件。斗毆雙方的“聚眾”,要求斗毆雙方至少一方人數為三人以上,雙方人數均為三人以上,還是雙方總人數三人以上,目前理論界尚未有明確的結論,司法實踐中則要求至少一方人數為三人以上,才可能符合本罪的構成要件,即在司法實踐中對于雙方均僅二人的情形,是不能認定為聚眾斗毆罪的,但當一方已達三人之后,對另一方不足三人的情況下,對該不足三人一方認定為聚眾斗毆即產生分歧,這也是本文所要討論的焦點所在。筆者基于前述分析,認為從“行為人集合”為基本單位考量犯罪主體角度出發,聚眾斗毆罪所要求的犯罪主體不再是一般犯罪主體可以等同于單個行為人的概念,而應該是一個行為人集合的概念,故筆者認為,聚眾斗毆罪中的“聚眾”要件,只有成就己方人數已聚集達三人以上之時,方符合“聚眾”之要件,以此符合該罪犯罪主體對于行為定性的要求。
(2)聚集人數不足三人的一方,不符合該罪“聚眾”要件,即不符合聚眾斗毆罪之主體要件。司法實踐中,當存在一方人數不足三人與另一方人數已達三人進行斗毆之時,如何評價行為各行為人責任,理論界爭議較大,兩高未出臺相應的司法解釋,各地司法機關[2]出臺的指導意見不一。誠如上所說,各地司法機關對“一方已達三人的情況下,就不足三人一方是否構成本罪”,主要存在兩種意見:有條件構成和一律不構成本罪。如江蘇省司法機關出臺的文件[3]認為:“雙方均有互毆的故意,斗毆時一方達三人以上,一方不到三人的,對達三人以上的一方可以認定為聚眾斗毆,對不到三人的一方,如果有聚眾行為的,也可以聚眾斗毆罪論處,如果沒有聚眾行為的,不以聚眾斗毆罪論處,構成其他罪的,以其他罪論處。”上海市司法機關出臺的文件[4]則認為:“雙方基于不法動機相互斗毆,但僅一方超過三人的,該方可以構成聚眾斗毆犯罪,另一方不構成本罪,構成其他犯罪的,依法處理。”天津市司法機關出臺的文件意見與上海市的意見一致。導致上述產生較大分歧的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是對犯罪構成之犯罪主體在本罪的認識上產生了標準二元性。筆者基于前述對“共同性”的分析得出,在聚眾斗毆犯罪中,犯罪主體的認識應立足于該罪中各行為人所形成的集合,考量的首先是一方和另一方的人員組成的集合,對達三人以上的一方,在司法實踐中對其認定為符合聚眾斗毆罪的主體是沒有爭議的;對不足三人一方,認定該方不具備“聚眾”要件是適宜的,因為如果認為不足三人一方也構成聚眾斗毆罪,則勢必認定該不足三人一方也符合“聚眾”要件,那么就不得不考量該“眾”從何而來,進一步解釋就只有從對方“借人”而來湊足本方之“眾”,這樣的解釋顯然是有違“罪責自負”的原則,更涉嫌在對犯罪主體評價時采雙重標準,即在否認雙方均二人斗毆時不構成聚眾斗毆罪的情形之下,又承認當一方三人之時,對該二人一方的人員也認定聚眾斗毆罪,這顯然是矛盾的。
通過上述的理論分析,在法律適用方面,筆者認為對本文案例的第一種意見處理是適當的,它嚴格按照法律條文的語義,對聚眾雙方的行為進行分別具體的評價,體現了罪責刑相一致的基本原則。
三、司法適用的價值選擇分析
就本文所討論的案例而言,所涉案人員均為20歲出頭的年輕小伙子,甲與其前女友秦某在四川已生育了兩個小孩,因性格不合一年前秦某離開了甲,兩個小孩由甲及其父母撫養。甲在重慶打工偶然得知秦某已在重慶結婚并生育一子滿月,甲心生不滿遂邀約了其四川老家的工友乙找到了秦某,甲通過秦某的電話與秦某的丈夫A發生了爭吵,并相互威脅要弄死對方,之后,甲與A便在電話里約定了地點解決問題。甲背著乙、秦某購買了折疊刀,并在約定地點等待A的過程中讓乙買了軟水管防身;A得知甲的來由后,遂糾結了其工作理發店的其他工作人員B、C、D等九人前往約定地點,后雙方打架約一分鐘,A一方人員重傷后雙方停止打架行為。就上述案件背景與各行為人行為的判斷,以樸素正義觀考察,除甲因造成了嚴重的后果應承擔最重的責任,A因糾集了多人承擔次重的責任外,其余如乙、B、C、D等人均應當承擔差別不大的較輕責任。
若按照本文上述第三種意見處理,甲、乙構成聚眾斗毆罪的共同犯罪,對乙而言,其手持金屬軟水管應認定為“持械”情節,根據法律規定[5],乙的行為法定刑則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B、C、D等人行為無加重情節,法定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誠如上述分析,本應對乙、B、C、D等人判處差別不大的刑罰時,但因法定刑的差別規定而無法實現,因此,第三種意見在司法實踐中的運用[6],是有違“罪責刑相適應”基本原則的。另外,我們還可以假設A僅邀約了B一人前來與甲、乙打架,其余情節均相同的情況下,對乙的定性也必然發生改變,就此對乙而言,豈能因他人的行為來確定自己的責任?
按照本文上述第一種意見處理,則完全可以避免第三種意見適用的矛盾,甲、乙構成尋釁滋事罪的共同犯罪,對乙而言,根據法律規定[7],其法定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B、C、D等人的法定刑仍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故對乙、B、C、D等人判處相差不大的刑罰是可以實現的。
四、結語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司法適用是法律實施的最后一關,公平公正的司法,努力讓人們在每一個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是我們司法實踐者追求的目標。本文以聚眾斗毆案的真實案例為基礎,通過理論的一般分析和司法實踐中所應堅持的價值選擇分析,認為聚眾斗毆罪的構成要件之主體要件,是應當從行為人集合的概念出發考量是否入罪,而在出罪、量刑處罰時再回歸到單個的行為人本身,以此來彰顯定罪與量刑之間的差別與聯系,以期準確適用法律。
注釋:
[1]該案源自2017年重慶市巴南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的蔣某某等人聚眾斗毆案。
[2]主要是上海、天津、江蘇、浙江等地的省級司法機關出臺的司法意見。
[3]《辦理聚眾斗毆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蘇高法〔2009〕56 號。
[4]《關于辦理聚眾斗毆犯罪案件的若干意見(二)》,滬高法〔2013〕377 號。
[5]《刑法》第 292 條第 1 款第(4)項規定,持械聚眾斗毆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6]重慶市巴南區人民法院對本案的判決即是乙構成聚眾斗毆罪(持械),從犯,判處有期徒刑1年10個月;B、C、D等人均構成聚眾斗毆罪,考量坦白或自首情節后,判處有期徒刑11個月、8個月(緩刑1年)不等。筆者認為該法院為了對乙處以較輕刑罰,單獨牽強對乙認定從犯,屬司法自由裁量權使用不當。
[7]《刑法》第293條尋釁滋事罪的基準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重慶市巴南區人民檢察院[401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