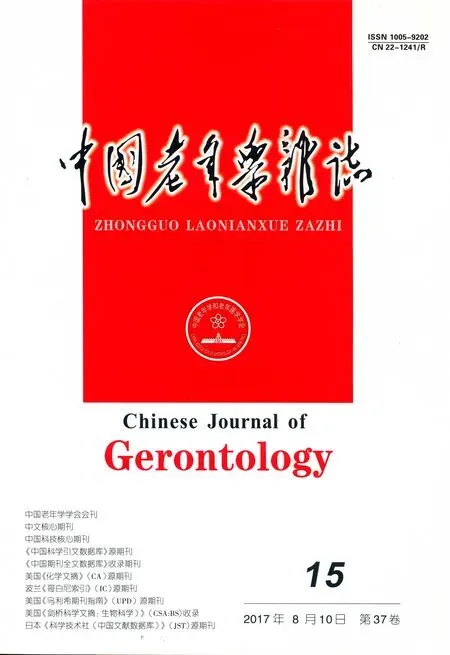肝臟活檢的臨床應用
何學學 孫 昱 屈 昊 荊 濤 萬泰虎 左 剛 季尚瑋
(延安市人民醫院感染科,陜西 延安 716000)
肝臟活檢的臨床應用
何學學 孫 昱1屈 昊2荊 濤1萬泰虎1左 剛1季尚瑋1
(延安市人民醫院感染科,陜西 延安 716000)
肝臟活檢;臨床應用
近年來肝臟活檢已成為臨床肝臟病學領域最常用的檢查技術,是臨床急、慢性肝病患者診斷、鑒別診斷及選擇治療方案的重要工具,是多種肝臟疾病診斷及疾病臨床療效評價的“金標準”,為各種肝臟疾病的預后和指導治療提供信息。肝臟活檢可用于膽汁淤積性肝病、藥物性肝損傷(DILI)、肝臟局灶性病變(FLLs)、不明原因肝功能異常及急性肝衰竭(ALF)、遺傳和代謝性疾病等診斷,還可用于慢性病毒性肝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自身免疫性肝病(AIH)的分期診斷和療效判定以及肝移植術后肝功能異常性質的判定。
1 膽汁淤積性肝病
膽汁淤積性肝病是各種原因引起的膽汁形成、分泌和/或排泄異常引起的肝臟疾病,分為肝內和肝外膽汁淤積。肝外膽汁淤積包括肝外膽管、肝總管及膽總管的梗阻,通過影像學可以確診;肝內膽汁淤積須通過多種影像學排除肝外膽汁淤積,并根據臨床癥狀、結合肝臟活檢作出正確診斷〔1〕。成人膽汁淤積性肝病包括肝細胞性和膽管細胞性膽汁淤積,通常經病史采集、體格檢查及相關輔助檢查,可作出診斷。對于無法解釋的肝內膽汁淤積且血清AMA抗體陰性者應考慮行肝臟活檢。兒童膽汁淤積性肝病中膽道閉鎖和Alagille綜合征是主要病因,新生兒膽汁淤積推薦行肝臟活檢,并應由有經驗的病理學專家進行診斷。膽道閉鎖的典型特征包括小膽管反應、膽小管膽栓、匯管區水腫和肝門纖維化。然而,疾病早期行肝臟活檢(6周齡前),上述特征不能完全出現,有可能需要再次行肝臟活檢或行術中膽管造影〔2〕。
2 DILI
DILI是最常見和最嚴重的藥物不良反應,是肝臟疾病高發病率和死亡率的一個重要病因,按發病機制可將DILI分為固有型DILI和特異質型DILI。固有型DILI具有可預測性,與藥物劑量密切相關,個體差異不顯著;特異質性DILI則為不可預測性,臨床較為常見,與藥物劑量常無明顯相關性,個體差異顯著,臨床表現多樣化,是引起急性肝衰竭和慢性肝損傷的主要病因〔3〕。DILI是一個排除性診斷,早期精確的診斷很重要,但具有挑戰性,且目前尚無特異性標志物〔4〕。當最初證明一種藥物是否為引起藥物性肝損傷的病因時,肝臟活檢是非常重要且必不可少的〔5〕。病理學家診斷DILI時將肝組織損傷模式進行明確分類,不僅可與臨床表現共同明確此次肝損傷的病因,而且還可直接確切評估肝損傷的嚴重程度,有助于指導臨床管理〔4〕。DILI損傷的靶細胞主要包括肝細胞、膽管上皮細胞及肝竇和肝內靜脈系統的血管內皮,損傷模式復雜多樣,與基礎肝病的組織學改變也會有相當多的重疊,故其病理變化幾乎涵蓋了肝臟病理改變的全部范疇。肝細胞型DILI在病理上可表現為急性小葉性肝炎、慢性小葉性肝炎及肝細胞脂肪變性等;膽管損傷型DILI在病理上可表現為單純毛細膽管淤膽,也可與肝細胞損傷同時存在而表現為混合型(包括淤膽性肝炎、混合性肝炎);而肝臟血管內皮細胞損傷可引起特發性門脈高壓癥、肝竇阻塞綜合征及肝小靜脈閉塞癥等。不同藥物可導致相同類型肝損傷,同一種藥物在不同個體也可導致不同類型的肝損傷〔3〕。但是,肝臟活檢在多種藥物與肝損傷之間的因果關系評價中的作用尚不明確〔5〕。在某些DILI病例,所用藥物與肝損傷類型相對固定,肝臟活檢可以揭示某些藥物的特異的組織學特點,如胺碘酮或丙戊酸鈉可引起脂肪性肝炎,硫唑嘌呤和6- 巰基鳥嘌呤可引起結節再生性增生〔6〕。當通過積極保肝治療而肝功能未見明顯好轉或懷疑存在DILI以外的其他診斷時需行肝臟活檢〔6〕。
3 FLLs
FLLs包括惡性肝臟病灶(肝細胞癌、膽管癌)、良性肝臟病灶(肝細胞腺瘤、血管瘤、局灶性結節增生、結節再生性增生)和囊性肝臟局灶性病變(單純性肝囊腫、膽管囊腺瘤、囊腺癌、多囊肝、包蟲病)〔7〕。準確的FLLs診斷需完整的病史、體格檢查、影像學檢查和病理組織學檢查,其中影像學檢查是FLLs診斷中最重要的環節〔7〕。影像學技術往往很容易通過特征性表現識別FLLs的性質,因而肝臟活檢通常不是必需的;但當影像學特征不典型時,行肝臟活檢則是必要的,肝臟病理組織學及免疫組織化學方法在診斷FLLs中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8〕。當肝硬化患者出現典型的影像學征象時通常可以做出肝細胞癌的診斷〔9〕,而當影像學表現不典型時,則應行肝臟活檢明確診斷。膽管癌患者如果不宜手術則應行肝臟活檢以便制定治療方案。對于影像學檢查無法明確診斷而肝臟活檢可確定治療方案的懷疑肝細胞腺瘤者,應行肝臟活檢。對于肝臟的結節再生性增生,一般病灶較小,在影像學上與肝硬化結節難以區分,需行肝臟活檢以鑒別。肝血管瘤及局灶性結節增生者,一般經CT或MRI即可明確診斷,故常規不推薦行肝臟活檢,但當局灶性結節增生與肝細胞腺瘤在影像學上難以區分時,由于在臨床處理方面二者完全不同,往往需要行肝臟活檢以明確診斷。對于無癥狀的單純肝囊腫、膽管囊腺瘤、囊腺癌及多囊肝、包蟲病而言,一般不建議行肝臟活檢〔7〕。肝臟活檢病理組織學可鑒別癌前病變(不典型增生結節)與早期肝癌,同時還可在形態學上對不典型的肝細胞癌進行診斷并指導預后〔10〕。但是,Venkatesh等〔8〕的研究發現,對于肝內較小的占位性病變而言,由于活檢難以準確定位,約有10%結果為假陰性。此外,肝臟活檢有造成癌腫種植轉移的風險,引起針道轉移的危險因素目前尚未明確,可能與腫瘤的大小及組織學分化程度〔11〕、穿刺針的類型、穿刺針的直徑、穿刺的次數和穿刺過程中隨帶正常組織細胞的數量有關,Jain〔10〕的研究建議使用同軸穿刺針可減少腫瘤播散的風險。
4 不明原因的肝功能異常及ALF
對于通過全面的病史采集、體格檢查、生化學、血清學以及影像學檢查后仍無法明確診斷的不明原因肝功能異常患者,肝臟活檢一直被認為是一種重要的診斷手段〔9〕。一項對354例不明原因肝功能異常患者行肝臟活檢的研究結果顯示,64%的患者診斷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其他還包括藥物性肝損傷、原發和繼發性膽汁性肝硬化、自身免疫性肝炎、酒精性肝病、原發性硬化性膽管炎、血色病、淀粉樣變性和糖原貯積癥,但仍有少數患者病因不明,6%的患者顯示肝臟組織學正常,而26%的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肝纖維化,6%的患者有肝硬化表現;18%的患者經肝臟活檢后改變了治療方案,3個家庭納入遺傳性肝臟疾病的篩查〔2〕。在確定不明原因的肝功能異常時,應仔細評估行肝臟活檢的利與弊,在全面無創檢查后仍不能確診時才應考慮行肝臟活檢。
同時,肝臟活檢可為ALF提供重要的臨床信息,可明確病因診斷及指導治療(如自身免疫性肝炎、Wilson病、傳染性肝炎或代謝障礙性疾病)〔12〕。然而不幸的是,許多ALF患者存在嚴重的凝血功能障礙,不宜行經皮肝穿刺活檢。我國2012年發布的《急性肝衰竭臨床指南》中推薦當通過病史采集或血清學檢查不能明確ALF的病因時,可考慮行經頸靜脈肝穿刺活檢。
5 遺傳和代謝性疾病
肝臟活檢有助于遺傳及代謝性肝臟疾病的診斷及鑒別診斷,如血色病、肝豆狀核變性(Wilson病)、糖原貯積癥、α- 1抗胰蛋白酶缺乏癥(A1AD)、囊性纖維化、進行性家族性肝內膽汁淤積綜合征、膽汁酸合成障礙等。但是,某些代謝性疾病,如囊性纖維化相關肝臟疾病(CFLD)損傷呈片狀分布,肝臟活檢可能會低估肝損傷的嚴重程度;13周齡以下嬰兒常規顯微鏡檢查法可能找不到特征性的嗜酸性小顆粒〔2〕。因此,相對于組織學改變而言,許多遺傳及代謝性疾病具有典型的血清表現型,肝臟活檢并不是這類疾病診斷所必需的。
6 慢性病毒性肝炎
慢性HBV感染可分為不同的疾病階段,即免疫耐受期、免疫清除期、非活動或低(非)復制期和再活動期。肝臟活檢對于判斷慢性乙型肝炎肝損傷嚴重程度和指導治療十分重要。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療的適應證主要基于血清HBV DNA水平、轉氨酶水平及組織學分級和分期〔13〕。對于HBV感染者而言,當其生化學/轉氨酶水平未達到各指南建議的抗病毒治療適應證時,了解其肝臟組織學改變則有助于指導治療方案的選擇〔9〕。Alam 等〔14〕通過對499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臟組織學和ALT與年齡和血清HBV DNA水平的相關性進行評價,結果顯示ALT水平與肝臟組織學活動指數(HAI)和纖維化程度呈明顯正相關,HBeAg陰性患者較HBeAg陽性患者HAI評分更高;年齡>30歲者HAI評分和纖維化分期明顯升高。因此,建議對HBeAg陰性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年齡>30歲者無論其ALT水平是否升高均推薦行肝臟活檢,以ALT>1.5×正常值上限(ULN)取代2×ULN作為抗病毒治療的指征。AASLD指南及APASL指南均建議ALT<2×ULN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當HBeAg陽性、血清HBV DNA定量≥20 000 IU/ml或HBeAg陰性、血清HBV DNA定量≥2 000 IU/ml時應行肝臟活檢,但二者對患者的年齡要求略有不同,AASLD指南建議>40歲,而APASL指南的推薦意見則更為積極,建議>35歲〔15,16〕,EASL指南對此未做詳細說明。同時,在抗病毒治療前后行肝臟活檢病理組織學比較還可了解長期抗病毒與組織學改善的關系。Papachrysos等〔17〕通過對50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在抗病毒治療前后行肝臟活檢病理組織學比較,結果發現經抗病毒治療后的肝臟組織學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
對于慢性丙型肝炎患者而言,只要血清中HCV RNA可測,不論ALT水平如何,均應行抗病毒治療以延緩其疾病進展,無需通過肝臟活檢指導抗病毒治療。但是,肝臟活檢到目前為止仍被認為是慢性丙型肝炎患者治療前初始評價的關鍵部分,而且病理組織學是評價抗病毒療效的“金標準”〔18〕。Mitchell等〔19〕通過對348例慢性丙型肝炎患者在抗病毒治療前后行肝臟活檢病理組織學比較,結果發現112例獲得持續病毒學應答的患者肝臟炎癥和纖維化均得到明顯改善。
7 NAFLD
NAFLD與肥胖和胰島素抵抗相關聯,被認為是代謝綜合征在肝臟的表現,主要是甘油三酯在肝細胞內堆積所致〔20〕。NAFLD包含一系列的病變,從良性脂肪變性到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肝纖維化、肝硬化和肝細胞癌〔21〕。影像學檢查雖然對分析肝臟脂肪變性(尤其是中度至重度脂肪變性)非常敏感,但卻不能區分單純性脂肪肝和脂肪性肝炎,也很難衡量肝纖維化的程度〔22〕,而肝臟活檢不僅可明確NAFLD的診斷,還可評價肝纖維化的程度和范圍。目前,肝臟活檢是診斷NAFLD、評估NAFLD的嚴重程度和肝纖維化分期的金標準,是目前唯一能夠在形態學上區分單純性脂肪肝和脂肪性肝炎的手段〔20〕。Vuppalanchi等〔21〕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肝臟活檢標本的長度與NASH的診斷率呈正相關,活檢標本長度<10 mm者診斷率為29%,而≥25mm者診斷率則達65%。
8 AIH
自身免疫性肝病主要包括AIH、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PBC,原名為原發性膽汁性肝硬化)和原發性硬化性膽管炎(PSC),診斷主要基于臨床、生化、病理組織學和膽管的發現,同時需要仔細排除其他引起肝臟損傷的重要原因,包括酒精、病毒、藥物和毒素、遺傳代謝性疾病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等〔23〕。
對于AIH患者而言,肝臟活檢不僅對疾病診斷具有重要價值,對指導治療亦具有重要意義。當血清生化學、免疫學及臨床表現擬診為AIH時,需行肝臟活檢以明確診斷〔24〕。一旦確診后應及時給予免疫抑制劑治療,治療的最佳持續時間目前尚不明確,當肝功能及血清IgG水平恢復至正常、自身抗體滴度明顯降低或消失以及肝臟組織炎癥修復時方可考慮停藥。因此,在考慮停止治療時建議行肝臟活檢〔2〕。
PBC的診斷須滿足下述三條中的兩條:(1)膽汁淤積的血清生化學證據;(2)血清AMA或AMA- M2陽性;(3)肝臟活檢顯示非化膿性破壞性膽管炎及小葉間膽管損傷。盡管肝臟活檢不是診斷PBC所必需,但約有5%- 10%的PBC患者血清AMA或AMA- M2陰性,此時PBC診斷需行肝臟活檢〔25〕。
PSC的診斷主要基于膽管造影檢查,主要表現為膽管串珠樣、不規則及狹窄改變;無創MRCP對成人PSC診斷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分別為86%和94%。因此,肝臟活檢作為一項有創性檢查,用于PSC的診斷是非必須的〔2〕;但約有5%的PSC患者為小膽管型PSC,病變僅累及肝內小膽管,膽道影像學檢查無明顯異常發現,肝臟組織學檢查對于診斷膽道影像學正常的小膽管型PSC則是必需的〔26〕。
9 肝移植術后肝功能異常性質的判定
肝移植后進行肝臟活檢和組織學評估是此類患者術后管理的一個基本方面。針對肝移植術后肝功能異常,通過肝臟病理組織學改變判斷是同種異體移植物排斥反應、移植術后缺血再灌注損傷、膽管損傷或阻塞、病毒感染、原發疾病復發還是藥物性肝損傷,從而做出特異性診斷是至關重要的〔9〕。同時,免疫抑制治療作為肝移植的輔助治療,肝臟活檢還可用于指導何時停用免疫抑制劑。
Bedossa等〔27〕提出“Liver biopsy:The best,not the gold standard”。雖然肝臟活檢是多種肝臟疾病診斷、鑒別診斷及治療效果評價的“金標準”,但肝臟活檢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為肝臟活檢標本僅代表于整個肝臟組織的1/50 000〔2〕,且標本取材、病理組織學圖像及觀察者間等均存在差異性,均可影響肝臟病理組織學的診斷等。同時,肝臟活檢是侵入性操作,需留院觀察數小時。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非侵入性標志物(NIM)廣泛應用于臨床,包括血清學標志物檢查〔如纖維化指數、APRI指數(AST/血小板計數)、纖維化評分及PGAA指數等(如α2- 巨球蛋白、γ- GT、載脂蛋白A1、凝血酶原時間等)〕和多種影像學檢查手段方法(如Fibroscan、Fibrotest等)。
總之,自19世紀末以來,利用肝臟活檢病理組織學檢查得出精確的診斷,正確地將肝臟活檢與非侵入性標志物相結合,更有益于各種肝臟疾病的診斷、預后和指導治療。
10 參考文獻
1 Cholongitas E,Burroughs AK,Dhillon AP.Evidence- based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J〕.Third Edition,2010;46:762- 70.
2 Ovchinsky N,Moreira RK,Lefkowitch JH,etal.The liver Biopsy in modern clinical practice:a pediatric point- of- view〔J〕.Adv Anat Pathol,2012;19(4):250- 62.
3 中華醫學會肝病學分會.藥物性肝損傷診治指南解讀〔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15- 9.
4 Kleiner DE,Chalasani NP,Lee WM,etal.Hepatic histological findings in suspected drug- induced liver injury:systematic evaluation and clinical associations〔J〕.Hepatology,2014;59:661- 70.
5 Fontana RJ,Seeff LB,Andrade RJ.Standardization of nomenclature and causality assessment in drug- induced liver injury summary of a clinical research workshop〔J〕.Hepatology,2010;52(2):730- 42.
6 Khoury T,Rmeileh AA,Yosha L,etal.Drug induced liver injury review with a focus on genetic factors,tissue diagnosis,and treatment options〔J〕.J Clin Translat Hepatol,2015;3:99- 108.
7 Marrero JA,Ahn J.K Rajender reddy on behalf of the practice parameters committee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gastroenterology.ACG clinical guideline: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focal liver lesion〔J〕.Am J Gastroenterol,2014;109(9):1328- 47.
8 Venkatesh SK,Chandan V,Roberts LR.Liver masses:a clinical,rad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perspective for:perspectives in clinical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J〕.Clin Gastroenterol Hepatol,2014;12(9):1414- 29.
9 Fox AN,Jeffers LJ,Reddy KR.Liver biopsy and laparoscopy.schiff′s diseases of the liver〔J〕.Eleventh Edition,2012;3:44- 57.
10 Jain D.Tissue Diagno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J Clin Exp Hepatol,2014;4(S3):S67- S73.
11 Ahn DW,Shim JH,Yoon JH,etal.Treatment and clinical outcome of needle- track seeding from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the Korean〔J〕.J Hepatol,2011;17:106- 12.
12 Lee WM,Larson AM,Stravitz RT.AASLD position paper:the management of acute liver failure:Update 2011〔J〕.Hepatology,2011;54(9):1- 22.
13 Gobel T,Erhardt A,Herwig M.High prevalence of significant liver fibrosis and cirrhosis in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with normal ALT in central europe〔J〕.J Med Virol,2011;83:968- 73.
14 Alam S,Ahmad N,Mustafa G,etal.Evaluation of normal or minimally elevated alanine transaminase,age and DNA level in predicting liver histological changes in chronic hepatitis B〔J〕.Liver Int,2011;31(6):824- 30.
15 Lok ASE,McMahon BJ.Chronic Hepatitis B:update 2009〔J〕.Hepatology,2009;50(3):1- 35.
16 Sarin SK,Kumr M,Lau GK,etal.Asian- Pacific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on the management of hepatitis B:a 2015 update〔J〕.Hepatol Int,2016;10(1):1- 98.
17 Papachrysos N,Hytiroglou P,Papalavrentios L,etal.Antiviral therapy leads to histological improvement of HBeAg- negative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J〕.Ann Gastroenterol,2015;28:374- 8.
18 Puoti C,Guarisco R,Spilabotti L,etal.Should we treat HCV carriers with normal ALT levels?The′5Ws′dilemma〔J〕.J Viral Hepatitis,2012;19:229- 35.
19 Shiffman ML,Sterling RK,Contos M,etal.Long term changes in liver biopsy following treatment of chronic hepatitis C virus〔J〕.Ann Hepatol,2014;13(4):340- 9.
20 Mazhar SM,Shiehmortza M,Sirlin CB.Noninvasive assessment of hepatic steatosis〔J〕.Clin Gastroenterol H,2009;7:135- 40.
21 Vuppalanchi R,Unalp A,Vannatta ML,etal.Effects of liver biopsy sample length and number of readings on sampling variability in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J〕.Clin gastroenterol H,2009;7:481- 6.
22 Karim MF,AI- Mahtab M,Rahman S,etal.Non- 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 A Review〔J〕.Mymensingh Med J,2015;24(4):873- 80 .
23 Rust C,Beuers U.Overlap syndrome among autoimmune liver disease〔J〕.World J Gastroenterol,2008;14(21):3368- 73.
24 Green KR,Willis R,Nathlee McMorris J,etal.Autoimmune hepatitis in a Jamacian cohort spanning 40 years〔J〕.Human Antibodies,2013;22:87- 93.
25 Purohit T,Cappell MS.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pathophysioloqy,clinical presentation and therapy〔J〕.World J Hepatol,2015;7(7):926- 41.
26 中華醫學會肝病學分會,中華醫學會消化病學分會,中華醫學會感染病學分會.原發性硬化性膽管炎診斷和治療專家共識(2015)〔J〕.臨床肝膽病雜志,2016;32(1):23- 31.
27 Bedossa P,Dargere D,Paradis V.Sampling variability of liver fibrosis in chronic hepatitis C〔J〕.Hepatology,2003;38:1449- 57.
〔2016- 07- 27修回〕
(編輯 滕欣航)
吉林省衛計委重點實驗室項目(2011Z027);吉林大學基本科研業務經費項目(450060445245)
季尚瑋(1973- ),女,副教授、副主任醫師,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肝臟疾病診治研究。
何學學(1989- ),女,碩士,主要從事肝臟疾病診治研究。
R575
A
1005- 9202(2017)15- 3882- 04;
10.3969/j.issn.1005- 9202.2017.15.107
1 吉林大學中日聯誼醫院 2 吉林大學醫學部臨床醫學七年制2011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