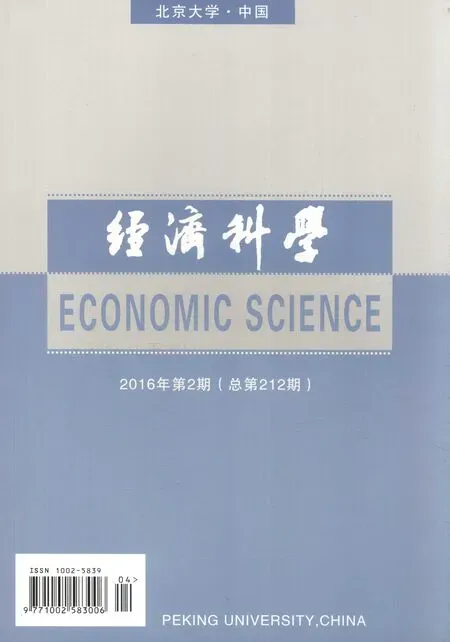企業何時選擇平衡創新模式有利于績效提升?*
陳建勛 馬薈瑩
?
企業何時選擇平衡創新模式有利于績效提升?*
陳建勛1馬薈瑩2
(1.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 北京 100029) (2. 中國航空規劃設計研究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 北京 100120)
本文從平衡的角度探討了企業選擇平衡創新模式對其績效的系統影響效應,以及其影響效應在什么條件下存在差異。基于制度理論,從企業對制度的被動遵從和主動響應兩個方面入手,本文對所提理論檢驗后發現:企業選擇平衡創新模式對其績效提升具有微弱顯著的正向作用,組織復雜化在平衡創新模式與企業績效間起著倒U型調節作用,而組織集權化在兩者之間的調節作用則不顯著。在高管團隊戰略柔性高的條件下,平衡創新模式對企業績效提升的作用進一步增強。
平衡創新模式組織集權化組織復雜化高管團隊戰略柔性
一、引 言
作為技術創新的主體,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與國家創新能力的建設密切相關。從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實踐來看,歐美大型跨國公司每年投入高達數十億美元用于支持其研發機構和技術團隊的創新實踐,以保持企業旺盛的創新活力和市場競爭力。與大型跨國公司相比,我國企業的技術創新現狀卻不容樂觀。一方面,中國企業創新投入偏低,據統計,2011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發經費支出為5 994億元,僅占主營業務收入的0.71%,而歐美發達國家這一比例一般介于2.5%~4%;另一方面,我國企業研發經費的64%用于現有產品和技術的改造,而只有24%用于新產品和新技術開發的研究。以上數據不僅反映了我國企業在研發投入上的不足,而且在技術開發和改造上呈現不平衡特征,存在資源投入錯位和缺位的問題,這導致了創新資源投入的低效,削弱了技術創新的成效。
針對以上問題,理論界呼吁企業應加強對創新過程和創新行為平衡性的管理,選擇一種平衡創新模式,尤其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實現資源在不同創新行為之間的合理配置以實現創新的平衡性,對于提升企業績效具有積極意義(Cao et al., 2009;Patel et al., 2013)。但是,現有文獻存在兩種不同的研究結論,如He和Wong(2004)的研究表明平衡創新模式有利于企業績效提升,而Cao等人(2009)的研究結果則發現這種影響效應并不顯著。基于此,一個可能的理論拓展方向是探討在企業實現創新平衡性的過程中受到許多因素的制約或調節,在什么樣的條件下企業選擇平衡創新模式有利于績效提升,而在什么條件下則對績效提升的作用不顯著?也就是說,平衡創新模式的作用邊界條件是什么,現有文獻對該問題的研究仍比較有限。圍繞該研究問題,本文以制度理論作為理論基礎,從企業對制度的被動遵從和主動響應兩個方面,探討了企業遵從不同的組織制度安排下以及高管團隊具備響應制度變化的不同戰略柔性條件下,企業選擇平衡創新模式對績效提升的差異化影響效應。
二、理論基礎與假設推演
(一)理論基礎
制度理論認為,制度通過為企業設定具體的條件和標準,會激勵或限制企業的選擇和行為(Scott,2008)。企業為了獲得所需要的資源,往往遵從制度所設定的規范和標準,表現出一定的制度合法性,從而達到企業與制度間的相互匹配和適應(Meyer 和 Roman,1977;Scott, 2008)。組織制度是由多種制度安排耦合(Coupling)而成,耦合性是組織制度的效率源泉,因為單獨某項制度往往難以提升組織制度的效率,而組織制度之間的耦合,或者組織制度與組織其他經營要素(如組織資源、組織能力等)之間的耦合,才是組織制度的效率源泉(高照軍,武常岐,2014)。新制度理論認為,企業的出現本身就是一種節約交易成本和提升效率的制度設計與安排,企業制度又是由一系列具體的制度安排所構成,如分配制度、決策制度等。
企業對制度的反應類型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被動遵從型,這種企業往往遵從已有的制度安排與設計要求,服從相關的制度規范與標準,通過獲得合法性地位來獲取對企業有利的資源和能力。遵從制度規范和要求盡管有利于節約交易成本,但是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遵循制度規范和追求經濟效率往往會產生沖突,會對企業造成沖突的制度壓力;第二類是主動響應型,即在面臨制度要求和壓力時,企業采取具有象征意義與符號作用的“脫耦”行為(decoupling),表面上實施制度所規定的行為要求,但事實上對制度規范的某些行為進行動態調整與主動改進,在一定程度上緩和兩者沖突給企業帶來的挑戰(陳嘉文,姚小濤,2015)。企業的這種脫耦行為要求企業具備一定的戰略柔性和動態能力,借此能夠及時洞察制度要求的變化及動態調整企業的資源和能力,從而緩解遵從制度規范和追求經濟效率之間的沖突,降低制度對企業發展帶來的不確定性(陳嘉文,姚小濤,2015)。
綜上,基于制度理論,本文從企業對制度的被動遵從和主動響應兩個方面入手,嘗試探討企業實現創新平衡性的過程中制度所發揮的作用。具體而言,一方面,從被動遵從已有的制度安排(如集權化與復雜化的制度安排)下,企業選擇平衡創新模式對其績效會帶來什么差異化的影響效應;另一方面,從企業主動響應制度變化和沖突的角度出發,探討當高管團隊具備戰略柔性來動態應對制度變化,及其戰略柔性高低不同的條件下,企業采用平衡創新模式對其績效會帶來的怎樣不同的影響效應。
(二)文獻回顧
March(1991)基于資源有限性和組織作為平衡系統的潛在假設,從組織學習的角度提出企業存在兩種不同的創新行為,一種是探索新知識、發現新機會、開發新技術的探索式創新行為,另一類是對現有知識、技術和能力進行提煉和應用的利用式創新行為。由于這兩種創新行為對企業造成不同的張力,所需的資源訴求也不相同(Gupta et al., 2006;March, 1991)。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兩者分享和競爭企業的資源和能力,而作為決策者而言,將無可避免地要在兩種創新行為之間和資源配置決策間進行平衡。為便于表述,本文將平衡探索式和利用式創新行為的創新模式稱為平衡創新模式。
關于平衡創新模式能否提升企業績效,目前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企業實現創新的平衡性由于能夠規避創新風險和優化資源配置從而能夠提升績效,如He和Wong(2004)的實證研究表明,探索式和利用式技術創新行為之間的不平衡性不利于績效改善,從而建議企業應該保持創新的平衡性;Fernhaber和Patel(2012)的研究表明,平衡創新模式對于績效提升具有積極作用;Patel等人(2013)的研究進一步佐證了這個觀點;王建、胡瓏瑛、馬濤(2015)運用上市公司的數據,通過文本分析的方法,驗證了平衡創新模式對于績效提升的積極作用。
另外一種觀點認為,采用平衡創新模式需要企業具備很強的整合與矛盾管理能力,否則會因為過大的沖突以及溝通成本的提高而對企業績效帶來負向作用(Ghemawat和Costa,1993)。Cao等人(2009)的實證研究也表明,平衡創新模式對企業績效提升的作用并不顯著。針對這兩種不一致的研究結論,正如現有研究所指出的,在平衡創新模式影響企業績效的作用過程中,往往受到許多情境因素的調節或“干擾”。本文認為,企業遵從已有的組織制度安排和高管對制度變化的戰略柔性可以通過影響企業內部的資源配置過程和效率,進而影響到企業的經營績效。因此,企業選擇平衡創新模式不僅受到組織制度安排的限制和約束,而且還需要與高管戰略柔性保持匹配。
(三)假設推演
1. 平衡創新模式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效應
盡管現有文獻對平衡創新模式影響效應的研究結果存在分歧,但學者們并不否認其積極效應,即它可以幫助企業控制技術創新過程中的系統性與失衡性風險,降低技術創新的失敗率(Cao等人,2009;March,1991)。如果企業過多從事利用式而忽略探索式技術創新,由于路徑依賴的作用,將會使企業鎖定在無效或低效的狀態,因無法對未來環境做出及時調整而可能被市場競爭所淘汰;相反,當企業過分從事探索式而忽略利用式技術創新,則會增加企業技術創新的風險,使其陷入“創新陷阱”,形成“探索—失敗—無回報變革”的惡性循環,也不利于企業績效的提升。He和Wong(2004)的實證研究也發現,探索式和利用式技術創新之間的不平衡與銷售增長率負相關。據此,本文提出:
假設1:平衡創新模式對企業績效提升具有正向影響效應。
2. 組織集權化在平衡創新模式與企業績效之間關系的調節效應
企業技術創新的過程往往受到組織制度安排的規范和約束,尤其在進行資源配置過程中,組織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和規范資源配置的導向和優先順序,對于創新資源的分配效率具有重要影響。作為一種決策制度安排,集權化的組織制度是指組織在決策時,正式權力在管理層級中的集中化程度。權力高度集中在高層領導者,問題要由下至上逐層反映,并最終要由最高層決策時,代表集權化程度高的組織制度安排。反之,則代表集權化程度低的組織制度安排。
平衡創新模式涉及到資源的配置決策和執行過程,決策權所處的位置不同,導致“縱向”信息傳遞和權力整合的程度也不同,從而資源配置的效率和效果也不同。如果企業被動遵從集權化程度過高的組織制度安排,由于決策高度集中于高層管理者,容易導致企業內部各部門間的信息溝通鏈條加長及信息失真度提高,造成創新資源在不同部門間配置的缺位和錯位,進而導致探索式和利用式技術創新間的資源分配失衡而不利于企業績效的提升;如果企業被動遵從集權化過低的組織制度安排,由于決策權過度分散到各個部門和員工,導致探索式和利用式技術創新之間的整合難度加大,不利于企業在二者之間進行資源的有效整合和平衡,也不利于改善企業績效;而當企業遵從“松散的耦合”(loosely coupled)之適度集權化的組織制度安排,則能夠提高信息溝通的效率和質量,發揮基層員工在技術創新中的積極性和自主性,既降低了資源配置錯位的概率,又減輕了平衡兩種技術創新的整合難度,從而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陶厚永、劉洪和呂鴻江,2008)。據此,本文提出:
假設2:組織權化在平衡創新模式與企業績效之間起著倒U型調節作用。
3. 組織復雜化在平衡創新模式與企業績效之間關系的調節效應
實現創新平衡性的過程也是企業內部各部門和員工相互協作和配合的過程,企業的“橫向”協作制度安排也影響平衡創新模式效應的發揮。一般而言,在規模大,組織結構復雜的企業中,部門與員工之間的協作難度加大,合作成本提高。通常而言,規模大的企業具有較高的復雜性,因為它擁有的專業職能更多,可以完成更復雜的任務(呂鴻江、劉洪和程明,2008)。作為一種協作制度安排,復雜化的組織制度是指構成企業的不同元素和不同層次間相互作用并使組織整體表現出多樣性、變異性、動態性、不可預知性等的復雜特征(Damanpour,1996;呂鴻江、劉洪和程明,2008)。也就是說,一個企業的層級越多、分工越細,組織復雜化程度就越高。
如果企業被動遵從復雜化程度過高的組織制度安排,企業內部的合作和協調過程變得更為復雜,從而導致協作效率的的降低與交流成本的提高。這樣,約束企業行為的正式規則也會增多,從而降低企業對外部環境變化的反應能力。因此,在復雜化程度過高的組織制度安排下,探索式和利用式技術創新的效率會因為組織過度復雜而降低,無法有效處理兩種技術創新在資源需求上的沖突和矛盾,導致企業的創新資源管理的失衡性,不利于企業績效的提升;反之,如果企業被動遵從復雜化程度過低的組織制度安排,那么,組織職能結構和形態過于簡單,所掌控的資源有限,這時探索式和利用式技術創新對資源爭奪的沖突和矛盾更易凸顯,也不利于企業績效的提升;當企業遵從適度復雜化的組織制度安排,組織內部具有適中的多樣性、合理的管理層級和恰當的專業化分工,不僅可以提高探索式和利用式技術創新的效率,而且能夠有效化解二者在資源競爭上的沖突,從而通過實現技術創新的平衡發展來提升企業績效。據此,本文提出:
假設3:組織復雜化在平衡創新模式與企業績效之間起著倒U型調節作用。
4. 高管團隊戰略柔性在平衡創新模式與企業績效之間關系的調節效應
從企業對制度的主動響應方面來看,由于不同制度規范對企業造成的沖突的需求和壓力,為了保持制度遵從與效率追求之間的平衡性,企業需要具備適應制度變化的動態能力,也就是需要具備一定的戰略柔性。現有文獻目前對戰略柔性還未形成統一的定義,但其核心含義表示企業及時調整戰略以適應環境(包括制度環境)變化的能力(Roca-Puig et al., 2005)。企業的戰略決策通常由高管團隊來制定,對制度變化的主動響應往往通過高管團隊的戰略決策來進行實施,這樣,高管團隊應對制度變化的能力至關重要(Smith和Tushman, 2005),由此,高管團隊戰略柔性的概念應運而生,它代表高管團隊根據環境變化及時調整或改變戰略決策的能力。
企業在實現創新平衡性的過程中,往往要對相互沖突的技術需求以及制度規范造成的不同壓力進行主動響應和動態適應,這要求高管團隊能夠及時、動態的對這些需求做出響應并采取戰略措施。當高管團隊戰略柔性高時,創新過程中對企業造成的資源沖突的需求能夠更快被識別和發現,從而高管團隊能夠及時調整和改變戰略決策來更快的化解資源配置上的沖突,通過及時的調整資源配置方案來實現資源在探索式和利用式技術創新之間的平衡,進而通過控制創新風險來降低創新失敗的概率,減少企業損失,提高企業績效。據此,本文提出:
假設4:高管團隊戰略柔性在平衡創新模式與企業績效之間起著正向調節作用。
三、研究方法與變量測量
(一)數據來源與研究樣本
本文采用問卷調查的方式收集數據。樣本企業依據以下原則篩選:須處于競爭性而非壟斷性的產業;須具備獨立的法人資格和完整的經營實體而非分支機構;須具備一定的年限和規模。基于以上原則,參考Jansen等人(2006)在研究創新能力時的樣本選擇標準,本文選擇年限大于3年,規模不少于100人的企業作為樣本,這是因為技術創新能力的培養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技術投資和能力積累,小微企業在起步階段往往難以積累大量的資金從事研發和技術創新以及保持技術創新的平衡性,因此,需要一定的經驗和規模來規避創新風險和克服新企業劣勢。
本研究問卷調查的對象是北京、山西和內蒙古三個省份實體企業中負責具體業務的高管人員。在行業協會的幫助下獲得樣本企業信息后,再輔助結合企業黃頁、互聯網、公開數據庫和人際網絡等方式來獲得企業的調研數據。對于北京地區的企業,在征得企業高管人員的同意后采取現場調研的方式;對于山西和內蒙古的企業,在通過電話或電子郵件獲得樣本企業高管同意后通過郵寄的方式發放問卷,并附上貼好郵票的回執信封和回復地址。事后統計分析顯示,不同調研方式獲得的數據沒有顯著的差異,說明調研方式對數據的影響并不顯著。
(二)問卷設計程序
為盡量避免同源誤差的影響,本研究將問卷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由企業中具體負責不同業務的高管來測評:其中,技術創新由具體負責技術創新實踐的技術副總來填答;組織結構和高管團隊戰略柔性由人力資源副總來評價;企業績效由財務副總來填答。除特殊標注,本研究問卷采取國際上通行的李克特(Likert)5點刻度來測評,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同意,3表示一般,4表示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為提高變量的信度和效度,本文盡量采取國際上成熟的測量工具,并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進行適當修訂和調整。對于英文量表的翻譯則嚴格遵循國際上通行的雙盲翻譯程序。此外,本研究在調研過程中保證問卷的匿名性,并盡可能采用通俗語言來表述題項,以盡可能降低同源誤差對數據質量的影響。
在設計出正式問卷后,本研究共發放450份問卷,回收245份,刪除52份無效問卷后,有效問卷共計193份,總計由579位企業高管人員參與測評,有效回收率為42.89%。樣本企業中,就企業特征而言,成立時間在6-15年間的企業占多數(59.6%),多數企業的員工人數在100~500人之間(78.3%);從所有制結構來看,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占絕大多數(82.9%);從所處產業來看,絕大多數企業(83.9%)處于制造業和IT產業。
(三)變量測量方法
平衡創新模式:在平衡創新模式下,探索式和利用式技術創新之間是一個連續體的兩個端點,一方的增強會削弱另一方(Gupta等人,2006),因此企業需要對兩者進行平衡。探索式和利用式技術創新的量表來自Lubatkin等人(2006),原始量表各由6個題項構成,但在因子分析中每個變量各存在一個交叉載荷項,刪除后兩者各由5個題項構成(如探索式技術創新的示例題項包括“本企業能在打破常規思維中尋找新的技術創意”等,利用式技術創新的示列題項包括“本企業逐步調整產品或服務以滿足現有顧客的需求”等)。該變量由企業的技術副總進行測評,其Cronbach ’s α系數分別為0.81和0.70,表明較好的信度水平。在西方現有文獻中,平衡創新模式由探索式和利用式技術創新的差值的絕對值計算而成(Cao等人,2009;He和Wong,2004)。但本文及前期的研究成果表明,這種測量是一種機械的平衡觀,無法反映二者的相對平衡。因此,本文采取有機平衡觀的計算公式,假設以x代表探索式技術創新水平,y代表利用式技術創新水平,計算公式1-︱x-y︱/(x+y)可用來測量二者的相對平衡程度。也即,相對于能力水平較低時計算出的平衡度值,能力水平較高時計算出的平衡度的值更接近于1。①
企業績效:該量表來自Lubatkin等人(2006),由財務副總進行評價。具體指標包括財務績效(如凈利潤率、銷售利潤率、現金流量等)和創新績效(如新產品開發績效等)。由于本研究的樣本企業為非上市公司,很難獲得公開的財務數據,這樣,按照現有文獻的做法(Jansen等人,2006),由財務副總依據“與主要競爭對手相比,本企業在一系列績效指標上的表現如何(1=非常不滿意,5=非常滿意)”來測評。該變量的Cronbach ’s α系數為0.79,顯示良好的信度水平。
由于探索式和利用式技術創新、企業績效都是單維度變量,我們采用結構方程模型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來檢驗各測量工具的結構效度。我們建構了一個3因子假設模型,發現該模型的擬合度(χ2=180.61,=132,RMSEA=0.044,CFI=0.96,TLI=0.96)優于2因子競爭模型(將探索式和利用式技術創新合并為1個因子,其擬合度指數為:χ2=346.67,134,RMSEA=0.091,CFI=0.88,TLI=0.87)和單因子競爭模型(將所有題項合并為1個因子,其擬合度指數為:χ2=715.64,=135,RMSEA=0.150,CFI=0.72,TLI=0.69),表明探索式和利用式技術創新、企業績效具有良好的效度。
組織集權化和組織復雜化:組織集權化的量表來自Jansen等人(2006),由5個題項構成(示例題項如“本企業內,凡事都要向上級請示,否則難以實施”)。該變量的Cronbach ’s系數為0.81,顯示良好的信度水平;組織復雜化的量表來自Damanpour(1996),由2個題項構成(示例題項如“相對于主要競爭對手而言,本企業的崗位設置相對較多”)。其Cronbach ’s系數為0.70,達到門檻值,信度水平可以接受。
高管團隊戰略柔性:該量表修改自Roca-Puig等人(2005),反映高管團隊應對外部環境變化以快速調整戰略的能力,由6個題項構成(示例題項如“本企業的高管團隊具備根據環境變化及時改變戰略方向的能力”),該變量由人力資源副總來測評,其Cronbach ’s系數為0.80,表明良好的信度水平。
我們對組織集權化、組織復雜化和高管團隊戰略柔性三個變量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發現3因子假設模型的擬合度(c2=191.64,=74,RMSEA=0.078,CFI=0.91,TLI=0.90)優于2因子競爭模型(將組織集權化和復雜化合并為1個因子,其擬合度指數為:c2=275.81,df=76,RMSEA=0.117,CFI=0.75,TLI=0.70)和單因子競爭模型(將所有題項合并為1個因子,其擬合度指數為:c2=566.59,df=77,RMSEA=0.182,CFI=0.38,TLI=0.27),表明,組織集權化和復雜化,高管團隊戰略柔性也具有良好效度水平。
控制變量:在企業特征方面,本文控制了企業年限(1=1~5年,2=6~10年,3=11~15年,4=15~20年,5=20年以上)、企業規模(1=100~200人,2=201~500人,3=501~2000人,4=2001~3000人,5=3000人以上)。由于所有制和產業類型屬于類別變量,需要將其轉換為虛擬變量進行回歸所有制類型(1=民營企業,0=其他)、所處產業(1=制造業,0=其他)。企業戰略對技術創新模式和結果會產生較大的影響,因此我們控制了三種戰略類型,分別是探索者戰略(由4個題項測量)、防御者戰略(由2個題項測量)和分析者戰略(由2個題項測量)。按照高層梯隊理論(Hambrick和Mason,1984),企業績效是高管一系列心理和行為屬性的反映,因此,企業家的屬性特征也會對企業績效產生影響,本文控制了企業家年齡(1=35歲以下,2=36~40歲,3=41~45歲,4=46~50歲,5=50歲以上)、企業家任期(1=1~3年,2=4~6年,3=7~9年,4=10~12年,5=12年以上)、企業家教育水平(1=高中及以下,2=大專,3=本科,4=碩士,5=博士及以上)、領導班子規模(1=1~3人,2=4~6人,3=7~9人,4=10~12人,5=13人)四個變量。
四、實證分析與研究結果
表1顯示了本研究主要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及兩兩間的相關系數。由于本研究既涉及到調節變量對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關系的線性調節效應,也涉及到對兩者之間關系的倒U型調節效應,本文采用多步調節回歸模型(Moderated Multiple Regression)進行假設檢驗。第一步將控制變量引入回歸方程,第二步加入自變量,第三步加入調節變量及其平方項,第四步加入自變量與調節變量的線性交互項,及自變量與調節變量平方的曲線交互項,如果曲線交互項系數顯著,則說明存在調節變量對自變量與因變量間線性關系的曲線調節效應(Dawson, 2014; Zhang et al., 2010)。表2顯示了本文的回歸分析結果。
假設1提出,平衡創新模式對企業績效具有正向影響。在控制變量的基礎上,本文發現平衡創新模式也對企業績效具有正向影響,但是其顯著性呈微弱水平(Model 2,=0.129?,<0.1)。假設1得到部分支持。
假設2提出,組織集權化在平衡創新模式與企業績效間起著倒U型調節作用。表2顯示,平衡創新模式與組織集權化平方的交互項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并不顯著(Model 5,=-0.168,ns)。假設2沒有得到支持。
假設3提出,組織復雜化在平衡創新模式與企業績效間起著倒U型調節作用。表2顯示,平衡創新模式與組織復雜化平方的交互項對企業績效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Model 5,=-0.257*,<0.05),從而,假設3得到支持。
假設4提出,高管團隊戰略柔性正向調節平衡創新模式與企業績效間的關系。本文發現,平衡創新模式與高管團隊戰略柔性的交互項對企業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Model 7,=0.193,<0.05),從而假設4得到支持。

表1 均值、標準差與相關系數
< .05(雙尾);**< 0.01(雙尾)。括號內為主要變量的信度水平。

表2 組織集權化和復雜化、高管團隊戰略柔性在平衡創新模式與企業績效間關系的調節效應檢驗
注:an=193;?< .10;.05;.01;< .001。
五、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與理論貢獻
依據制度理論,從企業對制度的被動遵從和主動響應兩個方面入手,本文探討了在什么條件下企業采取平衡創新模式更有利于提升績效的研究問題,運用中國193家企業的多源測評數據,對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設進行了檢驗。研究發現:企業采取平衡創新模式對企業績效具有微弱的正向影響,當企業遵從適度復雜化的組織制度安排時,平衡創新模式對企業績效提升的作用最大,而當企業遵從適度集權化的制度安排時,其績效提升作用則不顯著。在高管團隊戰略柔性較高的企業中,平衡創新模式更能夠增強對企業績效提升的影響程度。相對于現有文獻,本文的學術貢獻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基于制度理論,本文從企業對制度的被動遵從方面首次明確了平衡創新模式發揮作用的最優組織制度安排,進一步厘清了平衡創新模式的作用邊界。現有文獻對平衡創新模式的研究大多關注于前因和后果影響因素的研究,而針對其在什么條件下能夠發揮更大或最大作用的研究成果則相對有限。本文發現,企業遵從不同的組織制度安排,平衡創新模式對企業績效提升的作用存在差異,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之前文獻中存在的不一致的研究結論。具體而言:當企業遵從適度復雜化的組織制度安排時,平衡創新模式對企業績效的提升作用最大,而當企業遵從適度集權化的組織制度安排時,其對企業績效的提升作用則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適度集權化所創造的“松散的媾合”狀態讓職能部門或員工在資源分配過程中由于難以把握恰當的平衡的“度”而造成資源分配的失衡,并且,這個“度”可能因時因地而在動態變化,從而可能增加了具體部門或員工進行技術平衡的難度。綜上,針對現有文獻中平衡創新模式出現的不一致的研究結論,本文認為,平衡創新模式對企業績效的提升作用是顯著還是不顯著,取決其與企業的組織制度安排的耦合與匹配,不同的匹配條件導致其作用發揮存在明顯不同。這樣,本文不僅進一步厘清了平衡創新模式的作用邊界,也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現有文獻的研究結論。
此外,近年來組織理論的學者提出一種TMGT(Too-Much-of-a-Good-Thing,過猶不及)的觀點(Pierce和Aguinis,2013),認為過猶不及的現象普遍存在于制度理論、戰略管理、創新理論等研究領域中。而本文的研究結論則表明,適度的組織制度安排并非對于平衡創新模式都是最優的,更進一步,適度或適中的制度安排雖然能夠避免過低或過高兩個極點的弊端,但是要實現恰當的“中”和“度”,則需要企業具備較高的動態識別和平衡能力,因為“中”和“度”的標準可能是不斷變化的,否則將可能導致企業“陷入中端”(stuck in the middle)而無法獲得任何一端的優勢。從而,對于近年來組織理論中出現的眾多論證TMGT觀點的研究成果,本文認為這種效應可能并不具有理論普適性,也應考慮其適用邊界和條件。
第二、本文從企業主動響應制度變化的方面首次明確了作為戰略決策者的高管團隊戰略柔性存在差異的條件下,平衡創新模式對企業績效提升作用的差異性,進一步豐富和深化了新熊彼特技術創新理論和高層梯隊理論。本研究發現,面對制度規范和變化對企業造成沖突的壓力和要求,在高管團隊戰略柔性高的條件下,平衡創新模式對企業績效提升作用進一步增強。本文的研究結論進一步深化了新熊彼特技術創新理論,該理論之前將市場結構、壟斷強度和企業規模等因素納入到理論體系中探討技術創新的復雜過程,而本文則將關注點進一步細化和深化,具體到企業內部決策者微觀層面,將決策者的能力這一因素納入進來,探討了企業采用平衡創新模式與高管團隊戰略柔性之間的復雜交互作用過程,從而將新熊彼特技術創新理論的關注點從傳統上分析企業外部環境因素轉向關注企業內部的決策者微觀層面,從更微觀的視角來進一步剖析技術創新過程的復雜性。
此外,本研究也進一步豐富了高層梯隊理論(Hambrick和Mason,1984)。該理論近年來的一個研究趨勢是從高管團隊的人口統計特征研究逐漸轉向高管團隊的行為過程研究,以期更好的理解高管團隊復雜的互動過程給企業戰略決策和企業績效所帶來的影響。現有研究中盡管對企業層面的戰略柔性研究較多,但是尚沒有檢驗高管團隊層面的戰略柔性對企業所帶來的影響,本文首次嘗試檢驗高管團隊的戰略柔性存在能力差異的條件下,平衡創新模式對企業績效所造成的差異化影響,從而將高管團隊戰略柔性變量納入到高管團隊行為過程的研究之中,進一步豐富了高層梯隊理論。
(二)研究局限和未來研究方向
盡管本文的研究結論具有一定的理論貢獻,但也存在以下兩個局限:第一,盡管本文的自變量、因變量和調節變量分別由企業中不同的高管來測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同源誤差的影響,但是由于難以獲得企業層面的多次數據,采用橫截面數據進行的檢驗難以嚴格驗證變量間的因果關系。為了驗證是否存在互為因果關系,本文按照 Landis 和 Dunlap(2000)的方法,以平衡創新模式作為因變量,企業績效作為自變量,檢驗了企業績效對平衡模式的影響,以及企業績效與組織集權化/復雜化和高管團隊戰略柔性的交互對平衡創新模式的影響,結果發現這些影響都不顯著,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橫截面數據所造成的互為因果的問題,但是在以后的研究中建議能夠進行縱向研究,收集自變量和因變量在不同時間點的數據,從而更好的驗證因果關系;第二,本文的企業樣本并非上市公司,在難以獲得客觀的財務績效數據的情況下,本文按照現有研究的做法(Cao等人,2009),以高管測評的主觀績效數據作為替代。盡管現有研究也表明主觀績效和客觀績效指標間存在較高的顯著相關性可以進行替代,但是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考慮收集上市公司的樣本,分別運用客觀和主觀績效指標來對本文的研究結論做進一步的檢驗。
1. 陳嘉文、姚小濤:《組織與制度的共同演化:組織制度理論研究的脈絡剖析及問題初探》[J],《管理評論》2015年第5期。
2. 高照軍、武常岐:《制度理論視角下的企業創新行為研究—基于國家高新區企業的實證分析》[J],《科學學研究》2014年第10期。
3. 呂鴻江、劉洪、程明:《最優組織復雜性理論探析》[J],《外國經濟與管理》2008年第10期。
4. 陶厚永、劉洪、呂鴻江:《組織管理的集權-分權模式與組織績效的關系》[J],《中國工業經濟》2008年第4期。
5. 王鳳彬、陳建勛、楊陽:《探索式與利用式技術創新及其平衡的效應分析》[J],《管理世界》2008年第3期。
6. 王建、胡瓏瑛、馬濤:《吸收能力, 開放度與創新平衡模式的選擇——基于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J],《科學學研究》2015 年第2期。
7. Cao, Q., Gedajlovic, E., Zhang, H. P., 2009,“Unpacking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Dimensions, Contingencies and Synergistic Effects”[J],, Vol. 20, No.4: 781-796.
8. Cohen, J., Cohen, P., Aiken, L. S., and West, S. G., 2002, “Applied Multiple Regression/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M],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
9. Damanpour, F., 1996, “Organizational Complexity and Innovation: Developing and Testing Multiple Contingency Models”[J],, Vol. 42, No.5: 693-716.
10. Dawson, J. F., 2014, “Moderation in Management Research: What, Why, When, and How”[J],, Vol. 29, No. 1: 1-19.
11. Fernhaber, S. A., and Patel, P. C., 2012, “How do Young Firms Manage Product Portfolio Complexity? The Role of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Ambidexterity”[J],, Vol. 33: 1516-1539.
12. Ghemawat, P., and Costa, J., 1993, “The Organizational Tension Between Static and Dynamic Efficiency”[J],, Vol.14: 59-73.
13. Gupta, A. K., Smith, K. G., and Shalley, C. E., 2006, “The Interplay Between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J],, Vol. 49, No. 4: 693-708.
14. Hambrick, D. C., and Mason, P. A., 1984, “Upper Echelon: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J],, Vol. 9, No.2: 193-206.
15. He, Z., and Wong, P., 2004, “Exploration vs. Exploitation: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Ambidexterity Hypothesis”[J],, Vol.15, No. 4: 481-494.
16. Jansen, J. J. P., Van Den Bosch, F. A. J. H., and Volberda, W., 2006, “Exploratory Innovation,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Antecedents and Environmental Moderators”[J],, Vol. 52, No. 11: 1661-1674.
17. Landis, R. S., and Dunlap, W. P., 2000, “Moderated Multiple Regression Tests are Criterion Specific”[J],, Vol. 3, No. 3: 254-266.
18. Lubatkin, M. H., Zeki, S., Ling, Y., and Veiga, J. F., 2006, “Ambidexterity and Performance in Small-to Medium-Sized Firms: The Pivotal Role of Top Management Team Behavioral Integration”[J],, Vol. 32, No.5: 646-672.
19. March, J. G., 1991,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 Vol. 2, No.1: 71-87.
20. Meyer, J. W., and Roman, B., 1977,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J],, Vol. 83, No. 2: 340-363.
21. Pierce, J. R., and Aguinis, H., 2013, “The Too-Much-of a-Good-Thing Effect in Management”[J],, Vol. 39, No.2: 313-338.
22. Roca-Puig, V., Beltrdn-Martin, I., Escrig-Tena, A. B., and Bou-Llusar, J. C., 2005, “Strategic Flexibility as a Moder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itment to Employees and Performance in Service Firms”[J],, Vol. 16, No.11: 2075-2093.
23. Scott, W. R., 2008,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deas and Interests”[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
24. Smith, W. K., and Tushman, M. L., 2005, “Managing Strategic Contradictions: A Top Management Model for Managing Innovation Streams”[J],, Vol.16, No. 5: 522-536.
25. Zhang, Y., Li, H. Y., Li, Y., Zhou, L. A., 2010, “FDI Spillovers in an Emerging Market: The Role of Foreign Firms’ Country Origin Diversity and Domestic Firms’ Absorptive Capacity”[J],, Vol. 31: 969-989.
(WH)
①具體計算方法和理論機理參見王鳳彬、陳建勛和楊陽發表于2012年《管理世界》第3期上的《探索式和利用式技術創新及其平衡的效應分析》的文章。
* 本文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號:71572037,71102074)和協同創新項目(項目號:201502YY002B)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