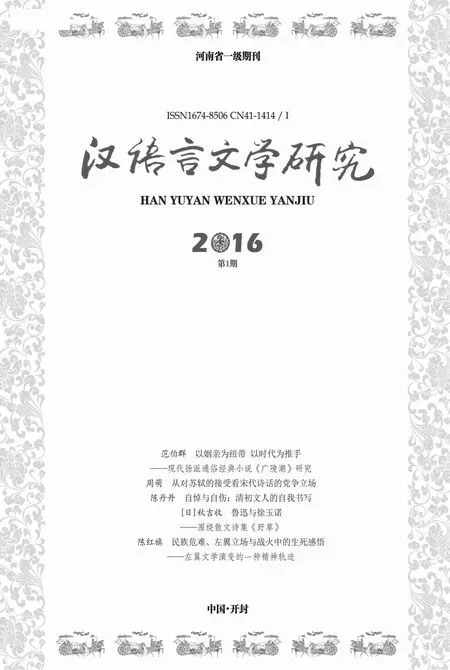民族危難、左翼立場(chǎng)與戰(zhàn)火中的生死感悟*——左翼文學(xué)演變的一種精神軌跡
陳紅旗
?
民族危難、左翼立場(chǎng)與戰(zhàn)火中的生死感悟*——左翼文學(xué)演變的一種精神軌跡
陳紅旗
摘要:20世紀(jì)二三十年代是中國(guó)社會(huì)動(dòng)亂異常頻繁的歷史時(shí)段之一。在這種背景下,左翼作家抒寫了底層民眾的生存困境,揭露了“死神”的真面目。由于左翼知識(shí)分子總在體認(rèn)理想碰壁的無(wú)奈和人生無(wú)常的虛無(wú),因此他們承受著常人難以體會(huì)和感知的精神痛苦與心理煎熬。左翼文藝界通過自身的左翼立場(chǎng)和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勞苦大眾建立了精神聯(lián)系,并把自己植入到后者的悲苦與激憤之中,這就使得他們收獲了那個(gè)時(shí)代最廣闊的痛苦和力量,也使得他們的歌吟和抒寫洋溢著其他文人難以生成的激揚(yáng)熱情和樂觀精神。抗戰(zhàn)元素的植入使得左翼文學(xué)與“抗戰(zhàn)”更加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左翼作家將“有意義的死”視為一種精神的延續(xù)和人生的圓滿,而不是一種生命的終結(jié)和肉體的痛苦。在革命斗爭(zhēng)和抗日救亡運(yùn)動(dòng)中,左翼作家為自己的青春和心靈留下了獨(dú)特的印跡,也獲得了其他知識(shí)分子難以體知的生死感悟。
關(guān)鍵詞:左翼文學(xué);左翼立場(chǎng);民族危難;抗戰(zhàn)元素;生死感悟
左翼文學(xué)作為一種激進(jìn)的文學(xué)形態(tài),它不僅在追求時(shí)代精神的過程中彰顯了自身的左翼立場(chǎng),還在民族危機(jī)和戰(zhàn)火中抒發(fā)了抗敵御侮的愛國(guó)情感;與此同時(shí),左翼文學(xué)也對(duì)“為人生”的內(nèi)容進(jìn)行了革新。因此,20世紀(jì)30年代中國(guó)文學(xué)出現(xiàn)了明顯的矛盾絞纏現(xiàn)象:一方面,這一時(shí)期的文藝界幾乎在使用同一套話語(yǔ)體系,但相互之間不斷發(fā)生錯(cuò)綜復(fù)雜的論爭(zhēng),以至于這一時(shí)期的文學(xué)中充滿了“浮躁凌厲”的氣息;另一方面,民族國(guó)家危機(jī)將各派知識(shí)分子匯集到了救亡圖存的政治維度上,使得這一時(shí)期的文學(xué)充滿了政治元素,也令各派知識(shí)分子產(chǎn)生了迥異的人生感受。對(duì)于左翼知識(shí)分子而言,他們的人生感受更多地被死亡陰影、抗?fàn)幱蠛图嵡榫w所纏繞,這是現(xiàn)代派、新月派、國(guó)家主義派、民族主義文藝派、“自由人”、“第三種人”、海派、京派、論語(yǔ)派的知識(shí)分子很難甚至根本不會(huì)產(chǎn)生的人生感受。
一、生存困境的抒寫與“死神”真容的顯形
20世紀(jì)二三十年代是中國(guó)社會(huì)動(dòng)亂異常頻繁的歷史時(shí)段之一,軍閥混戰(zhàn)、水災(zāi)旱災(zāi)、資本家的壓榨、土豪劣紳的剝削和帝國(guó)主義侵略等,使得底層民眾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為此,在左翼作家的筆下,讀者會(huì)經(jīng)常看到敘述者/被敘述者對(duì)于生活無(wú)法忍受和求生存之難的抒寫與悲嘆。對(duì)諸多天災(zāi)人禍景象的書寫,折射了左翼作家對(duì)底層民眾苦難生活的同情和內(nèi)心難以言表的痛楚,也傳遞了他們對(duì)不合理制度、不公正現(xiàn)象的批判意識(shí)和憤怒情緒。
在大革命高潮時(shí)期,左翼知識(shí)分子曾經(jīng)感受到改造社會(huì)乃至創(chuàng)造歷史的快感,但階級(jí)斗爭(zhēng)的殘酷性令他們的情感與生命體驗(yàn)日漸深厚起來。他們感受到更多的是“死亡”的迫壓和“憤怒”的集結(jié)。“死神”之首就是帝國(guó)主義侵略者。蔣光慈早在1925年就告訴讀者,“青島的日本資本家殺死我們中國(guó)工人,/上海的日本資本家繼續(xù)著起來響應(yīng),/上海的英巡捕更殺傷我們無(wú)數(shù)的學(xué)生”①蔣光慈:《血花的爆裂》,《蔣光慈文集》(第3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408頁(yè)。;他還在1926年紀(jì)念“五卅”慘案時(shí)寫道:“我憶起來南京路上的槍聲,呼號(hào),痛跡,/和那沙基的累累的積尸,漢江的殷紅的血水。”②蔣光慈:《血祭》,《蔣光慈文集》(第3卷),第425頁(yè)。穆木天則揭露了日寇欺騙和屠殺無(wú)辜群眾的惡行:“這是一九三二年的夏天,/那些天真的民眾受了帝國(guó)主義的掃射,/他們就了他們所預(yù)想不到的死,/在那青青的山坡之旁,陽(yáng)光輝耀之下。”③穆木天:《掃射》,王訓(xùn)昭選編:《一代詩(shī)風(fēng)——中國(guó)詩(shī)歌會(huì)作品及評(píng)論選》,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頁(yè)。“死神”之二是國(guó)民黨當(dāng)權(quán)派。郭沫若在1927年4月9日就告知了世人蔣介石的劊子手面目:“他的總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營(yíng),就是慘殺民眾的大屠場(chǎng)。他自己已經(jīng)變成一個(gè)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兇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獪的劊子手了。”④郭沫若:《請(qǐng)看今日之蔣介石》,《郭沫若選集》(第2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頁(yè)。“左聯(lián)”告知世人:“國(guó)民黨摧殘文化和壓迫革命文化運(yùn)動(dòng),竟至用最卑劣最慘毒的手段暗殺大批革命作家的地步了!我們的革命作家李偉森,柔石,胡也頻,馮鏗,殷夫,是在二月七日,被秘密活埋和槍殺于龍華警備司令部了!”⑤中國(guó)左翼作家聯(lián)盟:《中國(guó)左翼作家聯(lián)盟為國(guó)民黨屠殺大批革命作家宣言》,《前哨》,1931年4月25日,第1卷第1期,第2頁(yè)。葉紫的小說《電網(wǎng)外》揭示了國(guó)民黨的團(tuán)防兵是怎樣把無(wú)辜民眾當(dāng)成“匪徒”來加以屠殺的。歐陽(yáng)山的小說《鬼巢》用象征手法曲筆揭露了國(guó)民黨當(dāng)權(quán)派鎮(zhèn)壓廣州起義的血腥殺戮。“死神”之三是各類剝削階級(jí)和特權(quán)階層。曹禺劇作《雷雨》中的周樸園為了掙一筆“絕子絕孫的昧心錢”,故意讓自己承包的江堤出險(xiǎn),淹死2200個(gè)工人,每條性命扣300元錢。又如:穆木天有詩(shī)句,“千金寨的數(shù)萬(wàn)礦工被活埋”⑥穆木天:《我們要唱新的詩(shī)歌》,《一代詩(shī)風(fēng)——中國(guó)詩(shī)歌會(huì)作品及評(píng)論選》,第3頁(yè)。;瞿秋白有詩(shī)句,“說到農(nóng)民真?zhèn)模笏土耸呤。€要交租納稅養(yǎng)閑人,/地主官僚就是閑人精”⑦史鐵兒:《東洋人出兵》,《文學(xué)導(dǎo)報(bào)》,1931年9月28日,第1卷第5期,第10頁(yè)。。而周文的小說《雪地》演示了大小軍閥是怎樣逼死下層士兵的。對(duì)于這些萬(wàn)惡的“死神”的所作所為,左翼作家的憤怒自然溢于言表。殷夫詩(shī)云:“血液寫成的大字,/刻劃著千萬(wàn)聲的高呼,/這個(gè)難忘的日子——/幾萬(wàn)個(gè)心靈暴怒……”⑧殷夫:《血字》,《拓荒者》,1930年5月10日,第1卷第4、5期合刊,第1154頁(yè)。蒲風(fēng)詩(shī)云:“誰(shuí)野蠻?誰(shuí)企圖非有?/(誰(shuí)把黑白顛倒,模糊?)/呵呵,我們是地底的狂流,/是地底積下怒潮年載久!”⑨蒲風(fēng):《六月流火》,《蒲風(fēng)選集》(上冊(cè)),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430頁(yè)。
透過這些作品,我們不難理解20世紀(jì)30年代左翼作家在經(jīng)歷激昂興奮的大革命高潮后,在面臨各派反動(dòng)勢(shì)力的血洗和殺戮時(shí)所產(chǎn)生的難以抑制的悲憤。
二、“個(gè)”的痛楚與“群”的悲苦
在與帝國(guó)主義勢(shì)力和國(guó)民黨當(dāng)權(quán)派的長(zhǎng)期斗爭(zhēng)過程中,左翼作家的抗壓和抗擊打能力越來越強(qiáng),但這并不代表他們沒有恐懼和煩惱。實(shí)際上,他們作品中既留下了他們的豪氣和壯志,也留下了他們的惆悵和痛苦。而戰(zhàn)云密布、民不聊生的情形不斷加重左翼知識(shí)分子的苦痛,令他們產(chǎn)生至為深邃的人生感受。這里不妨以魯迅作于1932年的兩首詩(shī)為例:
無(wú)題二首
故鄉(xiāng)黯黯鎖玄云,遙夜迢迢隔上春。
歲暮何堪再惆悵,且持卮酒食河豚。
其二
皓齒吳娃唱柳枝,酒闌人靜暮春時(shí)。
無(wú)端舊夢(mèng)驅(qū)殘醉,獨(dú)對(duì)燈陰憶子規(guī)。①魯迅:《無(wú)題二首》,《魯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年版,第438頁(yè)。
這是魯迅分別為日本友人濱之上信隆和坪井芳治所作的詩(shī),體現(xiàn)了他極為復(fù)雜的心境。在日寇侵略的戰(zhàn)爭(zhēng)陰影下,作者思緒萬(wàn)千,既然看到了國(guó)家前途的危難和黯淡,又怎能不惆悵、痛苦呢?而酒闌人靜,舊夢(mèng)驅(qū)除了殘醉,面對(duì)孤燈,想到人民的苦難,只會(huì)增添更多的怨怒和憂傷,正所謂:“獨(dú)對(duì)燈陰,清時(shí)難得,矧嘔心深夜,為人民鳴其怨怒,與啼血之子規(guī)正復(fù)相似乎!憂思難忘,出之深折。”②曹禮吾:《魯迅舊體詩(shī)臆說》,長(zhǎng)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頁(yè)。也是在1932年,郁達(dá)夫作《題劍詩(shī)》:“秋風(fēng)一夜起榆關(guān),寂寞江城萬(wàn)仞山。九月霜鼙摧木葉,十年書屋誤刃環(huán)。夢(mèng)從長(zhǎng)劍驅(qū)流豹,醉向遙天食海蠻。襟袖幾時(shí)寒露重,天涯歌哭一身閑。”③郁達(dá)夫:《題劍詩(shī)》,《郁達(dá)夫詩(shī)詞集》,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第150頁(yè)。在國(guó)家危難之際,作者悵惘于自己“讀書無(wú)用”,恨不能仗劍殺賊,夢(mèng)中醒來對(duì)于民族劫難唯有心酸痛哭卻無(wú)以解憂。更令人痛心的是國(guó)民黨當(dāng)權(quán)派的不作為和賣國(guó)行徑:“北地小兒耽逸樂,南朝天子愛風(fēng)流。權(quán)臣自欲成和議,金虜何嘗要汴州?屠狗猶拼弦上命,將軍偏惜鏡中頭!饒他關(guān)外童男女,立馬吳山志竟酬。”④郁達(dá)夫:《過岳墳有感時(shí)事》,《郁達(dá)夫詩(shī)詞集》,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頁(yè)。面對(duì)這種漢奸得志的世道,進(jìn)步知識(shí)分子只能是彷徨四顧卻又無(wú)地彷徨,他們?cè)谌耸篱g找不到超脫隱逸的仙境,他們也不想找,因?yàn)樗麄円呀?jīng)堵死了自己的人生退路,他們只能不斷向前。由于左翼知識(shí)分子總在體認(rèn)理想碰壁的無(wú)奈和人生無(wú)常的虛無(wú),因此,他們承受著常人難以體會(huì)和感知的精神痛苦與心理煎熬。
相比于魯迅、郁達(dá)夫等沉郁渾厚、痛徹肺腑的人生體悟,其他左翼作家的人生感受要清淺、通透得多。他們從戰(zhàn)友的犧牲中滋長(zhǎng)仇恨,在赴死之途中尋求完成使命和獲得真理的路標(biāo):“我們底小兄弟,/可敬可佩的C.Y.同志!/槍殺的,/你微笑而死去!/這是使命,/這是真理!”⑤柔石:《血在沸——紀(jì)念一個(gè)在南京被殺的湖南小同志底死》,《前哨》,1931年4月25日,第1卷第1期,第18頁(yè)。他們?cè)陴嚭黄戎忻靼琢朔纯苟窢?zhēng)才是唯一的求生之路,悟出了勞苦兄弟只有團(tuán)結(jié)起來才能無(wú)所畏懼、傲視群丑的革命真理:“你,榨盡了血和肉的饑寒的工農(nóng)!/你,被賣了身體的殖民地的奴隸!/涌向前去,我們一起,/向前去,向反帝個(gè)主義戰(zhàn)的火線下去。/炸烈彈,毒瓦斯,軍艦,大炮,飛機(jī),/威嚇得民族資產(chǎn)階級(jí)的狗,/卻鎮(zhèn)壓不了我們的蜂起!”⑥凌鐵:《饑餓的襤褸的一群》,《文學(xué)導(dǎo)報(bào)》,1931年10月23日,第1卷第6、7期合刊,第5頁(yè)。與其他專注于文學(xué)甚至立志成為“文學(xué)家”的作者不同,諸多左翼作家之“志”并不在于文學(xué)本身。比如,蔣光慈曾立志作一個(gè)“俠僧”,狂想自己快意恩仇于江湖,鏟盡人間惡霸;馮鏗將步槍視為自己的“情人”,其志向就是成為一名英勇殺敵的紅軍戰(zhàn)士;華漢的小說透露出了他對(duì)戎馬生涯的懷念和對(duì)“將軍夢(mèng)”的追求;殷夫的詩(shī)明確告知世人,他要做“海燕”那樣的斗士,要像普羅米修斯那樣給人類以光明……的確,那個(gè)時(shí)代的激進(jìn)知識(shí)分子有幾個(gè)只愿做一個(gè)文學(xué)家呢?他們歌頌列寧、孫中山等革命英豪,贊美顧正紅、劉華等工人領(lǐng)袖,也歌頌高爾基、拜倫那樣的世界文豪,但他們真正推崇的絕非高爾基、拜倫的文學(xué)功績(jī),而是希望成為叱咤風(fēng)云的革命豪杰。雖然明知這不太現(xiàn)實(shí),但胸懷世界、鐵血丹心、飲馬江湖的夢(mèng)還是敢做的。當(dāng)然,所有的左翼作家都沒有這樣的政治能力和實(shí)際干才,不然他們就不是作家了。也正因?yàn)楹芸炀陀辛诉@種自知之明,所以他們才開始用心去創(chuàng)作,以期在文學(xué)世界里繼續(xù)追尋自己的豪杰夢(mèng)和革命理想。而這種追尋也讓他們?cè)谧晕曳此己蜕矸菡J(rèn)同中獲得了更豐厚的人生體驗(yàn)。
盡管左翼知識(shí)分子熱血沸騰、革命勁頭十足,但實(shí)際政治斗爭(zhēng)的復(fù)雜性和殘酷性卻證明他們終究是強(qiáng)權(quán)之下的弱者。茅盾蝸居上海自家三樓、十個(gè)月足不出戶以躲避國(guó)民黨的追捕直至遠(yuǎn)遁日本;魯迅不管如何痛恨租界都不得不在面臨危險(xiǎn)時(shí)避難于此;郭沫若在大罵蔣介石和南昌起義失敗后只能無(wú)奈逃到日本避難;丁玲、蕭軍、王實(shí)味、艾青、周文等諸多左翼文人先后奔赴延安;“左聯(lián)”五烈士事件的發(fā)生等,種種事實(shí)都證明進(jìn)步知識(shí)分子與當(dāng)時(shí)的國(guó)家機(jī)器相抗衡是沒有好結(jié)果的,他們最終往往不是逃離就是死亡。但左翼知識(shí)分子的可貴之處在于:他們充滿了“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力量,他們經(jīng)常會(huì)面臨生死抉擇,但最后還是選擇站在大眾一面,選擇站在國(guó)民黨當(dāng)權(quán)派和帝國(guó)主義勢(shì)力的對(duì)立面。就創(chuàng)作而言,與“死神”對(duì)壘使得他們的作品中充滿了“血色”,比如僅在蔣光慈的詩(shī)中就出現(xiàn)過“熱血”“鮮血”“心血”“血液”“血跡”“血潮”“血痕”“血濺”“血祭”“血水”“血衣”“血液”“血痕”“血流”等詞。可以說,“血”成了左翼作家經(jīng)常描寫的對(duì)象,是他們渲染血腥慘景的一個(gè)重要詞語(yǔ)和意象,也是他們刺激戰(zhàn)友們?nèi)?fù)仇的重要觸媒:“今年的黃浦江中鼓蕩著血潮,/偌大的上海城但聞鬼哭與神號(hào)”①蔣光慈:《寫給母親》,《蔣光慈文集》(第3卷),第458頁(yè)。;“今日我們的血液寫成字,/異日他們的淚水可入浴”②殷夫:《血字》,《拓荒者》,1930年5月10日,第1卷第4、5期合刊,第1155頁(yè)。;“血在沸!/心在燒!/地球在震動(dòng)!/火山在爆發(fā)!”③柔石:《血在沸——紀(jì)念一個(gè)在南京被殺的湖南小同志底死》,《前哨》,1931年4月25日,第1卷第1期,第15頁(yè)。“是的!祖國(guó):/你會(huì)在戰(zhàn)爭(zhēng)中誕生啊!/你是在血的空氣里呼吸,/你也在炮火中營(yíng)養(yǎng)血液!/最大的災(zāi)難不能磨滅你,/血色的日光正輝照著你勝利的旌旗”④馬甦夫:《祖國(guó)》,王訓(xùn)昭選編:《一代詩(shī)風(fēng)——中國(guó)詩(shī)歌會(huì)作品及評(píng)論選》,第148頁(yè)。;“八月的黃浦江!/你卷起抗戰(zhàn)的血火,/咆哮了解放的怒吼”⑤王亞平:《八月的黃浦江》,《王亞平詩(shī)選》,北京:中國(guó)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80頁(yè)。;“紅光是我們的精靈,是給帝國(guó)主義殘殺了的烈士們的鮮血!”⑥馮鏗:《紅的日記》,《前哨》,1931年4月25日,第1卷第1期,第20頁(yè)。就這樣,通過對(duì)“血”的抒寫和對(duì)“紅”的渲染,左翼作家將憤怒和激情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出來,“血”十分疏散卻是盡情潑灑在他們的筆下,它使得這些作品在悲摧之中充溢著活力。在暴戾兇殘的中外劊子手面前,在極度的憤怒悲慟之中,在歷經(jīng)磨難和摧殘之后,左翼知識(shí)分子依然保有著剛毅不屈的戰(zhàn)士姿態(tài)和“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愛國(guó)大志。這正是現(xiàn)代文學(xué)史難以遺忘他們的根本原因。
與左翼作家相比,那些沒有投身革命和故意遠(yuǎn)離戰(zhàn)火的作者們同樣富含現(xiàn)代意識(shí)、時(shí)代精神、愛國(guó)立場(chǎng)乃至悲憫情懷,但他們竭力躲避戰(zhàn)火、沉溺于個(gè)人悲歡、迎合庸眾甚至為統(tǒng)治階級(jí)“幫閑”和“幫忙”的作品,在格局、視域和氣度上難免顯得“小氣”“狹隘”和“局促”。例如胡適,作為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化和文學(xué)乃至語(yǔ)言改革的先驅(qū),一生堅(jiān)持自由主義,其思想不可謂不進(jìn)步,影響不可謂不大,他雖然與國(guó)民黨政府合作,但一直葆有知識(shí)分子的獨(dú)立思想,他對(duì)于國(guó)民黨的專制統(tǒng)治還是極為反感乃至痛恨的,他曾對(duì)徐志摩表示,“二十世紀(jì)應(yīng)該是全民族爭(zhēng)得自由的時(shí)期”,但在專制制度之下,只有服從與不服從,根本“沒有我們獨(dú)立思想的人的生活余地”。⑦胡適:《歐游道中寄書》,《胡適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8-59頁(yè)。問題是,他對(duì)國(guó)民黨政府始終抱有幻想,希望“好人政府”的理想能夠在國(guó)民黨人的身上得以實(shí)現(xiàn),這種政治認(rèn)識(shí)上的局限性使得他難免會(huì)背離時(shí)代精神。再如林語(yǔ)堂,早期文風(fēng)極為潑辣,針對(duì)北洋軍閥及其幫兇“正人君子”之流寫過《祝土匪》《打狗檄文》等富有“土匪精神”的批判文章,其革命精神一度被人們廣泛稱道,但他最終滑向了“內(nèi)心的歸隱”,對(duì)于敵人主張“費(fèi)厄潑賴”(Fair Play)和“不打落水狗”,在1932年創(chuàng)辦《論語(yǔ)》和1934年編輯《人間世》期間大力提倡幽默的小品文寫作,專注于筆調(diào)的風(fēng)雅、精致、雍容、漂亮、縝密、閑適和輕快,此后更沉迷于內(nèi)道外儒的人生哲學(xué)觀和“儒道交融、寓道于儒的政治哲學(xué)觀”,⑧張西山:《論〈京華煙云〉主題及林語(yǔ)堂的政治哲學(xué)》,《西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2年第3期,第141頁(yè)。這不能不說是一個(gè)悲劇。從純藝術(shù)的角度來看,林語(yǔ)堂的散文富有幽默氣息、諧趣意旨、淡然之味和幽隱意境,在和平年代這種會(huì)博得“庸人之歡心”的寫法本無(wú)可厚非。從個(gè)人的角度來看,林語(yǔ)堂在武漢擔(dān)任國(guó)民政府外交部秘書期間,先后目睹了槍斃“土豪劣紳”和工人、農(nóng)民、學(xué)生時(shí)尸骨成山的景象,以致于對(duì)政治“深感厭倦”乃至完全絕望,這并無(wú)可指責(zé)之處。但從知識(shí)分子的責(zé)任和良知的角度來看,如果他的文字會(huì)將屠夫的兇殘“使大家化為一笑”①魯迅:《“論語(yǔ)一年”——借此又談蕭伯納》,《魯迅全集》(第4卷),第567頁(yè)。,會(huì)讓讀者遺忘民族恥辱甚至?xí)饷褡宓膭?chuàng)傷記憶,那么這樣的作品肯定難以獲得左翼知識(shí)分子的認(rèn)同和尊重。與林語(yǔ)堂的“幽默”散文、梁實(shí)秋的“雅舍”散文和周作人的“苦茶”散文相比,左翼作家的文風(fēng)實(shí)在太不從容和太過肅殺了。但客觀地說,是那樣的現(xiàn)實(shí)環(huán)境逼得左翼作家形成了這樣的文風(fēng),他們正是用這樣的文風(fēng)揭露了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的黑暗。也只有在左翼文學(xué)中,我們才會(huì)了解到那么多的民族屈辱和民眾苦難,才會(huì)發(fā)現(xiàn)文學(xué)是如何在挽救民族記憶和“恥辱遺忘癥”②朱學(xué)勤:《我時(shí)常想起魯迅、胡適與錢穆》,《雜文選刊》(下旬刊)2010年第4期,第23頁(yè)。的。在左翼文學(xué)這里,我們看到了一群被民族恥辱和民眾苦難所折磨的心靈正在集體煎熬著,在戰(zhàn)火紛飛的亂世時(shí)代里,在詩(shī)人無(wú)眠的暗燈殘影里,在異端噤聲的政治語(yǔ)境里,左翼作家憂憤深廣的作品注定會(huì)被歷史銘記和挖掘。
心靈備受煎熬令左翼作家非常喜歡描寫底層民眾的“悲苦”情狀,不過與蘇曼殊、廬隱極力再現(xiàn)自身悲苦身世的寫法不同,左翼作家書寫悲苦的文字并非是為了咀嚼一己的悲哀和痛苦,而是為了釋放壓抑已久的憤怒,更是為了對(duì)癥下藥、給出“出路”。應(yīng)該說,看到民間的悲苦并非左翼文學(xué)的專利,但凡有點(diǎn)良知的知識(shí)分子都能看到天災(zāi)人禍、政治紛爭(zhēng)和綿延不斷的戰(zhàn)亂給普通人乃至民族和國(guó)家?guī)淼目嚯y遭際。關(guān)鍵是對(duì)于這種“悲苦”怎樣去看?有的人選擇逃避,有的人選擇消解,有的人選擇無(wú)視,有的人選擇嘲弄,而左翼知識(shí)分子選擇直面苦痛和尋找生路。在左翼文學(xué)尤其是早期革命文學(xué)中,一個(gè)非常常見的套路是很多作品會(huì)有一條“光明尾巴”,比如:戴平萬(wàn)的《村中的早晨》從老農(nóng)老魏憂心于自己晚景凄涼的處境寫起,結(jié)尾寫的是他在兒子阿榮的勝利中看到了農(nóng)村革命的光明前景;孟超的《鹽務(wù)局長(zhǎng)》從鹽民掙扎在死亡線上的事實(shí)寫起,結(jié)尾則寫了鹽民造反成功的情節(jié);蔣光慈的《沖出云圍的月亮》從王曼英絕望于大革命的失敗寫起,結(jié)尾寫的是她在愛人李尚志的療救下獲得了新生;華漢的《女囚》從革命者趙琴綺被逮捕和備受凌辱寫起,結(jié)尾寫的是她夢(mèng)見武裝的工農(nóng)砸開牢門并看到霞光“把滿天渲染成新鮮的赤色”;洪靈菲的《大海》從三個(gè)老農(nóng)艱難掙扎借酒消愁寫起,結(jié)尾卻寫成了農(nóng)民改天換地、當(dāng)家做主的情節(jié);茅盾的《虹》從梅行素飽受封建家庭牢籠束縛的苦悶寫起,結(jié)尾寫的是她在共產(chǎn)黨員梁剛夫的引領(lǐng)下匯入群眾洪流并獲得了新生;丁玲的《韋護(hù)》以韋護(hù)和麗嘉沉迷于二人世界的溫柔鄉(xiāng)寫起,結(jié)尾寫的是他們先后悔悟并奔赴廣州去參加了革命;胡也頻的《光明在我們前面》從白華失望于自己所熱衷的無(wú)政府主義運(yùn)動(dòng)寫起,結(jié)尾寫的是她在共產(chǎn)主義書籍和共產(chǎn)黨員劉希堅(jiān)的引領(lǐng)下參加群眾運(yùn)動(dòng)并加入工人隊(duì)伍等。這樣的寫法很容易受到批評(píng),或被視為左翼文學(xué)致命的藝術(shù)窠臼。但很少有人意識(shí)到,這其實(shí)是左翼作家在向讀者“暗示出路”,這要比新月派不知道“風(fēng)是在哪一個(gè)方向吹”的狀態(tài)有活力得多,正如時(shí)人所評(píng)價(jià)的那樣:“出路!出路!這便是與自然主義不同之點(diǎn),正因?yàn)樽髡呤且詿o(wú)產(chǎn)階級(jí)的意識(shí),去觀察社會(huì),所以才有這么一個(gè)出路,它不但是寫出病狀,還要下藥,這‘暗示的出路’便是革命文學(xué)的活力,沒有這個(gè)活力,便不成其為革命文學(xué)。”③芳孤:《革命文學(xué)與自然主義》,《泰東月刊》,1928年6月1日,第1卷第10期,第14頁(yè)。當(dāng)然,這種革命出路并非完美的出路,但至少他們給出了一條可行的出路。由于對(duì)革命前景過于樂觀和有著革命必勝的信念,左翼文學(xué)中的悲苦描寫不會(huì)令人產(chǎn)生愁苦無(wú)助的感覺。在這一過程中,盡管早期左翼知識(shí)分子的革命高潮來臨感覺近于幻覺,但相比于迷茫甚至虛無(wú)者來說,找到“出路”的心理感受還是非常美好的,而這正是左翼文學(xué)獨(dú)特的藝術(shù)標(biāo)志之一。
及至“左聯(lián)”成立以后,左翼文藝界對(duì)于自己的發(fā)展路向已經(jīng)非常明確,反映在文字層面上就是,幾乎每一個(gè)盟員都會(huì)吶喊:“無(wú)產(chǎn)階級(jí)聯(lián)合起來!”而這句口號(hào)背后所意指的“出路”——擁護(hù)和完成蘇維埃運(yùn)動(dòng)——已經(jīng)非常明確。針對(duì)這一“出路”,“左聯(lián)”給盟員們制定了非常明確的任務(wù)。比如“左聯(lián)”機(jī)關(guān)刊物《文化斗爭(zhēng)》第一卷第一期共發(fā)表六篇文章,每篇文章都針對(duì)這種“出路”給予盟員以相關(guān)“使命”或“任務(wù)”的要求。潘漢年認(rèn)為《文化斗爭(zhēng)》的使命是:“要樹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建立正確的革命理論,爭(zhēng)取廣大的青年群眾,起來為蘇維埃政權(quán)斗爭(zhēng)!另一方面為著廣大蘇維埃區(qū)域工農(nóng)兵對(duì)于新文化的需要迫切,要努力蘇維埃文化運(yùn)動(dòng)的創(chuàng)造。”①潘漢年:《本刊出版的意義及其使命》,《文化斗爭(zhēng)》,1930年8月15日,第1卷第1期,第2頁(yè)。谷蔭(朱鏡我)在《反對(duì)帝國(guó)主義進(jìn)攻紅軍》一文中號(hào)召道:“快快全國(guó)總蜂起起來,全國(guó)的總反對(duì)帝國(guó)主義起來,來回答帝國(guó)主義底進(jìn)攻紅軍,來?yè)碜o(hù)以武漢為中心的數(shù)省的蘇維埃政權(quán)首先的勝利!”②谷蔭:《反對(duì)帝國(guó)主義進(jìn)攻紅軍》,《文化斗爭(zhēng)》,1930年8月15日,第1卷第1期,第3頁(yè)。他還在《取消派與社會(huì)民主黨》一文中向反革命營(yíng)壘喊出了“打倒帝國(guó)主義!”“擁護(hù)社會(huì)主義的蘇俄!”③谷蔭:《取消派與社會(huì)民主黨》,《文化斗爭(zhēng)》,1930年8月15日,第1卷第1期,第5頁(yè)。等口號(hào)。社會(huì)科學(xué)家聯(lián)盟在擁護(hù)蘇維埃代表大會(huì)宣言中喊出的是“擁護(hù)中國(guó)蘇維埃政權(quán)!”“武裝擁護(hù)蘇聯(lián)!”“創(chuàng)造蘇維埃文化!”④社會(huì)科學(xué)家聯(lián)盟:《擁護(hù)蘇維埃代表大會(huì)宣言》,《文化斗爭(zhēng)》,1930年8月15日,第1卷第1期,第6頁(yè)。等口號(hào)。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家聯(lián)盟在宣示自己的“反社會(huì)民主主義宣傳綱領(lǐng)”中明確強(qiáng)調(diào):“只有推翻整個(gè)帝國(guó)主義在中國(guó)的統(tǒng)治,徹底消滅地主資產(chǎn)階級(jí)的政權(quán),建立工農(nóng)兵蘇維埃中國(guó),聯(lián)合蘇聯(lián),爭(zhēng)取社會(huì)主義的前進(jìn),這才是整個(gè)中國(guó)殖民地民族的解放之終極。”⑤社會(huì)科學(xué)家聯(lián)盟:《反社會(huì)民主主義宣傳綱領(lǐng)》,《文化斗爭(zhēng)》,1930年8月15日,第1卷第1期,第11頁(yè)。也因其如此,“左聯(lián)”才會(huì)要求每個(gè)盟員都應(yīng)該“堅(jiān)決的執(zhí)行自我批判和克服逡巡的動(dòng)搖的傾向,特別是和右傾的傾向作斗爭(zhēng)”⑥左聯(lián)執(zhí)行委員會(huì):《無(wú)產(chǎn)階級(jí)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新的情勢(shì)及我們的任務(wù)》,《文化斗爭(zhēng)》,1930年8月15日,第1卷第1期,第10頁(yè)。。一個(gè)刊物上篇篇文章都在為“蘇維埃”進(jìn)行聲援和鼎力支持,換在其他的時(shí)代,這種“宣傳”刊物會(huì)令讀者覺得既空洞又粗礪。然而,跳動(dòng)在左翼文人的文字里的,卻是非常明透的意旨、真切的希望和厚重的責(zé)任。這樣的文字僅從宣傳或政治層面來理解是不夠的,這其中還包含著新的道德觀念和階級(jí)情感。或者說,在左翼文學(xué)激昂的“口號(hào)”之中,還包含著更深廣意義上的底層關(guān)懷精神和普世價(jià)值取向。魯迅在1934年的一首《無(wú)題》詩(shī)中寫道:“萬(wàn)家墨面沒篙萊,敢有歌吟動(dòng)地哀。心事浩茫連廣宇,于無(wú)聲處聽驚雷。”⑦魯迅:《無(wú)題》,《魯迅全集》(第7卷),第448頁(yè)。該詩(shī)是魯迅在中國(guó)最黑暗的年代中所寫,時(shí)值日寇入侵華北,國(guó)民黨節(jié)節(jié)敗退之余,卻加緊了對(duì)中央蘇區(qū)的軍事圍剿和對(duì)進(jìn)步文藝界的文化圍剿。但從魯迅的詩(shī)中可以看出,左翼知識(shí)分子在如此惡劣的政治環(huán)境中依然沒有給自己留有什么精神退路,他們不僅以飽經(jīng)風(fēng)霜的心靈體認(rèn)著廣大民眾的痛苦,還在大眾的沉默中聽到了“驚雷”的震顫和革命的怒吼聲。與自由知識(shí)分子等多以衰敝的心態(tài)無(wú)奈體認(rèn)時(shí)代的痛苦情狀相比,左翼知識(shí)分子的人生體悟雖然簡(jiǎn)單,卻因“心連廣宇”而可謂“悟在天成”。
三、左翼立場(chǎng)的確立與激憤情緒的宣泄
在左翼文學(xué)的早期形態(tài)“普羅文學(xué)”興起之時(shí),國(guó)民黨御用文人認(rèn)為左翼文人之所以成立各種聯(lián)盟和組織,是為了彌補(bǔ)政治上的“失意”,比如署名“敵天”者認(rèn)為,“一班失意的文人學(xué)士們,因?yàn)樽霾坏讲块L(zhǎng),做不到委員,就五花八門預(yù)定出一個(gè)下等的計(jì)劃”⑧敵天:《嗚呼“自由運(yùn)動(dòng)”竟是一群騙人的勾當(dāng)——報(bào)告之二》,《民國(guó)日?qǐng)?bào)·覺悟》,1930年3月18日,第4張第2版。——成立“中國(guó)自由運(yùn)動(dòng)大同盟”這類組織來滿足自身政治權(quán)力維度上的缺失心理。這種臆斷無(wú)論在邏輯還是現(xiàn)實(shí)層面上都不值一駁,因?yàn)樽笠碇R(shí)分子根本不是要與國(guó)民黨政府調(diào)和、合作乃至為其服務(wù),而是要推翻當(dāng)時(shí)的國(guó)民黨政權(quán),建立新的無(wú)產(chǎn)階級(jí)政權(quán)。或者說,左翼思想文藝界成立各種組織的確含有政治維度,但又不限于此,正如“左聯(lián)”成立時(shí)所確定的組織行動(dòng)總綱領(lǐng):“(一)我們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的目的在求新興階級(jí)的解放。(二)反對(duì)一切對(duì)我們的運(yùn)動(dòng)的壓迫。同時(shí)決定了主要的工作方針,是:(一)吸收國(guó)外新興文學(xué)的經(jīng)驗(yàn),及擴(kuò)大我們的運(yùn)動(dòng),要建立種種研究的組織。(二)幫助新作家之文學(xué)的訓(xùn)練,及提拔工農(nóng)作家。(三)確立馬克思主義的藝術(shù)理論及批評(píng)理論。(四)出版機(jī)關(guān)雜志及叢書小叢書等。(五)從事產(chǎn)生新興階級(jí)文學(xué)作品。”①記者:《中國(guó)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成立》,《拓荒者》,1930年3月10日,第1卷第3期,第1130頁(yè)。通過文學(xué)活動(dòng)來支持世界無(wú)產(chǎn)階級(jí)解放運(yùn)動(dòng)和向國(guó)際反無(wú)產(chǎn)階級(jí)勢(shì)力作斗爭(zhēng)的態(tài)度、立場(chǎng)和目的,使得左翼知識(shí)分子在創(chuàng)作中收獲了自我實(shí)現(xiàn)的成就感。這也是左翼文藝界價(jià)值取向、政治意識(shí)、思想立場(chǎng)得以確立的標(biāo)志性認(rèn)識(shí)。
進(jìn)步思想文藝界的上述左翼立場(chǎng)并非突變完成,而是有一個(gè)從意識(shí)漸變到精神裂變的過程。在“五四”之后,注重社會(huì)批判或認(rèn)同暴力革命的知識(shí)分子逐漸轉(zhuǎn)向“左翼”,他們?cè)诔蔀樾挛膶W(xué)運(yùn)動(dòng)中的“暴徒”的同時(shí),也因承擔(dān)的社會(huì)責(zé)任和堅(jiān)守的政治立場(chǎng),而成為當(dāng)權(quán)者眼中的政治異端和C.P(共產(chǎn)黨)分子,他們所發(fā)表的言論被國(guó)民政府認(rèn)定為“反動(dòng)言論”。在此期間,由于政治領(lǐng)域的劇變,左翼知識(shí)分子的價(jià)值取向和人生道路都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由國(guó)民政府的擁護(hù)者變成反對(duì)者,尤其是在1927年清黨運(yùn)動(dòng)發(fā)生后,他們把這種變化公開彰顯出來,在“左聯(lián)”成立之前,他們往往以浪漫諦克式的書寫來呈現(xiàn)這種變化,而在“左聯(lián)”的規(guī)訓(xùn)和國(guó)民黨的文藝統(tǒng)制下,他們轉(zhuǎn)向了一種以寫實(shí)主義為主的文學(xué)寫作。就這樣,他們?cè)?0世紀(jì)30年代形成了自己的文學(xué)風(fēng)格和美學(xué)范式,并走向了藝術(shù)上的成熟期。發(fā)難期、萌生期和發(fā)展期的左翼文學(xué)作品當(dāng)然有諸多幼稚之處,更有的因政治生態(tài)、文化背景和時(shí)代語(yǔ)境的變化而失掉了被閱讀的意義。但在這樣一個(gè)表面看起來很簡(jiǎn)單的變化過程當(dāng)中,左翼作家卻得到了極為豐富的人生體驗(yàn)。以丁玲為例。丁玲以《夢(mèng)珂》《莎菲女士的日記》《暑假中》和《阿毛姑娘》等刊載于《小說月報(bào)》上的系列小說而成名,她的早期作品延承的是“五四”思潮追求個(gè)性主義、女性解放的思想主題,充滿了“五四”式的感傷情緒和寂寞之感:“我那時(shí)為什么寫小說,我以為是因?yàn)榧拍瑢?duì)社會(huì)不滿,自己生活無(wú)出路,有許多話需要說出來,卻找不到人聽,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機(jī)會(huì),于是便提起了筆,要代替自己給這社會(huì)一個(gè)分析,因?yàn)槲夷菚r(shí)是一個(gè)很會(huì)發(fā)牢騷的人,所以《在黑暗中》,不覺的染上一層感傷。”②丁玲:《我的創(chuàng)作生活》,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7集),第15-16頁(yè)。及至參加“左聯(lián)”后,她的創(chuàng)作發(fā)生了明顯變化,隨著《韋護(hù)》《母親》《一九三〇年春上海》《水》《莎菲女士日記第二部》《多事之秋》和《奔》等作品的問世,讀者可以清晰地看到她是怎樣在與過去的夢(mèng)幻、感傷告別,怎樣從注重個(gè)人的悲歡離合轉(zhuǎn)向反映現(xiàn)實(shí)重大題材,以及怎樣“審判我自己,克服我自己,改進(jìn)我自己”③丁玲:《莎菲女士日記第二部》,《丁玲全集》(第4卷),第9頁(yè)。的。在左翼文藝界看來,以《水》為代表的小說意味著一種“新的小說的誕生”④丹仁:《關(guān)于新的小說的誕生——評(píng)丁玲的〈水〉》,《北斗》,1932年1月20日,第2卷第1期,第235頁(yè)。,而對(duì)于作者丁玲來說,其轉(zhuǎn)變后的小說創(chuàng)作和政治立場(chǎng)在給她帶來牢獄之災(zāi)的同時(shí),也給她帶來了常人難以體會(huì)到的苦痛經(jīng)歷和生死感悟。丁玲的經(jīng)歷固然具有其獨(dú)異性,但丁玲的苦痛并非為她自己所獨(dú)有,而是面臨過生死抉擇處境的諸多左翼作家的相當(dāng)普遍的感受。
與左翼文學(xué)相比,其他流派作家的筆下同樣充溢著煩憂和憤怒之感。當(dāng)左翼知識(shí)分子投身于偉大的無(wú)產(chǎn)階級(jí)革命斗爭(zhēng)之時(shí),自由主義知識(shí)分子正在被“健康與尊嚴(yán)”問題煩擾著,他們將左翼文學(xué)視為“偏激派”來加以反對(duì):“我們不崇拜任何的偏激,因?yàn)槲覀兿嘈派鐣?huì)的紀(jì)綱是靠著積極的情感來維系的,在一個(gè)常態(tài)社會(huì)的天平上,情愛的分量一定超過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過互害與互殺的動(dòng)機(jī)。我們不愿意套上著色眼鏡來武斷宇宙的光景。我們希望看一個(gè)真,看一個(gè)正。”⑤徐志摩:《〈新月〉的態(tài)度》,《新月》,1928年3月10日,創(chuàng)刊號(hào),第7頁(yè)。民族主義文藝運(yùn)動(dòng)倡導(dǎo)者正在試圖用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chǎng)和情緒來裹挾中國(guó)文學(xué):“現(xiàn)在,中國(guó)文壇上正充滿了反民族主義的,傳統(tǒng)思想的,以個(gè)人為中心思想的文藝作品,受了宣傳的中國(guó)民眾,因此還是一盤散沙,還是一堆堆不可利用的垃圾。中國(guó)民眾沒有集團(tuán)的力量,在國(guó)際上沒有地位,都是文藝作品所宣傳出來的結(jié)果。”①傅彥長(zhǎng):《以民族意識(shí)為中心的文藝運(yùn)動(dòng)》,《前鋒月刊》,1930年11月10日,第1卷第2期,第3頁(yè)。“自由人”正在為“民族文藝運(yùn)動(dòng)”、國(guó)家主義文學(xué)的法西斯主義和左翼文藝運(yùn)動(dòng)的藝術(shù)政治化現(xiàn)象而憂憤,因?yàn)樗鼈兌甲璧K了文藝的自由創(chuàng)造。他們還強(qiáng)調(diào):法西斯主義文學(xué)“是特權(quán)者文化上的‘前鋒’,是最丑陋的警犬,他巡邏思想上的異端,摧殘思想的自由,阻礙文藝之自由的創(chuàng)造”;“藝術(shù)雖然不是‘至上’,然而決不是‘至下’的東西。將藝術(shù)墮落到一種政治的留聲機(jī),那是藝術(shù)的叛徒。藝術(shù)家雖然不是神圣,然而也決不是叭兒狗。以不三不四的理論,來強(qiáng)奸文學(xué),是對(duì)于藝術(shù)尊嚴(yán)不可恕的冒瀆。”②胡秋原:《阿狗文藝論》,《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史料選》(第3冊(c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18頁(yè)。“論語(yǔ)派”正在為小品文和“幽默”被攻擊而義憤:“埜容君嘆人間何世,我卻正在嘆世間何人?世間上若只有埜容其人者,則亦只有大品文章,處盛世則揖讓王庭,歌頌圣德,處亂世亦只有慷慨激昂,長(zhǎng)吁短嘆,更必有善哭民族,或相對(duì)潛然,或放聲大哭,或發(fā)起跪哭團(tuán),要求欠薪,或組織破壞團(tuán),向弱小女子示威,此輩人與我老死不相往來可也。”③林語(yǔ)堂:《論以白眼看蒼蠅之輩》,《申報(bào)·自由談》,1934年4月16日(第四張)。“醒獅派”則在為中國(guó)霸權(quán)的旁落而“感懷”:“普恩加賚是吾師,克烈門梭更不疑,他日政權(quán)如在手,要當(dāng)橫海制倭夷。”“六卻英夷百戰(zhàn)功,髫齡讀史慕文忠,當(dāng)年一炬焚鴉片,民族精神萬(wàn)古雄。”“華胄千年文化古,楚歌四面國(guó)基危,從今教養(yǎng)兼生聚,霸越亡吳事可期。”④曾琦:《感事書懷偶成數(shù)絕》,中共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xiàn)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冊(cè)),北京:中國(guó)文獻(xiàn)出版社,2011年版,第599頁(yè)。以是觀之,左翼知識(shí)分子與其他流派的知識(shí)分子在沿著不同的路向?qū)で笳胬碇T,可通往自由、審美的文藝之路尚且充滿艱難險(xiǎn)阻,更何況是通向充滿血與火的民主政治和階級(jí)斗爭(zhēng)之路,因此,前者的熱情要更加充溢,同時(shí)內(nèi)在的悲苦也更加厚重。
透過左翼文學(xué)中那些同情下層民眾悲苦遭際的作品可知,這里面所表現(xiàn)出來的左翼知識(shí)分子的激憤情緒,并非僅僅是一種“激憤之語(yǔ)”或情緒宣泄,被茅盾批評(píng)為文藝上的“白色的妖魔”⑤石萌:《“民族主義文藝”的現(xiàn)形》,《文學(xué)導(dǎo)報(bào)》,1931年9月13日,第1卷第4期,第10頁(yè)。的“民族主義文藝派”也會(huì)盛怒,主張書寫精雅、幽默小品文的“論語(yǔ)派”在被批評(píng)后也會(huì)惱怒,“自由人”“第三種人”看到左翼文學(xué)“獨(dú)霸”文壇時(shí)也會(huì)憤怒,“新月派”在面對(duì)“時(shí)代的變態(tài)”時(shí)也會(huì)心生怨懟,“海派”在被指責(zé)欺世盜名、胡編亂造、充滿銅臭氣時(shí)也會(huì)暴怒,……。然而,左翼文藝界以略顯“簡(jiǎn)單粗暴”的人間情感和粗疏闊落的藝術(shù)體悟,與勞苦大眾建立了精神聯(lián)系,并把自己植入到后者的悲苦與激憤之中,這就使得他們收獲了那個(gè)時(shí)代中最廣闊的痛苦和力量,也使得他們的歌吟和書寫洋溢著其他文人難以生成的激揚(yáng)熱情和樂觀精神。
四、抗戰(zhàn)元素的植入與抗?fàn)幰庾R(shí)的高揚(yáng)
隨著日寇的節(jié)節(jié)入侵和中共推行無(wú)產(chǎn)階級(jí)革命進(jìn)程的放緩,尤其是國(guó)防文學(xué)的倡導(dǎo),處于民族戰(zhàn)爭(zhēng)背景下的左翼文人放棄了以往的“成見”,開始全力為中華民族和國(guó)家免于日寇的荼毒而吶喊狂呼,這使得左翼文學(xué)與“抗戰(zhàn)”更加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1935年中共方面發(fā)表“八一”宣言《為抗日救國(guó)告全體同胞書》和《論反對(duì)日本帝國(guó)主義的策略》之后,成立“制日本帝國(guó)主義和漢奸賣國(guó)賊的死命”⑥毛澤東:《論反對(duì)日本帝國(guó)主義的策略》,《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史料選》(第3冊(c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55頁(yè)。的民族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很快成為中國(guó)社會(huì)各界有識(shí)之士的共識(shí)。此后,上海文化界馬相伯等三百余人有鑒于中華民族的危機(jī)日迫,發(fā)起了救國(guó)運(yùn)動(dòng),并發(fā)表《上海文化界救國(guó)運(yùn)動(dòng)宣言》,而在這三百多人中僅“左聯(lián)”盟員就有王淑明、白薇、周立波、艾蕪、何家槐、沈西苓(沈葉沉)、沈起予、沙汀、周鋼鳴、陳荒煤、唐弢、徐懋庸、許杰、許幸之、麗尼、戴平萬(wàn)、聶紺弩、魏金枝、關(guān)露等。審視1936年以后左翼作家的言論,它們表現(xiàn)出了與“左聯(lián)”成立前后明顯不同的精神氣度:“在國(guó)防文學(xué)的旗子下面,一定要除去一切狹窄的宗派思想和意氣;凡中國(guó)人,只要不是萬(wàn)惡不赦的賣國(guó)賣民族的明中暗里的漢奸,只要不是甘心做亡國(guó)奴的豚犬,都是國(guó)防文學(xué)的營(yíng)盤里面的戰(zhàn)友。”①立波:《關(guān)于“國(guó)防文學(xué)”》,《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史料選》(第3冊(cè)),第266頁(yè)。而抗戰(zhàn)元素的大量植入顯然為左翼知識(shí)分子帶來了不同的生命感悟。
盡管國(guó)民黨政府禁止在文藝作品和電影中吶喊反日口號(hào),但左翼作家還是通過隱喻、暗示等筆法表達(dá)了他們的愛國(guó)情愫,也展現(xiàn)了與以往階級(jí)斗爭(zhēng)情緒高昂情狀不同的精神氣氛。丁玲到陜北后寫就的第一篇小說《一顆未出膛的槍彈》(1937),描寫陜北紅軍的一個(gè)小馬夫被東北軍某連抓獲,連長(zhǎng)下令槍斃他,他卻鎮(zhèn)靜自若地說:“連長(zhǎng)!還是留著一顆槍彈吧,留著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殺我!”②丁玲:《一顆未出膛的槍彈》,《丁玲全集》(第4卷),第131頁(yè)。他的大無(wú)畏精神、視死如歸的氣度和聯(lián)合抗日的立場(chǎng)終于感動(dòng)了這群東北軍下層官兵,他們擁抱著他并熱情地把他舉了起來。這樣的寫法在“左聯(lián)”成立之初是不可想象的,是肯定會(huì)受到批判和被指責(zé)犯有“調(diào)和主義”錯(cuò)誤的。奚如的《在塘沽》(1936)開篇立調(diào):“這是一個(gè)涂染著永難磨滅的恥辱的都市——塘沽。有名的‘長(zhǎng)期抵抗’主義者們,曾經(jīng)在這兒同‘友邦’簽訂過有名的協(xié)定。”③奚如:《在塘沽》,《海燕》,1936年1月20日,第1期,第4頁(yè)。小說寫一個(gè)為日寇貼寫著“中日滿提攜呀,獨(dú)立自治呀!”標(biāo)語(yǔ)的茶房——“老疙瘩”并非天生的漢奸,如果不是因?yàn)閲?guó)民黨的“不抵抗”讓他沒有飯吃,他也不會(huì)去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而如果給他機(jī)會(huì)與東洋人拼命,他也會(huì)抽刀去殺日寇做個(gè)“男子漢大丈夫”的。滬生的《記十二月二十四日南京路》(1936)記錄了愛國(guó)民眾在南京路抗日游行時(shí)的情狀,盡管他們受到了巡捕們的鎮(zhèn)壓,但他們“忿怒的咆哮”——“打倒╳╳帝國(guó)主義!”等口號(hào)也激起了愛國(guó)者的反抗意志。路丁的《一·二八前進(jìn)》(1936)通過記敘一次街頭紀(jì)念“一二八”的示威游行活動(dòng),歌贊了愛國(guó)群眾的偉大力量和中華民族的不屈精神:“腳下是流過自己的和敵人的血的土地,頭上是耀著自由光芒的太陽(yáng),在這中間,便是一顆偉大的,充滿了毀滅一切力量的不愿做奴隸的心,中華民族的心。”④路丁:《一·二八前進(jìn)》,《海燕》,1936年2月20日,第2期,第7頁(yè)。與其他流派知識(shí)分子的筆下充溢著人事滄桑之感有所不同,20世紀(jì)30年代的左翼知識(shí)分子經(jīng)歷了太多人生劫難,尤其是戰(zhàn)火的洗禮讓他們的筆下凝聚著剛毅之感,而對(duì)個(gè)體苦難乃至死生的勘破,又使他們獲得了對(duì)于民族、國(guó)家、世界的新的視域和感悟。
事實(shí)證明,左翼作家對(duì)于抗戰(zhàn)氛圍的把握是非常敏銳和精準(zhǔn)的,他們以小見大,在國(guó)民黨的報(bào)紙新聞里也能敏感地抓出那團(tuán)“氛圍氣”,從而獲得壯烈、崇高的審美體悟。胡風(fēng)曾經(jīng)記錄過兩則《申報(bào)》上的“北平通訊”:
青年熱血淋漓滿街頭:迨至南池子中間,突有大批警察及保安隊(duì),一面用兩架水龍放水噴擊學(xué)生,一面用鐵棍及指揮刀實(shí)行與學(xué)生沖突。當(dāng)時(shí)學(xué)生個(gè)個(gè)抱定為國(guó)犧牲精神,雖赤手空拳,亦毫不示弱。糾察隊(duì)奮勇當(dāng)先,大演奪刀慘劇,其余學(xué)生,一鼓向前,實(shí)行與警察肉搏。結(jié)果,卒將水龍奪下。是役警察與學(xué)生互有受傷。后大隊(duì)繼續(xù)南行,并高呼勝利口號(hào),歡迎民眾自由參加愛國(guó)運(yùn)動(dòng)。出南池子西行,入西長(zhǎng)安街,經(jīng)前軍分會(huì)門前時(shí),又與大批軍警沖突。警察以兩次失敗于學(xué)生,故此次迎擊甚烈,大刀鐵棍,著處無(wú)情,是役學(xué)生被擊傷者十余人……。
鵠立講演悲壯凄愴:既決定露宿后,各校學(xué)生派代表分別購(gòu)辦食物,因?qū)W生皆由早七點(diǎn)出發(fā)一粒未下。東北大學(xué)學(xué)生二百余人,準(zhǔn)備枵腹過夜,師范大學(xué)及附中男女同學(xué),捐資購(gòu)買燒餅千余套,贈(zèng)與東北大學(xué)充饑。是時(shí)各校學(xué)生分別向市民講演,全體學(xué)生,哭聲凄愴,圍立兩旁之市民,無(wú)不落淚涕泣。迫至晚七時(shí)余,在城外各校學(xué)生,多有返校率領(lǐng)學(xué)校工友,攜大批被褥及冷水供給露宿同學(xué)應(yīng)用者……。⑤胡風(fēng):《文藝界底習(xí)風(fēng)一景》,《海燕》,1936年1月20日,第1期,第18-19頁(yè)。
在胡風(fēng)看來,由于北平的愛國(guó)學(xué)生看破了日寇步步蠶食、陰謀分裂和全面侵略中國(guó)的陰謀,所以他們舉行示威游行和愛國(guó)演講,這是他們?yōu)榱俗杂珊头纯古`命運(yùn)的一種英雄壯舉,他們?cè)敢馀c國(guó)家共生共死的態(tài)度結(jié)出了美麗的“人民之花”,他們的悲憤是一切中國(guó)人的悲憤,他們的行動(dòng)本身就是“一首抒情詩(shī)”,在這樣的氛圍下,那些夢(mèng)想著做“無(wú)冠的皇帝”和“奴視”他人的藝術(shù)家,因“動(dòng)物的個(gè)人主義”而患上了“從集團(tuán)主義的感情之萎縮發(fā)展來的病”,散發(fā)著“有毒的質(zhì)素”,①胡風(fēng):《文藝界底習(xí)風(fēng)一景》,《海燕》,1936年1月20日,第1期,第18-20頁(yè)。他們的丑惡嘴臉、自私行徑必然會(huì)受到唾棄和批判。胡風(fēng)的批評(píng)是非常有針對(duì)性的。與諸如自由主義知識(shí)分子僅看到學(xué)生在制造社會(huì)混亂和破壞秩序不同,左翼知識(shí)分子透過這些熱血青年的聲音和壯舉,一方面感受到的是中國(guó)人民不愿做奴隸的悲憤和痛苦,另一方面看到了中華民族為了占取生存權(quán)是怎樣翻開“壯麗史詩(shī)”這動(dòng)人一頁(yè)的。兩相比較,雙方的境界和品格可謂高下立分。盡管很多自由知識(shí)分子的藝術(shù)感悟力、藝術(shù)靈氣、藝術(shù)感覺、藝術(shù)功力和藝術(shù)水平要比普通的左翼作家高明得多,但他們所欠缺的是左翼作家推翻現(xiàn)行政權(quán)和社會(huì)秩序的勇氣,所匱乏的是左翼作家與底層民眾一心同歸的信仰,他們將自己的藝術(shù)靈氣和審美感悟獻(xiàn)給了小資受眾,卻沒有想到底層民眾更需要精神滋養(yǎng)。當(dāng)他們主動(dòng)選擇遠(yuǎn)離和放棄“大眾”時(shí),也就難免會(huì)被“大眾”所疏離和拋棄。
不同于常人和某些知識(shí)分子的“忍從”心理,左翼作家總是要在陰冷的霸權(quán)暗影、專制體制和戰(zhàn)火連天的世界里唱起激昂的抗?fàn)幹琛JY光慈早在1925年寫就的一首詩(shī)中就曾傳達(dá)出決不“忍從”的斗志:“頂好敵人以機(jī)關(guān)槍打來,我們也以機(jī)關(guān)槍打去!/我們的自由,解放,正義,在與敵人斗爭(zhēng)里。/倘若我們還講什么和平,守什么秩序,/可憐的弱者呵,我們將永遠(yuǎn)地——永遠(yuǎn)地做奴隸!”②蔣光慈:《血祭》,《蔣光慈文集》(第三卷),第425-426頁(yè)。詩(shī)人的詩(shī)興是由“五卅”流血紀(jì)念周紀(jì)念日而引發(fā)的。而類似于“五卅”這樣值得紀(jì)念的日子實(shí)在太多了,如“五一”“五九國(guó)恥日”“九一八”“一二八”“八一三”等。是故,左翼作家似乎從來都不缺少抒發(fā)反抗意緒的由頭和題材。魯迅將他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受于1936年成文奉獻(xiàn)給日本讀者,他將自己無(wú)法接受陀氏“忍從”的主張解析得非常清楚,他認(rèn)為在中國(guó)沒有俄國(guó)的基督,在中國(guó)君臨的是“禮”而不是“神”,百分之百的“忍從”在一般人的身上是沒有的,因此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挖掘下去“恐怕也還是虛偽”,因?yàn)楸粔浩日吲c壓迫者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是不同的,而陀氏的“忍從”“太偉大”,是并非人們所能修煉的“功德”。③魯迅:《陀思妥夫斯基的事——為日本三笠書房〈陀思妥夫斯基全集〉普及本作》,《魯迅全集》(第6卷),第412頁(yè)。魯迅雖然極為贊賞陀氏對(duì)于“窮人”病態(tài)心理的深入挖掘和高超的心理分析才能,但他對(duì)這個(gè)“殘酷的天才”的“忍從”思想和基督式的寬恕精神是反對(duì)的。由對(duì)陀氏世界觀、人生觀和倫理觀局限的批評(píng),魯迅等于再一次強(qiáng)調(diào)了他以往言說過的“被壓迫者對(duì)于壓迫者,不是奴隸,就是敵人,決不能成為朋友”④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后記》,《魯迅全集》(第6卷),第451頁(yè)。的灼見,從而向日本讀者暗示了中國(guó)人民不可能與日本侵略者“相互提攜”共建“東亞共榮圈”的道理。當(dāng)左翼作家由現(xiàn)實(shí)感悟到“忍從”思想不可有、“抗?fàn)帯币饽畈豢蔁o(wú)的時(shí)候,他們其實(shí)找到了最簡(jiǎn)單的真理和最執(zhí)著的信念以及最實(shí)用的政治原則。
不同于其他知識(shí)分子常見的步入中年后的保守心態(tài),左翼知識(shí)分子依然充溢著濃郁的抗戰(zhàn)熱情和超出了“五四”思想范疇的生命感悟。與“五四”青年作者相比,左翼知識(shí)分子由于經(jīng)歷過各種反革命政變、工農(nóng)革命運(yùn)動(dòng)和抗日救亡運(yùn)動(dòng)的洗禮,因此有著更為豐富的生死體驗(yàn)。或者說,他們的人生感悟和世事體驗(yàn)并非由家事、個(gè)人私事引起,而是由國(guó)事天下事引發(fā)的,所以具有明晰的針對(duì)性和相對(duì)的完整性:他們的創(chuàng)作不再如一些“五四”作者那樣任由情感自由流動(dòng),以致于感傷、憂郁等低沉的情緒肆意泛濫,他們會(huì)更加明了自己的創(chuàng)作動(dòng)機(jī),會(huì)將自己深沉的情感傳向特定的接受對(duì)象。不同于其他20世紀(jì)30年代文學(xué)作者中年感悟的繁雜和充滿糾葛,左翼知識(shí)分子的感悟往往容易確定,相對(duì)清楚。同樣是閱讀周作人的《五十自壽詩(shī)》:“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xué)畫蛇。老去無(wú)端玩骨董,閑來隨分種胡麻。旁人若問其中意,且到寒齋吃苦茶。”在讀出了周作人“淡然物外”①曹聚仁:《周作人先生的自壽詩(shī)》,《申報(bào)·自由談》,1934年4月24日(第4張)。的出世心態(tài)后,劉大杰對(duì)于其“寄沉痛于悠閑”的感悟感動(dòng)得“凄然淚下”②林語(yǔ)堂:《周作人詩(shī)讀法》,《申報(bào)·自由談》,1934年4月26日(第5張)。,而左翼知識(shí)分子則讀出了其消極出世的意蘊(yùn)并大加嘲諷:“先生何事愛僧家?把筆題詩(shī)韻押裟。不趕熱場(chǎng)孤似鶴,自甘涼血懶如蛇。選將笑話供人笑,怕惹麻煩愛肉麻。誤盡蒼生欲誰(shuí)責(zé)?清談妮妮一杯茶。”③埜容(廖沫沙):《人間何世?》,《申報(bào)·自由談》,1934年4月14日(第5張)。從生命感悟方面來說,此詩(shī)作者廖沫沙肯定沒有周作人的深透,但在他看來,周作人的選擇是有問題的。這問題的所在就是周作人不僅沉溺于一己的空靈而無(wú)視神州大地的重重苦難,而且還用錯(cuò)誤的出世思想和人生觀來誤導(dǎo)“蒼生”、麻痹國(guó)民的精神。廖沫沙的理解肯定存有誤讀之處,但其所思所想體現(xiàn)了典型的左翼理路。左翼作家希望從感喟的詩(shī)句中見出作者的熱血丹心和愛國(guó)之志,為此他們中的很多人執(zhí)意通過淺顯的文句去激揚(yáng)愛國(guó)青年乃至勞苦大眾的生之意志和反抗情緒。
五、中國(guó)意識(shí)、樂觀態(tài)度與愛鄉(xiāng)情結(jié)的彰顯
當(dāng)左翼文藝界以集體意識(shí)、階級(jí)意識(shí)、大眾意識(shí)和國(guó)防意識(shí)“壓制”著同時(shí)代其他文學(xué)中的個(gè)體意識(shí)、精英意識(shí)、自由意識(shí)和漢奸意識(shí)時(shí),他們?cè)噲D建立新的“中國(guó)意識(shí)”“民族意識(shí)”和“愛鄉(xiāng)意識(shí)”。
在日寇日益猖獗的危機(jī)局勢(shì)下,“中國(guó)”和“中華民族”在左翼作家筆下成了兩個(gè)出現(xiàn)頻率極高的名詞。在“兩個(gè)口號(hào)”之爭(zhēng)的文章中,這兩個(gè)詞被大量地重復(fù)使用著。“民族革命戰(zhàn)爭(zhēng)的大眾文學(xué)決不是只局限于寫義勇軍打仗,學(xué)生請(qǐng)?jiān)甘就鹊鹊淖髌贰_@些當(dāng)然是最好的,但不應(yīng)當(dāng)這樣狹窄。它廣泛得多,廣泛到包括描寫現(xiàn)在中國(guó)各種生活斗爭(zhēng)的有意識(shí)的一切文學(xué)。因?yàn)楝F(xiàn)在中國(guó)最大的問題,人人所共的問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④魯迅:《論現(xiàn)在我們的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病中答訪問者》,《文學(xué)界》,1936年7月10日,第1卷第2號(hào),第10頁(yè)。“我以為現(xiàn)階段的中國(guó)民族革命戰(zhàn)爭(zhēng)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應(yīng)該是‘國(guó)防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⑤徐懋庸:《“人民大眾向文學(xué)要求什么?”》,《光明》,1936年6月10日,第1卷第1號(hào),第14頁(yè)。“自從鴉片戰(zhàn)爭(zhēng)以后,中華民族不斷地遭受了帝國(guó)主義的經(jīng)濟(jì),政治,文化種種侵略,這構(gòu)成了中國(guó)人民大眾的苦難的源泉,引起了他們的要求民族解放的無(wú)止境的運(yùn)動(dòng)。”⑥周揚(yáng):《現(xiàn)階段的文學(xué)》,《光明》,1936年6月25日,第1卷第2號(hào),第97頁(yè)。盡管持續(xù)受到國(guó)民黨政府禁止發(fā)表抗日言論的政策的打壓,但左翼文學(xué)中依然因滿溢的愛國(guó)主義精神而流露出了對(duì)祖國(guó)的一切尤其是對(duì)愛國(guó)民眾的愛。當(dāng)然,也有左翼作家因提倡“國(guó)防文學(xué)”削弱乃至放棄了自身的左翼立場(chǎng),并對(duì)國(guó)民黨重新燃起了政治清明、救國(guó)救民的奢望與幻夢(mèng)。所以魯迅告誡左翼文藝界決不能停止歷來的反法西斯主義和反對(duì)一切反動(dòng)者的血的斗爭(zhēng),且要將這些斗爭(zhēng)具化到抗日反漢奸的斗爭(zhēng)“總流”中去,最關(guān)鍵的是:“決非革命文學(xué)要放棄它的階級(jí)的領(lǐng)導(dǎo)的責(zé)任,而是將他的責(zé)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階級(jí)和黨派,一致去對(duì)外。這個(gè)民族的立場(chǎng),才真是階級(jí)的立場(chǎng)。”⑦魯迅:《論現(xiàn)在我們的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病中答訪問者》,《文學(xué)界》,1936年7月10日,第1卷第2號(hào),第9-10頁(yè)。事實(shí)證明,魯迅的提醒是非常及時(shí)的,他之所以大力提倡“民族革命戰(zhàn)爭(zhēng)的大眾文學(xué)”和不愿解散“左聯(lián)”,是因?yàn)樗兄鼮檎_、精準(zhǔn)的“中國(guó)意識(shí)”和“民族意識(shí)”。
革命作家曾經(jīng)非常認(rèn)真地探究過“小我”和“大我”的倫理關(guān)系,希冀借此找到自我在大時(shí)代中的位置和在革命運(yùn)動(dòng)中激揚(yáng)生命的高潮體驗(yàn)。然而他們真正找到這種體悟要等到抗戰(zhàn)運(yùn)動(dòng)蜂起之時(shí),是時(shí)的抗日民氣鼓蕩情形令人激動(dòng)不已,一切都要為抗戰(zhàn)服務(wù)幾乎成了所有人的共識(shí),不認(rèn)同這一點(diǎn)的人會(huì)受到猛烈的批判,起自1938年的對(duì)“與抗戰(zhàn)無(wú)關(guān)”論的斗爭(zhēng)的大爆發(fā)就是一個(gè)例證。梁實(shí)秋在編輯《中央日?qǐng)?bào)》副刊《平明》時(shí)向各界約稿,他表示:“于抗戰(zhàn)有關(guān)的材料,我們最為歡迎,但是與抗戰(zhàn)無(wú)關(guān)的材料,只要真實(shí)流暢,也是好的,不必勉強(qiáng)把抗戰(zhàn)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戰(zhàn)八股’,那是對(duì)誰(shuí)都沒有益處的。”①梁實(shí)秋:《編者的話》,《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史料選》(第4冊(cè)),第243頁(yè)。應(yīng)該說,梁實(shí)秋的觀點(diǎn)從文藝自身和形式邏輯的角度來說并沒有什么錯(cuò)誤,但在文藝界卻引起了軒然大波,遂被口誅筆伐。客觀地說,左翼文藝界對(duì)于梁實(shí)秋言論的解讀存在誤讀現(xiàn)象乃至“栽贓”嫌疑,之所以如此:其一是因?yàn)榱簩?shí)秋的言論不合時(shí)宜;其二是因?yàn)樽笠砦乃嚱缗c梁實(shí)秋“結(jié)仇”已久,因此他被尋找批評(píng)靶子的左翼文藝界故意誤讀不可避免;其三是因?yàn)樽笠砦乃嚱绶磳?duì)書寫與抗戰(zhàn)無(wú)關(guān)作品的藝術(shù)傾向早在“兩個(gè)口號(hào)”之爭(zhēng)時(shí)就已經(jīng)表現(xiàn)得非常明顯,比如郭沫若在反對(duì)提倡“民族革命戰(zhàn)爭(zhēng)的大眾文學(xué)”口號(hào)時(shí)強(qiáng)調(diào)說:“‘國(guó)防文學(xué)’之提出正是要叫作家們跑上抗日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而提出這口號(hào)的都是左翼作家。他們很明白而正確的適應(yīng)著目前的現(xiàn)實(shí)及政治的要求而擴(kuò)大了向來的組織,他們并沒有所‘囿’因而也似乎用不著再拿新的口號(hào)來‘推動(dòng)’。”②郭沫若:《蒐苗的檢閱》,《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史料選》(第3冊(cè)),第405頁(yè)。激進(jìn)的左翼知識(shí)分子連魯迅和茅盾提倡一個(gè)新的口號(hào)都要加以批評(píng),更何況是梁實(shí)秋提出的“反動(dòng)”主張呢?
在抗戰(zhàn)烽火熊熊燃燒的特定歷史時(shí)期,與“絕望”相對(duì)應(yīng)的“樂觀”是左翼文學(xué)中習(xí)見的一種態(tài)度和感情。1935年12月魯迅在國(guó)內(nèi)階級(jí)矛盾和國(guó)際民族矛盾極為尖銳的時(shí)代背景下作詩(shī)道:“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塵海蒼茫沉百感,金風(fēng)蕭瑟走千官。老歸大澤菰蒲盡,夢(mèng)墜空云齒發(fā)寒。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斗正闌干。”③魯迅:《亥年殘秋偶作》,《魯迅全集》(第7卷),第451頁(yè)。在看到國(guó)民黨統(tǒng)治下一片肅殺、凄涼光景和大批國(guó)民黨官員逃難的同時(shí),魯迅一方面為流離失所的人們感到深深的悲哀,另一方面更看到這是中國(guó)所面臨的黎明前最黑暗的時(shí)刻。奚如的《宣傳隊(duì)》(1936)寫華北一個(gè)小村莊的人們急切地想要了解政局的發(fā)展路向,正當(dāng)他們擔(dān)心自己要當(dāng)亡國(guó)奴時(shí),村里來了一個(gè)由12個(gè)北平學(xué)生組成的宣傳隊(duì),學(xué)生告訴村民們,東洋鬼子即將殺到這里,面對(duì)華北五省即將被漢奸出賣給日本鬼子的局勢(shì),村民們只能自己救自己,于是村里的救國(guó)會(huì)順利組織起來了。作者批判了軍警憲兵不去打東洋鬼子卻死命鎮(zhèn)壓愛國(guó)學(xué)生的愚蠢與毒辣,歌頌了村民們純樸的保家衛(wèi)國(guó)意識(shí)。羅烽的《值得祝福的人》(1936)講述了一個(gè)被日本帝國(guó)主義暴君壓迫的普通日本士兵岡田,不愿意為本國(guó)的階級(jí)敵人驅(qū)使來殺害中國(guó)的無(wú)辜士兵,終至被逮捕送回日本。小說表達(dá)了對(duì)岡田的敬意,因?yàn)樗且粋€(gè)“值得祝福的人”。抗日戰(zhàn)爭(zhēng)的勝利不僅要靠中國(guó)軍民的努力,也要依憑日本友人的幫助。上述幾部作品的情形可以證明,左翼作家還是看好抗日戰(zhàn)爭(zhēng)勝利前景的。比較起來,左翼作家在“樂觀”的同時(shí)也同樣會(huì)憂愁,但他們憂愁的是“宗派主義”“關(guān)門主義”對(duì)思想文藝界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阻礙;憂愁的是國(guó)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抗日不作為”;憂愁的是國(guó)民黨發(fā)動(dòng)全面內(nèi)戰(zhàn)的愈演愈烈;憂愁的是文藝大眾化運(yùn)動(dòng)開展的形式、內(nèi)容不理想,憂愁的是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的難以落到實(shí)處:“爭(zhēng)取工作的具體化,踏實(shí)化,擴(kuò)大化,這是統(tǒng)一戰(zhàn)線底要義。”④辛人:《論當(dāng)前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底諸問題》,《現(xiàn)實(shí)文學(xué)》,1936年8月1日,第1卷第2期,第174頁(yè)。左翼文藝界所“憂愁”的東西,不僅體現(xiàn)了他們的良知,也體現(xiàn)了他們愛國(guó)愛民的高尚情感和良好品格。反過來,也正是這種情感和品格讓他們看到了中華民族團(tuán)結(jié)一心必然戰(zhàn)勝日本帝國(guó)主義的勝利前景。
在左翼作家因戰(zhàn)火而生成的感悟中,有自由主義文學(xué)所沒有的悲切苦嘆、憤怒譏嘲和光明憧憬等諸般感受雜糅在一起的感喟,這正如《中國(guó)的一日》的“廣告詞”所說的那樣:“從這里傳出了中國(guó)每一個(gè)角落里的人們的:悲壯的吶喊,沉痛的聲訴,辛辣的咒詛,含淚的微笑,沸涌的熱情的潛流,醉生夢(mèng)死中的囈語(yǔ),全無(wú)心肝者的獰笑,宗教迷信者的麻醉;然而也從這丑惡與圣潔光明與黑暗交織成的‘橫斷面’上,看出了希望,看出了樂觀,看出了人民大眾的覺醒,因?yàn)橐幻婀倘皇腔囊c無(wú)恥,然而又一面是在嚴(yán)肅的工作。”①《現(xiàn)代中國(guó)的總面目——〈中國(guó)的一日〉》,《光明》,1936年11月10日,第1卷第11號(hào)。就具體創(chuàng)作而言,我們不妨以《光明》月刊上刊載的一些詩(shī)歌為例。臧克家在《霧警》(1卷4號(hào))中寫道:“夜間,幸福飾好了別人的夢(mèng),/我卻苦苦閉不煞眼睛,/拉長(zhǎng)了的嘆息/結(jié)起了斷續(xù)的‘霧警’,/明天就走!我愛這一身泥土,/不愿散給綠海上的清風(fēng)。”“霧警”發(fā)出的悲切之聲令人不堪聽,而國(guó)土的淪喪更是令人無(wú)法接受。張澤厚在《秋收》(1 卷8號(hào))中替農(nóng)民叫屈、嗟嘆:“哎,不怨天干恨打仗,/農(nóng)忙時(shí)候拉夫耽擱多,/哎,不怨天干恨苛政,/繳清糧銀才準(zhǔn)做生活。……窮人無(wú)命活,/莫米淘上鍋,/呵,饑餓!饑餓!/饑餓的火焰要把世界翻轉(zhuǎn)過!”詩(shī)人批判戰(zhàn)爭(zhēng)、拉夫和苛捐雜稅把農(nóng)民逼上了饑餓的絕路,也把他們逼上了反對(duì)剝削壓迫的抗?fàn)幹贰H吴x在《十二月的行列》(創(chuàng)刊號(hào))中寫道:“十二月的步武喲,更堅(jiān)實(shí)地展開吧,/看,橫蠻的強(qiáng)敵已經(jīng)在發(fā)抖!/一九三五年的戰(zhàn)鼓喲,擂得再響些吧,/聽,沉睡的中國(guó)已經(jīng)開始怒吼!”他還在《“東北永遠(yuǎn)是我們的”》(1卷7號(hào))中狂吼:“讓四萬(wàn)萬(wàn)人同在整齊的步伐聲中:/用無(wú)數(shù)憤怒的喉嚨,/狂熱地吼出意志的聲響;/讓全中國(guó),讓全世界,讓全宇宙/都裝滿這種音波——/‘東北永遠(yuǎn)是我們的!’”在詩(shī)人看來,一旦人民開始反抗,中國(guó)就會(huì)覺醒,她的怒吼聲必將響徹云霄,令日寇喪膽。施誼在《一條腿——紀(jì)念十一周年的五卅行列》(1卷2號(hào))中借助一個(gè)參加“五卅”游行活動(dòng)的獨(dú)腿者之口說:“兩條腿的人們,/你們的努力應(yīng)當(dāng)加倍!/在反抗╳╳帝國(guó)主義的戰(zhàn)線上,/一條腿的也不甘后退!”蔣錫金在《流尸》(1卷3號(hào))中寫道:“別打點(diǎn)這些流尸往那兒去,/聽遠(yuǎn)近的號(hào)角戰(zhàn)鼓,/要去死線上奪取一條生路,/更會(huì)有千萬(wàn)流尸接連往海上飄,/不做奴隸!流尸也要張著嘴叫。”令人驚悚的比喻,所映照出的卻是不屈的靈魂。王門在《“把我們開到最前線”——囚人之歌》(1卷5號(hào))中寫道:“肉動(dòng)起來便是力量,/心跳出來便是炸彈呀!/給我們跟著民族/來創(chuàng)辟光明的翌晨吧!”連囚徒都要開到前線進(jìn)行抗日,因?yàn)橹挥腥绱瞬庞小肮饷鞯囊畛俊笨裳浴}R達(dá)在《松花江上的歌聲》(2卷9號(hào))中表示,他從“年青人”的身上看到了中國(guó)的光明前景:“年青人,/烈火一般的真情,/相信中國(guó)的永生;/相信我們的青春!//槳兒在手里,/努力劃行,/遙遠(yuǎn)的路程,/前途是光明的閃映。”宇昂在《那一天就快要到來——獻(xiàn)給前線抗敵戰(zhàn)士》(2卷4號(hào))中鼓勵(lì)抗日將士道:“不殲滅仇寇永不甘休,/血染的河山將永為我所有!/那一天就快要到來,/‘光明’就在我們的前頭!”關(guān)露在《風(fēng)波亭》(1卷6號(hào))中寫道:“風(fēng)波亭,/我在你歷史底故事中/看見和知道了許多許多的事情:/我看見血染的英雄的背影/看見屈膝而諂笑的奸臣。/知道絞刑架賽過十字架的光榮,知道曾經(jīng)在敵人面前跪過的秦檜/還在岳王墓上/跪到如今!”這等于是在警告漢奸賣國(guó)賊,他們必將如秦檜那樣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郭沫若的《們》(1卷10號(hào))歌頌了“群體”的偉大力量:“當(dāng)我感覺著孤獨(dú)的時(shí)候,/我只要把你,和我或我的親近者,結(jié)成一道;/在我的腦中回環(huán)得這樣的幾聲:/我們,咱們弟兄們,同志們,年青的朋友們……/我便勇氣百倍,筆陣可把千人橫掃。”詩(shī)人的勇氣和底氣來自于這樣的事實(shí):志同道合者的抗日決心和愛國(guó)情懷已經(jīng)匯成了一股橫掃走狗、漢奸、劊子手和喪心病狂的文化摧殘者、和平破壞者的洪流。
左翼作家很喜歡從戰(zhàn)火中挖掘愛國(guó)者對(duì)已經(jīng)或即將淪亡國(guó)土尤其是故鄉(xiāng)深沉的愛的氣息。楊騷在《福建三唱》中夸贊自己的故鄉(xiāng),“頭枕武夷山,/腳洗太平洋;/胸藏豐富的礦產(chǎn),/頸纏閃耀的閩江,/呼吸要震動(dòng)中原的乳峰/伸手好摸南國(guó)的頭臉”,因此詩(shī)人深情地表示“我愛我的故鄉(xiāng)”。②楊騷:《福建三唱》,《光明》,1936年6月10日,創(chuàng)刊號(hào),第31頁(yè)。在詩(shī)人心中,如此美好的故鄉(xiāng),如果“我們”還不去努力護(hù)衛(wèi),她們就會(huì)成為第二乃至第三個(gè)東北三省。舒群《在故鄉(xiāng)——紀(jì)念我們的‘九一八’》深情地吟唱道:“四季的景色,/年年在我眼前劃過;/在故鄉(xiāng),/長(zhǎng)大了我。//我愛——/我的故鄉(xiāng);/我愛——/在故鄉(xiāng)。”③舒群:《在故鄉(xiāng)——紀(jì)念我們的‘九一八’》,《光明》,1936年9月10日,第1卷第7號(hào),第456頁(yè)。可是“九一八”事變后故鄉(xiāng)被日寇霸占了,所以“我”不會(huì)忘記故鄉(xiāng)的三千萬(wàn)奴隸在受苦,“我”將用“不成歌的歌詞”唱出“人類的不平”和寫出“世界的不公正”。關(guān)露在《故鄉(xiāng)我不讓你淪亡》中寫到:“我愛你,有如愛我的/父母,兄弟,我忠實(shí)的朋友”①關(guān)露:《故鄉(xiāng)我不讓你淪亡》,《光明》,1936年10月25日,第1卷第10號(hào),第660-661頁(yè)。,憶起故鄉(xiāng)和祖國(guó)的現(xiàn)狀令詩(shī)人倍感“惆悵”,但他發(fā)誓不讓故鄉(xiāng)淪亡。田軍在《我家在滿洲》中痛惜自己的家鄉(xiāng)被日寇霸占:“我沒有了家——我家在滿洲:/我的家現(xiàn)在住滿了惡霸,/他們的戰(zhàn)馬拴在門前的樹上,/那樹原先是大家乘涼的,/馬卻啃光了它們的皮,/明年它們不會(huì)再有綠葉森森。”②田軍:《我家在滿洲》,《海燕》,1936年1月20日,第1期,第23頁(yè)。臧克家在《肉的長(zhǎng)城》中歌頌了綏東抗戰(zhàn)將士用自己的血肉身軀筑起“長(zhǎng)城”保衛(wèi)國(guó)土的英雄形象:“好男兒/給祖國(guó)打起了肉的長(zhǎng)城!/死也不退一步,/——退一步損一寸國(guó)土!/猛打,/立住腳;/進(jìn)一步,/——奪回一寸山河!”③雷石榆:《被強(qiáng)奸了的土地上》,《夜鶯》,1936年6月15日,第1卷第4期,第246頁(yè)。羅烽在《憶故鄉(xiāng)》中將故鄉(xiāng)比作“情人”來加以思念:“我獨(dú)待黃昏,/我佇望著東北飛來的云,/情人啊!/你是不是逃亡?/不,那末為什么慌慌張張?/哦,假如你事情不忙,/就留宿一宵吧,/我呀,我害了想思:/——那別后的故鄉(xiāng)。”④羅烽:《憶故鄉(xiāng)》,《現(xiàn)實(shí)文學(xué)》,1936年8月1日,第1卷第2期,第245頁(yè)。施誼在《今年是收復(fù)失地年》中為“一二八”五周年紀(jì)念日“獻(xiàn)歌”道:“今年,是收復(fù)失地年!/是中華的子女,快結(jié)成民族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是中華的子女,快結(jié)成民族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⑤施誼:《今年是收復(fù)失地年——一九三七年‘一二八’五周年日獻(xiàn)歌》,《光明》,1937年1月25日,第2卷第4號(hào),第1025頁(yè)。詩(shī)人熱盼國(guó)家能夠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抗日,收復(fù)失地。在左翼作家的筆下,“失地”尤其是“故鄉(xiāng)”總會(huì)激起他們無(wú)盡的哀愁和濃濃的愛意,這“愁”與“愛”催促著他們寫下了那些既情感張揚(yáng)又通俗易懂的詩(shī)句。
六、死亡暗影下的生命感悟
在戰(zhàn)火紛飛的時(shí)代里,左翼作家的生命體驗(yàn)必然會(huì)涉及到“死亡”問題,而他們也曾或明或暗地表達(dá)過對(duì)于“死”的感悟。事實(shí)上,左翼作家筆下涉及到的死亡情景、描寫或暗示實(shí)在太多了,幾乎所有關(guān)涉工農(nóng)武裝起義、義勇軍抗日、愛國(guó)青年示威游行、國(guó)共內(nèi)戰(zhàn)題材的作品都會(huì)寫到“死亡”現(xiàn)象,反過來這又進(jìn)一步刺激左翼文藝界更加熱衷于抒寫“死亡”題材。也正是在特定時(shí)代、歷史和政治背景下,1936-1937年間涌現(xiàn)出了一批題目帶有“死”字的作品。
毫不夸張地說,左翼作家對(duì)“死亡”的描寫和抒寫肯定是中國(guó)現(xiàn)代作家中最多的,這與他們所面臨的死亡威脅最多直接相關(guān),也與抗戰(zhàn)烽火中“死亡”已成為一種司空見慣的現(xiàn)象有關(guān)。章泯的《死亡線上》寫一戶北方農(nóng)民家庭在自家田地被日寇巧取豪奪之后很快就陷入饑餓的邊緣和死亡的陰影中,老農(nóng)夫希望兒子大虎出去謀生活貼補(bǔ)家用,大虎對(duì)此表示反對(duì),他認(rèn)為只有參加義勇軍才有活路。但父親和母親不同意大虎的想法,他們視之為要去當(dāng)“土匪”,為了穩(wěn)住大虎,他們讓大虎與其表妹桂英訂親,大虎的姨媽也將全部家當(dāng)——桂英父親死后留下來的12塊錢拿出來,準(zhǔn)備做一點(diǎn)兒小生意,正當(dāng)他們沉浸在開雜貨店后就有了生路的美夢(mèng)時(shí),兩個(gè)走狗帶著一個(gè)日本人來抓壯丁,他們不但將錢財(cái)搜刮一空,還將桂英也擄走了。劇本揭示了不反抗日寇只有被侮辱和死路一條的道理。⑥章泯:《死亡線》,《光明》,1936年11月25日,第1卷第12號(hào),第784-783頁(yè)。姚雪垠的小說《生死路》寫縣長(zhǎng)不怕日本兵卻怕“共權(quán)黨”,因此他要把家眷和財(cái)物送走,結(jié)果他的汽車被“土匪”老染匠在大山口劫走,為了彌補(bǔ)損失,這個(gè)土皇帝給山里百姓增加了“賠償捐”,還逼著老百姓拆掉慶祥寺為日寇修碉堡,而催逼得極為緊急的苛捐和“碉堡費(fèi)”終于迫使老百姓走上了武裝暴動(dòng)的“生死路”。⑦姚雪垠:《生死路》,《光明》,1937年6月10日,第3卷第1號(hào),第7-13頁(yè)。艾群的《半個(gè)老吳的死》寫排長(zhǎng)老吳在湖南打內(nèi)戰(zhàn),已經(jīng)25歲了還沒有娶妻,打仗期間部隊(duì)停留在一個(gè)小村莊里,長(zhǎng)官和士兵們都借機(jī)去玩弄“雌頭”。他因?yàn)榘滋焓芰笋T老二小老婆的勾引,晚上熬不住便趁著酒勁爬窗而入準(zhǔn)備去滿足自己的性欲,可待他撲上床才發(fā)現(xiàn)連長(zhǎng)已捷足先登,隨后他就因?yàn)椤巴〝秤袚?jù)”被長(zhǎng)官槍斃了。小說揭露了國(guó)民黨軍隊(duì)軍紀(jì)廢弛的內(nèi)幕,也暗諷了國(guó)民黨熱衷于打內(nèi)戰(zhàn)的惡行。①艾群:《半個(gè)老吳的死》,《中流》,1937年1月15日,第1卷第9期,第521-524頁(yè)。白朗的《生與死》寫老伯母一開始不理解兒子為什么去當(dāng)“土匪”,直到兒媳被日本鬼子強(qiáng)奸后自殺和知悉兒子在珠河抗日戰(zhàn)場(chǎng)上陣亡之后,她才理解了兒子的選擇,于是她借助監(jiān)獄換監(jiān)的機(jī)會(huì)和利用自己作為看守的便利條件放走了八個(gè)女政治犯,雖然她被日寇處死,但她死得其所。②白朗:《生與死》,《中流》,1937年2月20日,第1卷第11期,第611-619頁(yè)。蘆焚的散文《關(guān)于死》寫自己因病臥床閱讀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而想到了“死”的問題,進(jìn)而探究了中俄兩國(guó)人民對(duì)待“死亡”的態(tài)度的同與異。③蘆焚:《關(guān)于死》,《中流》,1937年4月5日,第2卷第2期,第95-98頁(yè)。唐風(fēng)的小說《丁少白的死》寫幽居在租界中的貪官丁少白搜刮了很多錢財(cái)放在所謂日本友人吉二郎的手里,此后他被人舉報(bào)“勾結(jié)╳匪圖謀反動(dòng)”,隨之即被槍斃,而他的錢財(cái)也隨著吉二郎返歸家鄉(xiāng)不翼而飛,至于到底是誰(shuí)誣陷了丁少白,敘述者暗示正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吉二郎,因?yàn)檫@是他施行的一個(gè)非常巧妙的謀財(cái)害命之計(jì)。作者的愛憎不言而喻,既表示這是丁少白們應(yīng)有的下場(chǎng),又嘲諷了那些將日本賊寇當(dāng)“友邦”者的愚笨。④唐風(fēng):《丁少白的死》,《中流》,1937年7月20日,第2卷第9期,第475-478頁(yè)。李雷在《丁令威之死》一詩(shī)中,借一只白鶴的視角,展現(xiàn)了日寇在東北奸掠燒殺的兇殘行徑,而它也被日寇槍殺,死在了它心愛的太子河邊和一群與惡霸“爭(zhēng)生命的人們”的眼中。⑤李雷:《丁令威之死》,《中流》,1937年8月5日,第2卷第10期,第557-558頁(yè)。與“五四”作者將“怕死”視為生命中“滋苦之因”⑥廬隱:《麗石的日記》,戴錦華編選:《廬隱代表作》,北京:華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4頁(yè)。的感受不同,左翼作家更喜歡通過作品傳達(dá)“寧愿站著死,不愿跪著生”的生命觀,這使得他們?cè)诿媾R死亡問題時(shí),似乎根本沒有可困惑之處。
相比于戰(zhàn)死、被殺等非正常死亡而言,1935-1936年間巴比賽、高爾基、魯迅等文豪的相繼辭世,更容易引發(fā)左翼文藝界的感傷情緒,令他們產(chǎn)生“不能急切排遣的虛空的感覺”和“不愿意旁人知道的凄涼的激動(dòng)”,⑦立波:《一個(gè)巨人的死》,《光明》,1936年6月25日,第1卷第2號(hào),第124頁(yè)。也令進(jìn)步文藝界興起了頻繁的對(duì)已逝作家——普希金、劉復(fù)、徐志摩、劉夢(mèng)葦、劉大白、朱湘、白采、朱大枬、歌德、赫曼、竇綠苔、雨果、海涅、彼得斐、石川啄木、小林多喜二、尤金·奧尼爾、狄更斯、契訶夫等的紀(jì)念活動(dòng)。立波在紀(jì)念散文《一個(gè)巨人的死》中歌頌了高爾基摯愛生命和一生戰(zhàn)斗的精神,贊美了其能夠把“慈祥的愛和火焰般的憎惡”融合在一起的偉大文學(xué)成就,并稱其為“生活的無(wú)畏的巨人”。⑧同上,第125-128頁(yè)。任鈞在《獻(xiàn)給偉大的死者》一詩(shī)中哀嘆道:“我們剛剛沒有了巴比賽,/此刻又沒有了你,高爾基!/上下古今有那一種損失/能夠跟我們的相比?!……”⑨任鈞:《獻(xiàn)給偉大的死者》,《光明》,1936年7月10日,第1卷第3號(hào),第212頁(yè)。許幸之在《莫斯科的喪鐘》一詩(shī)中歌贊高爾基是“俄羅斯的雄大的巨鷹”“刻苦的俄羅斯民族底象征”“暴風(fēng)雨中的海燕”“黑冰洋里的白浪”“洪荒時(shí)代的太陽(yáng)”和“俄羅斯的史詩(shī)”,稱他發(fā)揚(yáng)了“俄羅斯的精神”,認(rèn)為他更是“替大眾烘糕餅的工人”“種植自由花果的園丁”“為勞苦階級(jí)勤勞的苦力”“給蘇聯(lián)人民守夜的衛(wèi)兵”“制造新文化的鞋匠”和“人類受難者的父親”。⑩許幸之:《莫斯科的喪鐘——追念偉大的死者》,《光明》,1937年6月25日,第3卷第2號(hào),第109-111頁(yè)。至于紀(jì)念魯迅的文章更是難以計(jì)數(shù),比如1936年11月1日和1936 年12月1日分別出版的《文學(xué)》第七卷第五號(hào)和第六號(hào)上都刊載了《魯迅先生紀(jì)念特輯》;1936年11月5日出版的《中流》第一卷第五期是《哀悼魯迅先生專號(hào)》,隨后的兩期《中流》也刊發(fā)了諸多紀(jì)念魯迅的文章;1936年11月10出版的《雜文》(《質(zhì)文》第二卷第二期)刊載了《追悼魯迅先生》特輯;1936年11月15日出版的《作家》雜志(第二卷第二號(hào))刊載了《哀悼魯迅先生特輯》;1936年11月16日出版的《譯文》(第二卷第三期)上刊載了“哀悼魯迅先生特輯”;1936年12月1日出版的《小說家》第二期刊載了《哀悼魯迅先生特輯》,而其前一期則是《抗敵專號(hào)》等等。這既是進(jìn)步思想文藝界一次大規(guī)模紀(jì)念魯迅的活動(dòng),也是一次對(duì)“魯迅之死”乃至“死亡”問題本身的嚴(yán)肅探討。當(dāng)左翼文藝界將魯迅視為“民族魂”時(shí),他們其實(shí)已經(jīng)向世人曉諭了“魯迅之死”乃至死亡本身的生命意義和價(jià)值所在。
左翼文學(xué)對(duì)于死亡現(xiàn)象的淡視或曰對(duì)于獻(xiàn)身精神的鼓勵(lì),是其在后世備受苛責(zé)的一個(gè)原因。左翼文學(xué)中的確存在不珍惜生命的傾向,甚至?xí)霈F(xiàn)教唆青年“以血的洪流淹死一個(gè)敵人,以同胞的尸體填滿一個(gè)缺陷”①魯迅:《空談》,《魯迅全集》(第3卷),第281頁(yè)。的錯(cuò)誤導(dǎo)向,但左翼作家的本意并不在此,他們是希望以個(gè)體的死來?yè)Q群體的生,他們更多的是把“怎樣去死”作為一種精神選擇來加以抒寫或敘述。在思考“死亡”問題的左翼作家中,魯迅無(wú)疑是最深刻的,他的雜感《死》不僅梳理了自己生前的不舍和不忍,還向世人預(yù)告了他死后的情狀和態(tài)度。魯迅對(duì)于生的執(zhí)著,使他對(duì)于死并不怎么感到“黑暗”和“虛空”。在這一點(diǎn)上,左翼作家是大致相通的,他們更多的是將“有意義的死”視為一種精神的延續(xù)和人生的圓滿,而不是一種生命的終結(jié)和肉體的痛苦。可以說,正是在對(duì)“生與死”的選擇和體悟中,他們認(rèn)識(shí)到個(gè)體生命的價(jià)值在于追求人間的自由、公平、正義和真理。在某種意義上,左翼知識(shí)分子是不幸的,因?yàn)樗麄冓s上了一個(gè)有著無(wú)邊黑暗和紛飛戰(zhàn)火的亂世;而他們又是幸運(yùn)的,因?yàn)樗麄冓s上了一個(gè)可以青史留名的革命時(shí)期,在革命斗爭(zhēng)和抗日救亡運(yùn)動(dòng)中,他們?yōu)樽约旱那啻汉托撵`留下了獨(dú)特的印跡,也獲得了其他知識(shí)分子難以體知到的生死感悟。
【責(zé)任編輯鄭慧霞】
作者簡(jiǎn)介:陳紅旗,廣東嘉應(yīng)學(xué)院文學(xué)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yàn)橹袊?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與文化研究。
*基金項(xiàng)目:本文為國(guó)家社會(huì)科學(xué)基金青年項(xiàng)目“中國(guó)左翼文學(xué)研究”(10CZW058)、教育部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青年項(xiàng)目“中國(guó)左翼文學(xué)的發(fā)難與演進(jìn)(1927-1937)”(09YJC751035)、廣東省高等學(xué)校學(xué)科與專業(yè)建設(shè)專項(xiàng)資金科研類項(xiàng)目“世界性的‘紅色三十年代’與中國(guó)左翼文學(xué)的嬗變”(2013WYXM0106)和廣東省高等學(xué)校人才引進(jìn)專項(xiàng)資金項(xiàng)目“中國(guó)左翼文學(xué)的演進(jìn)與嬗變(1927-1937)”(粵財(cái)教〔2013〕246號(hào))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