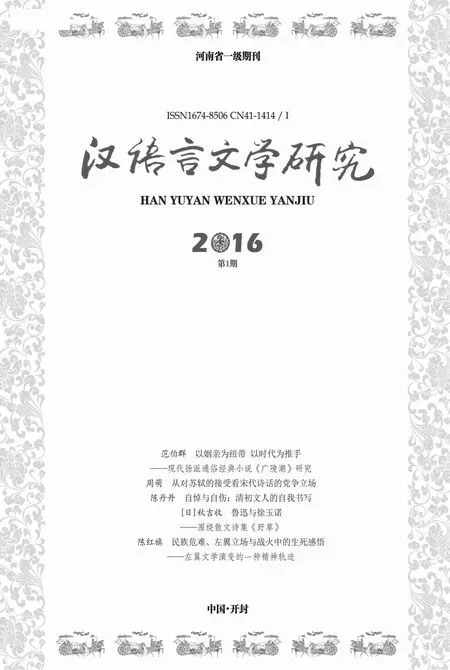論民初文學報刊的獨特風貌*——以《民權報》《小說叢報》為例
侯運華
?
論民初文學報刊的獨特風貌*——以《民權報》《小說叢報》為例
侯運華
摘要:民初報刊生成于社會轉型時代,具有新舊雜陳的特征:一方面表現為駢體小說創作的繁榮,既承繼駢體擅長抒情、烘托氛圍的傳統,亦對駢體表現范疇進行拓展,增大其功能;同時,改良駢體句法,使其適應時代變遷和表現對象的變化。一方面發表諸多反映社會生活的白話小說,描繪具有時代先鋒色彩的人物形象,與現實建構密切的關系。因此,《民權報》與《小說叢報》凸顯出文學性、趣味性、娛樂性、商業性等眾多特性雜糅一體的特點。這種特征的凸顯,不應僅僅作進步、落后的價值判斷,亦不宜武斷其道德得失,而應闡釋其標志文學轉型的獨特意義與重視讀者的借鑒價值及對鴛鴦蝴蝶派等小說流派形成的影響。
關鍵詞:《民權報》;《小說叢報》;駢體小說;白話小說;獨特風貌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課題“期刊史料與20世紀文學史”(11&ZD110)的階段性成果
民初是中國報刊發展的黃金時代,在晚清培育的傳媒基礎上,民初報紙、期刊更加繁榮。一方面,相比晚清報刊而言,民初報刊與政治關系更為密切,不少報刊就是黨派創辦、宣傳其政治主張的陣地;另一方面,為了吸引讀者對報刊的興趣,擴大發行量,許多報刊積極創辦副刊、連載小說以增加刊物的趣味性,因此成就了民初小說家,也醞釀了“鴛鴦蝴蝶派”等小說流派。為了探究民初報刊的真貌,本文擬以《民權報》《小說叢報》為例,探究民初報刊對小說創作、文本內蘊以及小說流派的影響。
一
《民權報》于民國元年(1912)3月1日創刊,周浩為發行人,戴季陶、何海鳴等任主編,自稱“系自由黨全體同人組成”,和同盟會——國民黨各報的觀點接近,公開揭露袁世凱的假共和、真帝制的丑惡面目。該報與《中華民報》《民國新聞》二報都是同一時期出版發行,并以言論激烈著名,因為報頭橫立,在報界有“橫三民”之稱。該報日出對開三大張,副刊占一整版,不標刊名,由蔣箸超、吳雙熱等擔任主編,除發表一些小品文字外,還刊有大量的長篇連載小說,其中著名的有徐枕亞的《玉梨魂》、吳雙熱的《孽冤鏡》、《蘭娘哀史》,李定夷的《霄玉怨》、《紅粉劫》等。該報于民國二年(1913)第二次反袁運動失敗后被袁世凱政府下令禁售,被迫停刊。①參閱賈樹枚等:《上海新聞志》第一編報紙、第二章民國時期報紙(1912-1949),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頁。
《民權報》副刊連載的小說主要是被稱為“哀情小說”的長篇駢體小說,代表作品即是上述《玉梨魂》等。從文學史的視角觀察之,可以發現其具有三方面的價值:其一是開啟了“鴛鴦蝴蝶派”文學;其二是開創了長篇駢體小說創作熱潮;其三是蘊含著現代意蘊。
“鴛鴦蝴蝶派”雖然有著不同的解釋,但其基本內涵是指20世紀初形成于上海的一個文學流派。學界公認徐枕亞的《玉梨魂》是“鴛鴦蝴蝶派”的開山之作。所謂“五虎將”與“四大說部”:前者為徐枕亞、包天笑、周瘦鵑、李涵秋、張恨水;后者為《玉梨魂》《廣陵潮》《江湖奇俠傳》《啼笑姻緣》。其所開啟的以才子佳人為人物架構、融傳統道德意識與現代文化觀念于一體的小說類型,也成為后世“鴛鴦蝴蝶派”作家、甚至所有言情小說家借鑒的范式。因此,應該承認“哀情小說”對“鴛鴦蝴蝶派”的形成是具有決定性影響的。
以《玉梨魂》《孽冤鏡》和《霣玉怨》為代表的“哀情小說”,具有駢體韻文與散體古文相結合的文體特點、切合時代思潮的情感內蘊和借鑒中外小說技法的藝術特征。其存在,不僅成為當時很多作家摹寫的對象,而且拓展了中國小說的表現空間,使駢體長篇小說成為中國小說的一種獨特形式,是民初文壇不容忽視的文學現象。有學者評論:“近代駢體小說熱潮的出現,從某種程度來說,這是近代駢文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特征;駢體小說的盛行其實也是對清末不徹底的小說界革命的某種回應;民初文人以駢文形式創作小說,追求小說自身的審美與趣味,使駢體小說的創作走上了充分發掘人性、表現人生的‘為文學’之路。”①謝飄云:《近代駢文創作特征論》,《中國韻文學刊》2014年第2期。此論點是符合民初小說的創作特征的。
若是從內蘊方面觀察之,則可以發現“哀情小說”蘊含著相當鮮明的現代意蘊:一方面表現為對時代風貌的概括描摹。如《玉梨魂》敘述何夢霞帶領學生到鵝湖果育學校參觀時,彼此見面行握手禮以及對學校、學生風貌的描寫,呈現出與舊學校截然不同的特點。《霣玉怨》第三回展現了當時女校開運動會的場景,也是中國傳統小說中不可能出現的景象。近代思潮傳播的主要空間之一是學校,傳播的主要對象為學生,因此,哀情小說集中描寫學校出現的新事物、新禮儀等,便具有為時代寫真的價值。不僅如此,有的文本甚至刻畫了當時最激進的人物,如《孽冤鏡》即正面描寫了陳毅庵、陳廬俠、武立三等革命黨人及其革命活動,更令人難忘。一方面表現為西方理念的引入。如《玉梨魂》中第十一章筠倩所謂:“今者歐風鼓蕩,煽遍亞東,新學界中人,無不以結婚自由,為人生第一吃緊事。”《孽冤鏡》第三章和第五章、《霣玉怨》第一回均有相似的表述。《玉梨魂》第二十二章敘述筠倩彈風琴唱歌向往“自由之樂”,卻“一身之事無主權”,顯然處于追求自由、堅守主權與服從父命、家族責任的矛盾之中;第二十九章其日記曰:“自由,自由,余所崇拜之自由!西人恒言:‘不自由,毋寧死。’余即此言之實行家也。”凸顯出對自由理念的認同,并引用“不自由,毋寧死”來表達必死的信念。《雪鴻淚史》中夢霞感慨自己命運時,也認為“上帝不仁”。這些體現西方文化基本理念的詞語,連同《玉梨魂》第一章出現的“博愛主義”等詞,反映出民國初期青年人思想的轉變,他們已嘗試著用這些語言表達自我的感情,用西方文化的理念分析事物。或如何夢霞用西方心理學知識解釋噩夢(第二十章),或如王可青愿死后用顯微鏡透視其眼膜,以表達至死不忘環娘之情(第十五章)。甚至主人公的相愛,也因為對方對西方文化有深刻的理解——《霣玉怨》中劉綺齋正是郊游時在李公祠聽到史霞卿對“不自由,毋寧死”的獨到見解才愛上她的。這些內蘊,對后世言情小說不無影響。
二
《民權報》停刊后,聚集在《民權報》副刊的徐枕亞、吳雙熱、李定夷、蔣箸超等人并未放棄文學事業,而是開始籌劃《小說叢報》。該刊于1914年5月出版,月刊,12開本。至1916年7月為22冊,周年紀念時增刊1冊。從13期開本縮小,出版12冊。后又以16開本出版9冊,至1919年8月停刊。共44冊。主編為徐枕亞、吳雙熱。據筆者統計,《小說叢報》共刊載小說427篇,其中文言小說403篇,占99.944%;白話小說24篇,占0.056%。應該說《小說叢報》是傳統文學占據絕對優勢的刊物。
從其刊載小說的體式上看,有長篇小說、短篇小說、筆記小說等;若按照語言分類,則有文言小說、白話小說等;若依照內容分,則有哀情小說、社會小說、家庭小說、技擊小說、歷史小說、俠義小說、滑稽小說、偵探小說等。如果考察作品的來源,則有創作,有翻譯,亦有譯述、仿寫等。無論是分類的隨意,還是文本來源的不規范,均表現出中國文學轉型期的過渡色彩。
從刊物設置欄目看,早期有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文苑、譯叢、諧林、筆記、傳奇、彈詞、新劇、余興等。刊物欄目的新舊雜陳、中外俱有,恰恰凸顯出民初文壇多元化的色彩。至第三年,欄目設置更見特色,分別以《小說海》《翰墨林》《海客談》《記事珠》《香艷集》《蓮花舌》《歌舞臺》《碎錦坊》等命名。宛如招牌式的三個字,古色古香的意蘊,加上封面的美人圖,無不凸顯出《小說叢報》典雅自守的審美追求。同時,還應該意識到:該刊欄目設置,在凸顯文學性的同時,亦凸顯娛樂性、消遣性。其“諧林”的詼諧幽默、“余興”的休閑品質、“傳奇”與“筆記”的獵奇特質、“譯叢”和“新劇”的與時俱進等,均表明《小說叢報》從創刊時便注意內容的多元性、照顧市民讀者和學生讀者的多重需求。調整欄目后,雖然名目更換,內蘊則無大的變化,增加的《香艷集》《歌舞臺》等依然注重娛樂性。這些特征的存在與凸顯,使《小說叢報》成為早期“鴛鴦蝴蝶派”的代表刊物之一,為該派的形成做出了獨特貢獻。
《小說叢報》刊載的文言長篇小說共12部,分別是《雪鴻淚史》(1914-1915年第1—18期,除第13期缺,共17期載完)、《琵琶淚》(1914年第6、7、9、11期)、《棒打鴛鴦錄》(1915年第13、14、16、18、19、20、21、22期)、《情天幻影》(1915年第17—21期)、《斷腸花》(1916年第3卷第1—5期)、《閨語》(1916年第3卷第1—5期)、《情劫》(譯文,未署名,1916年第3卷第2—5期)、《桃李因緣》(1917年第3卷第7、9、10期)、《遁形記》(1917年第3卷第8、9、10期)、《古硯記》和《黠賊》(1917年第4卷第2—5期)、《香國春秋》(1918年第4卷第7、8、9期)。雖然總體數量略高于白話長篇小說,但真正成就獨特的作品卻少,只有《雪鴻淚史》和《玉梨魂》產生了較大影響。最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其刊載的駢體小說,無論是傳承駢體韻文的雅緒,還是擴展駢體文的敘事、描述功能等,均具有文學史價值。
駢文興起于漢魏,成熟于南北朝時期。唐宋間雖受古文運動的影響,仍然被文人喜愛,創作出不少佳作;明清時期,因與八股文結緣——八股文中的前中后束四股每股由兩段(又稱兩扇或兩股)互相對偶的文字組成,合起來八小股組成四大股,于是俗稱八股文或八比文;比者,排比也。其用法與駢文相似,故學八股者必學駢文。晚清時,學者對其進行了充分的理論研究,出現諸多駢文理論著作,如劉麟生的《中國駢文史》、錢基博的《駢文通義》、瞿兌之的《駢文概論》、孫德謙的《六朝麗指》等。理論方面的研究為民初作家認知駢文的特點奠定了基礎,其多用對偶形成的對稱均衡的美感、多用典具備的含蓄雅馴的古韻以及講究平仄造成的閱讀節奏等,均使其成為民初作家爭相使用的文體。正如有學者所言:“當時大量駢文小說的出現,應是整體文學風氣使然。當時文人嘗試以流行文體寫小說,應該可以理解。……民初的駢文小說更與清末文壇風氣與流行文體有密切的關系。”①趙孝萱:《“鴛鴦蝴蝶派”新論》,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頁。考察《小說叢報》的駢體小說,一方面應該注意具有重大影響的《雪鴻淚史》,一方面不能忽視眾多短篇駢體小說。在全部文言長篇小說中,《雪鴻淚史》以散體為主,時時穿插駢文,形成具備敘事和抒情特質的新文體。如第一章敘述幾年間家庭變故后慨嘆:“人比春煙,事如春夢。只此萬戶春聲,依舊洋洋盈耳;昔日天倫樂事,節節思量,皆斷腸材料矣。”②原刊沒有標點符號,此處為引者所加。后文所有期刊引文同,不一一注明。以意象引入,以虛詞(矣)入句,既增加行文的變化,亦方便議論世情。即便是寫景,徐枕亞也別具一格:“時或扶病花前,聽鶯窗下,青春大好,白發無情,輒夫對景傷懷,臨風雪涕。”景為襯托,感慨寄寓其中。第二章敘述與石癡分別后,“余”返校途中所思所想:“花明驛路,不勝去國之思;草長階除,詎免索居之感?迢迢千里,可與相共者,惟有江上清風、窗前明月耳!”則是以典型的駢句抒發孤獨、飄零之情。小說敘述白梨影丈夫死亡、撫孤獨居的生活:“偕老百年,遂成夢幻;遺孤六尺,又復累人。……秋月春風,如意事消磨八九;事老撫幼,未亡人生活萬千。”隨后感嘆自我處境:“余也萍蹤飄蕩,身為入幕之賓;花事闌珊,魂斷墜樓之侶。絳盤雙蠟,尚知替客長啼;春水一池,漫說干卿底事。蒼昊無情,遍布傷心之境;青年多難,孰非失意之人?不知我者謂我輕薄,知我者謂我狂癡。杳杳天閽,真欲訴而無從矣!”飄零他鄉、知音難覓的感觸、傷心失意、不為人知的情懷,均通過駢句迸發出來。其他如第三章何夢霞致白梨影的信,第十四章何母與梨影的來往書信等,也是典型的駢體文。于敘事、致意之際,亦承載著通達情意、表白衷曲的內蘊。研讀這些亞文本和穿插其中的駢句,既可發現其句式的靈活——有典型的四六句寫景,更多的不再是單純的四六句,而是根據表達的需求組合句式。也應該看到其利用書信抒情的妙處——符合通信者的心態與修養,解決了小說敘述中過多揉進駢句的弊端。作為民初影響巨大的小說《雪鴻淚史》的這些特點,無不對其他創作者具有示范作用。
統計該刊駢體特征明顯的短篇小說,共24篇,另有駢體文8篇。這些文本中,真正嚴格運用四六文進行創作的極少,如人則《擬燕山外史》(1916年第19期)刻意模仿《燕山外史》,但寫得很短,顯然難以繼續了。絕大部分短篇駢體小說在兩個方面凸顯出價值:一是拓展了駢體的表現范疇。駢體擅長寫景而不便說理,但是,這批小說使其既能夠描繪場景、環境,亦能夠抒發情感,還能通過議論闡明道理,甚至刻畫人物心理。如果細加辨析,則發現不同作家在創作小說時對駢句的使用特點不同。鐵冷、圣陶、慕韓、式穉、綺緣、瘦石等作家的小說在描繪環境、烘托氛圍、描寫風景時,多用駢句,呈現出與傳統文學中駢句使用特征相似之處。鐵冷是該刊主要作家,其《血鴛鴦》(1914年第1期)、《憶香別傳》(1914年第2期)、《更無一個是男兒》(與楚聲合著,1915年第10期)等皆言情,或通篇駢句如《血鴛鴦》,尤其擅長描繪環境:“龍華道上,車水鞭絲;石室門前,紅愁綠慘。蒼松濤涌,遍地風波;白打灰飛,漫天蛺蝶。楚歌四面,靈均埋沉汩之冤;麥飯一盂,杞婦動崩城之哭。若斷若續,媲孤雁而益哀;不疾不徐,與悲笳而相和。”典型的四六句,將悲劇的環境與氛圍皆渲染出來。或如《憶香別傳》以駢句寫人:“神湛湛如秋水,氣溫溫若春蘭。”其居處則“小筑香巢,雅潔可愛。挹鐘山之翠,映斜照之曛,風景絕佳。”圣陶的《玻璃窗內之畫像》(1914年第2期)為言情小說,《貧女淚》(1914年第3期)為社會小說。前者描寫子晉見玻璃窗內女郎的半身畫像而愛上此人,歷經波折終于見到女孩卻未能結合的故事。描繪女郎情態時多用駢句:“云鬢微松。煙波欲滴。柔荑支口,若有所思。御輕羅衫,雅稱身材;窄不切肌,寬不飄舉。”慕韓的《有情眷屬》(1914年第2期)開頭即以駢句寫景,中間亦不時穿插駢句描寫人物、勾勒環境。式穉的《江采霞傳》(1914年第4期),開始的環境描寫、中間的烘托氛圍、后來描寫人物命運與結尾的感慨皆用駢句,充分體現了駢句的多種功用。綺緣的《月明林下美人來》(1916年第19期)乃幻情小說,文本先以駢句勾畫出清麗的美景,再刻畫二位美人的姿態、美貌,亦給人以恰到好處之感。瘦石的《不堪回首》(1917年第3卷第6期)也是典型的駢體文,通篇使用駢句,無論描寫環境,還是描繪人物,均為駢句。枕亞、秋夢、觀弈、儀鄦等作家則以駢句抒情、議論,且多用典故。枕亞的《駢指案》(1914年第6期)本標為“紀事小說”,卻以駢句抒情:“秋風又起,征人之歸興不增;皓月空圓,思婦之傷心曷極?織罷回文,難覓寄愁之使;聽來秋籟,都成怨別之聲。”其《碎畫》(1915年第7期)敘述名妓凌靈與名士于浪峰的哀情故事,卻以一幅畫為線索,構成典型駢體文。小說以駢句抒情如:“心傾一面,約踐三生。薄命憐卿,甘心作妾;多情負我,放膽藏嬌。柳如是慧眼雖高,錢虞山虛名空誤!”情感之深、用典之妥,均屬上乘。《芙蓉扇》(1915年第8期)描寫凌翔的癡情,多有駢語;《泣顏回》(1915年第9期)則以大段標準的四六句進行抒情、議論;秋夢的《十姊妹》(1914年第6期)以駢語描繪風俗,用典恰當;觀弈的《篋詩記》(1916年第3卷第4期)通篇駢句為主,講述主人公哀情,卻有堆砌典故之嫌;儀鄦的《雙魚佩》(1915年第4期)也是駢句為主的小說,卻主要以駢句展開議論,抒發感情。如抒發思念之情曰:“烏乎!山上有山,藁砧何在?游子之蹤不返,閨中之眼欲穿!”再感慨好夢終圓云:“噫嘻!情天不老,好夢終圓。想瑤佩于天臺,重逢劉阮;聽笙歌于緱嶺,得遇王喬。”可見,駢文的表現范疇確實大大拓展了。
二是改良駢體句法、適應時代變遷和表現對象的變化。徐枕亞《碎畫》中的駢句已經改良很大,如描寫凌靈之美:“若以其眉比春山,猶嫌其秀而未神;以其眼比秋水,猶嫌其清而未活;以芙蓉擬其面,得其淡而失其韻;以楊柳擬其腰,有其姿而無其態。”野鶴、冀良、周瘦鵑等人的創作,在改良駢句、適應新時代方面走得更遠。野鶴的《批霞那之禍史》(1917年第4卷第2期)最為特殊,刊物歸類為“社會短篇”,敘述發生在倫敦的一樁欺騙案件。就文體特征講,小說首先采用駢體,中間穿插駢句,實為譯述小說——結尾云:“仆本不諳西文,此篇為萬梅館主昔日告余者。原著何名,著者何人及刊布于某書,都已不復省憶。”值得關注的是,不僅敘事空間轉換為倫敦、理勿普(今譯“利物浦”)等,小說中大量出現英語譯音和新名詞——“批霞那”乃piano(鋼琴)的譯音、“密昔思”乃Miss(小姐)的譯音、“勃朗林”(今譯“勃朗寧”)乃英語Browning的譯音等。另外還有“虛無黨”“政治犯”等西方詞匯。這些元素的出現,對傳統駢體文均形成沖擊。冀良的哀情小說《媚娘恨史》(1918年第4卷第5期)敘述媚娘與筠郎的情感故事,歷經磨難卻相聚甚短,結婚不到一年,筠郎即咳血而亡。此文以駢句為主,駢句運用相當靈活——既融入白話虛詞,亦改變駢句四六句形態,五言、七言均有,如小說開頭即如此:“彤云羃羃,萬白狂飛;疏樹嫩葩,搖曳無力。惟時一角湖山,改變了舊時面目,呈種種黯淡凄慘之色。”也有典型的駢體句式描寫悲情:“昊天不吊,鴛侶分飛。云抱日而不曉,眉恒蹙而生悲。”周瘦鵑的倫理短篇《金縷衣》(1919年第4卷第9期)敘述作家衛硯香創作劇本《繡衣記》給中華大劇場,因“用意過高文字過深”遭拒,其孫女小霞私下修改之,終于演出成功的故事。小說反映海派作家的生存狀態:“雖小說家之名銜較為動聽,實則一高等苦力耳!”討論戲劇語言“懼不通俗”的問題,實際上呼應了新文學倡導的文學語言變革;而開頭所用駢句也發生較大變化:“春光淡沱,萬綠成圍。大地明媚若披錦,草角花鬢,似亦作美人媚態,一一發為妍笑。”既有駢句痕跡,更多散句寫景,乃接近白話的淺近文言,成為“鴛鴦蝴蝶派”成熟期語言的標本。正是駢句的功能拓展,使駢體能夠成為創作小說的主要手段,并蔚然成風,形成流派;也正是對其進行改良,才使得這批小說能夠為民初的讀者所接受,并為文本承載新思潮創造了條件。
三
《小說叢報》共刊載白話小說24部,其中白話長篇小說9部,分別為《潘郎怨》(自第3回開始,1914年第2、4、5、6期)、《小說迷》(1914年第2、3期)、《學時髦》(1914年第3、4、5、6、7期,刊完;1915年第7、8期,未完)、《剩水殘山錄》(1915年第8、9、10期,未完)、《情海風花錄》(1916年第3卷第2、3、4、5、8、9、10、11、12期,刊完)、《燕語》(1916年第3卷第7、9、10、11、12期,刊完)、《商婦琵琶記》(載1917—1918年第4卷第1、2、3、4、5、6期,未完)、《紅亭淚》(1918年第4卷第7、8、9期,未完),《假幣案》(自第9章開始,1914年第2、3、4、5、6期)。總體看來,這些小說一方面是完璧較少,刊完的只有3部,難以體現該刊的白話小說風貌;一方面內容上尚乏新意,語言上尚保留文言向白話轉變的痕跡,如《剩水殘山錄》等。故論述《小說叢報》刊載的白話小說,以15部中短篇小說為主。
白話小說的數量雖然很少,其中仍具有不可忽視的內涵,因為是傳統文學陣營中的白話小說,更能夠凸顯中國文學內部變革的信號,亦能從獨特角度建構新文學發展的圖景。從其表現的內蘊看,這批白話小說以反映社會現實為主,恰恰與《小說叢報》中的文言小說言情為主不同。吳雙熱不僅是民初駢體小說的重要作家,也是白話小說的熱心作者。他喜歡選擇現實生活中的不良現象進行諷刺,以滑稽的筆法描繪世相中丑陋的一面。其《學時髦》敘述出身鄉村的田阿鼠盲目學習城里人的時髦裝扮,穿洋裝、說外語,結果丑態百出,直到其結婚時依舊怪模怪樣,成為笑料。小說借此諷刺食洋不化者,解構了“時髦”和文明結婚等現象,也表現出作者對外來文明的嘲諷態度。其《蟲學校》(1914年第2期)類似童話,講述大眼田雞和長腳螞蟻邀請劉海蟾出資三百金創辦的蟲學校,因為采用新法辦學,很受歡迎,遭一幫私塾先生妒忌。當盤矢蟲和地鱉蟲帶來一群冬烘來挑釁時,被教體操的大腳螞蟻打得落荒而逃。武的不行,再文斗,大眼田雞以國文取勝。這樣,蟲學校大興,成為從幼稚園、初小、高小到中學、大學俱全的大雜燴,所聘教習則是“一知半解的假教育家”。小說一方面讓新學戰勝舊學,認同時代發展趨勢;一方面對新學中魚龍混雜、徒有虛名的本質進行揭露,凸顯出作者對新學有深刻的認知。獨鶴的《小說迷》敘述一個堂吉訶德式的人物“小說迷”脫離現實、癡迷于小說境界之中,結果只能是屢屢碰壁:他學《封神榜》里的人物駕云飛行,卻砸壞了人家的餛飩攤;學武松打虎打瘋狗,反被狗咬;學寶玉初試云雨情,拉住母親的八九歲丫環親熱,被父親打得皮開肉綻;學張生跳墻鄰家、落進糞桶并遭打;學趙云拉嫂救侄,卻導致其死亡;學諸葛亮唱空城計致家被竊等。通過一系列荒誕行為,反諷小說于人的價值,解構了文本開始所云“小說這樣東西是入人最深動人最易的”的觀點。定夷的《潘郎怨》雖非完璧,卻也有對現實的多方面反映:如第六回既有對立憲運動的議論,也有兩種女性觀的辯論——江筠秋認為:“女子能督理家政,不勞男子分心,就算能夠盡職”;吳英仲強調:“現在女學方興,女子的事業正未可限量。西方多女豪杰,安知東方不能產生呢?”第七回筠秋表示喜歡哀情小說中宣傳的婚姻自由理念,英仲則對現實中“一班青年浪子借自由結婚的名義做出許多傷風敗俗的事”感到憤慨,決心與筠秋一起做個榜樣給人看看。綺緣的《戰禍》(1917年第4卷第4期)則從更大的視角否定了戰爭,作者否定文明、否定人類、否定世界,既攻擊第一次世界大戰、也批判國內南北戰爭,雖然其藝術成就平平,其內涵卻具有相當深刻的現實性。
如果說前述小說還是對現實社會的調侃、諷刺,那么,天僨的《清涼》(1916年第3卷第3期)則是直接描寫中國近代社會底層人因為無力納糧而被清糧所人員抓走的情形。本是電話公司工人的何然,因為對方口音問題,誤以為是叫自己,結果被關押起來。在那里,何然看到了非人的環境:接連被折磨死的佃戶和管理者的草菅人命。直到他趁亂打電話給公司,公司來人才將其解救出去。這部小說非常有現代意蘊——人物以電話公司的工人為主,是近代中國最新出現的社會階層;情節方面,先是通過誤會讓何然被抓,然后通過其視角反映出農村地主和收租者對下層百姓的盤剝,最后讓他通過電話自救,很有時代特色。而人物設置的時代色彩不僅僅為這一部小說所獨具。在《小說叢報》刊載的白話言情小說中,很多作品的主人公都轉換了身份,成為極具時代先鋒味兒的人物。如瘦楳的《車中美人》(1917年第3卷第10期)敘述京師大學堂的大學生唐庵僧與青樓俠女秦玉卿的愛情經歷。無論男性的身份,還是女性的自贖其身、勇退強盜等,均具有超越傳統才子佳人小說之處。其《黃金美人》則敘述留日學生沈鐵癡和表妹趙劍貞的愛情故事,男性為留學生,女性則能夠贈五百金鼓勵愛人留學,終使其學有所成,二人也得以成婚。可見,《小說叢報》登載的言情小說人物中,新型知識分子已經成為一種人物類型。而女性性格、受教育程度與愛情結局的描述,也具有民初社會的鮮明特征。
當然,作為以傳統文學為主的作家群,其創作也保留有較為濃郁的傳統色彩。或如雙熱的《大除夕》(1916年第3卷第2期)描述36歲的主人公因為嫖賭害一生,通過其除夕夜的懺悔,凸顯警世主旨。或如一廠的《青樓亦有女貞花》(1917年第3卷第5期)歌頌淪落青樓的孫蕙娘出污泥而不染的品質,其《孝女復仇記》(1917年第3卷第6期)則肯定張彩姐為父復仇的行為。凡此種種,則可視為白話小說中傳統內蘊的遺響。正如在同一時期編輯《小說時報》的包天笑所言:“大約我所持的宗旨,是提倡新政制,保守舊道德”①包天笑:《在商務印書館》,《釧影樓回憶錄》,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版,第389頁。。《小說叢報》的創作者與編輯們也有著相似的思想。唯其如此,才會出現在新的載體(刊物)上使用白話傳播傳統道德理念的現象,這是民初小說刊物的標志性特征。
研究民初報刊《民權報》和《小說叢報》,既能夠幫助我們了解民初報刊的真實樣貌,也可以借此透視民初報刊新舊雜陳的特征:不僅是西方新潮與傳統思想并列其中、翻譯小說與文言短篇雜居刊內,而且凸顯出文學性、趣味性、娛樂性、商業性等諸多特性雜糅一體的特點。這種特征的凸顯,不應僅僅作進步、落后的價值判斷,亦不宜武斷其道德得失,而應該闡釋其標志文學轉型的獨特意義與重視讀者的借鑒價值,以及對“鴛鴦蝴蝶派”等小說流派形成的影響。
【責任編輯鄭慧霞】
作者簡介:侯運華,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