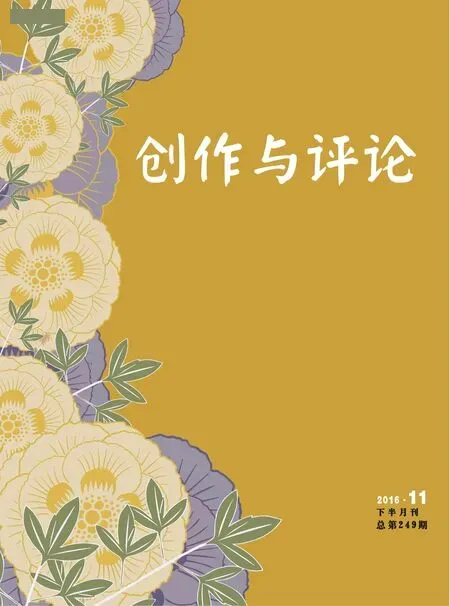戰爭、歷史與記憶
——兼談中國現代文學與現代歷史互動的新動向
○易 彬
戰爭、歷史與記憶
——兼談中國現代文學與現代歷史互動的新動向
○易 彬
主持人語:
易彬在學術界以研究穆旦著稱,他長期潛心于穆旦的史料收集、整理和甄別,在此基礎上相繼完成了數十萬字的《穆旦年譜》和《穆旦評傳》,為穆旦研究的推進和更新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最近他對詩人彭燕郊的研究也是重要的工作,已經有成果陸續問世。易彬的研究建立在扎實的史料基礎之上,但同時又有鮮明的問題意識,他大膽懷疑,小心求證,因此總能推陳出新,別有已見。相信易彬未來會為研究界提供更多更好的成果。
程光煒 楊慶祥

易彬1976年出生,湖南長沙人,文學博士,先后畢業于湖南師范大學(1998)、南京大學(2001)、華東師范大學(2007),現任長沙理工大學文法學院中文系教授,為湖南省高校學科帶頭人培養對象,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新詩、湖湘文學與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三項,發表論文近百篇,有《穆旦評傳》《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談話錄》等著作五種。
抗日戰爭是20世紀中國最為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曾經牽動著國人的每一根神經末梢。抗戰(戰爭)文學及相關敘述也始終是蔚為大觀。但在數十年之后的今天看來,盡管時間在不斷流徙,歷史本身卻并未變得足夠清澈,那些幸存下來的抗戰老兵此刻已進入了生命的暮年,一些當初異常慘烈的圖景也已如同一堆土丘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而那些被有意無意掩蓋或扭曲的史實卻還躺在歷史的角落等待著破解或澄清,打撈歷史,修復或重建歷史記憶,依然是一個急迫而嚴肅的話題。令人欣慰的是,近年來,一些肖像展、口述史、歷史遺跡的田野調查以及歷史圖片的重建天日,昭揭了若干重新進入歷史的路徑;而藉由新的歷史語境的激發而衍生的一些文本,以及口述歷史、田野調查等方法論的運用,也使得中國現代文學與現代歷史的互動這一老話題出現了一些新的動向。
一、“從一張具體的面孔開始”
先從地方媒體《瀟湘晨報》“湖湘地理”欄目六年來所采集的抗戰老兵的肖像說起。
據報道,“湖湘地理”欄目從2009年開始采集抗戰老兵肖像,到2012年9月,共尋訪到了201位老人(當時,湖南地區已發現、確定的抗戰老兵為477人),其中,15位老人在此期間離開了人世。“未曾忘記:湖南抗戰老兵肖像展”當時在長沙月湖公園藝術中心展出——“從一張具體的面孔開始”,展廳懸掛著一張張老兵肖像,入口處有“湖湘地理”欄目組自印的老兵明信片、畫冊《未曾老去:湖南抗戰老兵肖像輯》以及其他一些和湖南抗戰有關的書籍,角落里則播放著崔永元策劃的大型歷史紀錄片《我的抗戰》。據說,這是“全國第一個專業級、大規模的抗戰老兵肖像展”。越三年,更多的老兵被尋到,但黑色方框或者“已故”字樣也更頻密地出現(暫未得到具體數據)。2015年8月,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又在長沙市博物館舉辦了“TA特別紀念”展,除了肖像之外,還有相關文物資料,出版畫冊《無名之輩:湖南抗戰親歷者肖像輯(下)》。從“未曾忘記”到“無名之輩”,從“老兵”到“親歷者”,措辭發生了些許變化,不變的還是“從一張具體的面孔開始”。
名之為“肖像展”,展出的倒基本上不是老兵們的肖像特寫,而是多取中景、全景,相當部分還是大全景或遠景。照片均為黑白色,攝影者顯然著意標出一種頗為凝重的色調。每一張肖像下端均配有幾百字的文字,介紹老兵從軍的歷史與眼下的生活狀態——看起來,攝影師不僅試圖展現出一張張“具體的面孔”,也試圖展現老兵們的晚景。
所展出的湖南抗戰老兵們,經歷各不相同,有的參加過黃埔軍校,有的是被抓壯丁強征入伍的;有的從抗戰一直打到解放戰爭,轉戰大江南北,有的則是短期抗戰,和隊伍失散之后,就回了家。但有一點大致是相同的,那就是在抗戰大軍之中,他們基本上都是普通的下層兵士,是行進大軍中的那么一個小黑點,是隨時可能被子彈擊中而殞命他鄉的無名戰士,是歷史敘事難以觸及的盲點。
抗戰老兵們的現實生活呢?盡管并非完全刻意,肖像展同時也展出了老兵們差強人意的現實生活。從肖像下端的介紹文字以及《瀟湘晨報》“湖湘地理”欄目陸續刊載的記者采訪手記類文字來看,“救助”是一個出現頻率很高的詞。相當一部分幸存下來的抗戰老兵如今都是“湖南老兵之家”(并未獲準注冊的民間組織)這類機構與志愿者的救助對象。有的則長期住在社會福利院。就長沙地區而言,有人根據是否有離休待遇或退休工資,推測有1/5的老兵條件尚好,1/5中等,3/5條件很差。省會長沙尚且如此,湖南其他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何以當年在戰場上奮勇殺敵的勇士們晚景會落得如此之凄涼呢?究其原因,多半還在“國”字上。介紹文字之中,屢屢有這等文字:黃埔軍校第18期的老兵趙定一(生年不詳,現住長沙市第一社會福利院),“曾有段時間不愿承認自己是‘黃埔生’”①。
他們的人生故事呢?《我的抗戰》團隊稱他們所接觸的3500余名抗戰老兵,有90%的人是一生之中第一次接受采訪(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據此推測,“湖湘地理”欄目組所遇到的情形多半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近年來興起的重新認識抗戰歷史的潮流,這些抗戰老兵的故事可能僅僅在他們老家那個狹小的空間里傳布——但也可能連他們子女都知之甚少——也可能他們根本就沒有子女。
由此,不難勾描這些抗戰老兵的人生軌跡:參加抗戰時20歲左右,可能并沒有念過幾天書;抗戰結束回到家鄉,又被內戰的烽火所困;好不容易盼來了全國大解放,參加“國軍”的經歷卻成為了歷史的罪證,很可能會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分子”,遭受政治歧視或牢獄之災;及到風氣終于扭正的新時期之后,又已是花甲之齡,生活可能還很窘迫——此等人生,又有何種機緣可以來講述自己的故事呢?
抗戰結束至今已70年,在歷史長河之中,這自然不過是短暫一瞬,對于幸存下來的抗戰老兵而言,卻可說是已走到了生命的大限之際。能否趕得上那些耄耋老兵的歷史故事,有時候需要一種生命的機緣,比如“湖湘地理”欄目組在岳陽找到曾經參加過三次長沙會戰的老兵方桂賢(1919-2012.6.20)的時候,僅僅趕上了他最后的日子,理發師已經在給他做最后的凈面了,6天后,老人過世。又如家住永州、已經失聰、聽不懂普通話的彭程銀老人(1918-),也已經難以與人交流了,“在老人破碎的記憶中,6年行伍生涯只剩下‘晚上走路,白天打仗’和‘后來有病跟不上隊伍就回來了’……等只言片語”。
盡管“現在已經錯失口述歷史的最佳時機”②,但是,“搶救歷史”,同時讓那些沒有權利講述自己故事的抗戰老兵——讓那些長久沉默的人開口說話,仍是很多媒體人、歷史學者的工作動力所在。
二、“一個老兵的遠征”
歷史如何呈現,記憶如何表達,在不同的人物或語境之中,是有著重要的差異的。絕大多數老兵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但也有知名度很高的,比如曾經參加中國遠征軍赴緬作戰、經歷了緬北生死撤退、現居湖南平江的老兵朱錫純(1924-)。其社會知名度多半得益于他本人對于歷史的講述。
朱錫純寫得一手好字,早年參加戰爭的時候在抗日流動宣傳隊;進入中國遠征軍后,為第一路第5軍新22師政治部少尉干事,主要工作是負責保管每駐一地的風俗、習慣、人口、特產等資料,曾先后兩次撰寫戰地日記,不過均毀于當時的戰火之中。1943年4月傷愈,從印度回到昆明之后,朱錫純沒有重回部隊,而是進入了機關學校學習。之后經歷看起來比較平淡,在昆明娶妻,后來回到老家湖南平江。1989-1992年,開始撰寫回憶錄。200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朱錫純老人獲得了國家頒發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60周年紀念章”。此后,全國多家報刊、電視臺、各大網站相繼報道了他的事跡,如北京電視臺拍攝的專題片《一個老兵的遠征》(最終播出的節目約有47分鐘),《我的抗戰》攝制組拍攝的“野人山”專題等等。2010年9月,朱錫純的回憶錄以《野人山轉戰記:一個遠征軍幸存老兵的戰地日記》之名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印刷字數達21萬之多。
從這等簡要描述不難發現,相比于絕大多數幸存下來的抗戰老兵,金質勛章獲得者朱錫純至少有兩點明顯不同:其一,朱錫純不是一個沉默者,早在輿論風氣尚未開放的年代,他就開始有意識地書寫他的故事。這些年來他接受了不同媒體的采訪,他和他所講述的中國遠征軍故事顯然得到了更為廣泛的傳播。其二,與那些被媒體找到、然后接受采訪的老兵不同的是,朱錫純是主動的講述者,他所講述的也并非片段式的歷史故事,而是非常完整地敘及中國遠征軍第一次赴緬作戰的情形,從遠征軍的由來講起,之后是出發、打仗,再往下是大撤退途中的諸多慘狀,最后是抵達印度。
當然,這部在抗戰結束40多年之后憑借個人記憶而寫成的“野人山轉戰記”稱不上是“日記”,也算不得是嚴格意義上的文獻史料,而更近于紀實文學或者野史。不過,除了《后記》里的必要交代外,作者始終將故事控制在當時的中緬印戰場之上(緬北叢林的撤退經歷占了相當篇幅),其中雖施用了不少小說筆法,讀來頗有戲劇性、情節性,但語調帶有一種悲愴意味,敘述總體上也是平實的,少有后設性的歷史視角,可說是關于中國遠征軍第一次赴緬作戰的形象讀本,有助于讀者窺見當時的一般情形。
近年來,關于中國遠征軍的出版物多有出現,其中如《血祭野人山:一個中國遠征軍老兵的自述》③,帶著并不恰當的獵奇心理或演義語調,若要類比,我倒更愿意提及曾出任滇緬公路工程管理局局長的譚伯英在抗戰勝利前三個月所寫的《修筑滇緬公路紀實》。④滇緬公路的修筑也是抗戰中非常重要的事件,它是在現代機械設備極其有限的條件下進行的,有相當數量的民眾在筑路過程之中因為感染瘧疾而不幸罹難。全書的寫作初意雖在紀實,但書中多有語調低沉的段落,多有游移于工作場景之外的細節,比如寫到勘察公路時,會花較多篇幅去寫寡婦們的墳墓和貞節牌坊背后的故事;而關于“蝴蝶和啼叫的小鳥”的想象,則表達了對于古已有之的愁緒的理解。看得出,即便是抗戰即將勝利——滇緬公路所肩負的偉大使命將成為不可否認的史實,但作者還是將生命事實置于工程事實之上,顯示了對于個體生命和歷史的尊重。⑤對于風俗的記載原本是少尉干事朱錫純的職責使然,但據他本人所稱,《野人山轉戰記》初稿之中原本有不少關于風俗的段落,但后來為了突出抗戰主題而一律刪去了。這種處理方式自然符合歷史表述的慣性,顯示了宏大主題對于個人書寫的規約,對作品的藝術效果卻可能有所損壞。不過,總體上可以說,這本書與《修筑滇緬公路紀實》大致上處于同一層級,均可說是具有較高藝術水準的文字。
總而言之,通過一種回憶的本能以及一種書寫的能力,當年的少尉干事朱錫純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展現了自己的形象,在公眾的抗戰歷史記憶中占據了一個比較獨特的位置,有理由相信,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之內,抗戰敘事之中,朱錫純以及朱錫純所講述的中國遠征軍的故事都會被反復講起。
三、記憶或遺忘(一)
從歷史認知的角度來看,《野人山轉戰記》所蘊涵的記憶或遺忘的話題是尤為醒目的。書中有不少歷史人物,但也有一些人物,雖有名有姓,但在今天看來,已近于無名者,比如一位名叫李國良的戰士,22師政治部上尉,濟南人,時年近30歲。他曾經和朱錫純一道在野人山里艱難穿行,卻沒能幸運地走出去,臨終之前他曾作七絕一首,托朱錫純抄好,并替他領幾個月津貼寄給他在西南聯大讀書的女友。但是,當朱錫純拖著傷病之軀終于抵達印度之后,他所有的衣服、連同那個寫有地址的紙條都被扔進火化坑付之一炬。60多年之后,在《一個老兵的遠征》節目之中,朱錫純老人面對電視鏡頭,仍記得那首七絕,“聯軍履北斷歸途,投筆從戎志未酬。革裹尸還猶自愧,流亡何語謂班侯。”也還在為無法完成戰友遺愿而痛哭不已。
戰士“李國良”就那樣無聲息地死于異國他鄉,死亡的消息大概從未傳遞給那個在西南聯大讀書的女孩——可能也從未傳遞給家鄉的父母,他的故事在朱錫純說出來之前,大概也只能說是一片黑暗——即便是朱錫純說了出來,李國良的父母、他的戀人(又有誰知道他們的名字呢?)多半也已經無法再聽到了……
放大到抗戰歷史的大圖景來看,“戰士李國良”的這般境遇無疑具有某種典型性:在數以千萬計的抗戰大軍之中,他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無名戰士。如果說幸存下來的部分老兵還有機緣來講述戰爭的故事的話,那么,當年那些不幸陣亡的年輕戰士則多半陷入到了某種歷史(敘事)的宿命軌道之中,成為了推動歷史前進的那種強大而無名的力量。
面對時間和歷史無情的遺忘規律,“打撈歷史”也就具有獨特的意義。粗略說來,“打撈歷史”大致可分為兩個層面:一個是它本來就在那里,等待著一個機緣去找到它,如各類文獻資料,章東磐等人主編兩冊“國家記憶:美國國家檔案館收藏中緬印戰場影像”可謂此一方面非常突出的例子。⑥影像從何而來?是當時盟軍照相兵所拍攝的,兩萬多張和抗戰有關的照片存在于美國國家檔案館,厚厚兩冊不過是選取了其中的幾十分之一而已。另一個層面則是諸如田野調查、口述歷史的采集與寫作等。
但仔細辨正,這兩個層面都遺留著不少有待進一步解決的問題:那些已經存在的東西自己并不會跳出來說話,歷史(比如照片)固然是在那里,能否被發現則依然只能等待某種生命機緣。《國家記憶》操弄者章東磐曾感慨:“中國抗日戰爭的影像實在是太少了”,“抗戰史本就極度缺乏來自視覺的佐證”。⑦對于抗戰時期的中國軍人而言,照相決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國家記憶》主編之一、國民革命軍第46軍新編第19師第56團少校營長宴福標之孫宴歡即曾談到,2006年之前,家中沒有一張祖父的照片,就連父親都不知道祖父的樣貌。宴福標抗戰前畢業于黃埔軍校,陣亡于湖南戰場。現在能找到的唯一的照片是在湖南省檔案館的“敵偽人員”專柜,黃埔軍校的畢業照。⑧宴福標這樣出身于黃埔軍校、且身為營長的中級將領尚且如此,那些無名的年輕兵士能否為家人留下一寸照片那也就可想而知了。而美國國家檔案館里的那些堆積如山的照片自從1946年被歸檔之后,絕大部分從來就沒有被打開過。如今,幾百張照片匯集成的兩冊《國家記憶》供人重溫歷史,但這也并非照片本身的選擇,出版資源總是有限的,更多的照片顯然無法被選擇——更多“充滿苦難和光榮的面容”還是只能繼續靜靜地躺在那些檔案袋里,聽憑歷史緩緩流過。
實際上,關于抗戰,除了影像記憶,當事人——特別是那些底層戰士的敘述也是相當匱乏的。抗戰史專家戈叔亞先生曾談到大陸、臺灣、美國、日本等國家(地區)在抗戰歷史書寫上的差異⑨,大致而言,美國、日本都有詳細的戰史和大量的回憶錄(盡管水平良莠不齊),臺灣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或更早時期,組織了對抗戰全史的編撰和對老兵進行口述歷史的采訪和記錄。相比之下,由于政治語境等方面的原因,大陸的相關工作很不完善,較早時期的普遍士兵的個人口述史或回憶錄相當稀見。
國民黨將領的相關回憶文字倒是有不少,但往往容易受到政治語境的牽制。近年來,“原國民黨將領抗日親歷記·正面戰場”系列(分不同的戰場,共10冊)被整理出版,其中有一卷為《遠征印緬抗戰》⑩,作者包括杜聿明、宋希濂、鄭洞國等國民黨高級將領。以杜聿明所撰《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為例,杜聿明曾任中國遠征軍第1路副司令長官兼第5軍軍長,后在淮海戰爭中被俘,成為了新中國的階下囚,直到1959年獲得特赦釋放。《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即是隨后所發表,其中的推諉姿態與辯護語氣,以及對于“友軍”英國人的責難,都可以比較明顯地見出政治語境牽制的痕跡。?
四、記憶或遺忘(二)
進入歷史自然有著不同的方式。
2009年以來,先后熱播的《我的團長我的團》《中國遠征軍》等電視劇充分顯示了歷史演義的本色,也將“中國遠征軍”推向了公眾的視野當中。由知名電視人崔永元策劃、曾在全國數十家電視臺同步上映的大型電視紀錄片《我的抗戰》歷時8年才得以完成,耗資高達1.3億元,采訪3500人,集成影像200萬分鐘,搜集歷史老照片300萬張。兩冊“國家記憶”的主事者章東磐成功利用了美國國家檔案館的影像資源,看起來對于當年的戰爭有著全方位的觸及,足以調動起更為廣泛的歷史記憶。相比之下,由地方媒體所操弄的“未曾忘記:湖南抗戰老兵肖像展”充分彰顯了其地方性,其聲勢沒有那么大,故事和人物肖像的采集僅限于湖南地區,卻也憑借一種獨特的真實感而將人帶入到抗戰的歷史記憶當中。
這里想借助章東磐的工作來談一談歷史記憶的話題。章東磐是軍人的后代,不過如今一般意義上的“抗戰老兵”不同,其父親當年不是“國軍”,而是“共軍”,新中國成立之后,其政治待遇有天壤之別。?概言之,章東磐的工作主要有兩個路徑:一個是在云南從事滇西抗戰的田野調查工作,駕車或步行,重走當年的滇緬路,探尋高黎貢山、松山、功果橋、惠通橋等戰爭遺跡。另一個則是從美國國家檔案館海量復制抗戰時期盟軍照相兵拍下的照片。就其所實際呈現的記憶形態而言,又可分為打撈與修正兩個向度。
如前述,打撈工作在影像記憶的呈現方面成效非常之顯著,已整理出版的數百張照片,按照不同主題進行了分類,第一冊別有意味地從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抽出五個主題句,即“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這大致是以時間為序展開的。第二冊則是以緬甸、印度、“飛虎隊”、民生、墓地、敵人為題,以地域或同類主題進行分類。藉此,關于抗戰的國家記憶得以大面積地恢復——照片中有蔣介石、史迪威、各級將領等知名人物,但更多的是來自前線的無名戰士——無名戰士的群像記憶進入到了公眾的視野當中。章東磐顯然也非常看重這些重見天日的照片的效應:“有了這些畫面和文字相互映襯,這段歷史中將有多少懸疑被澄清呢?”
“打撈”所對應的就是“遺忘”——“每一年諾曼底海岸吹響軍號,當年為自由而戰的軍人得到全世界致敬的時候,我們的怒江邊寧靜如常,只有水牛在巨大彈坑形成的塘子里打滾。”?在實地勘察之后的故事講述之中,章東磐屢屢感慨歷史遺跡的湮沒,很多當年的戰場,別說紀念碑,連簡單的標識說明文字都沒有,比如《石碑》中有這樣的文字:
我們是在昨晚才知道的石碑。這個村子讓我感覺到了猛烈的撞擊,許多年來,我一直留意著幾十年前的那場中日戰爭。由于政治因素,那場戰爭中的大量史實都被如兄弟般比肩浴血的國共雙方商量好了似的有意淡化甚至涂抹掉了,所以發生在石碑的廝殺竟變成了一個全新的故事出現在我眼前,僅僅幾十年,中日雙方投入幾十萬兵力,出動陸海空三軍的那么慘烈的戰爭竟然被隱藏得如此不留痕跡,就像被淹沒在江水下的巨石。?但如何看待記憶錯亂——如何修正記憶,章東磐的做法也不盡相同。《“少尉”葉進財》寫了一位喜歡吹吹牛,將自己“升了官”的老兵,其語氣基本上是一笑而過,著筆更多的還是老兵那凄慘的晚境。但對于那些蓄意造假的“偽書”,即如他為《國家記憶2》所寫的序言《我為什么像狗一樣咬住你們不放》所示,措辭是相當嚴厲的。
章東磐的矛頭所向是一本叫做《軍碑一九四二》的書,序言詳細分析了作者在身份、軍事知識、時間敘述等方面明顯存在著造假的現象,并非“從‘記憶的閘門’里流淌出來的真故事、真歷史,而是用別人的食材佐料拼湊起來”的、“偽得離譜的、漏洞比破漁網還多”的一本書。但其筆力所向,也并非老兵,而是“這本書的策劃者、編輯者、出版者和推薦序言撰寫者”:
到今天,僅存的他們都那么大年紀了,顛沛流離的戰亂,生不如死的后半生,老了,老了,逢慣了噩運的人生突然熬出了頭,有人關注他們了,前來聽講故事的人多,老人們吹點小牛加上記憶偏差是難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對這部偽書面世的無盡憤怒全部是對著這本書的策劃者、編輯者、出版者和推薦序言撰寫者的。如果你們僅僅是一位訪問者、傾聽者、記錄者,我不會挑剔你、責備你。但你傳播了這個信息,就一定要對進入公眾視野的歷史真實性負責任。
本來這些老人是挺到了風燭之年才收獲這么一點點遲到至暮才來的尊重,而你們的無知與名利之欲推著老人一步步縱容自己,走上了收不住腳、回不了頭的說謊之路,直至恥辱纏身。你們親手為這些曾以青春捍衛祖國尊嚴的昨日軍人搭建了晚節的絞刑架。?這篇序言曾以《請〈軍碑一九四二〉的參與者認錯》為題在紙媒和網上多有傳播,應該說,已經具備了相當的輿論效應。也因為對于歷史細節的特別看重,章東磐特別強調“立場、方法與知識”的重要性,這是“對所有的調查及后續工作參與者的要求,包括講述者、記錄者、編輯者、出版者,甚至被邀來寫撐場子前言與站臺推介的權威人物”。他聲稱“大量托名于‘口述史’‘紀實’與‘回憶錄’的書籍”,“能達到‘重新解釋歷史’水平”,“一本也沒有”,達到“把資料的真實性負責任地作好”這個“基本水準”的也都“少之又少”。此話或許有些絕對,但確是道出了相關工作及寫作的困境所在。?
五、中國現代文學與現代歷史互動的新動向
抗戰老兵朱錫純1980年代后期開始寫作、1990年代前期完成的個人回憶錄,差不多20年之后方才出版,這顯然得益于200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以來風氣的轉變——歷史風氣在轉變,落實到中國現代文學與現代歷史的互動這一老話題,也可以發現一些新的動向,那就是歷史、戰爭和民族苦難對于寫作的再激發,以及歷史對于寫作的糾正。
最近一個引起輿論較多關注的例子是在2013年——中國抗戰勝利68周年、中國遠征軍仁安羌大捷71周年、南岳忠烈祠這一中國規模最大的紀念抗日陣亡將士陵園落成70周年,1月,緬甸仁安羌大捷紀念碑落成,之后,仁安羌大捷202位陣亡將士總靈位從緬甸迎回祖國;7月7日,總靈位入歸南岳忠烈祠。此前此后,一批詩歌文本與詩歌活動紛紛出現——7月7日靈位安放儀式的當天,湘詩會、衡陽市作協等機構還在忠烈祠舉行了“祭奠抗戰英烈專場”詩歌朗誦會。新的詩歌文本中,最為厚實的當屬海男2012年下半年完成的、長達31節的《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出緬記》?。在“微詩歌”當道的時代,長詩寫作的難度遠勝于往昔,“中國遠征軍出緬記,已縈繞我心頭太長的時間”——為了這首長詩的寫作,海男在歷史資料查閱、情感醞釀等方面都做了充分準備。其效應也已初步顯現出來,媒體報道中國遠征軍將士總靈位入歸南岳忠烈祠事件時,頻頻引述的就是海男的詩句:“我回到了親愛的祖國,我撤回了它溫熱的腹部”。
關于這首長詩,我將在其他場合另文討論,這里想從詩中的一個細節來簡略談談文學與歷史的互動話題。這個細節是“草鞋”:
傳說中的中國遠征軍士兵們大多數都腳穿草鞋赴緬
是的,我看到了用中國鄉野間的茅草或稻草
編織的草鞋。我知道中國工農紅軍爬雪山過草地時
腳上穿的也是草鞋,因為草鞋是我國家的土地上最旺盛的
野草和稻草的編織體。因為穿上草鞋可以離我們的爹娘更近一些
可以離我們故土的星月更近一些。因為穿上草鞋可以更輕快的
抵達戰場可以縱橫中越過壕溝,可以勇往直前
傳說中的中國遠征軍就這樣穿上草鞋來到了亞洲的主戰場
在那時刻,無論是穿草鞋的、穿膠鞋的穿皮鞋的將士們
臉上都充滿了英勇赴戰的豪情,盡管每個人都知道
赴戰者生死未卜……1940年代曾經從軍、到達過印度的杜運燮曾有一首詩就叫做《草鞋兵》,發表時特別加注釋以說明:“緬甸華僑稱入緬國軍為‘草鞋兵’,以別于英印軍隊的‘皮鞋兵’”。?可以說,“草鞋兵”乃是公眾關于中國遠征軍戰士形象的基本想象,甚至可說是遠征軍士兵的代稱。
章東磐關于“草鞋兵”曾與《1944:松山戰役筆記》?的作者余戈有過筆戰,大致情況是,章東磐根據美國國家檔案館的照片,認為當時遠征軍士兵“不全是”草鞋兵,也有穿膠鞋或繩鞋的。這也可算是歷史細節的核實,對文學想象倒并不會產生多大誤判。但他發現中國駐印軍除了發制式軍鞋外,還會按月發放“草鞋費”,“讓他們可以用這些錢購買自家編草鞋的原料”。何以如此呢?章東磐的推斷值得注意:士兵訓練出汗極多,穿草鞋“解決了防止腳氣病的難題”——“草鞋也許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容易得出結論:中國士兵窮苦到連一雙軍鞋都沒有”。以此來看,“草鞋”固然是國力貧弱的一個基本表征,即如當時中國軍隊在武器裝備等方面全面落后一樣,但其中也還是有著現實層面的認知角度。
若此,“穿上草鞋可以離我們的爹娘更近一些/可以離我們故土的星月更近一些。因為穿上草鞋可以更輕快的/抵達戰場可以縱橫中越過壕溝,可以勇往直前”這樣的詩句,實際上超出了“歷史想象”的范圍,多少有些濫情的傾向——概言之,即以一種當下的情感遮蔽了更為精確的歷史認知。此一問題放大來看,涉及到“歷史想象”的限度問題,即在對歷史進行文學重構的過程中,如何在“歷史”與“情感”之間搭成必要的平衡,這是寫作者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歷史”與“情感”之間的平衡問題,不妨換個角度來看——在很多關于中國遠征軍的敘述場合,如《我的抗戰》《野人山轉戰記》等,都會引述詩人穆旦在1945年抗戰勝利之際所作《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中的詩句,特別是詩歌最末四行:
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
還下著密雨,還吹著細風,
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
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干而滋生。
1942年初,穆旦毅然放棄西南聯大的教席,參加中國遠征軍,任隨軍翻譯,出征緬甸抗日戰場,之后則是與朱錫純一樣,經歷了極其慘烈的緬北大撤退。據此所寫的《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一般讀者或許會被“無言的牙齒”“綠色的毒”一類超常規的表述所迷惑,認為詩中多是夸張、奇異的描繪。但在有著類似經歷的人看來,卻是“如實的哀挽”。?而穆旦在稍早的時候寫下的長詩《隱現》(1943年3月)之中,也有著這樣的句子:
為什么一切發光的領我來到絕頂的黑暗,
坐在山崗上讓我靜靜地哭泣。
以朱錫純老人的《野人山轉戰記》為參照,“坐在山崗上讓我靜靜地哭泣”這樣一行實是全無渲染之處,也絕非故作冷靜之語,而是在目睹太多的死亡之后,內心悲慟景狀的一種直觀呈現。可以設想,坐在山崗上“靜靜地哭泣”的那樣一個形象,其內心所涌動的或許是關于生與死、有限與終極,此案與彼岸一類思緒。也或許,只剩下那樣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到底能不能走出那令人恐怖的叢林?完全可以說,抗戰老兵朱錫純的這部《野人山轉戰記》為這類寫作提供了最為形象的注腳。
穆旦是慘烈戰爭的親身經歷者,其寫作自然有其獨特的時代性與切身感,海男的《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出緬記》以及書寫滇西戰爭的《戰爭安魂曲》一類寫作則彰顯了當代語境的激發作用,這無疑也能引導當下的讀者對于歷史記憶的重構——歷史的面目既已逐步打開,關于戰爭、歷史與記憶的話題無疑有了新的討論空間,但如何進入歷史,如何化解歷史的謎局,如何甄別敘述的真偽,又如何在文學經驗與歷史事實之間搭成必要的平衡等等,顯然也都是值得細致考量的命題。
注釋:
①參見2012年8月28日《瀟湘晨報》“湖湘地理”欄目的相關文字。
②抗戰史家戈叔亞觀點,參見《東方早報》2012年12月26日“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70周年祭·學術”專刊上的相關文字。
③黃三叢:《血祭野人山:一個中國遠征軍老兵的自述》(修訂版),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
④譚伯英等著,戈叔亞譯:《血路》,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⑤易彬:《滇緬公路及其文學想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7年第4期。
⑥章東磐主編:《國家記憶:美國國家檔案館收藏中緬印戰場影像》,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章東磐、宴歡、戈叔亞主編:《國家記憶2:美國國家檔案館收藏中緬印戰場影像》,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⑦章東磐:《在異國尋找歷史的背影》,章東磐主編:《國家記憶:美國國家檔案館收藏中緬印戰場影像》,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頁。
⑧參見章東磐主編的《國家記憶:美國國家檔案館收藏中緬印戰場影像》一書獻辭部分,宴歡執筆的相關文字。
⑨參見《東方早報》2012年12月26日“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70周年祭·學術”專刊上的相關文字。
⑩杜聿明、宋希濂等:《遠征印緬抗戰》,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初版,2010年9月新版。
?該文初刊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所編《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中華書局1960年版。
?嚴格說來,“原國民黨將領抗日親歷記·正面戰場”系列圖書是頗成問題的出版物,所有史料均未標注出處。歷史文獻這般處理顯然會妨礙讀者對于語境的認知。
?身為遠征軍后人的鄧賢即曾坦言:當年他曾因為父母對過往的“緘口不言”,一度認為自己是“有罪的人”的子女而“備感孤獨絕望”。參見《大國之魂》一書的引言部分《歷史的堅果》,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
?章東磐:《在異國尋找歷史的背影》,章東磐主編:《國家記憶:美國國家檔案館收藏中緬印戰場影像》,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頁。
?章東磐:《父親的戰場:中國遠征軍滇西抗戰田野調查筆記》,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頁。
?章東磐:《我為什么像狗一樣咬住你們不放》,章東磐等主編:《國家記憶2:美國國家檔案館收藏中緬印戰場影像》,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3頁。
?近來,有的材料稱不少老兵的回憶如同抗日神劇,六歲就如何如何,又如何如何神勇地打鬼子,這里邊固然有耄耋老人記憶差錯方面的原因,也是口述資料采集者的失職所致,缺乏相關歷史知識,對口述歷史的知識理念也不甚了然。
?海男:《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出緬記》,《詩歌月刊》2013年第1期。
?杜運燮:《詩四十首》,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年版,第1頁。
?該書算得上是文化暢銷書,2009年8月第1版,我手頭上的為2010年10月版,是第5次印刷本。
?唐振湘、易彬:《由穆旦的一封信想起的……》,《新文學史料》2005年第2期。
*本文系2013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的理論建構與實踐形態研究”(項目編號:13CZW084)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長沙理工大學文法學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