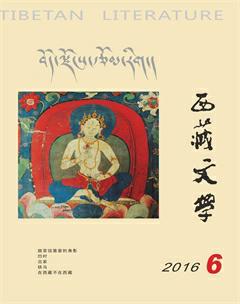凹村
2016-12-17 00:44:26雍措
西藏文學
2016年6期
雍措
烏嘎:阿爺用過的鍋
在凹村,我有一座泥巴房,一條狗,兩條要走的路。
去年秋天,凹村東口子刮來的風,吹斷了村口的百年老樹,大樹斷裂的那一刻,風剛好走到屋頂,掀落了十幾片青瓦。那時的我,坐在灶臺前,左手握著一把枯草,右手拿著火柴,正為點不點燃這把枯草而苦惱。
點燃枯草,只需要我輕輕劃燃火柴,時間很短,一粒玉米落不到地上,一個跳蚤來不及蹦到我身上。可是,看著空空的鐵鍋,我始終沒勇氣點燃這把火。
這口鐵鍋已有百年歷史,阿爺逃荒時,從南邊一個茅草屋里撿到的。當時,這口鍋被幾個大石頭支撐著,里面有蓋住鍋底的水。水黑里泛黃,阿爺把頭伸過去,水面出現一張臉,他嚇了一跳,急忙縮回頭,左右看了看,沒人,才知道這水里的人臉,原來是自己。長頭發,一副馬臉,脖子跟雞脖子一樣細。這張臉不像人,像鬼。鬼,阿爺沒見過,不過,那時的人們,把害怕的東西,都當成鬼。饑荒年代,人長得奇形怪狀,沒個人型,阿爺說,人比鬼可怕。
鍋底的炭灰沒有溫度,拿在手上,冷冷的。阿爺知道,這口鐵鍋是被人遺棄了。他想去摘一根藤子做繩,把鍋背在背上,陪他一路往南走。他邊走邊想,這個丟了鍋的人,一定是尋到了好生活。要知道,一口鐵鍋,在那時,至少可以和家里還有點底的人,兌換幾個水巴子饃饃。
一簇藤子茂盛地生長在荒坡上,阿爺走過去,邊折藤子,邊自言自語地對藤子說著話:“地底有肉吃?還是一路逃荒人的屎尿把你養得白白胖胖?……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