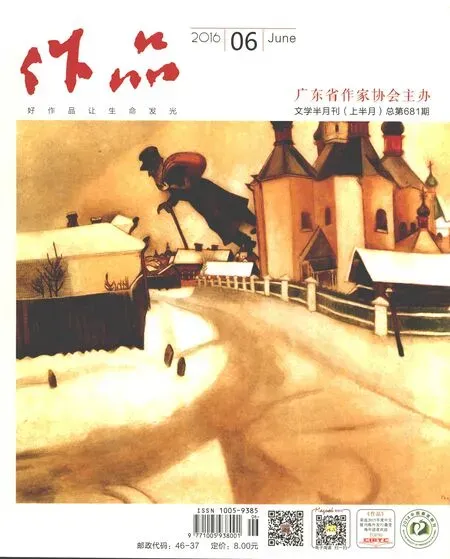對一場戰爭的描述
文/張中民
對一場戰爭的描述
文/張中民
張中民生于七十年代,河南葉縣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河南省文學院簽約作家,近年以小說創作為主,先后在《作品》、 《芙蓉》、《小說界》、 《莽原》、 《山東文學》、 《安徽文學》、《廣州文藝》、 《當代小說》及臺灣、香港等地文學雜志發表長、中、短篇小說,有作品獲獎并被轉載。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比南方更遠》、《賺他一千萬》、 《闖入江湖的魚》、 《傷心的村莊》等。
人不尊重歷史,便會被歷史遺忘。
真相是歷史存在的一種形式。
——題記
一
天剛擦黑,村口橋頭處便熱鬧起來。吃過晚飯的人們擠在那里,邊納涼邊聽一個光頭老者在那里講故事。
這個在人群中講故事的便是阿福。
聽阿福講故事是一種享受。阿福講的故事與眾不同,他不講妖魔鬼怪、才子佳人,甚至也不講現實生活中的軼聞趣事,單講他過去的經歷。
阿福說他的經歷是一部講說不盡的人生大書——
阿福年輕時當過兵,曾經有過一段不同尋常的軍人生涯,是后來返鄉才回到我們村的。至于阿福當的什么兵不知道。因為他一會兒說自己是“八路”,一會兒說是“國軍”。在他顛來倒去的敘述中,也把我們弄糊涂了。不過他扛過槍打過仗,而且和敵人在戰場上真刀真槍地干,經歷過血與火的洗禮卻是事實。那種慘烈和悲壯用他的話來說是“尸橫遍野”“血流成河”,真正到了驚天地泣鬼神的地步。所以至今回想起來都讓他心有余悸……
說到這里你可能已經明白,阿福的故事帶有一定的自傳性。自傳有什么不好?許多作家都寫過自傳,讀起來同樣讓人唏噓不已,扼腕感嘆。按說自傳性的故事并無多少新奇。如果不進行一番夸張和描述,誰的自傳會那么吸引人?可是阿福卻不,他只撿那些精彩有趣的內容講。講到精彩處,他站起來手舞足蹈地表演,樣子像中了魔。阿福本來下嘴唇較長,一講到這里,他的下嘴唇就會跟著哆嗦起來,看上去像犯了“羊羔瘋”,口吐白沫、四肢抽搐,樣子挺嚇人。不過大家都知道他此時已經完全進入到忘我之中……
老鴰,你別在那里瞎胡噴,你給我說說你那時在哪兒?好像有意和阿福作對,等他剛把故事講到精彩處,坐在橋頭另一端的老常突然沖他暴喝一聲。正在激動中的阿福突然像被兜頭潑了盆冷水,一下子被“凍”在那里。
老常也是村口橋頭上的常客。只要有時間,他就拿把芭蕉扇,坐在橋頭另一端,一邊蹺著二郎腿,一邊忽扇著扇子,瞇起眼在那里假寐,像隔岸觀火的第三者。你千萬不要以為老常對這邊漠不關心,其實他一直豎著耳朵在認真聽這邊的熱鬧。就像故意惡作劇似的,一旦聽到阿福講到精彩處,他就像程咬金似的,拿著板斧跳出來,出其不意地撂上兩句,就把整個火熱的氣氛給攪亂了。老常個頭瘦小。別看他坐在那里不顯山露水,但說出的話常有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因此他和阿福被人稱為一對“冤家對頭”。
老鴰是阿福的外號。我們那里一般稱賣嘴者為“老鴰”,意指窮嘴呱嗒舌,不切實際的胡侃。一聽老常在旁邊敗自己的興,阿福頓了頓,梗起脖子沖老常罵道,你個龜孫,你管老子那時在哪兒?老子在你娘的床上!
我知道你在我娘床上,不過我知道你是在那里找奶吃。老常“嘻嘻”一笑化解了阿福的侮辱,當即反擊,哼,我還不知道你那德性!
阿福看自己的一招制敵沒擊敗老常,只好抬手指著自己左側大腿上的一塊傷疤大聲說,睜開你那瞎眼看看老常,你看看老子的腿是咋傷的?實話告訴你,這就是證據!這就是當年老子打仗時被小日本炮彈打中的……
你別在那里瞎胡扯,誰不知道那是你小時候要飯被狗咬的。難道這也值得炫耀?老常反唇相譏,我看你還是趕快回家找個尿盆浸死算了……
一看對方在實施人身攻擊,阿福急忙展開攻勢進行反撲。于是兩人很快便雞爭鵝斗地拌起嘴來。
二
阿福不是老常對手。不是說他斗不過老常,而是說他缺乏老常的機智,加上他說話不夠利索,所以常常被老常拿住軟肋。而阿福的軟肋就是老常揭穿他的“國軍”身份。這還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阿福做“國軍”時當過共軍俘虜。其實這有什么?誰身上沒有污點?誰臉上都有洗不干凈的時候。比如老常。別看他在拿阿福軟肋時占住上風,但接下來的情況便急轉而下,朝他不利的方向發展。
——老常的老婆長得人高馬大,有幾分姿色。但凡有姿色的女人往往看不起自己猥瑣的男人。而老常的老婆最看不起的便是丈夫的低矮和瘦弱,私下便和鄰村一個五大三粗的男人相好。那年夏天,中午從田里干活回來的老常意外發現老婆的奸情,一下就把那個男人堵在家里。為了報復他,同時也想借此警告老婆,老常故意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不動聲色地跑進廚房,抱起一個冰在水缸里的沙瓤大西瓜當場殺開,執意要“請”男人吃冰鎮西瓜。男人剛和女人辦完事,此時正在恢復元氣,如果不吃顯得不夠人情,可是如果吃下去就會傷到身體……結果在老常堅持下,男人只好吃了半個冰涼西瓜。沒想到落下病根——他的陽物從此再沒有舉起過,終生成了“廢人”…… 對于自己這一杰作,老常很長時間都為之得意洋洋沾沾自喜。哼,老子總算報了那男人給自己戴綠帽子的仇,從此再不用擔心他爬老婆身子。
按說懲治奸夫淫婦本是大快人心之事,然而由于涉及到自己老婆,一般人都不愿公開,老常也是這樣。加上他平時做事嚴密,把此事封得很死,可是不知怎么回事,這個秘密居然被阿福知道了。這成了他和老常爭斗時的殺手锏。每次爭斗拌嘴,只要自己一處于下風,阿福就把這個絕招拿出來一砍一個準,常常把老常砍得遍體鱗傷。不過兩人的相互攻擊僅限于君子之間的那種口角之爭,并不動手。于是他們的攻擊便帶有一定的玩笑和戲謔。常常是攻擊完了,兩人照樣和好如初,相互之間根本不存在矛盾,這就使故事之外又多了層有趣的內容。
言歸正傳。阿福繼續在那里講自己的故事。
他那天講的是“國軍”抗戰的事。那是1937年底,阿福所在的“國軍”在蔣介石嫡系部隊湯恩伯的帶領下來到徐州戰場,配合李宗仁在臺兒莊作戰布防。在那場徐州保衛戰中,阿福所在的部隊一連打了三天三夜,后來實在頂不住時只好往下撤。
為啥要撤?當時阿福的說法很玄。不撤不行,老日武器太厲害。究竟厲害到啥程度呢?阿福用手比劃說,日他奶奶,老日的炮彈像長了眼一樣,不是在空中直來直去地飛,而是會拐彎,像怪物一樣在空中飛來飛去,專找打擊目標,所以凡被子彈盯上的躲都躲不開,最后只有被擊中。你想老日武器那么厲害,國軍咋能不敗……
這時一個小毛頭從后邊拱過來盯住他奇怪地問,老鴰,聽你說得這么玄乎,那老日的炮彈是不是像飛毛腿導彈,只要一出膛,一打一個準?
啥飛貓腿飛狗腿的,我不懂,反正老日武器就是先進,先進得超出你的想象,要不“國軍”會吃敗仗?
還是共軍厲害!小毛頭反駁,共軍都不怕他小日本,不是硬把他們給趕跑了嗎?
你說的也對,不過老日打敗仗也與他們劫數有關。阿福瞥了小毛頭一眼,不是有句老話說叫“日落西山”嗎?別看小日本那么猖狂,可是一遇到劫數就完了。你看他們打到咱河南豫西這一帶大山的時候還不是退了?其實那不叫退,是敗,你知道嗎?是被咱中國人給打敗了……
所以說還是“共軍”厲害,要不剛才你說“國軍”頂不住,共軍一上來就把小日本給打跑了?
你個小毛孩懂個啥球?阿福伸手輕輕拍了拍小毛頭的腦袋,還是回去摸摸你褲襠里長幾根毛再和我討論這個問題。
小毛頭吐了吐舌頭,身子往后一縮,躲進人群里不說話。
其實阿福腿上那塊傷疤我見過,像片楊樹葉子似的烙在他左大腿正前方。后來我曾經問過他有關這塊傷疤的來歷。阿福指著自己的左大腿很自豪,咳,說起這塊傷疤,那可是大有來頭。那天下午,我們正在戰場上和小日本打得激烈,不防被一發打過來的炮彈擊中了,可我當時并不覺得疼,仍然在那里抱著槍和大伙一起頑強戰斗,一直打到戰斗結束,我才拖著這條傷腿回到部隊……
受傷后你當時沒后退,說明你很堅強嘛!
那當然,阿福拍著胸脯把脖子一梗,咱是誰呀?為了打老日,別說傷了一條腿,就是拼上一條命也得跟他們干!
看阿福一副英雄氣概的樣子,我不由瞪大眼睛,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
三
阿福是我們村里公認的講故事高手。由于他講的故事與眾不同,生動有趣,聽得多了,不由你不信以為真。因此直到多少年后,我都在心里琢磨他所講故事的真實性。
其實我就是當年那個向他發難的小毛頭。
我是當兵后上的軍校。我曾經聽授課導師講過許多有關抗日戰爭的歷史。作為一名軍事院校畢業的文職官員,在系統學習有關軍事知識這些內容時,無論如何繞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段在人類歷史上留下慘痛記憶的重大歷史事件。
由于有阿福所講的故事在先,所以后來我在軍校學習后,便對他的講述產生了懷疑,當年他所講的故事又有多少是真實的?因為故事畢竟是故事。為了吸引大家,我想阿福極有可能虛構一大部分內容,運用說書人的夸張手法表現自己,這才吸引了我們。為證實他所講故事的真實性,我曾查過一些軍事資料中有關彈道方面的知識。比如說彈道導彈的射程和原理問題,除涉及到物理學知識外,還與高等數學有關,具體到武器裝備的設置和發明等問題,都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僅憑想象是不行的。又比如說導彈要在空中完成打擊目標時的操作規程,這又涉及到物理學中的拋物線和代數中的坐標問題,所有這些都要有科學依據,用數據來證明,怎么能像阿福故事中所講的那樣神乎其神?因此我對他的“老日子彈像長了眼睛,只盯著目標追殺”的話更是難以相信。子彈會長眼那成什么了?違背基本常識和科學依據。要知道,武器是人類軍事學家根據一定科學知識發明制造出來的,怎么可能會變得那么玄乎?不過有一點我相信,阿福的故事除一部分真實外,有很多內容都是虛構的。這虛構恰恰成了我們那個年代知識匱乏的精神食糧。
在那物質貧乏的年代,我就是靠著這份營養不良的精神食糧一步步成長起來的。
說到這里我可以明白地告訴你,我自小是個故事迷。只要聽說有人講故事,我經常會跑去聽得如醉如癡的。所以在阿福的講述中,常常勾起我對一些戰爭場面的想象,人物和故事情節在我腦子里像演電影一樣變得生動起來。稍大一些,我在不少抗戰片中經常看到我軍英勇善戰的英雄形象,當然也經常看到那些賊頭賊腦,愚蠢至極的日軍在我軍官兵機智勇敢的打擊下,常常被揍得丟盔棄甲抱頭鼠竄時,常常開心得捧腹大笑。也是在那個時候,我心里開始涌起一種軍人的自豪感。并由此激勵我生出一個心愿:長大后,我一定要當兵,當一名在戰場上英勇殺敵的英雄!
初中畢業后,我輟學在家一直在尋找當兵機會。可是那些年,對農村孩子來說當兵并非易事,除自身條件不錯外,還要有關系,不然要想去當兵,門兒都沒有。為了實現這個愿望,我在父親幫助下,經過連續兩年努力,才如愿以償地到部隊穿起了軍裝……
為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我在部隊里勤學苦練,經過三個月的新兵連訓練后,很快成了一名優秀的解放軍戰士。后來當我意識到在部隊里如果沒有知識,當完三年兵后,很快就會被復員回家,于是我開始努力學習文化課。把考軍校當成自己留在部隊的目標。
工夫不負有心人。那兩年,我在部隊里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硬是咬著牙通過自學啃下了高中全部知識。等第三年軍事院校招考時,我作為全團唯一一名僅有初中文憑的考生被河北一所軍事院校錄取,這才實現了人生的夢想!
四
我是在軍校學習期間,一次無意中在軍校圖書館里查資料時,意外發現一篇有關當年徐州保衛戰的一段文字記載:
1937年12月,侵略華東的日軍侵占南京后,第13師團北渡長江,進至安徽池河東岸的藕塘、明光一線;侵略華北的日軍第10師團從山東青城、濟陽間南渡黃河,占領濟南后,進至濟寧、蒙陰、青島一線。日本大本營為打通津浦鐵路(天津-浦口),使南北戰場聯成一片,先后調集8個師另3個旅、2個支隊(相當于旅)約24萬人,分別由華中派遣軍(1938年2月18日由華中方面軍改編)司令官畑俊六和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寺內壽一指揮,實行南北對進,首先攻占華東戰略要地徐州,然后沿隴海鐵路(蘭州-連云港)西取鄭州,再沿平漢鐵路(北京-漢口)南奪武漢。中國軍隊由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先后調集64個師另3個旅約60萬人,以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地區,抗擊北線日軍南犯,一部分兵力部署于津浦鐵路南段,阻止南線日軍北進,以確保徐州。
這場戰爭從1938年1月16日開始到5月6日,持續打了三個多月。其中在臺兒莊戰役那場戰斗中一連打了三天三夜,到第二天傍晚時分,日軍借助地面部隊的掩護和攻擊,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轟炸。國軍所在的第二軍團1125師58團遭到日軍狂轟濫炸,不少士兵被日軍飛機和地面迫擊炮的火力擊中,傷亡慘重,最終不得不撤出陣地……
據后來清點戰場時統計,在這次戰爭中,被日軍敵機和迫擊炮打死打傷的國軍士兵約有三千五百多人,其中不少士兵死于流彈,另有大部分士兵被流彈所傷……
這是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2版《關于徐州保衛戰真相》的一段文字。讀到這里,我不禁又想起我們村里的阿福。阿福當年所講的是不是就是這段歷史?如果是,那么他所講的故事便有了幾分真實。不過我同時也感到有些疑惑,阿福所講怎么與這段文字記載會有如此大的差距呢?帶著這個疑問,我請教了我軍校的導師白銀忠大校。白老師告訴我說,小周,有關徐州保衛戰的歷史已經沒有多少可考性,現今所記載的文字大多是靠后來者的回憶錄整理出來的,所以你大可不必為此較真。如果你真想弄清這個問題,只有去北京軍事博物館看看那里的抗日戰爭紀念館,也許在那6萬多平米的展廳里會讓你看清一切,不過我相信,你去看過之后就會認為我說的沒錯。白老師的話讓我大吃一驚,他怎么能這樣給我解釋?難道是這段歷史記載有誤?
我沒去北京軍事博物館查閱有關這方面的資料,而是一直把這個問題壓在心里。后來我去北京出差時,順便拜訪了一位徐州保衛戰的親歷者——原國民黨第二軍團1125師58團團長劉大白將軍,聽到了有關這場戰爭的另一種說法:
我記得非常清楚,那場戰斗打得異常慘烈,國軍的三個軍團打到最后只剩下兩個師的兵力。劉大白充滿深情地回憶說,我們第三團損失得最為慘重。全團士兵的子彈都打光了,這時日軍仍然在那里狂轟濫炸,怎么辦?我們只有和日軍拼刺刀,與他們展開白刃戰!上邊有敵機轟炸,地面有日軍的迫擊炮,我們就是在那種情況下與日軍展開斗爭的。我記得當時由于我軍傷亡慘重,我的身邊已經沒有多少人,為了擊退敵人,那天下午我沖在陣地最前邊,正要指揮大家堅持戰斗時,一發流彈射了過來,這時我看見旁邊一個河南老兵身子一抖,左腿好像被擊中了,于是他身子一歪倒在了地上。許多人看到這里,都紛紛做好了獻身準備,與日軍展開了激烈的戰斗……
劉將軍,你還記不記得當時那個河南老兵的情況?
我記不大清了,劉將軍搖著花白的頭無奈地嘆著氣說,畢竟過去五十多年了,我怎能記得那么清?不過確有其事。
劉將軍,你的記憶不會出錯吧?
怎么可能會出錯?劉將軍斜著目光看了我一眼,認真地說,我所講的是我親眼所見,怎么可能有假?
看著劉將軍慢慢嚴肅起來的表情,我知道自己有點過于冒犯,所以才惹得老將軍不滿。不過有一點我明白,歷史就是事實,是誰也改變不了的。人的大腦會出錯,教課書會出錯,但歷史卻不會出錯。它總是以客觀存在的方式記錄著過去的一切。
五
阿福已經老得不成樣子。五年前的夏天,我回家探親時還見到了他。
那天中午,司機開著車把我拉到故鄉村口的橋頭時,我看到阿福像座雕塑一樣,須發皆白地獨自坐在那里,給人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樣子。這時他身邊已經沒人聽他講故事,可他仍然坐在那里自言自語地說著什么……
可他身邊并沒有人呀,他在和誰說話呢?我不由感到有些奇怪。
我從車上下來,輕輕地走到他身邊。這時我發現阿福塌蒙著眼睛,根本沒有發現我的存在,仍然在那里饒有興趣地說著什么。我湊上去認真聽了聽,原來他正在和幾個故事中的人物說話:
小李子,你個膽小鬼,怎么一聽到槍聲就嚇得尿褲子?看看你的膽吧!
真有你的大個子老趙,一槍撂倒他媽的一個小日本兒,照你這種打法,不怕他小日本厲害,上來一個打一個,上來兩個打一雙,哈哈,又打中了,又打中了……
咦,怎么不對勁呢?小日本怎么從左邊攻上來了?快,小四川,把槍瞄準,千萬別讓小日本兒搞偷襲!他奶奶的這幫雜種可真夠狡猾的,趁我們對付右邊的敵人,他們倒從左邊摸過來了……
打,給老子狠狠地打——
哎喲,我的娘呀,小日本的子彈咬住我的腿了……他媽的小日本兒,我日你親娘,你咋偷偷摸摸放冷槍?有本事和老子面對面真刀真槍地干一場!
……
阿福像個說書人坐在那里眉飛色舞地講著。我知道他此時一定又進入到忘我之中。可惜現在沒有人聽。過去的聽眾現在不是忙著做生意,就是跑到城里打工,誰還有心聽他講這些老掉牙的故事?
老常呢?咦——怎么不見老常呢!哦!我突然想起老常已經去世好幾年了。當年唯一一個可以和阿福斗嘴的小老頭兒已經作古。沒有聽眾和對手的阿福,現在成了孤家寡人,只有在那里自說自話。我想他之所以這么做,一定是耐不住寂寞,即使沒有聽眾,他也要坐在那里講自己的故事。他就是靠這種講故事的方式來打發自己的日子。想到這里,我不由湊上前去和他打起招呼:
福爺,你怎么一個人坐在這里呀?
阿福抬起頭,睜開快要爛掉的眼圈打量著我問,你是誰呀?
我是國棟,你怎么把我給忘了?我是老周家的老三國棟!
啊,我想起來了,你是國棟,你,你不是去當兵了嗎?
是呀,我是去當兵了!
好好好,當兵好,當兵好,阿福看著我身上的軍服,伸出手在上邊摸了摸,不無羨慕地說,我聽說你在部隊里當了大官?
也不是什么大官,就是個跑腿的,在部隊里混碗飯吃。
國棟這孩子老謙虛呀,阿福感嘆起來,都說你出去當兵后考上了軍校,畢業后留在部隊里當了大軍官。
那是謠傳,其實我啥都不是,就像你當年一樣,是個跟在人家大官屁股后邊跑腿的小兵。
我可不能和你比,我那當的是啥兵?狗球不是!阿福頓了頓,臉上的皺紋堆積成溝溝壑壑的山川,這時他忽然問道,哎,國棟,我問你個事兒?
你說福爺。
都說你是在部隊里當大官的,有知識有學問,我問你徐州保衛戰的事兒你應該知道吧?
知道一些,福爺,怎么了?
其實也不怎么,我就是想問問你,當年小日本兒的子彈是不是會長眼睛?
這我可說不好。我笑了一下,這牽扯到軍事方面的專業問題,我得回去請教有關方面的軍事專家。
其實不用請教,我早就知道!阿福突然內行地說,小日本的子彈不會長眼,更不會拐著彎追人,那是我瞎編的……
福爺,打仗是很嚴肅的事情,你怎么能胡說?我迷惑不解地看著他。
咋?難道就不興我給你們開個玩笑?說到這里,阿福咧開缺了牙齒的嘴巴嗬嗬笑起來,我知道那樣說不對,是有意夸大,我這樣說是為了哄你們這幫小年輕玩兒的……
哄我們玩的?我不由疑惑起來,那我常爺說的那些話是怎么回事?
啥咋回事?阿福撇著嘴,老常那樣說還不是故意逗我!其實他知道啥?在家種了一輩子地,連遠門都沒出過,他能知道啥?還不是拿我窮開心。
阿福的話突然讓我有種失重感,我覺得眼前的一切都變得虛幻起來……
福爺,恍惚中我說,你能不能再給我講講那個過去的故事?
哪個故事?
就是你過去講的那個有關徐州保衛戰的事。
咋?你還沒聽夠!阿福又嗬嗬笑起來,都是多少年前老掉牙的事,有啥好講的?別再聽我胡說八道,還是回去好好當你的大軍官吧!可千萬別再細究這個事兒,說到這里,阿福壓低聲音湊過來說,我現在老糊涂,記性也不中,啥事都想不起來。何況時間過去那么長,我哪能記得那么清楚?
看阿福坐在橋頭上沐浴在夏天的陽光里,一副悠閑自在的樣子,我一時有種找不到北的感覺……
站在白花花的陽光下,我一遍遍地反復問自己,這么多年來,難道是你自己搞錯了嗎?可是我究竟錯在哪里?
六
三年后的一天,我出差路過故鄉,順便拐到家里看望父母時,橋頭上卻沒看見阿福的身影。我不覺有些奇怪。一打聽才知道,原來阿福早在半年前就去世了。
父親對我說,阿福“走”那天,事先沒有任何征兆。上午大家從他身邊路過時,見他獨自一人坐在橋頭上,也不知道嘴里在說些啥,只聽他在那里嘟嘟囔囔地說著。反正大家都對他的絮絮叨叨習以為常,所以也不感到有啥奇怪。可是后來從他身邊路過的忽然聽不到他說話,起初還以為他坐在那里睡著了,便想上前叫醒他回家休息,可是連叫幾聲他都沒回應,只好上前推他,誰知阿福竟然頭一歪倒了下去,原來不知道他何時就已經死了。他死在自己的講述中,連半點痛苦都沒有……
聽著父親的講述,想到阿福走得如此安然,我鼻子不由一酸,知道一個活著的歷史從此翻過了新的一頁,開始變得模糊起來……
補記:
據一則軍事資料記載,1938年4月,河南一個名叫吳福貴的國民黨士兵在徐州保衛戰中被日軍一流彈所傷,從此落下精神妄想癥,整天處于臆想之中。退伍復員后回到老家,常年靠對那場戰爭的回憶向人描述生活。終年93歲。
(責編:王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