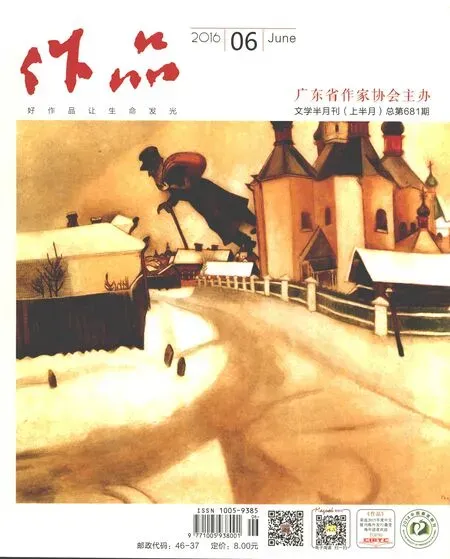有鳳來(lái)儀
文/楊怡芬
有鳳來(lái)儀
文/楊怡芬
楊怡芬1971年出生,浙江舟山人,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中國(guó)作協(xié)“21世紀(jì)文學(xué)之星”叢書入選者,2010年度浙江省青年文學(xué)之星,魯迅文學(xué)院第13屆學(xué)員。曾獲《作品》雜志社“魯迅文學(xué)院高研班學(xué)員作品征文”小說(shuō)獎(jiǎng)。2002年開始寫作,已在《人民文學(xué)》、《十月》、《花城》等期刊發(fā)表中短篇小說(shuō)70余萬(wàn)字,出版中短篇小說(shuō)集《披肩》、中篇小說(shuō)集《追魚》,有小說(shuō)入選年度選本及選刊。
我真不明白我為什么那么喜歡她。
我們是在市總工會(huì)的演講比賽上認(rèn)識(shí)的,我是工作人員,她是參賽選手。市總工會(huì)的演講比賽歷史悠久,說(shuō)不清是從哪一年開始的,反正,二十多年前,我參加工作的時(shí)候,它就有了。我工作第一年,就報(bào)名參加了比賽,同辦公室的姐姐勸我不要去,因?yàn)榇饲拔覀兙謴膩?lái)沒有一個(gè)人在這么大的全市比賽中獲過獎(jiǎng),沒希望的事,去做它干嘛?還有,萬(wàn)一講砸了,會(huì)被人家笑話的。我說(shuō),沒事,不就去演講一下嘛,學(xué)校里我們常常演講的。就這樣,我去了,得了一個(gè)二等獎(jiǎng),高興得我們局的工會(huì)主席在單位院子里的黑板上寫喜報(bào);第二年,我又去了,得了個(gè)三等獎(jiǎng)。反正,走下坡路了,自己也就見好就收。其實(shí),得獎(jiǎng)也就高興一陣子,最讓人高興的是能交到幾個(gè)朋友。二十年前的交通沒現(xiàn)在方便,那會(huì)兒選手報(bào)到后同吃同住得呆上兩天,不像現(xiàn)在,上午來(lái),下午就散了,都說(shuō)不上一句話。也許就因?yàn)榛斐曰旌冗^,對(duì)這每年一度的比賽有感情,偶爾得了個(gè)做工作人員的機(jī)會(huì),我就欣然來(lái)了,做了前臺(tái)接待,簽到、分發(fā)議程,還有引導(dǎo)座位,除此外,但凡選手出聲相求,只要我能幫,我就一定幫。當(dāng)然,我知道沒一個(gè)選手會(huì)念我的好,一轉(zhuǎn)背,他們?cè)缇桶盐彝恕?/p>
她是個(gè)例外。
那天,她來(lái)晚了,頭一個(gè)選手已經(jīng)在開講了,她才到。
“姐姐,你,你有衛(wèi)生巾嗎?”她湊到我耳朵邊說(shuō)。她用了點(diǎn)香水,那味道,我聞著像蘭蔻的“真愛奇跡”,我年輕的時(shí)候,也特愛這款。至于衛(wèi)生巾,這不是問題,我包里總有一包備用的。生氣過度、緊張過度、興奮過度,都有可能引發(fā)月事。這女孩子就是這樣,緊張過頭了。我把衛(wèi)生巾塞到她手里的時(shí)候,她的手冰冰冷的。她一轉(zhuǎn)身,我看到她的裙子上有一團(tuán)血痕,那裙子是白色的裹裙。我叫住她,跟著她一起去了衛(wèi)生間,把我身上的套裝換給她。腰頭松了近兩寸,我就用一個(gè)小燕尾夾幫她別了一下。她看著鏡中的自己,挺滿意的。說(shuō)實(shí)話,她自己那套穿的像是來(lái)相親的,換了我的衣服,才更像個(gè)胸有成竹的選手。她去比賽了,我呢,費(fèi)了老大勁洗掉那團(tuán)血漬,在干手機(jī)下面把裙子吹了個(gè)半干,幸虧裙子腰圍是有彈力的,我吸了口氣,穿上了。在盛夏,穿著足足小了兩號(hào)的衣服,你想想,這個(gè)樣子能見人嗎?我都不敢看鏡子中的自己。幸好我隨身帶了一條真絲披肩,本來(lái)是預(yù)備萬(wàn)一室內(nèi)空調(diào)太冷時(shí)保暖的,現(xiàn)在剛好用來(lái)裹身子。等我把自己收拾妥當(dāng),對(duì)著鏡子,我看到了一個(gè)像從印度歌舞電影里走出來(lái)的女人。這會(huì)兒,我才想到,我根本沒留下她的電話號(hào)碼,甚至,我都沒讓她簽到,我現(xiàn)在能做的就是趕緊坐到我的老位置去,等她來(lái)找我。
我坐在那里,垂頭看書,不打算和進(jìn)出的人有目光交流,暗暗祈禱千萬(wàn)不要遇到熟人,一個(gè)都不要。
但就是有一個(gè)人走到我面前,站在那里一動(dòng)不動(dòng),我只好抬起頭來(lái),果然看到了一張大笑臉。是我的高中男同學(xué)。他斜著眼睛從上到下地瞄我,就好像我什么都沒穿。我和這個(gè)家伙,有一回差一點(diǎn)就“禮節(jié)性”上床。那次同學(xué)聚會(huì),我有點(diǎn)醉了,他送我回了旅館的房間。孤男寡女,不發(fā)生點(diǎn)什么,似乎反倒不對(duì)頭——大概他是這么想的。我止住了他的動(dòng)作,我說(shuō):“哎哎哎,別毀了我們的友情好不好。”他也笑了,說(shuō):“你真不禮貌!”
從那之后,我真的滴酒不沾了。我也有點(diǎn)刻意回避他,同學(xué)聚會(huì)里如有他,我就告假不去,只聽說(shuō)他仕途得意,一切都很好。我也就聽聽過,畢竟,在各自的日常中,我們并沒有什么交集,但這回兒,我這么妖嬈地坐在會(huì)議室門口,偏又被他撞上,我的臉還是騰騰地紅了起來(lái),我甚至已經(jīng)開口解釋了一下我身上這套衣服的來(lái)源。
“噢!”他恍然大悟:“怪不得!我還以為你變了呢。”
幸虧沒有第三個(gè)人聽到我們之間的對(duì)白。
“我們單位也有個(gè)選手來(lái)參賽,我過來(lái)給她鼓鼓勁!”他也開口解釋了一下他在場(chǎng)的原因,然后我們客氣道別,他進(jìn)場(chǎng)去聽演講,我依舊在老地方垂頭看書。我?guī)Я藗€(gè)KINDEL,下載了七八十本書呢,看上一年都沒問題。那天我在讀的是《紅樓夢(mèng)》,正讀到尤三姐用鴛鴦劍抹了她自己,不知怎么,每回讀到這里我都會(huì)想,這才是一個(gè)好的收梢啊,難道尤三姐和柳湘蓮能過得了平常日子?
那天,我停下來(lái)問自己,我怎么會(huì)這么想呢?
這些年來(lái),我過的也就是平常到不能再平常的日子。年輕的時(shí)候,我也在舞臺(tái)上光鮮過,雖然是小舞臺(tái),但也總是舞臺(tái)嘛,我當(dāng)過主持人,朗誦過詩(shī)歌,演講、給話劇念旁白,到最后,是在給一場(chǎng)演講比賽當(dāng)簽到的工作人員。舞臺(tái)下,我結(jié)婚生養(yǎng),買菜做飯,工作兢兢業(yè)業(yè)誠(chéng)惶誠(chéng)恐,好歹升了個(gè)副科級(jí),就這樣,把平常日子都過了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了啊。
我就這樣發(fā)了一陣呆,又把書頁(yè)退回去幾頁(yè),再讀讀尤三姐的收梢,也許,我剛才問自己的答案就在這幾頁(yè)書里呢。哪有那么容易找到答案的?我把書頁(yè)一陣亂退,退到了貴妃省親那一章。《紅樓夢(mèng)》就是那樣,平常和聚會(huì)盛宴混搭,那些人天天盼聚會(huì)似的。那個(gè)有千竿翠竹的清幽所在,先被寶玉結(jié)結(jié)實(shí)實(shí)為頌圣題的“有鳳來(lái)儀”,后讓元春貴妃給改成了平平實(shí)實(shí)的“瀟湘館”。也許,人富貴久了,一眼就能看到平實(shí),也不會(huì)以平實(shí)為恥;我們這些人,都還是初嘗“物質(zhì)”滋味(跟富貴還差十萬(wàn)八千里呢),都是跟寶玉一樣,動(dòng)不動(dòng)就要端出鳳儀來(lái)的,怎么敢就老老實(shí)實(shí)題個(gè)“瀟湘館”呢?
我正一邊讀一邊亂想,她來(lái)找我了,小臉緊張興奮之后紅潤(rùn)之至,這粉嫩,真叫吹彈得破。我們就又到衛(wèi)生間把衣服換了回來(lái)。如此,我才長(zhǎng)松了一口氣。
“真的太謝謝你了。”小姑娘說(shuō)。
我說(shuō):“這個(gè),有啥好謝的?沒事。”我拿出簽到表,看她在表格中簽了自己的名字,寫全了手機(jī)號(hào)碼。董小如。電話號(hào)碼后四位一溜是2。
我們進(jìn)場(chǎng)去等宣布比賽結(jié)果,在二等獎(jiǎng)的名單里,頭一個(gè)就是董小如,她倒只是笑瞇瞇的,朝我飄了飄眉毛,前幾排卻有一個(gè)男生激動(dòng)得跳起來(lái)。她湊到我耳邊說(shuō):“我男朋友。丑死了!”董小如白裙飄飄地上臺(tái)領(lǐng)了獎(jiǎng),她男朋友在臺(tái)下不停拍照,等她下臺(tái)后,又挽上她,一副恨不得全天下人都知道他是她男朋友的架勢(shì)。董小如特意找到我跟我告別,她說(shuō):“您有名片嗎?”名片這東西,我的包里也有,就順手給了她一張。
接到她的電話是在半個(gè)月后,她說(shuō)她在我單位門口,我驚訝了一下,等著她問我房間號(hào)碼,可是她說(shuō):“張姐,你下來(lái)一下好嗎?”到了門口,我才明白為什么她只能叫我下來(lái),原來(lái),她給我?guī)?lái)了一筐西瓜。
“朱家尖的西瓜,自家地里出的。”她和我合力把這筐西瓜扛上了我的車。
她的額頭上沁了汗珠,棉布T恤背部也濕了一塊。我都不知道她怎么把這筐西瓜拿過來(lái)的。我說(shuō):“到我辦公室去坐會(huì)兒吧!”
這個(gè)辦公室我已經(jīng)呆了快十年了。有幾盆綠植,無(wú)非是文竹、綠蘿,還有一盆時(shí)不時(shí)會(huì)開出小花來(lái)的多肉。墻上的小畫也有幾幅,是孩子學(xué)油畫時(shí)候臨摹莫奈的。冷氣開得足,進(jìn)門沒多久,她的汗就都收了,我給她倒的菊花茶也涼到可以入口了,她坐在沙發(fā)上開始放松起來(lái),攤手?jǐn)偰_,斜靠著沙發(fā),開始夸墻上的畫不錯(cuò),“那池塘里的水就像真的會(huì)流動(dòng)一樣,還閃亮,哎呀,還有小草和泥土的倒影!”她說(shuō)的,也正是我最欣賞的一處。我就開了柜門打算找出莫奈的畫冊(cè)來(lái)讓她看,但就是找不到,一疊獲獎(jiǎng)證書倒是翻出來(lái)了,她拿在手里看,尖聲說(shuō):“哇!你和我一樣,千年老二啊!”我示意她輕聲一點(diǎn)。我的正主任就在隔壁辦公室。她笑了,低了嗓門說(shuō):“一等獎(jiǎng)都是給‘偉光正’的選手的,我們這樣和風(fēng)細(xì)雨的,能二等獎(jiǎng),就不錯(cuò)了。”
這些年,我也是這么想的,但想到最后,參加了那么多回演講比賽,居然一次也沒得過一等獎(jiǎng),總是遺憾。當(dāng)然,這種遺憾,她這樣的年紀(jì),是不會(huì)有的。
我們說(shuō)說(shuō)笑笑,我覺得和她處得很輕松自然。到了我這個(gè)年紀(jì),孩子都上大學(xué)了,對(duì)年輕小姑娘,自覺不自覺就端出媽媽架子來(lái),難得的,董小如讓我覺得我就比她只大了那么一點(diǎn)點(diǎn)。送走她后,我特意把她的電話號(hào)碼存在手機(jī)里了。我還靜靜坐了一會(huì)兒,平復(fù)一下剛才興奮了的心情。她讓我想到我跟她一般大的時(shí)候的一些事情,甚至,我想起了幾乎已經(jīng)被我遺忘的一個(gè)年長(zhǎng)閨蜜。當(dāng)年,我是董小如,她是我。對(duì)了,我們也是在演講比賽中認(rèn)識(shí)的,我們都是選手,吃住在一起,特別投緣,演講賽后,就跟小姐妹一樣走動(dòng)了,算起來(lái)她年長(zhǎng)我十歲總有的,那年,我二十出頭,她三十出頭,孩子上幼兒園了。開頭也是我去找她的多,后來(lái),她會(huì)叫上我一起玩。我并不覺得她比我大很多,我記得我也跟她討教過一些羞于問媽媽的問題,她都答得很自然,似乎一切本該如此的樣子。這會(huì)兒,我想著她,心頭居然一軟。
有緣的人,總會(huì)在預(yù)約之外的地方碰到。
每年農(nóng)歷六月十九前后,只要有空,我就會(huì)去普陀山進(jìn)香。那幾天,舟山街上滿是背著個(gè)黃布袋的女人,年紀(jì)大的有,年輕的也有,大家看著都覺平常。每年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前后朝山進(jìn)香,在舟山,幾乎算是一大民俗。據(jù)我觀察,這民俗波及區(qū)域,寧波、上海和福州這一帶,都在其中。三個(gè)十九的前夕,普陀山上燈火通明,人山人海,渡船快艇整夜不歇,說(shuō)是海上仙山,實(shí)為不虛。年輕的時(shí)候,我就喜歡混跡在進(jìn)香的人群中,三步一拜,從法雨寺旁的香道拜上佛頂山,做夢(mèng)一般。現(xiàn)在的我,總是在十九前后三天里選個(gè)好天,那幾天雖也人多,但多得恰如其分,不會(huì)擁擠,也不用處處排隊(duì)。
那一天,我正走在從普濟(jì)寺到紫竹林露天觀音的步行道上,那段防腐木鋪就的棧道,緩緩從百步沙上過,道旁青松蔽日,隔著松林就是沙灘,浪頭優(yōu)雅地涌上退下,聲響也不大,做步行時(shí)的背景音,再好不過了。我緩步走著,后來(lái)的行人一個(gè)接一個(gè)超過我,有一個(gè)女孩在快要掠過我的時(shí)候停了下來(lái),我聞到了“奇跡”的香味,也聽到了她欣喜地叫聲:“張姐!”
這一邂逅,就有點(diǎn)“在千萬(wàn)人中,遇見了你”的意味了。
我看了看她身后。董小如笑了,說(shuō):“他呀,太煩了!來(lái)進(jìn)香,我才不要帶他呢。”我們倆就搭伴去拜了露天觀音,說(shuō)是搭伴,我們的話也并不多,也沒有勾肩搭背,也就是不前不后這樣走著,對(duì)著這一片蓮花洋和對(duì)面的珞珈山,默默無(wú)語(yǔ)。
一直到黃昏時(shí)分,我們才回程,到城內(nèi)時(shí),已經(jīng)路燈初上。我說(shuō):“我們一起去吃個(gè)飯吧?”她微笑點(diǎn)頭,好像實(shí)在應(yīng)該一起去吃個(gè)飯的樣子。
我們點(diǎn)上菜,我還叫了瓶紅酒,我說(shuō):“喝不完你就打包走。”她說(shuō):“哪會(huì)喝不完?我們兩個(gè),干掉一瓶,不在話下。”我真的有好久沒喝酒了,不過,今天這不算應(yīng)酬,心情放松地自酌,面前還有個(gè)賞心悅目的小美女,喝上一兩杯,那是不成問題的。一杯酒下肚后,我開始跟她講我剛畢業(yè)那會(huì)兒參加市總工會(huì)演講賽的事情,說(shuō)到我們單位的工會(huì)主席往黑板報(bào)上用白粉筆字寫喜訊,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憋住了才沒笑出來(lái)。我也說(shuō)到了那位比我年長(zhǎng)十歲的閨蜜胡姐,甚至說(shuō)到了她的豐胸細(xì)腰,腰身一尺七,胸卻是D杯,背影看著瘦怯怯的,當(dāng)面一看,真有點(diǎn)驚心動(dòng)魄。董小如斜著眼看我,說(shuō):“這也是我的尺寸,你覺得我驚心動(dòng)魄不?”我笑了:“哎呀,那時(shí)我才多大?沒見過世面。現(xiàn)在不會(huì)了。”接著,我好像又和她講了講我那時(shí)候追的星,第一是張國(guó)榮。電視機(jī)和錄像機(jī)都設(shè)好定時(shí)開機(jī),早上一睜眼醒來(lái)就看張國(guó)榮的演唱會(huì),最愛他輕擺臀部,真的,相比他迷離的眼神,我對(duì)他的臀部更入迷。這話都說(shuō)出來(lái)了,顯然,那天,我的酒喝得太爽快了。董小如報(bào)了一個(gè)男星的名字,說(shuō)是她的男神,她說(shuō):“不過奇怪了,現(xiàn)在的男生都好像沒有臀部的,那個(gè)瘦啊……”那男星的名字,我聽過就忘了。人到一定年紀(jì),真的會(huì)和流行絕緣。我有個(gè)年長(zhǎng)的攝影師朋友,有回在沈家門夜排檔遇到周迅,有幸和她說(shuō)幾句話,但是他“不認(rèn)識(shí)周迅”,這事情,我們年輕人一直笑話他,他呢,一直以此為傲,然后,我忽忽長(zhǎng)到這個(gè)年紀(jì),才發(fā)現(xiàn)“不認(rèn)識(shí)”明星是件多么正常的事情啊。
這個(gè)感慨,我卻懶得和董小如說(shuō),說(shuō)了,那就是倚老賣老,何必呢。于是我就又開始說(shuō)胡姐,說(shuō)我們那時(shí)候的演講比賽。
我講得很投入,直到董小如站起來(lái)恭恭敬敬招呼:“汪局,你也在啊。”我才看清,我那男同學(xué)站在我身邊。他笑著拖開椅子,在我們桌邊坐下來(lái):“小楊,這也太不夠意思了吧?喝酒都不叫我的。”我說(shuō):“哎呀,本來(lái)我就是個(gè)沒意思的人嘛。”董小如招呼服務(wù)員又加了一副杯碟,給他倒上了一杯紅酒。我們的紅酒,也就夠倒這一杯了,菜也吃完了,董小如要加菜,我說(shuō):“不用了吧?我們以后再請(qǐng)汪局吃飯吧。”我那男同學(xué)也是喝過酒了,脖子都紅通通的,坐在那里,看看她,又看看我,問:“你們倆認(rèn)識(shí)?”我說(shuō):“嗯,好朋友。”汪同學(xué)狠狠拍了我一下背:“那你怎么不早說(shuō)呢?害我這兩年都沒好好照顧你的小姐妹!對(duì)了,那天演講,我就是去給小董加油的呀。早知道你們認(rèn)識(shí),我就要你張羅慶功宴了!”他又轉(zhuǎn)頭對(duì)董小如說(shuō):“我和你楊姐,那是穿開檔褲一起大的交情,你叫她姐,好比我就是你姐夫,以后有什么事,筆直和我說(shuō)!”董小如笑著點(diǎn)頭,一邊在電話里和她男朋友說(shuō)飯店的地址,和汪同學(xué)一起吃飯的人也來(lái)找他了,于是,我們就散了。
我們走到飯店門口,她男朋友已經(jīng)在那里了,我和他們告別后,一個(gè)人步行回家。舟山的氣候,入夜后就夜涼如水,我越走越清醒,和胡姐有關(guān)的舊日時(shí)光也越來(lái)越清晰,方才知道,我其實(shí)想告訴董小如的是關(guān)于胡姐另外一個(gè)故事。
話說(shuō)我和胡姐越來(lái)越熟了,熟到我會(huì)和她訴說(shuō)失戀的煩惱,她呢,會(huì)和我說(shuō)調(diào)動(dòng)的苦楚,他們夫妻分居兩地,她一個(gè)人把自己的工作、住房都弄好了——她是個(gè)能干的人,但她老公的調(diào)動(dòng)一直卡在那里,她說(shuō):“幫忙的人沒真把這事放心上啊。”我也替她著急。但這事情,光著急也沒用。她也張羅給我介紹新男友,有一回,連人帶飯局都張羅好了,只要我到個(gè)場(chǎng)。她說(shuō):“你只要穿得漂漂亮亮來(lái)就好了。”我就去了。一桌人的飯局,都是胡姐的朋友和同事,我被安排在一個(gè)并不年輕的人旁邊,看樣子已經(jīng)四十多了,整個(gè)人端著,像一定要人知道他多莫測(cè)高深的樣子,一桌的人都叫他李局。飯吃好后,接著去跳舞,那時(shí)候時(shí)興跳交誼舞,李局是分配給我的舞伴,他的話不多,我們就這樣一支舞一支舞地跳,彬彬有禮地跳,也不覺得有什么不妥。他跳舞時(shí)話也不多,也沒問我從哪里來(lái)的這樣初次見面會(huì)問的問題,只是有時(shí)候會(huì)隨著樂曲節(jié)奏捏捏我的手。有一支舞跳到中場(chǎng)的時(shí)候,我的腳崴了一下,那天我穿著高跟鞋,這一崴,到底痛的,我就退下來(lái),縮到我們?cè)诘哪莻€(gè)小包廂的角落里,那里燈光打不到,黑咕隆咚的。從我這個(gè)角度看過去,胡姐已經(jīng)接替我在和李局跳了,他們跳得很默契,步態(tài)懶洋洋的,松弛得很。過了一會(huì)兒,又有一對(duì)進(jìn)包廂來(lái)了,他們沒看見角落里的我,一半也是太心急了,當(dāng)著我的面摟在一起,密不透風(fēng)地親吻著摸索了一會(huì)兒,看得我心驚肉跳。好在,也就那么一會(huì)兒。那女的先說(shuō)話了:“今天看樣子是小胡給李局在介紹對(duì)象?”男的笑了一聲,說(shuō):“那女的是小胡的閨蜜,這下好了,成娥皇女英了。”女的躲進(jìn)他懷里,說(shuō):“別掉書包,什么什么啊?”那男的卻懶得解釋,索性就又把女的吻了個(gè)密不透風(fēng),摸了個(gè)無(wú)所不至。我在那里走也不是,留也不是,萬(wàn)一他們一回頭看見我,那多尷尬啊。他們吻好了,拉好了衣服,又開始剛才的話題,那女的顯然已經(jīng)把這典故想起來(lái)了,她說(shuō):“小胡這招好毒啊,她的小姐妹嫁給李局,以后她還是李家半個(gè)女主人,是吧?”男的說(shuō):“我看小胡倒不是為這個(gè),她是為她老公的調(diào)動(dòng),要李局實(shí)打?qū)嵉貛兔ζ饋?lái),這樣老吊著,總不是個(gè)事情。”女的有點(diǎn)生氣了,說(shuō):“我看你也是被小胡魔住了!否則,怎么像她肚里蛔蟲似的!”男的說(shuō):“姑奶奶,我就一個(gè)身子,都在你那里呀。”
蠟燭不點(diǎn)不亮。當(dāng)時(shí)的我,如果沒有這一對(duì)野鴛鴦來(lái)點(diǎn)醒,一定還會(huì)以為來(lái)和我相親的人根本就沒來(lái)呢。
這一對(duì)踩著舞曲的尾巴又滑進(jìn)了舞池,我也趁著一曲終了的混亂從安全門那里走了。也是盛夏,站在午夜的定海街頭,我渾身哆嗦。那時(shí)候手機(jī)還是“大哥大”,是奢侈品,我的寢室里沒裝電話,要聯(lián)系我,還是得打辦公室電話。接下去的足足一個(gè)月,聽電話前,我都先看一下電話號(hào)碼。我害怕,如果胡姐打電話找我,我應(yīng)該怎樣說(shuō)話。但胡姐一直沒有打電話來(lái),我也不再去找她,似乎很輕易的,我們的親密就消散了。
那么,現(xiàn)在的我,能原諒她么?我一邊走,一邊問自己,直到回家洗了睡下,我還是沒有給出答案。
盛夏過了,初秋過了,日子都獲得了加速度,一不留神,就不留痕跡地過去了,或者也可以這樣安慰自己,因?yàn)樘綗o(wú)事,所以日子飛快,這是好事。到冬天的時(shí)候,董小如來(lái)說(shuō)準(zhǔn)備和男朋友結(jié)婚了,日子定在轉(zhuǎn)年五月份。送她什么結(jié)婚禮物呢?挑來(lái)?yè)烊ィ疫x了一顆淡粉色的日本Aokya海水珍珠,十二厘米直徑,渾圓無(wú)瑕,光澤是從珠體最深處發(fā)出來(lái)的,又潤(rùn)又亮。董小如很喜歡,喜歡到拿它配了婚紗,婚禮現(xiàn)場(chǎng),那顆珍珠閃閃發(fā)亮,無(wú)來(lái)由地讓我想到鮫人的淚珠。汪同學(xué)自然也在,被安排在我身邊,不知怎么,一高興,我就告訴他,新娘脖子上的那顆珍珠是我送的。他盯著新娘看了半天,說(shuō):“真美啊,除了說(shuō)真美,還有什么好詞嗎?”確實(shí),新娘董小如美得讓人看著遙不可及。他又低聲說(shuō):“你看看新郎,配不上她啊。”我裝沒聽見,只顧看董小如和那顆珍珠。婚禮快結(jié)束的時(shí)候,我那汪同學(xué)突然和我說(shuō):“有件事,我想我還是先告訴你吧,我可能輪崗到你單位當(dāng)局長(zhǎng),百分之九十是定下了。”我怔了半天,才回過神來(lái)。
接下來(lái)一段日子,我坐在辦公室里,總是心神不寧。過了一個(gè)月,先是任命文件下來(lái),緊接著,人就來(lái)了。同事們有知道他是我同學(xué)的,便悄悄恭喜我,說(shuō):“這下好了,你這個(gè)千年老二馬上就能扶正了。”同學(xué)們就更是鬧猛,張羅著要來(lái)一個(gè)聚會(huì)慶祝一下,聽說(shuō)汪同學(xué)倒是一推再推,說(shuō)是一不過是平調(diào),二呢萬(wàn)事還是低調(diào)一些的好,但是這場(chǎng)聚會(huì)還是被定下來(lái)了,汪同學(xué),不,汪局長(zhǎng)說(shuō):“你叫上董小如吧。”我打電話過去的時(shí)候,董小如在那頭先遲疑了一下,問道:“張姐,你是當(dāng)真去的嘍?”我說(shuō):“那是,我肯定在的。”
同學(xué)聚會(huì)向來(lái)是放松的,一幫人又回到“從前”,無(wú)論喝酒的還是不喝酒的,座上沒一個(gè)是安靜的——你也沒法安靜,你一安靜,就顯得與這飯局格格不入了。我還是開戒喝了點(diǎn)酒,因?yàn)楹笈逻€在,畢竟自己把住了。不知怎么,董小如和汪局長(zhǎng)一起成了桌上的焦點(diǎn),她喝了不少酒,我說(shuō):“哎呀,留點(diǎn)肚子過會(huì)兒唱歌喝嘛!”我們有個(gè)同學(xué)開了個(gè)量販?zhǔn)降目ɡ璒 K,同學(xué)聚會(huì)的保留節(jié)目就是一幫人飯后殺到他那里,占據(jù)他那里最大的包房,鬼哭狼嚎一陣散散酒。很多時(shí)候,說(shuō)是散酒,其實(shí)是再喝一場(chǎng)酒。這次也是。董小如走路已經(jīng)有點(diǎn)發(fā)飄了,我攙著她走,她說(shuō):“張姐,要么我回家吧?”我說(shuō):“你這樣子去,你那醋壇老公要罵我的。我們還是先去唱歌的地方散散酒,我一滴酒都不會(huì)讓你喝的,你放心。”我都這樣打了包票了,自然強(qiáng)硬著要說(shuō)到做到。我知道我同學(xué)的包房里有給散酒人躺一趟的長(zhǎng)沙發(fā),有一層紗幔和唱歌的地方隔開。我也曾躺過一回的。到了之后,我就把她徑直送到那個(gè)地方,脫了她的鞋子,又讓人拿了一床毯子來(lái),讓她睡下了。我呢,在她身邊坐著,拍著她讓她安心睡。她蜷著身子,頭抵著我的大腿,這睡姿,像個(gè)孩子,有一刻,我簡(jiǎn)直要掉下淚來(lái)。
同學(xué)們?cè)谄鸷遄屚艟殖瑁谖覀儼啵潜晃覀兘凶銮楦柰踝拥模徊恍⌒模@樣的卡拉OK就會(huì)變成他的獨(dú)唱音樂會(huì),可是,今天他卻和一個(gè)女同學(xué)在合唱一首《明天我要嫁給你了》這樣的老歌,唱得連調(diào)子也跑了。過了一會(huì)兒,他進(jìn)來(lái)了,打了個(gè)手勢(shì)讓我去唱歌。他輕輕地拉了我起來(lái),自己坐到我坐過的位置上,董小如迷糊中呢喃了一聲,頭又向他的大腿那邊移過來(lái)一點(diǎn),汪局長(zhǎng)坐穩(wěn)了,也像我那樣輕輕拍著她。我站了一會(huì)兒,他看也不看我,只是垂頭欣賞酣睡中的董小如。我又站了一會(huì)兒,看了看原先的這層紗幔不知道什么時(shí)候換成布簾了,可我還是退出來(lái)了,自己去點(diǎn)了一首《北國(guó)之春》。同學(xué)們依舊是鬧,歌也唱,酒也喝。我一只耳朵聽著布簾子后面的動(dòng)靜。有同學(xué)問“汪局人呢?”我回答說(shuō):“他有點(diǎn)事情,過會(huì)兒就回來(lái)。”布簾子后面沒有什么大動(dòng)靜,只有一次我好像聽到董小如呢喃了一聲,我豎起耳朵聽,可并沒有第二聲異樣的傳來(lái)。鬧到十點(diǎn)半,同學(xué)們說(shuō)主角都逃了,我們也散了吧,我說(shuō),你們先走,我等會(huì)兒和董小如一道走。
等他們散盡,我在布簾子外又逡巡了一陣,才撩開進(jìn)去。董小如面朝里依舊睡著,汪局見了我,滿面春色,朝我得意地眨了下眼睛,一邊人就要往布簾走。我一把拉住他,一邊說(shuō):“小如,睡醒了嗎?我們走吧。汪局,你打電話叫你的司機(jī)過來(lái)吧。”汪局只好站住,在那里給他司機(jī)打電話,董小如呢,也不應(yīng)我的話,只一個(gè)人默默起來(lái),原先束著的頭發(fā)現(xiàn)在披散開來(lái),遮住了臉。她悶聲不響地撩開毯子,裙子齊齊整整的,然后坐起,低頭穿好鞋,也不讓我扶,打頭走在前面。我們?nèi)送嚕人土硕∪缁亍\嚿希∪鐝陌锶〕鍪嶙樱杨^發(fā)梳成一個(gè)紋絲不亂的馬尾,再拿出香水小樣,在耳背后點(diǎn)了一點(diǎn),車?yán)餄M滿的“真愛奇跡”的味道。汪局打開了一瓶礦泉水給她,她也接了,默默喝著。我給她老公打過電話說(shuō)過五分鐘到的,我們車到她家樓下的時(shí)候,他已經(jīng)在樓道門口等著了。我和董小如一起下了車,跟他說(shuō):“啊呀小陶,真不好意思,鬧到這么晚才送回來(lái)。”她老公說(shuō):“沒事,小如跟著張姐玩,每回都蠻開心的。”董小如在樓道的暗影里用平常跟我道別的語(yǔ)調(diào),高高興興地喊:“張姐,再見啊!”這回的聲音,像是高興過了頭,我聽得后背一陣發(fā)冷。
過了一周,又過了一周,董小如都沒有打我電話,倒是她老公小陶給我打了個(gè)電話,說(shuō):“張姐啊,你能勸說(shuō)小如這周別和你一起去杭州玩嗎,要么你們帶上我?這個(gè)周末正好是她生日呢,她說(shuō)回來(lái)再過。遲了的生日,再過,有什么意思啊?”我愣了愣,猛想起汪局昨天有意無(wú)意跟我說(shuō)要去杭州看煙火大會(huì),我掙扎了一下,馬上打起精神說(shuō):“你還是把小如借給張姐吧!煙火大會(huì)的票子,我好不容易弄到兩張,難得的呢。你們天天膩一起的,我就借一天還不行么?”放下電話,我一陣惡心。
第二天上班的時(shí)候,我把這通電話和我的回答都復(fù)述了一遍,汪局聽著笑了:“這小陶,還會(huì)來(lái)手反調(diào)查啊?那就委屈你這周末呆在家里別出門了吧。”我也對(duì)著他笑,說(shuō):“董小如頭一次到我辦公室來(lái)就嘲笑我是千年老二,她這一向沒在你面前笑話我吧?”汪局收了笑容,說(shuō):“她說(shuō)她再也不想見你了,我勸也勸不好。都怪我。你的事,你放心好了,我都會(huì)弄好的,本來(lái),也是應(yīng)該弄好的,我不過是順?biāo)浦邸!?/p>
董小如果真沒有再來(lái)找我,倒還是小陶有一次打電話來(lái),說(shuō):“張姐,小如升職宴,她這兩天忙,叫我打電話。”我沒等他說(shuō)時(shí)間地點(diǎn),先就說(shuō):“我不是和小如說(shuō)了嗎?那天我正好老家有客人來(lái),走不開的,以后我單請(qǐng)吧!”
零零星星地,汪局會(huì)跟我說(shuō)些董小如的喜訊,總之,是順風(fēng)順?biāo)N夷兀菜闶欠隽苏?dú)立主持一個(gè)部門,處處覺得累,反倒懷念起做千年老二的時(shí)光。真的,以前我心里坦蕩,吃得下,睡得著,面色純凈,現(xiàn)在色斑一天天多了起來(lái),照鏡子的時(shí)候,我都不敢正眼看自己,就是在不得不對(duì)鏡梳妝的時(shí)候,我都眼神閃爍。
鏡子是唯一能與自己面對(duì)面的地方——你說(shuō)說(shuō)看,還有別的地方嗎?而我,對(duì)鏡中的自己也能視而不見,即便是刷睫毛膏這樣需要小心觀察的事情,我也能順手做來(lái),不費(fèi)眼力。垂頭在KINDEL上讀書的時(shí)候倒是越來(lái)越多,《紅樓夢(mèng)》被我翻來(lái)翻去,聚會(huì)啊看戲啊,這樣的章節(jié),我看得最投入,它們是戲中的戲,虛中的虛,能把我忽忽地吸進(jìn)去。
(責(zé)編:王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