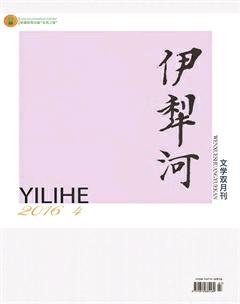大雁落腳的地方
小時候,媽媽偶爾說,你生在新疆巴彥岱。只聽音,不知是哪幾個字,在幼稚的心里,就以為是“八煙袋”,恍惚中覺得那地方是一塊曠野,有很氣派的大煙袋碼成一排,八柱裊裊的白氣上升。
我半歲時隨父母到北京,在城墻里長大,再哪兒也沒去過。人只道鄉下的孩子易孤陋寡聞,其實京城的人于外面的世界,也一樣模糊,對荒遠的邊疆地理知識幾乎是零。幾十年前,西北是遠在天邊的概念,那八個煙袋,誰知在哪個犄角旮旯冒煙呢?
于是巴彥岱又濕又重地扎入我的童年記憶,像沉入墨水瓶底的一支藍羽毛。
參軍學了醫,自從懂得了生理解剖生命起源,我對出生地空前地重視起來。我們從哪里來?這是一個永恒的命題。無數學者望洋興嘆,終生尋覓,不得其解。這個深奧的哲學問號,若從醫學角度來說,倒是易如反掌。你的母親孕育你的過程,她行走的地方,吃進的食物,飲入的清水,看過的流云,聽到的小調……這些物質的精神的元素,累積著架構著混淆著鑲嵌著,一秒秒一天天地結晶了你。
你就是你,不是其他的葉子和花,不是豬馬羊和狼,不是沙粒和谷子,這其中一定有大邏輯。生命之所以奇異,在于一個個零件的精致組裝。把那些新鮮的血和肉搭配起來的主宰者,是一個多么能干而霸道的調酒師啊!想想看,即使是稱為你父親的這一個男人,和被稱為你母親的這一個女人,在這一個特定的時刻孕育了你,如果不是在這一個特定的地域,用當地的特產充填了你生命的輪廓,你也必定不是此番模樣。
我們挺拔的骨骼,來自那里飛禽走獸體中的鈣和磷。我們明澈的目光,來自那里田野中綠纓垂地的碩壯胡蘿卜。我們飄揚的發絲,來自那里山巒上烏云籠罩電光石火的黑夜。我們紅潤的嘴唇,來自那個鐵匠鋪里熊熊燃燒的烈焰……
出生地是一枚隱形金箍,出生的那一瞬,它就不動聲色地套在了每個人的頭上,叫你終生無法褪下。我們嗅到的第一縷空氣,是那里的草木釋放。我們喝到的第一滴甘泉,是那里的巖石沁出。我們看到的第一眼世界,是那里的風云變幻。我們聽到的第一聲響動,是那里的萬物呼吸……
我開始纏著母親,講我出生的故事。母親的記憶如雨中磚地上的紅葉,零落但是鮮艷潔凈,脈絡清晰。她說,你出生在新疆伊寧,那是一座白楊之城。那里的白楊不像內地的白楊,有許多幽怨眼睛。那里的白楊沒有眼睛,每一棵都像銀箭,無聲地射向草原無邊無際的天空。
母親說,我出生在秋天,父親在遠方執行任務。母親說,部隊里成了家的男人和女人,平日都是分開住的。惟有到了節日,才是團聚的時刻。母親說,大禮堂里,拉上許多白布簾子,分割成一個個獨立小屋,那就是軍人們的臥室了。母親說,節日的黃昏,女人們早早就躺下了,在四周雪白的布籠中,悄悄地等待自己的丈夫。母親說,夜深了,查哨歸來的男人們,像潛入敵營一般,無聲地在白布組成的巷道穿行,走到自己的屬地,持槍的手,像雄鳥的喙一樣銜開白簾,溫暖地滑翔進去。
母親說,部隊里的孩子,就孕育在白布簾子背后,如果從禮堂的房頂看下去,那些布做的田野和畦,和如今冰箱里儲藏冰水的塑料格子差不多。我忙問,我是那樣來到的嗎?母親說,不是。因為職務,父親和母親享有一棟古老的俄式木屋。它高大涼爽,有寬寬的木廊。惟一美中不足的是,不知建于何年何月的地板,每當你腳步穿過的時候,就會和著你的節奏簌簌抖動。
母親說,懷你的時候,父親率領騎兵,要去遠方。他把照顧母親的擔子,交給一個年長的警衛員,名叫小胖子。母親說,那個兵,大約有四十歲吧?現在沒有這樣老的兵了,那時有。幸虧他的年紀比較大,要不這個世界上,可能就沒有你了。
母親說,整個懷孕期間,她完全吃不下尋常的食品,聞什么都吐,體重銳減。醫生說再不補充營養,大人孩子都危險。小胖子很著急,他是四川人,會做飯,殫精竭慮地把能夠想出的吃食,因陋就簡地做出來。盛在大粗碗里,端上來讓母親聞聞,看哪一樣能吃得下去。母親對所有吃食,都大饑若飽,置若罔聞。終有一天,母親嗅到一縷奇異的香味,不覺食欲大動,問小胖子,你吃什么呢?能不能讓我也嘗嘗?小胖子說,我在喝野鴿子湯。
在俄式木屋不遠處,有一座廢棄的糧倉。糧倉高而窄的窗戶,像古堡的透氣孔。每天早晨,小胖子打開窗戶,然后就忙自己的事去了。糧倉的地上,散落著陳年的霉谷粒,糧倉的每一寸墻壁,都蒸發著糧食干燥熏香的氣息。鋪天蓋地的銀灰色野鴿群飛來了,從窗口魚貫而入。到了夕陽傾斜的辰光,小胖子突然從墻外關閉窗戶,使糧倉沒入黑暗。然后揮著一把大掃帚沖入門內,旋風般撲打,鴿羽紛飛……
懷你十月,我只吃了不到十斤的大米和一點野菜。剩下的營養,全靠野鴿子湯支撐,母親很嚴肅地說。
我追問道,您一共吃了多少只野鴿子啊?
母親想了想說,一天少說也有十只,幾百天算下來,總有幾千只了。
我大驚,憤憤地說,您也太能吃了。要是綠色組織知道了,會對您提出抗議的。
母親糾正我說,不是我能吃,是你能吃。一生下你,我就再也不吃野鴿子了。
不管怎么說,這數字也大得可怕,我最多只能承認自己是1000只野鴿子變的。
一想到自己平凡的生命之弦上,掛著千只野鴿,墜得心緒彎出弧形。1000對鴿翅,將是怎樣一片掠過蒼穹的翠藍的云?1000只鴿鳴,將是怎樣一曲繚繞云端刺入肺腑的歌?1000雙鴿眼,將是怎樣一束眺望遠方洞穿云霧的光?1000堆鴿羽,將是怎樣一片潔白的雪能融化萬古寒冰?假如我這一生虛擲光陰,對不起造化,對不起自然,對不起我的父母,也對不起架構我生命的羽翼豐滿飛翔不息的千朵生靈!
母親臨產的時候,父親從營地騎馬趕來。母親已住進蘇聯人開的醫院,躺在產床上,輾轉反側。病房不讓父親進去,父親只好在醫院病房的窗戶上,久久地凝視著母親。然后,一揚鞭,飛身上馬,再赴疆場。
你第一次見到你父親,已經是滿月后。那時,你已是一個大孩子了。母親說。
然后,父親又走了。母親抱著我,住在古老的俄式木屋。夜里我愛哭,母親就徹夜抱著我。母親膽小,不敢點燈,就在漆黑的夜里,守我到天明。門口有一棵小榆樹,樹影在夜風里,像鬼魅一般伸縮著指爪。
無數次的講述歷史之后,我對母親說,咱們回一趟新疆吧?去看木房子、小榆樹和野鴿子。
媽媽漫聲應著,幾乎不抱希望地說,好啊好啊。只是新疆太遠,伊寧太遠。
對話埋在土里,好像古墓中的蓮子,酣睡著,不知何時才會綻成花?
1997年夏秋,我和母親同赴新疆,以結夙愿。母親已近70高齡,當汽車翻越天山的時候,我十分緊張。那是一條年久失修的戰備公路,已很少有人走。一邊是壁立的猙獰懸崖,一邊是千尺深淵。山頂的冰川,在炎熱的8月,融化成無數道淋漓的小溪,從峰頂汩汩墜下。
我悄聲對母親說,您害怕了?母親說,有一點。我說,您當年從伊犁離開去北京的時候,難道沒有翻越天山嗎?怎么倒好像是第一次看到這種險峻呢?母親說,那時,我懷抱你,沒有看過一眼山,我一直在看你。
汽車駛近伊犁的時候,心怦怦跳,我對自己說,一定要大睜著眼睛,把記憶變得像一卷新錄像帶,事無巨細都拍下來,留著以后慢慢回味。
然而竟像中了蠱,睡著了。叫醒我的是一個猛烈的顛簸,已到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的首府伊寧市中心。滿目是青蒼的綠,高聳入云的綠,劍拔弩張的綠,煞煞作響的綠——高大矗立的伊犁楊!不長憂郁眼睛的伊犁楊!耳邊聽到母親喃喃說,都認不出來了啊,哪里是當年的老房子?在伊犁的日子里,母親第一個也是最后的愿望,就是找到她和父親住過的地方。我本來以為這不很難,就算地表建筑有了相當大的變化,但山川依舊,地名還在,只要踏破鐵鞋,還怕找不到嗎?
然而,我錯了。伊寧發生了太大的變化,從母親茫然的眼神里,我發現她記憶中的伊寧,仿佛是另外一個星球上的地方,同這方土地不搭界。赤日炎炎下,母親說,那時漫天大雪啊,我坐著雪爬犁……我懷疑都是這季節鬧的,大約應該在隆冬來。白雪的城市和青楊的城市,永遠無法重疊。
我幫母親梳理頭緒。母親說,老房子的周圍有一家飛機場。我想這是一個顯著的目標,《伊犁河》的編輯熱誠相助,第二天一大早,帶著我們直奔機場而去,繞著機場轉了三圈,不想母親對那里的地形地物毫無反應,說,房前還有一條河,房后還有一座山,這里一馬平川,不是啊不是。我說,機場嘛,當然是平的了,也許是修機場的時候,把山平了,把河填了?
母親不置可否,看得出,她不信服我的解釋。找來機場的工作人員,向他打聽這里原先的地形,以證明我的猜測。沒想到他肯定地說,這里沒有山,也沒有河。從來沒有。我看,老人家說的那個機場,不是我們這個機場。你母親五十年代初期就離開伊犁,那時這座機場的圖紙還沒畫出來呢。
于是有了老機場的懸念。
我們又驅車去巴彥岱。這是一個赫赫有名的地方,幾乎每個伊犁人都知道,但當我細究這地名是什么意思的時候,又誰都說不清楚。
巴彥岱是一個小鎮,我們的車緩緩駛過,好像在檢閱路旁古舊的土屋和新的建筑。我不斷地問母親,是了嗎?想起一點了嗎?母親總是漠然地搖頭。
新疆小鎮特有的十字形短街,很快就被車輪丈量完了。往回開,再走一遍。我對司機說。正在修路,地表的積土和曬干的驢糞,化作旋風樣的灰塵,快樂地裹挾在車的后方,像赭黃色的陳舊面紗,把巴彥岱半掩半藏,母親索性走下車去,期望巴彥岱的土地,會直接告訴她點什么。母親的遲疑已經延展為沮喪。我的記性真的這么糟了嗎?不對啊,我怎么一點也想不起來了?就算房子被拆了,山也被削平了嗎?還有那條河?河邊的柳樹呢?母親低聲自語,憤憤不平。
四周悄悄,母親已經離開這里44年了,沒有人負責回答她陳舊的問題。我妄想開動我的直覺,像獵狗一樣四處巡視。但是可悲啊,我的神經末梢,對這片蒼翠的原野,毫無反應,同一路上翻越天山跋涉北疆所見過的任何相似景色一樣,只是淡淡地欣賞。
我決定放棄尋找,不論是巴彥岱還是八煙袋,這樣對她老人家的壓力可能輕些。我說,有很多歸國的老華僑,都找不到自己的家。不是您記性不好,是這個世界變化太快。
母親不理我的油嘴滑舌,繼續苦苦地凝視巴彥岱。一車人都跟著焦急,我于是拉著母親走到一處風景秀麗的小渠,對隨行的記者說,麻煩您給我和母親合張影。這里就是巴彥岱。
母親不服,說,你那時什么都不記得,憑什么說這里就是巴彥岱?
我說,您倒是記得,可您的巴彥岱在哪里?這里怎么就不是?為了更有說服力,我攔住過路的一個穿袷袢的維吾爾老人,問,這里嗎,叫什么名字?
那老人漢語不很通,瞇著因為老而變作灰藍的眼珠看著我,不答話。我干脆直奔主題,用手在身旁畫了一個大圓,然后說——巴彥岱?
他好像遇到故知,快樂地重復:巴彥岱、巴彥岱!
我面對母親,怎么樣?這里就是巴彥岱。
于是我和母親,在我所指定的我的出生地,照了幾張相。平心而論,四周景色不錯。草原在午后陽光下灼熱地呼吸,波光粼粼,猶如晃動著自九天而下的玄紫色紗幕。腳旁的小草,像無數神奇的吸管,把蒼黃大地的水分,變成了綠色油漆,不慌不忙地涂抹在自己向陽的葉面上。也許是顏料不夠,葉子背面就比較馬虎,涂得清淡些,露了霜白的底色。野花英勇地高舉著花莖,把小小的花盤,驕傲地進裂到近乎水平的角度,竭力把自己的美麗一面展示出來。好似一個細胳膊的小伙子,一往情深地仰著臉,向藍天求愛。雖結局不一定樂觀,仍充滿了令人感動的柔腸。
我很中意此地的風景。母親不再吭聲,那神情分明在說,這里雖然好,但不是你出生的地方。
回宿處的時候,母親說,你出生的那家醫院,總是應該能找到的。她的神氣很執著,好像已被我摻進一個贗品,這家醫院一定要貨真價實。
那家醫院還在,但已改造得面目全非。眼前是和普通醫院一樣高大而四通八達的主樓、熙熙攘攘的愁眉苦臉捏著藥袋的雜色人流和飄逸的白衣。我和母親在藥氣汗氣中穿行,問一個護士,這個醫院當年的婦產科在哪里?那個護士匆匆走著,一邊走一邊丟著話,你要問現在的婦產科,我告訴你。要是問原來的,誰知道?
連續問了好幾個人,都被干脆地回絕。母親一臉的茫然,也許昨天我的指鹿為馬刺激了她,她不愿再無望地尋找,對我說,我們走吧,即使找到了醫院,也找不到你爸爸看我的那扇窗戶了。
我便依偎著母親,慢慢向醫院的大門走去。就在這一瞬間,千真萬確地,我聽到血脈深處劇烈的嘆息,心被攥緊又松開,痛得窒息。
我果決地對母親說,請隨我來。不由分說地牽了她,向一個我也說不清的方向,義無反顧地走去。
人很多,不停地碰撞,我疾速穿梭,不住口地說著對不起,宛若行進在曠野雜草間。碰到的人不再有鼻子有眼睛,只是一些木樁。七折八拐,在厚厚的樹叢之后,看到僻靜處有一棟老木屋。
它在綠籬中蹲踞著,好似千年蘑菇。自屋頂沖刷而下的杏色雨跡,仿佛歲月的鞭痕,略有彎曲,在木疤處拐了個小彎,依然執拗地向下。
我的血翻起泡沫,激烈地鼓蕩著。看——就是那扇木窗!我握著母親的手大叫。那一刻,感到彼此的肌膚,在盛夏里冰冷如雪。
墻壁上有一扇木窗。木窗和它寬大的窗臺,漆色斑駁地幽閉著,鎖定四十五年前一位戍邊的將士和最初的父親久駐的目光。
是嗎?是這里嗎?母親輕聲反問著,伏在窗欞上,處處撫摸,好像那里還遺有軍衣的擦痕。俯身比量著詢望屋內的角度,好像父親的視線,還如探照光柱一般,筆直地懸浮空中。許久,緩緩的說,正是從這個地方,你爸爸他第一次看到你……
我僵僵地立著,感覺時光順流與逆流的波紋。
還需確認。無人知曉數十年前此地的格局。終于找到一位維吾爾族老人,捋著飄拂的白胡須說,半個世紀以前嗎,這里是蘇聯人開的醫院。后來嗎,都拆了,蓋了新的樓了。現在嗎,只剩這最后的屋檐,原先是專門接娃娃的房……
我長久凝視窗戶,時間隧道,一身戎裝的父親,牽著他的戰馬,屹立遠方。
母親說,連我都認不出的地方,孩子,怎么就像有絲繩拽著,你一下走到這里?
我說,媽媽,不要忘了,我也來過這里。在我的記憶深處,我記得這條路。這里是我第一眼看到的世界。從這扇木窗中,我認識并記住了父親的微笑。
到了臨離開伊犁的前一天,母親有些不好意思地對我說,我還想找找那座老房子。我說,還去巴彥岱嗎?母親說,不了。就讓車在伊寧街上隨便轉吧,也許突然就看到了,也說不定。
我實在不知如何再向主人提出要求,為了老房子,我們已麻煩人家多次。但伊犁州公安局的李局長說,老人家來伊犁不容易啊,今生今世也許最后一次了。說什么也要找到這個地方。于是他派出了局里最有經驗的偵查員,幫助我們。
老王瘦而干練,目光鷹隼一樣銳利,像搜索逃犯一般,開始詳盡地了解情況。
您敢肯定門前那是一條河,不是一條渠?新疆的渠溝很多,有的也很寬,波濤滾滾的。老王抽著莫合煙說。
是河,因為它是彎彎曲曲的,人修的渠是取直的。岸邊有很粗而疙疙瘩瘩的樹,老樹,樹葉落在水上。母親說。
您的記憶很肯定,附近有一座山?
小山,不高。肯定有,在河的北面。母親說。
老王站起身來,說咱們走吧。我已經知道那大概的方向了。
我和母親半信半疑地跟著老王上了車,他對司機低語了一聲,車就飛快地沿著白楊大道駛去。
到了一處疏朗的房舍,周圍有不濃不密的林子,地面有些殘存的鵝卵石,像半睜半閉的疑惑之眼。
其后發生的事,恍若慢鏡頭。母親一躍下了車,踢著那些鵝卵石,飛快地向遠處的房舍走去。我想緊跟上,老王示意我拉開距離,以給母親一個獨立回憶的空間。于是放她蒼涼地一人走向往事,我們默默地跟隨。
母親舉步如飛,跑到一所孤獨的木屋旁,目光如啄木鳥,從地基敲到檐頂,然后又一寸寸地鑿下,好像要把那些木欞中的年輪剝出來。
我以為母親會說什么,結果她什么也沒說,就倒著身子,退開了。我忙湊過去,沒想到她又疾步走上前去,我緊跟,聽到了她對木屋說的話——你怎么比原來變矮了?哦,是了,我們都老啦!
母親拉著我的手,登上木屋的臺階。那臺階吱吱扭扭響著,這聲音親熱地召喚母親,從她的耳鼓潮水般地蔓延開去,擴展到整個身心。
這是一座說不上年代的俄式建筑,當年不知漆過何種顏色的油漆,現在已完全脫落,連綠豆大的一點遺跡都不曾留下。
每一寸木紋都裸露著,好像森林老人住的原木房子。高高的挑檐,抗拒著歲月的磨損,依舊尖銳地飛翔著,幾乎把草原湛藍的天空刮出傷痕。檐口的滴水槽已經殘破,水線蜿蜒,好像一把用舊的木锨還牽著淋漓的泥漿。屋頂上小塔式的煙囪半邊坍塌,露出被壁爐焰火熏黑又被風雨漂白的栗色。懸山的邊緣已成鋸齒,惟有山墻像倔強老人的脊背,昂然挺立著。陽臺的欄桿,有美麗的螺旋狀絲紋,不可思議地保持著精致的形態,透出當年的華麗。游廊很寬敞,木地板由于多年無數雙鞋的摩擦,生出短而茸的木刺,在舒緩的木弧中被浮土半遮半掩。
一把大鎖禁錮著歷史。母親緊張地扒著門縫向里張望,如同孩童。老王不知用了什么辦法,找來一個全副武裝的士兵,開了門。原來這里和半個世紀以前一樣,是軍隊的產業。
木屋的中央是氣勢宏大的客廳,雖堆滿雜物,仍看出往日的磅礴。四周是布局嚴謹的小房間,年代久遠,已察不出主人修造時的匠心。我們在灰塵中走動,攪起嗆人的煙塵。母親的目光如蛛網一般,打撈著游動的往事。她一定是看到了我所無法窺視的影像,與那時年輕的自己對話。
你好啊!老房子,我來看你來了。你還記得我嗎?這就是當年那個愛哭的孩子啊!我們一道從北京來看你,你還記得我們嗎?母親拍打著積滿青灰的欄桿,對著空中自語。
我和母親拉開一米遠近,怕驚擾了她的思緒。沒想到母親執意拉著我,好像面對久久不見的親戚,不停述說——那里,就是我睡的床,抱著你,坐在床上。那些夜晚,總也盼不到天亮……她指著一個堆滿軍械的角落—那里,就是小胖子煮野鴿子湯的地方。她指著回廊的拐角處。你該叫他小胖子叔叔的,要是沒有他的好心,這世界也許就沒有了你。他如果還在世,該有八十歲了——那里,就是整夜搖晃的小榆樹啊,天!它長得這么高,成了老榆樹了……她指著窗口處的樹枝,我眨眨眼,看到那樹應聲彈下幾斑蒼涼的綠淚。
木地板在我們的腳下波動。我問母親說,它們是不是晃得更厲害了?母親說,沒有,它們和以前一模一樣。真奇怪。哦,對了,人是熬不過木頭的。
那位開鎖的士兵,從我們的對話中,明白了原委,恍然大悟道,啊,我知道啦!你們想它了,就從北京趕來看它。你們來得正好,再有一個星期,它就被卸成一堆木板。
在城市建設的整體規劃中,已幾次動議拆除這老屋,不料每次臨動手的時候,就出些意外的變故,阻止了工程。這一次,推土機已備好,再不會拖延了。
呵,我明白了。老屋一直在等著我們,等著母親布滿褐斑的手最后的撫摸。等待當年的孩子,再看一眼它斑駁的木紋。
老王后來告訴我,50年代,貫穿伊寧市的河流只有兩條,背后依山的就是這條河。后來,城市變遷,山被砍平,填了河床,地表上的舊貌已杳無音訊。此地原來確屬巴彥岱管轄,但行政區劃幾經變更,如今已歸屬市區,難怪母親在巴彥岱尋不到了。
我們依依不舍地告別老屋,我從搖曳的榆樹上摘下幾片樹葉,從地上掬了一拯黃土。我會把它置于父親的墓前,我猜他會在有月亮的晚上,輕輕地聞著樹葉,用手指捻著黃土紛紛落下。父親一生戎馬生涯,他眷戀他騎馬挎槍走過的地方。
母親安寧了,好像同我交割清了生命的最后一筆賬目,我卻接過一副沉重的挽具。你已知道生命的源頭,你不由得張望生命的盡頭,心中惴惴。當你有朝一日,一切歸于永恒,背負黃土,仰望星空,檢點一生:畢淑敏啊,你可對得起三千銀翅、一蓬綠陰、古舊的木紋和一個名叫小胖子的老兵?!
離開新疆前,我應邀做了一場講演。主題發言以后,我說,我有一個私人問題,求助大家。我出生在伊寧巴彥岱,我不知巴彥岱是什么意思?誰能幫我解答?不一會兒,紙條遞上來了,說: “巴彥岱是蒙古語,意思是——大雁落腳的地方。可惜大雁落腳又飛走了,你何年再回新疆?”
我一時熱淚盈眶。新疆是我生命的始發站,只要我還在天際運行,無論飄到何方,都會像彗星回歸。
又傳上來一張標著“新疆大學”的紙條,上書:“我們幾位伊寧人,想把自己的家騰出來,為你建一間文學館。讓天下的人們都記得,伊寧出了個你。”
我沉吟,為著家鄉人的熱忱。半晌,我說,畢淑敏何德何能,能承受伊寧人的如此盛情?我的老鄉們,聽我一句話,自家的房子,還是好好裝修,住得寬敞一些為好。如果實在空閑,就開一個小飯鋪,賣手抓羊肉和伊犁草原上的馬奶酒吧!那是天地的精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