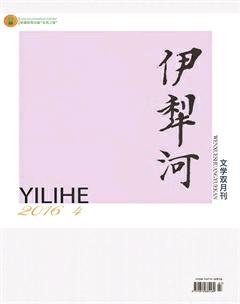那個(gè)夏天
趙勤
肖莉莉是個(gè)怪人,自從離婚以后的這幾年,我覺得她越來越怪。
有個(gè)段子說,給女人介紹對(duì)象,二十歲的女人會(huì)問長得帥嗎?三十歲的女人會(huì)問有錢嗎?四十歲的女人最直接,人在哪里?偏偏肖莉莉是個(gè)例外,三十八歲還在單身的她既不關(guān)心外貌,也不在乎是否有錢,甚至不是那么著急見面。
周六中午的上島咖啡,人不多,音樂聲音低低的,冷氣開得足。這個(gè)微胖的男人發(fā)際線高,頭發(fā)有點(diǎn)少,手里握著刀叉進(jìn)餐時(shí),尚還自信。侍者撤掉餐盤后,他就有點(diǎn)不自在。坐在對(duì)面的肖莉莉不看男人,也不看旁邊的我,大談中醫(yī)養(yǎng)生,說什么腎主毛發(fā)……
看著對(duì)面這個(gè)可憐的男人不停地拿紙巾擦額頭上的汗,這讓他顯得更加局促不安,我知道這次的見面又是沒有結(jié)果的。
主要原因不在肖莉莉不好,她是太好了,人長得好,嫻靜又干練,文雅又知性,在外企干財(cái)務(wù)工作,收入豐厚,還一直在資助著一對(duì)孤寡老人,總之她一身優(yōu)點(diǎn)就是找不到男人結(jié)婚。要說也不是找不到,喜歡她的男人也很多,剛才8號(hào)男人還在給我電話,想讓我再撮合一下他們。我是喜歡肖莉莉,真想和她結(jié)婚的,你再給她說說吧,電話掛斷前,他是帶著哭腔給我說的這句。我把帶她見過的男人,按見面的早晚,相處的時(shí)間長短排了個(gè)隊(duì),肖莉莉見過的男人實(shí)在太多了,為了不至于弄混,我想出按號(hào)碼稱呼這個(gè)辦法。
這個(gè)8號(hào)男人是我同事的哥哥,喪偶無孩,做藝術(shù)品拍賣行生意,也是個(gè)成功男士。見過面對(duì)肖莉莉很滿意,后又交往了小半年時(shí)間,郎才女貌的一對(duì),我曾經(jīng)很看好這個(gè)8號(hào),可是肖莉莉?qū)λf斃就斃了。認(rèn)識(shí)她快三十年了,我懷疑她根本不像她給我說的那樣,她根本不想結(jié)婚。
肖莉莉是我的中學(xué)同學(xué),我們一起重讀過,共同度過了那段灰暗的少女時(shí)代,這使得我們倆的友誼比別人要特殊一點(diǎn)。后來雖然我們大學(xué)沒有在一個(gè)城市,但畢業(yè)后都回到了烏魯木齊。這些年同在一個(gè)城市生活,因?yàn)橄嗤某砷L背景,也因?yàn)槎际浅鞘械募木诱撸谶@個(gè)城市都沒有根基,我們是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好的知己。我們有太多的相似之處:她離婚,單身,沒有孩子,而我雖然結(jié)婚多年,可是李濤經(jīng)常出差,加上我們一直沒有要孩子,使得我也像半個(gè)單身,總之我的過去和她的過去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也許是這些個(gè)原因,我和肖莉莉關(guān)系甚好。
微胖的男人終于坐不下去了,他說還要去單位加班,肖莉莉和我都沒有挽留,他終于匆匆忙忙地先走了。
你都已經(jīng)單身那么多年了,快要四十的人了,不找個(gè)男人過日子,什么才是合適的?其實(shí)無論你找了誰,到最后都是過日子這么簡單,不要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
反正我現(xiàn)在沒有強(qiáng)烈的結(jié)婚愿望,我覺得我還沒有長大到必須要結(jié)婚的年齡,她說。
姑娘,你還沒有長大,你都是資深少女了,我說。
關(guān)于戀愛和結(jié)婚的話題,我們的談話總是這樣進(jìn)行不下去。我其實(shí)是希望她有個(gè)正常的生活,我覺得她的生活不正常,在我的印象里,迄今為止她都沒有一場(chǎng)像樣的戀愛。
周末的早上,肖莉莉不由分說把我拽出來,一定要我陪她去前山鎮(zhèn),說是要去看一位老朋友,一位已經(jīng)故去的老朋友。
前山鎮(zhèn)是我和她出生的地方,離烏魯木齊三百多公里,是一個(gè)被沙漠戈壁灘包圍的小鎮(zhèn),在地圖上都找不到這個(gè)名字。這么多年過去了,我們的父母都遷出去了,她已經(jīng)七八年都沒有回去過了,她還有什么老朋友在那里,還是故去的老朋友?我覺得奇怪,但沒有問她。她行事一向有著特立獨(dú)行的特點(diǎn),我曾經(jīng)暗自揣測(cè),可能和她離婚后一直單身有關(guān),這是個(gè)敏感的話題,我盡量不碰,但她大體還是靠譜的,要不我也不會(huì)和她那么多年都是好朋友。
我們來到前山鎮(zhèn)四小隊(duì)的時(shí)候是正午。
壯闊的一片棉花地,一眼望不到邊。正午的陽光下,棉花葉子綠油油的,一陣風(fēng)吹過,巨大的“嘩啦嘩啦”的聲響在耳邊,像是松濤,又像是呼喊聲,心里極震撼,卻又說不出任何話來。
這里曾經(jīng)是我們讀高中的學(xué)校,只是已經(jīng)過去了二十多年,以前的教室、操場(chǎng)、宿舍、食堂都不在了,都變成了一望無際的棉花地。
我站在田埂上,感慨萬千地看著壯闊的棉花地,肖莉莉一言不發(fā)地沉默著,她帶著我走了一段彎彎曲曲很長的小路,走到一處稍高一點(diǎn)的緩坡處停了下來。緩坡四周長滿了草,靠著左邊有一處小土堆,像個(gè)墳冢,上面也長滿了青草。她圍著小土堆走了一圈,拔了拔土堆上的蔓草,又從隨身帶的包里拿出些蘋果和梨,一個(gè)一個(gè)擺在土坡上。土里埋著誰?她沒有說話。我只能暗自猜測(cè),地下的人和她是什么關(guān)系?認(rèn)識(shí)她這么多年,最近我卻有種需要重新認(rèn)識(shí)她的感覺。
她擺完水果,又掏出煙來,點(diǎn)上一支,吸了兩口,插在土里。做著這些事時(shí),她臉上是肅穆的表情,我不明就里,可是面對(duì)此情此景卻不由跟著她心情沉重起來。
我們?cè)谕炼亚翱偣惨簿痛袅税雮€(gè)多小時(shí),又開車去鎮(zhèn)中心轉(zhuǎn)了一圈,和二十年前變化太大了,我已經(jīng)完全不認(rèn)識(shí)了,以前的鎮(zhèn)中心就是一排小平房,沿街的就是鋪面,買些日常生活用品,大白天也沒有多少人。如今的鎮(zhèn)上樓房林立,五六條街縱橫交錯(cuò),不寬的馬路上小商小販擠擠挨挨的,叫賣聲、小孩子的嬉鬧聲不絕于耳……我感慨著變化之大,世事的滄桑。肖莉莉沉默著,沒有說話。
我問她要不要聯(lián)系在這里的同學(xué)見個(gè)面,一年前高中畢業(yè)二十年同學(xué)在烏魯木齊聚會(huì)時(shí),我被選為副秘書長,我有完整的同學(xué)通訊錄,在前山鎮(zhèn)還有五個(gè)同學(xué)。她說不要聯(lián)系了,她要辦的事情辦完了,我們這就回去。
回程的路上,她沒怎么講話,好像專心在開車。眼前掠過的風(fēng)景都是模糊的,我的心回到了從前。
想什么呢,那么出神?她問。
哦,在想高考前的那一段時(shí)間,又想起“女高音”——教英語的李老師,她是我噩夢(mèng)的女主角。我對(duì)英語的恐懼和她連在一起,一想起她就讓我想起英語,一想起英語,我馬上就能想到她說話的樣子,她的尖尖的嗓音,我說。
你還沒有忘記她啊,恐怕她早就想不起來你了,如今她也應(yīng)該有六十多歲了吧,她說。
人生就是這個(gè)樣子,你念念不忘的,也許在人家只是一個(gè)模糊的曾經(jīng),我暗自感慨人生的無常。
車上放著齊秦的那首《直到世界末日》,這是我們上中學(xué)時(shí)愛聽的歌:
如果世界末日真的有審判
所有人類剩我們兩個(gè)
不管付出任何的代價(jià)
我愿為你釘上無悔的十字架
不要怕啦……啦……啦……
一直到世界末日等你回答
士兵們放下他們的槍
頑皮的孩子收起了翅膀
憤怒的火山停止喧嘩
異常的平靜埋伏著多少不安
風(fēng)暴漸漸升高大地開始動(dòng)搖
我在風(fēng)中呼喚你聽見了嗎
別在世界末日來臨之前
口中仍然隱藏著那句話
你愛我嗎
不要怕啦……啦……啦……
一直到世界末日等你回答
他們唱啦……啦……啦……
一直到世界末日等你回答
你還記得,那年高考前,我們班有個(gè)女生自殺了嗎,她說。
記得呀,那是個(gè)二連的女生,我們還去過她家地里拾過棉花。她好像是在學(xué)校旱廁被社會(huì)小青年猥褻,當(dāng)時(shí)學(xué)校里傳瘋了。我記得她瘦瘦的,瓜子臉,膚色白凈,左邊耳朵前面向下的位置有塊指甲蓋大的胎記,她總微微低著頭,齊耳的短發(fā)剛好可以遮住那塊微紅的胎記。
剛才的那個(gè)墳是她的,她是因?yàn)槲也潘赖模f。
她不是自殺嗎?
是自殺,但是因?yàn)槲也艑?dǎo)致她的自殺,她說。
高三重讀的時(shí)候,我和肖莉莉不只一個(gè)班,還是同一個(gè)宿舍,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件事情,我預(yù)感到她將要告訴我一個(gè)秘密。
雖然過去了近二十年,我還是可以清楚地記得那個(gè)教室在農(nóng)田邊上,幾排平房圍成了一個(gè)很大的四合院的樣子,我們的教室在最后面一排,教室的后面是寬寬的林帶,林帶再過去就是農(nóng)田了,地里種的是棉花,一望無際看不到邊。那個(gè)夏天是我迄今為止人生最灰暗的一段時(shí)間,我怎么能忘記呢。
肖莉莉的聲音變得有點(diǎn)壓抑的沙啞,這讓我產(chǎn)生了一種幻覺,給我講故事的人好像不是我認(rèn)識(shí)了近二十年的那個(gè)肖莉莉,而是一個(gè)陌生人。
一
那時(shí)候我經(jīng)常在清晨起來去背書,太陽還沒有完全升起來,紅彤彤的,但威力不大,涼風(fēng)習(xí)習(xí),校園里都是拿著課本念念有詞用功的學(xué)生,我喜歡在教室背后的林帶邊上背課文,那里人少。有時(shí)候我早起,也不是為了背課文,是為了去樹林邊走一走,林子里有蒲公英,開著黃色的小花,還有一種叫不上名字的植物,葉子很大,葉面不是光滑的,長著一層薄薄的、毛茸茸的細(xì)絨,折下來,斷裂的地方流出粘稠的、透明的汁液,聞上去有點(diǎn)腥香的味道。隨處走走,我會(huì)想一些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比如他。他很優(yōu)秀,學(xué)習(xí)好,籃球打得好。課間,我經(jīng)常會(huì)在他必經(jīng)的路上走過,可他沒有注意過我,一個(gè)學(xué)期過去了,我們連個(gè)招呼都沒有打一聲,他應(yīng)該從來不知道我的這個(gè)心思,而我也沒有對(duì)誰講過。閑逛的時(shí)間總是過得好快,上課鈴響起來的時(shí)候,我總是有點(diǎn)慌張,還沒有準(zhǔn)備好一天的心情。
在那個(gè)事情之前,我只和他有過一次接觸。第一次是一個(gè)周末的中午,我午睡起來,抱了一摞書去教室,太陽明晃晃的當(dāng)頭照著,睜不開眼睛,走在樹影稀疏的林蔭道上,快到拐向教室的那個(gè)小路口時(shí),迎面跑過來一個(gè)人,躲閃不及,撞了滿懷,書掉了一地,我跌坐在地上,半天都沒有回過神來,居然是李元展,他也趔趄了一下,停了下來。他身上有種混合著汗味的其他味道,不是臭味,也不是香味,是一種混沌的、曖昧的味道,我的大腦有短暫的眩暈。他滿臉的歉意,“對(duì)不起”說了好幾遍,手忙腳亂撿起地上的書遞給我,轉(zhuǎn)身就走了。
我是在他走后,看見剛才摔倒的地方有一粒灰色的玻璃紐扣,撿起來放在手心,還有溫度,不知道是體溫還是太陽曬的,我留下了它。
到現(xiàn)在我也說不清楚,當(dāng)初是怎么和李元展走到那一步的。每天都要背單詞,隨時(shí)都會(huì)抽考,還要排名,還要按名次去拿自己的卷子,我已經(jīng)學(xué)不下去了,可是還要學(xué),我就快要學(xué)瘋了。
有個(gè)周末,我沒有回家,我害怕聽到父母的嘮叨,害怕看到奶奶那張皺成核桃殼的臉,中午吃過飯我在宿舍睡午覺,聽到隔壁有人在敲男生宿舍的門,敲得山響。我起來打開門,看見是李元展,這讓我有點(diǎn)緊張,以致有點(diǎn)結(jié)巴。他說他來找隔壁的王明他們幾個(gè)打球。他們好像在教室呢,中飯吃完就沒有回宿舍,說完我低下了頭。李元展看著我問,去不去教室?我脫口就說一會(huì)去。說完連我自己都奇怪,我原本想睡午覺起來洗衣服的,怎么改主意了。他說他走了,在教室等我。
看著他走遠(yuǎn)的背影有點(diǎn)奇怪又有點(diǎn)歡喜。不是要去打球嗎,怎么又說要在教室等我,難道他知道我喜歡他?你知道,那個(gè)時(shí)候的喜歡,也是很單純的,只是喜歡看見他,看他打球,看他寫作業(yè),看他打掃衛(wèi)生……只要看見他在那里,就很高興。
我到教室的時(shí)候,李元展在玩鋼筆,他把筆拿在手上轉(zhuǎn)來轉(zhuǎn)去不掉下來,我看著他,他看著筆,轉(zhuǎn)來轉(zhuǎn)去的筆好像有了魔力,看得我有點(diǎn)暈。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到他跟前去的,也不記得當(dāng)時(shí)我們說了些什么。午后的陽光穿過窗戶玻璃照在課桌上,旋轉(zhuǎn)的鋼筆閃閃發(fā)光,他的聲音有種極大的催眠作用,事后怎么也想不起來,是怎么跟他去了棉花地。一切就那樣發(fā)生了。只記得當(dāng)時(shí)有一點(diǎn)疼痛,有一點(diǎn)害怕,可是又有點(diǎn)興奮,很混亂的感覺吧。很多年以后想起來,具體細(xì)節(jié)都想不起來了,只記得他走了以后,我一個(gè)人坐在空蕩蕩的教室里,一些說不清楚的緊張和漫長的空虛包圍著我……
你就是那個(gè)時(shí)候來找我的,你看見我在發(fā)呆,以為我生病了。你去宿舍端了滾燙的紅糖水來給我喝,你說肚子疼,喝了熱熱的紅糖水就好了。你拿手絹擦拭了我額頭上的汗,你以為是疼的,你同情地看著我。其實(shí)你不知道,那是嚇到了。具體害怕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就是怕得要命。當(dāng)時(shí)不害怕,是事后坐在教室里,才害怕的。
這件事有誰看見了,我不知道。當(dāng)時(shí)李元展先離開的棉花地,我走出來的時(shí)候看見了李元展在和一個(gè)叫豹子的社會(huì)青年講話,我低著頭從他們身邊走過,感覺到豹子的眼睛看穿了我,剝光了我身上的衣服。還沒有走到教室,有個(gè)女生叫我,是英語課代表吳琳,她騎著自行車,從東邊大路上過來,穿小路走,路過校園,看樣子是剛從地里回來,車后座上還夾著干活的農(nóng)具。她和我打招呼,問我周末沒有回家啊,我虛于應(yīng)付,不知道自己說了什么,就慌忙進(jìn)了教室。
自從發(fā)生了那件事后,在路上遇見李元展,我都不敢看他,低著頭快步走過去了。我和李元展卻是因?yàn)檫@件事生疏了,我們?cè)诼飞嫌鲆姡坏貌豢磳?duì)方時(shí),看到的都是對(duì)方躲避的眼神。
天氣越來越熱,高考的倒計(jì)時(shí)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每天逼近。摸底考試也越來越頻繁,有一次我考了全班倒數(shù)第十,去講臺(tái)上拿卷子的時(shí)候,我抬眼看了一下教室,正遇上李元展的目光,那里面有什么我不知道。放學(xué)后我在教室里坐著,李元展來到我的面前。
我已經(jīng)考疲了,怎么也學(xué)不進(jìn)去了,我說。他什么也沒有說,我們就那么坐了一會(huì)。后來我就跟著他去了棉花地……
這件事情一旦發(fā)生,就不好結(jié)束了,我們像是特工、地下工作者,在老師和同學(xué)看不見的地方約會(huì)。每次也沒有說什么,那種肉體關(guān)系,好像是彼此需要,又彼此扶持,是一種安慰又是一種毀壞。我不知道李元展怎么想的,在我是矛盾極了,我知道這不對(duì),可是我又渴望,完了以后又后悔。
二
在我的記憶里,那個(gè)夏天好像永遠(yuǎn)都在做題、考試、排名次。
那個(gè)夏天是我有生以來最熱的一個(gè)夏天,又悶熱又絕望。英語老師拿著考試卷子走進(jìn)教室,啪的一聲響,她用力地把卷子摜到講臺(tái)上,桌面上騰起細(xì)小的白色粉塵,嗆得我不由咳嗽了一聲,她用力看了我一眼,往前走了兩步,站在第一排中間,說話之前習(xí)慣地用手推了推眼鏡架:這次考試成績出乎我的想象啊,有人居然考了9分,9分啊,怎么做出來的,就是一頭豬亂填,也不會(huì)只考9分!女高音的震顫讓我耳朵發(fā)麻,我的頭都要低到桌子下面了,默念著不是我,不是我……就在我默念的空檔,廖梅,女高音在喊我的名字,在全班同學(xué)的注視下,我一步一步走到講臺(tái)上拿回來我的卷子,我真恨不得死掉算了,或者大地裂開一條縫,讓我掉下去好了。同桌胡小勇同情的看著我,他小聲對(duì)我說,你怎么搞的啊,全選,也不會(huì)只有9個(gè)對(duì)的啊!他不知道那種同情的目光可以殺死人的。從那以后我就死了,我的心死了。
老師進(jìn)行的是魔鬼般的訓(xùn)練,三天一大考,兩天一小考,考完還要排名次,上課發(fā)卷子的時(shí)候老師倒著念排名,第一個(gè)上去拿卷子的是倒數(shù)第一名。那時(shí)我天天都被單詞、考試、排名糾纏著。
我們五個(gè),我和肖莉莉還有三個(gè)男生都是從團(tuán)部一中留級(jí)過來的,插班在應(yīng)屆生的班里,沒有玩伴,我最好的朋友就是肖莉莉,那三個(gè)男生和肖莉莉?qū)W習(xí)都比我好,我是最差的一個(gè)。那時(shí)候我們住校,周五下午騎自行車回家,星期天下午再騎自行車回到學(xué)校。
宿舍和教室隔著一條馬路遠(yuǎn),也是一排平房,第一間是男教師宿舍,只有一個(gè)教地理的男老師,第二間是女教師宿舍,也只住了一位女教師,再過來是女生宿舍,然后是男生宿舍,然后是水房,再然后是學(xué)校的倉庫。
我們剛?cè)サ臅r(shí)候,教師的男女宿舍各住了一位教初中的教師,也就是半學(xué)期的時(shí)間,他們結(jié)婚了,女教師搬到了男教師宿舍里,他們的窗簾老是拉著,門框上也釘了一塊布簾,進(jìn)出開門看不見里面。
他倆很安靜地生活在我們隔壁。我在門前晾衣服,會(huì)裝作不經(jīng)意地瞄上幾眼他們的窗戶和門,我有點(diǎn)好奇他們?cè)诜块g做什么,但經(jīng)常是白費(fèi)心機(jī),那個(gè)門從來都是關(guān)著的,窗戶上更是什么都看不見。
肖莉莉說的那個(gè)女生,我有記憶是因?yàn)樗⒄Z學(xué)得很好,曾經(jīng)讓我羨慕和嫉妒。
她是英語課代表,每次收作業(yè)的時(shí)候,齊耳的短發(fā)一甩一甩的,那時(shí)候好像她忘了胎記,不怎么掩飾。她天生有語言的天賦,朗讀起課文來,聲音很好聽,發(fā)音很標(biāo)準(zhǔn),甚至比那個(gè)女高音的李老師還標(biāo)準(zhǔn)。
前兩年放映電影《金陵十三釵》時(shí),片子中那個(gè)叫墨玉的妓女和假神父講話時(shí),說的一口流利的英語,還讓我想起多年前的她,她和她有一樣的口音。
她喜歡李元展,這在我們來學(xué)校不久就知道了。李元展長胳膊長腿,學(xué)習(xí)好,籃球也打得好,有很多女生喜歡他。有時(shí)候放學(xué)后不回家,幾個(gè)男生會(huì)在校園的場(chǎng)地上打一會(huì),常常引得女生在一邊看,中場(chǎng)休息時(shí),只有她會(huì)大大方方地給李元展遞上水或者飲料。李元展接過水便喝,好像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其他女生也只是看看就散了,并沒有誰會(huì)做什么,那時(shí)候的喜歡很朦朧也很渺茫。
開學(xué)不久,學(xué)校安排學(xué)生干農(nóng)活,我們?nèi)ミ^她家拾棉花,她父親是個(gè)四川人,黑黑瘦瘦的,個(gè)子不高,總是擰著眉毛,一副苦大仇深的樣子,講話嗓門大,又總是說不清,嘟嘟囔囔的像是在吵架。他安排我們按照指定的位置拾棉花,挨著順序排,不能挑行。我們幾個(gè)人一字排開,低頭拾棉花,而她好像因?yàn)楦赣H的咋咋呼呼有點(diǎn)不好意思,沉默著不怎么說話。干活很有眼色,幫我們抬袋子,過秤,倒棉花,動(dòng)作熟練麻利,不像在學(xué)校里弱不禁風(fēng)的樣子,看來在家也是經(jīng)常干活的好手。
我因?yàn)槔钤沟木壒剩惨驗(yàn)榕⒆幽募刀剩低涤^察她,在背后打量她。可是她始終神情平靜,手腳麻利地過秤,報(bào)數(shù)字,倒棉花。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我在觀察她,或者知道故意做出平靜的樣子?
她爸爸總是大著嗓門喊叫她去干這個(gè)或者那個(gè),整個(gè)下午指揮得她團(tuán)團(tuán)轉(zhuǎn)。她的母親沉默著干活,聽見她父親大聲地嚷嚷,會(huì)抬起頭來,小心翼翼地看她父親一眼,臉上掛著歉疚的笑,有點(diǎn)苦相。現(xiàn)在想想,其實(shí)那時(shí)候她還是孩子,卻已經(jīng)在干大人的農(nóng)活了。有時(shí)候我會(huì)想,如果她的爸爸知道半年后她會(huì)自殺離開人世,大約不會(huì)那么對(duì)她大呼小叫的吧。命運(yùn)的殘忍就是在你不知道后來會(huì)怎么樣,而忘乎所以。
五月底,天氣熱了起來。學(xué)校的氣氛也凝重起來,各科的課都講完了,體育課早就停了,分配給了語文和數(shù)學(xué)老師加課。英語老師沒有課加,就讓我們?cè)缟咸崆岸昼妬斫淌遥齺碇v前一天的考試卷子。那真是一段“題山卷海”的日子,每天都在發(fā)卷子,每天都在模擬考試,我和我的同桌胡小勇幾乎一天也不會(huì)說上一句話,那么多卷子沒有做完,沒有時(shí)間也沒有心情講話。
最后的那一個(gè)半月學(xué)習(xí)太緊張,男生幾乎不打球了。我有一次看見她在放學(xué)的路上等人,好奇心讓我停住了腳步,我裝作去食堂打飯的樣子,慢慢地走著,眼睛卻一直在看她那邊,不一會(huì)李元展來了,然后他們?cè)谥v話,說的什么我完全聽不見,看樣子爭(zhēng)執(zhí)了起來,我正猶豫著要不要走過去,李元展已經(jīng)騎著自行車走了。
這件事過去不久,有一次摸底考試,吳琳的英語居然不及格,只有53分,我們都以為“女高音”要發(fā)飆了,但不知是因?yàn)槟罴八粘煽兒玫乃叫模€是這樣天天考試考疲了,倒是沒有惡言相向,輕描淡寫地說,下次注意,再考這么差就要叫家長了。倒是吳琳自己,低著頭,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子。她也有今天,我充滿惡意地想。
還有21天就要高考的那天早上,英語老師已經(jīng)站在講臺(tái)前,準(zhǔn)備講卷子了,才發(fā)現(xiàn)大家手里沒有昨天的考卷,教室里一片小混亂,她剛要發(fā)火,發(fā)現(xiàn)吳琳不在教室。是誰去拿了卷子來,老師那天講了些什么,我都忘記了。但我記得吳琳再也沒有來教室,她自殺了,喝農(nóng)藥。那天下午,她的父母來過學(xué)校,眼圈紅紅的,她父親,那個(gè)黑臉的四川漢子,仿佛老了許多。他們?cè)谛iL辦公室呆了很久,我們要放學(xué)時(shí),他們才從校長辦公室出來,一前一后相跟著走了。
她是因?yàn)槌煽兿陆怠毫Υ螅€是因?yàn)槔钤共抛詺⒌模也恢馈5乙驗(yàn)樗淖詺ⅲ瑓s有一種莫名的、深深的失落。
三
事情做得再隱蔽,也有疏忽的時(shí)候,那是一個(gè)有月亮的夜晚,下了晚自習(xí),李元展站在教室的后門口看著我,我知道他的意思,我找了理由讓你先走了,自己磨磨蹭蹭地走到最后。我跟著李元展又一次來到教室后面的棉花地。剛走進(jìn)去,就看見前面有人,可是要退回去已經(jīng)來不及了,那個(gè)人兩步并作三步已經(jīng)走到了李元展的跟前。李元展轉(zhuǎn)身面對(duì)我,用身體擋在了那個(gè)人和我之間,對(duì)我耳語,快跑!我來不及多想,狂奔起來,跑出好遠(yuǎn)才停下來,回頭張望,并沒有人追過來。
后來李元展給我說那個(gè)人是豹子,他叫我不要害怕,還叫找一件穿舊的內(nèi)衣給他,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我按他說的做了。后面發(fā)生的事情,你都知道了,那個(gè)叫豹子的小混混帶著其他幾個(gè)社會(huì)青年來過學(xué)校好幾次,他們?cè)诓賵?chǎng)上看我們上體育課,他們?cè)诜艑W(xué)的路上排成一排擋住路吹口哨,不知道那個(gè)是啥曲調(diào),我們當(dāng)時(shí)都叫它流氓口哨。
那一段時(shí)間,我心里害怕極了,可是又不敢給別人說,白天想得多了,晚上會(huì)做噩夢(mèng),半夜醒來,一身的汗水。你以為是要考試了,壓力太大,其實(shí)你不知道,我內(nèi)心的恐懼。
沒過多久,學(xué)校里瘋傳一個(gè)女生被社會(huì)男青年猥褻了,就在教室那塊棉花地里或者學(xué)校旁邊的旱廁里,誰也說不清楚到底發(fā)生了什么,大家也都不知道那個(gè)女生究竟是誰,傳言散布的最快,沒有幾天全校的師生好像都知道了這件事,大家都在議論,有些細(xì)節(jié)說的神乎其神、活靈活現(xiàn)的。
終于有一天,上自習(xí)的時(shí)候,有同學(xué)鬼鬼祟祟地議論,早上看見一個(gè)女生的內(nèi)衣掛在學(xué)校旱廁門口的樹上。
這件事給學(xué)生單調(diào)的校園生活帶來了不小的震動(dòng)和談資,女生各懷心思的議論著,又暗自猜測(cè)和想象著事情的經(jīng)過,轉(zhuǎn)而又慶幸著自己不是那個(gè)女生。說著說著,就傳成了那個(gè)被猥褻的女生是吳琳。她一向自恃學(xué)習(xí)好,很得老師的寵愛,不怎么隨和,倒霉鬼是她,也符合大家的想象。
那一段時(shí)間以至于宿舍幾個(gè)住校女生晚上都不敢去教室上晚自習(xí),一定要去,也是叫上隔壁的男同學(xué)一起去,再一起回。
我知道沒有女生被猥褻,我知道那是李元展放出的謠言,是為了讓我擺脫干系。
我像一個(gè)賊,偷了東西藏好后,看著人們?cè)谡遥抑罇|西是一步一步怎么被偷的,也知道藏在那里,可是我不能說,我不想讓人家知道我就是那個(gè)賊,可是我想讓人們找到那個(gè)丟了的東西。
再后來,豹子他們經(jīng)常到學(xué)校來溜達(dá),李元展被他們叫到一邊竊竊私語,保安看見了,會(huì)很粗暴地趕他們走。再后來,那個(gè)叫吳琳的女生喝農(nóng)藥自殺了。緊接著就要考試了,學(xué)校里一片壓抑的氣氛。
一個(gè)活生生的人死了,還有比這個(gè)更可怕的嗎?我想問一問李元展那天他和豹子到底說了什么,可是他總是躲著我。
天氣熱得可以擦出火花來,坐在教室里寫作業(yè),汗珠就從鼻子上、脖子里冒出來,順著皮膚流下來,衣服的后面常常有一小片是浸透的。老師也快要喪失最后的熱情了,摸底考試不再排名,只是考試,講卷子,日子獲得了表面的平靜。
那時(shí)候我倒不害怕了,可能是擔(dān)心得太久,麻木了,心里反倒平靜了。考試結(jié)束,我們?cè)谒奚岽虬欣睿液湍愀髯匝b好行李,在自行車后座上綁緊,就各回各家了。那個(gè)假期,我沒有出過門,我不知道別人考的怎么樣,憑著小聰明,我考得還不錯(cuò),上了本科的分?jǐn)?shù)線
那個(gè)夏天永遠(yuǎn)地結(jié)束了。
我再也沒有見過李元展,盡管他就在同一個(gè)城市的隔壁學(xué)校。
肖莉莉一口氣說這么多,聲音里透著和她不相稱的滄桑和疲憊,仿佛把她一輩子的力氣都用來講述這個(gè)事情了。
不知道說什么好,突然很想抽一支煙,緩解一下我壓抑的心情。
我拿起細(xì)長的紙煙,咣當(dāng)一聲,打火機(jī)的聲音顯得特別大,煙霧繚繞中,你更需要一個(gè)心理醫(yī)生,我說。其實(shí)我知道自己也需要一個(gè)心理醫(yī)生,但我不會(huì)去真的找醫(yī)生,我知道那沒有用。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就是想有個(gè)人說說,給個(gè)知道的人說說……這么多年,我都是一個(gè)人,一看見男人裸露的身體,我就想起那個(gè)夏天,那個(gè)死去的女同學(xué)。我不能安心地戀愛,結(jié)婚。我偷偷資助著吳琳的父母,卻不敢讓他們知道我是誰……肖莉莉有點(diǎn)嗚咽起來。
我安慰不了她,也無力安慰她。
我懷疑記憶是不真實(shí)的,每個(gè)人會(huì)按照自己的需要裁減、刪改、增加細(xì)節(jié),來完成自己的記憶,尤其是對(duì)自己重要的事件。
原來每個(gè)人的心里都有一個(gè)不曾過去的秘密,我們背負(fù)著各自的秘密生活著。肖莉莉講給我聽了,她可以傾訴了,心理學(xué)上講傾訴意味著解脫和放下的可能,意味著重新開始的可能。可是有多少的秘密只能是秘密,或者永遠(yuǎn)還是秘密的好。
至于那個(gè)夏天與我到底發(fā)生了什么,那是另一個(gè)故事了,不說也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