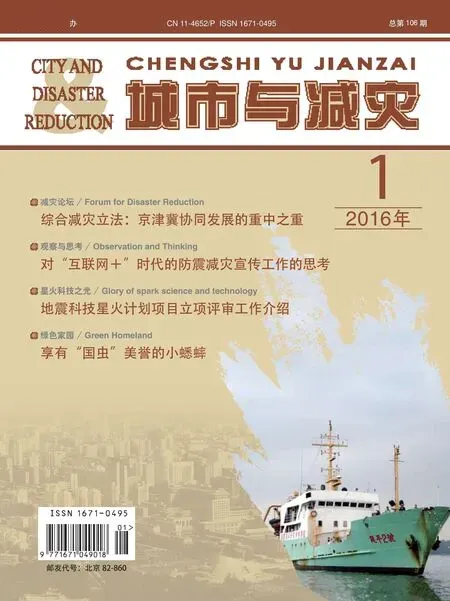點(diǎn)亮著的最后一盞燈
河北省地震局 王恬恬
點(diǎn)亮著的最后一盞燈
The last lantern, still lighting
河北省地震局 王恬恬

后郝窯水化觀測(cè)站
新年的鐘聲敲響了,聽著廣播里晚會(huì)主持人和觀眾的倒計(jì)時(shí),一個(gè)中等身材的男人站起身。
他走到墻邊,抬手撕掉了掛歷上僅存的一頁。
遠(yuǎn)處傳來隱隱約約的鞭炮聲,院子里早已熟睡的狗一下子興奮地起身叫起來。
不知是外面刮起了風(fēng),還是上躥下跳的狗兒驚動(dòng)了什么,他模糊間聽到一些異聲。趕緊披上外套,走出了屋門。
走到后院巡視了一圈,小狗跟在身后,似乎也在幫著查看著什么。
“一切正常,還好還好。”這個(gè)中年男人嘴里嘟囔了兩句,然后徑直向屋子的另一個(gè)方向走過去。
這是一幢很小的房子,圓形的房身上蓋著一個(gè)尖頂。推開門,里面空空的,唯獨(dú)中間有一個(gè)通往地下的扶梯。他順著里面的扶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空間似乎比第一層更加狹小低矮了。但就在這狹小的空間層里竟然還是一個(gè)“套間”。穿過勉強(qiáng)能站著走過的小門,就看見桌子臺(tái)面上滿滿擺放著儀器盒子,還有幾本老舊卻工整的記事本。
掀開已經(jīng)磨去本色的記事本封皮,內(nèi)頁上寫著這樣兩行字:
工作日記(十九)
程德慶
懷來地震臺(tái)后郝窯水化觀測(cè)站位于懷來縣城東南約13千米處,那里地處官?gòu)d水庫庫區(qū)西北,人跡罕至,荒草叢生,離那里最近的村莊后郝窯也有1.5千米。程德慶一待就是20年,一干就是7000多個(gè)日日夜夜。
門外一聳一聳的小土丘上,只剩下風(fēng)吹過留下的斑駁,但在他眼里卻是最美的風(fēng)景。遠(yuǎn)處傳來漸行漸近的車鈴聲,雖然短暫,卻是他耳里最動(dòng)聽的旋律。總跟在他身后的小狗,雖然不是名貴的品種,但卻是他最親近的伙伴。
二十多年前的程德慶也擁有著和那個(gè)時(shí)代年輕人一樣的夢(mèng)想,夢(mèng)想著去大城市,夢(mèng)想著憑著自己的力量獲得讓父母為之驕傲的成績(jī)。
可每當(dāng)他腦海中浮現(xiàn)出父親漸行漸遠(yuǎn)的彎駝身影,每當(dāng)他聽到直至深夜仍在獨(dú)自忙碌的母親唉聲嘆氣,在他心中總會(huì)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那時(shí)的程德慶還是個(gè)少不經(jīng)事的孩子,他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每天都在做什么,他唯一記得的是從小就很少見到父親。后來,他長(zhǎng)大了,懂事了,才從母親的只言片語里知道父親是一名工作在地震預(yù)報(bào)前線的水化觀測(cè)員。
歲月轉(zhuǎn)瞬即逝,三十年過去了,父親老了,干不動(dòng)了,可是未來的日子該由誰來干?原本早該退休的程父因?yàn)檫t遲找不到接班人選而一直無法回家養(yǎng)老,安度晚年。直到有一天,有人向單位提議,讓程德慶來接父親的班。此時(shí)的程德慶其實(shí)已經(jīng)有了一份屬于自己的工作,在一間花圃種植管理花草,這是他從小的愛好。父親的一個(gè)電話,從此就改變了程德慶的一生。
長(zhǎng)這么大第一次和父親面對(duì)面坐著,望著父親布滿滄桑紋路的面孔,程德慶只說了一句話:“這份工作,沒人去干,那我就去干!”

那一年,程德慶家的萬年歷上印著“1995”。
時(shí)間總是喜歡開玩笑,當(dāng)你希望它慢些走的時(shí)候,它飛逝如梭,可當(dāng)你期盼它快一些的時(shí)候,它又蹉跎了你我。
在程德慶工作的后郝窯水化觀測(cè)站有兩口井,一個(gè)是懷3#,另一個(gè)就是懷4#。懷4#在院內(nèi),主要用來觀測(cè)水氡、水汞和氫氣。而懷3#距離懷4#約五六十米,負(fù)責(zé)著土壤出氡、土壤溢出氫的測(cè)量。這兩口井在觀測(cè)方面都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程德慶每天都要重復(fù)的一項(xiàng)工作就是走到懷4#下,那個(gè)圓身尖頂?shù)姆孔永锩娴牡诙硬伤畼樱瑫r(shí)利用工作室里的儀器觀測(cè)井下水位及出水?dāng)?shù)量等日常數(shù)據(jù)。
在程德慶的辦公桌上擺放著兩個(gè)本子,其中一本就是他的工作日記。本子的封皮已經(jīng)被徹底磨花,上面印刻的鎏金字也早化為斑跡,里面的字卻是密麻中顯現(xiàn)出嚴(yán)謹(jǐn)與工整。有些時(shí)候記錄的內(nèi)容多些,有時(shí)記錄的少些,可每天都會(huì)出現(xiàn)這樣一段記錄:
5:30準(zhǔn)時(shí)起床,做好水氫化驗(yàn)準(zhǔn)備工作;
6:40到取懷3#和懷4#水樣,同時(shí)測(cè)氣溫、水溫、水壓等;
7:00鼓泡,連做4個(gè)平行觀測(cè);
8:00讀數(shù)開始,連做4個(gè)平行讀數(shù),對(duì)懷3#和懷4#交叉觀測(cè);
10:00左右完成觀測(cè)后,送水樣。
就這樣,同樣的內(nèi)容被記錄了幾千遍,但并不是簡(jiǎn)單的復(fù)制,因?yàn)槔锩娉艘涗涍@些日常規(guī)律的工作內(nèi)容外,還要記錄工作中出現(xiàn)了哪些問題,如測(cè)水結(jié)果出現(xiàn)哪些異常和井下水的自流受到哪些突發(fā)干擾,陰雨天出現(xiàn)哪些危急情況等。程德慶說:沒人讓我記錄這些,但是我必須記,只有這樣我才能督促自己時(shí)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不懈怠,不讓自己在工作中出現(xiàn)差錯(cuò)。
1995年的一天,那是個(gè)下著大雪的深冬。剛剛干上這份工作的程德慶還沒有什么經(jīng)驗(yàn)。因?yàn)橐伤畼樱栽绯?點(diǎn)準(zhǔn)時(shí)起床,進(jìn)行所有的設(shè)備儀器檢查后,6點(diǎn)40分開始采樣。年輕的程德慶手里拿著一個(gè)直徑約5厘米的圓底瓶子——被稱為氣體分離器的東西緩緩地湊近出水口。可是再小心謹(jǐn)慎,也無法將噴灑出來的熱水完全地收集到瓶子里,而漏到外面的熱水直接都噴到了程德慶的手上。滾燙的熱水使得程德慶本能地往回縮了一下手,可是緊接著他又拿穩(wěn)了瓶子繼續(xù)取水。他心里清楚,站上的設(shè)備有限,哪怕是這樣的玻璃取水器也很少。一旦他今天手抖摔壞了,那么今天的取樣工作就完全耽誤了。大雪還在下,程德慶穿過院子,幾片雪花落在他手上的一小片通紅上,立刻消失不見了,只留下一陣酸麻的刺痛感。
1998年,張北地震。這一年發(fā)生的事讓程德慶一輩子都忘不了。懷來臺(tái)站為地震預(yù)報(bào)測(cè)定提出了重要的數(shù)據(jù)意見。但因?yàn)槭且揽恳粋€(gè)點(diǎn)的觀測(cè),盡管井中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也無法確定震中、震源以及時(shí)間和地點(diǎn)范圍。程德慶說,短臨預(yù)報(bào)是40天,也就是只能說出在這40天范圍內(nèi)可能要發(fā)生的地震。按照當(dāng)時(shí)(1997年)的預(yù)測(cè),時(shí)間卡到12月31日,就已經(jīng)到了40天的最后期限。而最終于次年也就是1998年的1月10日發(fā)生了張北地震。前后預(yù)測(cè)相差了10天,震級(jí)預(yù)測(cè)和實(shí)際震級(jí)相差甚小。雖然按照當(dāng)時(shí)的地震預(yù)報(bào)能力,根本不可能將地震預(yù)報(bào)得準(zhǔn)確無誤,但是能預(yù)測(cè)出這樣的結(jié)果,對(duì)于地震預(yù)報(bào)工作已經(jīng)實(shí)屬不易。
也就是這樣一次工作經(jīng)歷,讓程德慶充分體會(huì)到自己從事的這份工作對(duì)于地震監(jiān)測(cè)的重要性。他第一次清楚地了解到作為一個(gè)地震人,自己肩負(fù)的使命。
到了下井的時(shí)間,他掀開井下第三層的蓋板,一大股熱氣迅速?gòu)牟坏揭黄椒矫滓姺降亩纯谔庈f出,著實(shí)嚇人一跳。太熱了,熱到遠(yuǎn)遠(yuǎn)超出了一個(gè)正常人的承受程度。程德慶笑著說:“平時(shí)我一個(gè)人在的時(shí)候,只穿著內(nèi)衣就下去了。”說著說著,好像又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地低頭笑了起來。這時(shí)的懷4#已經(jīng)經(jīng)過了改造,程德慶記得很清楚,懷4#改造是在2007年,當(dāng)時(shí)的改造工作時(shí)間緊任務(wù)重,他在完成本職觀測(cè)任務(wù)的同時(shí),還必須協(xié)助和盡可能確保各項(xiàng)改造工程的順利進(jìn)行。建設(shè)新井,最艱巨的任務(wù)就是井管的改造重建,因?yàn)榫芾锪鞯牟皇瞧胀ǖ牡叵滤前耸畮锥鹊母邷責(zé)崴J┕すと讼戮艿篱_孔的時(shí)候,不小心被噴涌而出的熱水燙到手臂,導(dǎo)致大面積皮膚損傷脫落,被趕緊送往醫(yī)院。而這邊熱水還在不停地從孔洞里冒出,一下子出了這樣的情況,其他工人都害怕了,根本不敢靠近。可是如果不繼續(xù),管道就無法正常運(yùn)轉(zhuǎn),所有的重建工作都將停止。盡管有了多年的工作經(jīng)驗(yàn),但面對(duì)這樣的突發(fā)情況,程德慶心里還是沒了底。可他轉(zhuǎn)念一想,所有人里除了他找不出第二個(gè)對(duì)付熱水更有經(jīng)驗(yàn)的,這個(gè)時(shí)候就是硬著頭皮也得上。于是只說了句“我來,我不怕燙”,然后迅速找到一根細(xì)鐵絲,用鐵絲拴住毛巾,在高溫和壓力的作用下,吸了熱水的毛巾一下子被吸進(jìn)洞口。熱水停止了噴射,工人們就利用這寶貴的時(shí)間檔,趕緊將連通雙井的中間管道焊接到洞口處,改造工程順利完成。
等程德慶從井底鉆出,時(shí)間已經(jīng)過去了十一二分鐘,看似短短的十幾分鐘卻讓人倍感煎熬。等他站到二層地面上時(shí),身上薄薄的衣衫已經(jīng)被汗液浸透,滾圓的大汗珠不時(shí)地從額頭滑下。


程德慶揉搓了幾下右手上的疤,開始在院子里巡視排查其他的儀器設(shè)備間。“九五”改造之后幾乎所有的儀器都已經(jīng)數(shù)字化讀數(shù),經(jīng)過“十五”改造以后,更是達(dá)到了網(wǎng)絡(luò)化的標(biāo)準(zhǔn)。盡管大部分的儀器都不再需要人工操作,可一旦遭遇雷雨天氣,就會(huì)有損壞的危險(xiǎn)。雷擊會(huì)對(duì)儀器產(chǎn)生致命性的損傷,盡管改造后的后郝窯水化觀測(cè)站,在整個(gè)臺(tái)站外部加裝了防雷防護(hù)網(wǎng),室內(nèi)連接儀器的電源也都采用避雷裝置。如此重重防護(hù),依舊不能起到百分之百的保護(hù)作用。在懷來臺(tái)的另一個(gè)子臺(tái)東梁臺(tái),就因?yàn)槔讚魧?dǎo)致8臺(tái)儀器癱瘓的重大損失。程德慶感受到巨大的壓力,后郝窯一年四季風(fēng)大少雷雨,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隱患,一旦發(fā)生,第一時(shí)間能維修調(diào)整的盡他所能,實(shí)在無法修護(hù)的必須搶時(shí)間報(bào)上級(jí)臺(tái)站,派人來查修。這也使得每到陰雨天氣,程德慶的神經(jīng)就會(huì)繃得異常緊張。
“鈴鈴鈴……”,屋里傳來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程德慶迅速?gòu)脑鹤优芑匚荩娫捘穷^是程德慶家所在村兒里的人,說是有人收到了預(yù)報(bào)地震的信息,信息里詳細(xì)描述了地震的震級(jí)、震源,時(shí)間甚至精確到了幾分幾秒。全村老小全都跑到家門外避難。程德慶聽到這兒,意識(shí)到了問題的嚴(yán)重性,他依靠掌握的知識(shí),明確告知電話那頭這是謠傳,不可信。放下電話,他馬上向臺(tái)里匯報(bào)情況,臺(tái)里同事仔細(xì)查看各項(xiàng)數(shù)據(jù),均未發(fā)現(xiàn)任何問題。程德慶沒有耽誤一秒鐘,把這個(gè)結(jié)果告訴了村里人,平息了一場(chǎng)地震謠傳的風(fēng)波。

而那一年的冬天,也是這樣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電話那頭是妻子焦急的哭訴聲,兒子半夜發(fā)高燒,昏迷不醒。程德慶慌了神,可是他無法離開。真的連幾個(gè)小時(shí)的都離不開嗎?利用睡覺的時(shí)間也不能趕回去帶孩子去看病嗎?一連串的疑問涌上心頭。可程德慶的一句話讓人啞口無言:“十幾年來,我沒有睡過一個(gè)安穩(wěn)覺,孩子身邊有他媽,可臺(tái)里只靠著我一個(gè)人哪。”
是啊,哪怕夜里起風(fēng),程德慶都會(huì)警醒地起床排查一遍,這些在程德慶的工作日記里都清楚記錄著。“我不知道該怎么彌補(bǔ),只能不去想這些,一門心思值好班,記好錄……”滿滿的都是無以言表的辛酸。
看了看墻上的鐘表,已經(jīng)是上午9點(diǎn)50分。程德慶立刻跟上了發(fā)條似的,麻利地將之前取好的水樣放進(jìn)一個(gè)盒子里,然后用一個(gè)布包包住,揣到懷里,小跑著出了院子。
院子不起眼的一個(gè)角落里停放著一輛破舊不堪的三輪車,程德慶跨上車座,院里的小狗也一個(gè)縱身躍上來,擺出一副馬上出發(fā)的架勢(shì)。他們要把采集好的水樣送去懷來臺(tái)。程德慶所在的觀測(cè)站距離懷來臺(tái)13千米,需要每天往返一次。來回都是顛簸的土路。一路上他一只手扶車把,另一只手緊緊地?fù)еb著水樣瓶的布包。車子真的很舊,一路上吱吱嘎嘎,時(shí)不時(shí)車子后的小狗還會(huì)因?yàn)榭吹绞裁炊d奮地叫兩聲。對(duì)于它來說,這應(yīng)該就算是放風(fēng)了吧。
程德慶想著過去——那時(shí)還是輛自行車,有一年冬天大雪過后,路面積雪被凍成了堅(jiān)實(shí)的冰,再加上原本路面就溝壑不平,根本沒辦法騎車子,他只能推著走,一邊走腳下一邊打滑。最后推著車子走了三四個(gè)小時(shí)才走到。把裝著水樣的容器交到臺(tái)站同事手里的時(shí)候,感覺立刻松了一大口氣。“我摔一下不要緊,可要是這瓶子摔了,那我罪過就大了。”后來因?yàn)檎旧先彼枰痰聭c去村上拉水,臺(tái)上就給他換了輛三輪車,剛換的時(shí)候挺好,可時(shí)間久了,風(fēng)吹日曬的,就成這樣了。現(xiàn)在不用拉水了,正好帶著它出去遛遛。說著往后面掃了一眼,示意在說車上的小狗。這個(gè)小家伙對(duì)于程德慶來說,早已不是被人遺棄的小可憐,而是他生活中最好的伙伴。
等到程德慶回到站上,已經(jīng)是快中午了。院子的一頭是用來做飯的“廚房”,說是廚房,其實(shí)也只是一間屋子里架了個(gè)爐灶。房子是“九五”改造后翻新的,在那之前整間屋子的房頂都已經(jīng)塌陷,靠一根粗大的木樁支撐著。加上用水困難,每天都要來回兩個(gè)小時(shí)去附近打水。可如此艱苦的條件,程德慶堅(jiān)持了6年。這6年里,他沒有和臺(tái)上領(lǐng)導(dǎo)叫過一次苦,發(fā)過一次牢騷,只是默默地承受著,付出著。
再堅(jiān)強(qiáng)的漢子也會(huì)有病痛。禁不住長(zhǎng)時(shí)間的勞累,程德慶患上了腎結(jié)石,甚至還出現(xiàn)了尿血癥狀。他一人在臺(tái)站,根本無人照料,妻子要在家照顧孩子和年邁的父親,不可能到臺(tái)上去照顧他。臺(tái)上向領(lǐng)導(dǎo)反映了情況,衡量后決定由他人暫代程德慶的工作。可程德慶一口拒絕了,代班的同事不熟悉這里的情況,不了解需要注意的問題,左思右想,他都覺得不能因?yàn)樽约旱膫€(gè)人情況而耽誤了工作。于是他向領(lǐng)導(dǎo)要求,自己只需要趁工作空當(dāng)治療即可。疼就用手頂著,最后,沒有住院,沒有輸液,程德慶在站上的廚房里熬了半個(gè)月的中藥便控制了病情,自始至終沒有耽誤一天工作。
程德慶,這個(gè)中等身材外表看上去完全與強(qiáng)悍無關(guān)的男人,最終也沒有被病痛打倒。
秋天的傍晚,院外種著的黃瓜已經(jīng)都掛上了秧,翠綠的瓜頭頂著一朵朵黃色的小花。透著從葡萄架滲出的余暉,小狗撒著歡兒又蹦又跳。簡(jiǎn)簡(jiǎn)單單的一些顏色,給枯燥的院子增色不少。正像程德慶辦公桌里裝滿抽屜的獲獎(jiǎng)證書,既是一份份榮耀,更是一次次的激勵(lì)。
夜深了,漆黑一片的四周,唯獨(dú)顯現(xiàn)出站上的這一點(diǎn)光亮。程德慶又在做臨睡前的最后一次巡查,身后的小黃狗安靜地跟隨著,生怕發(fā)出一點(diǎn)多余的動(dòng)靜都會(huì)擾亂主人集中的精神。
(攝影 范志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