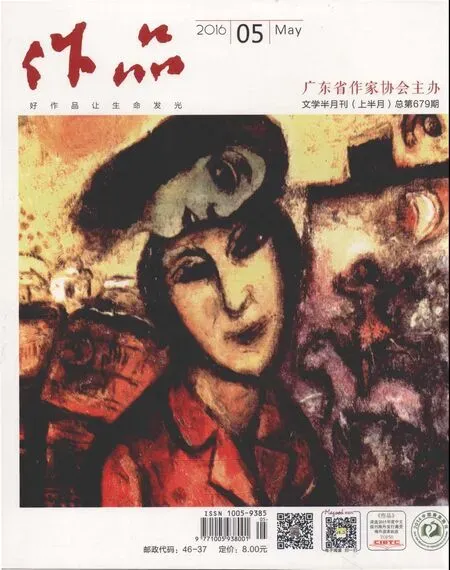寂靜的浦西
文/顧青安
寂靜的浦西
文/顧青安
顧青安女,原名侯麗芳,1994年生于甘肅。寫小說和散文,文字見于《美文》、 《高中生之友》、 《中學(xué)生百科》、 《哲思》、 《課堂內(nèi)外》等刊物。
小說的序言部分就定下了一種家族史詩的基調(diào),也渲染了悲傷的情緒——主人公生在天寒大雪,被視為不祥的征兆。當(dāng)讀者讀到這樣的開頭時,胃口就被吊了起來,因為家族冗長的命運連結(jié)起來,往往能造就一個引人入勝的小型的傳奇。這樣的傳奇幾乎存在于每一個普通的家庭里,如果不被作者一層層揭開,它們永遠(yuǎn)都會保持緘默。這也是我們樂此不疲地被這種故事吸引的原因,當(dāng)故事展開,家族的歷史被赤裸裸地展開,我們總會感同身受,潸然淚下。當(dāng)然這篇小說也不例外,一開始就有讓人讀下去的欲望。
這篇小說以孫女的口吻,講述著祖母的故事。這一層親人的關(guān)系,看似親密,卻也注定了一種疏離感。孫女不僅是站在事件之外,更是站在時間之外,祖母的形象因此散發(fā)著獨有的神秘感。雖然我們或多或少讀過類似的故事,但顧青安的這篇小說簡潔、有力,幾乎不帶任何多余的渲染和矯飾,在同類型的故事里顯得非常純粹,可讀性也很強。在這種筆調(diào)下,祖母和曾祖母兩位可敬的女性形象愈發(fā)動人。
讀完這篇小說,還會想起作者開頭描寫的段落,“土墻的背后是湛藍(lán)的天,有成群的不知名的鳥群盤旋飛過,發(fā)出鳴叫,有幾只俯沖下來,落在不遠(yuǎn)處的灌木叢里,沒了蹤跡。”——“浦西”便是土墻背后的世界,仿佛是在災(zāi)難過后的一種小小獎賞,雖然它并不光輝偉大,卻也散發(fā)著寂靜和平凡的神性,值得大家品讀、回味。
——栗鹿
序 言
我的祖母出生于1945年正月十六,時值天寒大雪,老一輩人多說不吉利,命運多舛,視為不祥。自此祖母漫長而寂寥的一生,從未過過生辰。
太爺爺,在冬天最后一場大雪銷聲匿跡的時候,給孩子起名趙吉吉。
愿其長女一生平安吉祥。
祖母所出生、長大的地方是西部清水鎮(zhèn)塔北村,太爺爺去世得早,祖母是眾姊妹之首,童年多寒食果腹,破衣加身。由于過早辛苦操勞,身子瘦弱矮小,像是隨時可以被北下的寒風(fēng)和隔日的饑餓送去與太爺爺團聚的可憐的孩子。
她一生默默無聞,一生窮困潦倒,一生顛沛流離,一生心無掛礙。
草草數(shù)語,便似能涵蓋一生。
也許那些丟失的日子與生活的困苦如同頓河上化掉的堅冰,都和過往的歲月一般悄然流逝了。
但這并不是一個關(guān)于祖母的故事。
1955年,祖母穿過塔北村那個巨大的麥場,跨過清水鎮(zhèn)界,越過頓河,到達了今天的浦西鎮(zhèn)。
于是,就有了后面的故事。
頓河外的世界
祖母一直想去頓河外的世界看看,她想知道頓河那頭是不是有巨大的麥場,麥子高高地摞起來,麥垛高得仿佛一眼望不到頂。是不是有巨大的棉花地,可以阻絕冬天寒冷的侵襲,是不是家家屋子里都有熱乎乎的暖炕,人將腳一伸上去,就會感覺全身都暖和了起來。
那時候,她以為,頓河之外的世界,無疾苦,無寒冷,無災(zāi)病,無憂愁,自由平等,信仰隨心。
便是世人所說的人間樂土。
所以她跨出塔北的腳步并未有絲毫猶豫,身上沒有一斗米就毅然決然的向未知的路程出發(fā)。因為家里已經(jīng)沒有多余的存糧了,為了留給冬日里還要給別人家洗衣服的母親和年幼的弟弟吃,她選擇在一個沒有星星的夜晚悄無聲息的離開了。
走的時候最小的弟弟縮在那個黑暗的門口大聲哭泣,她怕弟弟的哭聲吵醒熟睡中的母親,走過去輕輕地用手捂住他的嘴。
“噓,別哭。阿姐給你去找吃的,天亮就回來了,你要聽話。”
“知道了,阿姐,我等你回來。”
她猛烈地點了點頭,蹲下身用力地抱了抱那個顫抖的小人兒,然后頭也不回的沒入了遠(yuǎn)方的黑暗里。
祖母饑寒交迫的走了三天,一路乞討,最終叩響了舅舅家的木門,舅母看見立在大風(fēng)中的祖母,堅持不讓她進門。兩只手牢牢地把住門框,三角眼里的眼珠咕嚕嚕地直轉(zhuǎn),連聲罵道:“喪門星又上門了!”祖母無奈只好在舅舅家門外的草房里蜷縮了一宿,半夜乘著舅媽熟睡,舅舅才偷偷走出來抹著眼淚將兩個黑面做的饅頭塞給她。
“孩子……你走吧……是舅舅對不起你……”聽舅舅這么說,祖母已經(jīng)完全明白了。她默默地起身擦掉舅舅眼角的淚珠,小心翼翼地將那兩個饅頭裹在破爛的衣襟里,頭也不回地走出了草房。
她轉(zhuǎn)身要離開的時候,聽見舅舅悶聲喊了一句。
他說:“吉吉,你要活下去啊……”聲音夾雜著濃濃的哭腔和不可遏制的絕望。想來他也清楚,在這么個年代里,與她血脈相連的這個外甥女卻不知何時會在某個不為人知的角落里死去。
她后來一直在想,那時候她瀕臨死亡卻依然向往著頓河外的天堂,那里也許天氣溫和晴朗,遠(yuǎn)方遙遠(yuǎn)的平原上響起動聽的風(fēng)吟鳥唱,平房頂上的煙囪里炊煙繚繞,只是她后來才知道,原來浦西的冬天也是會下雪的!
祖母離開舅舅家門前的那片迷霧森林后,望著森林上方那片巨大的星河,不知道該往哪里跑,寒風(fēng)吹得她的身子瑟瑟發(fā)抖,她感到從未有過的無助和絕望。
她突然感覺到很疲憊,她的身體已經(jīng)開始搖擺,冥冥中她覺得快要死了。寒風(fēng)撕裂著她單薄的身體,她被漆黑的天穹壓得有些頭暈,腳下的路卻一直都走不完。
心里不知哪里來的念頭,她總覺得她要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
她深知明天深不可測,往前走才是最好的希望。
就這樣,她一路艱難乞討,做工,來到了浦西。
拖著身體前行的乞者
曾祖父在浦西鎮(zhèn)口撿到祖母的時候,太陽正從玉龍灣升起來,清晨的第一絲陽光打在了鎮(zhèn)口那座布滿了彈痕的土墻上,他愉快地伸了伸懶腰,哼著秦腔想靠在土墻上抽支老旱煙,卻看見土墻下已經(jīng)失去知覺的祖母,他過去一看,人還沒有死,一拍大腿,便把祖母背回了家。
祖母在前一天傍晚拖著已經(jīng)孱弱之極的身體到了玉灣村,她覺得她似乎走了很久,終于她抬起頭看到一面土墻。
她看到土墻散發(fā)著青煙和光暈。
土墻的背后是湛藍(lán)的天,有成群的不知名的鳥群盤旋飛過,發(fā)出鳴叫,有幾只俯沖下來,落在不遠(yuǎn)處的灌木叢里,沒了蹤跡。
她恍惚間看到那枚懸掛在玉龍灣的落日,然后因為長期的饑寒交迫,她就那么倒在了村口的那堵土墻下 。
她實在是太累了,她的身體再也無法前行,她的雙腳再也無法去尋找頓河外那片樂土。她覺得她的靈魂一定是快要升天了,不然下一秒鐘她怎么會看見一片金碧輝煌的屋宇,漫天的金光揮灑在她腳下的這片土地上,她聞到了飯菜的香味,她聽到了附近嬰兒的啼哭和狗吠,她聽到了田野里麥子被風(fēng)吹動,飽滿的顆粒在風(fēng)里相互撞擊,發(fā)出窸窸窣窣的聲音。
她的眸子已經(jīng)被耀眼的陽光映成了金黃色,她的神態(tài)安詳,再無憂懼,再無痛苦!
她扯開嘴角艱難地說道:“上天保佑!”
她想,她找到了,頓河外的天堂。
咧開干癟的嘴角笑了一下,她終于微笑著暈了過去。
曾祖父名安德生,時年六十三,晚年膝下只得祖父安明澤一子,雖家中貧寒,對獨子極其溺愛,那年祖父在浦西的鎮(zhèn)里上初中,是浦西為數(shù)不多的讀書人之一,這件事也讓曾祖父在人前風(fēng)光了不少,平常在羅老漢那些人面前吹牛的時候也硬氣了不少。
他逢人便問:“唉,你家的噢巴嘎呢?”
旁人聽得莫名其妙,問他:“什么是傻巴噶?”
他像沒聽到一樣兀自洋洋得意:“這你們就不知道了吧,奧巴嘎就是狗的意思!俄語!俄語知道嗎?”
眾人這才做恍然大悟,齊齊道:“噢……傻巴噶!”然后一哄而散。
曾祖父有些尷尬,他早晨聽兒子背外文便順口學(xué)了一句,本想顯擺顯擺,卻不想鬧了笑話。他也不在意,吧嗒吧嗒抽著旱煙上地里去了。
祖父早些年極其驕縱,看見家里多了一個吃白飯的人,氣得摔了碗就走,曾祖父急得在地上直跳腳,下巴上的長胡子隨著他的粗氣一上一下的跳動,祖母嚇得不敢吭聲。
“這個不孝子……吉吉,你不要理她……你就在這里呆著,放寬心,凡事有我,看我回頭怎么教訓(xùn)這個龜兒子。”
曾祖父看著瑟縮在墻邊的祖母,微笑著喊道。
祖母一生嘗盡人間冷暖,晚年提起這位我從未見過面的曾祖父,依舊是感激敬重居多,在當(dāng)年那個人吃人的世界里,給了一個陌生人生還的希望!
祖父晚年也曾評價過他去世多年的父親,只得短短八字卻似涵蓋了他的一生。
“明善處世,得人敬重。”
曾祖父尤其喜歡祖母的勤快善良,又心疼她的家世,于是便做主將祖母許配給了當(dāng)年還在上學(xué)的祖父。
“1963年,兒媳趙吉吉嫁予明澤為妻,為人溫良恭候,是為安家之福!”
多年之后,我翻看曾祖父的手稿,也只得這寥寥一句。
祖母的秘密
祖母嫁入安家的背后,當(dāng)然并沒有曾祖父在手稿上記錄的那句話那么簡單,除了曾祖父一力主張促成,祖父與各家親戚鄰居都表示了反對。
祖父更是半個月不曾回家,后被曾祖父強行從親戚家里揪了回來,強迫成了婚。盡管成婚后的祖父依舊是半月不回家,但曾祖父總覺得自己給兒子挑了一個好兒媳,賢惠勤快。
其實曾祖父想得很簡單,自己已經(jīng)老了,兒子明澤說到底還是小孩兒的心性,家務(wù)農(nóng)活竟是半分也不會,雖說是念了幾天書,終究是無大用處的。自己給她物色的這個媳婦,好歹可以照顧他的衣食住行,也算是后半輩子有個依靠了!
這么想著,他忽然有些愧疚。自己見吉吉身世可憐,便存了讓她進安家的念頭,人家女娃啥都會,倒是自己兒子……唉,以后這光景過不好了,怕是要連累吉吉了。
可是自己總有一天是要死的,到時候明澤只怕無法自力更生。這么想著,他額間蒼老的皺紋仿佛又深了一些。
因著那一絲愧疚,又或者是有別的原因,曾祖父生前對祖母極好,并不曾有半分苛待。
祖母入安家,祖父一直對她很冷淡,嫌棄她是一個乞丐,動不動就對她冷嘲熱諷,連正眼都沒有瞧過她一眼。無論曾祖父如何訓(xùn)斥勸說,他們之間的關(guān)系沒有任何緩和。她做的飯菜只要稍微有一點不合口,他抄起碗便向她砸,她只得尖叫著險險地避開,然后眼神怯懦地站在原地不敢看他。祖父瞧她這副模樣更是生氣,冷哼一聲便出了房門。
臨走前他說:“趙吉吉,我要是你,肯定早就滾出這個家了!”
望著丈夫,她淚如雨下。她知道他嫌棄她,厭憎她,從來不把自己當(dāng)做妻子看待。
但她還是默默地弓著身子收了地上的破碗,沉默地做著每天她都做的事情。
曾祖母在家里總是木訥而寡言,多數(shù)時候她都坐在門檻上曬太陽,兩只嬌小的腳丫并在一起,瞇著眼睛就是一天。
她話極少,個子較尋常女人高大,眉眼開闊,從臉上依稀可以看出年輕時的樣子。
祖母老是覺得曾祖母一定是一個有故事的人,因為從她狹長的眼睛和靜默的神情里,她恍惚間覺得幾乎看到了一個女人的一生。
她們婆媳之間的關(guān)系是緩和的,因為彼此都沉默寡言,要做什么事的時候,曾祖母便會在門檻里扯著嗓子喊:“吉吉……吉吉……”
有的時候,曾祖母也會拉著祖母在她常坐的門檻上聊天,這時候祖母總是很高興,覺得她們之間的關(guān)系仿佛更親近了。
曾祖母說:“吉吉……你真像年輕時候的我。”
她說:“吉吉,你真是個可憐的孩子。”
隨即曾祖母的眼里竟然流出了兩行濁淚,沒有人知道曾祖母為何哭泣。祖母只當(dāng)是婆婆心疼她的遭遇,心里感動莫名。便越發(fā)地孝順這個古怪的長輩!
慢慢地,慢慢地,隨著日子的推移,祖母很高興的發(fā)現(xiàn),祖父對她的伺候竟不再排斥,至少很少摔過碗筷了。她覺得很開心,她覺得以后祖父一定會慢慢轉(zhuǎn)變對她的態(tài)度,為了這一絲絲希冀,她在家里干活更加賣力!
在這個家里呆得越久,她便知道的越多,漸漸地……漸漸地……她發(fā)現(xiàn)家里所有的人,每個人都藏著一個秘密。
于是,祖母向我講述了另外一個故事!
那一場寂靜的愛戀
曾祖母名叫沈九禾,沈家世代在離玉龍灣十里遠(yuǎn)的浦西鎮(zhèn),家里是一個小地主家庭,雖然算不上富裕,好歹曾祖母幼時倒也不曾有溫飽的顧慮,家里有些田地,還雇了幾個長工干活。
曾祖母十九歲的時候,在冬日清晨的一場大霧里恰逢出門,卻看見暈倒在門口的一名八路軍,便救了他。待得人清醒了問話,卻道是附近打游擊的散隊遇到了襲擊,僅他一人逃脫,又因彈盡糧絕,無法支撐,才冒險進村尋找食物,不想體力不支,暈倒在曾祖母家門口。
曾祖母對這個英勇的軍人,幾乎是一見鐘情。喜歡他的英勇,喜歡他鋒利的眼神,怎么看都比鎮(zhèn)上那些只會摸麻將子和抽大煙的漢子都強。
她幾乎衣不解帶的照顧這個來路不明的軍人,不顧父親的反對,在朝夕相處的過程中,兩個人很快便陷入熱戀。
只是軍人傷好后卻急著想回大部隊,想報告這邊的情況。祖母不依,總覺得他這一走,便永遠(yuǎn)不會再回來。
軍人無賴的跟她解釋道:“九兒,我這樣子跟逃兵有什么區(qū)別,你不要逼我了好嗎?”
曾祖母無力地癱軟在地上失聲痛哭,即將失去愛人的痛苦幾乎讓她痛不欲生。
她哽咽著問道:“林越,你還會回來嗎?回來娶我嗎?”
身旁的林越蹲下身來輕輕地?fù)碇氐溃骸熬艃海乙欢〞貋淼模葢?zhàn)爭結(jié)束,我便回來娶你。”
聲音鏗鏘有力,充滿了堅定的信念,依附在他懷里的她竟然再提不起反駁和質(zhì)疑的力氣。
林越必須要走,戰(zhàn)爭進行得如火如荼,外地已經(jīng)搶占了祖國大片的領(lǐng)土,外面的很多人民都飽受戰(zhàn)爭的磨難,到處都分離崩析。
沒有人可以逃脫這一切。
或許是受上天庇佑,浦西特殊的地形讓它避免了戰(zhàn)爭的荼毒,但很快,他相信戰(zhàn)爭一定會蔓延到這里,沒有人可以幸免于難。
所以,他走了,臨走時他將他的手槍留給了她。
“一定要保護好自己……等我回來。”林越看著她的眼睛直直地說道。
她留著眼淚答應(yīng)了他,目送他的身影在大雪里越走越遠(yuǎn)。
“等來年風(fēng)起,我來看你。”
他的聲音穿過窸窸窣窣地大雪,像是帶著某種魔力般,準(zhǔn)確地傳入她的耳朵里,他相信她能明白。
那時候,對于命運多舛的人生,以及渺茫的時間,阻擋在他們中間這一事實,他們無可奈何。可是。籠罩在她心頭的那一絲不安,漸漸消逝了。余下的,只有那個記憶中的背影,越走越遠(yuǎn)……
祖母講到這里突然有些悲傷,我猜想也許這個故事并沒有一個好的結(jié)局。
“那最后林越回來了嗎?”我急急地問道。
“誰知道呢,或許回來過,或許始終沒有回來。”祖母的聲音好像是從那遙遠(yuǎn)的過往傳來,帶著宿命般的遺憾和嘆息。
“況且人生啊,從來都是由不得我們自己去選擇的!”祖母深深地嘆氣。
是啊,那么寂靜的愛戀,要么他們曾經(jīng)歷生死,要么便是一別終身,淡漠如君子。
祖母告訴我,曾祖母這一生,怕是都忘不了那個雪夜,那時候曾祖母以為她十八歲時就看破了天下,熟知,原來我們耗盡周身氣力看清的,不過是這個世界的冰山一角罷了!
最后一顆子彈
沒有持續(xù)的和平,沒有持續(xù)的繁榮,所有的一切在人性的毀滅下,都開始走向滅亡的道路。
糧食越來越少,餓死的人越來越多,冬天越來越寒冷,好多人都熬不過這個冬天去了。好多扛不住的人都上湯山當(dāng)了土匪,一伙一伙地人扛著大刀,背起砍柴的家伙就干起了搶劫的行當(dāng),搶得光明正大,義正言辭。
這一年,世道都變了,人開始吃人了。
只是曾祖母心心念念想了三年的人,始終沒有回來。
時間不久,沈家老太爺便被土匪擄去了山上,山上傳下消息來,說如果沈家不交出多余的存糧,便將沈老太爺?shù)念^剁了,吊在浦西鎮(zhèn)口的那棵大槐樹上。聽到消息的沈家老太太當(dāng)場就暈了過去,曾祖母更是大驚失色,不知所措。
好在全家人冷靜下來后,才勉強商量了一個對策,決定拿家里的兩千斤糧食,從山上把沈老爺換下來。
沈家人拉著騾子隊好不容易登上了湯山,這湯山頂上聚集了一窩土匪,在浦西地界內(nèi)無法無天。
土匪首領(lǐng)揭開糧食袋子一看,不高興地道:“你們沈家就只有兩千斤,你們騙我吧,還是不把沈老爺?shù)拿?dāng)回事……”隨即便冷哼一聲看著沈家眾人。沈家一應(yīng)人都嚇得腿腳酸軟,好歹曾祖母也算冷靜,提出說要先看看家人的安危。
沈老爺被帶出來的時候,衣衫襤褸,肯定是受了刑,曾祖母不知道哪里來的勇氣,跑到她父親身邊扶住了那個幾乎搖搖欲墜的身影。
土匪頭子嗤笑了一下開口道:“我們也不為難你們,再拿兩千斤,你們便可以回家了,這么點糧食,我們這么多弟兄怎么分!”
沈家人均是敢怒不敢言,湊齊這兩千斤已經(jīng)是非常不容易了。
曾祖母心想,這土匪如此貪得無厭,要完兩千斤必定還會要得更多,今日這情景怕是不能善了了。
她猛地掏出林越走前留給她的手槍,指著眾人,一字一句道:“我這里有十發(fā)子彈,九發(fā)送給眾位,最后一發(fā)是為我自己準(zhǔn)備的,倘若眾位收了這兩千斤糧食,放我們下山,就什么事都沒有!”
眾人均是一愣,不想一個弱女子手上有槍。一土匪嘴里喊著嚇人的玩意就沖將過來,曾祖母眼睛一閉便開了一槍。
雙腿不可遏制的顫抖,額頭上冷汗直冒。
這是她第一次殺人,那人卻沒死,她打中了腿部,只是剩下的人卻都不敢動,怕死是每個人的本能。
就這樣,曾祖母孤身一人,帶著沈家眾人下了湯山。
直到成功下山后,曾祖母才癱軟在地上,大聲哭泣。
祖母說到這里的時候,也是敬佩萬分,佩服一個女子的膽識和勇氣。但是我卻怎么也無法將這個年輕時意氣風(fēng)發(fā)的女子與那個晚年自縊的曾祖母聯(lián)系在一起,究竟發(fā)生了什么,導(dǎo)致人的命運轉(zhuǎn)變得如此之快!
對于安家的這場變故,祖父的手稿里只有四字記錄。
“世道無常。”只是簡單四字,字跡卻模糊不清,隱約判斷是有水漬浸染,想來祖父寫到這里回憶起曾祖母,也是情難自禁,潸然淚下。
浦西的落日
后三年,林越一直沒有回來。曾祖母家道中落,在家里人的強逼下嫁給了安德生。她再也沒有奢望,沒有幻想,收起了意氣風(fēng)發(fā),收起了年少風(fēng)華,收起了無果的四年,老老實實地做了一個鄉(xiāng)村婦人。
安德生驚喜交加的看著這個雖然已經(jīng)快三十歲,卻依舊風(fēng)華逼人的女子,自是心里樂開了花。只是安家那位以前在沈家做過長工的安家老太爺卻不這么想,心心念著以前的沈家大小姐最終也是要落到給自己每日端茶送飯,便好生愉快。
曾祖母在安家過得并不快活,不論曾祖父對她如何好,也改變不了她在安家要做苦力的事實。
安家兩位老人絲毫不憐惜這個往日的主人,家里的重活幾乎落到了她的肩上,她沒有絲毫怨言,像是已經(jīng)認(rèn)了命。
曾祖母一直沒有離開浦西,她心想如果有朝一日林越回來,怕是找不見她,所以她只能呆在原地等他,即使她自己清楚,那個人怕是再也回不來了。
或者他已經(jīng)做了高官,或者他已經(jīng)死在了戰(zhàn)場上。
每天太陽落山的時候,曾祖母就坐在鎮(zhèn)口的那棵大槐樹下,望著湯山頂上的那枚落日,風(fēng)來風(fēng)又起。她腳下的那條小路也一直沒有外人進村,于是她望啊望,卻始終沒有望見眼底的那抹地那抹青色。
曾祖父一生摯愛曾祖母,敬重那個挺身持槍的身影。他一生尊敬她,信任她,宛如對待最默契的伴侶。
曾祖父直到暮年才得一子,頗為愛重,孩子卻不是曾祖母所出。
曾祖母入安家多年,無所出,安父或以為有什么怪病,執(zhí)意讓曾祖父再娶,要求多次無果。晚些年,隔壁桃花塢的林家女子才進了安家,曾祖母竟是沒有半點不喜,不久林秀梅產(chǎn)得一子,安家舉家齊歡。
本來故事到這里就結(jié)束了,祖母講到這里也陷入了沉默,可是生活沒有結(jié)束,那么故事也將繼續(xù)。
曾祖母的自縊
曾祖母特地挑選了一個午后在屋后的偏房里自盡了,時值中秋,死的時候只有祖母在家里,死狀安詳。待得曾祖父跟祖父歸家,才知噩耗。
曾祖父顫顫巍巍地泣不成聲,只是一聲接一聲地說:“你終是解脫了……”
解脫了什么,為什么解脫,無人可知。命運就是一個巨大的齒輪,上面背負(fù)著的每個人都有一顆沉重的靈魂。
圣者克里斯朵夫渡過了命運那條河,他問肩上的孩子:“孩子,你究竟是誰?你為何這樣沉重?”孩子答道:“我是未來的日子。”
真正讓我們無法解脫的真的是未來日子嗎?
曾祖母發(fā)喪后,祖父便攜了一些值錢的行李離開了,他固執(zhí)地相信別人所言,是因為祖母沒有給曾祖母飯吃,才導(dǎo)致自己的母親因為忍受不了饑餓,自盡而死。
他走的那天,玉龍灣起了一場大霧,祖母站在土墻外看著那個決然的身影,沉默的哭泣。
是的,她這一生,都在沉默,接受命運的安排,所以她不出聲,不解釋,但她并不懊喪,并不卑微。她昨天夜里在祖父的包裹里偷偷塞了家里值錢的物什。
她想,她要為曾祖母保守那個秘密。
桃花塢的林秀梅嫁入安家后,家里的一應(yīng)雜務(wù)便都由曾祖母做,林秀梅從未將這個每天都將頭包裹在頭巾里的女人當(dāng)做自己的姐姐,她娘家窮困,嫁來安家后又隨即生了一個胖兒子,她的地位水漲船高,竟是享受了一把小姐的待遇,一應(yīng)吃喝都由曾祖母伺候。安家老太爺和老太太冷眼看著家里的一切,并不出面回護這個向來勤快孝順的大媳婦。他們更注重香火傳承,生了孩子的自然就是家里的大功臣。
事情好像就應(yīng)該這樣繼續(xù)發(fā)展,曾祖父給膝下唯一的兒子取名——明澤,尤其愛重。
林秀梅向來是個好吃懶做的女人,生了孩子只管讓曾祖母帶,曾祖母膝下無子,更加愛護這個孩子,頗為憐愛,就像對待自己的親生兒子。
祖父六歲時,曾祖母看見林秀梅在廚房責(zé)打年幼的明澤,趕緊放下手里的簸箕,沖到灶房護著他,期間與林秀梅起了爭執(zhí),猝不及防間林秀梅摔倒在地,后腦勺被柴火上未除盡的釘子扎穿,當(dāng)場死亡。
年幼的明澤撲在曾祖母懷里大哭,不知道發(fā)生了什么事。曾祖母蹲下身抱著祖父,身體不可遏制的顫抖,她的腦海中不自然的浮現(xiàn)出她第一次開槍殺人的時候的感覺,無邊的恐懼翻江倒海的襲來,她只得將懷里的孩子擁得更緊。
地上的林秀梅的眼睛還保持著死亡前一秒的姿勢,眼睛瞪得橢圓,像是經(jīng)歷了某種巨大的刺激。
她的血開始大面積的滲出,混著地上的泥土,呈現(xiàn)出一種奇異的紅色。
曾祖母抱著孩子突然開始嘔吐,那種從胃里散發(fā)出的惡心幾乎讓她把苦膽都吐了出來。
人越來越多,所有的人都回來了。她的公婆,還有鄰居……好多人都圍著她,好多人都進來了,抬了尸體又出去了,身邊有人在嚶嚶哭泣,指天罵地,很多的東西讓她喘不過氣。
有好事的閑話婆陰陽怪氣的說道:“桃花塢那伙子人,家里姊妹眾多,今兒的事怕是不能善了了……”
安家老太太狠狠地瞪了一眼地上的曾祖母,隨即便撲倒在地上大聲哭道:“我們安家是造了什么孽啊……竟然出了人命!”說完竟是跪在地上用手錘著地面大聲地喊叫。
聞風(fēng)趕來的鄰居七嘴八舌的議論著,突然人群中有個聲音就這么突兀的響了起來。
“我說,沈家妹子,莫不是你瞧不上林家這丫頭,存心將她推倒了。”
聲音一出,人群里頓時炸開了鍋,所有人的眼神直刷刷地瞅著蹲在地上的曾祖母。她一言不發(fā),也不出聲解釋。
直到此時,曾祖父才匆匆歸了家。
他進門第一件事,就是拉起在地上的曾祖母,轉(zhuǎn)身面向眾人。
“我相信九禾,你們其他人莫要再亂說。我們安家的事自己會處理,今天勞煩大家操心了,入土的時候還要麻煩大家咧,諸位且先回吧!德生在這里謝過了!”
曾祖父深深鞠了一躬后,眾人的議論才漸漸平息下來。被嚇壞的祖父此時才“哇”地一聲哭出聲來。
在眾人的注視下,那個一直躺在曾祖母懷里的孩子終于開口說了第一句話。
“媽媽自己摔倒了……”
聽完這句話的曾祖母伸手摸了摸這個在關(guān)鍵時刻保護了她的孩子,默默流淚。
從此以后,曾祖母一生撫養(yǎng)祖父長大,有如骨肉至親。
只是,她怎么也放不下,這個口口聲聲喊自己娘親的孩子,自己卻親手殺了她的母親。
曾祖母走的時候一定很迅速,過往的一生如同電影般的在她腦海里劃過,她一定是看見了什么,所以才想對一生中最重要的人說一句話。
嘴唇微張,聲音卻被吞進了胃里,再也沒有出來!
“曾祖母是因為林秀梅的事情無法面對祖父才自殺的嗎?”祖母漫長的敘述結(jié)束后,我疑惑的開口。
“要是無法面對的話,她估計早就走了!你曾祖母生前對你祖父那么疼愛,就算你祖父因為當(dāng)年生母的死而對你曾祖母存有怨恨之心,這么多年那一絲怨恨怕是早就煙消云散了。”祖母伸手拉起掉落在地上的毛毯,蓋在膝蓋上。
“那是因為她一直都沒有等到林越嗎?”我想了想,覺得這個理由才是曾祖母自殺唯一合理的解釋了。
“林越其實回來過。”祖母平靜地說道。
“什么?”我吃了一驚。
“你祖父十歲那年,林越從很偏遠(yuǎn)的邊疆回來了,聽說從部隊下來后便轉(zhuǎn)到某個小城市做了官,穩(wěn)定后他輾轉(zhuǎn)到浦西,找到了你曾祖母。”
“啊,那曾祖母為什么沒跟他走呢?”
“是啊,我也想知道她為什么沒有走。”
也許她深信,命運的選擇從來都是最好的安排。
隔年風(fēng)又起
時值傍晚,曾祖母正在廚房準(zhǔn)備給全家人蒸一鍋玉米面的饅頭,曾祖父在院里給騾子喂草。然后曾祖母就通過廚房那個狹窄的窗戶看到一個陌生的男人進了院子,好像是過路人,她準(zhǔn)備出去留下那個趕路的人吃過晚飯再走。
可是她一出門就愣在了那里,林越端端地站在那里,眼神定定的看著她。
她下意識地把身子往后一縮,雙手胡亂的在胸前臟臟的圍裙上抓著。
她就那么直直地盯著他,想著匆匆二十年的時光啊,竟然就這么悄悄溜走了。
他老了很多,身子不似多年前那般挺拔,臉龐發(fā)福了不少,鬢間有些許白發(fā),但唯一沒變的是他看她的眼神,溫柔的,寂靜的。
她握緊了顫抖的雙手,微微用力,指甲便嵌入了掌心里。
曾祖父像是一點都沒有發(fā)現(xiàn)她的異常,朝還呆愣在原地的林越介紹到。
“這是家里掌柜的,你大老遠(yuǎn)過來不容易,留下來吃飯吧!”
說完便自顧自拉著林越進了堂屋,留下一臉復(fù)雜還沒緩過神來的曾祖母留在原地。
晚上一桌人圍在一起吃飯,曾祖母坐在林越對面,神色坦然的像主人一樣招待遠(yuǎn)道而來的林越,她的神情那么自在,沒有激動,沒有喜悅,沒有難過和怨懟,她的目光如幽深的井水一般寂靜無波。
“那幾年,我給九兒寫了好多信,隨信還郵寄了一些錢財,只是都如石沉大海一般杳無音信。我因為工作問題,一直沒有抽出時間來接她,卻沒想到,這一隔竟是將近二十年了。”
林越柔聲講著,曾祖母慢慢的將嘴里的咀嚼已久的食物吞進了胃里。
“你過得可好?至今一人嗎?”曾祖母終于開口。
“得知你結(jié)婚后,我便成了家。我太太身體弱,邊疆氣候不好,前些年鬧過一次大病,便去了。”
“你也要照顧好自己才是。”頓了頓,曾祖母開口說道。只是她的眼睛卻始終落在桌上的一尺三寸里,從始至終,沒有看那個昔日的故人一眼。
“成婚前,我曾隨信附上了我的地址和車費,希望你能來找我!卻不曾想意外收到一封回信,信上說你已嫁人。后來世事匆忙,沒能回來。如今親眼來瞧瞧,總是好的。”他說得緩慢,語氣游離。
曾祖母聽到這里終于皺了皺眉,她記得這些年并沒有收到任何信件,自己沒有他的通聯(lián)地址,又何來給他寫信告知自己嫁人一事呢?
曾祖母突然轉(zhuǎn)頭看了身旁沉默不語,不停低頭吃飯的曾祖父一眼,然后她抬手給他碗里夾了一筷子咸菜。
曾祖父抬頭望了她一眼,嘴唇哆嗦著似有千言萬語。
飯畢,桌上的人各懷心思。
夜里曾祖母輾轉(zhuǎn)反側(cè),難以入睡。曾祖父眼睛睜得大大的,眼睛瞅著漆黑的屋頂不發(fā)一語。
然后他就聽到曾祖母開口道:“信是你寫的?”
“不是我……是我讓明澤寫的。”曾祖父囁嚅著說道。
曾祖母忽然嘆了口氣:“錢是人家的,拿了總歸是不好,明天要還給人家才好。”
“前些年的錢我都不知道,有一回我撞見爹將信封里的錢拿了出來,然后將那些信扔到灶火里燒了!我怕你心里惱火,跟爹起沖突,就沒敢跟你提。你不要生氣,他們肯定不是故意的,你也知道他們不識字,肯定不曉得那些信是找你的。后來有天那人給你寄來了一大筆錢,信里要你按照地址坐車去找他。我心里一迷糊就讓明澤給他回信了,可是你放心,那筆錢我原路退給他了。”
曾祖父說得很急,想來也是覺得理虧。
曾祖母沒吭聲,眼睛直晃晃的望著他,那雙眼睛跟明鏡似的,照得他不知所措。
曾祖母心里這些年的疑惑終于豁然開朗,他們怎么會不知道呢?那些厚厚的信件和錢財,就算不識字,找人看看也是可以的。然后林秀梅的到來,這么多年所遭受的白眼和冷遇,這一樁樁一件件,卻原來,從不是無緣無故的。
被曾祖母這么一望,曾祖父心里愈加內(nèi)疚自責(zé)。
“算了,我也沒想到,這么多年了他還會來找你,如果你愿意的話,就跟他走吧!總歸是安家人對不住你,這么多年,你受的苦已經(jīng)夠多了。”
“夜深了,早點睡吧!”曾祖母說完竟是一翻身睡去了。
曾祖父萬萬沒想到曾祖母會這么輕而易舉的揭過這件事,就好像是她昨天錯過了一道雨后的彩虹一般簡單。
可是那雨后的彩虹尚有再現(xiàn)的時候,人的命運呢?錯過了,便是錯過了。
林越走的時候,曾祖母在村口那棵大槐樹下送他,如同千萬次她站在這里等他歸來一樣。
“你老了很多,看起來過得并不好,當(dāng)年為什么不肯來找我呢?”
曾祖母突然眼淚就出來了,心里是說不清的酸澀之極的情緒,讓她忍不住想哭出聲來,但她沒有。她就那么抬頭,望了望槐樹枝頭的那一抹極淡的云彩,眼淚就瞬間沒入了眼底,悄無聲息。
“你可是對我有怨言,怪我當(dāng)年沒有等你?”曾祖母反問道。
“都這么多年過去了,想來你也是有苦衷的。”林越緩緩的搖了搖頭。
“但是現(xiàn)在,你還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嗎?”他想了想還是懷著一絲希望問道。
曾祖母心里大慟。
玉龍灣的落日終于跌入了山谷,留下一抹燙金的顏色,那個人像多年前的那個雪夜一樣,消失在了視線里。
曾祖母裹著頭巾進門的時候,曾祖父“唰”地一下從炕上竄了下來。
曾祖母神色如常,她平靜的喝了一口水,然后準(zhǔn)備解了頭巾做飯,就像她很多次回家后的情形一樣。
“你怎的……怎的又回來了?”他以為,下午的那場送別后,她再也不會回來了。
“我去做飯,你把柴火劈了,明天明澤上學(xué)要帶到學(xué)校里去。”說完曾祖母自顧自往廚房走去了。
曾祖父突然老淚縱橫,那樣子像是有人搶走了他心愛的那桿老煙槍,他分明是開心的,卻覺得心臟好像被人用大錘重?fù)袅艘话恪?/p>
他隱約明白,那一刻,他永遠(yuǎn)的失去她了。
“如果有一天你要是死了,我一定去找你,這是我愿意做的。但是如果你活得好好的,我卻不想和你過。”
那是曾祖母對林越說的最后一句話,她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
她在漫長的歲月里,恪守一個為人妻子,為人母親的本分。盡心照顧家庭,看著兒子成家,然后在那個缺衣少食的日子里,在那個林越逝去后的某個下午,她去做她愿意去做的事情了。
她一生都在向那個遠(yuǎn)去的背影靠近,那是她心里想做的,她便做了。
我在等你
祖父在外漂泊幾年,花光了祖母留給他的盤纏,在城里終是混了個灰頭土臉,迫不得已賣了身后最后一件棉襖,落魄歸家。
他推開那扇熟悉的木門的時候,看到的就是這樣的一副場景。
他的父親身子佝僂,瘦骨嶙峋,顴骨高高突出,眼神渾濁地坐在家里那把破舊的搖椅上。他的妻子正蹲在地上,捧著父親的雙腳清洗。盆子里濺起的水花打濕了身旁的泥土。
陽光在房頂鋪射下來,他年輕的妻子,神情專注,恍若未聞。
心里的酸楚翻江倒海的向心口涌來,他低著頭,鼻子一酸,眼淚差點掉下來。
他看著對面這個灰頭土臉的女人,不理解她怎么還在這里。
祖母看著他的眼睛,嚴(yán)肅而專注的陳述道。
我在等你。
是的,她就是在陳述一個事實,她堅守在這個家里,照顧公公,等待那個不知道何時才能歸來的丈夫。家里的鍋里只剩下一把她從山上挖的野菜,米缸里空空如也。
她終于松了一口氣,眼神歡喜。
下午公社分的糧食就下來了,我去領(lǐng)。你先吃這個。
祖父看著手里的野菜團,大口大口的吞咽著。
家里的勞動力都要去公社干活,他不在的日子,這個女人成了家里唯一的勞動力,養(yǎng)活著父親。
那一刻,祖父抱著蒼老的曾祖父泣不成聲。
后來的日子很平靜,祖母笑著向我講述道。看著她蒼老面容都遮不住的笑意,我猜想她必是過了人生中一段美好時光。這日子如此美好,以至于連回憶都散發(fā)著迷人的香氣。
很快,祖母有了五個孩子,也有了我的父親,為家里幼子。
祖父給父親取名,希望。
父親出生后,家里幾乎陷入了絕境,一家人的溫飽成為每天必須要解決的難題。他們必須為生存考慮。
后來,祖父毅然拋棄玉灣的祖屋,舉家遷往浦西。搬家的理由只有一個,在浦西,一個人的工分要比在玉灣村多一分,而就這一分,卻可以讓他們多一份糧食,好養(yǎng)活龐大的家庭。
自此,安家整個龐大的家族便開始在浦西開支散葉,當(dāng)然這是后話。
對于那段過往,祖父手稿里也只有一句感慨,就那一句卻似乎已經(jīng)說出了他全部想說的話。
“活下去。”
“這是多么奇妙的輪回啊,十年前,我的舅舅告訴我,一定要活下去,十年后,我的丈夫告訴我,一定要活下去。于是,就這一件事,卻幾乎耗盡了我半生的力氣。”祖母的手搭在藤椅上,有風(fēng)吹過,她的白發(fā)比珍珠還要美麗。
我的祖母一生都是寡言而無趣的人,認(rèn)識的人都這么說。
然而就是這么一個人,經(jīng)過歲月的打磨,卻更散發(fā)出一種令人折服的光彩。
于是,千山萬水美好。
是的,這是兩個女人的故事。
但這并不只是兩個女人的故事。
我于這世間的縫隙窺探人生,人生不過千奇百怪、光怪陸離的一回合而已。
人生倉皇打馬而過,不過寂寂一瞬,由此,對于生命之苦難,災(zāi)厄,尚可不畏懼,過好一生。僅此一點,我甘之若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