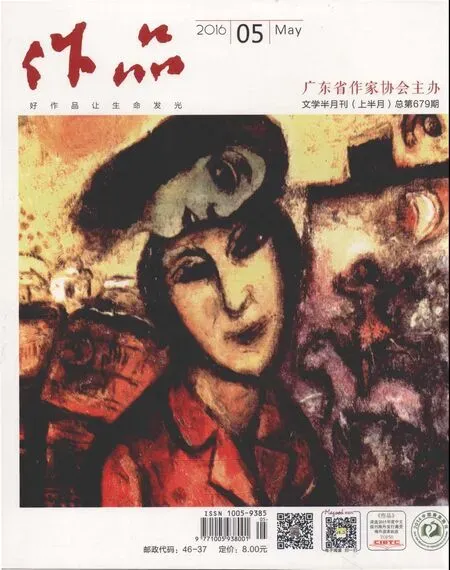會飛的父親
文/李 浩
會飛的父親
文/李 浩
李 浩男。1971年生于河北海興。發表作品260余萬字。有作品被各類選刊選載。小說、詩歌入選30余種各類選集和大學、中學讀本。作品譯成英、法、日、韓等文字。著有小說集《誰生來是刺客》、 《側面的鏡子》、 《藍試紙》、 《告密者》。長篇小說《如歸旅店》、 《鏡子里的父親》。曾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第三屆蒲松齡小說獎,第十二屆莊重文文學獎,第九屆《十月》文學獎,第九屆《人民文學》獎。第九屆、第十一屆河北文藝振興獎,首屆都市小說雙年獎等。
1
我準備寫作第三篇《會飛的父親》。我想,這一次,我將加入一點寓意在里面。這本是米沃什的句子。原句是:“現在我想講米德爾的故事:我且放進一點寓意。”
好吧,我且放入一點寓意。這也是我的習慣,我習慣如此,一向,我總是概念先行——我覺得這是一個被誤讀、被用壞的好詞兒。沒有這一點寓意,父親是無法飛起來的,我以為。游戲性是文學的另一條翅膀,反復地寫《會飛的父親》,是我留給自己的游戲。
這時問題來了:父親不能僅靠寓意飛翔。他還需要其它的輔助,譬如飛機,滑索,火箭,飛毯,床單,或者鳥的翅膀。或者熱氣球。熱氣球不能用,在卡爾維諾《樹上的男爵》中,哥哥柯西莫就是拉著熱氣球垂下的繩索“升入了天空”——我當然不希望自己是渺小的后來者,這篇小說我不準備再使用所謂的“互文”。飛毯,是阿拉伯人的專屬,父親借不來它,它不合適。至于床單……當然更不可以了,俏姑娘,蕾梅苔絲,她乘坐床單和塵世的責任、鬼火告別,這個出現于《百年孤獨》的美妙段落我已經在《鏡子里的父親》中借用過一次,第三次,等于是第三次把愛情說成是玫瑰,書上說這樣就是平庸的愚蠢。是的,飛毯,床單,熱氣球,不是父親此時能得到的,它們屬于紅筆劃掉的禁用詞。
想想前面:第一篇《會飛的父親》,里面的父親是憑借想象飛走,他不存在,沒有出現過,是一個模糊的虛詞,對他的種種飛翔完全是兒子的幻想,他被賦予神跡和能力,當然,這和父親“離去”的真實距離遙遠。第二篇,父親依然沒有借到翅膀,我有意讓他始終沉在日常里,他的飛只是象征——我在這里面就加入了一點兒寓意。
暫時把寓意放在一邊,現在,更為關鍵的問題是,我如何能讓父親從地面上飛起來。這是個問題。有難度的問題。這時我還不想制造神話,神話,是下一篇的。是的,我曾試圖把翅膀塞給父親,在他的肩胛處涂上粘接的蠟——但隨后,它又一次遭到否決。我將即將飛起的父親按住,拔光了所有的羽毛。
那,我的父親,他還可以建造一個龐大的器械,憑借它從一個山坡處向下滑翔……似乎可以。這是一個解決之道。和這個身份相稱——我的父親,李老師,是一個鄉村詩人。我計劃,讓父親重回鄉村詩人的身份,他希望飛翔,這樣會讓他贏得更多的尊重,而尊重一向那么稀薄……
最后一刻,我再次放棄了它。
當然可以塞入寓意,這沒問題,鄉村詩人的身份本身就有寓意感,何況還有尊嚴,飛翔……我放棄它是因為它留下的空隙太小。這是一個小口徑的氣球,里面放不進太多的氣體,那一小點兒的寓意如果僅像櫻桃的大小,也是我不想的。再說,在我的《鄉村詩人札記》里邊,這樣的寓意已經放置過一次,將它重新拿出來,就會看到浮在上面的種種銹斑。父親的飛翔需要另外的路徑。
他,或許,需要一雙飛行鞋?
我把“飛行鞋”寫在一張購物小票的紙上。背面。
2
我如何,才能讓父親再次飛起?這不僅是個問題,還是個難題。
他沒有飛起來的渠道。沒有路徑。沒有飛行的鞋子。沒有腿——好吧,這屬于靈感:會飛的父親,在他飛起來之前我干脆讓他更低,讓他更沒有可能——我決定,在這篇小說里,父親將是一個,坐在輪椅上的人。他不止飛不起來,就連普通的生活,跑和跳都已不再能夠。不止如此,我還要,讓他完成自我囚禁——出于羞愧、虛榮、對尊嚴感的呵護以及對觀看的拒絕,他,要把自己囚禁在一個房間里面,足不出戶。那間房子將成為他的殼,他是一只軟殼的蝸牛——我說過我要在里面塞入點寓意,這個殼將成為寓意的部分:車禍使父親更深地縮進了殼里,他的怯懦本性更強烈地呈現出來,當然,在我們這個家庭中間他還是一個堅固而強大的存在,他要時不時地向我們施壓,施威,讓我們不能忽視他,并把他的不快樂加到我和我們的身上。
可此時,他依然沒有飛翔起來的渠道。《會飛的父親》不能不提到飛翔,這個飛翔必須給予父親,否則,它就……我的踟躕依然在這里,而且在“降低”之后,飛翔的可能性又一次遭受限制,我如何說服自己和閱讀者,這個被按在輪椅上同時又將自己囚禁于房間中的父親能夠學會飛翔,并且可以飛離他不習慣也不喜歡的生活。
它,實在費思量。一天,一天。我想,我也許應當暫時地放棄它,我還有別的什么需要寫作,譬如一個大水將至的故事,譬如一個殺人犯的故事,他殺了自己的女友和她的妹妹,選擇了逃亡,而追逐他的警察則是鄰居,她告訴女兒的是另一個故事:樓上的死亡不是真的,忙碌的擔架抬走的不過是一碗雞湯。再譬如,一個德國故事:一個德國人,在二戰時作為少年的兵員來到蘇聯,這時他完全是懵懂的根本沒受過多少訓練。第二天,他站崗,蘇軍的士兵摸了上來。出于怯懦,他沒有發出呼喊也沒有摸到自己的槍——這一日,是德軍敗退的開始,之后的結果當然就像歷史中寫的那樣。這個德國士兵一路躲躲閃閃返回到故鄉,此時的故鄉已經滿目瘡痍,它被蘇軍占領,而他的妹妹也已經死去。接下來許多年,他過著平靜的生活而內心里卻時時波濤洶涌,自責近乎壓垮了他——他以為,是自己的怯懦導致了帝國的潰敗,并導致了妹妹的死亡,因此上,他在無法洗刷掉自己的恥辱之前不配得到任何的快樂。在之后的日子里,他試圖秘密潛入蘇聯刺殺某個人或某些人,計劃還算周詳,但新聞里,他名單上的人卻一個個減少直到斯大林也已去世,這個計劃還沒有進行。在日常里他是平靜的,但容不得別人嘲笑,更容不得別人說他怯懦,在那時他則完全是一只有怪癖的刺猬。時間在走,一年一年,他慢慢地老了,而柏林的墻已被推掉,蘇聯不復存在……滄海桑田,鄰居們越來越與他格格不入,而他時不時會在記憶里沉浸,不能自拔。這一日,來了兩個白俄羅斯的人,一男一女,他們來德國旅行……老人接待了他們,和他們談及二戰,兩個人對此毫無興趣,只是女孩偶爾談及,她的爺爺曾參與過戰斗不過很快在戰爭中受傷沒有隨部隊進入到波蘭。恰是這句話引起了這個已經老年的德國人的熱情,他邀請他們在他的家里住下來。晚上,老人拿出自己藏了很久的軍刀,反復的擦拭著——也許,這是一次機會,他終于有機會向人們證明,他戰勝了怯懦,哪怕為此搭上性命。或許,有機會,我會在文字中讓這個老人說出:他并不愛那個帝國。但他也不接受帝國毀滅的疼痛,何況,它的毀滅似乎與他的怯懦失職有關。“我大約能理解你們所說的正確。只是,我的不一樣。”
這是一篇構思許久的小說,早在三年前我就寫下了提綱,或許,開始寫作它更為合適。我坐在電腦前,刪除了“會飛的父親”,換上“怯懦者”——它等于撕掉了一頁。即使使用電腦,我也聽到了紙片被撕碎時的那種聲響。
新故事將要開始。不過,對于《會飛的父親》牽掛還在。它是一粒未曾發芽的種子,只要它在,只要有了適合,芽還是會發出來的,我相信。
3
是什么阻擋了我對德國故事的書寫?可能還是這粒種子,它構成了堵塞。它擋在曲徑瓶的瓶口,使可能的水流總是不暢。這時它還是硬的。
如鯁在喉。它讓我想起布羅茨基的詩句,他說,有關魚的詩,就像是一根梗于喉嚨里的魚刺——真是恰當的比喻——在這里,似乎已經刪除的標題也如魚刺,我看不見它,但它在著,并時時用刺痛感對我完成提醒。放下它的努力是無效的,我做得不夠,面對電腦上的白紙之白,面對《怯懦者》,輪椅上的父親總是不經意地出現,在那邊,不住地咳。
劣質的煙嗆到了他。
妻子向我談及玻璃,先是“自殺”的鏡子:它突然地從高處摔下來粉身碎骨,沒有征兆也沒有人動它。后來是窗戶,剛剛擦過的玻璃又被小雪弄臟,而那個高度卻讓她暈眩……好,好啊,父親的故事來了,它冒出了繼續下去的芽:我讓父親的輪椅爬行到一個高處,無論是樓頂,工地,橋頭還是別的什么,有個高度就足夠,至于這個高度在哪可以在寫作中慢慢思量,他試圖飛身下去,不,我不會讓他真的飛下去,而是會將他安排在那個位置上——那是個支點,但在文章結束,他只會固定于這個支點上,“飛而不翔”——我設想,面對找見他的我,父親作出這樣的解釋:我想向下面看看。就是這樣。而我站在他的位置上向下,飛翔的快感、暈眩感和恐懼感同時落在我的身上,我不知道在那一時刻,我是否理解了自己的父親。
可以開始了,就如此開始:我將“怯懦者”刪除,然后將“會飛的父親”換回來:當然,這是個新的,和之前的那些字沒有聯系,電腦不會記憶,即使我使用的是五筆。
4
我且放入一點寓意。
一場車禍,將父親固定于輪椅上:原本,我試圖在這里就放入寓意,譬如車禍之禍,要在這個“禍”上賦予……接下來的一刻我又否定了這個想法,這不是一個恰當的方式。需要的寓意將在后面出現,它只是枝杈,過多的枝杈會奪走核心感,影響到樹木的生長。原本,我還想為父親的車禍找一個緣由,不可告人,但車禍使它獲得了呈現——接下來的一刻我再次否定,它會將小說引向另外的方向,而那個方向,并不是我想要的。
在構思中,我將安排父親哭泣,而在囚禁的時間里,我將安排父親面對火爐發呆,像一段不思考的木頭……這樣的安排讓我興奮。因為它可以使用引文。我喜歡使用引文,這是一個相當固執的嗜好,或者怪癖,或者“掉書袋”,或者其它的什么——它時常顯得不可遏制。是的,我不太準備修正我的這一嗜好,在之后的寫作中它還會獲得延續,我的理想也是寫一部“全部用引文完成的偉大的書”——
我的父親將這樣哭泣:“這個坐在床中間哭泣的人看上去很像我父親。他在哭泣。眼淚順著臉頰流淌。能看出來,他正為什么事痛苦不堪。看他這樣,我就明白有什么事不對勁兒了。他噴涌得像消防水龍頭被敲掉了栓,他的哀號在所有這些房間里沖出沖進。我將手置于胸前,以一種安慰的口氣說,‘父親’,這并沒有使他從悲傷中走出來。它忽爾高聲尖叫,忽爾低聲嗚咽。他的幅度變化極大,他的雄心也不相上下。我又說了一遍:‘父親’,但是他不理睬我……”而在囚禁中,關于父親的文字將會是這樣:“父親開始足不出戶。他封起那些爐子,研究起永遠捉摸不定的火焰的本質,體驗著舔舐煙囪出口處閃亮的煤煙的冬季火蛇的咸咸的金屬味和煙氣味。那段時間,他總是在不同房間的某個高空地帶癡迷地干著形形色色的修理的小活兒……他開始與各種實際事務漸行漸遠。”我準備,將這樣的文字塞入到我的小說中去,讓它們鑲鉗于……我承認在我想到讓“父親”降低將他困在輪椅上的最初便想到要使用這兩段引文,它們幾乎同時,只有細究起來“父親坐在輪椅上”才會略略靠前那么一點兒。唐納德·巴塞爾姆,《我看見父親哭泣時的情景》,另一段文字則來自于布魯諾·舒爾茨,《鳥》。我愿意在我的寫作中加入它們,我愿意,和那些對我影響深刻的文字構成互文。
我幾乎要塞進去了,這完全是舉手之勞。我也確實將《我看見父親哭泣時的情景》的句子塞入到了小說里面,但隨后,又刪除了它。出于一種我也說不清楚的考慮,大約是不夠合適。還有一種可能就是,當時,我的手邊沒有《白雪公主》,而書櫥里也沒能找到。那么多的書,有時翻撿起來真是費勁。
克制使用引文的嗜好,對我來說頗有難度。這時,我依然還在猶豫:是否,要重新加入它和它們?它,和這則故事的血型是匹配的。
5
整個故事將如此設計:父親受傷,車禍,被迫坐進了輪椅,讓善于奔跑的他驟然地低于了生活。他無法接受,當然無法接受,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他因此變得無能,進入到一種可能的“丑陋”的生活,這會讓他感覺羞愧,無助,甚至豎起刺猬的刺。在一段時間的囚禁之后,“與世隔絕”之后,父親忽然變得——我要讓他變化,開始他的“積極生活”:與老人們下棋,打牌,在經歷了一些不快之后他有了一個新去處:籃球場,成為備戰的縣籃球隊的“編外教練”(書寫這樣的生活于我不太具備難度,生活中,我的父親確是體育迷,也曾任學校籃球隊的教練和裁判。平時,因為妻子的關系我也偶爾觀看NBA比賽,熟悉一些技術術語)。然而坐在輪椅上的父親、話多的父親并不能讓那些陌生的面孔信服,他們聽從的是教練的呼喊而不是我父親的,這讓我的父親很是氣憤。每次回到家里,他依然處在氣憤之中,痛斥幾號球員完全沒有球感,痛斥教練的指揮和換人總是失當,如何如何……在家里,只有母親會對他表達不滿:你看就看,別給人家亂指揮,你就看不見人家的臉色!都煩你啦!你當你是誰?這個不行那個不行,就你行?你腿好著的時候就行?我們當然要制止他們的爭吵,勸告母親讓著父親點,畢竟,他不痛快,畢竟,現在有這樣一個去處(我要讓父親變成一個話多的指揮者,他愿意“插手”一切事物,包括之前他從來不感興趣的。他仿佛是一個百事通達的行家,從而有了一貫固執的“正確”,更不容忍辯駁——輪椅上的生活讓他更加脆弱有了更多的刺,同時也讓他更不寬容。弱的,向更弱的進行施加,向自己的家人施加,我要讓故事里的父親變得這樣,這則故事需要這樣的“寓意”,它是之前就已經想好了的)。但受挫會有。當父親越過邊界,對家庭之外的人員發號施令和訓斥的時候他的受挫感就來了——還是籃球場,父親自己把輪椅搖到教練身邊,他根本看不到教練的臉色。教練沒說什么,但一個高大的球員卻急了,他把手里的球遞到我父親的手上:你不讓我上,你上。你上我的位置!父親當然不能。但父親的嘴還是硬的——你打不了這個位置,看你剛才的表現,這些天來的表現,我發現你太僵硬,不靈活,也飛不起來,技術不扎實。當年我打的就是你這個位置,當年……我弟弟想勸阻住那個沖動起來的小伙,他不過去也許還好。
球場,父親不能去了,他也不愿意去了。在經歷一系列的挫敗之后,父親再一次“隔絕”起來,他重新成為個人的孤島,變回到弱者,更弱者,軟殼的蝸牛,在那些日常的、瑣細的、不具有傷害可能的事物中也不肯探出頭來。偶爾,他會在房間里偷偷地哭,我們在另外的房間里自然看不到這些。結尾是:某個夜晚,父親從他的房間里消失,我們睡著對此毫無察覺,直到夜起的母親發現了身側的空蕩。她呼喊我們,我們出去分頭尋找,最終我在一個高處(這個高處,是樓層?高地?或者其它的什么?我沒有想到,這個可以暫時不思量,留給寫作的渠,我想水會自然而然地流至那里)尋見了父親。當然,我得小心翼翼,只是靠近他,和他的輪椅坐在一起。這時天邊已有微光,借著光,我可能看到他手上磨出的血:為了這個高處,他一定極為艱難。他朝著遠處張望,仿佛我是陪他到來的那個人,一直在。“爸,你在看什么?”我問。“鳥。它們飛到那邊去了。”然而,我并沒有看到一只鳥的存在,我,只看到了高處的暈眩(結尾,和之前的設想有了一些小的變化。變化還會發生,它將伴隨寫作的全部過程,這也是貯含的魅力和趣味之一,我覺得)。
似乎還不錯。已經可以向下進行。我要把波瀾預留出來,這屬于小說技藝的常規,不具備太多的難度。當然,我也已經想好,父親需要停留在那個高處而不是讓他真的“飛翔起來”,否則,它就會落入到某種俗套,我要讓他被沖動和恐懼反復糾纏——我知道這樣的心理,恐懼時常會有所戰勝。在寫作開始之前,我設計最多的恰是最后一段,盡管我一時看不清父親腳下是樓頂還是橋頭,或者別的……我設計了那天的晨曦,設計了向下的昏和暗,設計了……它是一個有爆發感的點,不,它不能爆發,我要做出渦流更要做出表層的平靜,它要在平靜中止住,但回聲在,回聲悠長——是的,我要的效果是這樣。
寫作,從明天開始。它已經不可能再有消失。我給自己放一天假:暗黑破壞神,我使用法師,使用冰系、電系、火系的魔法和游戲中的惡魔作戰,這一戰斗是古老的也是新鮮的。
6
夢見改變了我的方向,它給予了另一個結局,不期而至:那天晚上,我夢到了父親,夢到了一個集市和擁擠的眾人。它是夢,所以我們都比此時年輕。夢里的父親沒有輪椅,他當然不需要這個,他需要的是氣球——他把買到的氣球遞給了我的兒子。
意外的是,夢里的父親真正有了飛翔。
夢中的父親背景高大,他拉著我兒子向前,擠開眾人:眾人的中間,有一架黑色的滑翔機,不是電視里出現的那種,它更像是一臺由舊鐵組成的機器,沒有機翼——機翼,是在我父親飛翔起來之后突然出現的,他帶著巨大的轟鳴絕塵而去,消失于遠方(直到寫下這段文字,我才意識到我的兒子在他爺爺坐進滑翔機內的時候就沒有了蹤影,在那么多人之間,我沒有半點兒為他的擔憂。在夢里,他還是個孩子,沒有一米八的身高)。
“出事了,”有人喊,接著眾人朝遠方涌過去……我愣了一下,一種不祥的預感讓我驚醒,這時天已經大亮,妻子已在客廳:那日的NBA七點開始,她喜歡的詹姆斯迎戰馬刺。“我剛才做了個夢,”我對她說,“它,可能會改變小說的方向。”“什么?”
是的,方向,我決定放棄父親到操場指揮籃球訓練的描述,有了這個結局,那個故事和其中的寓意已不重要——我將把我的這個夢作為結尾,而它,或多或少會分解結尾的力量,而且會使小說變得過于綿長,我以為。我需要為小說建立平衡,哪怕是種“危險的平衡”,而父親到操場指揮的篇幅不會太少,當我加給它的力量過大時,那結尾的,父親乘坐滑翔的機械飛走的力量勢必遭受影響——我無法將二者變成合力,讓它們產生“共通感”——有一個有關雕塑的故事,羅丹為巴爾扎克雕像。像雕成了,它幾乎是完美的,尤其完美的是巴爾扎克的那雙手,所有的觀眾都對它的存在發出驚嘆……結果是,暴力的羅丹使用了斧子。他砍掉了“巴爾扎克”的手——因為,它奪走了對巴爾扎克神情的注視,而那,則是羅丹更為重視的。對于這篇小說而言,我也只得使用斧子,無論有著怎樣的惋惜。同樣讓我惋惜的還有之前想好的結尾,相對而言,夢中提供的這種似乎更有意味。在確定使用夢境提示的結尾之后,它依然有小小的分叉:一是,按照夢中的提供,父親坐上滑翔機,在巨大的轟鳴中飛走,越來越小,直到我們再也找不到它,天空中只剩下灰蒙蒙的空;另一則是,這是一次有故障的飛行,笨拙的父親手忙腳亂,他的操作出現了錯誤——當我們,趕到出事的地點,他正從泥濘之中濕漉漉地爬出來,而舊鐵組成的滑翔機已經摔得不像樣子。
這兩個結局有著各自的……我將它們放置在天秤的兩端,然而我的這架天秤始終擺蕩不已——好吧,暫時放下,反正它只會在后面出現,我可有思考的時間,在這個細節上可以暫時不做糾纏:現在,開始。
7
我說,“把我的父親囚禁起來的是……一次車禍。據說他本可躲過那劫,然而一向善于奔跑的父親卻突然在路中停了下來,直到失控的桑塔納2000將他撞飛出去——那么高,超越了他所能的想象,他感覺自己在天上飛了一天或者更久……”我讓它成為敘述的支點,有了這個支點,故事就有了泉眼。我想,這篇小說的敘述,嗯,中速略慢,我讓它帶出一點松木的、樹脂的氣息,同時帶出的還有——日常生活的粘稠度,是的,是這個詞,粘稠度,這篇文字應當較上一篇《會飛的父親》更粘稠些,我要更多地加入生活和計較的雜質,我要讓妻子、弟弟、弟媳、母親一同參與到這則故事的渦流并成為其中的部分,至于兒子……他不出現。在有了各自的分擔之后,作為“人物”他沒有特別之處,沒有特別需要的承擔。
我承認所有原型都來自我的家人,我只會雜揉一些很小的“雜質”進去:小說里的母親既是我的母親,不過我把我大姨的一些性格、對事情的處理方式會添加在她的身上。弟媳,她的存在是重要的,我想象她是——是的,“一切都對我有用——我聽到的事情,我看見、讀到的東西;總之,任何東西都以某種方式給我正在做的工作提供幫助。我變成了一個貪食現實的人。但是,要達到這一境界,我必須經歷那種苦修、苦練的工作。”
第一節,車禍。父親陷入了輪椅。語調平緩,短促,介紹性的小節。
第二節,父親將自己囚禁起來。他會把自己囚禁在臥室的房間里。在囚禁之后他是沉默者,他不說話或者只有最簡單的表達,喧嘩的是我們,我們試圖對他“理解”也試圖以另外的力量拉拽他——這是起點,點到為止。
第三節,喧嘩需要繼續。不止一件樂器。母親的,她是言說的核心,需要在敘述中建立固定機位:她的不滿,怨懟,憤恨,惱怒。對她的勸慰當然要用其它的樂器演奏,它們停在一個低頻,時斷時續……之后,場景轉移,母親退場。這一章節父親并不出現,但他,一直占居于話題的核心。
記得有次講座,李敬澤談及《紅樓夢》,他說大觀園里的姑娘媳婦們遇人說的都是頗讓人順耳的客套話、恭維話,但里面卻總有不經意包裹著的小刀片。好吧,某些刀片可以借來使用。
第四節。弟弟和弟媳試圖說服我們,讓父親和我們住在一起——這個提議遭到拒絕,這個拒絕來自父親。父親堅持著自我的囚禁,它會得到再次的強化。他是一座孤島。其實母親也是,我和我們也是。不過,車禍和車禍所帶來的,讓父親的孤島性質得到進一步的彰顯……這是我在寫作這篇《會飛的父親》之前就預留的寓意,它會進入到顯微鏡下——當然,作為策略,我不讓父親言說,不讓父親過多地參與到言說,他和他的,要盡可能通過我們的喧嘩勾勒出來。故事里的其他人盡可能地呈前,行動著言說著,而父親則像一團影子。這團影子慢慢地,成為固體的性質。
敘述依然緩慢,粘稠,雜質紛多,有一股緩緩下墜著的傾向。
它成為一件和耐心比賽的事情。我站到閱讀者的角度,思量:它就一直這樣下沉?我的耐心即將耗盡,是否還要再堅持一下,再一下下?我承認我在猜度,博弈,既要盡力地拉伸閱讀者的耐心又同時不至讓它耗盡。它會有個臨界的點,我嘗試著找到它,在盡可能靠近之處將它拉升起來。我是一個匠人,我懂得……這是阿赫瑪托娃的一句話,掉書袋的嗜好又一次回到我的身上。
我且加入一點寓意在里面……飛翔成為渴望,越是不可能,它則越強烈一些。從日常中飛走,或許是父親積蓄很久的愿望,而當這種可能被完全地截除之后……但父親,事實上,父親不會談到它,絕對不會。我懂得這個父親,他是我的父親同時也大抵是我,不會。是的,所有的寓意都不會自動呈前,在此時的故事和結尾的飛翔之間,需要一個鋪墊,它既是一層的波瀾同時也是通道:我怎樣,能讓父親在集市上的飛翔成為他堅持的可能?要知道,他坐在輪椅上,不肯見人。要知道,讓他不顧我們和管理者的反對而以殘疾人的身份堅持坐上滑翔機,需要力量也需要合理性……我突然意識到這個結局有某種的突兀感,風箏的樣子,而我之前的所做都是沉的實的,而沉下、落實也是這篇小說的主體基調,不能傷害它。我,應當設置一個怎樣的情境,細節,波折,讓父親不言說的這個“渴望”以一種生活態的樣式呈現出來?
這是個問題。它需要得到解決。還以水流比喻:水流下來,經過溝,壑,受石頭和坡地阻擋,樹枝和樹葉的阻擋,它變得曲折,也會沖開某些并不堅固的,攜帶它們順流而下。現在,水流遇到的是一個高大的坡,它被囤積,旋轉,積累……堰塞感。我要為這條水流尋找恰應的去處。去處在那兒,它已經早早地被固定下來,這沒什么好丟臉的,問題是,我得采取手段讓它越過,沖刷,最終匯入。真得費思量。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要不要,為父親的車禍建立“秘密的理由”,給它延接毛細血管?我承認早有預謀,在第一節的敘述中,我讓父親停在路中的原因成迷,不做解釋——父親,在我們所見的日常生活之外還有另一種生活,秘密的卻是屬于他更渴望的?父親,在那個秘密生活中,他的孤島性質會不會得以緩解或者稀釋,還是基本等同于我們所見的日常,釋放和遮掩同樣在著?
為什么你要旅行?
因為房子太寒冷。
為什么你要旅行?
因為旅行是我在日落和日出之間常做的事。
你穿著什么?
我穿著藍西服,白襯衫,黃領帶和黃襪子。
你穿著什么?我什么也沒穿,痛苦的圍巾使我溫暖。
你和誰睡覺?
每夜我和不同的女人睡覺。
你和誰睡覺?
我一個人睡覺,我總是一個人睡覺。
你為什么向我撒謊?
因為實話像別的不存在的事物一樣撒謊,
而我熱愛實話。
你為什么要走?
因為對我來說什么都沒更多意義。
你為什么要走?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馬克·斯特蘭德,《獻給父親的挽歌》。又一次想到了它。它曾在我的長篇《鏡子里的父親》中鑲入,我喜歡這首無以倫比的詩,充滿著深意和悖論和悠長意味的詩——我準備再一次將它給予這個父親,它的血液將融入于小說敘事的血管里——或許,我應當為父親安排另一個女人。或許,那個女人其實一直拒絕。他去找那個女人,她不在,或者她有別的客人,反正我父親只得悻悻地返回,結果遭遇了車禍。或許,我可以安排弟媳打聽到這些,她在其中添油加醋之后盡數倒給母親,而母親則……如此延此方向,留給母親的戲份會得到驟然地加強,它會成為另一股水流,不是匯入而是向另外的方向流出——我當然可以給它設計終點,讓它不至于奪走太多,何況這一細節的加入會使小說生出更多的繁復和厚重來……
這是又一個費著思量的問題,需要仔細權衡。一個小時。兩個小時。我在電腦前發呆,隨手抄起些什么:《鱷魚街》,《希尼詩文集》,《特朗斯特羅姆詩選》……它們沉默著,用自己的聲音沉默,不肯為我決定。另一個女人。另一個女人。她應當是怎樣的一個人?又一個小時,天暗下來,外出的妻子回來做飯。七點半,CBA比賽,妻子討厭馬布里的北京而喜歡易建聯的廣州,這一毫無理性的偏見讓她的觀看有著太強的傾向性。我也跟著觀看比賽,有意遺忘剛才的思量,反正暫時沒有結果,不如……比賽結束。受挫的妻子很是忿忿,而我重新坐到了電腦前。半個小時。我用游戲來打發,玩著蜘蛛紙牌——
之后的決定有著偶然的成分:我決定不做銜接,讓它只是空出的線頭,父親在車禍之前的前史我不做任何的交待,我也不準備為他再找那個一直面容模糊的女人了。我要和馬克告別,他不在這里,不出現,實在抱歉。
分掉的力量我可以補回,但,另一個女人的出現,會讓小說進一步變“俗”。它會滑向平庸,讓我成為第三十個把女性比喻成鮮花的詩人,我以為。當然,如果加入前史,我也必須在前面重新設置埋伏著的支點:它不能憑空出現——天上掉下個林妹妹,這樣的小說中不能。小說當然是弄虛作假,但它在它開始建立的邏輯中或伸或展,它也必須有讓人“信以為真”的力量——我也沒有太多的興趣掘開路面重新鋪設一條新管線。
8
“首先,有個想法,一種圍繞某個人、某個處境的推想、某種只是發生在心里的念頭。然后,我就動手記下來,做卡片,寫出故事脈絡——人物從這里開始,到那里結束;另一個人物從這里開始,在那里結束——總之,拉出一條條小小的線索來。等我一旦動手創作時,首先把故事的總框架搭起來——可是從來也沒有按框架寫過,因為一寫起來我把框架就完全改變了;但這個總框架對于我開始動筆還是很有用的……”巴爾加斯·略薩曾這樣說過。他如此,于我心有戚戚地談到小說的生成,從一個想法、一個圍繞某個人、某個處境的推想開始,然后搭起框架——可當我一開始寫作,這個框架就開始改變,我添加,抽掉,解除,又重新找回……略薩說,在動筆之后他就不去操心,“而且寫得很快”——在我這里,情況卻往往不是如此。我的時間會停滯,為一個場景,細節,一句對話,一個詞,一個詞的移動……
我寫得很是緩慢。但一直試圖,讓它呈現出仿佛是信手拈來的樣子。
9
第五節、第六節、第七節,敘述再一次放慢,集中于一日,讓這一日長于……這一日,被安排在除夕,在新和舊的支點上,我和父親,和所有的家人當然希望這一日后舊殼蛻去而新生開始,盡管那樣要求時間有些牽強。放在這一日,還因為它總是被過多地賦予,譬如歡樂,譬如團圓,譬如親密與和氣,譬如相互的恭維——這是復雜的一日也是具有表演性的一日。在小說之外,在我的日常中,它也是如此:復雜的一日和具有表演性的一日。在虛構中,父親折斷了腿,被安排的復雜和表演中必須注意到它:“一家人,都付出著小心,仿佛在房間的某處埋藏著小小的炸藥,它,很可能因為某句話的火花而發生爆炸,而每個人,在這樣的爆炸當中都會受損。”
它本不在預想之內。它是偶然想到的,在我處理堰塞、挖掘新水渠的時候。我覺得其中包含著一縷微弱的光,它來自于電視:我安排,父親在這個復雜和表演的日子里做出了妥協。他要打開自我虛擬的、柵欄上的鎖,進入到客廳里:讓他合理地進入客廳也頗費腦筋,我當然不能使用強力,它不會有效。于是,我安排了客人,我安排客人和父親的熱絡關系,那些由他將父親“推到外面”則完全可能,何況是這樣一個日子。好吧。這個活,交給招喚出來的客人做。
這,不能本質性地解決問題,父親還要退回,是的,我需要設計他的退回,否則故事就失去了它的曲蜒,父親性格里的固執也就無從得以體現——要知道,他是那種我所習見的“家長們”,那些父親們的行事中都有不可違背的乖張,這一點應當得到體現。好吧,他還要退回,我設計在午飯之后——怎樣把父親重新拉回客廳里,讓他坐在電視旁觀看?經過一番的挑撿,掂量,我安排家人們在下午離開,只有我在——終于,父親不再拒絕。電視。體育臺。這是生活里我父親的習慣,我把他的習慣同樣拿來,塞給輪椅上的父親,讓他目不轉睛滑翔,電視里的滑翔。那時,我還將它看成是鋪墊,是一個過渡性的波瀾,它要沖出缺口,在已經想到的結尾處形成高潮。這時,我讓父親反復地提到自己的腿。他注意著,也試圖讓我注意到——一向孤島著的父親,在這個復雜著的節日里開始言說,當然,這也是被積蓄起的。
我寫下眾人們的忙碌。我要讓父親依然處在“孤島”的位置上,盡管他已經來到客廳,就在我們進進出出、說說笑笑的范圍之中。這時,塞入一點寓意的想法又一次沉渣泛起,他可以有個杯子,他可以“不小心地”制造玻璃破碎的聲響引起注意,或者,“我看見父親哭泣時的情景”,他故意捶著自己的腿,把輪椅搖得吱吱響……過去在家里一向強勢的父親已經變成“軟殼的蝸牛”,可他,還有力氣將怨憤、惡毒和不甘向我們釋放出來,他不允許我們忽略他的存在尤其是他的痛苦,特別是在這樣一個節日里——“弱者,往往施虐于更弱者”——在前面,母親的言語中已經有所攜帶,它不需要太多補救性的鋪墊工作……不過我沒有那樣書寫。
我需要把所有的羽毛都扎入鳥的肉里去,并連接血管和神經。新想出的細節當然是漂亮羽毛,但連接工作讓我卻步——這時,故事的匯聚已經基本完成,它有了喧響,枝外的枝能舍就舍——至少在這篇文字中應當如此。我承認我越來越喜歡在我的作品中有更多的繁復的容納,但,但是,就短篇而言,我必須克制讓它無限制繁衍的可能。它需要一個相對的、具有圍繞感的核心。在這里,這個核心應當是,飛翔。
10
父親盯著電視。而電視里,山坡上的滑翔依然在繼續。“此時,它采用的是裝在滑翔傘上的‘主觀鏡頭’,它在飛,從這個角度可以看見景色的倒退,起伏和抖動。父親沒有注意我們的來來往往,而是,再一次把自己沉進了電視里,他的身體隨著鏡頭的變幻而調整著,或者左側,或者右側,或者抬頭……父親在飛翔,一個健全的父親在飛翔,這時他完全忽略了“在這邊”的生活,忽略了自己頭上漸多的白發和有著復雜氣味的身體,忽略了折斷的腿和里面的釘子,忽略了胃痛、絕望和不安——他和電視里的那個飛翔者融成了一個。他聽得見風聲的呼嘯,他感覺得到身體的起伏,感覺得到在氣流中攀升時的艱難,感覺得到來自山谷的巨大吸力,感覺得到風吹打在臉上時的抖動,他……在經過他身側的時候我偷偷看到,父親的眼里含著淚水。”
這段文字出現之后,我才恍然,它應當是結局,這是最后一波的高潮,夢里出現的那個飛翔已經不再需要。它提示了我,而我故事的構架也一直盡力地伸向它,但到此,它大約會是蛇足——不,在這篇題為《會飛的父親》的小說中,我要,始終將父親按在低處,我不給他飛起的機會,一次也不給,一點兒也不給,我給的,只是……一個想法。一個愿望。而已。
我要囚禁住他。其實,源自于生活的力量更大,我以為。
(責編:王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