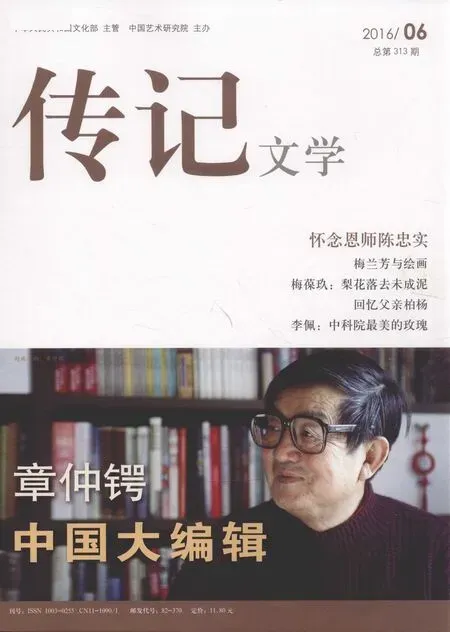“孤島”兒女(六)
文 楊世運(yùn)
“孤島”兒女(六)
文楊世運(yùn)
謹(jǐn)以此作品
獻(xiàn)給為拯救國(guó)難而獻(xiàn)出青春和熱血的中華優(yōu)秀兒女們!
【長(zhǎng)篇紀(jì)實(shí)文學(xué)】
第八章 慶功酒
四
他豈能甘心,第二天又趕到金寶花園,在案發(fā)現(xiàn)場(chǎng)里里外外,像一只獵犬似的東嗅西嗅。圍墻他察看過(guò)了。圍墻外的死胡同他也來(lái)來(lái)回回走了不知多少趟。學(xué)校的教室更沒(méi)放過(guò),連窗玻璃都敲掉了好幾塊,也沒(méi)收集到什么疑點(diǎn)。
正午太陽(yáng)當(dāng)頂,他還在花園里轉(zhuǎn)悠。天氣太熱,他脫了皮鞋只穿一雙拖鞋也覺(jué)腳指間不舒服,一屁服就坐在水泥小路上,翹起臭腳摳腳丫子。突然他靈機(jī)一動(dòng),眼睛盯住了鑲嵌著鵝卵石的水泥小路。畢竟他曾受過(guò)軍統(tǒng)的專業(yè)培訓(xùn),此刻他就在這小路上重新動(dòng)起了腦筋。冀老爺子就是在這條路上散步時(shí)被打死的,槍手選定了有利地點(diǎn)有利時(shí)間。可是,槍手怎么會(huì)知道老爺子有一早一晚散步的習(xí)慣呢?又怎么知道老爺子散步的地點(diǎn)必定是這條鵝卵石小路?會(huì)不會(huì)是個(gè)內(nèi)鬼?如果是內(nèi)鬼,此人又會(huì)是誰(shuí)?命案早不發(fā)生晚不發(fā)生,為何偏偏發(fā)生在老爺子做大壽的第三天清晨?會(huì)不會(huì)是祝壽的人中混進(jìn)了可疑之人?如果是這樣,這個(gè)可疑之人會(huì)不會(huì)到花園來(lái)踩過(guò)點(diǎn)?在這鵝卵石小路上留沒(méi)留下過(guò)足跡?
越往下推想,鄢紹寬越是心花怒放,耳畔似乎已聽(tīng)到丁、李二主任和日本人的夸獎(jiǎng)聲,飛黃騰達(dá)的日子觸手可及。他要趕緊回76號(hào),要求照相高手陪他再來(lái),拿上專用照相機(jī),把花園里、小路上近日留下的足跡全都照下來(lái)!
鄢紹寬興奮不已,急著回76號(hào)。女主人金寶留他吃過(guò)午飯?jiān)僮撸f(shuō)不必。金寶要叫司機(jī)開轎車送送他,他說(shuō)那更不必,“我必須依然低調(diào)行動(dòng),裝成個(gè)查電線的電工,提上我的電工箱,連黃包車都不能坐,一路步行回去”。
回76號(hào)的路上,鄢紹寬的后背也像長(zhǎng)了眼睛,高度的警惕加小心。終于離開租界,進(jìn)入完全由日本人掌控的滬西地區(qū)。抗日分子們把這里稱作“滬西歹土”,鄢紹寬卻認(rèn)為這里是他的自由天堂。抬頭望,76號(hào)越來(lái)越近,他更加覺(jué)得輕松愉快了。
76號(hào)被上海老百姓稱為“殺人魔窟”,行人經(jīng)過(guò)這里都要繞道走,就怕招惹麻煩。離76號(hào)不遠(yuǎn)處的一條弄堂名叫康家橋,過(guò)了康家橋,更是76號(hào)的絕對(duì)安全地段。康家橋開了一家白鐵店、一家食品店和一家香煙雜貨店,這其實(shí)都是76號(hào)的“眼睛”。香煙店的女老板原來(lái)是江湖上的姐妹,和佘愛(ài)珍關(guān)系甚密,30多歲,頗有幾分姿色。鄢紹寬早就對(duì)她有意,只恨自己職位太低,不敢高攀。現(xiàn)在,鄢紹寬想到自己馬上就要立功就要高升了,心中得意,腳步輕快,一搖一晃搖進(jìn)了香煙店。
“來(lái)包煙,揀最貴的!”
“什么事這么高興,臉上藏不住笑?”
“高興事確實(shí)有,不過(guò)現(xiàn)在不是對(duì)你說(shuō)的時(shí)候。”
“啥時(shí)候說(shuō)?”
“等我請(qǐng)你喝酒的時(shí)候,就不知你給不給面子?”
“喝酒我當(dāng)然要去,不給你面子,還能不給酒席面子?”
“一言為定?”
“就等你一聲‘請(qǐng)’字。”
“小生這廂告辭了。”
“走你的吧,多準(zhǔn)備點(diǎn)好酒好菜。”
鄢紹寬心里歡喜,出了店門卻迎頭撞見(jiàn)一樁觸霉頭的事:一個(gè)年近20歲的叫花子,身上臭哄哄,大夏天還穿著一件黑黢黢的破棉襖,一張?bào)a臟的臉像是八輩子沒(méi)洗過(guò),伸出一只黑手,向鄢紹寬要錢。
“滾!也不看看這是什么地方,要飯要到閻王殿了!”鄢紹寬怒吼道。
叫花子卻不識(shí)時(shí)務(wù),纏住鄢紹寬不放,一雙臟手扯住鄢紹寬的白襯衣,頓時(shí)衣服上染上一片黑。鄢紹寬怒火中燒,拳打腳踢,把叫花子掀翻在地。叫花子在地上亂打滾,突然一翻身,抓起鄢紹寬放在地上的“電工箱”,爬起來(lái)就朝公共租界方向猛跑……
小赤佬,敢順手牽羊拎走老子的箱子,這還了得?“電工箱”里裝的是鄢紹寬的緝偵工具,還藏有一把手槍!“站住!看老子不整死你!”鄢紹寬拔腿就追趕。
香煙店女老板站在柜臺(tái)內(nèi)哈哈大笑,笑得直不起腰。一笑叫花子不知天高地厚,竟然跑到康家橋來(lái)要飯,不要命了!二笑鄢紹寬好窩囊,堂堂一個(gè)76號(hào)的特工,竟叫一個(gè)渾身破衣?tīng)€衫的小叫花子搶走了箱子。當(dāng)然小叫花子無(wú)異是虎口拔牙,他怎么能跑得過(guò)鄢紹寬?等被一把抓住,小命就玩完,明年的今天是頭周年。等鄢紹寬收拾掉小叫花子返回,女老板準(zhǔn)備要好好取笑他一番。
鄢紹寬追趕小叫花子,小赤佬怎么跑得比兔子還快?鄢紹寬越追心越慌,天啦,若叫他跑進(jìn)了租界可就麻煩了,抓住他后還不好當(dāng)場(chǎng)就把他弄死,難出一口鳥氣!“小赤佬!別跑了!”
只見(jiàn)一位衣著體面的先生遠(yuǎn)遠(yuǎn)地迎面走來(lái)。此人綢衣綢褂,腳穿真牛皮涼鞋,頭戴一頂太陽(yáng)帽,鼻梁上架一副太陽(yáng)鏡,蓄著一撮小胡子,一看就知道是個(gè)日本人。鄢紹寬像遇到了救星,忙用半生不熟的日語(yǔ)又叫又比劃:“太君!攔住小偷!”
體面的日本先生會(huì)意,迎面攔住小叫花子,順勢(shì)奪過(guò)“電工箱”。
“好!”鄢紹寬一聲歡呼。呼聲未落,只見(jiàn)體面的日本人胳膊一揚(yáng),將木箱摔向空中,木箱飄飄然向鄢紹寬飛來(lái)。
“太君好功夫!”鄢紹寬一邊贊嘆,一邊抬頭揚(yáng)臂來(lái)接木箱。突然,只聽(tīng)“咣”、“當(dāng)”兩聲,木箱沒(méi)接住,落在了地上,而鄢紹寬也緊隨其后,身子朝前一踉蹌,撲倒在地。
過(guò)路的人們不知發(fā)生了什么事,紛紛躲避。一眨眼功夫,小叫花子和體面的日本人便已消失得無(wú)影無(wú)蹤。
“人去了這么久,箱子怎么還沒(méi)追回來(lái)?”香煙店女老板等了好久,等得不耐煩了,出店來(lái)觀望。遠(yuǎn)遠(yuǎn)的,她望見(jiàn)馬路上倒下有一個(gè)黑影,不用猜,是小叫花子被鄢紹寬給弄死了,像碾死了一只螞蟻,活該。可是這個(gè)鄢“金條”,他跑到哪里去了呢?
又過(guò)了許久,仍不見(jiàn)“金條”的身影。女老板感到奇怪,關(guān)了店門,順馬路往前走,看看那個(gè)被弄死的尸體是不是小叫花子。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死在地上的竟然是鄢紹寬!槍口在腦門子上。摸摸鼻子,早就沒(méi)氣了!
讀者朋友無(wú)須猜想便已明白,“小叫花子”便是鄭鐵山,而“日本太君”則是周鶴鳴。
五
魯婉英在金寶花園待了幾天,無(wú)時(shí)無(wú)刻不在惦記周鶴鳴。
終于等到金寶干娘發(fā)出話來(lái):“老七,你伺候了我這幾天,該歇歇了,回去吧!”
魯婉英像接到了特赦令,火燒火燎趕回妙香樓。上了三樓趕緊推開鶴鳴的書房,房里空蕩蕩沒(méi)有人。又慌忙到鄭鐵山住的小屋里尋找,也沒(méi)有人影。
迎面遇見(jiàn)了小桃紅,魯婉英忙問(wèn):“見(jiàn)著周少爺和小茶壺沒(méi)?”
小桃紅答:“見(jiàn)著了呀!”
“啥時(shí)候見(jiàn)著的?”
“就今天呀!”
“那他們現(xiàn)在人呢?”
“可能又到四馬路逛舊書店去了。”
“逛書店?”
“你走了這幾天,他倆閑得慌,就天天出去逛舊書店,買便宜書。有時(shí)候一逛就是大半天。”
“我的天,書呆子呀,都什么世道了,天天看書有啥用場(chǎng)?”
魯婉英懸著的一顆心放了下來(lái),急忙出門,要親自把她的鶴鳴給找回來(lái)。剛出來(lái),卻見(jiàn)周鶴鳴和鄭鐵山有說(shuō)有笑地正往回走,每人手里都捧著幾本線裝老書。
回到妙香樓,關(guān)緊書房門,魯婉英忙對(duì)周鶴鳴交代道:“鶴鳴,這些日子你和鐵山千萬(wàn)別再出門了!再近的地方也別去!”
“為什么?”
“你倆哪里知道,現(xiàn)在外面太危險(xiǎn)了!就在冀干爹被打死的第三天晌午,76號(hào)的一個(gè)人也被打死了!”
“啊?在哪兒給打死的?”
“在康家橋,離76號(hào)不遠(yuǎn)!”
“誰(shuí)被打死了?”
“你還記得不,那天給老爺子拜壽,我指給你看過(guò)這個(gè)人。”
“不是他倆,是鄢紹寬!”
“鄢紹寬,鄢紹寬……”
“就是那個(gè)長(zhǎng)脖子大金牙,外號(hào)‘金條’,76號(hào)的破案專家。”
“是他呀,他為什么被打死?得罪了誰(shuí)?”
“他誰(shuí)也沒(méi)得罪,怪只怪他接連跑到金寶花園,這里偵偵哪里探探,想要探出是誰(shuí)打死了冀老爺子。那邊的人不打死他打死誰(shuí)?”
“哪邊的人?”
“不是共產(chǎn)黨,就是重慶分子。聽(tīng)說(shuō)這個(gè)槍手厲害得很,會(huì)飛檐走壁,來(lái)無(wú)影去無(wú)蹤,打槍不用瞄準(zhǔn),專打天靈蓋!連76號(hào)的人都害怕了,到處設(shè)暗哨要抓到這個(gè)人,你倆這些日子千萬(wàn)別再出門!”
“三哥,魯姐說(shuō)得對(duì),明天你別再去逛書店了!”鄭鐵山出聲附和。
“鶴鳴,你也別光是看書,煩悶時(shí)叫鐵山陪你下下象棋。”
鄭鐵山突然像想起了什么:“哎呀魯姐,你對(duì)你干娘家的人說(shuō)過(guò)什么嗎?”
“說(shuō)過(guò)什么?”
“你說(shuō)沒(méi)說(shuō)過(guò)我三哥見(jiàn)到過(guò)長(zhǎng)脖子大金牙?”
“沒(méi)有呀!我說(shuō)這干什么?”
“那你說(shuō)沒(méi)說(shuō)過(guò),你和我三哥在花園里看過(guò)花?”
“這個(gè)我更不會(huì)說(shuō),我們倆的私事,我擺給別人干啥?哎,鐵山,你咋突然問(wèn)起這些?”
“我怕我三哥遭人亂懷疑。”
“你也太多慮了,他們懷疑一千人一萬(wàn)人,也萬(wàn)萬(wàn)不會(huì)懷疑到我家人的人頭上呀!”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wú)。不怕一萬(wàn),就怕萬(wàn)一。”
“鐵山你提醒的也對(duì)。你放心,有魯姐在,誰(shuí)也休想動(dòng)你三哥一根手指頭!”
第九章 走進(jìn)魔窟
一
76號(hào)增兵布陣四處搜尋槍殺冀墨清、鄢紹寬的槍手,忙了好幾天連個(gè)影子也沒(méi)搜著。
但沒(méi)想到卻有了意外收獲,捉到了另外一條大魚:軍統(tǒng)局上海情報(bào)站站長(zhǎng)熊劍東。
熊劍東,又名熊俊,浙江省新會(huì)縣人,曾留學(xué)日本士官學(xué)校,歸國(guó)后在馮玉祥將軍的屬下當(dāng)參謀。此人文武兼?zhèn)洌瞬烹y得。抗戰(zhàn)后他臨危受命,被任命為軍統(tǒng)局上海站站長(zhǎng),兼任國(guó)民政府軍事委員會(huì)行動(dòng)軍淞滬特遣分隊(duì)長(zhǎng),又兼任嘉定、太倉(cāng)、昆山、淞江、青浦、常熟六縣游擊總司令。他把家安置在上海租界內(nèi),化裝成生意人從昆山回上海看望夫人,不幸被76號(hào)的暗哨抓捕。
一定要救出熊站長(zhǎng)!軍統(tǒng)局局長(zhǎng)戴笠親自下達(dá)了死命令。
這本來(lái)是軍統(tǒng)的事,但齊紀(jì)忠聽(tīng)說(shuō)后卻心情激奮,躍躍欲試。他立即面見(jiàn)陳而立站長(zhǎng),陳述自己的想法:軍統(tǒng)、中統(tǒng)是自家兄弟,營(yíng)救熊站長(zhǎng),我們也應(yīng)當(dāng)出一把力。
陳而立感到為難:“你的想法當(dāng)然不錯(cuò),但是日本人現(xiàn)在抓到的是一條非比尋常的大魚,76號(hào)的漢奸特務(wù)們高興得大擺宴席慶賀。他們一定會(huì)嚴(yán)加防范,我們?cè)趺慈ゾ龋俊?/p>
“硬來(lái)當(dāng)然不行,必須智取。”
“怎么智取?”
“要完成這一艱巨任務(wù),我想好了一個(gè)最合適的人選。”
“誰(shuí)?”
“鄭蘋如。”
“鄭蘋如?不行不行萬(wàn)萬(wàn)不行!”
“為什么不行?”
“她畢竟是個(gè)女孩子呀,眼下也不過(guò)才20歲,如果不是戰(zhàn)爭(zhēng),她的生活天地應(yīng)當(dāng)在教室,在圖書館。可是現(xiàn)在,我們已把她發(fā)展為編外人員,她為我們的工作盡了那么多力,我們應(yīng)當(dāng)感謝她,也應(yīng)該保護(hù)她。她利用她的有利條件收集情報(bào),我看就目前這種狀況就可以了,不可再給她布置危險(xiǎn)的任務(wù)。”
“營(yíng)救熊站長(zhǎng),恰恰這件事對(duì)于鄭蘋如來(lái)說(shuō)不會(huì)有任何危險(xiǎn)。”
“為什么?”
“她有別人所不具備的得天獨(dú)厚的條件。”
“你是說(shuō)她會(huì)一口流利的日語(yǔ)?會(huì)日語(yǔ)又怎能救出熊站長(zhǎng)?”
“不是會(huì)日語(yǔ)這個(gè)條件,你聽(tīng)我慢慢對(duì)你說(shuō)……”
二
齊紀(jì)忠約鄭蘋如見(jiàn)面,地點(diǎn)竟選在兆豐公園。
兆豐公園前門對(duì)愚園路,后門接極司菲爾路,地處滬西“越界筑路”地段,如今是日本人的天下。人們把滬西這一片豺狼橫行的地段稱為“滬西歹土”,生活在“孤島”內(nèi)的市民,除非迫不得已,都盡量避免離開租界來(lái)到這是非之地,以免遭遇無(wú)妄之災(zāi)。
愚園路,如今的“雅號(hào)”是“漢奸一條街”,因?yàn)橥艟l(wèi)“國(guó)民政府”的“達(dá)官貴人”大都在這條街居住,包括汪精衛(wèi)本人,還有周佛海、陳春圃、羅君強(qiáng)、褚民誼等等。吳四寶、佘愛(ài)珍兩口子,也早已搬家住進(jìn)了這“一條街”。
“齊先生,你怎么選這樣的地方跟我見(jiàn)面?”
“你放心,最危險(xiǎn)的地方也最安全,你忘了一句話嗎,燈底下最黑。”
“你考慮得真周到,我有時(shí)候很佩服你。”
“僅僅是‘有時(shí)候’佩服我?”
“齊先生,原諒我失言。你緊急約見(jiàn)我,有什么任務(wù)?”
“任務(wù)十分重要,我倆得慢慢走仔細(xì)談。來(lái),靠近我,別離得太遠(yuǎn)。”
“為什么?”
“你看這里是什么地方?這里是日本人的天下,是虎狼窩呀!為了不被人懷疑,我倆現(xiàn)在必須裝作一對(duì)情侶,你必須挽住我胳膊,挽緊一些!遇見(jiàn)了日本人,你得用日語(yǔ)同他們打招呼,明白嗎?”
“明白了。”
話音未落,只見(jiàn)兩個(gè)吊兒郎當(dāng)?shù)娜毡颈孀邅?lái),四只眼珠子直盯著鄭蘋如。鄭蘋如視若無(wú)睹,用日語(yǔ)對(duì)齊紀(jì)忠講話。兩個(gè)日本兵一聽(tīng)是日本小姐,趕緊溜開。
齊紀(jì)忠得意地一笑。
游園的日本人,一個(gè)個(gè)趾高氣昂,神情張狂,仿佛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他們的財(cái)產(chǎn)。鄭蘋如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悄悄對(duì)齊紀(jì)忠說(shuō):“你是叫我來(lái)受國(guó)恥教育的吧?”
齊紀(jì)忠回答說(shuō):“如今在上海,不可一世的日本人像逐血的蒼蠅,數(shù)量越來(lái)越多。虹口那一帶不算,日本人早已把那一帶稱為‘小東京’;而現(xiàn)在的滬西,也快變成他們的‘本島’了!七七事變之前,上海的日本人,日本兵不算,總共兩萬(wàn)多人,短短兩年多時(shí)間,翻了一倍多,將近六萬(wàn)人。特務(wù)來(lái)了,發(fā)橫財(cái)?shù)耐稒C(jī)商來(lái)了,就連一些浪人、地痞、流氓、無(wú)賴,也都蜂擁而至,都想從咱中國(guó)土地上大撈一把!”
耳畔突然傳來(lái)“嘿!嘿”的狂叫聲,像鬼哭狼嚎。原來(lái)是個(gè)日本浪人,一身武士打扮,光溜溜的腦袋上系著一條白布,布條上印有一張紅“膏藥”,雙手揮刀,正對(duì)著一棵大樹練刀功。樹干上貼有一張白紙,白紙上歪歪扭扭寫有“支那豬”三個(gè)字,這“武士”張牙舞爪,每向“支那豬”砍一刀,就惡狠狠地叫一聲“死拉死拉”,好端端的一棵大樹,已被砍得千瘡百孔。
鄭蘋如實(shí)在看不下去,拉著齊紀(jì)忠的胳膊拐向一條小路。
終于再聽(tīng)不到那“死拉死拉”野狼般的嚎叫聲,兩個(gè)人在長(zhǎng)椅上坐定,齊紀(jì)忠講出了新的工作任務(wù)。
“營(yíng)救熊站長(zhǎng)?怎么營(yíng)救?劫獄?”
“真是小孩子話,76號(hào)像鐵打銅鑄一般,劫獄從何下手?再說(shuō),劫獄這粗活兒,也用不著你動(dòng)手。”
“那讓我干什么?”
“你得去見(jiàn)一個(gè)人。”
“誰(shuí)?”
“你的校長(zhǎng)。”
“校長(zhǎng)?”
“你不是曾在上海民光中學(xué)讀過(guò)書嗎?”
“是呀!”
“這個(gè)人我當(dāng)然知道,我們天天都在和這個(gè)大漢奸做斗爭(zhēng),76號(hào)的一號(hào)頭目……”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什么其二?”
“現(xiàn)在我告訴你,這兩個(gè)人其實(shí)是同一個(gè)人。”
“啊?這怎么可能呢?你說(shuō)笑話吧?”
“哦,我想起來(lái)了!難怪前些日子我聽(tīng)民光中學(xué)的一位老師說(shuō),民光出了個(gè)大漢奸,原來(lái)說(shuō)的就是丁默呀!”
“他當(dāng)校長(zhǎng)時(shí),見(jiàn)過(guò)你沒(méi)有?”
“見(jiàn)過(guò)。”
“所以現(xiàn)在把重任交給你,你得以當(dāng)年學(xué)生的名義到76號(hào)去見(jiàn)丁校長(zhǎng)……”
“求他放了熊站長(zhǎng)?”
“是。”
“這不可能吧?他這條豺狼能聽(tīng)我的?”
“不妨試一試吧。你并非單兵作戰(zhàn),只要你能走進(jìn)76號(hào)見(jiàn)到姓丁的一面,后面的事我自有安排。”
“就沒(méi)有別的營(yíng)救辦法?”
“我們經(jīng)過(guò)了認(rèn)真推演,就這個(gè)辦法最有效,也最安全。”
三
民光中學(xué)的師生們,特別是女學(xué)生們,忘不了這個(gè)厚顏無(wú)恥的“丁校長(zhǎng)”。
可是現(xiàn)在齊紀(jì)忠要叫鄭蘋如走進(jìn)76號(hào),她該怎么辦?
見(jiàn)鄭蘋如猶豫不決,齊紀(jì)忠便反復(fù)做鼓動(dòng)勉勵(lì)工作。他說(shuō)組織上已做好萬(wàn)無(wú)一失的周密安排,只需鄭蘋如同丁默見(jiàn)兩次面就行。第一次見(jiàn)面,話不必多說(shuō),禮節(jié)性拜訪,速去速回。第二次去見(jiàn)面更加沒(méi)有危險(xiǎn),因?yàn)椴幌竦谝淮问青嵦O如單獨(dú)去,而是有人陪同,并且由陪同的人唱主角,鄭蘋如只是配角。
明知山上有虎,偏往虎山行。為了營(yíng)救抗日游擊隊(duì)總司令,鄭蘋如只能接受命令了。
殺人魔窟76號(hào)離千年古寺靜安寺不遠(yuǎn)。在走進(jìn)魔窟之前,鄭蘋如首先進(jìn)入神廟,祈求神靈的護(hù)佑。她虔誠(chéng)地拜了觀音菩薩,仿佛見(jiàn)到觀音正用滿懷憐憫的目光望著她。她求了一支簽,阿彌陀佛,雖不是上上簽,但也并非下簽,而是中上簽。解簽的讖語(yǔ)寫道:“鳥籠有門未鎖,魚池?zé)o餌有鉤,兇吉自在一瞬間。”
感謝菩薩指點(diǎn),我會(huì)小心再小心的,絕不可粗心大意,自投羅網(wǎng)。
離開靜安寺,轉(zhuǎn)個(gè)彎向西北方向走,幾分鐘之后就來(lái)到百樂(lè)門大舞廳之前。百樂(lè)門坐西朝東,正門外就是極司菲爾路(即今萬(wàn)航渡路)。繼續(xù)向西北方向而行,過(guò)了愛(ài)文義路(今北京西路)路口,就離開了公共租界,置身于陰風(fēng)慘慘的由日本兵控制的“滬西歹土”。
76號(hào)像一只狼眼睛,離愛(ài)文義路只有幾百米的距離,日夜露著兇光,窺視著租界。
今日的76號(hào),門牌號(hào)的顏色仍舊是藍(lán)底白字。
想起上海門牌號(hào)碼的顏色,鄭蘋如的心里也不能不哀聲長(zhǎng)嘆。
上海被列強(qiáng)們瓜分為租界地后,在外國(guó)人眼里,中國(guó)人就變成了“下等賤民”。租界內(nèi)因?yàn)槭峭鈬?guó)人的天下,門牌號(hào)碼的顏色便是亮眼的藍(lán)底白字。而華人區(qū)的門牌號(hào)碼,顏色不能“高攀”租界區(qū),只能是白底黑字。但是租界當(dāng)局對(duì)住在華人區(qū)的達(dá)官貴人網(wǎng)開一面,允許他們的門牌號(hào)碼顏色也使用藍(lán)底白字。76號(hào)的房主原來(lái)是國(guó)民政府的安徽省主席陳調(diào)元,因此才有破格享受藍(lán)底白字的“榮耀”。
鄭蘋如不由又聯(lián)想到在外灘公園門口曾經(jīng)掛出的那個(gè)牌子:“華人與狗不得入內(nèi)”。我的中國(guó)母親啊,你已被欺辱到了什么程度?哪年哪月,你才能擦干眼淚昂起頭來(lái)?你的女兒在為你抗?fàn)帲齽e無(wú)選擇,只能努力抗?fàn)帲?/p>
76號(hào)的大門,表面看起來(lái)沒(méi)什么特別之處,但門內(nèi)卻藏有玄機(jī)。
第一道門修有一座牌樓,非中非西,不倫不類。上海市民們私下議論:汪精衛(wèi)又要當(dāng)漢奸又要立“貞潔牌坊”,看看76號(hào)的牌樓,像不像個(gè)棺材蓋子?
為了掩人耳目,汪精衛(wèi)親自下指示,在76號(hào)的牌樓上畫了個(gè)國(guó)民黨的青天白日的黨徽,又寫上孫中山的一句話:“天下為公”,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天下為公”的后面拴著兩條狼狗。“青天白日”的圖案被挖了兩口黑洞,洞里是重機(jī)槍的槍眼。
進(jìn)入第二道門,面目更加猙獰。院子的東西兩側(cè)兩排平房,分別是“警衛(wèi)大隊(duì)”隊(duì)部和各個(gè)名目的“辦公室”,還有刑具俱全的審訊室,鐵窗森森的看守所。
第三重門,是大院子正中的“大洋房”的鐵門,戒備尤其森嚴(yán)。因?yàn)檫@里邊有丁默、李士群的辦公室、臥室,還有秘密的“重犯”牢房和女牢房,另外還有“犯人反省室”“宣誓室”等等。
在大洋房的西側(cè),還有一幢三開間兩進(jìn)的石庫(kù)門樓房。一樓經(jīng)過(guò)大拆大改,變成了一座大禮堂。汪精衛(wèi)政權(quán)的許多重要會(huì)議就是在這禮堂里召開的。禮堂里還經(jīng)常唱戲,來(lái)聽(tīng)?wèi)虻亩际峭艟l(wèi)、周佛海等高官和日本人。
大院子里還有一排十分顯眼的新建筑物,是別墅式的洋房,專供“太上皇”和他的“大臣”們居住。“太上皇”的“大臣”們?nèi)藬?shù)并不多,只有七八個(gè)人。而“太上皇”的軍銜也不高,只不過(guò)是個(gè)準(zhǔn)尉,連真正的尉級(jí)軍官的行列都未進(jìn)入,手下的七八個(gè)兵最高級(jí)別是曹長(zhǎng)。但是,別看他們官不大,權(quán)力可是比天還大。丁默、李士群雖屬“將軍”級(jí)要員,也得在他們面前點(diǎn)頭哈腰。
人們對(duì)76號(hào)談虎色變,而今天鄭蘋如一路走來(lái)卻是面不改色。剛走到大門外,就見(jiàn)一個(gè)青面獠牙的惡鬼突然沖出,手槍直逼鄭蘋如胸口:“站住!干什么的?”
鄭蘋如心一跳,趕緊鎮(zhèn)定下來(lái),用日語(yǔ)回答:“找人的。”
“什么?”惡鬼沒(méi)聽(tīng)清鄭蘋如說(shuō)什么,“別咕嚕,拿通行證!”
鄭蘋如不慌不忙,又說(shuō)了兩句日語(yǔ):“我是來(lái)找人的,要什么通行證?”
這一回惡鬼聽(tīng)明白了,我的個(gè)爺呀,原來(lái)來(lái)的是位日本小姐!立即換了一副奴才面孔,滿臉堆笑,哈巴狗似的點(diǎn)頭哈腰。鄭蘋如更加從容,微微一笑,又說(shuō)了兩句英語(yǔ),把面前的特務(wù)更弄得暈頭轉(zhuǎn)向。他豈敢造次,慌忙指使另一個(gè)特務(wù)快去搬救兵,自己在這里大陪笑臉,比手劃腳對(duì)日本小姐說(shuō)道:“你的,大大的貴客,請(qǐng)?jiān)谥蛋嗍业模淖模院蛏院虻模 ?/p>
鄭蘋如也邊用日語(yǔ)回答邊比手勢(shì):“謝謝,不用進(jìn)屋了,我就站在這里等你的長(zhǎng)官來(lái)接。”
懂日本語(yǔ)的“救兵”來(lái)了,他就是統(tǒng)治76號(hào)的日軍“最高司令長(zhǎng)官”澀谷準(zhǔn)尉。此人也確實(shí)有“司令”派頭,因?yàn)樗L(zhǎng)相酷似他崇拜的土肥原賢二將軍,也是圓鼓鼓的腦袋,肥頭大耳,鼻下一撮小胡子,并且在76號(hào)擁有至高無(wú)上的權(quán)力,因此常認(rèn)為自己就是一個(gè)大將軍。遠(yuǎn)遠(yuǎn)看到一位像櫻花一樣漂亮的日本小姐在等候,只覺(jué)得心花怒放,兩眼發(fā)光。見(jiàn)面后一對(duì)話,才知自己是白高興,小姐是來(lái)找丁默的。但是,能首先接待美女畢竟是件幸事,澀谷的熱情不減,親自為鄭蘋如帶路,一路暢通,把客人領(lǐng)到“大洋房”二樓丁默的辦公室。進(jìn)屋之后,他也同客人一起落座,并沒(méi)有離開的意思。
太好了,鄭蘋如心里想道:鳥籠外多一只洋狗,反而能牽制土狗了!
澀谷搖頭,回答說(shuō)他不屑于學(xué)說(shuō)中國(guó)話,因?yàn)橹袊?guó)人是劣等民族,中國(guó)話就要被消滅了,支那人將來(lái)統(tǒng)統(tǒng)都得說(shuō)日本話。“76號(hào)這里配有兩個(gè)日語(yǔ)翻譯,一男一女,你要喊哪一個(gè)來(lái)為你服務(wù)?”
鄭蘋如忙擺手,對(duì)澀谷說(shuō):“不用麻煩您了,我懂中國(guó)話,可以直接和丁主任對(duì)話。我從前認(rèn)識(shí)丁主任,多年不見(jiàn),今天從這里路過(guò),順便來(lái)看看他。您陪我坐坐吧,我說(shuō)幾句話就走。”
終于等到美女面對(duì)自己說(shuō)話,并且是一口流利的國(guó)語(yǔ):“丁校長(zhǎng),您好,打擾您了!”
“丁校長(zhǎng)?你怎么稱我丁校長(zhǎng)?”
“丁校長(zhǎng),您真是貴人多忘事,真的不認(rèn)識(shí)我這個(gè)學(xué)生了?”
“你是……”
“我是您在民光中學(xué)當(dāng)校長(zhǎng)時(shí)的學(xué)生呀!”
“噢,你這么一說(shuō)我覺(jué)得有點(diǎn)面熟了,讓我想一想……”
“我姓鄭,名叫鄭蘋如。校長(zhǎng)您忘記了嗎,那時(shí)您常常夸我說(shuō)我日語(yǔ)講得好,英語(yǔ)成績(jī)也好。您還經(jīng)常找我談話,鼓勵(lì)我。”
“想起來(lái)了想起來(lái)了!你爸爸是同盟會(huì)元老,你媽媽是日本人,東京的大家閨秀!你可是比那時(shí)候更漂亮了!嘿呀呀,真是女大十八變,越變?cè)胶每囱剑∈悄年囷L(fēng)把你吹到我這陋室來(lái)了?”
“丁校長(zhǎng)您可真會(huì)說(shuō)笑話,您這里層層設(shè)卡戒備森嚴(yán),到您這里來(lái)比進(jìn)皇宮還難,怎能說(shuō)是陋室?早聽(tīng)說(shuō)您現(xiàn)在是黨國(guó)要員,您的學(xué)生都為您驕傲,所以我今天從這里路過(guò),突然想起您,就進(jìn)來(lái)拜望拜望。想不到盤查得這么嚇人,早知道這樣就不來(lái)拜望了!”
“要來(lái)要來(lái),一定要常來(lái)!盤查是對(duì)別人的,你是我學(xué)生,當(dāng)然應(yīng)該例外!我給他們交代一聲,以后凡是你來(lái),通報(bào)了‘鄭蘋如’這三個(gè)字,就是通行證,一路綠燈!”
“丁校長(zhǎng)您真會(huì)開玩笑。”
澀谷聽(tīng)明白了,狗臉笑成了貓臉:“喲西,常常地來(lái)喲!”
“謝謝準(zhǔn)尉,謝謝丁校長(zhǎng)!”鄭蘋如準(zhǔn)備告辭。
鄭蘋如忙起身:“丁校長(zhǎng)再見(jiàn)!”
“咦?怎么剛坐下,茶還沒(méi)喝一口就要走呢?別走別走,就在這里吃午飯,我馬上交代接待室的人好好安排!”
“謝謝丁校長(zhǎng),我還有急事要去辦,只是順路先來(lái)拜望,認(rèn)個(gè)門路。”
“真有急事?”
“真有急事,在老校長(zhǎng)面前學(xué)生還敢說(shuō)假話?”
“那你哪一天才能再來(lái)?”
“我想來(lái)就來(lái),反正現(xiàn)在我們學(xué)校停課了,我有的是時(shí)間。”
“你在上哪所大學(xué)?”
“法政學(xué)院。”
“好,好學(xué)校!你們學(xué)校里有我的熟人,以后你有什么事需要我?guī)兔Γ嬖V我一聲。你爸爸媽媽現(xiàn)在怎么樣,身體都好嗎?”
“都挺好。丁校長(zhǎng)對(duì)不起我實(shí)在不敢多耽誤了,那邊還有人正等著我,我該走了。”
“那好吧,恭敬不如從命,我和澀谷準(zhǔn)尉一同送你出去。你可一定要常來(lái)常往喲,我隨時(shí)準(zhǔn)備歡迎你!”
四
“是的。我還見(jiàn)到了那個(gè)名叫澀谷的日本兵準(zhǔn)尉。”
“太好了,初戰(zhàn)告捷!”齊紀(jì)忠顯然對(duì)鄭蘋如的行動(dòng)十分滿意。
鄭蘋如也慶幸自己有驚無(wú)險(xiǎn):“謝天謝地,靜安寺的神簽太靈了!”
“什么?行動(dòng)之前你還到寺廟里抽簽了?”
“抽了個(gè)中上簽。”“你還信這個(gè)?”
“唉,我的一位好朋友說(shuō),人們?cè)绞菬o(wú)助,越是希望真有許許多多的神仙幫助,比如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還有灶神爺、土地爺、龍王爺、關(guān)帝爺……”
“你的什么朋友?男朋友還是女朋友?”
“男朋友呀!”
“叫什么名字?”
“名字你無(wú)須問(wèn),反正這人你不認(rèn)識(shí)。”“他現(xiàn)在在哪里?在上海?”“不在上海,出國(guó)留學(xué)去了。”“在哪個(gè)國(guó)家?”
“齊先生你不要打破砂鍋問(wèn)到底好不好,快接著說(shuō)正事吧!”
“嗯,現(xiàn)在我給你布置新的任務(wù)。”
“下一步,怎么行動(dòng)?”
“你?”
“我?我怎么能露面?”
“那是誰(shuí)?”
“唐逸君。”
“唐逸君是誰(shuí)?”
“唐逸君不是外人,她是熊劍東站長(zhǎng)的夫人。”
“噢……”
“這能行嗎?”
“這個(gè)你就不必操心了,我心里自有把握。”
“為什么?”
“等你見(jiàn)到熊夫人你就明白了。應(yīng)該怎么運(yùn)作,我已對(duì)熊夫人一一作了交代。這一回,得完全看她如何唱主角。你只須向姓丁的介紹,就說(shuō)唐逸君是你的大表姐……”
(待續(xù))
責(zé)任編輯/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