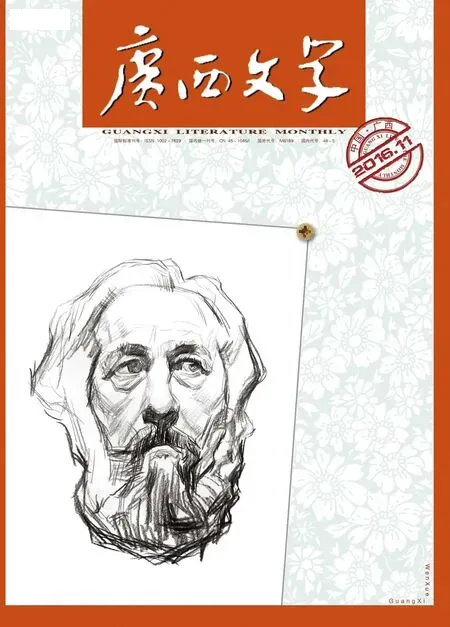拓夫的詩
2016-11-26 01:24:32拓夫
廣西文學 2016年11期
一個手拿彈弓的人
一個人
一個男人
一個年輕男人
站在公園樹下
他手拿彈弓
眼睛四十五度向上
那是一棵樹的某個枝杈
或一只不存在的鳥
或一個女人的面孔
或者干脆
就是天空
我在不遠處
靜靜看著他
他手里那顆彈子
始終沒有
射出
灰 燼
我把一沓舊信
拿到樓下空地
點燃
看紙一張張由白
變黑
熟悉的字一個個撲進火光
當我用一根棍子
撥動余火
灰燼借著風
回頭看了我最后一眼
老鼠過街
早上上班
看見一只老鼠
橫穿馬路
有汽車駛過
它稍微停下躲閃
在車與車的縫隙間
它飛快跑到馬路的另一邊
天空下著小雨
路口紅燈綠燈交替
人們忙著趕路
無人喊打
在春天行走
一步大約是七十公分
一公里要走一千三百多步
用時十一分鐘
繞南湖一圈是八千一百七十米
從韋拔群李明瑞雕像出發
依次經過
游船碼頭
南湖大橋
地鐵工地
公務員小區
區黨委大樓
以及
開花的木棉
結籽的榕樹
跳舞的大媽
蹣跚的孩子
地上的路一半紅
一半黑
我喜歡走在紅色的這邊
喜歡看前面走著的
健康豐滿的女子
這些天突然發現
湖邊散步的大肚子女人
多了起來
我長出一口氣 對自己說
這才像是個
春天的樣子
【敘事性詩歌詩論】
這應該是相對于抒情性而言。敘事和抒情都好理解,加上“性”,很容易迷糊。
先得搞清楚,詩歌敘的這個“事”是什么概念。事件?事情?事實?應該都是。那么問題來了:怎么個“敘”法?
以“事”為基本元素,構建起詩的支撐。“我”可以是記錄者、呈現者,也可以是親歷者。
這個“性”,就是詩性、靈性,是實事向虛指轉化的催化劑。
我在敘事的時候,我知道我在寫詩。而不是別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