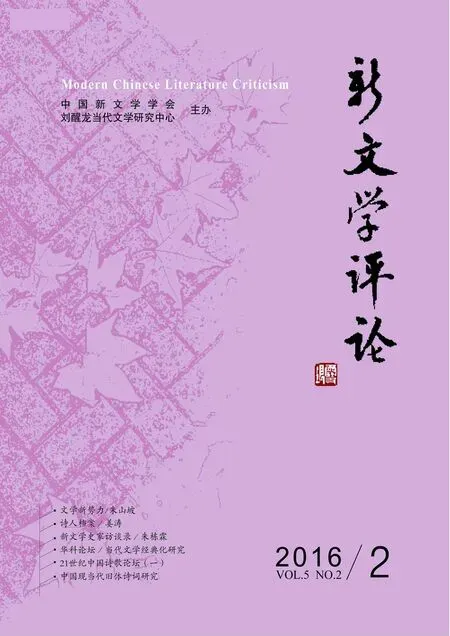“王二”:蠻荒年代的精神幽靈
◆ 張棋焱
?
“王二”:蠻荒年代的精神幽靈
◆ 張棋焱
“王二”的身份辨識與身份游離
“王二”是王小波小說中連貫出現的人物,他的經典形象幾乎都打上了“文革”時代的烙印。《黃金時代》的創作背景是70年代中期,文本中記載“王二”時年21歲,因此王二大約生于50年代;在《紅拂夜奔》和《革命時期的愛情》中,“王二”與王小波一樣,都是1952年生于北京;《似水流年》中的“王二”出生在1950年……王二的出生年代、背景、瘦高的身形,甚至曾經在美國客居、歐洲旅行的經歷都與王小波有著相似之處。 《黃金時代》中的王二“面色焦黃,嘴唇干裂,上面沾了碎紙和煙絲,頭發亂如敗棕,身穿一件破軍衣,上面好多破洞都是橡膠粘上的,蹺著二郎腿;坐在木板床上,完全是一副流氓相”①;《革命時期的愛情》中的王二“才過二十歲,就長了連鬢胡子,臉上爬滿了皺紋,但一根橫的也沒有,全是豎著的,自然卷的頭發,面色黝黑,臉上疙疙瘩瘩。臉相極兇,想笑都笑不出,還有兩片搟了氈的黑眉毛”②;《我的陰陽兩界》中的王二,“長了一嘴絡腮胡子,活像一個老土匪,而且滿嘴都是操你媽”③。王二雖為知識分子,但素來不拘小節,不愛打扮,穿著邋遢、相貌不堪;王二雖為下鄉知青,但不甘遵循知青時代的話語語境和生存規則,以相貌和心靈上的“痞子”形象、智慧和有趣的方式來對抗時代的荒誕規則。王小波筆下的知識分子,與傳統“士”階層人物形象格格不入,完全顛覆了知識分子的典型形象;王小波對知識分子外在形象的塑造,折射出了他筆下知識分子的生存困境。
對個體的尊重、對自由的渴望,對權力、公共意志的抗拒,是王二堅守的品質。“王二”用常識解構社會既定生存規則,用黑色幽默般的生存智慧拆解權力和欲望的生存理念,是極權社會下知識分子生存困境的寫照,也是先進知識分子在“文革”時期的反抗縮影。王小波通過“王二”的現代性人格特征的書寫表達了其對自由知識分子身份的認定標準和期望。也可以說,游離在小說文本中的“王二”形象,幾乎是王小波本人思想的倒影。
用常識解構反常識的生存規則
在“文革”時代,人人浮夸,思想的禁錮、人性的扭曲,民眾在封閉時代里的狂歡,致使人在社會中只能按照社會規則、權力話語而行。但王小波認為:除了自由主義立場,知識分子沒有其他立場可取。他認為,平庸的角色、不斷地為社會變換扮演角色,持續壓制著人的發展。王小波在致李銀河的書信中寫道:“把人都榨干了,我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盡義務,我們自己的價值標準也是被規定了的。”他筆下的王二始終保留著不羈的精神思想,訴說著挑逗的時代話語,飽含著對自由理性的追求;王二對自己所處時代制定的荒誕規則不以為然,質疑規則、質疑權力,不能不被劃為“另類”。
王二個性孤傲,不屑于那一套反常識的社會人情規則,導致人際關系的處理比較艱難。《黃金時代》中,他和陳清揚“偉大友誼”的緣起,是兩個因素促成,一是“農忙時隊長不叫我犁田,而是叫我去插秧,這樣我的腰就不能經常直立。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腰上有舊傷……”④,按常識判斷,王二不適合插秧,人人知道;可惜他并未因此巴結討好隊長,認為隊長應該會按常理來安排,定不會勉強有腰傷的人插秧。正是因為王二嚴重忽視了權力的重要性,導致被隊長安排專干插秧的活兒,最后腰傷復發。二是王二“隊醫務室那一把針頭鍍層剝落,而且都有倒鉤,經常把我腰上的肉鉤下來”⑤,隊里的醫務室把人的生命當作兒戲,護士不經嚴格培訓便上崗,針頭不經檢測便使用,導致病情在治療中愈發嚴重;王二認為陳清揚“對針頭和勾針大概還能分清”,去找陳清揚打針而相識。《三十而立》中的校長,解釋王二不能出國的理由:“大家說,放你這樣的人出去,給學校丟人。同志們對你有偏見……”⑥按常識來判斷,一個人是否應該出國學習,是按照學術科研的成果以及是否必要來安排,但校長列舉出的王二不適合出國的理由,竟是外在形象不好,出國會給偉大祖國丟臉,滑稽之至,令人發笑;《似水流年》中的王二認為“我向來不怕得罪朋友,因為既是朋友,就不怕得罪,不能得罪的就不是朋友”⑦。這也是交朋友的常識,如果友情只是用來相互吹捧、吃喝玩樂,那就有悖“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友法則,但王二因不怕得罪人,而失去了許多所謂朋友。然而,王二所遇到的常識問題,并非個體性問題,而是時代虛偽的生存規則所造成的普遍問題,王二所做的事情和持有的邏輯,看起來似乎“很傻很天真”,但實質上是用常識來反抗了反常識的生存規則,這是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對社會的尊重和對人的尊重。
《革命時代的愛情》中少年王二冷眼旁觀當時的煉鋼熱潮,并且思考高爐溫度與煉鋼純度之間的關系,后來還請教過冶金學教授,一個有常識的人不會相信煉鋼是用家用鐵鍋可以煉出來的,也不會相信一畝地可產萬斤糧食的浮夸;王二通過對荒誕“煉鋼”事件的思考,達到了思想上的掙脫,沒有被時代話語所洗腦、禁錮。《黃金時代》中的王二響應號召,去云南的偏遠地區當知青鍛煉自己,但卻沒有專心革命,而是對“性”產生了極大的興趣,這看起來是不務正業,實則符合常識和常理。一個正在讀書的青年,突然不讀書學習了,而是下鄉種地,精神生活的空虛必然帶來身體的空虛,對性的渴望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并非是什么破壞革命的違法犯罪。王二作為年輕人,直面身體上的需求,同時用對“性”的大膽實踐來反抗權力。在王二對生存規則的反抗中,常常用身體進行對抗,王二的“性”像是一面懸在空中的鮮艷旗幟,在高空蔑視“文革”的社會規則和主流文化,向他們招手,向他們挑戰。王小波說:“只有在非性化的時代,性才會成為生活主題,正如只有在饑餓年代,吃才會成為生活主題。”王小波通過性的問題進行了 “對人的生存狀態的反思”。王二正是要通過這樣一種方式,向人們展現生活的常識、生存的規則,控訴摧毀人性的時代,體現出對個體的尊重,保存人的尊嚴。
王二除了行為上的反常識,在思想邏輯上也是反常識的。王二的思維與當時的大多數人背道而馳,大多數人用時代盛行的荒誕、反常識的生存邏輯來對生活中的任何事件予以“審判”,把人的尊嚴、人的權利當作玩具和游戲來踐踏和擺布。然而,大多數人所遵循的所謂規則和邏輯甚至不符合常識和人情,讓人啼笑皆非。如《黃金時代》第一章這樣寫道:
我是這樣想的:假如我想證明她不是破鞋,就能證明她不是破鞋,那事情未免太容易了。實際上我什么都不能證明,除了那些不需證明的東西。春天里,隊長說我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眼,使它老是偏過頭來看人,好像在跳芭蕾舞。從此他總給我小鞋穿。我想證明我自己的清白無辜,只有以下三個途徑:
1. 隊長家不存在一只母狗;
2. 該母狗天生沒有左眼;
3. 我是無手之人,不能持槍射擊。
結果是三條一條也不成立。隊長家確有一棕色母狗,該母狗的左眼確是后天打瞎的,而我不但能持槍射擊,而且槍法極精。在此之前不久,我還借了羅小四的氣槍,用一碗綠豆做子彈,在空糧庫里打下了二斤耗子。當然,這隊里槍法好的人還有不少,其中包括羅小四。氣槍就是他的,而且他打瞎隊長的母狗時,我就在一邊看著。但是我不能揭發別人,羅小四和我也不錯。何況隊長要是能惹得起羅小四,也不會認準是我。所以我保持沉默。沉默就是默認。⑧
又如,要證明陳清揚和王二的無辜:
我說,要證明我們無辜,只有證明以下兩點:
1. 陳清揚是處女;
2. 我是天閹之人,沒有性交能力。
這兩點都難以證明。所以我們不能證明自己無辜。我倒傾向于證明自己不無辜。⑨
這是因為“大家都認為結了婚的女人不偷漢,就該面色黝黑,乳房下垂”⑩,陳清揚在這樣的生存語境下,卻要拼命證明自己不是破鞋,證明大家認為的所謂“常識”是錯誤的。如果一個人已被社會既定為一種“破鞋形象”,而這個人又千方百計想證明自己不是破鞋,實際上說明她已在內心認可了“破鞋可恥”這樣的一種公共道德觀,急于逃脫這個道德枷鎖。如此一來,這個人就已經被這樣一種道德觀綁架了,開始了自證清白之路,而“清白”與否的標準界定,卻是人們心中的反常識的判斷,是一個無法證偽的問題。而王二卻用自己對陳清揚破鞋形象的“認定”來對抗當時不符合常識的生存規則。
陳清揚竭力讓王二證明她不是破鞋,王二卻說“但是我偏說,陳清揚就是破鞋,而且這一點毋庸置疑”。這段話的邏輯看似有些無厘頭,但實際上很有意思,有這么兩層意蘊:第一層,王二所處的年代,人云亦云成風,個體喪失獨立思考的意識。所以,跟隨大眾的偏向,對個體而言才是最為保險和安全的辦法。對王二而言,即使在邏輯上無法證明陳清揚是破鞋,但事實上她是破鞋已經成為現實的口伐,是大眾所指的“破鞋”。邏輯讓位于現實,這就是特殊歷史時期荒誕的生存規則。王二在起初只能非邏輯地跟隨現實行走在荒誕生存規則的沼澤中。第二層,更為隱性的伏筆是,他計劃用自己和陳清揚的媾和實現陳清揚是破鞋的事實,從而讓陳清揚是破鞋在邏輯上獲得完滿。“王二”讓荒誕在邏輯上獲得合法性,從而解構了“革命年代”的生存規則。

用理性追尋生存智慧


王二的文化品格和理性的思索,恰恰表現出了對于人類存在的真正關注,表達了對于建構人類普遍價值和共同命運的關懷。王二只是歷史潮流中一個普通的人,一個小人物,他處在那個虛空的年代,不去走溜須拍馬、入黨提干這樣的道路,而是用生存的智慧告訴普通人,人應該如何理性、自由、真實地活著。這是千千萬萬的普通人難以做到的,正因為這一點,王二精神上的自由和理性才能獲得文化與價值上的認可和期許。
王二作為歷史大變革潮流下的知識分子,堅守了知識分子的理性思維,對理性的探尋經歷了重重波折和困難。王二對理性的追尋有真實的一面,也有“智慧的虛偽”的一面。王二被“出斗爭差”和花樣百出的“批斗”折磨,王二在寫交代材料時,事事都如實交代,包括和陳清揚敦“偉大友誼”的細節,弄得看材料的人尷尬不已又沉迷其中。后來,王二開始用自己的智慧保護自我、尊重自我,比如王二在人保組寫交代材料時,沒有交代偷越國境的事,因為他認為“沒有必要說的話就不說”。后來,他帶人保組的人去他和陳清揚住的地方實地勘察,王二指認場地,人保組無論如何不相信,后來王二就不帶他們去看了,因為“沒必要做的事就別做”。這是王二在苦難和愚弄中得出的生存智慧,也是王二對生存事實的一種尊重方式,對人的尊嚴的一種理性保護。《三十而立》中的王二,為了出國而奮力科研,結果出國的名額落空,自己被調包頂替,又被謠言弄得心神不寧,覺得生活很無趣,但是他卻用自己獨有的阿Q式的“樂觀主義”生活,時時安慰自己。支撐著他而行的,正是理性的生存思維和對人性的洞悉。王二的理性建立在對社會規則的明晰之上,建立在他的生存智慧之上,王二明白多說無益多做無益,唯一的方法是用自己的生存智慧來理性地生活,保留“文革”時期作為人的尊嚴和底線。
錢理群曾在演講中說,“本來在整個社會激進時,知識分子應該保守一點;當整個社會保守時,應該激進一點,這是知識分子和一般人區別所在。可中國的知識分子恰恰相反”。中國知識分子在政治的絕對控制和權力的重壓下,往往不敢言,不能言,王二卻通過真實的語言、異于常人的邏輯,甚至是“想入非非”的思維,來追尋失去的理性世界。王二在整個激進卻無激情的時代,深切感受到“無智”民眾被權力操控的悲哀,而王二在整個時代的“無智”中注入了“明白的理性”和“深沉的勇氣”。
對生存趣味的挑戰

《我的陰陽兩界》中,小孫想要治好王二的陽痿,將來還會寫一部紀實醫學報告或者心理學、社會學方面的研究報告,要干好這件事,和王二結婚是必然的,否則就會受到社會的指責。考慮到這個偉大的計劃,為了確保它的萬無一失,還得演出戀愛的戲碼,讓世人信服。這樣荒誕的“為科學而獻身”的行為,究其原因:非婚同居治療陽痿,是要受到社會輿論譴責的。乍一看,結婚治病似乎是一種荒誕的、不可理喻的做法,但實質上他們用這樣荒誕有趣的行為來對抗社會中既有的信條,用黑色幽默來對抗荒誕,挑戰公共信條,反抗權力。
被王小波稱為“我的寵兒”的作品《黃金時代》中說道:“在我的小說里……真正的主題,還是對人的生存狀態的反思。”在文本中,王二常常在那個“革命時期”反思自己,反思權力,反思“革命”,反思生存狀態。王二的生活也是有趣的,王二的生存空間主要在兩個層面上:一是外在自然環境,即王二下鄉插隊所生活的“農田”、出逃的“后山”、“荒地”、“森林”、“玉米地”等,王二作為知識青年,在這樣的自然環境中生存,在田地上勞作,顯然不能使自己得到精神上的滿足,反而在荒謬的污蔑中,正常生活受到無端干擾,只得出逃到后山、荒地等清靜之地尋求安寧,用“出逃”的方式來堅守自我。王二受了傷,不住醫院,卻突發奇想去了后山,過著一種恬淡的田園生活,好不逍遙自在,面對這樣無趣無智的時代,他選擇了自己創造生活的趣味,而非順從于當時民眾思想被控制的狂歡中。二是王二生存的人文現實環境,那是一個“批斗”橫行、常常“交代”、相互傾軋的“無智”時代,這個現實的生存環境對于王二來講,有著太大的殘缺,王二為了堅守自由的精神,只能選擇退卻,用自己的生存方式尋找理性的自由和樂趣。
《黃金時代》中王二被打受傷之后,獨自進山,羅小四帶人去醫院找王二,沒找到,詢問隊長,隊長卻說“誰是王二?從來沒聽說過。羅小四說前幾天你還開會斗爭過他,尖嘴婆打了他一板凳,差點把他打死”。誰知道這樣提醒之后,隊長就更想不起來王二是誰了。于是,王二便說:“大家都說存在的東西一定不存在,這是因為眼前的一切都是騙局。”王二認為,“對于我自己來說,存在不存在沒有很大關系”。公共性存在和個體性存在的關系,更多的是指,個體在一種社會公共關系中得到承認,比如在生產大隊里大家是否認為有王二這個人存在的問題,在當時民眾的認知中,王二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不被承認的小人物,而他也甘愿如此被不公共關系所認知,所以他覺得在這種公共關系中存在不存在無所謂。實際上,在那個時代,公共關系是不認可任何個體的。但是作為個體,他如何獲得自身的存在認知呢?那就是從肉體性上,從他和陳清揚的性中獲得肉體的認知,這是他能夠確認個體存在的唯一方式,用肉體反抗宏大,用肉體證明存在。性是一種很個體性的行為,而且是不可取代的個體性活動。就像他人可以取代某個個體成為公共關系里的某種角色,比如隊長、軍代表等等,這種角色性的存在是可以被取代的,但是性是他人無法取代的。
性作為人類的自然需求,本來是沒有顏色的,甚至應該是美好的。但是,從西方宗教的角度來看,禁欲、對性的壓抑是一個重要的文化特征;從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來看,性絕不是一個可以公開談及的話題。王二們在小說中多是身強體壯的年輕人,性是他們的天性和自然需求,王小波的性描寫是干凈的,王二對待性的態度是坦然的、自然的、健康的。王二的顛覆性對抗則是用荒誕行為本身來對抗荒誕,展現其對生命歡樂的極力渲染與刻意張揚。正如《黃金時代》中的陳清揚,人們可以肆意談論她的“破鞋”身份,但卻不能公開談論有關性的行為。性,成了王二的反抗方式之一,他用性來表達對社會權力和荒謬規則的對抗,是一種對非性時代的最具力量和顛覆性的反抗方式。《革命時期的愛情》中,王小波在序言中寫道:“這是一本關于性愛的書。性愛受到了自身力量的推動,但自發地做一件事在有的時候是不許可的,這就使事情變得非常地復雜。”文本中,王二和老婆在英格蘭,在一片森林里“享受一個帶有霧氣,青草氣息和寂靜無聲的性”。性本是一種自發的行為,是個體之間的私密之事,但這樣一個應當充分自由和自主的事情,在當時卻變得狹隘和轄制,“革命時期對性欲的影響,就像肝炎對食欲的影響一樣大”。王二用自由的性來反抗當時的“革命時期”,反抗壓抑人性的時代。

王二形象的功能

王二作為時代里的小人物,他的形象超越了精英受難史帶給我們的震撼和意義。王二是“知青”,是學校里的普通教師,是豆腐廠的小工人,是工讀學校的校長;王二從來不是干部,不是手握話語權和行政權力的精英團體。但是,王二這樣的小人物成為受難的主體,它的意義在于讓王二形象承載更多的歷史語境和歷史功能。大眾所熟知的精英受難事件,只是歷史時期中的粒粒塵埃,王二作為小人物,用自己幽默的方式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受到緩慢的、侵入骨髓的傾軋和屠戮,這是更應被記住的受難細節。
王二形象的美學意義
王小波在《似水流年》中說:“在我看來,人生最大的悲哀,在于受愚弄。”而王小波筆下的王二卻總是處在“看”與“被看”、“愚弄”與“被愚弄”的循環之中。正因如此,王二的形象顯得頹廢而又激進,痞子而又正經,富于詩意而又粗鄙不堪,在幽默的詩意中完成對生存世界的獨特審美。
王二的人生如戲一般上演,一直在“看”與“被看”、“愚弄”與“被愚弄”中循環往復。《黃金時代》中,王二的人生是一場表演,和陳清揚一起“出斗爭差”,“看”臺下的觀眾,“看”其他一起被批斗的“演員”,仿佛自己置身事外,作為“人”在看一場滑稽的表演;而當自己和陳清揚上臺,又變成了“被看”的演員,久而久之,已然對批斗會麻木了,陳清揚甚至做好一切準備,等待上臺“被看”。斗爭過后,王二和陳清揚回到住處,為了證明自己不是批斗的機器,而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便開始用性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反抗權力的荒誕,拾回自己的尊嚴。這還不算完。王二和陳清揚經常被反反復復的審查弄得疲憊不堪,審查中,讓他們寫交代材料,他們積極愉快地匯報了搞破鞋的過程,也指認了發生“破鞋”罪行的場所,卻不被領導和民眾相信;審查過后的再次審查,又是問同樣的問題,說同樣的話,他們反反復復被權力所“愚弄”。然而,他們始終原原本本交代做愛的經過,弄得看材料的領導十分欣賞、躁動不已,他們用自己的真實“愚弄”了權力。最后,“被愚弄”的王二反而用自己的真實“愚弄”了掌握話語權的領導。

王二是個幽默的人,這種幽默不在于語言的滑稽,而在于王二敢于自嘲的性格。自嘲是一種自我矮化,王二的自嘲或許更像網絡語言上“自黑”一詞的含義。敢于自嘲,敢于自我污名化,為的是嘲弄外部世界,通過自嘲的行為揭示生存世界的荒誕和日常生活的真相。英國戲劇評論家馬丁·艾思林在《荒誕派戲劇》一書中,指出了荒誕派戲劇的美學特征,其中一個重要的方式是:用輕松的喜劇形式表達嚴肅的悲劇主題。王二的自嘲、反抗更像是一出荒誕派戲劇的現實體驗。《我的陰陽兩界》中,王二被年輕的孫姑娘幸運選中,要為他治療陽痿,后來陽痿還真被這種奇特的方式給治好了,王二又回歸了正常的生活,上樓開會,被選拔為骨干,被單位公派出國……如果只是寫到這兒,那王二的生活還是極其膚淺的生活,王小波的小說也是極其膚淺的小說。王二用黑色幽默所反抗的荒誕,它真正的意義在于揭示出:回歸正常生活的王二,卻像被套上了什么東西。這個東西就是自由的枷鎖。盧梭曾說過:“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這樣荒誕、幽默、滑稽的故事有了這樣一個嚴肅的悲劇性意味,這是王二的幽默意義。
結語

注釋:
①王小波:《黃金時代》,《王小波全集》,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4頁。
②王小波:《黃金時代》,《王小波全集》,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頁。
③王小波:《黃金時代》,《王小波全集》,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28頁。
④王小波:《黃金時代》,《王小波全集》,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頁。
⑤王小波:《黃金時代》,《王小波全集》,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頁。
⑥王小波:《三十而立》,《王小波全集》,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頁。
⑦王小波:《似水流年》,《王小波全集》,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頁。
⑧王小波:《黃金時代》,《王小波全集》,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5頁。
⑨王小波:《黃金時代》,《王小波全集》,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5頁。











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