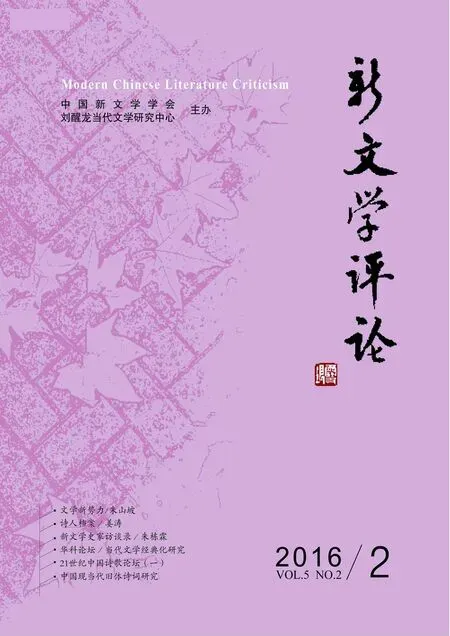“再給它們兩天南方的氣候”
◆ 姜 濤
?
“再給它們兩天南方的氣候”
◆ 姜 濤
十多年來,“70后詩歌”的提法,作為泛濫全社會(huì)的“代際”話語之次級衍生品,不斷出現(xiàn)在相關(guān)的詩歌批評和編纂中。詩人胡子(續(xù)冬)早就預(yù)言,在當(dāng)代文學(xué)主板市場極不規(guī)范的情況下,作為概念股的“70后詩歌”,即便沸沸揚(yáng)揚(yáng)上市,最終也會(huì)因“不合格包裝引發(fā)的大量投訴和文本業(yè)績的匱乏”而淪為一支垃圾股。我實(shí)在是同意這種說法,加上自己也曾忝列某個(gè)序列之中,更是相信某種集體同一性的虛妄。然而,十年后再看,當(dāng)時(shí)的想法可能有點(diǎn)傲慢、也太輕佻了,在并不高明的營銷策略之外,這支“概念股”還是包含了基本的現(xiàn)實(shí)性。這種現(xiàn)實(shí)性,不是由好事者四處張貼的美學(xué)標(biāo)簽來說明,更不是由“新陳代謝”的歷史豪情來保證,而是因?yàn)?0年來當(dāng)代中國的劇烈變動(dòng),的確給出了時(shí)間的節(jié)奏,先后給出了幾代人的界限。當(dāng)年曾在文學(xué)史想象中剃著進(jìn)取發(fā)型的青蔥少年,至今部分已年屆不惑,作為落寞大叔,或許更能感到這種節(jié)奏的強(qiáng)勁、專橫。
這一次,感謝《詩建設(shè)》同仁耐心編出的“70后”專輯,讓我有機(jī)會(huì)相對完整地閱讀同代人的作品,包括熟悉的與不熟悉的、認(rèn)可的乃至不大認(rèn)可的。走馬觀花的感覺是,當(dāng)代詩蓬亂蕪雜的圖像,似乎已被修剪成一畦畦整飭地塊,大部分的詩可以滿足美學(xué)與倫理多方面的要求,也幾乎沒有技術(shù)上、情感上徹底失敗的東西。即便忠實(shí)于相對類型化的主題,由于并不夸飾到喜劇的程度,也會(huì)顯出一份自如與精準(zhǔn)。對于一本詩選而言,能取得這樣的效果,其實(shí)相當(dāng)不易:
這就像園藝,為了精致
或者枝干更加挺拔,你必須修剪
它們的枝蔓。
——江離《南歌子》
借用上面的詩句,編輯也像一種“園藝”。從文學(xué)形象學(xué)的角度看,出于工作的耐心和趣味的認(rèn)真,或許可以說,《詩建設(shè)》的朋友們成功地編輯出了一種風(fēng)格,一種“70后”的風(fēng)格。它與詩歌理念、方式的統(tǒng)一無關(guān),而是顯現(xiàn)為總體寫作質(zhì)量的穩(wěn)定(入選詩人似乎構(gòu)成了當(dāng)代詩的中堅(jiān)),顯現(xiàn)為一種相對渾厚的語言姿態(tài)(即便有所激進(jìn)也不過分乖張),也顯現(xiàn)為某種被分享的情感類型(不少作品浸透了溫潤的抒情倫理)。即使出于“編輯”,這種代際的風(fēng)格還是大致可以信賴。
在當(dāng)代詩30多年野蠻的成長史上,不只一次趕上社會(huì)政治與世道人心的大變動(dòng),詩歌與詩人也曾有過十分醒目的時(shí)代形象。那些風(fēng)格強(qiáng)悍的前輩們,成長于運(yùn)動(dòng)與斗爭的火熱年代,往往能在特殊的轉(zhuǎn)折時(shí)刻,強(qiáng)有力地提出新的美學(xué),提出自己的方法論和世界觀,他們的寫作與表述,也往往有了“克里斯馬”的非凡氣象。針對沉悶的生活教條、語言教條,一些逆向提出的方案,無論多么粗糙、簡單,無論有多少夸飾和浪費(fèi),卻也總能歪打正著,洋溢了價(jià)值創(chuàng)造的率真熱情,也在更大的視野里,擴(kuò)張過語言和倫理的邊際。延續(xù)非凡的慣性,連創(chuàng)業(yè)之后的貪腐、享樂中,這代人也不乏自我戲劇化的英雄氣概。
相對而言,“70后”出生時(shí),大規(guī)模的群體性運(yùn)動(dòng)已經(jīng)過去,“文革”后期的中國其實(shí)不怎么折騰,家庭的規(guī)模也開始收縮,兄弟姐妹開始稀少以至于變得珍貴。鄉(xiāng)村的情況我不了解,至少在城市中,雙職工家庭模式帶來一種普遍的成長經(jīng)驗(yàn),不管頑劣與否,這代人與自己獨(dú)處的時(shí)間畢竟多了些,剩余的精力沒有更多牽扯到成人世界的熱鬧中去消耗,只能轉(zhuǎn)向日常性的學(xué)習(xí)、幻想、暴力和欲望。這方面,或者還缺乏社會(huì)學(xué)研究的支持,但70年代人是在一個(gè)相對平穩(wěn)、孤獨(dú)的環(huán)境中成長的,這帶來部分人性格的早熟,身上各種各樣的好壞毛病,不像前輩們那樣有機(jī)會(huì)大大發(fā)揚(yáng)。
二十世紀(jì),父親
已是長方的機(jī)器,
母親是折疊入墻的
床,是塞不進(jìn)抽屜的
日內(nèi)瓦湖,花園的尺寸
已是屋頂?shù)募覄?wù),山與云
是齒輪與皮帶,轉(zhuǎn)動(dòng)的燦爛
是砂石磨廢又一條小徑的火星。
——韓博《勒·柯布西耶雙親住宅》
韓博的寫作,體現(xiàn)了這代人心智早熟的一個(gè)極致,雖然已身為人夫人父,冷峻的洞察中還是包含了少年人的厭倦,又沒心思去刻意揮霍,回頭在與世界的不甚關(guān)聯(lián)中,打磨一個(gè)微觀而燦爛的人生系統(tǒng)。在句子和意象的自由傳動(dòng)中,不出意外顯出一副好眼光、好性格。
但早熟,并不一定就是優(yōu)勢,卻如同代批評家所稱那樣,導(dǎo)致各方面“尷尬”的處境。等到這代人結(jié)束漫長的少年時(shí)代,在上世紀(jì)90年代初,開始外出求學(xué)或自由飄蕩,各種轟轟烈烈的造山運(yùn)動(dòng)接近了尾聲,那些能夠強(qiáng)勁扭轉(zhuǎn)感受力的正反力量也基本耗盡,整個(gè)社會(huì)處在快速致富與快速自學(xué)之中,年輕人的野心更多表現(xiàn)在怎樣去游戲規(guī)則,而不是首先考慮去推翻規(guī)則。社會(huì)遷徙、分層帶來的重重震蕩,當(dāng)然也在神經(jīng)纖維上密集傳送,但社會(huì)主義時(shí)代的熹微記憶或小鎮(zhèn)情懷,也會(huì)在內(nèi)心形成牽絆,不肯發(fā)自肺腑地為時(shí)代亂象歡呼,認(rèn)真地對待變化中的一切。結(jié)果是,無論進(jìn)城鬼混、還是下鄉(xiāng)探訪,某種感傷、譏誚的小知識分子心緒,似乎還頗為流行,浮光掠影地造成某一類敘事抒情的套路。諸多“尷尬”合到了一處,無論經(jīng)商、進(jìn)機(jī)關(guān)、還是混跡媒體或?qū)W院,這代人中的佼佼者,即便占盡先機(jī),但大多還是低調(diào)致富、低調(diào)上進(jìn),網(wǎng)絡(luò)上尚缺乏他們可歌可泣的功德和丑聞。表現(xiàn)在寫作中,“70后”的詩歌技藝普遍合格甚至優(yōu)秀,結(jié)合特定的風(fēng)土與心性,發(fā)展出各自的斑斕色彩,但總體上說,這些風(fēng)格似乎不再具有“非凡”的氣質(zhì)。
對“非凡”的渴望,曾激發(fā)過上兩代詩人開疆?dāng)U土的語言激情,普遍壓抑也曾賦予激情以強(qiáng)勁的形式。前輩詩人可能的問題,是被既往“非凡”的時(shí)刻所凝固,對自身成就熟稔到不想有所突進(jìn)。對于后來者而言,“遺憾”不在于錯(cuò)過了造山運(yùn)動(dòng)的機(jī)遇,而是他們開始寫作的時(shí)候,當(dāng)代詩若干淺近的主張已開始固化、常態(tài)化。個(gè)人的風(fēng)格似乎可以從習(xí)得、磨煉中產(chǎn)生,而不再是自我掙扎、沖突的產(chǎn)物,也并非必然伴隨觀念上的否定與辯難。只要依了心性選取一種,安心或縱情地發(fā)展就是。大概十五六年前,曾與周邊友人提出一種“偏移”的詩學(xué),即:不再幻想另起爐灶,在承認(rèn)當(dāng)下寫作格局的前提下,試圖在一種修正關(guān)系中找到自己的可能。現(xiàn)在看來,這個(gè)看似世故、保守的立場,不是缺乏抱負(fù)的表現(xiàn),而是基于對當(dāng)時(shí)詩歌風(fēng)尚的一種信任。這樣說難免唐突了他人,因?yàn)榇撕蟛痪茫惭垡娡胁粩嘭Q起反叛、激越的旗幟,但彼此心知肚明,反叛的只是詩壇的秩序,而不真的具有價(jià)值原創(chuàng)的野心。挪用詩人孟浪的名句——“連朝霞都是陳腐的”,年輕人好勇斗狠,還是落在巴掌大的格套中。這也解釋了新世紀(jì)以來諸多耐人尋味的變化,我們不斷目擊了“崇低”與“崇高”、縱欲代言與良知代言之間的悄然轉(zhuǎn)換。
因?yàn)樵缡欤驗(yàn)樵趦r(jià)值前提上并不好斗,因?yàn)槟軌蛟谏鐣?huì)上較早地容身立命,我們不斷目擊這一代中的作者,不需要為了入場而炮制搶眼姿態(tài),反而能在相對獨(dú)立、縱深的地帶展開詩的“建設(shè)”,能在并不十分開闊的范圍內(nèi),盡量擴(kuò)張、拉伸語言的肌腱。那些肆無忌憚的想象力、自我凌虐的想象力,因?yàn)橛辛松畹拈啔v,似乎也不會(huì)脫韁于平凡實(shí)感之外,能如蝌蚪般自由甩動(dòng),帶著蝌蚪般沉重的頭顱和嬌小下身:
像訃告上的黑字,人在天下。
你們不
停地扭動(dòng)。像白紙上的蝌蚪。
——魔頭貝貝《履霜經(jīng)》
剛才說了,這本專輯中的作者,可算當(dāng)代詩寫作的中堅(jiān),相信不少人能持續(xù)寫出令人信賴的、可讀的作品。這一點(diǎn)毋庸多言,但從某種內(nèi)在限制的角度,倒可以再拉雜寫上幾句。
坦率地說,寫詩這個(gè)行當(dāng),目前表面熱鬧(你看大江南北,各類詩刊綠肥紅瘦,讓人眼花繚亂),實(shí)際不尷不尬,可能早早透支了曾有的歷史紅利。整個(gè)社會(huì)處在前途未卜的狀態(tài),詩人的寫作也缺乏清新的導(dǎo)航系統(tǒng),大家忙于應(yīng)酬、研討、集體出版,一切欣欣向榮的背后,或許是精神上普遍的松懈感。“70后”的作者們,對于寫詩的行當(dāng)敬重有加、勤勉有加,但一不小心也會(huì)構(gòu)成“不緊張”的中堅(jiān),體現(xiàn)當(dāng)代詩整體的水準(zhǔn),也體現(xiàn)了其內(nèi)在的界限。這幾年,有個(gè)不大穩(wěn)妥的想法,常和幾個(gè)朋友交換,這里不妨再重申一下,簡單說:當(dāng)代詩的前景,不一定在常態(tài)風(fēng)格的深化、制度化,而在能否恢復(fù)某種現(xiàn)實(shí)針對性和價(jià)值緊張感。改變的前提是,詩人應(yīng)考慮掙脫憤青、花花公子、神秘通靈者一類單調(diào)形象,主動(dòng)培育某種成熟的、開闊的、具有關(guān)聯(lián)感的人格。20年前,有感于時(shí)代、心境和文學(xué)趣味的變化,曾有人提出“中年寫作”的方案。回頭看,提出者當(dāng)時(shí)不過三十左右的小伙兒,因?yàn)闅v史經(jīng)驗(yàn)過快被壓縮,所以年紀(jì)輕輕就有了對晚期風(fēng)格的期待。“70后”一代心智早熟,但也可能因早熟而耽擱繼續(xù)成熟,許多秋風(fēng)遲暮之作還藏了少年情懷,就是一個(gè)明證。想到這里,有時(shí)恨不得遵從大師教誨:“再給它們兩天南方的氣候/迫使它們成熟”(里爾克《秋日》)。
當(dāng)然,成熟的表現(xiàn)不一而足,至少應(yīng)包含以下幾個(gè)方面:不再以小知識分子進(jìn)城或返鄉(xiāng)的感傷姿態(tài),來看待周遭世界的變化,這種視角除了自怨自艾,不能再說明什么;也不再扭捏于看似高深實(shí)則表淺的人文情懷,這種人文情懷即使有了各類文化經(jīng)典的包裝,也會(huì)因不斷自我回收而顯得沉悶;同樣,各類撒嬌賣乖、裝神弄鬼的技巧,將來也不會(huì)有太大的出息。成熟的心智會(huì)帶來語言和感受的層次感和針對性,也會(huì)喚醒語言創(chuàng)造的嶄新欲望。考慮到當(dāng)代詩在整體上還可能發(fā)育未完,對于高低錯(cuò)落的各代詩人而言,就沒有了先來后到、扶老攜幼的分別,這是一條共同的起跑線。對于包括自己在內(nèi)的一代人,雖然從未抱有特別熱烈的期待,但至少在這條起跑線上,有關(guān)寫作前景的想象,還有可能被再三地鼓起。
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