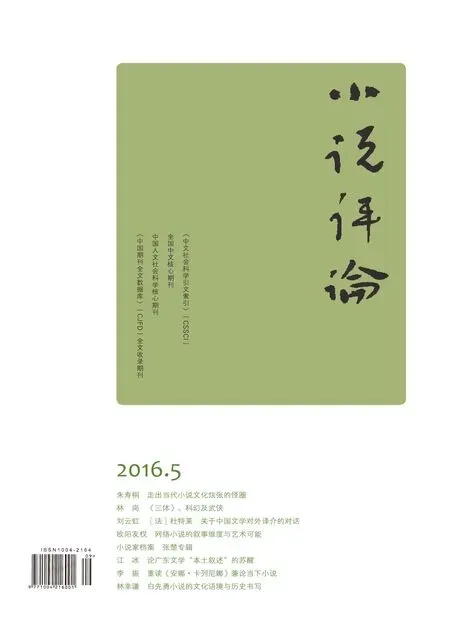論金仁順小說中的文學世界及人性建構
劉穎慧
論金仁順小說中的文學世界及人性建構
劉穎慧
一直以來,金仁順的小說被分為三種類型,青春成長小說、都市欲望小說、民族歷史小說,而作家也被冠以“女性作家、民族作家、70后作家”等稱謂。姑且不論諸如此類的劃分是否合理,當作家的身份與創作被主觀限定,難免會產生一種“戴著有色眼鏡”看人的視覺蒙蔽,深藏其中的內在意蘊往往被忽略。實際上,作家本人也對被貼上“標簽”表示無奈,“被標簽其實是粗暴的,很不公平的。但是從評論的立場上來說,他要評論一個時期、評論一群人,也只有這個辦法。所以說大家要互相理解。我是寫作的人,我是原創勞動者,我確實對標簽沒有感覺。 當然被標簽了那就被標簽了,也沒有關系。”①“擺脫”標簽的“束縛”、“剝去”創作題材的“外衣”細讀金仁順的小說,不難發現,對人性的探討及闡釋才是作家創作的“原動力”。無論是初入文壇還是日漸成熟,無論是古典還是現代,無論是鄉村還是都市,金仁順在表達人性豐富的同時,建構了屬于自己的文學世界。
一、殘酷的人生體驗
金仁順的小說筆觸一向冷峻,無論何樣情感始終平靜相對,從未流露出起承轉合的大喜大悲之感,這似乎也成為其獨有的風格。讀完金仁順的小說,合上書頁凝神思索,總有一股“冷香”飄過,既芬芳撲鼻卻又記憶深刻,令人回味許久。“即便‘殘茶涼透’,也會‘在水面上凝留下一股冷香’”②。面對人性的弱點,金仁順具有超乎尋常的理性,在她細膩而又銳利的文風下,人物的內心猶如纏絲剝繭般被逐層分離,赤裸裸地呈現在讀者面前。
面對人性中的多種體現,金仁順一改以往女性作家的溫暖情懷,也從未將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點去著力批判,而是選擇從容不迫地將人性的缺陷逐一揭開。金仁順筆下的人性往往是殘酷的,這種殘酷并不是人物表層的罪惡,而是不經意間的行為或者潛意識的驅使。“冷而尖銳的敘事方式,將人性秩序扭曲的瞬間撕開給人看,猶如北方的飄雪。她的文字具有清洗功能及其內斂的質地,又如月光的寒涼徹骨。”④撥開人性虛偽的“外套”,將真實的“肉體”展示給讀者,我們看到的是作家宛如醫生手術般的冷峻與不茍言笑,以及小說人物宛如手術臺上病人般的毫無掩飾,其中的殘酷意味不言自明,這正是金仁順在自己的文學世界里展開的“實驗”。
金仁順很善于講故事,講述故事的方法從不流俗。盡管她也在努力展示世間的人生百態和人物的復雜心理,但并未采用過多的敘事技巧。對她而言,小說不是炫技,而是雜糅出人性的本質。金仁順十分認真地在踏踏實實講述著每一個故事,正如她所言“寫作是件樸素的事。”⑤因此,我們在作家的創作中看到了一個又一個好故事,解讀到一層又一層復雜的人性,其中人性的殘酷是其小說慣于表達的風格。
《五月六日》里的祁政只是個初中生,頭腦中卻不斷涌現出各種犯罪的念頭,企圖綁架同學田原原、對不慎跌落井底的田原原視而不見、勒索田原原家屬等。原本美好的青春被殘酷與傷害所取代。《玻璃咖啡館》里的三名高三女生只因主觀臆斷咖啡館里那位打扮時髦的年輕女子品行不端,竟然穿著旱冰鞋主動向她沖撞,導致其流產。“在她的裙子上,有一塊紅色,正一點一點地開放成一朵碩大的花朵,花朵越開越大,越開越明艷。”此時,女子的身份也被揭開,在咖啡館中熱聊的男子不過是她的弟弟。三個女孩兒的無端猜測是野蠻、粗魯,主動傷害他人更是殘酷、冷血。金仁順筆下的青春不是激情、懷舊,而是充滿了殘酷與暴力。“我看不出青春有多少美妙之處,相反,青春就像莽林一樣,埋伏著陷阱和危機,充滿了暴力和死亡。一步行差踏錯,一生滿盤皆輸。”然而這種殘酷并不等同于所謂“青春小說家”所書寫的關于自身所經歷的種種痛楚,作家是將青年時期那殘忍的一層撕扯開來,實則仍是人性的表述。
金仁順對人生的思考還體現在死亡領域,死亡是金仁順小說里頻繁出現的情節。《盤瑟俚》的主人公“我”自十六歲起被父親當作換取酒錢的工具,每當父親的酒喝完就會有新的男人在黑夜里去“我”的身體里“旅行”。事情周而復始地發生著,然而這還不夠,當“我”被父親賣給酒鋪的男人,卻因過往而慘遭退婚。
“人,無論是人類或個人,一旦降臨于斯世,便被拋回如本能一樣恒常既定的狀態,墜入動蕩不安,開放無拘的境遇之中,其間僅有一點是確定不疑的:過去以及未來的盡頭——死亡。”⑥死亡是人類的終極命運,是文學的又一永恒母題,也體現著金仁順對人生殘酷本質的思考。自小出生并成長于礦區的她,對死亡是司空見慣的,“我習慣見到一些缺胳膊少腿的人,我也習慣于見到死亡。離開煤礦的前一年,正逢雨季,我們在課堂里,每天都能聽到有人死去的消息。”⑦對金仁順來說,死亡就如同家常瑣事一樣時時出現,并且習以為常,書寫死亡就如同吃飯、睡覺那樣平靜。當死亡頻頻見諸筆端,無疑增添了小說的殘酷因素。而金仁順的死亡又不僅僅是“死亡”而已,還伴隨著自殺或他殺。殺死自己或殺死別人,也許只有如此,才能彰顯出對自己或是他人命運的掌控。金仁順透過死亡,完成了對“命運論”枷鎖的突破。
二、善變的人物心理
金仁順的創作一直保持著對人性的冷峻審視,并努力挖掘人類心底潛藏的諸多感受。“我們在小說里尋找的,是人性深處的痛楚和弱點,并把它們盡可能準確地表達出來。”⑧金仁順在探討人物內心時,從不忽視和回避人性的普遍缺點。對于人性弱點的展示,作家的態度是積極的。她不喜虛偽的溫情,并將其看作是矯揉造作的表演,既可笑又可悲。“我們的社會正在變得越來越冷漠,越來越拜金,越來越自私,溝通變得越來越不可能。這是事實,我表達了事實,如此而已。”⑨的確,人性本就不完美,在當下這個價值觀不斷重塑的時代越來越善變。讀金仁順的小說,在看到一個又一個好故事的同時,能夠引發對人性深層次的思考。在作家精彩講述的背后,是對人性的“深度解剖”。初讀文本,很容易被文字表面的離奇所吸引,而再次體會,留下的是作家對人生的“玩味”。金仁順仿佛總是作家中最冷靜的那一個,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果敢。走進她的文學世界,原有的價值觀念經常被“摧毀”,甚至是重建,作家在解讀人性的同時也在建構新的價值觀。“她刻意地尋求著生活的真實感和重量感,并在敘述中剝離或者打碎我們既往的道德秩序,進而顛覆我們的閱讀和接受,盡顯出金仁順小說敘事的魔力。”⑩金仁順不是那種依靠長篇累牘來吸引讀者的創作者,但卻能夠運用精簡的文字傳達更多的啟示,也許這正是作家創作的最大意義。
回味金仁順的創作,作家對人性心理的最終解讀是善變。人物沒有被賦予傳統文學創作中善與美的本性,即使是在道德觀念、倫理價值等“大是大非”面前,仍然暴露出搖擺與猶疑。正因如此,小說中人物的選擇往往出人意料,情節常常“峰回路轉”,故事也就有了更強的可讀性。《彼此》里的黎亞非在結婚當天得知丈夫鄭昊前夜與前女友在一起,婚姻生活就像被植入了一顆“毒瘤”,時不時地加倍爆發,這個女人的惡毒言語使他們的婚姻名存實亡。命運常常驚人的一致,就在黎亞非與周祥生舉行婚禮的前夜,她竟然鬼使神差地與前夫鄭昊上了床,親手為自己的第二次婚姻植入了一顆新的“毒瘤”。結婚當天,“他們的嘴唇都是冰冷的。”小說到這里戛然而止且恰到好處,之后的婚姻生活無疑是對之前的重復,已無需贅言。在第一段婚姻中受到傷害的黎亞非,為什么做出與那個惡毒女人的同樣行為?遇到周祥生,是她新的愛情生活的開始,改變了原來如同一潭死水般的婚姻格局,對黎亞非來說這是新的救贖與希望,為何偏偏要在結婚前夜親手將其打破,而再次陷入到僵局之中。在愛情面前,金仁順筆下的男男女女是善變的,他們無法將過往那段情感里的溫柔與纏綿徹底斬斷,還愿意在往事里沉醉一次。小說中周祥生曾提出解決辦法,“當它是腫瘤,……摘了就完了唄。……跟往事干杯,大醉一回,然后開始新生活。這有什么不對的?這就像人的身體,絕對清潔、絕對健康是不存在的,有對立面,有矛盾沖突,通常更能增強免疫力。”?盡管如此,當同樣的事情真的來臨無論是誰都會慌亂,結婚當天,周祥生將婚戒掉在了地上。“時光的化骨綿掌早就拍打在我身上,我們看上去從容安詳,成熟穩重,但我們心里明白,毒液早已經絲絲縷縷滲入到我們身體的每一個角落,它們消滅了天真,留下了痛楚。”?金仁順小說的敘事節奏很快,但對心理狀態的把握仍然細膩,善變、懷疑、憂郁、搖擺不定的人性缺點展示得透徹而精準。這在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里早有體現,人類在很多重要選擇前面常常是猶豫的,“to be or not to be”同樣是文學的又一永恒母題。
《仿佛依稀》里新容的父親蘇啟智拋棄了母女倆,與女學生徐文靜展開了師生戀。多年后,在身患重病的父親面前,過往的恩怨煙消云散,母親黃勵也與自己憎恨了一生的徐文靜和解。《云雀》里的春風在打工期間結識姜俊,令她從“灰姑娘”變公主,搬進豪宅、開著私家車、成為校園明星,也因此吸引了大眾情人裴自誠的注意。兩份愛情“滋味”不同,一份如云雀茶般越品越深厚,一份充滿著青春的悸動與不安,搖擺于兩份愛情中的春風甘之如飴。《愛情試紙》里的李宇因懷疑丈夫方城出軌而吞服安眠藥自殺,搶救成功醒來卻被告知,這是朋友與她開的一個玩笑,目的是為了考驗當下社會中夫妻之間愛情的含金量。
我們看到,金仁順文學世界里的人物心理總是難以捕捉的,這使得他們的行為從不在讀者的意料范圍之內。作家對現代人性心理的熟稔,使她敏感地“嗅”到了人物心理的復雜及人性的善變。當原有的價值觀念不斷被顛覆、解構,新的價值觀念層出不窮,誰都無法斷定人性的終極定位在何處。金仁順用人性的矛盾、猶豫、懷疑、搖擺等復雜因素,進一步展示了人性的善變心理,將人性的探索繼續一直進行下去。
三、自私的人類欲望
在當下文化價值觀念變遷的時代,人類的個性得到空前的解放。向前追溯,也只有“五四”時期承擔著建立一種新的文學、文化的使命,其關注的重點在于“新文化”與“舊文化”的對抗。新時期以來的價值觀則執著于對人性壓抑與束縛的解放,將人類本身的潛在欲望激發出來。長久以來,人類將自我欲望視為羞恥與罪惡的念頭好似在一夜之間被拋諸腦后,大膽釋放出心底的愛欲方才符合人性發展規律。“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識正發生一個由極端壓抑人的本能欲望的政治烏托邦理想逐步過度到人的欲望被釋放、追逐、并在商品經濟的發展中被渲染成為全民族追求象征的過程,這種變化起先是隱藏在經濟政策開放、建設現代化大都市、與國際接軌等一系列的現代化的話語系統中悄然生長,最終則成為這一切目標的根本動機和最終目的。”?個人欲望取代全民理想成為人類的終極追求,作家金仁順正是成長于這個時代。敏銳的視角使她迅速抓住了人類心底最根本的欲求,物欲、愛欲、情欲在她的小說里張揚恣意的存在著、生長著。人們對欲望的渴求達到了“巔峰”,并且以不計代價、不惜犧牲一切的方式來試圖抓住每一根欲望的“繩索”。也許每一次緊緊地抓住是以傷害他人為前提,他們仍然在所不惜。無論親情、友情、愛情,都會在這一過程中淪為犧牲品。金仁順對人類欲望的展示,不僅僅是表達社會轉型時期人類欲望的過度膨脹,而是對人類自私本性的解讀。“在她的作品中,內心的欲望不是無度的放誕,相反是小心的收斂,是暗示與懷疑。”?金仁順的敘事是節制的,即使是在書寫人性中被壓抑許久早就想要奔涌而出的各種欲望時,仍然保持著一貫的冷峻。她的文字不是餐桌上的“紅燒排骨”,而是小火慢燉的“家常魚”,個中滋味需要“細嚼慢品”。金仁順的小說總是值得回味,我們常常訝異于她對于人性自私欲望的展示是那樣理性,而這恰恰是作家思考更加深入的體現。
長篇小說《春香》以古朝鮮時期的民間故事為原型,將春香與李夢龍的原本圓滿的愛情故事進行了重新解讀。小說中的香榭猶如“世外桃源”,在主人香夫人的經營下,逐漸成為獨立于世俗世界之外的一個自由樂園。自小成長于香榭的春香一直希望能擁有與母親香夫人同樣的人生,成為香榭的主人。在初戀情人金洙離開香榭后,春香遇到了李夢龍。李夢龍愛著春香,卻囿于貴族身份不能作出承諾。春香并沒有表現出留戀和不舍,天賦異稟的她不想嫁人,夢想著成為藥師。多年后,當李夢龍再次回到香榭,春香已然接替母親成為香榭的主人。李夢龍依舊叫她“春香”,春香卻淡然回答“李大人”。一聲“李大人”,仿佛魯迅先生《故鄉》里閏土的那一聲“老爺”,令人無盡心酸。金仁順筆下的《春香》顛覆了民間傳統對愛情的理想性塑造,愛情中的男女同樣是自私的,愛情是在利益面前可以被割舍的成分。
《高麗往事》講述了高麗王朝時期王宮里的一段往事。《桃花》書寫了夏蕙與季蓮心之間荒謬的母女關系,溫暖慈愛的母女情感在特定情況下被異化。作為母親季蓮心同樣愛著夏蕙,在她的精心打造下,夏蕙出落得清新漂亮。然而,夏蕙的兩段愛情卻都因季蓮心無疾而終。同學章懷恒與夏蕙只能算是曖昧,他的離去并未使這段被DNA纏繞著的母女關系分裂,然而西蒙卻不同。法國人西蒙是夏蕙真正體會到美好愛情的第一個戀人,卻轉而與季蓮心在一起。季蓮心對自己婀娜韻味的展示看似無意卻恰到好處,西蒙的眼神再也無法從她身上離開。直至夏蕙親眼目睹了季蓮心與西蒙的做愛過程,質問母親的夏蕙換來的卻是季蓮心給予的耳光和譏諷的話語。再也無法容忍的夏蕙,用一把刀回應了母親。小說將人類情感中最深厚的母女情誼進行了“拆解”,在情欲面前親情同樣可以犧牲,道德倫理約束早已不復存在。
金仁順小說里人物的欲望是復雜的,他們貪戀物質、權力、地位,也貪戀愛情、性愛、自由。由于貪戀的強度極大,欲望的滿足常常以傷害他人為代價,但并不會減少他們對欲望的渴求。這更加凸顯出人性的本質是自私的,在個人欲求面前其他一切都變得不再重要。此時,傳統的道德觀、價值觀、倫理觀在個人欲望的膨脹下被顛覆,新的價值觀卻并未明晰,我們看到的僅僅是人性在社會轉型時期呈現出的更多自私本性。在金仁順的文學世界里,人類欲望的繁復促使傳統觀念走向“崩塌”,人性的自私逐漸“浮出水面”,作家對人性的建構得以顯現。
有時,我們會驚異于作家文字的冷靜,她是如何面對筆下人物如此經歷卻還能平靜以待,也許這正是金仁順的魅力所在。作家用一向冷峻的視角看待世情,看待人性,人類的體驗、心理、欲望在其文學世界里得以書寫。盡管成長于七十年代,但金仁順始終保持著自己獨立的創作風格,并未被時代、流派所左右,寫小說和寫出好的小說是作家的一貫追求。如果在金仁順的文學世界里找尋作家堅持的理念,那一定是對人性的執著建構。
本文系2016年吉林省社科基金項目《新世紀“底層文學”的社會學研究》[2016BS51]、吉教社科合字[2016]400號、長師社科合字[2016]008號。
劉穎慧 長春師范大學
注釋:
①金仁順,鄧如冰:“高麗往事”是我靈魂的故鄉——金仁順訪談[J].西湖,2013,(5):70-75.
②趙強:殘茶涼透,在水面上凝留下一股冷香——讀金仁順的長篇小說《春香》[J].小說評論,2012,(6):103-106.
③⑩張學昕,梁海:“彼此”世界里的化骨綿掌——論金仁順的短篇小說[J].當代作家評論,2010,(4):178-184.
④鐘剛:華語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 ”提名[N].南方都市報,2009-03-01.
⑤⑩金仁順:寫作是件樸素的事[N].文藝報,2014-10-27.
⑥[德]弗洛姆.愛的藝術[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9.
⑦金仁順.這樣愛,這樣寫作[A].金仁順.愛情冷氣流[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248.
⑧⑨金仁順,高方方.文學,時光里的化骨綿掌——金仁順訪談錄[J].百家評論,2014,(1):46-50.
?金仁順.彼此[A].金仁順.彼此[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9:21、14.
?金仁順.時光的化骨綿掌[A].金仁順.時光的化骨綿掌[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2:60.
?陳思和.現代都市社會的“欲望”文本[A].陳思和.談虎談兔[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220.
?周立民.被囚禁的欲望——談金仁順及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創作[J].當代作家評論,2004,(5):101-109.
?金仁順.高麗往事[A].金仁順.玻璃咖啡館[M].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