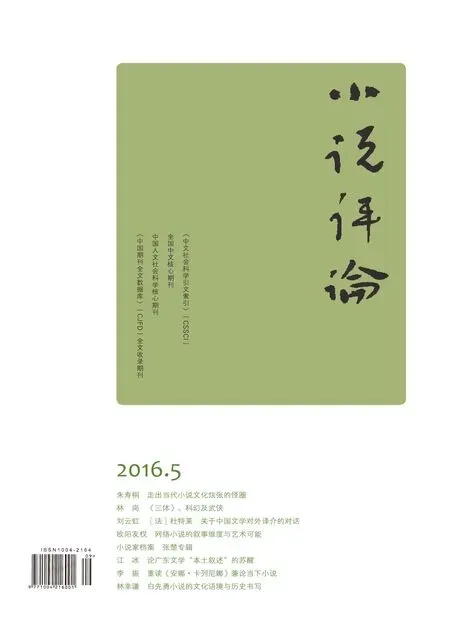論閻連科小說創作的重復性
唐 蓓
論閻連科小說創作的重復性
唐 蓓
2014年4月,漓江出版社再版了12年前梁鴻與閻連科的訪談錄《巫婆的紅筷子》。十多年前,閻連科還沒有創作出“絮語體”的《受活》,沒有構思出血淋淋的《丁莊夢》和“有傷風雅”的《風雅頌》,更遑論讓“神實主義”橫空出世的理論論集《發現小說》。“神實主義”作為閻連科對自己創作追求的一個概括,它的提出本身就附著了一定的神秘性和宗教性——根據閻連科自己總結,“神實主義”是“在創作中摒棄固有真實生活的表面邏輯關系,去探求一種‘不存在’的真實,看不見的真實,被真實掩蓋的真實……它與現實的聯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地仰仗于靈神(包括民間文化和巫文化)、精神(現實內部關系與人的靈魂)和創作者在現實基礎上的特殊意思”。①
饒有意味的是,十數年后,閻連科將他近十年創作的“耙耬系列”命定為“神實主義”寫作②之后,《巫婆的紅筷子》也完成了再版。在再版的訪談錄《巫婆的紅筷子》中,梁鴻與閻連科在開篇便不下六處談及寫作的重復性或差異性。③這次有意無意的再版,這場不經意的討論,不管是作為作者的閻連科還是作為論者的梁鴻,似乎都察覺到了閻連科在創作了十多年“耙耬系列”之后的今天,不同程度上已經開始面臨自我復制的創作陷阱。
一、靡靡不絕的鴉犬之音——意象的重復性
對不少系統閱讀過閻連科小說的讀者而言,一定不會對“狗”和“烏鴉”感到陌生,二者甚至在某種刻意而為的匠藝下“恰如其分”地出現在小說中顯要的位置。
在閻連科的諸多作品中,“狗”總跟消逝和殞滅緊密相連。狗不僅會跟著主人游蕩,會在受到驚嚇的時候吠叫,更會“恰切地”在希望消逝或生命殞滅的場景中出現。落魄的狗與失魂的人似乎在一種帶有神秘色彩的描寫中互文性地充斥著耙耬山脈的整個生活圖景。以殘疾人為描寫對象的《受活》異想天開地締造了一個沒有生存尊嚴的殘疾人村落,那兒的狗甚至也跟人一樣是殘缺的、沒有尊嚴的:“茅枝婆正在院里像喂孩娃樣喂著她的幾條狗。那狗也都是殘疾的,有的瞎,有的瘸,有的背上沒了毛,禿禿的一背都是癩疤兒,像墻上不平整的泥皮兒。還有的,不知那狗為啥就沒了尾巴了,少了一只耳朵了。”突出一人一狗一樹的生存困境的《年月日》甚至在開篇用“狗”來代言生命的孤寂與流逝:“先爺從早到晚,一天問都能聞到自己頭發黃燦燦的焦煳氣息。有時把手伸向天空,轉眼問還能聞到指甲燒焦后的黑色臭味……盲狗便聆聽著他午邁蒼茫的腳步聲,跟在他的身后,影子樣出了村落。”
盡管在閻連科的筆下“狗”所指涉的內涵區別于張賢亮《邢老漢與狗的故事》中人道主義的溫情載體,也非鄭義《遠村》里文化之根的符號,不是賈平凹《五魁》所體現的那種性的隱喻。但是,倘若同一個意象刻意地、機械地反復出現在一個作家橫跨十數年的不同作品中,過于依賴它來映射失望、貧困與死亡交織的底層生活經驗,以某種帶有神秘色彩和巫文化意味的符號標識“借殼上市”,并不偏不倚地在時日消逝與生命隕落的場景中“顯靈”,這無疑暴露出作家創作所陷入的自我重復,也反映出作家所提出的“神秘、民間與巫文化等元素”較為浮于形式——在小說創作中,對所謂神秘、民間、巫文化的理解和運用,在寬泛意義上沒有深入到人類精神領域的共時性空間,在微觀層面上又沒有突出某個地域在某段歷史階段中個體與社會、歷史的歷時性對話。
無獨有偶,“烏鴉”又跟驚恐與絕望密不可分。《堅硬如水》就有“不知啥兒時候雀、燕又引來了幾只烏鴉和黃鸝……它們都在幾尺遠近盯著她裸美的白脖子”的描寫。《日光流年》在描摹死寂的時候還特意提及烏鴉:“可眼下什么都沒了,沒了牲畜,沒了麻雀,連烏鴉也逃旱飛走了。”同樣重復著的特意描寫,也出現在《受活》里:“哭喚聲把山脈上所有的烏鴉、鳥雀都嚇得沒有蹤影了……麻雀在房子的坡臉上嘰喳得驚天動地著。烏鴉在院落樹上銜著草枝、柴棒壘著它那在六月的風雪中遭了災的窩。”不難看出,在“神實主義”世界里,“烏鴉”跟“狗”一樣是帶有神秘色彩和巫文化意味的符號標識,它作為一種具象化的“巫具靈器”,重復著閻連科經驗世界里的惶恐與驚懼。
在某種程度上,閻連科筆下那些跟消逝和殞滅緊密相連的“狗”,以及通過惶恐和驚懼來寄生的“烏鴉”,與陳忠實筆下那頭或隱或現的“白鹿”一樣,多少能折射出作家對鄉土想象、民間傳說的認知、迷戀與重構。對此,閻連科認為在現實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話、魔變、移植等都是“神實主義”通向真實和現實的手法與渠道。但是,“想象式的魔變”對于一個作家的單篇文本而言或許能夠突破某種認知的界限,使得文本具有更高的寬容度和更強的可塑性。但放之于一位作家多年的創作時間線上,“想象式的魔變”卻如此“巧合而恰切”地重復占據著他的敘事空間,這似乎是他必須加以反思和警惕的。
二、勾兌權力的買賣儀式——敘事模式的重復性
在《巫婆的紅筷子》中,閻連科談到了差異性,談到每一部作品都必須有所突破。我們不能否認他在小說文體藝術這方面所作出的嘗試,并且其效果也有目共睹的。為了突出幾代村民關于人與自然的抗爭、人與人之間的紛爭,閻連科選擇“索源體”來逆述《日光流年》的故事。為了在歷史的負重感和記憶碎片的跳躍性之間達到平衡,他又巧妙地以“絮語體”雕琢《受活》。為了從空間維度對發展、沿革的時間性作出釋述,地方志式的文體結構又使得《炸裂志》免于俗套。就閻連科的“耙耬山脈”而言,不同的文體很好地適應了相應的故事。但讓人遺憾的是,大多數敘事都難逃 “買賣”這個動作原型。
“買—賣”這個文本動作寄存在閻連科小說中的“得—失”敘事模式中,即耙耬山脈的村民為了掙脫土地的束縛、擺脫農民的身份屬性并發財致富,不惜一切放大個人欲求,追逐金錢、權力或試圖得到城市人的身份認同,但他們最終在出賣自己身體與靈魂的過程中失去跟現實談判的籌碼。《日光流年》的司馬藍為獲取開鑿靈渠的資金以實現村民們“活過四十歲”的愿景,不惜命令女人到外面賣淫賺錢,派使男人賣皮籌錢,甚至讓村民們自覺把自家的家當變賣以維持開鑿工程的進度。《丁莊夢》里朝覲式的狂熱使得賣血成為了一道快速致富的程序,“血頭”丁輝鼓動村民們賣血致富,村民們羨慕丁輝通過做“血頭”賣血來換得三層青瓦房。相似地,《受活》里的柳縣長為實現政治狂想給大家規劃出發財致富的藍圖,引導村民們成立“絕活團”來籌備購買列寧遺體的資金,村民們在發財致富的憧憬下不惜展覽自己的殘缺與痛楚來滿足“圓全人”的快感。甚至在新作《炸裂志》中,這個“賣”的動作,這份蔓延了十數年的自我重復性依然在作動:在孔明亮的“指導”下,村民們為了脫貧致富,女的紛紛效仿在外面通過開“娛樂城”提供性服務發了大財的朱穎,男的紛紛到外面的世界搶掠偷竊。
我們不難理解閻連科的構思:把“耙耬山脈”預設為一個和外部物質世界對立起來的、閉鎖禁錮的土地領域,它是以土地為本的生存意識跟以個人為主體的現代性相互交融與彼此對峙的精神空間。在交融與對峙過程中,以往認知中的“鄉土中國”圖景被打破,重塑的則是一片荒誕的土地。然而,在跨度十數年的創作中, “買—賣”的多次重復使得“耙耬系列”甚至“神實主義”小說體現出鮮明的閻連科特色的同時,又陷入了一發不可收拾的“閻連科癥候”。更值得深思的是,閻連科的長篇新作《炸裂志》在情節上甚至是對其短篇舊作《柳鄉長》的擴展與延伸,即《炸裂志》一定程度上是《柳鄉長》的擴寫。
在這個層面上,閻連科并沒有對人性的復雜相位進行更富有深度的挖掘和剖示,他仿佛缺乏對人性的隱秘之處以及情感的微妙角落進行推敲的耐心,反而沉溺在“荒誕”“苦難”“鄉土”的藍圖構想中。同時,他又沒有更多地涉足全球化、經濟改革、消費時代對鄉土生活方式、傳統觀念、倫理道德的沖擊和重塑,而是簡單地停留在探討作為歷史品格的人與作為生命本質的人如何置身于同一事件的感官層面和情緒層面。
三、充滿對峙的精神嬗變——失序存在的重復性
“得—失”的敘事模式宣告著閻連科在“荒誕”這條路上劍走偏鋒。而在超越荒誕的敘事表象之后,閻連科的“神實主義”小說所要探討的終極命題赫然是關于秩序的命題。秩序本來作為一種一致的行為模式,是寄存在人的全部活動事項中,但在審定秩序這一存在命題之時,閻連科那里,所表現的更多是一份關于秩序的質疑——對存在的存疑,對表現存在的集體行動秩序與個人精神秩序之間的沖突之疑惑。是閻連科“神實主義”小說創作的一個共性,也是閻連科在獨辟蹊徑的小說實踐過程中結合自身生命體驗所產生的思想詰問。甚至某種意義上,閻連科所演繹的 “神實主義”世界本身幾乎就是一個帶著無數疑問的“失序的世界”。
而閻連科筆下的耙耬世界,其存在的秩序表面上是一個由懼死到向生的過程:《日光流年》里的人為了打破活不過四十歲的命運,一代代地尋找突破命運的途徑;《受活》里的殘疾人為了讓自己“活出個所以然”,以殘缺的身軀支撐起各種絕技;《炸裂志》里的村民為了洗刷掉貧困的背景,在村長的帶領下齊心協力地將耙耬山脈里的一個村改造成超級大都市……在此意義上,耙耬山脈這個想象的世界似乎無不充滿著非常一致的現行秩序,即人們都有著非常強烈的愿望去擺脫死亡與貧困,去獲得新的生活;人們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做著同一件事情,那就是生存或獲得存在感。但實際上,由懼死到向生中間所體現的并非人性的光輝而是失控的秩序:人們在“致富”過程中,可以嗜血成性(《丁莊夢》),不得不割肉賣皮(《日光流年》),甚至樂意為“婊子”立牌坊(《炸裂志》),展示自己的殘缺的肉身(《受活》)。個人精神秩序的失范直接導致鄉土倫理和日常道德的淪陷——人們“力爭上游”背后的失序才是閻連科所關注的真實,而并非表面敘事的那層現行秩序。也正是這樣的失序,重復地出現在“神實主義”創作的多部作品中,袒示了作者對現行秩序的質疑,對現實主義的質疑,甚至是對真實世界本身的質疑。
“長期以來,我們的文學注重于描摹現實,而不注重于探求現實。現實主義在當代文學中被簡單理解為生活的畫筆,作家的才華是那畫筆的顏料。”④因此他強調自己要透過“神的橋梁”,到達“實”的彼岸——那種存在彼岸的“新的現實”和“新的真實”,是今天奉行的現實主義無法抵達和揭示的真實與現實。⑤當集體行動秩序遮蔽了個人精神秩序的時候,人的命運將會何去何從,才是“存在”這個命題的依據。也正因如此,《日光流年》中的那種夢魘般的疾病不是真實的準心,人們為了生存不惜賣皮賣肉這種失控的秩序狀況才是衡量真實的籌碼。正如《丁莊夢》里泛濫的賣血現象只是“看得見的真實”,而人們為了獲得存在的依據而心甘情愿地賣血才是作家“探求到的真實”。換言之,當既定的集體行為秩序跟未定的個人精神秩序產生碰撞的時候將會發生怎樣的結果,才是閻連科所要探求的真實。他以“秩序的潰敗”這一形式來表達他對秩序的態度——就像《日光流年》里人們賣皮賣肉來開鑿運河,最終流淌出的卻是死水;《受活》里殘疾人苦心經營所得來的錢最終被圓全人卷走。
但閻連科并沒有止于揭示失序的存在,他顯然希望通過“神實主義”進行一場具有救贖意味的嘗試,因此“神實主義”小說中往往會出現一位“存疑者”。《受活》里面的茅枝婆便是這樣的一位角色。她在年輕的時候經歷過“革命年代”,親歷集體行為秩序跟個人精神秩序產生碰撞所造成的失序。所以當柳縣長要繼續重復懼死而向生的歷史,繼續重啟那份曾將世人引入癲狂的集體行為秩序之時,茅枝婆便擋在路上。她爭取“退社”的舉動隱喻著對個人精神秩序的回溯,但她最終又同意絕活團的計劃又體現了她已不自覺地陷入集體行為秩序的泥潭里。相似地,在《丁莊夢》里,當所有人都以血液作為可再生的資源來獲得存在依據的時候,只有爺爺對這種高度一致的現行秩序表示質疑。即便是在新作《炸裂志》里面,閻連科也設計了這樣一個“存疑者”的角色:市長孔明亮的四弟孔明輝是一位游離于現行的集體行為秩序之外的人,即使當上了局長也不接受送禮,堅持步行上班。他被集體行為秩序中的人視為精神病人。但正是這么一個角色,通過解讀一本歷書,預言了炸裂市的命運。在孔明輝身上,我們可以明顯地察覺到他對集體行為秩序的質疑以及對個人精神秩序的堅持。巧妙的是,同樣是對秩序的存疑,《受活》里的茅枝婆跟《丁莊夢》里的爺爺在態度上都顯示出不同程度的游移,但新作《炸裂志》里的四弟孔明輝則非常堅定地恪守個人精神秩序。在這個細節里,我們也可以窺覓到閻連科的精神嬗變——在創作上又體現為不隨流不從眾,掙脫“約束和想象的軟弱”。用閻連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 長期在寫作上的自我約束,終于就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地大多喪失了自我,喪失了獨立的個性表達,喪失了獨立的思考和獨立的寫作方式,也形成了無意識的思想上的‘自我管理’。”⑥
四、結語
沒有相對固定的重復性和普遍性,就無法構成規律。沒有內在規律便喪失了構成“主義”的基本前提。閻連科的“神實主義”小說創作,其內部確實存在著不同程度的重復性或規律性。但這種重復性所構成的內在穩定性卻未能完全在理論角度將“神實主義”獨立出來。它反而更像是作家對虛構與真實、傳統性與現代性的某種突圍行為與經驗嘗試。這種重復性不單只揭示了閻連科自身對自己、對世界、對文學的認知,還在某個意義上互文性地構成了他的精神自傳。“神實主義不是哪個作家的發明創造或夢中囈語,而是在中國古典文學中早已有之,只是我們沒有從神實主義的角度去考查和研究”⑦——然而,單憑一位作家一系列作品中所出現的重復性便將其提煉出來并獨立生成一種“主義”,并從古今中外其他作家的相關作品中尋找理論支撐和舉證依據,這種做法顯然是單薄的。
雖然略顯草率地命定“神實主義”直接暴露了閻連科某種帶有主觀性的理論誤讀,但卻從客觀上反映出在接受現代性和審視本土空間的時候,作為中國當代作家一份子的閻連科在固有的“現行思想狀態”或“集體行為秩序”中突圍的果決姿態。因此也有學者認為,神實主義不是別出心裁的發明,而是對隱伏在創作思維的現象的發現,是閻連科在小說創作過程中面對“現實”這一命題時的精神自救。⑧這場精神自救必然會闖入各種“誤區”,但它更必然地是一個重構自身與外部世界關系的漫長過程。
唐蓓 暨南大學
注釋:
①閻連科. 我的現實 我的主義[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07頁。
②⑦閻連科.發現小說.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79,192頁。
③閻連科,梁鴻.巫婆的紅筷子:閻連科、梁鴻對談錄.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4月版。在該書的第44頁、第56頁、第57頁、第58頁、第94頁、第96頁等多處地方,均有記錄了閻、梁關于重復性和差異性的對話。
④閻連科, 神實主義產生的現實土壤與矛盾, http://read.dangdang.com/content_2484858?ref=read-2-D&book_id=17501
⑤閻連科.當代文學中的“神實主義”寫作——在常熟理工學院“東吳講堂”上的講演.東吳學術,2011年第2期。
⑥閻連科. 一派胡言:閻連科海外演講錄.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11頁。
⑧孫郁. 閻連科的“神實主義”. 當代作家評論,2013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