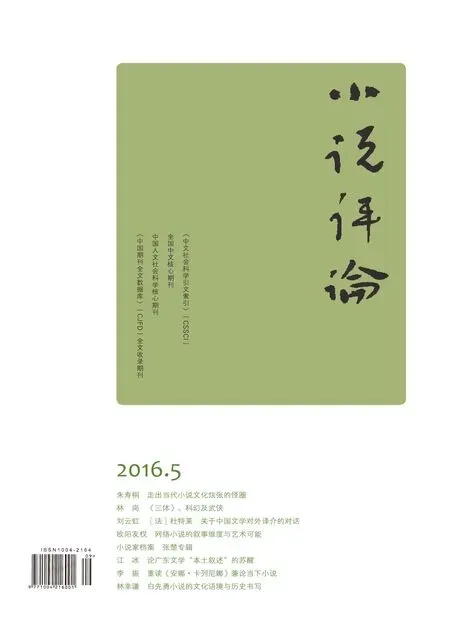張楚小說論
李建周
張楚小說論
李建周
張楚的小說,給人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修辭可信感。這種修辭可信感并非來自故事的傳奇性和事件的轟動性,而是來自作家對民眾熟知生活的戲劇性處理,來自隱藏與作家內心深處的空洞感,以及這種空洞感帶來的殘酷的詩意。日常生活的戲劇化處理使得張楚的小說帶有某種程度的先鋒性。這也是很多人在私下里討論張楚小說時經常談到的。但是細究起來,在先鋒寫作已經成為文學史常識的今天,僅憑這個概念標簽無法確切表述作家的真正創作內涵。那么,張楚的小說到底“先鋒”在什么地方呢?在筆者看來,這個秘密隱藏在文本的結構張力和作家的情感張力之中。
一、作為“認識裝置”的望遠鏡
初次在張楚的小說中讀到望遠鏡,是在《七根孔雀羽毛》的開頭。當“我”在陽臺上向對面樓房窺探時,驀然發現對面那個經常開著浴霸洗澡的女人,正在“裸著乳房駕著一臺望遠鏡四處鳥瞰”。這個“胖得像頭刮了毛的荷蘭豬”的窺視者,恰恰出現在“我”興致勃勃的窺視中。如此精妙的一個看與被看的場景,自然讓人聯想到視覺文化中的權力關系。有經驗的讀者會不由自主猜想,這個場景很可能是作家在為之后不同尋常的情節做鋪墊,可是張楚的興奮點卻很快發生了轉移,這一看似別有用心的場景倏忽一閃而過,除了使“我”遠離陽臺之外,并沒有暗藏更為隱秘的敘述動機。其實這種不經意間“浪費”的細節,在張楚的小說中還有很多,一方面可以看出作家在敘事策略上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作家捕捉日常生活細節的功力。
曲別針、長發、蜂房、孔雀羽毛、野薄荷等等,這些看起來毫不起眼的平常物象,經過作家的精心打磨,在文本中獲得了自足的生命和自由的生長空間。那些經過了作家類似現象學還原式處理的“事物”,成為文本的重要支撐點,與人物的命運發生隱秘的內在關聯,同時負載了作家對自我意識的探究。進而,這些有著很真確的具體性的小道具有可能成為張楚小說的重要裝置,起到關聯文本結構層級的作用。在我看來,《夏朗的望遠鏡》中的“望遠鏡”,就具有這種結構性意義。對我而言,“望遠鏡”是進入張楚小說世界的一個重要通道。
小說很容易讓人想到清代李漁的《夏宜樓》。我無法斷定張楚是否讀過《夏宜樓》,但可以肯定的是,望遠鏡在兩部小說中同樣具有支撐性作用。李漁把故事放在元朝末年,僅為極少數人所知的望遠鏡,在小說中成為超于世間的“神物”,在結構上成為故事發展的重要推手。偶得望遠鏡的書生瞿佶,跑到高山寺租下一間僧房,終日以讀書登眺為名窺視大家院戶,搜尋意中佳人。如果說李漁把望遠鏡的實用功能發揮到極致的話,那么張楚則把望遠鏡的非實用功能發揮到了極致。在西方各國用望遠鏡四處開拓殖民地的時候,書生瞿佶對它的中國式使用,讀來不免讓人唏噓。在《夏朗的望遠鏡》中,那架更為高級的天文望遠鏡的意義,恰恰在于它的實用功能在夏朗現實生活中的“無用性”。這個關于日常生活微觀政治的故事,并無大喜大悲的離奇情節,卻讓人看到隱藏在日常生活表象下的令人震驚的精神處境。夏朗與方雯是同一單位的公務員,一個老實厚道,一個通情達理。雙方父母同樣為子女辛勤操勞,算得上和諧;兩家也都是縣城里的“中產階級”,算得上門當戶對;兩人戀愛既偶然有平常,算得上美滿。但就是這樣看似和諧幸福的家庭,卻在上演著驚心動魄的日常生活微觀權力的斗爭。因方雯的父母買下婚房,所以與小兩口婚后同處一室。慢慢地,姑爺在方雯父母眼里由心頭肉變成了眼中釘,于是他們對夏朗由噓寒問暖變成處處刁難,由近乎諂媚的討好變成滿臉威嚴的訓斥。一心想擺脫被方家控制的夏朗,想自己買房,結果還是不得不和岳父家買了對門。同時由于孩子的出生,夏朗也一直在方家“優雅的蔑視”中和岳父母居住在一起,由座上賓變成了一個真正的陌生人。“望遠鏡”這個在夏朗庸常生命中至關重要的精神性存在,在岳父方有禮眼里只不過是個讓人“玩物喪志”的破玩具。它的“無用性”隱喻夏朗的精神追求在現實世界的無用性。這種精神生活的“無用性”,正如藝術在現代社會實用意義上的“無用性”一樣,成為反思現代性危機的重要切入點。
作為“窗口”的望遠鏡,讓夏朗發現了生活的另一面。換句話說,望遠鏡在小說中是夏朗的“認識裝置”,通過它,一個高于刻板的現實生活的另一個生存空間的大幕徐徐拉開。在這個意義上,看似無用的望遠鏡和《夏宜樓》中的望遠鏡,甚至和艾特瑪托夫《白輪船》、王小波《尋找無雙》中的望遠鏡,就有了本質上的區別。這里的望遠鏡不單單是小說的道具,而且是啟開文本深層結構的一個開關。通過這樣一個“認識裝置”,呈現一個如夢境般虛假和飄忽的世界,從而為千瘡百孔的日常生活找到一個對稱域,在既承受又抗辯的結構中呈現了欣悅與酸楚的內心張力。
如果說《夏朗的望遠鏡》中的“望遠鏡”具有結構意義的話,那么在其他多數作品中存在同樣的結構。在隱喻的意義上,張楚小說中呈現的日常生活,正像是“望遠鏡”中變形的“風景”。作家借助自己的“認識裝置”提煉“風景”時,將日常生活進行了變焦。這樣,在敘述日常生活故事時,擴展了文本的審美空間,呈現一種更為審慎的結構和情感的張力關系。
二、結構張力:“細菌”與“羽毛”
作家將目光聚焦日常生活的具體性,曾經是80年代后期的一種小說寫作策略。這一文學策略集中體現在新寫實小說家身上。從文化政治的角度來看,有對抗意識形態的操控和升華的隱秘動機。問題是這一敘述指向在新寫實作家那里并不是自明的。當他們將自己的筆觸轉向具體生活時,和內心的理想主義氣質形成一種尖銳的沖突,所以流水賬式的生活背后流露的是作家對自己所寫生活的抵制和抗拒。在之后大量的仿寫者那里,這種具體性的敘述策略滑向了簡單的經驗主義,甚至連基本的個人審美烏托邦都被掃除一空。在當下,面對爆炸式網絡信息的現場感和時效性,日常經驗書寫的有效性顯得十分可疑。在此背景下,張楚的探索顯現出了不尋常的意義。
張楚小說呈現的日常具體性嚴謹精準,摻雜著細微的社會觀察,以及階層的分化而滋生的復雜心態。作家并沒有僅僅滿足于對日常生活細節的還原,而是對這種具體性有著某種程度的反撥與抗衡,形成一種隱秘的內在張力。小說試圖呈現一種基質性的情境,將瑣屑、矯飾與殘酷、憂郁的東西放在一起,使得日常瑣事與內心的絕望相結合,通過并置構成小說的戲劇性。借助此,張楚一方面在經驗描述上精準地放大細部,顯示出日常生活令人驚心動魄的一面;另一方面在不同的結構層面努力發掘探究精神救贖的可能。
張楚小說到處有令人震驚的“細部”,這些地方真實可感、精確鮮明,讓人念念不忘。《七根孔雀羽毛》中李浩宇對宗建明講的“玩具上的細菌”非常典型:
“有誰會跟玩具過不去呢?我們這些人,不過是依附在玩具上的細菌。或者說連細菌都不如,只是一個個原子那么大的物質。外星人肯定也不是以我們通常認為的方式存在,他們可能是氣體,也可能是液體,更有可能是透明的非物質。他們干嘛非得以人類肉體的方式存在呢?”
這個被宗建明認為是基督徒或者瘋子的李浩宇,本來有著顯赫的家庭背景,父親是遠近聞名的大款丁勝,自己在縣城當公務員,無論是物質生活還是社會地位都有明顯的優越性,但是富二代的身份并沒有給他帶來內心的幸福安樂。相反,精神上不斷積累的傷痕使他極力渴望擺脫污濁的現實,而寧愿把心靈寄托在遙遠的外太空。“宇宙恐懼癥”表明其內心深深渴望心靈的依靠。他的“細菌理論”不僅是對自己生活基本狀況的描述,更是對當下現實生活真相的洞察,甚至是中國走向現代過程中啟蒙現代性和審美現代性自我糾纏的顯影化和具相化。
如同李浩宇的“細菌”一樣,宗建明對羽毛的珍愛同樣讓人感到不可思議。宗建明十分小心地把那七根孔雀羽毛放在已經破了口子的,上大學時買的棕色皮箱內。與之相伴的是開膠的乒乓球球拍,散發著霉味的獎狀,干掉的野花。這些物象構成一種挽歌式的回憶:“我已經忘記了這是我多少次打開它,在冬日昏暗的光線里欣賞這些羽毛了。屋子里沒有開燈。羽毛色澤黯淡,密集的絨毛上長著一只沉郁的藍眼睛。”這種個人回憶與80年代的理性主義氛圍是相互交融的。張楚的作品中時不時出現對80年代的眷戀與悵惘,但是歷史已經將兩個時代攔腰斬斷。在伯林看來,“對過去歲月的浪漫渴望,實質上是一種取消事件‘無情的’邏輯性的欲望。”①現實的邏輯是無情的,如同被人拋棄的理想主義一樣,這些宗建明個人記憶中神圣之物,在他的同居情人李紅看來不過是毫無用處的“破羽毛”。也只有在丁丁這樣不懂事的小孩子眼里,羽毛才莫名其妙具有了非要得到的重要意義。而那些“懂事”的大人,已經無法看到羽毛的詩意光澤。小說中七根孔雀羽毛“無意義”的意義,一如藝術作品之于物質現實。
“細菌”同“羽毛”在小說結構上是對稱的,就像李浩宇和宗建明是對稱的一樣。宗建明的堅守和李浩宇的彷徨形成一種對應,共同拓展了文本的精神空間。或者說,這兩個人和周圍的人形成一種對峙與張力,提示著小說中另一審美空間的存在。從這兩個人來看,他們有著不同的生活經驗,在敘述進程中又各自走向自己的反面,在文本結構上形成一種反向呼應。這種呼應的背后體現的是作家的一種詢喚,對日常生活邏輯“另一面”的詢喚。它不是意識形態抗辯似的“曠野呼告”,卻是一種更為內在的忍耐與堅守,雖然這種堅守在遭遇冰冷的現實時往往是失敗的,但是小說人物的失敗恰恰促成了藝術上的成功,一種在高速飛馳的時代列車上產生的眩暈感和揪心感油然而生。
現實的殘酷與內心的詩意如果糾結于一個人身上,會讓人骨子里感到黑暗的虛無,這樣的時代緊張感簡直是難以承受的。《曲別針》中的李志國,一個現實生活邏輯中司空見慣的成功者。他適應現代生活,不擇手段賺錢,因欲望膨脹與妻子感情淡漠,和妓女糾纏不清。不過這個兼具商人、嫖客和殺人犯多重身份的人,卻曾經是個愛寫詩的文藝青年。雖然詩意的夢想逐漸被現實生活碾碎,但是李志國并沒有完全被強大的現實邏輯所淹沒。為了緩解內心的緊張和焦慮,他迷上了路易斯裘德的曲別針藝術。由于和妓女的糾纏,他沒能接到病中的女兒打來的電話。當妓女想搶走女兒送給他的水晶手鏈作為報酬時,對妓女的憤怒和對女兒的愧歉終于在一瞬間爆發了。掐死人后的李志國,接到女兒再次打來的電話后卻一句話沒說,內心的緊張和糾葛也達到了可以忍受的邊界。曲別針這一封閉的回環式幾何圖形,與李志國內心的糾纏互為印證。生存困境、心靈扭曲、道德危機、良心發現等等多重時代意涵共存于一身。沉浸于欲望洪流中的李志國,在心靈不堪重負的折磨下付出了死亡的代價。盡管小說的結局略顯簡單,但人物的內心緊張感卻清晰可見。
如果沒有李志國的悲劇,這個廠長嫖娼的故事很可能成為一種生活輕喜劇,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張楚極力渲染李志國嚼曲別針自殺的悲劇場景,試圖尋找一種隱在的救贖的可能性。在社會矛盾激化、生存環境惡化、人欲肆虐的當下,這種審美烏托邦顯示出自身可貴的一面。作家對人物命運的悲劇性處理,背后隱含的是當下人和自己的物質世界之間的矛盾。個人審美烏托邦不是以構想美好的社會理想為特征,而是從個人理想出發,試圖維護人的自然屬性和拯救人性。它可以冷靜測量理想與現實的距離,也可以自由拉近幻想世界與現實世界的距離。雖然張楚并沒有刻意強調個人審美烏托邦,但文本結構上有意進行了探索,試圖在烏托邦和反烏托邦之間建構某種張力的平衡。在烏托邦審美救贖被無限推延的時代,這一做法顯得尤為可貴。
文學解決現實的能力是有限的,讓文學回到文學,這其實也是當代作家的一個隱秘的敘事傳統。對于小說藝術來說,試圖以喧鬧吼叫凸現自身價值僅僅是自欺欺人的藝術幻覺而已。張楚有意將生存場景與背后的多重精神幕布進行深層勾連,在沉靜下來的情感模糊地帶勘探真正的精神密碼,因為精神變得過分清晰的時候,恰恰是精確的算計取代了復雜的情感。
三、“風景”的冷與熱
“望遠鏡”中變形的“風景”是有溫度的,這一溫度負載著作家的自我意識及其美學評判。張楚小說呈現的日常生活“風景”,多是處于鄉村和都市兩個極端之間的小城鎮,這里幾乎集中了當代中國的社會綜合癥。作家描摹“風景”時,不經意間會透露出民眾秘而不宣的內心風景。當張楚以一種波瀾不驚,從容不迫的語調敘述時,還是能讓人很容易感到“風景”背后作家溫暖隱痛的內心情感。讀者在“風景”中驀然發現作家的心靈投影,在嚴峻的生活背后感到一種憂傷的撫慰。風景之冷和內心之暖的對比,預示著作家強烈的內心掙扎。隱藏在“風景”背后的作家自我意識的糾纏給文本帶來令人震驚的戲劇性。
在張楚的小說中,文本表面呈現的是一幅幅“冷風景”。在陰霾籠罩的華北平原,在處于鄉村和城市之間的小城鎮上,從街頭到家庭,從工地到工廠,從酒吧到網吧,只要深入人物內心,就會發現一種沉浸在時代喧囂背后的不安和焦慮。這從普通民眾時時顯露出來的戾氣中可見一斑。冰冷的現實以及人們各自的生命軌跡交錯混雜。底層民眾的內心生活與精神疑難,被各種形形色色的敘事不斷刪改和編纂,每一種敘事背后都是一種或宏大或微觀的權力關系。只要稍微留意從各種敘事的縫隙流露出來的真實的側影,就會發現當下生存境遇的嚴峻和精神的大面積潰敗。
人們的生活境遇卻并沒有因為財富的積累而有所改觀,依舊是低矮的平房,泥濘的鄉土路,被濃煙熏染的天空,更可怕的是小鎮人內心的齷齪與焦躁,貧瘠和悲涼。
《剎那記》中櫻桃,一個只有三個手指的丑姑娘,在母親的情感陰影中頑強地活著,唯一的女友劉若英不斷奚落和利用她,唯一惦念的男友羅小軍一直追打和羞辱她。被強奸卻連真相都沒有人可以訴說。既使九十多歲的老人,也無法逃脫步步緊逼的“冷風景”:“蘇玉美緩緩坐進鏟車里。她那么小,那么瘦,坐在里面,就像是鏟車隨便從哪里鏟出一個衰老皮膚皸裂的塑料娃娃。這個老塑料娃娃望了望眾人,然后,將老虎鞋放到離眼睛不到一寸遠的地方,舔了舔食指上亮閃閃的頂針,一針針、一針針地繡起來。”這是《老娘子》中出現的令人震驚的場景,這些“冷風景”是普通民眾真實的生活境遇的歷史見證,同時也是他們心靈傷痛的無望呼告。
在一路高歌猛進的現代化高速公路上,很容易忽視道路兩旁那些灰燼般的底層人群。他們常常要面對的精神的潰敗與物質的匱乏,他們想盡辦法逃離卻一次次陷入困境,他們有的用謊言來與現實困境抗衡,他們有的苦中作樂以期謀求一點點生存空間。對于關注底層生活景況的人來說,這樣的現實圖景并不陌生。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地下室式的“冷風景”,在張楚小說中并不是用來展示的,這使得張楚的小說和底層敘事區分了開來。張楚雖然寫到底層,但是并不愿意刻意展示底層的傷口,也無心像經典現實主義作家那樣,為時代提供歷史精確性的模擬圖景。作家意識到歷史的精確或準確并不能保證小說的品質,藝術真實有著更高的要求,所以試圖把小說的真實提升到生存的普遍性的層面,并與具體個人的個性生活融為一體。與模仿或復制現實相比,張楚的小說更像一個象征世界,通過對日常生活憂郁感傷的體驗,深入到多重人性的暗道,為人們提供思考當下精神處境的契機。
同樣是地下室式的“冷風景”,安德列耶夫的《在地下室里》探討了救贖的可能。一無所有的希日尼亞科夫生活于令人毛骨悚然的死神的注視中,荒誕可怕的惡夢和強烈的內心痛苦交織在一起。娜塔麗雅,一個沒有出嫁的姑娘手里抱著出生才六天的嬰兒,獨自行走在刮著徹骨寒風的冰天雪地里,卻不知道自己唯一可去投靠的妓女姐姐卡佳剛剛去世。然而正是在這樣絕望的令人窒息的場景中,女房東瑪特蓮娜老太太接下了娜塔麗雅的孩子,給嬰兒洗澡時孩子的哭聲使得整個世界都變了。無論是小偷、妓女,還是孤獨者、垂死者全都伸長脖子,臉上煥發出驚訝、幸福、燦爛的笑容。這個脆弱的小生命像草原上的一星火光,逐漸照亮了人們內心僅存的希望,就連垂死的希日尼亞科夫也獲得了新生,“破碎的胸膛里滾起熱淚的新浪花”。這并不是作家的天真浪漫,也不是簡單的理想主義,而是文學中發生的“事實”。在有著濃郁宗教背景的俄羅斯,故事中的嬰兒恰如隱身的上帝,負載著救贖的希望和信仰的力量。
在沒有嚴格宗教背景的當下中國,張楚不會像安德列耶夫那樣處理作品。盡管張楚對自己筆下的“冷風景”有著不滿,但卻并沒有直截了當給人救贖的力量。在書寫自己并不愿意看到的“冷風景”的時候,與之對話和抗爭就成為張楚的必然選擇。張楚的對話姿態不是橫眉冷對,有時候更像一個天真的大孩子,讓“冷風景”發出談談的詩意的光澤。看似“弱”的回應,卻顯示了更為內在的堅忍和耐心。張楚當然知道這樣處理是“弱”的,但是正如上帝之愛的“弱”一樣,盡管是微茫的,但卻是作為時代良心的作家不得不真正面對的。于是,就有了《大象》中溫暖的雙線結構:孫志剛夫婦尋找救助過患病養女孫明凈的恩人,病友勞晨剛幫助孫明凈尋找生父母,就有了《剎那記》結尾的七星瓢蟲,《地下室》中突然出現的鳳尾蝶,《細嗓門》中不斷閃現的粉紅色烏鴉,《七根孔雀羽毛》中反復渲染的長著眼睛的“羽毛”。這種詩意的光澤漸漸開始照亮地下室式的“冷風景”。或者說,它們和地下室式的“冷風景”構成一種結構上的對話。
在柄谷行人看來,作品中的風景是和作家孤獨的內心狀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可見,風景不是自在的,對風景的發現和描摹與作家的對內心的強烈關注是同時發生的,所以內心生活越是繁復和糾結,越有可能發現別人不能發現的風景。這樣,風景也就成了現實的一部分:“我們稱之為‘現實’者,已經成了內在化的風景,也即是‘自我意識’。”②在這個意義上,張楚小說中有兩個風景:外在的“冷風景”和內在的“熱風景”。而“風景”的冷熱正是張楚自我意識的兩面。盡管希望是微茫的,但是作家并沒有放棄在內心深處以審美之熱抗衡現實之冷。
張楚觀察世界的眼光和情緒,決定了小說如話家常式的敘述語調。和先鋒小說非人格化的敘述語調相比,張楚的小說對讀者沒有強烈的壓迫感,作者與讀者的情感交流是充分的和內在的。在先鋒作家筆下,非理性行為在人物面臨絕境時經常會被放縱,進行充滿恐懼感和荒誕感的實驗,這種實驗在當下的現實情境中,很容易演變成新的苦難奇觀和酷烈表演。同時,日常碎碎生活書寫中世俗形象持續發酵,小說中人物成為欲望的符號和化身。作家往往僅僅拘泥于現實經驗或感官感受,對之進行直接的演繹書寫,將深層的心靈悸動懸置。這兩種敘事策略在張楚身上,開始保持一種微妙的平衡。張楚有意對生活保持了恰當的克制與忍耐,并試圖尋找冷酷后面的悲憫,陰影背后的溫暖。自我意識中暖色調的存在,使得張楚的小說有著內在的理想主義氣質,但這種理想建基于對當下生存“冷風景”的洞察之上,并且在“冷”與“熱”的強烈對比中,呈現一種憂傷的緊張感。
本文系河北師大博士基金“文學體制與先鋒文學(W2010B05)”成果之一。
李建周 河北師范大學
注釋:
①【英】以賽亞·伯林:《現實感:觀念及其歷史研究》,潘榮榮、林茂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5頁。
②【日】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趙京華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