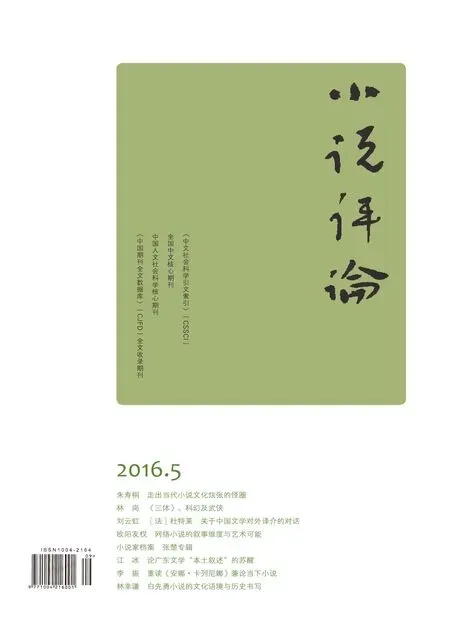沈從文早期的文學批評
張新穎
張新穎專欄 讀書記
沈從文早期的文學批評
張新穎
一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四歲的沈從文,一個發表了一些散文和小說的年輕人,撰寫了一篇批評長文,題為《北京之文藝刊物及作者》:“茲但就我所知而較足為此新興時代代表者數種來說,先列其名稱,對于各作家之藝術觀及作風,更于后分別略一言之。”小標題列出的刊物,即達十九種之多;對文壇的關注、對不同作者群體的了解和對刊物的熟悉程度,于此可見一斑。文中議論小說、散文、詩歌、戲劇各家創作,信手拈來,坦率真切,譬如——
他喜歡馮文炳的小說《竹林的故事》;熟人中凌叔華的作品,他說“劣點是人物總不大有生命,尤其是男的”,而不是“那些無論對什么都感到有缺點的‘小批評家’”慣用的“范圍太窄了,脫不了老爺太太小姐的話”之類的指摘。他順便掃了一筆,“我說的小批評家,這類人在北京是很多的。”
他贊賞徐志摩的散文,卻對他的詩,以及模仿或類似他的詩,有可謂尖銳的批評,他說,“從字的華美上增加詩的熱情”,把“一些老調子借為座上客”,讀者因為熟悉“就覺得他們的詩好”,“其實這種樣子下去,要詩的前途轉入一個新的境界,那是沒有希望的。志摩的詩,雖說已立了一個新的境界,……也許是詩興太熱烈了,下筆不能自己似的,總是傾筐倒匣的,……他的詩句子正因其為太累贅,所以許多詩句子徒美,反而無一點生命。”——令人驚訝的,不僅是他沒有因為徐志摩對己有恩而下筆有所顧忌,更重要的是由此而論新詩之弊病和前途,有如此反一般印象和議論的卓見。
他喜歡周氏兄弟的散文,而他們又那么不一樣:周作人的文章,“像談話似的,從樸質中得到一種春風春雨樣的可親處來”;“魯迅先生似乎就不同了。把他四十年所看到社會的許多印象聯合在一起,覺得人類——現在的中國,社會上所有的,只是頑固與欺詐與丑惡,心里雖并不根本憎惡人生,但所見到的,足以增加他對世切齒的憤怒卻太多了,所以近來雜感文字寫下去,對那類覺得是偽虛的地方抨擊,不惜以全力去應付。文字的論斷周密,老,辣,置人于無所脫身的地步,近于潑辣的罵人,從文字的有力處外,我們還可以感覺著他的天真。”
——這篇長文出自一個剛剛踏入文壇的年輕人之手,卻顯出文學思考和見識的相對成熟,這種成熟程度,可能還要高于同一時期他自己的創作;它還顯示出,對格局、大體的觀察和把握,對個別、特性的理解和辨識,這些方面的突出才能兼備而平衡。這樣的文章至少表明,沈從文不是一個自顧埋頭創作的人,他在自己的創作之外,還特別留意他所置身其中的文學的總體,以及別人的文學;而且,他有要把自己的看法說出來的沖動。注意到這些,以后看到他對文學運動、現狀和趨向發表意見,參與甚至引發文學論爭,撰寫系列的作家論、詩人論,就不會特別意外了。他也許無意做一個批評家,實際上卻常常忍不住力陳一己之見,哪怕因此而招惹是非。
二
一九二九年,沈從文到中國公學任教,開的課為新文學研究和小說習作,每周課時不多,想來應該是很輕松的;實際上,他花了很大的精力準備,耐心地編寫講義。這里要特別提出,這兩門新課,從國文系傳統眼光看來,似乎是沒有什么“學問”的,講課的人自己也不免低人一等的感覺;換種眼光看,卻實為開風氣之先的課程設置和教學實踐,其重要性要到很久之后才會被慢慢意識到。
沈從文的新文學研究課,第一個學期講中國新詩,第二個學期講現代小說,“新的功課是使我最頭痛不過的,因為得耐耐煩煩去看中國的新興文學的全部,作一總檢查,且得提出許多熟人”。一個本來專事創作的人,因為教學的需要,同時成了一個批評家和研究者;還不僅如此,另有超出個人之外的意義:很多年之后,中國新文學成為一門學科,研究這一學科史的人追根溯源,探尋究竟是什么人在什么時間于什么學校開設專門的課程,確認最早是朱自清一九二九年春季在清華開課,并編有講義《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不過,很少有人注意到,半年之后,即有沈從文在中公的新文學研究課;再過一年,沈從文到武漢大學教書,仍講此課,并印行了講義《新文學研究》。
以新詩發展為內容的講義《新文學研究》,鉛印線裝,前列“現代中國詩集目錄”,然后編選分類引例為參考材料,后半部分是六篇文章,分別論汪靜之、徐志摩、聞一多、焦菊隱、劉半農、朱湘的詩。
這一時期沈從文批評文字的產生,直接關聯于他大學教師的新身份,關聯于他在中公和武大講授新詩和現代小說的新文學研究課程,因而大部分即脫胎于他的講義;反過來,我們也可以由這些文字——《郁達夫張資平及其影響》《論聞一多的〈死水〉》《論汪靜之的〈蕙的風〉》《論焦菊隱的詩》《論馮文炳》《論郭沫若》《論落花生》《論施蟄存與羅黑芷》等系列作家論,以及《我們怎樣去讀新詩》《現代中國文學的小感想》等文章——想象沈從文的課堂。
不妨從不同的角度,抽出三篇來看:
先看《論聞一多的〈死水〉》,因為聞一多很重視這一篇評論。沈從文說,聞一多的作品有“一個‘老成懂事’的風度”,那種“理知的靜觀”“那種安詳同世故處,是常常惱怒到年青人的。”因為這樣的作品不符合通常對“詩”的想象和期待,不是“合乎一九二〇年來中國讀者的心情的詩歌”。由此,沈從文指出,朱湘的《草莽集》和聞一多的《死水》,“兩本詩皆稍稍離開了那時代所定下的條件,以另一種態度出現,皆以非常寂寞的樣子產生,存在。”特別是《死水》,“在文字和組織上所達到的純粹處,那擺脫《草莽集》為詞所支配的氣息,而另外重新為中國建立一種新詩完整風格的成就處,實較之國內任何詩人皆多。”因技術的“完全”,所表現雖然是平常生活的一面,“然而給讀者印象卻極陌生了。使詩在純藝術上提高,所有組織常常成為奢侈的努力,與讀者平常鑒賞能力遠離,這樣的詩除《死水》外,還有孫大雨的詩歌。”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日,在青島大學擔任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的聞一多給朋友朱湘、饒孟侃寫信說,沈從文“那篇批評給了我不少的興奮”,“他所說的我的短處都說中了,所以我相信他所提到的長處,也不是胡說。”(《聞一多書信選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224頁)
第二篇看《論馮文炳》,因為沈從文在文章里談到了自己。文章先談周作人的文體風格和趣味,由此進入對馮文炳(廢名)的論述,簡潔而清晰地勾勒出文學史的脈絡。沈從文對馮文炳有感同身受的贊賞,但又有非常的不同。他這樣說:
把作者,與現代中國作者風格并列,如一般所承認,最相稱的一位,是本論作者自己。一則因為對農村觀察相同,一則因背景地方風俗習慣也相同,然從同一方向中,用同一單純的文體,素描風景畫一樣把文章寫成,除去文體在另一時如人所說及“同是不講文法的作者”外,結果是仍然在作品上顯出分歧的。如把作品的一部并列,略舉如下的篇章作例:
《桃園》(單行本)、《竹林故事》《火神廟和尚》《河上柳》(單篇)
《雨后》(單行本)、《夫婦》《會明》《龍朱》《我的教育》(單篇)
則馮文炳君所顯示的是最小一片的完全,部分的細微雕刻,給農村寫照,其基礎,其作品顯出的人格,是在各樣題目下皆建筑到‘平靜’上面的。有一點憂郁,一點向知與未知的欲望,有對宇宙光色的炫目,有愛,有憎,——但日光下或黑夜,這些靈魂,仍然不會騷動,一切與自然和諧,非常寧靜,缺少沖突。作者是詩人(誠如周作人所說),在作者筆下,一切皆由最純粹農村散文詩形式下出現,作者文章所表現的性格,與作者所表現的人物性格,皆柔和具母性,作者特點在此。《雨后》作者傾向不同。同樣去努力為仿佛我們世界以外那一個被人疏忽遺忘的世界,加以詳細的注解,使人有對于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認識,馮文炳君只按照自己的興味做了一部分所歡喜的事。使社會的每一面,每一棱,皆有一機會在作者筆下寫出,是《雨后》作者的興味與成就。用矜持的筆,作深入的解剖,具強烈的愛憎有悲憫的情感,表現出農村及其他去我們都市生活較遠的人物姿態與言語,粗糙的靈魂,單純的情欲,以及在一切由生產關系下形成的苦樂,《雨后》作者在表現一方面言,似較馮文炳君為寬而且優。
第三篇,《論郭沫若》。即使仰仗“后視之明”,我們仍然無法確鑿地判斷,這篇尖銳的文學批評,與十八年后時代轉折之際郭沫若對沈從文嚴厲的政治批判,之間是否有隱秘的關聯,有多大程度的關聯;不必強作聯系,無妨存而不論。
沈從文說:從五四以來,郭沫若大量的翻譯和創作,“這力量的強(從成績看),以及那詞藻的美,在我們較后一點的人看來覺得是偉大的”;不過,“郭沫若可以說是一個詩人,而那情緒,是詩的。這情緒是熱的,是動的,是反抗的,……但是,創作是失敗了。因為在創作一名詞上,到這時節,我們還有權利邀求一點另外的東西。”這里的“創作”,主要指的是小說,郭沫若的《我的幼年》和《反正前后》,“雖是這是自敘,其實這是創作。……我們要問的是他是不是已經用他那筆,在所謂小說一個名詞下,為我們描下了幾張有價值的時代縮圖沒有?……他沉默的努力,永不放棄那英雄主義者的雄強自信,他看準了時代的變,知道這變中怎么樣可以把自己放在時代前面,他就這樣做。……在藝術上的估價,郭沫若小說并不比目下許多年青人小說更完全更好。”郭沫若“不會節制”文字,結果不免“多廢話”;不注意“觀察”,“他詳細的寫,卻不正確的寫”——而“創造社對于文字的缺乏理解是普遍的一種事。”
文章結束說:“讓我們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詩人上,煽動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與同情。小說方面他應當放棄了他那地位,因為那不是他發展天才的處所。一株棕樹是不會在寒帶地方發育長大的。”
一九三一年,沈從文的文學批評繼以新詩論《論朱湘的詩》《論劉半農〈揚鞭集〉》等,除此之外,更有長篇文章《論中國創作小說》,以近兩萬字的篇幅,敘論五四以來小說創作的發展和變化,涉及作家作品數量廣泛,評述真率扼要,以自覺的文學史意識,梳理出一份個人見解鮮明的新文學小說創作簡史。這篇長文,無論從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角度,還是從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史的角度,都有值得重新認識的價值。
張新穎 復旦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