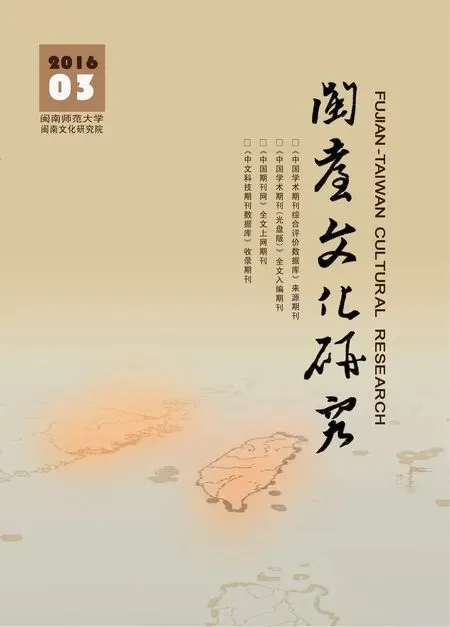淺論林語堂的復輔音聲母研究
董國華 郭偉宸
(閩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福建 漳州 363000;福建師范大學 文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淺論林語堂的復輔音聲母研究
董國華 郭偉宸
(閩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福建 漳州 363000;福建師范大學 文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本文針對林語堂上古聲母研究的論文《古有復輔音說》進行述評,主要分三個方面:(一)對20世紀前期興起的關于上古漢語復輔音聲母的爭論做簡要的概述;(二)介紹林語堂在國內首先提出的上古復輔音聲母的研究材料方法,肯定其對上古復聲母研究做出的貢獻;(三)林語堂在《古有復輔音說》中主要通過諧聲痕跡、聯綿詞來源兩方面對古有復輔音進行論證。
林語堂;音韻學;上古音研究;復輔音聲母
引言
以作家和翻譯家聞名于世的語言學博士林語堂先生,在漢語音韻學的研究領域也頗有建樹。他曾在德國萊比錫大學接受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學術訓練,并于1923年取得了博士學位。歸國之后,他將西方的語言學理論與中國的傳統音韻學結合起來,陸續發表了一系列音韻研究的論文,主要涉及四個方面:(1)上古韻部音值的構擬,如《讀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讀考>書后》《再論歌戈魚虞模古讀》《支脂之三部古讀考》;(2)上古聲母問題的討論,如《古有復輔音說》《古音中已遺失的聲母》;(3)上古方音音轉的討論,如《陳宋楚淮歌寒對轉考》《燕齊魯衛陽聲轉變考》《周禮方音考》;(4)漢代方言的區域劃分,如《漢代方音考一》《西漢方言區域考》。在上古韻部音值構擬、上古聲母問題、上古方音音轉以及上古方言區域劃分等幾個主要問題上,林語堂為漢語音韻學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做出了較大的貢獻。本文重點介紹和評價他關于上古復輔音聲母的研究。
一、20世紀前期古有復聲母說所引發的爭論
在上世紀20年代以前,上古漢語的研究是從《切韻》時期的中古音系為出發點,結合韻文、異文、諧聲、聲訓等材料來上推古漢語的“文獻語音”面貌。清代學者在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過相比顧炎武、江永、段玉裁、戴震、王念孫、孔廣森、江有誥乃至晚近的章太炎黃侃這一不間斷的學術梯隊在古韻研究上取得的皇皇碩果,上古聲母的研究則略顯單薄。誠如王國維的評價:“乃近世言古韻者有十數家,而言古字母者,除嘉定錢氏論古無輕唇舌上二音,番禺陳氏考定廣韻四十字母,此外無聞焉。”[1]古韻研究運用離析《廣韻》來系聯《詩經》韻腳、其他韻文入韻字及充分結合諧聲材料,對中古韻類不斷進行重新整合的方法取得了成功,古韻分部也由此愈演愈密,與此不同的是,上古聲母的研究整體上來看主要限于對中古聲母的歸并,并佐以一些古聲通轉的說明,從諧聲系統入手對上古聲母的探索還未完全展開。自錢大昕歸并古聲紐、江永的“古聲混轉”說及戴震的“古聲流轉”觀,晚近學者章炳麟的二十一紐“古雙聲流轉”說、黃侃的十九紐“古本音”說,乃至曾運乾于二十世紀20年代提出的“喻三歸匣”、“喻四歸定”說,上古單聲母的研究完成了文獻古音學所能達到的高度。
傳統音韻學研究所據材料總體上具有模糊性,這種材料的先天不足制約了文獻古音研究的精確度,研究的模糊性必然著結論的或然性,[2]尤其是在上古聲母研究中這種材料的缺陷較之古韻研究表現得更為明顯。歷來持單聲母觀的學者對不同聲母諧聲都歸以“通轉”來解釋,嚴學窘對舊學的通轉說描述如此:“通轉條例嚴格的,忽視例外,閉口不談異常諧聲現象,條例寬泛的,則不同聲紐之間幾近于無所不通,無所不轉”[3],陳獨秀一陣見血地批評通轉說:“唇喉可通轉,唇舌又可通轉,一若殷周造字之時,中國人之語音唇舌猶不分明,但嗡嗡汪汪之如蚊蠅犬豕之發音然。”[4]充滿主觀性的單聲母諧聲原則與漢字“六書”中“諧聲”、“假借”的音近機制的矛盾將清代學者所建立的漸趨精致的文獻古音學研究范式與紛繁復雜的漢語諧聲系統置于無可避免的沖突之中,以歸并聲母為主的古聲單聲母研究的范式危機隨之產生。直到西方歷史比較語言學進入中國以后,以一種新的假設——古有復輔音說的提出為契機,上古聲母的研究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局面。
最早提出上古漢語古有復輔音聲母的是英國傳教士艾約瑟 (J.Edkins,1823~1905),他在1874年第二屆遠東會議上提交的論文中根據諧聲材料提出上古漢語可能存在輔音p、t、k與l構成復聲母的假說,可惜的是艾約瑟的觀點在當時并沒有引起學界的重視。[5]
瑞典漢學家高本漢受艾約瑟啟發,在1923年發表的 《中日漢字分析字典》(Analyt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一書中指出有些主諧字與被諧字有復輔音聲母的關系,如“各”k-:“路”l-、“支”t-:“技”g-,這些諧聲是古漢語復聲母遺留的痕跡,隨后他在1933年出版的著作《漢語詞類》(Word Families in Chinese)中談論諧聲字中往往出現k-:l-和p-:l-的關系時,以k、l二母的諧聲關系為例提出三種復輔音聲母的可能性:
A. 各klak:洛lak
B. 各kak:洛klak
C. 各klak:洛glak
后來高本漢在他的《中日漢字形聲論》選擇了C式。[6]
中國國內首先倡導古有復輔音說的是林語堂。1924年他在《晨報》六周年紀念增刊上發表《古有復輔音說》舉例說明上古可能存在kl-(gl-)、pl-(bl-)、tl-(dl-)三種形式的復輔音聲母,并且提出研究復輔音的四條途徑:(1)古今俗語之憑證;(2)讀音及異文的憑證;(3)文字諧聲的憑證;(4)由印度支那系中語言作比較,證實中原音聲也有復輔音的材料。
潘尊行受林語堂啟發,于1929年《新月》第二卷第二期上發表《由反切推求史前中國語》一文,文章利用反切的歷史演變求證古有復輔音,并認為聯綿字的形成與復輔音有關。
吳其昌于1932年1月在《清華學報》七卷一期上發表《來紐明紐古復輔音通轉考》,從形聲、聲訓、方言、又音等方面來論證他“古時來紐明紐之為一音,通轉無別……此二紐之在古時為復輔音”的觀點,不足的是他引用的一些他以為是聯綿字的材料實際上是復合詞,并且他對所引材料并沒有絲毫音理上的分析。
1937年陳獨秀《中國古代有復聲母說》一文發表在《東方雜志》第34卷,文中援引古今中外的語言材料,以諧聲、聯綿詞、又音、方言等為依據結合與其他語言的比較,提出“古音不獨有復聲母gl、dl、bl,似復有mbl”的三合輔音聲母的假設,補足了高本漢與林語堂在證明古有復輔音所用材料上的補足。
1944年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探討了高本漢的“復輔音三式”最后認為A式是“可以無往而不利的”。除了帶l的復輔音聲母和上節我們提到過董同龢設想的喻四復輔音gd-、gz-的存在以外,他還指出有k-系與t-系、p-系、ts-系字相諧,t-系與p-系、ts-系字相諧等等復雜的諧聲關系存在,但又認為如欲對這些諧聲構擬復輔音聲母“決定他們的型式與出現的范圍在目前又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
陸志韋在其1947年出版的《古音略說》中的一篇文章《上古聲母的幾個特殊問題》里列舉了大量材料來證明《廣韻》中鼻音能與同部位或是鄰近部位的塞音和塞擦音相轉,以此構擬了明母mb-、mp-,泥母nt-、nd-,疑母k-、g-的復輔音形式。除此以外,他還認為《切韻》“力盧”跟其他它中古聲類之間存在較為普遍的通轉,討論了高本漢復輔音假設C式的可能,并在與暹羅語對比之上提出了上古漢語還有tl、l、sl等復輔音的假設。
上古漢語存在復輔音聲母的假設逐步引起國內外學者重視的同時,也出現了對之抱有質疑觀點的學說出現。唐蘭就是反對古有復輔音說的代表,1937年他在《清華學報》發表《論古無復輔聲母凡來母字古讀如泥母》逐一批評了林語堂關于古有復輔音聲母的假設和考證的方法,他以現代漢語方言全無復輔音、域外音對比也屬單文孤證、漢字的諧聲系統十分復雜p、t、k、l并見雜出規律難尋為由,認為林語堂所提出的方法不能證明上古漢語有復輔音。
綜合以上對20世紀上半期上古漢語復輔音聲母研究成果的回顧,可以看出上古復輔音聲母研究在當時尚處于假說提出的初步探索階段,親屬語言同源詞的比較這一極重要的途徑雖然已經林語堂提出但還未真正展開,所以我們不能指望這個時期的研究工作可以得出一個合理的且具有解釋力的復輔音聲母系統。正是因為新的學術范式尚未建立,所以對一些否定意見所提出的問題也未能很好地解決。王力先生也認為“從諧聲系統看,似乎有復輔音”,但他批判高本漢構擬復輔音的原則道:“其實依照高本漢的原則去發現上古復輔音聲母,遠遠不止十九種……上古的聲母系統,能這樣雜亂無章嗎?我不能接受高本漢上古復輔音的擬測。”[7]王力先生對當時究尚未成熟的古聲母復輔音研究所采取的保留意見也可以代表范式更替下學界對復輔音聲母說這一新觀點的存疑。
到今天為止,學界于復輔音研究已經取得了相當顯著的成果,在此不加敷述,我們很有把握相信可以根據諧聲、通假等傳統的文字、文獻材料加以利用漢藏語系其他親屬語言的同源比較這二重證據來驗證上古漢語確實存在復輔音聲母,而且這個復輔音聲母系統不是毫無秩序可言的。我們認為20時期上半期提出的復輔音假說來進一步解釋上古漢字諧聲系統及其他一些問題的方向是正確的。
二、林語堂的古有復輔音說
1.上古復輔音聲母研究方法的提出
今天的漢語各方言是沒有保留復輔音的,[8]在西方語言及西方語言學理論未進入中國之前恐怕沒有人會去思考漢語是否曾經存在過復輔音聲母。在高本漢對上古漢語存在復輔音聲母的假設提出沒多久,林語堂就在《晨報》六周年紀念增刊上發表《古有復輔音說》一文,在國內引發巨大反響。嚴學窘在回顧那一段歷史時說道:“高林二位,互不相謀,同時發難,石破驚天,引起中國學術界的廣泛注意,或闡揚其是,或指斥其非,凡討論漢語上古聲母問題的,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態度,不能不發表自己的意見。”[9]
林語堂在文中指出由于漢字表音的模糊性使然“所以就使古時果有復輔音,也必不易直接由字形上看出來”,即使漢語曾經有過一番巨大的變化古人也不可能知道,對此他強調:“我們切不可因為‘看他不著’便以為‘沒有這回事’,因為‘不見’便以為‘無有’。”對于如何考察上古是否有無復輔音,林語堂提出了四條途徑:
(1)尋求今日俗語中所保存復輔音的遺跡,或尋求書中所載古時俗語之遺跡;
(2)由字之讀音或借用上推測;
(3)由字之諧聲現象研究,如p、t、k母與l母的字互相得聲;
(4)由“印度支那”系(按:所指即今日所謂漢藏語系)中的語言做比較的功夫,求能證實中原聲音也有復輔音的材料。[10]
何九盈對此評價道:“林氏列舉的四條途徑,的確是研究復輔音的正路。”[11]今日上古漢語復輔音聲母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基本上是建立在這四個方法和相關的材料基礎上的。楊劍橋總結當代學界關于上古漢語復輔音聲母的研究,認為今天我們考察上古復輔音聲母主要以十二種材料為證據:(1)諧聲字;(2)聲訓;(3)讀若;(4)反切;(5)重文;(6)異讀;(7)音注;(8)異文;(9)方言;(10)聯綿詞;(11)古文字;(12)親屬語言。[12]我們可以看出這十二種證據實際上都是對林語堂四條途徑所提議之方法的進一步深入和擴展。上個世紀20年代上古漢語有復輔音聲母假說剛剛在學界中提出的同時,林語堂就以敏感的學術眼光指出考察復輔音聲母的四條途徑,這不能不說是林語堂作為一名優秀語言學者的先見。
2.對古有復輔音聲母假設的論證
(1)諧聲字的復輔音痕跡
古有復輔音聲母說是隨著單聲母的古音體系解決諧聲問題遇阻而生,林語堂在國內首先提出復輔音說自然也不例外。林氏認為諧聲系統“表面上的雜亂無章,若加以仔細考查,都能呈出有條理的現象”且“表面上愈雜亂,愈不規則,愈是我們尋找古音的好機會”,[13]他同之前艾約瑟、高本漢一樣,認為是來母與P、T、K三系聲母的諧聲是切入上古復輔音聲母研究的關鍵:
以“果”聲(k母)諧“裸”(l母)參考“菓”。
以“各”聲(k母)諧“路”、“洛”、“略”、“賂”……(l母)參考“客”、“格”。
以“柬”聲(k母)諧“蘭”、“瀾”參考“諫”。
以“僉”聲(k母)諧“殮”、“斂”“臉”參考“檢”、“儉”。
以“兼”聲(k母)諧“廉”字。
以“監”聲(k母)諧“籃”、“濫”(l母)參考“钅監”(“鑒”同)“覽”。
以“降”聲(k母)諧“隆”(l母)。
以“京”聲(k母)諧“涼”、“諒”(“亮”同)(l母)參考“景”。
以“鬲”聲(l母)諧“隔”、“膈”。
以“稟”聲(p母)諧“懍”、“廩”(l母)。
以“睦”字(m母)與“陸”字(l母)為同諧聲字。
以“繆”字(m母)與“戮”、“廖”、“寥”(l母)為同諧聲字。(注:按:睦、繆二字應為明母)
以“童”聲(t母)諧“龍”字(l母)參考“竉”字。[14]
林語堂列舉的這些諧聲字組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雖然數量上不多,但足以能表現P、T、K三系聲母都有與來母諧聲的傾向說明上古可能存在pl-、tl-、kl-這樣的復輔音聲母。但林語堂似乎還沒有把這些諧聲字組的眼光放得足夠開,否則他還應得到以下的諧聲現象:
睦(明):逵(群):陸(來)
繆(明):膠(見):瘳(徹):戮廖寥(來)
數(生)藪(心):屨(見):婁簍屢摟縷(來)
孿(生):彎(影):蠻(明):變(幫):戀孌巒欒鑾(來)
龐(並):寵(徹):龔(見):龍(來)
當然,如果要對這樣復雜的諧聲進行說明的話,則不是簡單地依靠漢字諧聲系統的內部構擬出pl-、tl-、kl-等雙合復輔音可以說明的。如“龐(並):寵(徹):龔(見):龍(來)”這一含有P、T、K、L四系聲母的諧聲字組,若擬“龐”*bl-、“寵”‘l-、“龔”kl-、“龍”l-,看似簡單清楚,但是這樣的構擬方法怎么決定l-出現的環境是一個棘手的問題,非得通過系聯所有與來母諧聲的漢字并為它們逐一夠擬為帶-l的復輔音聲母,而且這種看似沒有嚴格規律的復聲母系統缺乏上推下演的解釋力。
今天的上古音系研究相對上個世紀20年代剛提出復輔音說的幼稚時期已經成熟不少,以鄭張尚芳的研究為例我們來試看這個諧聲字組的復輔音聲母如何構擬。鄭張尚芳將上古並母構擬為*b-,來母*r-,見母*k-,以母*l-,知組一部分字來自帶前冠r-的音節,又強制中古二等和重紐三等字在上古都帶有墊音-r(注:王力曾為二等韻構擬-o-、-e-介音,以說明中古“等”的來源,鄭張-潘系擬音認為墊音-r-不僅導致中古一、二等元音不同且能解釋重紐三等韻在方言中的演變,能以復輔音解釋諧聲現象),其他等字視與來、以通諧與否決定是否帶墊音-l,據此他對這組諧聲字的擬音為“龐”*broo、“寵”*rho、“龔”*klo、“龍”*ro,因為諧聲聲符未必盡諧所有音素,尤其有的以Cr、Cl為聲基的詞根本身就帶有流音墊音,就可以通過流音諧聲,所以這些字都能以“龍”*ro為聲符,又根據藏文“龍”brug還可以為“龍”擬出一個原始漢語形式*hbro。[15]這樣的上古音系統能涵蓋諸多音韻學本身既存的問題,又能與親屬語言比較向上構擬語言的原始形式,相對來說比較具有條理性和說服力。復輔音聲母的系統性與解釋力不是上世紀20年代復輔音說剛提出時就能解決的問題,今天所取得的成績是奠定在一代代學者努力所得成果的基礎上取得的,并且許多已經提出的觀點仍有待檢驗,還有許多未能解釋的問題等待著我們解決。
(2)聯綿詞的復輔音來源
林語堂認為有許多“俗語”我們仍可以聞于今日方言口語之中的如“孔為窟窿”,見于古代文獻之上的如“螳曰突郎”、“團曰突欒”、“不來為貍”、“不律謂之筆”,這些“俗語”都是“極明顯復輔音的證據”,且這些古代復輔音聲母的痕跡都是以聯綿詞的形式存在。之前對這類非擬聲、疊音的聯綿詞在語音上的理解基本上認為是單音詞的衍音、緩讀或認為是反切的雛形,[16]林語堂嘗試從復輔音的角度對這些聯綿詞的產生進行與其他人不同的解讀,他不僅認為如“窟窿”、“突郎”、“突欒”、“不來”這類詞反映了原來應有“孔”klung、“螳”tlang、“團”tluan、“貍”blai這樣的音節的存在,而且他還提出這類聯綿詞是后來產生的一些疊韻詞的來源:
孔——窟窿——孔竉
團——突欒——團圞
頂——滴寗頁——頂寗頁
螳——突郎——螳螂
其中如“孔”字或經歷了以下的歷史音變:
孔——窟窿——孔竉
klung>k‘u lung>k‘ung lung[17]
林語堂認為從“孔”到“窟窿”的演變說明了聲母復輔音處于開始分立的時期,當復輔音kl-開始向k-l-“歧分”時,k與l中間增聲了一個元音u,而這個衍生出來的音節k‘u又容易受后一個音節的影響從而使k-音節所增生出來音節的韻母被原本l-后就帶有的韻母所同化,“韻變”形成疊韻聯綿詞的形式kung lung。林氏還指出這樣的“韻變”是漢語中常見的音變構詞形式,如“孿生”變讀為“孿宣”見《方言》卷三:“陳楚之間凡人獸乳而雙產謂之釐孿……趙魏之間謂之孿生。”郭璞注:“蘇官反”;“堀坎”變讀為“坅坎”見《儀禮·既夕禮》“堀坎”下注:“今文堀為坅”;廈門話“龍眼”讀作geng-geng音變軌跡為:liong-gan>leng-gan>leng-geng>geng-geng。[18]因此,林語堂確信一部分存于方言或古籍中的包括疊韻詞在內的聯綿詞,是上古有復輔音聲母在歷史音變后留下的痕跡,從這個觀點他假設上古復輔音肯能存在的形式:
kl-(gl-)式例
孔:窟窿 角:矻落 圈:窟欒 云:屈林
錮:錮钅路 窟礧:傀儡
pl-(bl-)式例
筆:不律 貍:不來 風:孛纜 蒲:勃盧
蓬:勃龍 槃:勃闌 旁:步郎
tl-(dl-)式例
團:突欒 螳:突郎 頂:滴寗頁 鐸:突落
禿:禿驢[19]
我們可以看出,實際上林語堂提出聯綿詞的復輔音來源觀與歷來的“衍音”、“緩讀”并沒有形式上的沖突,只不過“衍音”和“緩讀”是在單聲母音系下對聯綿詞現象的一種淺層面的解讀,而復輔音來源觀是對復輔音分立后產生一部分聯綿詞的構詞形式的溯源。但是這里碰到了兩個無法回避的問題:
第一,林語堂自己還說:“疊韻字的發生歷史,不必盡與復輔音字有關系。倘是沒有明白復輔音的證據,我們不能單靠疊韻證明該語之原有復輔音。”[20]這是林氏提出利用聯綿字考察上古復輔音的同時自己也已經看到的運用此方法則必然面對的困難——如何界定來源自復輔音聲母的聯綿詞。既然聯綿詞作為孤證不足以證明古有復輔音,如此一來甚至還會引起本末倒置的現象,本是用來證明古有復輔音的證據反倒成了需要解釋的對象,也就是說若要確認某一條聯綿詞是上古復輔音遺留的痕跡首先需要證明這條聯綿詞對應的字為復輔音再解釋它向聯綿詞的演變。
第二,林語堂沒有明確的證據證明“窟隆”、“突欒”的形式早于“孔竉”、“團圞”,他說:“如《宋景文》所記等成語之第一字皆入聲字,且發音極速,與tl、kl、pl之p、t、k發音最近,此等‘窟隆’、‘突欒’之字或為‘孔竉’、‘團圞’之所出。”[21]雖然于音理上來說似乎很有道理,但他無法說明孰先孰后,既然他意識到了“我們是找不出來‘螳螂’比‘突郎’近古的憑據”那么他也應該在提出這個觀點之前給出“突郎”的形式比“螳螂”更早的證據。對此杜其容道:“林氏文中所舉諸例都未必可靠,因為證據實在太過孤單,以孤證而欲成定論,至為危險。”這一批評是十分中肯的。
盡管林語堂提出部分聯綿詞有復輔音來源的觀點證據不夠充足,但后來的關于漢語聯綿詞族義根及漢藏同源比較的研究就從他的這個新的觀點中獲得了很大的啟發。聯綿詞族的根詞自于語根,根詞的意義不斷發生引申使得新詞一批一批地孳乳而生,義根所包含的特征成了新詞孳生的理據,這些從這些音義密切相關的新詞就形成了聯綿詞族。[22]郭小武提出聯綿詞族有共同的上級意義領域,而承擔詞族義的是聯綿詞前后兩個音節的聲母,[23]根據近來興起的以聯綿詞與親屬語同源詞的比較研究成果,根據邢公畹、張世祿、楊劍橋、嚴學窘、尉遲治平、董為光、白一平諸家成果的來看,一部分聯綿詞的確很有可能來自上古的復輔音聲母且能與親屬語言對應。[24]
注釋:
[1]王國維:《觀堂別集·后篇》,《王國維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7頁。
[2]李葆嘉:《清代古聲紐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98頁。
[3]嚴學窘:《古漢語復聲母論文集·序》,竺家寧編《古漢語復聲母論文集》,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頁。
[4]陳獨秀:《中國古代語音有復聲母說》,《東方雜志》第34卷第20~21號,1937年。
[5]竺家寧:《上古漢語復聲母研究的幾個問題》,龍莊偉、曹廣順、張玉來主編:《漢語的歷史探討 慶祝楊耐思先生八十壽誕學術論文集》,北京市:中華書局,2011年,第33頁。
[6]何九盈:《中國現代語言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291頁。
[7]王力:《漢語語音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 第17~19頁。
[8]但一些方言中或存有復輔音之遺跡。趙秉璇《漢語瑤語復輔音同源例證》(《晉中教育學院學報》1989年第2期)比較了“嵌l詞”p-l-、k-l-與瑤語對應的復輔音詞,陳潔雯《上古復聲母:粵方言一個半音節的字所提供的佐證》(《方言》1984年第4期)提出粵語中“胳”k l k、“筆”p l t等字例。
[9]嚴學窘:《古漢語復聲母論文集·序》,竺家寧編《古漢語復聲母論文集》,第5頁。
[10][13][14][17][18][19][20][21]林語堂:《古有輔者說》,《晨報》六周年紀念增刊,1924年。
[11]何九盈:《中國現代語言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292頁。
[12]楊劍橋:《現代漢語音韻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19~124頁。
[13]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1頁。
[14]衍音:章炳麟《新方言·釋器》:“說文,空,竅也,堀,兔堀也,引申凡空竅曰堀,字亦作窟,今人謂地有空竅為窟籠,籠者收聲也,或曰,窟籠合音為空。”黃侃《聲韻說略》中也說過:“瓜之音衍長之,則曰瓜蓏。”沈兼士《國語問題之歷史的研究》認為“原來言語中的單音詞,其后漸因便利起見,多半變為疊韻或雙聲的復音詞了(其中有另外加添語尾的),但是后來附加上的音,只是借一個字來表示他,卻沒有另外造字。”緩讀:宋鄭樵《通志·六書略·諧聲變化論》:“急慢聲諧,慢聲為二,急聲為一也,梵書謂二合音是也。如慢聲為‘者焉’,急聲為‘旃’。”宋洪邁《容齋隨筆·切腳語》也說:“世人語音,有以切腳而稱者,亦間見之于書史中。如以逢為勃籠,槃為勃闌,鐸為突落,叵為不可,團為突欒,鉦為丁寧,頂為滴寧,角為矻落,蒲為勃蘆,精為即零,螳為突郎,諸為之乎,旁為步廊,茨為蒺藜,圈為屈孿,錮為骨露,窠為窟駝是也。”
[22]徐振邦:《聯綿詞概論》,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191頁。
[23]郭小武:《試論疊韻連綿字的統諧規律》,《中國語文》1993年第3期。
[24]參考徐振邦:《聯綿詞概論》中對學界成果的概述。
〔責任編輯 吳文文〕
LinYutang’s Research of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Dong Guohua Guo Weichen
This paper aims at the research of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of Lin Yutang’s dissertation:Consonant Clusters Existing in the Ancient Phonetic System,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aspects:(a)a brief summary of the debate of ancient Chinese initial consonant which started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b)the introduction to research materials and methods first proposed by Lin Yutang in the domestic and his academic contribution in the field;(c)the demonstr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consonant clusters in the ancient phonetic system through the traces of pictophonetic characters and the origination of two-syllable terms.
Lin Yutang,phonology,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initial consonant cluster
董國華(1982~ ),男,河南汝州人,文學博士,閩南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郭偉宸(1987~ ),男,福建三明人,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字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