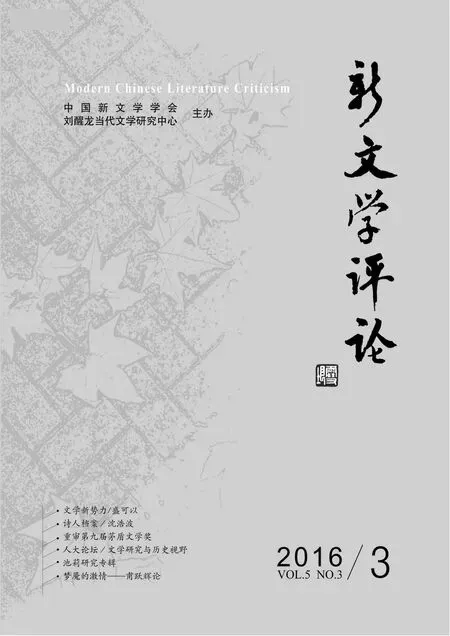兩種城市,兩類女人
——池莉新世紀小說初探
◆ 高國麗
?
兩種城市,兩類女人
——池莉新世紀小說初探
◆ 高國麗
池莉從1981年開始發表小說,至今已歷35年而創作頗豐,其中經歷了數次轉變,變中有常,常中有變,逐漸形成了老練獨到的個人風格。池莉一直以市民立場關注凡俗人生,她認同的“俗”不是惡俗,而是她多次解釋的“有人有谷子”①,是真實的現實。80年代初期以《月兒好》為代表的系列作品雖粗疏稚嫩,且有模仿“文革”結束后復蘇的主流人性論敘述的痕跡,但透著悠揚的靈氣和詩意;自1987年《煩惱人生》以來,池莉開始用“新孩子”的“新眼睛”觀察市民“神圣的煩惱人生”②,開鑿市民庸常生活的“詩意”,與欲告別理想主義的社會轉變不謀而合,很快在文壇引起轟動;90年代的中國社會隨改革開放的深入發生了劇烈變動,《來來往往》、《小姐你早》、《口紅》等都市言情小說偏于傳奇性,“在升騰和墜落之間”③演繹人生起伏;從《烏鴉之歌》、《水與火的纏綿》、《懷念聲名狼藉的日子》到《所以》,池莉頻繁地書寫女性在家庭和歷史中的命運或情感婚姻狀況,似乎自覺地開始為她們這一代“新孩子”的生命經歷命名。對于世俗生活,池莉不像之前那樣單純地表示認同,而開始透露出些許批判意味,并重新對她曾經“撕裂”的理想主義抱有一些期許。當然,35年來池莉創作的豐富性不能簡單地用這幾條線索涵蓋,其中一以貫之的是她對市民生活的極大熱情,和對武漢這座城市的持續關注。
漢味浸透的城市(武漢)一直是池莉寫作的土壤。到了新世紀,池莉開始表現城市的歷史和記憶的印記,側重于書寫家族歷史中女性命運在城市中的變遷。細想來,池莉筆下的城市分裂成兩種,或者說長著新/舊兩張面孔:一個是現代化的都市性武漢,另一個是頗有鄉土味的城鎮性武漢。
當代中國關于城市形態的想象總體來講分為兩種:以上海為代表的現代摩登都市和以北京為代表的文化性鄉土中國。趙園把北京的特點描述為“田園式的城市”,“是鄉村的延伸,是鄉村集鎮的擴大”,雖然“與鄉村生活結構功能不同,也同屬于鄉土中國”④,這是跟現代化的大都市對立的、有深厚文化積淀的一種城市形態。而陳思和以張愛玲的上海書寫為例,把區別于“頹敗”、“浮紈”的摩登都市的城市形態描述為“都市民間”,一種從底層發生的、與國家權利對抗的民間文化形態⑤。池莉在《生活秀》(2000)和《她的城》(2011)中描述的老城空間介于趙園和陳思和的描述之間,它不同于“田園式的城市”,也不以對抗性為特征,這些城鎮性武漢曾有過輝煌的歷史,到現在還是破舊的充滿商業氣息的小商品市場,堅韌而頑強,卻在歷史變遷中被擠兌到城市褶皺里,是一個保存了鄉土味的邊緣存在,由商販小攤、老房子、里分古巷、街坊鄰里等構成。它曾是最早開始商業化和城鎮化的地方,卻在現代化進程中停滯了,被甩在了城市的尾巴上,但這里又滋生了最原始最樸素的市民倫理。這是一個共時的、靜止的城;而《水與火的纏綿》(2002)和《所以》(2007)描繪的新城雖現代卻不很摩登,是一般意義上的都市,由工廠、單位、公路、咖啡館、公園、寫字樓、公共汽車等風景構成,是歷時的、線性的、流動的、承載著社會和歷史變遷的現代化空間。
池莉的兩座城市對應著兩種女人:老城里典型的市民階級女性和新城里的都市中產知識女性,她們與自己的城市分別形成一種對應和象征的關系。這兩種城市空間和兩種女人的背后是兩種生活邏輯的對立,老城代表的是以幾代居民知根知底的信任為紐帶的街坊倫理,新城背后是洪水猛獸般發展主義的現代的邏輯;同時,在文本的構造中,池莉明顯地把情感認同投向了行將消失卻依然頑強的老城,通過讓新城里的女人在老城里找到情感依托這一象征性表達,把老城塑造為具有治愈性的“藏污納垢”的烏托邦。
一、兩種城市空間和兩類女人
老漢口本在民國時期就是武漢城市的起源地,在改革開放的小商品潮中重新蘇醒,新武漢是八九十年代都市化進程的產物,這兩種城處于一個并置的空間,卻不是同一個武漢。一個是靜止的精確的,一個是流動的模糊的,這兩種城中住著兩種女人,她們和兩種城市之間形成了一種參差的律動。
1.兩種城市
書寫這兩種城市空間,池莉用兩種感知時間的方式來傳達兩種空間的特征和區別。正像《生活秀》中來雙揚的生活方式,“白天要睡覺,晚上做生意”,一天從下午三點開始,吉慶街的沸騰從晚上開始,城市的每天是有規律的,重復的。《她的城》對老武漢的城市節奏表現得更明確:老武漢以早上/中午/晚上為感知時間的單位,每天像是同一天,只有流逝和重復,卻沒有真正的變遷。“這個城市沒有早晨,一切從中午開始。”十二點過后,城市開始興奮,然后蜜姐坐在店里,招呼著來來往往的客人,直到晚上八點打烊。以蜜姐擦鞋店為代表的老城在時間上只有早上、中午、晚上,“天天復天天,年年復年年”,這是抽空了時間的舊城,這里的時間只是輪回。同時,老城的空間也是定格的,水塔街的聯保里是武漢最典型的里分,吉慶街是武漢最古老的街之一。這里的房子是建國以前就修筑的,時間讓它們陳舊,卻沒有產生空間位置的變化,它們依然是穩定的,這樣一種穩定的時間和空間在心理上給人一種安全的依托。
不同于老城用早上/中午/晚上來感知時間,新城總是用季節的輪回來推進時間和敘述:“秋天的長江”、“轉眼就是深秋了”、“寒冬到了”、“這是一個瘋狂的春天”、“春天又來了”、“這又是一個不正常的春天”,不斷地指明情節發展的季節,或者用季節來帶動情節發展。從春到冬,武漢四季很分明。季節的交替便是武漢這座城市獨特的時間語言。武漢地形特殊,造成“冬抱冰夏握火”的氣候特點,《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就開始通過季節感受描述武漢的市民日常。正是這種明顯的季節感受無意中開啟了池莉以溫度/季節感受時間流逝的寫作方法。季節的輪回在流動中伴隨的是城市的歷史變化,同時,季節的交替不是圓形的從春到夏的輪回,而是線性的往前推進,這個過程和歷史的發展是同步的。這樣一種時間帶來的是流動感和對變化變遷的惶惑感。“無根的、被不斷的擴張、重建與流動所構造著的都市,似乎以某種內在的想象性應和、撫慰著一個孤獨的‘新孩子’。”⑥《水與火的纏綿》中存在著一種復雜的象征性書寫。季節的春夏和秋冬,城市的復蘇發展和矛盾焦慮,火與水之間分別存有一種模糊的對應關系。池莉以季節的輪換推動歷史的變遷,在騷動的春天,吹來了改革開放的春風,對應的事件是燕子、鄺園、肖克等人去了廣州和深圳,新的時代來臨,芒芒進入“熱戀期”,芒芒和高勇領取結婚證。而發生在秋冬時節的是:高勇的出現、二人相處出現問題、搞砸的生日、愛情幻想破滅、婚禮(魔咒)等。時間的順序和發展的順序以及故事情節的發展的一致性透露出一種發展的邏輯和秩序。
除了敘述時間帶來的靜止/流動的差異體驗,兩種城市還有精確/模糊的空間感受。亨利·詹姆斯的學生珀西·盧伯克在《小說技巧》中討論過小說的“畫面”和“戲劇性場面”的關系。盧伯克認為小說呈現給讀者看的是輪番出現的畫面和戲劇性場面,畫面是敘述者在場描繪的,介入性強,而戲劇性場景是在聚焦燈下主人公自己表演的,敘述者隱退了⑦。老城的畫面感很強,用大量細節和耐心的敘述打造了一種毛茸茸的精確質感,在敘述精彩的地方敘述人引退,人物和場景開始自己表演。呈現的是一種定格的抒情性的畫面感,感覺大于故事,我們腦中總有一幅畫面:蜜姐坐在聯保里的擦鞋店柜臺前,一口一口漫長地抽煙,打量著來往的人和不變的城,頗有抒情意味。而到了都市之城中,大量的“一筆帶過性”的描述代替了“戲劇性場面”的呈現。池莉放棄了精致的描寫,取而代之的是探討兩性關系的自白性的分析和議論,常常用概述性的語言掃過流逝的時間,很多故事在場面和跨度上沒有展開,具體的描寫和玩味少了,跟老城的描寫相比,美感上顯得不足。這不僅是因為后者處理的時間跨度比較長,因而不太需要聚焦在某一個場景中,更是為了傳遞現代都市的模糊感,而不是老城的精確感。比較這兩種描寫方式,老城作為一個可能要消失,并且不會再生的空間,在敘述中被池莉帶上了懷舊的意味。對她的注視和把玩有種把城市他者化的視角,把她當成了欲望的對象,所以要用傾注抒情性的畫面感來呈現。池莉常常認同市民的價值取向,因此對這一古舊的商業化城市空間自然而然地傾注了一種審美關照。
2.兩類女人
這兩種城中住著兩類女人,一種是曾芒芒、葉紫代表的城市中產階級知識女性,另一種是來雙揚、蜜姐代表的典型的城市市民女性。對于世紀之交女作家筆下用女性寫城市的一批作品,賀桂梅將其指認為世紀之交懷舊視野中城市和女性的同構性書寫,城市往往長著一張女性的面孔,如鐵凝《永遠有多遠》中的白大省之于北京胡同,王安憶《妹頭》中的妹頭之于上海弄堂,池莉《生活秀》中的來雙揚之于武漢吉慶街⑧。其實來雙揚與吉慶街在某種程度上是《不談愛情》中“丈母娘”與“花樓街”的補充書寫,而這組形象在《她的城》中借蜜姐和水塔街聯保里進行進一步挖掘。如果來雙揚作為城市的“主體”代表著吉慶街,她和城市是同構的,那么吉慶街的形象就是這個既能干又被欲望化的女人形象,同樣,作為“人精”的蜜姐完全能勝任水塔街的代言人角色。可是到了現代之城,這里滲透著競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邏輯,如果去想象這樣一個城市的話,我們的腦海里可能會浮現一個健壯的、西裝革履的男性形象,他代表著一種前進的發展的面向,比如《生活秀》中的卓雄州或《她的城》中的駱良驥,正如他們的名字所揭露的:野心和前進。但我們看到池莉還是把主人公寫成了一類渺小的女性:《所以》中的主人公葉紫,就像“葉子”一樣渺小而沒有任何影響力,從小在家庭中不被重視,后來在三次婚姻中“拾取”了三次創傷和一次背叛。《水與火的纏綿》中的曾芒芒聽起來就是“真茫茫”(迷茫)。所以,曾芒芒和葉紫這類女人和城市的關系不同于蜜姐、來雙揚的主宰性,她們不僅不能對城市起到任何支配作用,反而被城市決定著。她們代表的就是人們對于現代這種城市邏輯的迷茫和無力感,在這樣一種迷茫、渺小、無力的情緒上,曾芒芒和城市形成了一種象征關系,她們總是不能駕馭生活和城市,她們和城市的同一性更像是在性格上。《她的城》用自戀的口吻將這個城市的特點描述為“敞——的”:“這就是武漢大城市氣派”,也就是推心置腹、毫無保留,這也是蜜姐的性格,而曾芒芒的城就像曾芒芒的性格一樣,像是“水與火的纏綿”,水與火即是季節的表征,也象征現代之城既“火”一般發展又“水”一般迷茫的狀態,就像既熱烈又寡淡的曾芒芒。
這兩類女性代表著城中女性的兩個階級,她們的差異本質上是價值觀、生活方式的對立。對于這兩種女人的解讀可以從池莉使用的對“手”的修辭來分析。《水與火的纏綿》關于城市和女人的想象落在曾芒芒的婚戀故事中。寫曾芒芒之所以選擇高勇,始于“這只俊美的手”:
一只手出現了。曾芒芒首先看見的是一只手。高勇的手。這只手伸到她的面前,遞給她一小塊面包……它是修長的,健壯的,優美的,它膚色潔凈,血管清晰,骨節有棱有角,他指甲橢圓又光滑,透出健康的粉紅色……她感覺自己的血液改變了方向和流速,都朝這只俊美的手匯聚。⑨
這雙手因其“坦白而豐富的表情”終于“說服”她選擇了他。有意思的是,這次曾芒芒作為一個女性,竟然對男性投去了“看”的目光(一般都是男看女,女“被看”),她用欲望的眼神注視著這雙手,一向比較“延宕”、缺少行動力的曾芒芒竟然在主動出擊。而相反的是,在老城中,女性的手作為一種客體被這樣注視著:
逢春在一旁已經把手套扯破了,脫下來了, 卷起來丟進了垃圾簍, 一雙年輕的手被悶得潮濕蒼白,青筋畢現,在她手背上畫了水墨一般, 卻也有一種惹人憐惜的好看。駱良驥一瞟一瞟的。⑩
“手”作為一種身體語言,承載著駱良驥“一瞟一瞟”的目光,池莉連來雙揚都不放過:“來雙揚就是一雙手特別突出”,“用她皎美的手指夾著一支緩緩燃燒的煙”,“卓雄州最初就是被來雙揚的手指吸引去的”。《所以》中也出現過葉紫為了“勾引”禹宏寬主動展示的手指。但蜜姐吸煙的兩手指是黃的,不再是被看的對象,因為其實在《她的城》中池莉對蜜姐的形象做了一些男性化的處理。
以上呈現的池莉關于城市空間中“手”的修辭意涵豐厚,“手”作為身體的一部分,是一個有吸引力的欲望對象,在兩種敘述城市的文本中對于“手”的不同呈現,背后蘊含的是兩種審美形態和婚戀標準。身為中產知識女性的曾芒芒,對愛情抱有一定的幻想,想尋找的是“橡樹和木棉”般平等的愛情:“作為樹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你有你的銅枝鐵干”,“我有我紅碩的花朵”。曾芒芒本來是一個看《約翰·克里斯朵夫》的有追求有幻想的女青年,但生活使她在城市中喪失了自信。相反,市民女性懷揣的是一種實用主義價值觀,這是一套“過日子”的生活倫理,所以她們理想的對象是有錢、懂得欣賞自己的美、體貼的成功男士,在這個意義上,她們本身把自己置于一個被看的位置上,她們要用自己的美貌去吸引理想的男性。知識女性保持的是一種天真的幻想,所以關于她們的故事結構只能是一個期待——失望——破滅的悲劇性書寫。而市民女性一開始就切實,安命,所以能處亂不驚,承受生活的一切不可承受之“輕”和“重”。這不僅代表兩種婚戀標準,更是兩套價值倫理和生活哲學。
3.兩種城市風景
這兩種城市空間擁有不同的城市風景。一種是固定的、陳舊的、有記憶的,另一種是行走的。老城的風景就是聯保里的一切:水塔、商鋪、里分、狹長的街巷、吊腳閣樓、小天井,尤其以巴掌大的蜜姐擦鞋店為核心。蜜姐擦鞋店位于最繁華的水塔街,但特別狹小,屋子一樓用蠟染的印花簾子隔開,里面供做飯和吃飯,外面當擦鞋店,二層是凌空搭起的一個吊腳樓,供婆婆居住。后門出來是長長的弄堂,聯保里臨街的房子“老朽破敗”,路面“到處開裂,污水橫流”。這個空間風景并不是一個詩意的完美存在,而是一個切切實實的藏污納垢的市民生活的空間,對空間的過度利用給人造成一種心理上的狹窄和局促。這種空間描寫傳達了老街的命運:一方面她粘著城市記憶,頑強地、穩定地屹立在那里,永不會消失,一方面她已經被現代都市擠兌到狹小的空間里,似乎越來越“窄小”。
而新城里的風景主要是行走的:公共汽車和輪渡。武漢是江城,形成了“一橋飛架南北,三鎮通達東西”的空間結構,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很多時候市民都要乘坐輪渡和公交車等公共運輸工具。而公共汽車、輪渡形成了武漢獨特的行走的城市風景,正切合了新城的流動性。池莉很注重以交通工具這種行走的風景來表現城市,《水與火的纏綿》中公交車、輪渡、飛機、火車等出現了數十次。曾芒芒生活中的大事都和公交車或輪渡有關:開始討論個人問題、遇見高勇、結婚遭劫、分娩。在這里它們也不只是運輸工具,以公交車為代表的運輸工具就像是“都會的血液”,促成了城市快捷的流動性。這一城市風景處在一個行走的過程中,公交車代表的是擁擠、快速的城市特點和節奏,車上的人不會關注窗外的風景,卻會關注車上的風景——陌生人。這是一個與陌生人交會的公共場所,其中大多數人是和自己相似的城市居民,也有一些施加性騷擾(破壞)的男人。這是一個可以公開觀察別人和反觀自己的場所,是城市縮微的一個斷面,為人物的獨白和思考提供了一個空間上的心理時間。池莉還特別描寫了一些潑辣豪爽的女售票員形象,潑辣豪放刻薄的女售票員和擁擠慌張的公交車形成一種對應關系。公共汽車、輪渡是連接家庭和單位的一個緩沖地帶,是一個人免于單位或婚姻家庭干擾的、可以獨立思考的空間段和時間段,是一個難得的城市“真空”狀態。這些公共空間往往以熱鬧的場面呈現這種都市生活的公共的一方面,人們既討厭公車的擁擠骯臟,又離不開它的廉價快捷。以公交車、輪渡等為載體的公共空間表征了城中女人的精神狀態,是都市女性心理的一面鏡子。在這個空間里雖然吵吵嚷嚷,但這種吵嚷只能加劇人與人之間的疏離,公交車和城里的人一樣準時準點地奔這奔那,支撐了城市的運轉和現代化。如果說來雙揚和蜜姐還能作為那個老城的主體性存在,融洽地代表那座城,那么曾芒芒和葉紫與城的關系,似乎有一種模糊的無力感,她們焦慮的精神狀態和城市的緊張和高速之間形成一種象征關系。
二、街坊倫理與現代邏輯的張力
這兩種城市空間塑造了兩類女性,兩類女性又反過來代表著兩種城市空間。這兩種城市空間承載的是兩種不同的歷史,而背后反映的是兩套大相徑庭的城市邏輯間的張力。以蜜姐為代表的老城象征著由幾代城市居民傳承下來的街坊倫理,和曾芒芒聯系著的新城則象征著不斷往前發展的現代邏輯。
1. 兩種歷史意涵:文化和發展
這兩種城市往往會選擇不同的敘述順序進入歷史。新世紀以前,池莉的小說基本上都是按時間順序來結構、推進情節的發展,但到了描寫老城,池莉選擇了插敘的手法從當下插入老城的歷史和記憶,老城是一個靜止的、永恒的城市空間,與新城相比較而存在,屬于一種穩定的當下的空間。以插敘的方式進入老城的歷史,先寫老城永恒的、定格的當下日常狀態,然后在人物關系的介紹或事件的發展中由人物講出相關的城市歷史,并把歷史轉換成了老街的文化積淀。從一個穩定的城市空間延伸出來的歷史變化并不能對城市空間和人物性格造成什么影響,所以城里的人就算經歷很大的變故,但當她看到“大街上的一切,都還在她眼睛里”的時候,就能處亂不驚,很快回歸生活。蜜姐中年喪夫,也曾痛不欲生,但她之所以能很快回到做生意、帶兒子、照顧老人的日常生活,就是因為對于城市,蜜姐是可以把控的。在這里,大歷史是外在于蜜姐和來雙揚的,歷史在她們眼里被“自豪地”置換成了城市的歷史,而城市的歷史是她們的祖輩創建的,所以歷史就是她們的家族史,是城市的文化積淀。換句話說,歷史的意義在老城中被轉化成了穩定的、深厚的文化積淀和家族記憶。《她的城》呈現出來的城市空間在一定程度上是混雜的,她是一個新舊交接地帶:
前五街道兩邊都是商鋪!多賣內衣襪子……而中山大道那邊!是近年崛起的商廈一幢又一幢!玻璃幕墻巨幅廣告!光怪陸離!趕盡時尚。
“商鋪”都是解放以前的老建筑,“商廈”是近些年崛起的新樓。而蜜姐的擦鞋店就出現在這樣一個交叉地帶。這里不全是老建筑,甚至還有酒吧,但酒吧也不是燈紅酒綠的那種酒吧,而是洋人開的“窗明幾凈,音樂低回,歌手現唱,燭光花草,香氛氤氳” ,咖啡飄香的文化酒吧,代表一種緩慢悠閑的老城文化。蜜姐擦鞋店是作為這樣一種城市空間的集中代表出現的,“店子小更合適立體地密集地充滿各種文化因素”,有趣的是,大學生們常來這里拍照和玩自拍,因為它是歷史積淀最濃的地方,把城市的歷史書寫成文化積淀,有一種為市民文化尋根的意味。在解放以前,蜜姐的祖父和丈夫宋江濤的祖父“開創了漢口這個城市和最先進的城市文化”,在這個意義上,老城的歷史被轉換成了積淀的城市文化和街坊間的倫理。
而在新城中,池莉選擇順敘來講述歷史和命運變遷,從1980年到1998年,從曾芒芒開始談戀愛到準備離婚,從改革開放到抵抗洪災,當代歷史的發展、人物的故事和小說敘述的推進是三位一體的。在這里,城市的歷史被置換成了現代這樣一種線性的發展邏輯。在歷史中完成的是流動的滄海桑田和社會巨變,這樣一種變動、不穩定的歷史之中,“文革”、被打倒、改革開放、市場化、失業潮、下海經商等使人的地位也容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鄺園從昔日的鍋爐工變成腰纏萬貫的大老板,并突然因病去世,高蘭曾經是給毛主席表演過節目的富家女,后來卻只能當一個賣湯圓的女工。這個城市是一系列歷史變遷的產物。歷史發展帶來的不穩定和沖擊,使得恒常的東西在瓦解。《水與火的纏綿》開頭和結尾時間的選擇頗能說明問題。故事始于反復點染的1980年5月的某一天,父母解除了“我”的禁忌:可以談個人問題了。同時,與反復出現的汽車、飛機、輪船形成對照,這個城市開始醒來、復蘇,走上現代化之路,發展經濟了,這是一個春天。而結尾設定在1998年百年不遇的大洪水,這種災難本身蘊藏著對從1980年到1998年這個發展過程的反思,洪水造成輪渡停航、公交被淹、機場被淹,現代化帶來的一切碩果都癱瘓了。《水與火的纏綿》開始于現代的發展,結束于對現代邏輯的反思。
2. 街坊倫理和現代邏輯之間
池莉把兩種城市背后的意識形態闡釋為兩種邏輯間的對立。其背后街坊倫理和現代邏輯的張力是通過分別標出異項來實現的。以城/鄉的格局標出了老城的城市性,以武漢/深圳(或廣州)的關系格局標出了武漢的現代性。
池莉的寫作一直以來都似乎滲透著一種城鄉之間的等級判斷。《生活秀》中把城鄉關系書寫成了來雙揚和九妹的關系。九妹的母親對生活的憧憬是“有錢,有城市戶口,有飽暖的日子,有健康的后代”,而久久就算健康也不會娶九妹是因為九妹畢竟骨子里是鄉下姑娘,來雙揚那樣的生活是鄉下姑娘九妹的奮斗目標。《她的城》中寫道,“鄉下女孩進城!一是文眉!二是染黃發!三是穿吊帶!四是說拜拜”,“到底是農村女人,進城十年八載也對皮鞋沒個把握”,“幾輩子的城市人與幾輩子的農村人!終究有隔”,逢春之所以不同于別的擦鞋女,是因為她是地道的城市人。池莉赤裸裸地書寫城鄉間的等級差序,通過把鄉村他者化來標出城市,這背后體現的是一套以老城空間為依托的市民的倫理和邏輯。老街雖是穩固的,但她作為一座商業化的城市,“是最早復蘇的小商品市場”,所以寧靜的表象下面也有逐利的商業邏輯。《她的城》一開始寫逢春擦皮鞋,“十五分鐘過去了”,“二十分鐘過去了”,“二十五分鐘過去了”,逢春還在擦皮鞋,蜜姐不得不發怒了。一個恒常不變的空間里竟然也要這么爭分奪秒,蜜姐的警句是“時間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話本來是說在時間中穩定的東西才是可靠的,比如愛情,但蜜姐的意思是擦鞋工人對于時間要進行精確的算計,以更多地賺錢;而蜜姐把擦鞋改成“美容”和“養護”就是實行了“概念就是金錢”的商業邏輯。但“金錢邏輯”在“她的城”里并不是決定性的,它小于幾輩人之間形成的以街坊倫理為表征的市民倫理。蜜姐就是這套自豪的、自足的街坊倫理的代表,這是一種“吃飯穿衣,飲食男女”的“過日子”的倫理,基于“城市居民之間那種因襲了幾代人的無條件信賴”,是“對人情世故深諳和遵守”,“這就是城市居民骨子里頭的生死盟約”,而蜜姐就是這種秩序的捍衛者。
因此蜜姐具有了“男性化特征”。在改革開放興起的小商品潮中,這個老城“又把蜜姐塑造了一番,這回塑造的方向是革命樣板戲里的阿慶嫂”,而阿慶嫂本來就是一個能干剛強卻沒有性別特色的女性。蜜姐是吸煙的,吸煙本來是一個偏男性化的動作,但在來雙揚那里,吸煙變成了一種被別人的欲望所玩味的“風騷”,可蜜姐吸煙的時候“瘦溜的手指伸過去!摸來香煙與打火機!取出一支煙!叼在唇間!噗地點燃!湊近火苗!用力拔一口”,“伸”、“摸”、“取”、“叼”、“噗”、“拔”,完全是男人的動作,此外,蜜姐還當過“軍人”,有“當兵的底子”,“總有女生男相氣派”,說話也“嘹亮豪爽”。從來雙揚到蜜姐,老城里的女人不再成為被欲望的對象,伴隨的卻是性別的男性化,其實蜜姐的男性化不是池莉處理女性問題的倒退,它恰恰有更豐富的意義。
首先,因為蜜姐是街坊倫理的捍衛者和執行人,與市民倫理不同的是,街坊倫理不僅來自市民之間的關系和他們的生活方式,還有一種無形的性別秩序。這一套倫理有底線和規矩。蜜姐的底線是“逢春不能在自己的店里出事”(紅杏出墻),因為這樣蜜姐一對不起逢春老公,二對不起“水塔街幾代人交往過來的街坊”,三對不起閣樓上的婆婆。蜜姐做事首先考慮的不是自己,而是街坊間的影響。蜜姐和逢春表面上是老板和雇工的關系,實質上是以這一套街坊倫理為紐帶的鄰里關系,也正是如此,逢春作為昔日寫字樓里的白領麗人才能拉下臉來擦鞋,這是一套大于金錢邏輯、大于一切的街坊倫理關系。
其次,蜜姐和逢春的關系存在一定的曖昧性,這就不難想象為什么蜜姐形象有男性化之嫌了:
蜜姐沖上來!一把拽住逢春衣袖!逢春隨之站了起來,蜜姐又打開擦鞋店大門!把逢春推了進去。進去一拉開關!忽地大亮刺刺的!兩人都把眼睛一躲!蜜姐急急地又關掉了燈……反身坐在了樓梯上!抱住膝蓋!說:“我的姑奶奶,這么晚了你到底要干什么啊?”
逢春動了動嘴巴!千言萬語都堵在嗓子眼! 說不出來!只有眼淚先撲簌撲簌流下來了!她又要強烈抑制自己不要哭!于是肩頭抽聳得厲害。
蜜姐說:“好吧好吧。我想起來了我忘記了給你錢。”
……逢春不接,哭腔哭調地說:“我又不是這個意思!我不是要這個錢!這錢我不要!”
蜜姐和逢春之間的這段描寫特別吻合言情小說中情侶間吵架的套路。蜜姐作為街坊倫理的代言人,本來和逢春之間是一種監視與被監視的關系,但二者經歷了頗有“言情”意味的一些發展以后,被處理成了閨蜜關系。池莉作為一個持市民立場的女作家,其性別觀比較溫和,自然不會在女性之間發展成一種同性愛敘述,盡管這樣,池莉還是提供了一種可能:女性之間可以形成一種自我解放的聯盟,來“一起協力對抗內心的痛苦與糾結,還有男人帶來的種種麻煩和打擊”。
不同于以城/鄉的格局標出老城的城市性,在新城書寫中池莉以武漢/深圳(或廣州)的對照標出了都市的前進性,以突出這種都市空間代表的現代邏輯。深圳作為率先進入改革開放的城市,一直是武漢的榜樣和先驅,是一個現代化的寓言。“去深圳”是一個美好的夢想,用來應對90年代市場化改革帶來的下崗失業潮。深圳也是財富和現代化、進步的象征。《水與火的纏綿》中的燕子和《所以》中的妹妹葉愛紅是這一批人的代表。深圳“是一個自由,一個解放,一個可能,一個懸念,一個心情,一根救命稻草”,其實武漢追隨深圳的就是現代的前進的發展邏輯。以“深圳”的參照來表達現代都市之“變”,文中對這一邏輯的展現也體現在一些物件的升級中。比如從80年代的單位電話到90年代的家庭電話、手機,從自行車、公交車/輪渡到無人售票公交車、出租車和飛機,從某種程度上說,新城就是在這種發展的邏輯中形成的。深圳作為更現代的都市,一方面給武漢帶來了發展和進步,主要是物質方面的進步,另一方面也帶來了破壞性的變化,主要是精神的焦慮。
在現代的發展的邏輯中,現代邏輯和婚姻的穩定性之間似乎形成一種背反式結構。池莉老是把現代邏輯的破壞性書寫為男人發達了就要離婚或出軌這樣一種模式,鄺園的故事、肖克的故事,甚至丈夫高勇的故事都運作在這樣一種模式之下。他們拋棄已有的生活去深圳或廣州闖蕩,是為了改善妻兒的生活,但當他們真的有能力改善家人生活的時候,他們繼續被一種現代的邏輯驅使:拋棄妻子,選擇更好的妻子。這種現代邏輯打破了人們生活的穩定性。池莉把背后的原因書寫為功利婚姻和物質婚姻的失敗。《水與火的纏綿》中曾芒芒和高勇的婚姻屬于雙方按照自己開列的世俗標準“按圖索驥”的功利婚姻。按池莉的話說:“就在我們打倒了封建包辦婚姻的同時,我們又以自由之名滋生了功利婚姻,就在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同時,我們又以經濟之名滋生了物質婚姻。”池莉的女性主人公在婚姻的秩序里不斷進行著“挫敗”—“尋找”—“挫敗”的循復探索,這使她的小說含有一絲宿命式的悲愁。因為在功利婚姻和物質婚姻結構之下,難有一個理想的男性婚姻對象。在新城中,一方面,發展的邏輯和婚姻的穩定形成一種背反式結構,把現代的破壞性書寫為男人有錢就要拋棄妻子這樣一種模式;另一方面,池莉也揭示了功利婚姻和物質婚姻的不穩定性。而在老城中,女性的婚姻角色頗為曖昧。賀桂梅寫到,在女性和城市的同構書寫中女性同時作為主體和客體,是被放逐于婚姻秩序之外的,從來雙揚到蜜姐,雖然二者都是婚姻秩序之外的女性,但池莉通過賦予蜜姐一個男性化的形象(而不是一個被看的客體),使得蜜姐成為一個更具主體性的女性,她們作為城市的主人,都代表的是男性化的那套市民倫理或街坊倫理,但蜜姐最后和逢春形成了一個具有抵抗男權性質的同盟,這個同盟一定程度上戰勝了蜜姐和老城代表的街坊倫理。
結語:煩惱地和烏托邦
在對這兩種城市空間的想象中,池莉某種程度上安排了二者的交融。在對老城的書寫中,池莉慣于安插一個外來者的視角,闖入這個穩定的城市空間。比如《生活秀》中的卓雄州和《她的城》里的駱良驥,他們都是一些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人士,都來自那個現代的新城。一方面,他們給這種非主流的老城投去的是把玩的、欲望的眼神,老城是他們的消費對象;另一方面,他們卻不可避免地被老城和城里的女人吸引,以至于卓雄州兩年內每天去買來雙揚的鴨頸,以至于駱良驥為擦一雙皮鞋掏了兩百多塊,奇妙的是,卓雄州對來雙揚的欲望竟然沒有“性”能力實現,駱良驥也在逢春面前自卑、緊張起來。他們雖為成功人士,卻并不能達到一個理想的狀態,這是現代都市的雙重意味:擁有金錢和發展,同時在光鮮表面之下存在很多問題。
對兩種女人的并置性書寫也有這種意涵。其實逢春也是一個外來者形象,她本來屬于“漢口最豪華的新世界國貿寫字樓”那個現代空間,蜜姐和逢春的關系是金錢倫理下的老板和雇工,更是街坊倫理下的鄰里,還是市民女性和知識女性這兩種女人的關系,池莉把兩種女人并置于“她的城”里。蜜姐諳熟這座城及后面那套人情世故、街坊倫理,而逢春這個生瓜生蛋是“不懂的”,二者關系的呈現其實包含了池莉的基本價值取向,而這一格局是池莉早期寫作中常出現的:在認同市民價值的同時,諷刺知識分子的劣性,表現在逢春這里是“小曖昧小情調小酸詞”。更巧的是,這座老城治愈了逢春的焦慮:都市中產知識女性都有的婚戀、生活的焦慮。逢春最初是因為和老公賭氣來擦鞋,在擦鞋的三個月里,逢春只看蜜姐這個人,就學到很多,很多問題得到了沉淀與分辨,逢春在蜜姐身上學到一種市民女性的智慧,治愈了她作為都市中產階級女性的焦慮病。

注釋:
①池莉:《創作,從生命中來》,《小說評論》2003年第1期。
②戴錦華:《池莉:神圣的煩惱人生》,《文學評論》1995年第6期。
③於可訓:《在升騰與墜落之間──漫論池莉近作的人生模式》,《當代作家評論》1998年第1期。
④趙園:《北京:城與人》,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頁。
⑤陳思和:《都市里的民間世界:〈傾城之戀〉》,《杭州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
⑥戴錦華:《神圣的煩惱人生》,《文學評論》1995年第6期。
⑦珀西·盧伯克著,方士人譯:《小說技巧》,《小說美學經典三種》,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第79~82頁、第102~103頁。
⑧賀桂梅:《三個女人和三座城市》,《女性文學與性別政治的變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46~249頁。
⑨池莉:《水與火的纏綿》,華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頁。
⑩池莉:《她的城》,《中國作家》2011年第1期。
北京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