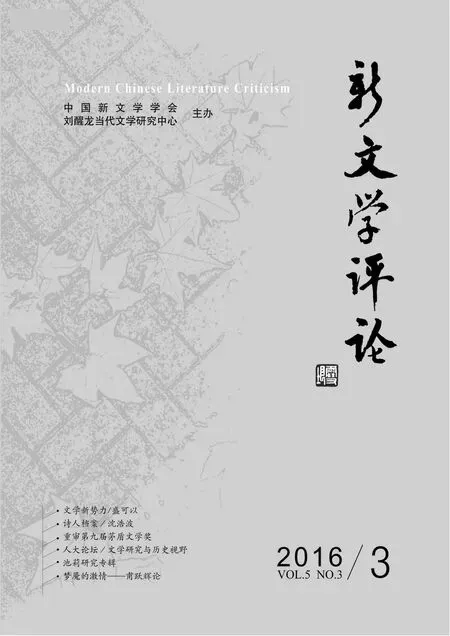論準左翼作家的暴力敘事
◆ 黎保榮
?
論準左翼作家的暴力敘事
◆ 黎保榮
前言 何為準左翼作家?
要明白何為準左翼,就得從左翼作家入手。左翼(left wing)的“左”(left)是指擁護社會主義的,左翼是指在政黨中的擁護社會主義者。但是中國的左翼(左聯)卻非政黨,只是一個群眾組織作家聯盟,里面有不少非共產黨員作家(如魯迅等)。根據有關資料,當時中共對“左聯”關心、領導不夠,只通過年輕黨員來執行運作,把其視為一般群眾的革命團體,忽略其作家身份(特殊的文學與思想斗爭),而注重其左翼的政治屬性①。它一方面并非政黨,另一方面具有政治屬性;一方面是作家,另一方面是左翼。隱約可知左翼作家是一個歧義百出、非常含混復雜的概念。從身份上看,似乎只有加入“左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作家才能被稱為左翼作家,但是,這種劃分方法有兩個問題難以解決:第一是“左聯”這個名稱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簡稱,換言之左翼作家早就存在,“左聯”只是這些左翼作家的聯盟罷了,是先有左翼作家然后才有了這個聯盟,這個時間順序和邏輯關系不能顛倒互換。第二,曾經參加“左聯”而又被“左聯”除名的作家算不算左翼作家?如葉靈鳳在三十年代初參加“左聯”,后因參加民族主義文學運動,于1931年5月被“左聯”執委會通報除名;又如周全平曾被選為“左聯”的候補常委,但1931年因一筆革命經費在他手里下落不明而被“左聯”執委會通報除名,他們到底算不算左翼作家?還是算“曾經的、從前的左翼作家”?從身份上推斷似乎比較困難,那么從精神傾向上看,似乎只有主張階級斗爭、無產階級革命的作家才算得上左翼作家,但是持這類主張的語絲社、創造社、太陽社又彼此針鋒相對,互不相讓,似乎很難判斷誰“更左翼”、“更無產”。而且,戴著“革命”的帽子耽于唯美主義和愛情書寫的葉靈鳳,寫過《塵影》但趨向“精神共產”并曾為民族主義文學刊物撰稿數篇的黎錦明②,甚至宣稱“曾受過小資產階級的大學教育的我輩,是決不能作未來的無產階級的文學”的郁達夫似乎在“精神傾向”上更多小資產階級的精神趣味,又很難算作嚴格的左翼作家。另外,寫過《八月的鄉村》的蕭軍,在革命經驗和革命精神上不比任何一個左翼作家遜色,卻未被批準加入“左聯”,只能被視為“同路人”,這恰恰形成了對精神傾向標準(以及以上的身份標準)的否定。那么,從第三個標準即創作風格(注重無產階級集體主義革命精神在創作中的作用,注重革命暴力,昭示革命必勝的信念,等等)來判斷,又如何呢?似乎也不大容易。因為左翼作家至少有三種“革命”風格:一種是革命理論色彩相對較濃的創作,如胡也頻、蔣光慈、洪靈菲、戴平萬、華漢等作家,他們的創作中時不時會出現諸如“集團的革命”、“統一的意志”、“無產階級精神”、“組織革命”、“為了無產階級”、“斗爭的本體”等等比較顯著、浮露的革命話語。一種是在人生寫實或鄉土寫實中顯示革命的必然性,如茅盾、柔石、魏金枝、沙汀、艾蕪、蔣牧良、葉紫、張天翼等“左聯”作家,以及葉圣陶、王統照、吳祖緗、巴金等非“左聯”作家(但他們都有“革命”傾向)。還有一種就是像東北流亡作家群那樣的直接書寫革命經驗和革命精神的作家創作,如“左聯”的端木蕻良、舒群,非“左聯”的蕭軍等等。這樣一來,三種風格誰更左翼呢?很難區別。即使說三種風格都是左翼風格,以表明左翼文學的豐富性,那么相似風格的非“左聯”作家是否也可以被稱為左翼作家?如果不可以,那么這個創作風格的標準也就等于無用。如果說可以,那么左翼(“左聯”)作家的隊伍一方面會進行擴大,將非“左聯”的作家納入進來,另一方面又會縮小,將非此風格的葉靈鳳等人“驅逐出境”。這樣,左翼作家和是否參加“左聯”就變得關系松散,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這個名稱就有自相矛盾自打嘴巴之嫌,左翼作家也就變成了一個非常不穩定的概念。
簡言之,身份、精神傾向和創作風格這三個標準都不足以嚴格限定左翼作家這個概念。那么,有一個折中的、相對辯證的分法是:一是參加“左聯”的都稱為左翼作家(同時具備革命精神傾向和創作風格的稱為嚴正的左翼作家,通稱左翼作家,楊義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注重的正是這種作家)。二是因為左翼作家只是作家的一個身份、一種特色,當作家的其他身份、特色比左翼作家更為顯著、更為獨特的時候,可酌情列為后一特色的作家,如楊義在其《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就將“左聯”的端木蕻良、舒群、李輝英等與非“左聯”的蕭軍、蕭紅共同列為東北流亡作家群,又將艾蕪、沙汀、周文等左聯作家全數歸入四川鄉土作家群,這應該是一種比較辯證的劃分方法。三是沒加入“左聯”,但又具有革命傾向和創作風格的作家,可稱為準左翼作家,如蕭軍、巴金、葉圣陶、王統照等等,這樣既保證了左翼作家的團體(“左聯”)性質,又照顧到準左翼作家的相似特征,又避免了非左翼作家這個概念的寬泛無邊、大而無當,可以說相當合理。說到底,左翼并非單純是一種流派和風格,更多是作家的一種政治身份或傾向。
一 巴金的暴力敘事
在20世紀30年代的準左翼作家當中,巴金、蕭軍、葉圣陶、王統照等人的小說創作都具有推崇尚武而鼓吹暴力的傾向,這一現象不能不引起我們研究者的高度重視。
眾所周知,巴金是一位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忠實信徒,巴金從對“專制的王國”似的“富裕的大家庭”的憎恨、不滿出發,開始覺得“社會組織的不合理”,要“改造”社會。他15歲的時候,他的這種苦悶情緒遇到了知音,那就是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節譯本),廖亢夫描寫俄國革命青年反抗沙皇統治而英勇犧牲的話劇《夜未央》以及《實社自由錄》第一集中的高德曼的文章。這些無政府主義的名家名文,以“煽動性的筆調”使青年的巴金的“心燒成灰”,并且“第一次在這另一國度的一代青年為人民爭自由謀幸福的斗爭里找到了我的夢幻中的英雄,找到了我終身的事業”,才“有了明確的信仰”。不久他就通過書信、會談等方式與重慶的無政府主義團體適社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并做了適社《半月》刊的同人和編輯。并組織了秘密的無政府主義團體均社,被稱為安那其主義者,找到了友情和信仰,無政府主義照徹了他“靈魂的黑暗”,使他“好像一只破爛的船找到了停泊的港口”,使他“懷著拜佛教徒朝山進香時的虔誠”。這種信仰使他直到老年也“一直不肯拋掉無政府主義的思想”③。正是這種信仰促使巴金1921年初就以芾甘的筆名發表了《怎樣建設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這樣飽含無政府主義思想的論文,他于1927年赴巴黎求學,探討無政府主義原理,翻譯了廖亢夫的《夜未央》和克魯泡特金的《倫理學的起源和發展》(上卷)等著作,并于1928年寫出了《滅亡》,正式將無政府主義思想融入其文學(小說)創作中。比較其他無政府主義思想,巴金更傾向于其中的暴力革命主張。
無政府主義的暴力革命主張,在巴金的眼中,大致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主張階級斗爭與革命。或者將政府毀滅于無的狀態,因為“政府是一種強權機關,是保障法律的,它只有殺害我們,掠奪我們的衣食住,又能侮辱我們,幫助資本家殺害貧民的。我們人類本是自由的,它卻創造出許多法令來束縛我們;我們是酷愛和平的,但它卻叫我們去戰爭”,所以,“我們要想尋幸福,第一步就是推翻它”。但這幸福的獲得是必須付出代價的,就是用“無量數的熱血”,“賭一點自由新血,與魔王破釜沉舟一戰而亡”,巴金極為狂熱地鼓吹“我愿我們的朋友和我們預備著滿腔的熱血,來干這最痛快、最愉快的革命事業,齊向這幸福的路上走!”④或者主張階級斗爭,反對資本家,因為“那些資本家,壟斷世界公有的財產,使我們貧民不能生活,政府不但不去罰他,反設法律來保護他。人民沒有吃的,只得搶些來吃;沒有穿的,只得搶些來穿;沒有用的,只得搶些來用;這都是那些資本家強迫我們人民做的。但是政府又說我們是強盜,要拿我們去槍斃”。故而要反對資本家及其保護者政府,“要建設真自由、真平等的社會,就只有社會革命”,否則“就要為資本家的魚肉了!”⑤鑒于人類“早分成為兩個對抗的階級”,他宣稱“無政府主義乃是階級斗爭中被掠奪階級的理想和觀念學”,并贊同“無政府主義真正的創造者是革命的無產階級”,認為“無政府主義者并不反對階級斗爭,而且還主張著”,因此,他極力推崇勞動階級的“橫暴”舉動,并建議“燒幾處縣知事衙門,搗毀幾所監獄,也可以幫助農民組織農村公社”,總之想法使暴動“帶有一點無政府主義的色彩”⑥。應該說,在無產階級反抗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問題上,在反抗黑暗政府問題上,巴金與左翼作家沒有多大分別(除了他的無政府主義色彩相對較濃一些),故此,巴金可以說是一位準左翼作家。另一方面,巴金還主張以暗殺作為革命的手段。他“并不反對暗殺”,認為“恐怖主義既是現社會的罪惡造成的,則只要現社會——多數人受苦少數人享樂的社會存在一日,它便不能避免”,“恐怖主義的要點在‘自衛’和‘報復’,‘自衛’是儆戒以后政府的行動,‘報復’是報過去的仇。這在‘地底下的’組織里是需要的”,“是‘地底下的’國家里應有的現象”,在俄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簡言之,他為暗殺尋找社會土壤的合理性。而且他還為暗殺(恐怖主義)尋找“精神與手段”的合理性:他自問自答:“我便反對恐怖主義,反對暗殺?不,不然。就恐怖主義的本身來說,它也有它的價值,我非但不否認,而且多少還贊同。”表明他對暗殺(恐怖主義)的價值的認可與肯定。他甚至認為在暗殺事件中“擲炸彈放手槍的人都有他不得不‘放’,不得不‘擲’的苦衷在”。這種“苦衷”或者為了“自衛和報復”,或者“為了愛”。巴金對“為了愛”的暗殺推崇備至,因為人造的各種制度漸漸將愛鏟除,使得人們彼此相恨,使得少數人壓制多數人,使得多數平民生于憂患,死于痛苦。“我們既不能活著使得人們彼此相愛,使受苦的多數人過幸樂的生活,那么,我們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來破壞那制度或維持著制度的人,使得‘憎’早點消滅,‘愛’早點降臨。因為我不能生活在這沒有愛來統治的世界上,我沒有力量來實現愛,那么我只能為愛之故而死。所以為了愛而殺人,而自己被殺。以我的一命報被殺者的一命,被殺者會感到種種痛苦,然而同樣的我以自己的痛苦來報償。”“極端的愛而不得不用恐怖主義表現出來,自己無所不愛,而不得不拋棄所愛的一切,殺身成仁,來為將來的人謀普遍的愛的生活”,這種為了愛而暗殺,為了愛而“破壞這恨的世界”的無政府主義戰士,“他的手槍,他的炸彈,不是鋼鐵和炸藥,而是自己的血和淚以及無數平民的血和淚造成的”,而這一切都是根源于廣博的愛。正因如此,巴金對“為了愛”而實行暗殺的無政府主義戰士的人格精神贊賞有加,將之譽為具有“崇高的人格”的“有偉大人心之至人”,“世間最優美的人”,并認為“這樣的死比耶穌之被釘十字架、蘇格拉底之仰毒藥,還要光榮得多。這才是真正是為愛之故而死呢!”對無政府主義的暗殺可謂推崇到登峰造極無以復加的地步。總之,無政府主義的暴力革命思想,使他“對于恐怖主義相當贊成,并且對于‘恐怖主義者’也極佩服”⑦。然而,歸根結底,這種暴力革命思想,雖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但對于熟讀四書五經和古代小說⑧的巴金來說,更多替天行道、殺身成仁⑨的中國俠-士文化的氣息,或者嚴格來說,是中國俠士傳統使巴金找到了無政府主義,也使無政府主義這種外來思想在中國俠-士文化的土壤中扎根,并成為他的信仰。這種辯證的關系,必須認真對待。
也正因此,在滅亡三部曲與愛情三部曲中作者宣揚無政府主義的暴力革命暴力暗殺,歌頌主人公肉體“滅亡”的獻身精神,我們很容易就能找到其暴力敘事的思想動機。
例如在《滅亡》中,巴金的無政府主義暴力革命思想主要體現為兩方面。一方面,是主人公杜大心的“憎恨哲學”,他對人壓迫人的社會與階級現實極端憎恨,他教人“憎”而不是教人“愛”。他反對愛、和平以及大自然的美,認為這些東西“欺騙人,麻醉人”,“我要詛咒人生!”“我已經敲遍了人生底門,但每一扇門上都涂滿著無辜受害者底鮮血。在這些血跡未被洗去以前,誰也不配來贊美人生。”正因為這種帶血的現實,杜大心強調:“我要叫人們相恨,唯其如此,他們才不會被騙,被害,被殺。”“我不能愛。我只有憎。”“我既然不能為愛之故而活著,我卻愿意為憎之故而死。到了死,我底憎恨才會消滅。”“至少在這人掠奪人、人壓迫人、人吃人、人騎人、人打人、人殺人的時候,我是不能愛誰的,我也不能叫人們彼此相愛的。凡是曾經把自己底幸福建筑在別人底痛苦上面的人都應該滅亡。我發誓,我拿全個心靈來發誓說,那般人是應該滅亡的。至少在他們滅亡之后,人們才能相愛,才配談起愛來。在現在是不能夠的。”面對各種因貧富懸殊、階級壓迫、社會不公而造成的悲慘境況,他要“宣告一個階級、一個社會底死刑”,歌頌撒旦的反抗。
正因如此,他不僅鼓吹憎恨哲學,還宣揚暴力抗爭,以流血、復仇來消滅憎恨之情與憎恨之源。“我所負的責任乃是擔起人間的恨和自己的恨來毀滅這個世界,以便新世界早日產生。我應該拿自己的痛苦的一生做例子,來煽起人們底恨,使得現世界早日毀滅,吃人的主人和自愿被吃的奴隸們早日滅亡。”為達此目的,他決定要做一個“為同胞復仇的人”,“以自己底壯烈的犧牲去感動后一代”,“就是死,也要像狼一般地奮斗到死,總得把敵人咬幾口才行!”但是這樣暴力復仇暴力抗爭的結果是“滅亡”,不僅是把幸福建筑在別人苦痛之上的壓迫者的“滅亡”(或詛咒其滅亡),也是反抗壓迫英勇獻身者的“滅亡”:他明白“對于最先起來反抗壓迫的人,滅亡一定會降臨到他底一身”,但是“在什么時候,在什么地方,沒有犧牲,而自由居然會得勝在戰場?”所以,“為了我至愛的被壓迫的同胞,我甘愿滅亡”。另外還是旁觀殺革命黨,沒有同情心的看客的“滅亡”:相信他的社會主義主張以及用革命推翻不平社會思想的革命者、“大孩子”似的張為群運送傳單被捕,被殘酷斬首,但看客們將之視為“殺人盛典”,爭先恐后“見見世面”,甚至咒革命者為“瘟豬”、“無父無君的禽獸”、“殺革命黨越慘越好”,甚至踢人頭玩。這種愚昧、奴性與冷漠使杜大心感到一種“不能抑制的憤怒”,“他現在確實相信所有這些人都要滅亡,而且要先他而滅亡”。他對看客感到“一種復仇的滿足了!”正是這樣的一種絕望發現,使他失去了“革命的對象”,如果為這種看客而獻身,革命又有什么用呢?又能改變什么呢?因為正是這種看客支持著黑暗壓迫的存在。
正因如此,在這三種“滅亡”的夾擊之下,他從暴力革命演變為暴力復仇,從為受苦的大眾復仇演成為個人復仇:“他應該用自己底生命來替‘他’(張為群)復仇。”于是,他從精神暴力(憎恨哲學、鏟除看客的心理)走向實實在在的暴力復仇(暗殺),他冒充新聞記者在總商會歡宴戒嚴司令的席上,向戒嚴司令連開四槍,打死一個馬弁,并開槍自殺。他的這種義無反顧的絕望復仇心態和孤注一擲的個人恐怖行為,得來的結果是:戒嚴司令沒有滅亡,半個多月就恢復了健康,倒是杜大心長久滅亡了,戒嚴司令因禍得福,得到巨額的物質賠償,而杜大心卻永劫不復,身體腐朽。這一種強烈的對比并不是對暴力復仇有所懷疑,而是彰顯了壓迫階級的殘忍、腐敗,并以此警示后人作前赴后繼的反抗。杜大心的這種雖有著“對于人類的深刻的憎恨”,但“終為愛而死”、“為愛之故而殺人”的思想與行為,正與巴金的《無政府主義與恐怖主義》中提及的“犧牲自己的生命來破壞那制度或維持著制度的人,使得‘憎’早點消滅,‘愛’早點降臨”、“為愛之故而死”、“為愛而殺人,而自己被殺”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有著驚人的一致,也與蔣光慈的《最后的微笑》中被壓迫者殺壓迫者天經地義的革命理學不謀而合。正是因為這種為了愛而實施暴力的反抗性與合理性,使得他的精神并沒有隨肉體而滅亡,反而感動后人,“他也不是白死的”,幾年以后全上海紡織工人實行大罷工,這場階級斗爭的領導人物就是曾經反對杜大心暴力革命思想和為愛而殺人流血思想的李靜淑。
這種暴力(階級斗爭、暴力革命)—滅亡—新生的寫作模式在《新生》、《死去的太陽》里再次出現,如《新生》里主張階級反抗、暴力革命的李冷被捕被殺,但是他的“滅亡”換來的卻是“新生”,“我底死反會給我帶來新生”,是像基督一樣的新生。此不贅言。
在接下來的愛情三部曲之中,滅亡三部曲那種“與汝偕亡”的暴力復仇思想逐漸有所收斂,或者嚴格地說,暴力復仇沖動被韌性戰斗的革命理性所限制,二者時有沖突,顯示出一種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例如在《雨》中,激憤的吳仁民反對用研究、讀書、宣傳等文弱的手段進行革命,主張“速成”的暴力反抗,他要“這個卑鄙的世界!就索性讓它毀滅也好!完全毀滅倒也是痛快的事,比較那零碎的遲緩的改造痛快得多”。這種暴力毀滅的情緒沖動使吳仁民強烈渴望“把生命作孤注一擲”,相信沒有“血”的進步是不存在的,他甚至要拿高志元帶回來的手槍去冒險(只是沒有找到手槍),“復仇的念頭咬著他的腦子和他的心”。最后,朋友們的理性、冷靜、韌性的戰斗精神使他認識到“仇敵是制度”,“這個黑暗的世界里的確潛伏著一種如此巨大的力量。……痛苦把無數的人團結起來,使他們把自己煉成一根鞭子,這根鞭子將來有一天會打在整個的舊社會制度上面,把它打得粉碎!”從暴力復仇沖動回歸韌性的革命斗爭精神。
而《電》在某種意義上是《雨》的精神寧馨兒。只不過吳仁民在這里變得理性沉穩,而他原來的激憤暴力復仇沖動被敏所繼承。小說在吳仁民等人與敏之間的理性與沖動、持久革命與暴力復仇的辯論展開。但是無論哪一種理性的革命思想都不能抑制敏的暴力暗殺(復仇)沖動,他置生死于度外,孤注一擲,用炸藥暗殺旅長,用自己的生命與鮮血詮釋了“為愛而死”、“不能忍受的生活應該用暴力毀掉”(《滅亡·七版題記》)、“用死來證實信仰”(《〈愛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以及巴金自己“我的憎恨是盲目的,強烈的、普遍的。……我常常把我的愛變成憎恨”,“感情與理智的沖突,思想與行動的沖突,理想與現實的沖突,愛與憎的沖突……把我拋擲在憎恨的深淵里”的復雜內心世界⑩。
從上可知,從滅亡三部曲到愛情三部曲,都存在著階級斗爭、暴力革命的思想與行動,那種“為愛而殺人”的無政府主義暴力復仇(暗殺)的沖動更是一直不減,到了《電》里面更是不可遏止、不受控制。到了四十年代的抗戰小說《火》三部曲里,巴金更把這種暴力暗殺正義化,這從他在《火》第一部、第三部里描寫暗殺漢奸的理直氣壯、大義凜然、激情洋溢就可以略知一二。
綜上所述,巴金小說中那種為民請命、替天行道、殺身成仁、血債血償、視死如歸的無政府主義暴力革命思想,恰恰是中國俠-士傳統的體現,在這里,外來的無政府主義思想被中國俠-士文化所浸潤,帶著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
二 東北準左翼作家的暴力敘事
而蕭軍、林玨、舒群等東北作家則與巴金等有所不同:一方面長期的日本殖民歷史和尚武事實曾對他們產生過潛移默化的心理影響。另一方面是作家身份的特殊性,他們也都具有過習武從軍、疆場廝殺的切身經歷,如蕭軍自幼癡迷中國武術,好為人打抱不平,1925年入陸軍34團當騎兵,1927年考入東北陸軍講武堂,曾當憲兵,后在東北憲兵教練處任少尉軍事及武術助教。舒群于“九一八”事變后加入抗日義勇軍。端木蕻良于“九一八”后參加在綏遠抗日的孫殿英部隊(舒群和端木蕻良雖然加入“左聯”,但是在“左聯”中他們的風格是非主流風格,其暴力敘事風格和茅盾、蔣光慈、葉紫、胡也頻、洪靈菲、華漢等等左翼作家不同,反而與準左翼作家蕭軍相似,具有東北作家群的風格特征,所以在此略為提及此二人未為不可)。再一方面是黑土地文化的獨特性。東北地域廣闊,跨海擁陸,山岳、密林、草原、沼澤、江河、平原相間,鳥獸蟲魚遍布,物產資源豐富,氣候極為嚴寒。這種獨特的自然地理條件致使東北土著民族便于以漁獵為生。而由于氣候嚴寒、環境嚴酷,東北各族長期延續的漁獵經濟及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習俗和精神價值取向,莫過于勇悍尚武(另一方面,團體的協作精神也比較重要)。而這種好勇斗狠、雄強剽悍的尚武風氣便使東北胡匪的大批出現成為可能。就如蕭軍回憶的那樣:
當時在民間雖然有這樣的諺語:“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但在我們的家鄉——遼寧錦州、義州一帶,人們卻并不這樣看待的。當兵和當匪不獨沒什么嚴格的區分以至恥辱的意味,相反的,這當兵竟成了那一帶某些青年人們的一種“正當”出路,一種職業,而且是一種近乎“光榮”的職業。這是因為當時統治東三省的大大小小軍閥,幾乎全是當兵或當匪出身的。例如有名的軍閥:張作霖、馮麟閣、張作相、湯玉麟(綽號湯大虎)、孫烈臣,以至后來成為抗日起義將領赫赫有名的馬占山(綽號馬老疙疸)將軍,就全是“綠林”大學出身,這是時代的產物,時代的風氣……
我家鄉那地方,地屬山區,民風是很閉塞、剽悍的,一般并不崇尚讀書。當軍官或“紅胡子”(土匪別稱)是一般懷有野心的青年所向往的理想。
換言之,由于東北民風剽悍,故而重武輕文,尋求出路時也往往走向尚武之業(從軍或當匪)。綜觀源自西漢而盛于清末以后的東北土匪現象,雖有無惡不作、殺人越貨的“惡”的一面,但也有官逼民反投身綠林,殺富濟貧、“替天行道”及在民族危難的歷史關頭奮起抗日的壯舉善舉。
從上可知,若從尚武角度切入,則可以說漁獵文化和土匪(兵匪)文化是黑土地文化的鮮明特色。
上述一切,無疑是東北作家作品擅長于暴力敘事的精神資源。由于是棄武后才從文,東北作家群筆下的暴力敘事,往往給人一種經驗追溯的真實感覺。如林玨的《血斑》,描寫了一個東北傷兵,面對著日本人的囂張氣勢,高呼著“祖國萬歲”的響亮口號,最后飲彈自盡,誓死不當俘虜。又如蕭軍的《八月的鄉村》,描寫唐老疙瘩因李七嫂而連累戰友戰死,主動請求鐵鷹隊長槍斃他以明軍紀。再如舒群的《戰地》,描寫姚中受傷為了不當俘虜,劉平向其頭部連開四槍,而后來劉平自己也為同一原因而飲彈自盡。這種為了不做俘虜,為了不連累戰友,為了使得戰斗力充分發揮而從容自盡的行徑,在暴力場景中傳達出一種寧死不屈、以身許國的英雄主義精神,將軍人的榮譽和軍人的氣節表現得慷慨悲壯氣勢如虹。東北作家慣于直接寫人物的暴力行為,特別是戰爭中的暴力描寫顯得迅速、真實而殘酷,盡顯戰場瞬息萬變的特征,與左翼作家的在想象中實施暴力的寫作方式存在著極大的差異。
與此同時,黑土地文化中的野性意識與胡子情結,更是他們藝術闡釋的書寫對象,例如蕭軍不僅在《側面》里渲染“我強壯”的剽悍人性,同時也在《第三代》中感嘆“女人也英雄”的民俗風情。
在《第三代》里,“女人”、“土匪”、“種”是詮釋尚武野性風俗的三個關鍵詞。就“女人”而言,凌河村的姑娘都喜歡好漢,而且她們自己就是英雄好漢,“能夠放槍也能夠殺人”,一旦被人侵犯就要勇敢反抗以命相拼,“我不管什么官員,什么人命……就是當今的皇帝……他如果侵害到我……我也要殺了他”;甚至勇悍得能當土匪,“有好些好樣的女人當胡子……騎馬打槍……自己報‘字’領幫頭比男人還干得兇!”不愧“英雄”、“好漢子”。她們都是“有刀一般斬斷力和蜂一般刺的女人”,具有應該生長在男人們身上的“最好的和最強硬的骨頭”,勇敢、堅強、剛毅是她們的總體性格特征。而“土匪”呢?像海交一樣,“作商人我又不愛財”,又因“一向是看不起那些王八似的無能的東西”而不愿做軍官,再就是因為沒地可種又受壓迫而不做農民,習慣于自由粗野,終于走向“作胡子”之路。他們“像天空的鷹一般地生活著”,“快樂、輕飄、蔑視任何東西”,自由不羈。他們不相信一切,只相信武力,“他們只相信手里的槍和腰里的子彈,只有和它們同在,在他們才有了生命,有了靈魂,有了膽量,有了一切”,只有這樣,他們才會覺得“自己全是合理而堅強地存在著了”,他們重視“勇敢和忠誠”。另外,他們講究綠林義氣,劫富濟貧,也絕不投降官軍而回來捉拿自己的伙伴,他們同心同德,有仇必報,“至死不投降!……至死要用這支槍替他報仇!”甚至“窮人要報仇……只有一條路——當胡子”。有仇不報非胡子。除了“女人”、“胡子”之外,《第三代》中的尚武野性風俗還體現在“種”的觀念上。或者是粗獷強硬的“種”:孩子“要像他那英雄的爹”,“真正凌河村的種子”有著“剛強的氣魄”。或者是勇于復仇的“種”:凌河村“連一個孩子也能放槍”,“他們兒孫是懂得仇恨的”,“若不給你一個報復,就不能算我爹的種子”。正是這種野性尚武的風俗與精神,才使得他們喜歡在太陽底下戰斗,而不喜歡貓頭鷹似的戰斗,才使得敢于反抗的老英雄井泉龍的笑聲成為“凌河村的靈魂”,也使得作者蕭軍也崇尚那種豪俠仗義剛烈頑強的精神氣魄,甚至敬佩土匪:“當胡子,我認為是好漢子干的,他們用自己的腦袋做本錢,所謂兩手換的買賣,堂堂正正地去搶奪,大大方方地來吃喝,痛痛快快地打死自己所不喜歡的人,這是多么豪俠的生活啊!”而這些正是東北民族的特色,也是東北民族自信自強的本錢。
而這種“尚武”崇拜與民族自強的狂熱情緒,一旦被置放于“救亡圖存”的時代背景之下,那么就形成了《八月的鄉村》等作品中那種剛烈無比的復仇心態。
例如蕭軍《八月的鄉村》中,“當過胡子”的抗日游擊隊隊長鐵鷹,“他殺起人向來是沒有溫情的……人們綽號全叫他鐵鷹,這是象征他的猛鷙和敏捷”,是個“勇武的英雄”。與此同時,他還是個“民族的英雄”。他率領戰士們浴血奮戰,使得戰士們“全要顯示自己是英勇的,沒有一點膽怯或憐憫來殺一個日本兵,更是殺日本軍官。他們鄙視這些東西,他們知道再無能也沒有。”他打仗“比任誰全英勇”,他是“一個英勇的隊長,一個守革命軍的紀律,和遵守革命軍命令的戰爭員”,他打仗是“有計劃的打”,“他懂得了怎樣思想;怎樣非撲滅了日本軍不可;怎樣把同志看成比自己的弟兄更親切;怎樣遵守和奉行革命軍的紀律”。他相信如果“不想作奴才,也不想被日本兵趕跑、殺死”,“要建設我們‘自己的政府’”,那么“一定要先把屠殺我們的日本兵,日本軍閥走狗們殺的一個不剩——一個不剩我們才能活著,我們子孫才能活著”。而農民出身又“當過兵”的陳柱司令更是一位英雄將軍,他要求革命戰士須有“鐵的紀律”,還要有“鐵的戰斗意志”,作“為勞苦大眾,為全世界弱小民族爭自由、爭平等的好漢”,這樣即使是死,也是“光榮的死在我們敵人的手里了!我們死是為了自己的志愿,為了替人民做革命的先鋒,為了自己的責任,為了目前新的世界,為了向壓迫、殺戮我們的同志,和殺戮我們姊妹弟兄的敵人復仇”。正是在陳柱司令和鐵鷹隊長這樣的民族英雄的帶領下,這支由農民、胡子、士兵組成的隊伍才具有了頑強的戰斗力和堅不可摧的復仇意志。
從以上幾部作品可知,野性被轉化成了民族性,胡子性格被演繹成了英雄人格,暴力敘事也因愛國主義的理想色彩,而理所當然地獲得了它藝術審美的合理價值。
三 文學研究會準左翼作家的暴力敘事
在20世紀30年代的準左翼作家中,沒有加入“左聯”的文學研究會作家如葉圣陶、王統照的暴力敘事與巴金、東北作家的暴力敘事相比,沒有巴金的無政府主義激情與俠士風范,也缺乏東北作家真實而野性的暴力書寫,當然也沒有左翼作家那種燃燒的革命激情與邏輯嚴密的革命理學,他們更多著一份文學研究會人生派作家的切實和穩重,不拔高人物的革命境界,也不肆意渲染暴力場景,他們的暴力敘事只是一種被控制得較好的人生敘事中的一個特征,是被其他各家暴力敘事所啟發的一個特征。
葉圣陶的《倪煥之》就將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和大革命(北伐)這一系列的暴力事件和思想事件串聯起來,展示主人公倪煥之從族的仇恨轉變為人的意識,再轉變為群的革命思想的心路歷程。茅盾就曾指出:“把一篇小說的時代安放在近十年的歷史過程中,不能不說這是第一部;而有意地要表示一個人——一個富有革命性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怎樣地受十年來時代的壯潮所激蕩,怎樣地從鄉村到都市,從埋頭教育到群眾運動,從自由主義到集團主義,這《倪煥之》也不能不說是第一部。在這兩點上,《倪煥之》是值得贊美的。”但是在這種人生探索的過程中,一直伴隨的卻是推崇暴力(革命)的思想。在辛亥革命的時候,那種革命的激情使倪煥之感到“仿佛有一股新鮮強烈的力量襲進身體,遍布到四肢百骸,急于要發散出來”,“一面旗子也好,一顆炸彈也好,一枝槍也好,不論什么,只要拿得到,他都愿意接到手就往前沖”。那種“種族的仇恨,平等的思想,早就燃燒著這個青年的心”。即使光復前后一切幾乎照舊,教育改革由強勢轉向弱勢,但在五四運動時他的演講仍不改暴力革命本色,認為“武人的升沉成敗里頭就交織著民族國家的命運”,號召國民應當有一種“民氣”,“采取直接的反抗行動”。而到了“五卅”運動時期,他更跳出教育救國的理想,指出“教育應該從革命出發”,接受了革命者王樂山的“要轉移社會,非得有組織地干去不可”的革命理想,與工人們一起游行示威,“齊握著仇恨的拳頭”,深深體會到“群眾的力量”與“反抗的必要”。在北伐期間,他與群眾一樣贊揚“為民眾”的革命隊伍,推崇勞工武裝斗爭,為這種偉大的“力的聲音”而如癡如醉。但是,大革命的失敗及隨之而來的白色恐怖,使得王樂山等革命青年紛紛被害,使倪煥之的革命勝利的幻想被炸得粉碎,雖然如此,他臨死前的暴力幻象仍沒消除他暴力革命的意志:
(王樂山)解開衣服似地拉開自己的胸膛,取出一顆心來,讓大家傳觀。大家看時,是鮮紅的活躍的一顆心;試把它敲一敲,卻比鋼鐵還要剛強。他又摘下自己的頭顱,滿不在乎地拋出去。接著他的動作更離奇了,他把自己的身體撕碎,分給每人一份……受領他的贈品的都感到贊嘆,像面對著圣靈。
很明顯,這種暴力幻象隱喻著將那種“比鋼鐵還要剛強”的敢于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精神流傳后世,象征著革命火種永遠不滅。正因如此,受其精神感染者才會像“面對著圣靈”一樣感服贊嘆。而當這種崇尚暴力的思想延續下去的時候,葉圣陶更在《英文教授》中把反對暴力抗爭的董無垢教授形容為一只“有垢”、“污垢”不堪的老鼠,這種對知識分子的貶損諷刺與蔣光慈的“精神自虐”(《咆哮了的土地》)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恰恰反證了葉圣陶暴力反抗思想的程度之深。
而王統照的《山雨》昭示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革命到來之必然。它首先揭示了農民活不下去的悲慘境況:預征錢糧,強派學款,天旱,土匪侵擾,討赤捐,出兵差,強迫筑路,過境的敗兵騷擾等等各種各樣接連不斷的災難,使得奚大有們“靠地吃飯”的幻想被打破,“無論怎樣,都成了地的奴隸!他得隨時交付無量次數的‘奴隸’的身價”。到后來,各種人為苦難更逼得奚大有徹底地“成了一個無產者”。這樣,要對付多如牛毛的苛捐雜稅徭役,要從“奴隸”變成“人”,勢必要“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使農民們走上各自的反抗道路。例如徐利,本就性情剛烈,是“陳家村中頂不服氣的一個漢子”,“就是不怕硬”,而且一身本領,渾身是膽,敢于與土匪作戰,敢于殺兵逃跑。這一切造就他“對困難的爭斗與強力反抗的性格”,后來被逼上梁山做土匪,火燒吳練長的房子,并下山報仇,是條敢于報仇的好漢子。而奚大有雖然比徐利馴順,具有農民的保守性,“老成保守的習性還沒完全去掉”,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壓迫使得“十六七歲時學過鄉下教師傳授的拳腳”的他逐漸爆發出原始的反抗性,當難以活下去時,他被杜烈的有錢有地有槍的是“吃人的老虎”的思想所啟蒙,被杜英所“引導”,更在兩天之內就被目光威嚴有力、態度鄭重明敏的“講主義”的祝先生所“征服”,于是從農民英雄好漢變成革命戰士,從農民的群體生活走向工人革命的集團生活,相信公道是要腳踏實地地爭取得來的,只有從原始的反抗轉向集團的反抗(革命),才能讓革命的大火燒遍全中國。
其他的準左翼作家的作品如魯彥的《野火》、《鄉下》,臺靜農的《建塔者》等,都從原來的鄉土寫實或人生寫實,走向暴力反抗,不能不發人深思。

注釋:
①馮雪峰:《回憶魯迅》,《魯迅回憶錄》(中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86頁。
②黎錦明:《黎錦明小說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96~297頁。
③巴金:《我的幼年》,《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3~1008頁。
④芾甘:《愛國主義與中國人到幸福的路》,《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542~543頁。
⑤芾甘:《怎樣建設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533~534頁。
⑥芾甘:《無政府主義與實際問題》,《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831~837頁。
⑦芾甘:《無政府主義與恐怖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742~749頁。
⑧巴金:《我的幼年》,《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7頁。
⑨芾甘:《無政府主義與恐怖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744~748頁。
⑩巴金:《愛情的三部曲·總序》,《巴金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44~45頁。
廣東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一般項目(2013WYXM0119),第53批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面上資助一等資助項目《“暴力啟蒙”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審美特征》(2013M530398)]
肇慶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