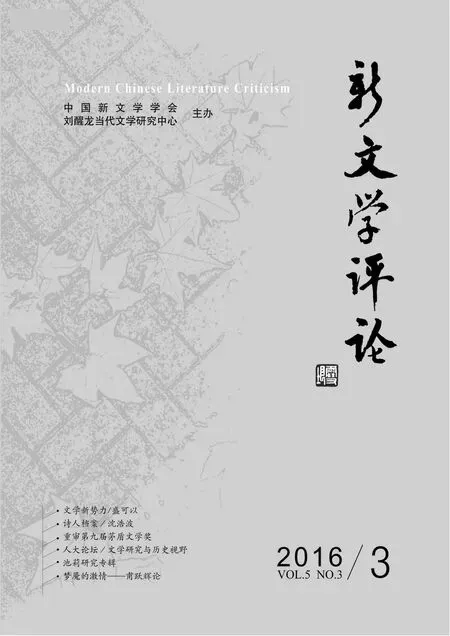時代回聲與生命感悟池莉小說創作論
◆ 陽 燕
?
時代回聲與生命感悟池莉小說創作論
◆ 陽 燕
從1978年發表第一首詩歌算起,池莉的文學創作迄今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而這個時間表恰好對應著中國改革開放,由傳統的政治主導型社會向市場化、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傳媒化轉型的歷史進程。作為一位對時代變革與生活變化有著敏銳觸覺的寫作者,池莉將其對于社會、歷史、文化、生活的觀察與思考訴諸文字,描摹了時代變化投射于日常生活的豐富側影,同時,與新時期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發展也保持了高度的契合。“現在的城市生活無時無刻不發生著急驟的變化,榮與辱、富與窮、相聚和別離、愛情和仇恨等等,皆可以在瞬間轉換,這是中國前所未有的歷史階段。希望與困惑并存,使人們的精神世界撞擊起了比物質世界更大的波瀾。我的小說,便在這波瀾中載沉載浮。”①池莉將時代的印轍與個體的生命感悟融匯一起,轉化成以市民為本位的文學書寫,以平民化的立場、仿真性的敘述、地域性的色調凝聚成極富世俗性與親和力的藝術個性,躋身1980年代末新寫實文學潮流的前列,并一直延續了強勁的創作勢頭,成為中國當代文壇頗具影響力與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追蹤時代步履且以普通市民生活為契入點的創作,既為池莉贏得了讀者的廣泛歡迎,獲得了市場的巨大成功,也因此備受質疑與爭議,使池莉小說及池莉現象擁有了更豐富多元的觀察角度與言說空間。
一
池莉的小說創作始于1980年代初期,《妙齡時光》、《鴿子》、《有土地,就會有足跡》、《月兒好》、《雨中的太陽》、《細腰》是她最早的一批“試筆之作”,表達對純真自由的愛情的渴望、對崇高理想與事業的追求、對真善美品質的守護,情感細膩、文筆雅致、風格清新。《月兒好》是池莉“第一篇引起國內注目的小說”②,描述了明月好經歷戀人悔婚、丈夫病亡、生活滄桑后依然保持人格尊嚴和精神高潔,并憑借其樂觀、堅韌、勤勞重新開拓生活之路的故事,使一個傳統的道德化的“棄婦”母題煥發了別致的新意。作者賦予主人公“被無情的歲月和故鄉的自然山水雕得如此美麗”的形象,用散文化的筆觸抒寫人物內心深處婉轉的情愫,用優美雋永的語言描繪襄河邊的風物人情,景物的明月和人物的明月相互映襯,營造出一種詩情畫意的審美意境。池莉早期的小說大多是一種“模仿性”的寫作,依據“前人的目光”看取生活,仿造“文學名著的創作成規、言說模式”進行寫作,情節簡單、人物純粹、主題明朗、富有理想化色彩與抒情性意味。初涉文壇的池莉難免單純輕淺,但她執著探索人生意義,側重發掘生活之美與人性之善,彰顯女性作者特有的敏感與細膩,為之后的文學之旅奠定了良好的開端。
行醫八年,池莉經歷了“赤裸裸的生與死,赤裸裸的人生痛苦”,其注意力日漸轉向“注重真實的人生過程本身”③。1987年,幾經退稿的《煩惱人生》在《上海文學》刊出,標志著池莉開始了“撕裂”過去、找到“自己”的創作新起點——作者從崇高、優美、詩意的文學慣例中走了出來,將視線轉向卑微平凡的小人物及其平淡瑣屑的世俗生活。《煩惱人生》以近乎攝像的方式“跟蹤”了普通產業工人印家厚24小時的行程,循著時間的變化和地點的轉換依次鋪敘了他一天中工作、生活及情感的流水賬,巨細無遺、單調瑣屑、煩冗沉重。這種極盡逼真的描述試圖還原生活的本來面目,展示其“毛茸茸”的質感,表現得富有彈性和張力,主人公的生存樣貌與心理狀態也把握得比較準確。作者將印家厚塑造為一個在理想與世俗、物質與精神之間搖擺游走的形象,他對工作與事業富有責任心、自豪感,對美好的情感也不乏憧憬和向往,但現實而具體的日常生活卻令其深陷其中,難以升華,無可逃避。如果說,《煩惱人生》涉及了面對理想失落時的些微掙扎,之后的《不談愛情》和《太陽出世》則將世俗性的日常生活完全書寫為普通市民生活的全部重心:前者從婚姻角度細致描述了知識分子莊建非和平民女子吉玲從戀愛到進入婚姻的種種糾葛,后者則逼真地記錄了趙勝天和李小蘭結婚、懷孕、生產、養育孩子的冗長瑣碎過程。池莉的“人生”三部曲為我們真實再現了一幅幅武漢市民凡庸平實的生活圖景:上班下班、擠車子、跑月票、工資獎金、柴米油鹽、住房緊張、氣候冷暖、雞毛蒜皮……“她不拔高、不放大、不矯飾,充分深入現實人生、日常生活及婚姻關系中的瑣屑、辛酸和艱辛。”④印家厚們的人生煩惱來源于物質困窘主導的日常生存的擠壓,其庸常困頓、沉重黯淡、毫無詩意的生活折射出了處身時代變遷漩渦中普通人群的敏感、不安與焦慮,成為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折點上“城與人”的一個縮影。
與“人生”三部曲類似的創作還有《一冬無雪》、《你是一條河》、《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綠水長流》,這些小說以普通人物為主角,以世俗生活為內容,采用生活流式的仿真敘事,語言質樸細致,以行文平實細瑣,契合了80年代末期新寫實主義的創作潮流。此外,池莉還以平民化的視角、世俗化的立場觀照歷史人物的命運起落,《預謀殺人》、《滴血晚霞》、《凝眸》追溯了歷史轍印中個人的生命遭際和心靈軌跡,揭示了歷史進程與個人生存之間的歧離與悖反。池莉將普通凡人的世俗人生推向前臺,重新確認了被傳統的宏大敘事忽視或遮蔽的個體存在,糾正了主流文學長久以來的高調話語、空疏風氣,這無疑具有特別的價值和意義,但同時,池莉對世俗生活的張揚又建立于顛覆、摒棄精神性價值體系的基礎之上,消解愛情的浪漫與詩意,拆穿理想主義的神圣和崇高,使其創作質樸有余、超越不足。
90年代中期之后,市場經濟全面鋪開,消費社會迅速形成,人們的生活和觀念出現了巨大變化,池莉的創作也發生了“戰略性轉移,正在由靜態人生素描轉為動態人生速寫。由社會結構內部關系的社會靜力學研究,轉為歷史過程、社會變遷等社會動力學研究”⑤。在此期間,池莉固然關注到了時代轉型中被動者、落伍者的猶疑、憤懣與抱怨,也描摹了金錢與實利的環境下堅持理想者的操守與寂寞,但她筆下的主人公已從活命順世的蕓蕓眾生轉向了不乏傳奇色彩的市井強者與時代弄潮兒。一個偶然的機會使孤苦伶仃的小丁從孤兒變成了百萬富翁(《化蛹為蝶》),本分勤謹頗有前途的機關職員王建國在外界的誘惑和刺激下終于下海經商(《午夜起舞》),陸武橋從一個當年的車間主任變身為餐館小老板(《你以為你是誰》),康偉業由一個肉聯廠工人成了叱咤商海的風云人物(《來來往往》),失業的來雙揚則一路打拼成了吉慶街上個體戶生意人的樣板與偶像(《生活秀》)。在經濟轉軌與市場競爭的新形勢下,陸武橋、康偉業、來雙揚,以及《口紅》中的趙耀根、《小姐你早》中的王自力、《水與火的纏綿》中的高勇、鄺園等,皆或被動或主動地離開了傳統體制,放棄固有的生活模式,他們不再延繼印家厚式的循規蹈矩、知足能忍、隨遇而安的生活態度,而是不滿現狀,拼搏進取,憑自己的遠見、膽識和能力開拓事業,以種種合法或不那么合法的手段致富。停薪留職、下海經商、個體戶、企業家、白領、商人、酒吧、飯店、歌廳成為池莉90年代小說中頻繁出現的新詞匯,在這些新詞匯構筑的新場景里,擺脫了生活重負與情感壓抑的“金錢英雄”康偉業們與宜欣、林珠、時雨蓬等更年輕、前衛的新人類一道,完成了池莉對于市場經濟時代金錢神話的書寫。同時,這些被稱為“都市傳奇”的小說的戲劇化故事模式、大眾化敘事風格、時尚化審美方式,也極大地契合了普通大眾的閱讀趣味,將池莉及其創作推向了暢銷書、影視改編等新的生產方式。
“體制與經濟的復雜變化,中國大陸男人這一群體經歷著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他們腐敗著,消亡著,或者成長著,成熟著。”⑥作如是觀察的池莉敘述了康偉業、趙耀根等人在商業競爭中不擇手段聚斂財富、在情感上拋棄妻子另結新歡的故事,既鋪排了金錢為之帶來的物欲膨脹和奢侈揮霍,也對其不負責、過分膨脹的欲望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諷刺和批判。盡管池莉力圖在“升騰與墜落之間”進行一種理性的折中的表達⑦,但總體而言,其創作更多的還是以不無欣賞的態度肯定物欲時代的世俗生活,賦予追逐金錢物欲者的行動無可辯駁的現實合理性。池莉以小說敘事進行著時代變遷中市民生活的現象式描述,但對變化所導致的精神應對、心靈反省卻涉及甚少,不乏倉促急就、流于表面的遺憾。
二
從初涉文壇的清新詩意,到新寫實時期的現實仿真,再到90年代中后期的“都市傳奇”,池莉敏銳捕捉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日新月異,并用獨特的視角反映變化中人們的現實生活,其創作呈現出了比較明顯的階段性特征⑧。從歷時角度觀察,池莉的小說創作的確發生了明顯的轉變甚至轉向,但池莉對個人創作一以貫之的東西尤其看重,她一再提醒讀者:“從我的主觀意識來說,我的文學立場和寫作視點,從八十年代到現在一直都沒有變化,只是進一步地在向縱深探索和發展……讀者感到的變化只是小說的取材、結構、語言之類的變化,都是技術變化,不是內核的改變。”⑨從池莉小說創作的整體來看,其所謂沒有改變的內核即是以市民形象和世俗生活為主導的寫作視點,以平民立場和世俗情懷為作品的普遍底色。
從“煩惱人生”三部曲開始,池莉即執著表現普通市民的生存狀態、命運浮沉、喜怒哀樂,從衣食住行、七情六欲、婚喪嫁娶、家長里短等普通人最日常而世俗的生活現象、生存狀態入手,觀照社會與生活的變化,并以此彰顯生活之真、人性之常。從印家厚、吉玲、李小蘭、趙勝天,到陸武橋、康偉業、趙耀根、來雙揚,這一系列人物及其故事構成了社會轉型背景下城市生活的演變與發展,彰顯了一個市民階層從萌芽、崛起到不斷壯大的過程。池莉筆下的人物形象盡管具有產業工人、公司職員、商人、小販、知識分子等不同的身份標識,但池莉大多從普通市民的角度去理解他們、詮釋他們,并讓他們帶著“市民”的文化與情感認同成為生活的主體、文學的主角,為市民文化爭取表征自身的話語權力。對于小市民這個概念及其指稱的特定群落與文化內涵,池莉自有一番客觀而清醒的認識:“自從封建社會消亡之后,中國便不再有貴族。貴族必須具備兩方面的條件:物質的和精神的。光是精神或者光是物質都不是真正的貴族。所以‘印家厚’是小市民,知識分子‘莊建非’也是小市民,我也是小市民。在如今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大家全是普通勞動者。我自稱為小市民,絲毫沒有自嘲的意思,更沒有自貶的意思。”⑩對市民具有高度情感認同的池莉非常認可世俗之于文藝的內在生命力,追求一種“大俗即大雅”的審美之境。因此,池莉宣言:“我希望我具備世俗的感受能力和世俗的眼光,還有世俗的語言,以便我與人們進行毫無障礙的交流,以便我找到一個比較好的觀察生命的視點。我尊重、喜歡和敬畏在人們身上正在發生的一切和正存在的一切。這一切皆是生命的掙扎與奮斗,它們看來是我熟悉的日常生活,是生老病死,但是它們的本質驚心動魄,引人共鳴和令人感動。”
池莉式的市民小說的出現,既是社會轉型期“放棄理想、疏離政治、肯定現世”的時代風潮影響的結果,也與池莉本人的思想觀念和生活際遇的變化相關,同時還與地域性的文化環境有密切關聯。對于武漢這座城市及生活于斯的市民,池莉懷有深厚的情感,正是透過武漢這個窗口,池莉觀察、探索并書寫下了時代變化及社會發展的脈動節律。池莉的創作多以武漢市民為人物原型,以武漢的世俗生活為書寫對象,以武漢的民俗風情為環境營造,建構起了一整套關于漢味文化的象征性符碼,成為湖北漢味文學的典范與代表。植根于武漢這片熟悉的土壤,池莉的小說涵蓋了數量豐富、元氣淋漓的漢味元素,包括武漢的地理風景(如長江大橋、水陸碼頭、吉慶街、漢正街、花樓街),美食特產(如涼面、熱干面、豆皮、糊米酒、鴨脖子、家常小菜),鄉情俗貌(如過江的輪渡、消夏的竹床陣),以及大量原汁原味、地道純正的方言俗俚,使小說真切細致、鮮活自然,富含生活的質感并充滿了濃郁的漢味氣息。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武漢是一個世俗化程度極高的城市,暴冷暴熱的氣候、艱窘惡劣的生存環境以及碼頭文化、商業文化的底蘊,共同滋養了武漢及其市民特有的民風脾性,展現為熱鬧喧囂、粗放世俗的文化氛圍,務實市儈、機智練達的處世準則,堅韌頑強、隱忍順應的人生哲學。池莉生動地刻畫了印家厚、陸武橋、吉玲、辣辣、來雙揚等市民能屈能伸、世故精明、潑辣幽默的性格特點,對武漢人將一切(包括愛情、婚姻)都看作“生意”的實用主義心態,及其蘊藏于內的粗野頑強的生命能量,都表現得十分到位。池莉的《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是漢味文學中堪稱標本式的作品,作者用極簡的筆墨、極短的篇幅鐫刻了一楨靈動鮮活且略帶喜劇色彩的武漢消夏圖,從酷熱無比的天氣到俏皮無聊的閑話,從家常的飲食起居到心理的彎彎繞繞,再點染以濃郁特色的方言俗語、民俗風情,舉重若輕地展現了武漢人充滿生之趣味的生存形式,刻畫了武漢市民樂感自在、充實坦然的文化性格。主人公燕華是一個典型的武漢姑娘,潑辣率真而又善良體貼,小說以其駕駛早班公汽“輕輕在竹床的走廊里穿行”作結,“她盡量不踩油門,讓車像人一樣悄悄走路”這個細節無疑是作者世俗情懷的外顯,為作品涂抹了一筆溫情脈脈的暖色調。
對池莉而言,市民小說既是題材意義上的概念,也關涉其特定的創作立場、價值趨向和審美趣味。在鮮明的平民立場和強烈的世俗情懷的驅動下,池莉拒絕提升、努力沉潛,對庸常困頓、毫無詩意的世俗生活報以認同、順應甚至贊美的態度,以一種平和溫馨的敘事口吻書寫日常現實,以溫情的目光檢視凡俗人生,以不無欣賞的態度肯定市民的道德人格,營構“活著就好”的“過日子”的生存哲學與達觀質樸的價值觀念。為了強化市民形象及其世俗化生活的真、美、善,池莉有意忽視對形而上精神層面的追尋與書寫,堅持以實用主義的市民價值觀念衡量世事人情,不惜用夸飾嘲諷的筆墨刻畫筆下并不太多的知識分子形象,如《你以為你是誰》中的李老師、《一去永不回》中的溫達功夫婦、《一夜盛開如玫魂》中的蘇素懷、《小姐你早》中的戚潤物等,皆自私軟弱、虛偽庸俗、冷漠固執、不近人情,與圓熟通透、怡然自若的市民形象構成鮮明對比。相反,《生活秀》中的來雙揚則呈現了另一番景象,雖然出身貧寒之家,卻在吉慶街上將生意做得紅紅火火,憑借其世俗生存中練就的本領智慧解決一個又一個的生活難題:放棄了背叛婚姻的丈夫,落實了來家老房子的產權歸屬,處理好了與父母和后母的關系,以務實態度對待與卓雄洲的愛情,交清了妹妹拖欠原單位的勞務費,照顧吸毒的弟弟與被父母忽略的侄子,將市井強者的人生傳奇推向極致。在池莉滿懷激情的筆墨浸潤下,來雙揚堅強自信、有情有義、光艷美麗、潑辣能干、游刃有余,堪稱市民生存哲學的完美典范,而對其性格行為中暴露出來的缺點與弱點,作者則多以“做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為堂皇借口給予寬容和諒解。顯然,過于強烈的世俗情懷與趣味影響了作者應有的理性判斷,對市民大眾的價值觀不加辨析地接受,對藏污納垢的市民生活情態缺乏必要距離的審視,難免淹沒了作者并不深入的思考,使池莉小說的內蘊變得單薄平淺。
三
以現實人生關懷為主調的湖北女性作家缺乏強烈、自覺的女性意識,她們的創作極少挑戰男權中心文化、解構男性中心話語,也極少專注女性的身體感受、內心欲望等隱秘體驗,而將女性的豐富性和微妙性融匯于社會生活之中。因此,筆者曾將湖北女性作家的創作稱為“準女性主義”的創作。作為湖北女性作家群中不可或缺的代表,池莉的小說尤其契合“準女性主義”的內涵。
創作伊始,池莉即對女性形象、女性故事、女性命運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妙齡時光》、《月兒好》、《細腰》、《青奴》等小說基本上都可歸結為“女人的故事”,主人公形象的刻畫也大都以溫柔、賢惠、善良、寬容等傳統美德為依歸。在《煩惱人生》等新寫實小說中,池莉同樣塑造了諸多女性形象,但“我們看到的卻是蕓蕓眾生中男人和女人共有的生存煩惱與艱辛,它并沒有因為性別的不同有什么本質的差別”。顯然,到1980年代末期,池莉以世俗人生為主旨的小說尚未觸及真正意義上的“性別”思考,她“關注的是普泛意義上的人而不是一種性別意義上的女人,她筆下的女性人物不是性別秩序的質疑者與挑戰者,僅僅是一種性別身份,而不具備價值判斷的意義”。即便如此,在有關現實人生、日常生活的觀察與書寫中,池莉已憑借其自身的善感、細膩、敏銳把握到了女性世界的兩個基本問題:其一是對愛情和婚姻的疑慮,其二是對女性獨立意識的崇揚,在池莉筆下,婚戀與女性這兩個關鍵詞更是非常深入地纏繞在一起。
《錦繡沙灘》可以視為池莉自覺將女性意識融入婚戀敘事的開端之作。主人公立雪有著敏感而纖細的內心,對愛情婚姻始終抱有浪漫的情懷與想象,而現實的婚姻生活卻令其深陷丈夫的隔膜與婆婆的非難之中,因而深刻體驗到“她的尊嚴她的價值在這個家里被粗俗地踐踏了”,女性的自我意識也由此萌生。冷漠的丈夫固然不可依靠,而原以為能夠寄托情感的趙如岳后來也暴露出了偽君子的真面目,在小說中,作者給立雪安排了一條“回歸”之路,以“孤軍奮戰”的方式去面對未來的人生長途。或者可以說,池莉的女性意識的覺醒是伴隨著小說人物對婚姻生活的體認得以逐漸完成的。《錦繡沙灘》之后,池莉筆下的女性形象越來越趨向成熟、理智、世故,她們開始自覺自愿地規避“無用”的愛情或“危險”的愛情,如《你是一條河》中的辣辣為嚴酷生活所迫不斷調整自己的性愛角色,卻始終拒斥無用書生小叔子的浪漫求愛;《綠水長流》中的女作家與邂逅的異性兩情相悅,甚至還有共處一室的偶然機緣,卻“寧愿留下一片美麗的缺憾”。池莉筆下對愛情持懷疑、拒絕、否定態度的女人們,已經不再將愛情婚姻視為自己畢生的“全部事業”,無論因講求生活實際而“不談愛情”,抑或因洞穿愛情的虛妄而“不談愛情”,這些主動放棄愛情的行動中已隱含了某種屬于女性主體的因子。
90年代中后期,隨著都市新傳奇的出現,池莉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更為豐滿細膩。開放的環境為女性發展提供了更闊大的平臺、寬廣的視野、多元的選擇,也為女性在社會生活中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保持人格與精神上的獨立自尊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來來往往》中的林珠一改池莉之前作品中常見的灰撲撲、粗拉拉的女性形象,而是一個明艷動人、聰明能干的白領麗人,她的出現使康偉業與段莉娜之間帶著計劃經濟時代印記的婚姻瀕臨危機,但池莉并沒有對第三者林珠作簡單化的道德審判,而以不無欣賞的筆墨刻畫了林珠投入愛時的真誠癡情與放棄愛時的果斷瀟灑,呈現了一個更有主見、更富理智、更能處變不驚游刃有余的女性形象。《云破處》和《小姐你早》是池莉女權色彩最濃郁的兩部作品,前者的最強音是曾美善以柔弱之軀憤怒殺夫的酷烈描述,后者的重心則是戚潤物與其他女性結成姐妹同盟懲罰背叛情感的丈夫的情節設計,小說尖銳呈現了“男性絕望”和“兩性對峙”的主題,主人公的女性意識也以強烈的夸張之姿和非理性的報復手段得到彰顯。
但《云破處》和《小姐你早》只是池莉女性意識覺醒的一次偶而為之的突進,池莉的大部分作品并不刻意將男女雙方置于強烈的性別對抗之中。事實上,池莉塑造的女性形象大都以溫和、圓潤、世故為底色,她們對自身性別意識的體認和表達并不偏執焦躁、撕裂沖撞,反而顯得沉靜自如、淡定從容,彰顯出一種母性的成熟氣度。正是憑借著這份生活歷練而就的成熟,梅瑩、辣辣、易明莉等母親或來雙揚等深具母性意識的女性才能看穿男性堅硬盔甲之下的軟弱,占據居高臨下的心理優勢,以沉默和距離來抗拒男性社會所主導的大眾情理與公共原則,以迂回和包容來抵御源自男性世界的圍困和侵蝕,既不自我否認,也不自我壓抑,祛除任何形式的依附以使自身獲得超越和自由。
池莉無意以孤立、懸空的方式描述女性,總是將女性生活融入更廣闊的社會發展與時代環境,描摹女性與社會、時代、歷史之間的緊密聯系。在《水與火的纏綿》和《所以》這兩部長篇小說中,作者以改革開放后中國近40年的歷史變遷為背景展現女性主人公的成長歷程及人生追求,曾芒芒和葉紫終于蛻變成長為能夠主宰自己命運的成熟女性,她們的對立物固然是一個個的男性、一段段的愛情與婚姻,但父母、兄妹、家庭以及整個的政治、社會環境都是她們大容量的人生舞臺,在池莉筆下,女性命運和社會歷史達到了比較深入的交融。池莉近作《她的城》雖然只是一個中篇,卻承載了作者非凡的野心,即如小說標題所提示的,池莉希望借此完成一部關于女性與城市、女性與時代、女性與生活、女性與女性之“真相”的書寫。小說以漢口最繁華的中山大道水塔街片區的一間擦鞋店為背景,塑造了店老板蜜姐、蜜姐的婆婆、擦鞋工逢春三個不同年齡、身份、性格的女性形象,既描述了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樂與酸甜苦辣,也敘寫了武漢這個城市的歷史淵源、前世今生及其氣質底蘊。小說以“敞的”這經典方言詞匯概括武漢的城市性格,三個女性主人公的性格氣質則與武漢這座城市相容相映、相互詮釋,即如蜜姐婆婆的寬容通透、蜜姐的精明灑脫、逢春的明亮快意。另一方面,小說將三個帶著各自歷史、經歷、命運、創傷的女性聚集一處,充分渲染了女性之間惺惺相惜、相濡以沫、溫暖默契的親情與友情。與《小姐你早》不同的是,《她的城》中的“姐妹情誼”并不以對抗男性權利為旨歸,而是遭遇生活劫難的女人們共同分擔精神痛苦、緩解心靈孤獨的庇護所,對男性不乏同情與理解,但女性之間卻獲得了更深層次的相互信賴與支持。
四
從新寫實到新傳奇,透過世俗生活、市民心態、城市形象、女性意識等不同角度的觀察與刻寫,池莉以小說的形式為1980年代以來這不斷變化的時代留下了鮮活的記憶,提供了某些證言。盡管得到的回應褒貶不一、毀譽參半,池莉的文學思考與藝術探索卻從未停止,在那些不乏商業氣息與市場印痕的小說里,已隱含了這樣的提問——當物質生活滿足后,精神困擾將以怎樣的方式呈現?伴隨著這樣的思索,進入新世紀之后,池莉的創作逐漸由都市的金錢傳奇回返到普通市民的生存,但此“回返”并非退回“人生”三部曲的原地,而是試圖超越物質擠壓下人生的黯淡與沉重,在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中發現詩意,重新建構對日常生活的審美觀照和精神價值。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將池莉2003年的《有了快感你就喊》看作其1987年《煩惱人生》的新篇章,但卞容大較之印家厚,已有了更豐富的性格內涵與不一樣的人生選擇。在《有了快感你就喊》這部小說中,池莉有意識地賦予主人公(卞容大)及其出生地(集賢巷)特別的文化意味,指示著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濡染之人、之地在市場化時代的變化。卞容大孤獨壓抑、內向敏感,同時也善良誠實、勤奮上進、富有責任感與事業心,以“積極的沉默”作為自己的生存之道與立身之本,但在父權桎梏、婚姻乏味、事業受挫等多重困境之下,普通職員卞容大早已喪失了陽剛之氣和生命活力。集賢巷中流行著錢財、器物、麻將、新衣,物化現象已經滲入了所有的血緣親情、人際關系之中,徒剩冷漠、猜忌和不信任,讓卞容大感覺自己“沒有親人”。然而,在生活中飽受辛酸掙扎之苦的卞容大并沒有就此沉淪,無論對勢利的父親還是難以溝通的妻子,卞容大都恪盡職責、忍讓寬諒,“男人”對卞容大而言不僅僅是性別意義上的概念,更是文化上、道德上的自我塑形。當卞容大因正義之舉遭受報復而下崗之后,他經歷了更痛苦的人生掙扎和更猛烈的心理沖撞,終于在一次應聘中決定“離開”和“遠行”。對于已經中年的卞容大來說,去西藏與其說是為優厚的工資待遇,不如說是“離開”和“遠行”所賦予的自我拯救的意義,卞容大終于為自己的人生打開了一扇窗,讓自己的人生有了些許詩意的光彩,真正體會到了“有了快感你就喊”的陽剛之意。在小說中,池莉直抒胸臆:“他是一個備受壓抑的窩囊的陽剛男人。可是他一直在堅持著什么, 一直在追求著什么,終于,他被迫開始了以逃離為形式的自我堅守與自我救贖。中國男人尤其需要這種精神,人性的、自由的、堅定的、革命的、悲壯的。”在各種訪談與自述中,池莉反復強調“有了快感你就喊”是一句充滿陽剛之氣的軍中格言,刊印于20世紀70年代美國大兵行囊里的火柴盒封面,這或許暗示著,在卞容大的故事里,作者試圖以西方的自由人性去修正完善中國傳統文化的理性原則與道德規范的企圖。
《托爾斯泰圍巾》則另辟蹊徑,崇揚了中國傳統儒道文化對庸常人生的詩意提升與發現。小說中,老扁擔和張華是兩個生活窮困、地位卑微的底層人,前者是進城的民工,后者是小區車棚的看守人,一個木訥寡言,一個爽朗樂天,池莉以這兩個形象詮釋了生活的意義和價值。老扁擔用七年如一日的堅持在小區收破爛,依靠自己的忍耐、敦厚、知好歹、懂感恩等“好品相”贏得了信任和臉面;張華中年喪夫、女兒癡肥、生活艱窘,但她從不自怨自艾,反倒古道熱腸,她精心照顧自己的女兒,也體恤他人、同情弱者、排解矛盾、主持公道,用善意、仁心和骨氣活得“自然、敞亮”。小說通過一個作家“我”來觀察、敘述老扁擔和張華的生活態度,“我”由此也得到精神凈化,感悟到“即便命運讓人窮困到某一田地,也可以做到孔子贊賞的境界: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
池莉的平民立場和世俗情懷讓她對知識分子抱有較深的懷疑和輕蔑,在其小說中,知識分子常是被貶抑的對象,精神生活和形而上的追求也常被作者給予漫畫式的夸張甚至無情嘲弄。池莉對知識分子不加分析地肆意諷刺也是導致其創作格局狹窄的原因之一,遭到了評論界諸多非議。然而,池莉的《看麥娘》是一個例外,或也是一個改變。《看麥娘》的敘述者“我”(即主人公易明莉)是國家一級藥劑師,擁有優越的社會地位、順遂的個人事業、閑適的生活環境,丈夫也積極進取、名利雙收。小說中,易明莉雖然并未遭遇普通市民日常的生活煩惱或底層市民難免的衣食之憂,卻被越來越強烈的焦慮感所籠罩,而焦慮根源于對人之生存意義的困惑與迷失。養女容容的突然失蹤使易明莉的焦慮更加放大,尋找容容的過程既是她感受現實環境欲望橫流、瘋狂混亂的過程,也是其逐漸清理生命內核、尋找生命真義和靈魂方向的過程。在易明莉的世界,無論是功利主義的丈夫于世杰,還是實用主義的養女容容,抑或母親、兄弟、上司、同事,都與其錯位疏離、相距遙遠,惟有看麥娘這種植物帶給她心靈安慰。看麥娘連接著易明莉記憶中相濡以沫的父女之情,記載著與上官瑞芳真摯恒久的友情,它指向澄澈、自由、明凈的精神境界,成為主人公超越困境、抵抗孤獨的心靈支柱。當質樸柔韌的植物看麥娘成為單純而充實的生存方式的總體象征時,小說對世俗生活的質疑批判已經讓位于對精神、價值、靈魂的尋找與求證,對池莉而言,這無疑是一次非常有價值的探索,讓我們看到了她立足世俗而又超越世俗的可能。
第四屆“大家·紅河文學獎”授予了池莉的《看麥娘》,認為“《看麥娘》雖屬寫實類作品,但池莉卻能寫出意外之境、意外之意來。表明作家從‘新’寫實走向了‘心’寫實。她不再只是世俗生活的記錄者和認同者,《看麥娘》是她創作的一次涅槃,也是小說精神的一次升騰”。對生命價值與存在意義的重新張揚,對詩意之美與藝術之真的重新開掘,使池莉的文學創作經過一個回環后進入了又一個新的通道,顯然,這是一種螺旋式的上升,讓人期待作者下一部更完美的升騰之作。
注釋:
①池莉:《說與讀者》,《池莉文集1》,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2頁。
②楊書案:《清水出芙蓉——我所認識的池莉》,《時代文學》1999年第2期。
③池莉:《創作,從生命中來》,《小說評論》2003年第1期。
④戴錦華:《池莉:神圣的煩惱人生》,《文學評論》1995年第6期。
⑤朱青:《生活的動感——池莉近作掃描》,《小說評論》1999年第4期。
⑥池莉:《讀我文章若受蘭儀》,《成為最接近天使的物質》,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273~274頁。
⑦於可訓:《在升騰與墜落之間——漫論池莉近作的人生模式》,《當代作家評論》1998年第1期。
⑧劉川鄂:《小市民 名作家:池莉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5頁。
⑨池莉:《〈懷念聲名狼藉的日子〉訪談錄》,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頁。
⑩池莉:《我坦率說》,《池莉文集4》,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23 頁。
湖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