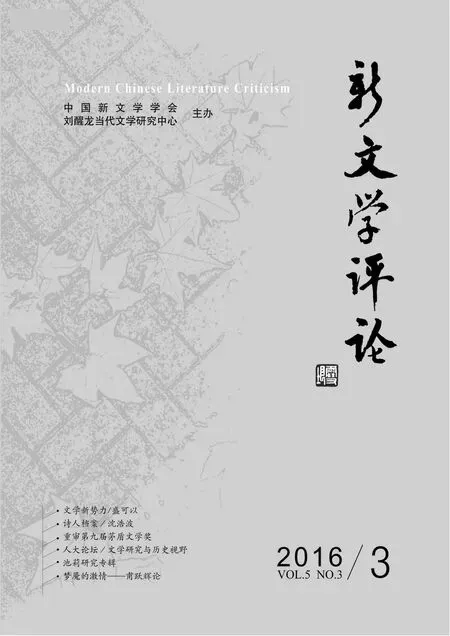無處安放的底層關懷
——解讀《生命冊》
◆ 石曉巖
?
無處安放的底層關懷
——解讀《生命冊》
◆ 石曉巖
2012年,河南作家李佩甫的長篇小說《生命冊》出版。該書與《羊的門》(1999)和《城的燈》(2003) 合稱平原三部曲,是“全面而系統地傳達出‘中原聲音’”的豫軍文學代表作。2015年,《生命冊》以濃郁的鄉土氣息和厚重的敘事風格獲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豫中平原這塊讓李佩甫魂牽夢縈的土地,是他的文學創作致力表現的地域,也是他的靈感源泉和精神家園。他以飽蘸情感的筆描摹豫中平原的人事風物,行文厚重細膩,感情深摯真切。以植物喻人,書寫土地與人的關系,是他習慣的寫作風格。他說:“我的寫作方向一直著力于‘人與土地’的對話,或者說是寫‘土壤與植物’的關系。我是把人當作‘植物’來寫的。”①如果說《羊的門》寫的是平原鄉村上“敗中求生、小中求活”的草,以草喻人,以豫中平原的土壤與本土植物的生長狀況及關系隱喻綿羊地上如羔羊般艱辛生存的人們;《城的燈》是將城作為平原鄉村的參照,寫在漫長苦難的歲月里忍辱偷生的農村娃受城里光的誘惑而逃離土地擠進城市的故事;那么《生命冊》則是以平原上的樹的生長狀態及背景暗喻無梁村人的命運。小說以第一人稱“我”敘事,講述主人公吳志鵬五十四年的人生經歷與感悟,同時也是一個已經從鄉村移栽進城市的知識分子對鄉村的回望與反思。
一、土地與人:沉重土地上的艱辛生存
“聚焦中原,思考中原”是李佩甫小說一貫的主題。前后創作歷時十余年的平原三部曲在人物和情節上并非連貫,但地域是一致的——一馬平川的豫中平原上的村莊(呼家堡、上梁村或無梁村)。《羊的門》介紹這是一塊歷史上飽受戰亂、饑荒、天災摧殘的綿羊地,一塊有氣無骨的平原。小蟲窩蛋、狗狗秧、敗節草、灰灰菜等是平原上最常見的草,它們“從沒指責過任何人”,“默默地讓你踩”。和草一樣渺小卑賤的,是處于底層的草民,平原人因為沒有山水的依托而立不住。《城的燈》里的土地“給人糧食”、“給人住”、“給人踐踏”,包容忍耐卻緘默不語。土地因年復一年的奉獻而貧瘠,村民們卻想盡一切辦法逃離土地,逃向有光的城去。平原上的人們與土地上的動物和植物一樣受,吃苦和忍住是生存的秘訣。——受是苦,是一年四季寒來暑往中無始無終的辛勤勞作。受也是活,是把土地扛在肩上行走的勇氣與擔當。
在《生命冊》里,李佩甫再次書寫瘠薄酷烈的自然環境里的土地與人。作者說:“無梁的風是很染人的。風無處不在。……無論春夏秋冬,就是不刮風的日子,也有風的神跡。”②“在無梁,沒有一片樹葉是干凈的。那是風的緣故。……風對樹的侵害是無聲的,它很少有刮倒樹的時候。但它常年一次又一次地去侵襲、撫摸你的半邊臉,那結果又會怎樣呢?”③因此盡管一馬平川四季分明雨水豐沛,無骨的平原上的無梁村正如它的名字一樣,“不長棟梁之才”。和樹相對應的是人。他們善良又惡毒,堅韌又愚昧,忠厚又狡黠,豪爽又奴性,隱忍又麻木,淳樸又善妒,機智又鉆營,仗義又勢利,這些看似相悖的品質奇妙地雜糅共生在每一個平原人的身上。小說里吳志鵬、駱駝、老姑父、梁五方、蟲嫂、杜秋月、春才等人物個性鮮明,命運令人唏噓,每一個人都掙扎著奔向夢想,最終卻宿命般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吳志鵬是吃百家奶長大的孤兒,也是饑餓年代“吃遍全村的蝗蟲”。“吃百家奶”意味著“我”“身后有人”,進城后也要背負著整個無梁村的土地和村人。“吃遍全村”意味著“我”讀大學可能并非因為個人的優秀而是現實的荒誕。村里人急切地督促老姑父去求人幫“我”爭取大學招生指標,與其說出于善意,不如說是期待甩掉累贅后的解放。而進城后到大學任教的“我”因不堪來自無梁村的接二連三的為村人辦事的“指示性字條”的重負而辭職經商,幾經商海浮沉看似功成名就卻最終幻滅。小說的結尾,“我”發現自己“幾乎找不到回村的路”了,“我”像“一片干了的、四處漂泊的樹葉”,可能永遠無法回到樹上了。打了十六年仗的老姑父本來是上尉軍官仕途光明,為了一見鐘情的愛情轉業復員成了農民,而脆弱的愛情迅速在每況愈下的貧窮生活和勢利村民的蔑視嘲弄中灰飛煙滅,剩下的就是老姑父與吳玉花夫妻之間仇人般曠日持久的戰爭——那是“以命相抵的搏斗”,無梁村的歲月抹去了老姑父全部的軍人特質。傲造的能工巧匠梁五方靠龍麒麟贏得了村人的敬慕和一個好媳婦,歷時兩年以一己之力在墊起的水坑上建了三間新瓦房。也因自己的驕傲、逞能和倔強得罪了村人,在批斗會上被推來搡去地過籮而遍體鱗傷。新房和家產被充公的梁五方趕走妻子后開始了漫長的上訪路,他的意氣風發在上訪的途中一點點磨損。小蟲窩蛋一樣的蟲嫂,為了在饑荒年代不讓三個孩子挨餓而偷,在村民“三只手”和“松褲腰”的恥笑中和日后在縣城甘當“細菌人”收破爛的艱辛中含垢忍辱,三個孩子進了城上了學安了家卻并不感恩娘,蟲嫂的死讓無梁村人憤怒,而三個孩子聽說蟲嫂留下了三萬塊的存折才搶著回來行孝。下放的知識分子杜秋月斯文老實,在無梁村日復一日挑尿、請罪的歲月里變得粗糙,也學會了民間的狡黠,他跑平反,甚至陰謀離婚,最終在與老婆劉玉翠的斗爭中敗下陣來,成了病人和廢物。而靦腆俊美的無梁村最巧的手藝人春才,在青春期的萌動和恥的罪感里閹割了自己,在晚年依然以“不摻假”的誠實悲壯地堅守在豆腐坊,是一個“很有骨氣的失敗者”。
在庸常惡劣的生存環境里,平原上的人善忍,也韌。無梁村的能人們始終在與命運堅忍頑強地搏斗,就像平原上長年的、持久的、命對命的、“樹與風的搏斗”。樹被風侵襲得“沒有一片干凈的葉子”,人在與生活的搏斗中變得“有氣無骨”。而忍和韌也是雙刃劍,平原上的樹可謂種類繁多——榆、桑、槐、楝、桐、椿、柳、桃……但它們一個可怕的共性是“離開土地之后”會“變形”④。樹的變形隱喻著人性的扭曲。吳志鵬、老姑父、梁五方、春才們在歲月的熬煎中變了形,寧彎不折,靠著忍和韌沒有折斷,卻缺乏振奮人心的精神力量。或許是出于對豫中平原的深沉情感和現實關聯,李佩甫沉迷于鄉村苦難經驗的書寫和中原文化根性的挖掘,卻未能以更廣闊的精神視野做出文化的批判和靈魂的審視,這是《生命冊》的一個遺憾。艱辛人生可能使人沉淪迷茫頹廢忍辱偷生,也可能使人振奮執著堅定愈挫愈勇。苦難可能使人絕望,但反抗絕望才能體現人性的高貴和尊嚴。人在苦難中成長壯大,依靠理想和信仰實現心靈的超越和靈魂的升華,書寫苦難只是過程而不應是終點。
二、愛恨交織的城市與鄉村烏托邦
從《羊的門》、《城的燈》到《生命冊》,平原三部曲呈現著城鄉社會的二元對立的敘事結構。作家顯然是偏愛鄉村的,小說主人公雖然懷著對現代化的向往奮不顧身地沖向城市,卻又以鄉村視角道德化地審判城市的物欲之惡。一方面,城市是富足光明的所在,是現代化的象征,是物質和精神的雙重高地。另一方面,城市又是冷漠、貪婪、欲望、淫蕩、罪惡的化身,是紙醉金迷萬劫不復的深淵。
《生命冊》的主人公吳志鵬就是以一種愛恨交加的復雜心情走進城市,他是“一匹企圖披上‘羊皮’的狼”,心里藏著狼性,卻在城里走出羊的姿態⑤,將在與城市欲拒還迎的搏斗中成長。初進城市時他盼望早日住上城里的樓房,有盞“屬于自己的燈”,娶個“美麗的城市女人”,“成為一個著名的學者”,就此實現人生價值。但問題是若吳志鵬們進城的全部目標僅僅是金錢、美色和權力,便只能放大城市的罪惡與欲望,不會使城變好,只能使城更壞。當以吳志鵬、駱駝為代表的知識分子以一種闖入者的姿態占領和入侵城市時,只能是城的異己者,很難與城和諧相處,更難真心實意地感恩、愛護、建設城,他們咬牙切齒地征服了城的同時,其實也喪失了知識分子的主體性。作為接受現代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本來應該成為溝通鄉村與城市的媒介物,搭建城鄉對話的平臺,對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關系做出理性分析和判斷,思考鄉間傳統的現代轉換,而吳志鵬、駱駝們顯然沒有完成這一使命,他們的行動不是縮小而是擴大了城鄉之間的裂隙。
吳志鵬這個“強行嵌進城市里的柳木楔子”,立志在城市的水泥地上“長成一棵樹”,只因為家鄉父老等著他“植下蔭涼”⑥,這個志向實在稱不上高遠。當羊一樣的點頭和微笑并非發自內心而是狼的偽裝和做戲時,當吃得苦中苦最終只為成為人上人時,吳志鵬、駱駝們在城市扎根之后必然要以掠奪的姿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乃至家鄉利益的最大化,“身后有人”對吳志鵬來說既是負擔更是依靠,而駱駝“必是拿下”的口頭禪體現出怎樣的得意與張揚。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早年經歷的貧賤與屈辱又怎能不化作“寒氣和毒意”在城市上空彌漫。聰明而有決斷的駱駝,在貪婪和欲望的驅動下鋌而走險,為了追逐金錢一次次沖破底線甚至不惜以拉他人下水的方式完成資本積累。駱駝最終跳樓自盡,消失在害人又害己的金錢陷阱中。當一心發財的駱駝居高臨下地稱藥廠工人為下人并毫無同情心地表示“只有下人才抱怨生活”時,這種“寒氣和毒意”再次浮現——未必是城教壞了他,更可能是他弄壞了城。相對來說,吳志鵬比駱駝有節制,在逾越底線時有反思。在駱駝自殺自己遭遇車禍時,他感嘆“上蒼賜予我們一雙眼睛,本是看路的。可我們的眼都出了問題”。一個真正的土地背負者背負的不僅是農村的土地,也包括城的土地。站在道德制高點對城市進行貶城譽鄉的道德審判,以此掩飾個體在不擇手段追逐金錢過程中的迷失與墮落,有辱土地背負者的使命與責任。
在吳志鵬和駱駝們享受著城的繁榮與現代、聲討著城的冷酷與罪惡的同時,還虛構了一個鄉村烏托邦,賦予它道德意義審美意義而非經濟意義上的美好想象。在吳志鵬們一次次懷舊式的深情回望中鄉村被罩上溫情脈脈的光環——“牛毛細雨”和“瓦沿兒的滴水”、“夜半的狗咬聲”和夜色里的“咳嗽聲”,“蛐蛐的叫聲”和“倒沫的老牛”,“靜靜的場院”和月亮下的“谷草垛”,“黃泥墻上的木橛兒”和“四條木腿兒的小凳”,“甚至于懷念家鄉那種有風的日子”……但這僅止于想象,無法落地還原成現實生活,畢竟貧窮不是美德,落后不是浪漫,狡黠不是智慧,麻木不是淳樸。當《羊的門》里的呼國慶、《城的燈》里的馮家昌、《生命冊》里的吳志鵬、駱駝們前仆后繼義無反顧地離開鄉村奔赴城市的時候,其實早已做好“再也回不去了”的準備了,甚至可能還有一點點驕傲地想著“再也不回去了”。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他們在城市遭遇的現代化照亮了記憶中鄉村的傳統,正是他們在城市居住的鋼筋水泥森林,喚起了對鄉村天然與綠色的留戀,正是城市的快節奏,勾起了他們對鄉村慢生活的懷念。
然而鄉村烏托邦的建構卻是對當今農村真實生活的逃避。毋庸置疑,1990年代以來的中國城鄉社會發生著巨大變遷,城鄉矛盾是當下中國面臨的嚴峻問題。一個殘酷的事實是,城市化日益加快的進程造成了鄉村的凋敝,中國的經濟騰飛伴隨著社會城鄉結構內部的裂變與重組。當市場化和全球化合謀瓦解傳統的鄉村社會時,農民們正經歷著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的雙重擠壓。在一定程度上,現代中國社會城市化的進程是以剝削鄉村為代價的,農村的勞動力資源和土地資源正源源不斷地流向工業、服務業和房地產業,農民外出打工與種糧收益的剪刀差在擴大而非縮小,由此衍生的三農問題、農民工問題、農村婦女問題、留守兒童與老人問題及環境保護問題等等都亟需關注。而吳志鵬們回避了這些問題,以文人的感傷而非知識分子的理性營造了想象中的鄉村烏托邦,試圖讓個體漂泊的靈魂在此休憩。《生命冊》也回避了這些問題,雖然小說的背景主要發生在1990年代以及新世紀,故事的講述卻停留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傳統鄉村的描述和改革開放初期問題的揭露,沒能將當前中國鄉村的現實問題納入作者的視野,這影響了小說鄉土敘事的深度與廣度,作家的底層關懷也因懸空而無處安放。當代文學貴在當下性,應執著于中國經驗和時代經驗的表達,應對當下社會現實保持敏感關注和理性分析。在一個崛起中國的大時代里的鄉土敘事,為城或鄉做二元對立的價值判斷顯得簡單粗暴。現代化也許不那么好,但我們注定在奔向現代化的道路上一去不返,無處可逃。《生命冊》對民間底層的深情厚意得益于作家的生活積累,但要真正實現弱者之護和底層關懷還需更強的精神力度和更深的理性思考。
三、 權錢崇拜的侵蝕與現代人格的缺失
在《羊的門》和《城的燈》里,李佩甫書寫鄉村社會權力場生態可謂駕輕就熟,對治人術、攻心術、權術和培植人脈官場哲學的描寫引人注目。《生命冊》沿襲了這一風格,用濃墨重彩書寫攻心術、商海潛規則,并以此反思中原文化中固有的官本位、錢本位意識,批判中原文化的惰性、奴性和保守性。
無梁村的權力崇拜是中原文化中官本位意識的一個縮影。“在無梁,凡是有職務的,只要給一個理由,人們就信。”⑦老姑父與吳玉花婚后無休止的吵架的起因是吳玉花接受不了軍官結婚后成了農民。而當老姑父當上村支書后,過街時“女人們的笑臉像葵花一樣處處開放”。吳志鵬研究生畢業留在省城,無梁村的村民不斷要求他為村人辦各種事,理由是“你是省里大干部”,“你一個電話,事不就辦了?”而無能為力的吳志鵬懷著愧疚的心情想的居然是:“我怎么不是省長呢?我要是省長,全都給他們辦了。我很想腐敗,可我沒有腐敗的條件哪!”⑧和權力崇拜伴生的是金錢崇拜。當初“我”上大學的指標是“用全村人的油,還有煙酒和老姑父的臉面換來的”⑨。“我”留城后三嬸托我辦事時交代“該花錢花錢,該送禮送禮”。杜秋月跑平反,村里人教育他:“你以為平反就那么容易?你得送啊!……送禮呀!你不送,誰給你平呢?”⑩村里人甚至一家一家給他湊柿餅、核桃、雞蛋和油作為禮品,因為“老杜要是平了反,就成了官身了”。而在駱駝眼里,金錢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利器。以超低價格收購鈞州制藥廠談不下來,駱駝嚷:“哪里不通,你給我砸,砸死他!那姓尤的,廠長,叫財務上給他送去一百萬。看他怎么說?”厚樸堂藥業公司改制上市的報告得不到政府批復,駱駝嗷嗷叫:“砸,砸死,要不惜代價!”面對清廉端方的副省長范家福和心高氣傲的夏小羽,駱駝用了攻心術,瞄準人的弱點發力,錢還是重要的工具——送給前者花一萬美金往返美國買的一粒袖扣,送給后者購買愛情別墅的一千萬資金,終于使改制上市的事情成了。
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中原大地上的權錢崇拜不僅是中原文化中負面因素畸形發展的結果,也有歷史的現實的多重淵源。中原大地經濟文化落后,天災人禍不斷,戰亂饑荒連綿,物質資源相對匱乏。在鄉村強權壓制下的村民由恐懼權力而崇拜、依附、甚至獻媚權力,是因為權力不僅能帶來物質上的富足、精神上的臉面,還能擺脫仰人鼻息的屈辱,獲得居高臨下的成就感。另一個能把人逼到死角的是錢,錢“成了尊嚴的象征”。吳志鵬和駱駝拼命想擺脫窮氣。吳志鵬喊出“錢爺爺,錢奶奶,錢祖宗”,把錢看作人生目標而辭職下海,駱駝則高叫:“錢!我現在就信一個字:錢!”《生命冊》開篇寫道:“這個世界上人跟人是不一樣的”,“每個人都是有背景的”。越有受過強權壓制和貧窮熬煎的生活背景,越知道權力和金錢的重要,也就越會絞盡腦汁地追求升官發財。
權錢崇拜也侵蝕了現代人格。在特定時刻,人性中的卑賤、懦弱、奴性和勢利被激發,愛情與婚姻摻雜了名利場中功利的算計,女性則被物化和矮化。老姑父為了愛情放棄了上尉連長的前程,卻得不到包括妻子在內任何人的理解——“老姑父自摘下肩章上的那三顆‘銀豆兒’之后就什么也不是了。他在無梁村的生活每況愈下,時常遭到站在石磙上碾篾子的女人們的蔑視和戲弄”。無梁村最聰明的匠人梁五方在被劃為新富農家產充公之后,踏上了三十三年的上訪路,在對“依靠政府”為自己平反的執著中誤了一生。堅持誠信經營的豆腐店春才斗不過賣假貨發財的豆腐大王,雖有骨氣卻是人們眼中的失敗者。吳志鵬認定窮是橫在他和梅村愛情之間無法跨越的鴻溝,認定一定要先有錢才能談愛,他從未想過有錢未必等于有愛,他的遠去是梅村后來的一連串厄運的開始。小喬對駱駝并無真愛,一切都出于錢的考量,愛情的虛無伴隨的是物欲的追逐。靠“賣自己”攢下第一桶金的蔡葦香有了錢后返鄉,引來了村里人又嫉又羨的目光,明知她的錢掙得不光彩,卻默許了村里的六個姑娘隨她而去。在小說結尾,蔡葦香搖身一變成了蔡總,并改了名叫蔡思凡,財大氣粗地給老姑父遷墳為自己正名。
《生命冊》中有對中原文化負面因素的批判,也有對鄉土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各種問題的反思,但作家在進行文化批判時顯得猶疑與徘徊。例如,作家對駱駝不擇手段的發家史同情多于批判:“我們每人心中都藏著一個‘駱駝’,都渴望或曾經渴望成為‘駱駝’。”“貧窮對人的戕害遠遠大于金錢對人的腐蝕。”小說描寫攻心術、潛規則、借殼上市的方式、釣女人的法寶、梁五方過籮、蟲嫂受辱、小喬色誘等情節細致入微,固然揭露了社會現實,卻更迎合了市場需求,滿足了讀者獵奇和窺視的心理,在批判現實的名義下將小說引向了黑幕小說的趣味和暴力情愛的奇觀化敘事,淡化了文學作品最重要的精神高度和人文關懷。讓人遺憾的還有小說中對女性的物化和矮化。在鄉村,蟲嫂雖然“割草割麥都是一把好手”,但要讓丈夫和孩子吃飽還是得靠松褲帶的“解放”。在城市,鄉下姑娘蔡葦香想出人頭地,同樣是從出賣身體做起,不論她怎樣潑辣聰明能吃苦。從吳志鵬的戀人梅村,到駱駝的妻子衛麗麗和情人小喬,再到副省長的女友夏小羽,都是依附于男人的存在,沒有自尊自立自愛的人生。她們無一不聰慧美麗,但卻是男性標榜自身成功與魅力的“物”,甚至與金錢權力相捆綁甘愿犧牲自我成為男性進階的工具。這些都使《生命冊》雖有志于“追溯時代與生命的艱難蛻變”,卻很難達到“土地背負者心靈史詩”的高度。

注釋:
①孔會俠:《以文字敲鐘的人——李佩甫訪談錄》,《創作與評論》2012年第8期,第70頁。
②李佩甫:《生命冊》,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51~52頁。
③李佩甫:《生命冊》,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頁。
④李佩甫:《生命冊》,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頁。
⑤李佩甫:《生命冊》,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8頁。
⑥李佩甫:《生命冊》,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 2頁。
⑦李佩甫:《生命冊》,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第55頁。
⑧李佩甫:《生命冊》,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第17~18頁。
⑨李佩甫:《生命冊》,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第57頁。
⑩李佩甫:《生命冊》,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第303頁。
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